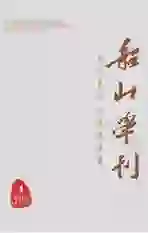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
2017-08-10林玉均
林玉均
摘 要: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关键词:王夫之;论语;解释;朱子;读《四书大全说》;药病说
一、引言
作为解析王夫之经学的第一步,笔者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做了他对《四书》的解释等一系列研究。到目前为止,已考察了王夫之对《大学》和《中庸》的解释。接下来,本文将考察王夫之对《论语》的解释。本文通过其与朱子解释的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要在一篇论文里考察王夫之《论语》解释的全部内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本文以《学而》篇至《雍也》篇的内容为中心考察王夫之的《论语》解释,其余部分将通过今后一系列的研究进行考察。
二、《论语》读法
朱子立足于道统说,认为儒学之道经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子,再传到孔子的弟子曾子、子思、孟子,孟子死后道统就断绝了。所以根据道统说,比起六经,他更重视孔子的《论语》、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孟子的《孟子》。朱子说孔子是圣人,子思、孟子是贤人,将二者加以区分。但是对于记录他们言行的《四书》,却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价值上的优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比如他把《大学》比喻为器具,把《论语》和《孟子》比喻为盛在器具里的食物①;他说“论语只说仁,中庸只说智”②,又说:“读论语,如无孟子,读前一段,如无后一段。”③在这些话里,都可以确认到这一点。
王夫之也承认孔子是圣人,认为《论语》是最能反映圣人言语和见解的书。
圣人之语,自如元气流行,人得之以为人,物得之以为物,性命各正,而栽者自培,倾者自覆。④
“人得之以为人”“物得之以为物”都是源于圣人之语。王夫之说,孔子的“气象如天地”⑤,是一个“全体天德”的人。⑥因此,王夫之明确把孔子与其他学者区分开来。他认为,就连与孔子并称为“孔孟”的孟子,也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在王夫之看来,只有孔子才是圣人。这一点可以从王夫之所说的“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⑦中得到确认。所以他认为,即便是同属《四书》,《论语》的水平也不同于《大学》《中庸》《孟子》,要用别的方法去读。⑧王夫之说,《论语》是“圣人彻上彻下语”⑨。那么,何谓“彻上彻下”?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
虽然不犯上、不作乱是乡党守法安分的“浅事”,但其中也包含着深奥的道理。⑩王夫之解释,周文王虽势力强大却服事殷国,或者周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避免犯上和作乱。B11这是“极乎下以通上”B12。
“孝弟为为仁之本,极乎上而大言之,而小者亦在其中。”B13例如,施恩于亲戚和朋友,与乡党和睦相处,“而仁及人”;到了春天,不杀死任何一只从冬眠中醒来的昆虫,不折断任何一个正在成长的树木,“而仁及物”,这些都是从仁道中产生的。B14王夫之认为,这是“极乎上以通下”。B15这种“极乎下以通上”和“极乎上以通下”正是所谓的“彻上彻下”。
再举一个例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王夫之在解释上文时强调,这一内容不仅适用于初学者,还适用于圣人。正如初学者“时习”则“说”,“朋来”则“乐”, “不愠”则为君子,圣人同样也是“时习”则“说”,“朋来”则“乐”, “不愠”则为君子。B16因此,为学之人只要一天用力于学,就会进入深奥的道理之中,相反即使学习得再久,也不能完全实现孔子所说的意义B17。王夫之将它比喻为覆万物之天和载万物之地。B18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出王夫之多么重视和高度评价《论语》。相反,他批判“异端”如挂羊头卖狗肉一般虚伪。B19
对此,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学而时习之”的“之”指称的是什么?有一天,一个僧人向几个儒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上来。B20王夫之说,“之”指“所习者”B21,从儒学者的立场来看,可以回答:“之”指称“天德王道、理一分殊、大而发育峻极、小而三千三百”等等。B22就是说,“之”并不是具体地指称某一件事情,而是统称“古今学者之全事”B23。他主张,《雍也》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的“之”指称的也不是某一件事情,而是“广大该括,则又遇方成圭,遇圆成璧”B24的一般对象。《论语》中泛泛下一“之”字的例句也都是这样的。B25王夫之批判,尽管如此,还要把“之”确定在某一个对象上的话,那就是“舍康庄而入荆棘”。B26
因此,王夫之向读《论语》的人们提出的要求是,不要把《论语》局限在那个时代去理解,而是要超越时代和地域,普遍适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在这种意义上,王夫之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的正是被他称之为“药病说”的《论语》读法。所谓“药病”,就是对症下药,就像对某种病症使用某种药物一样。孔子在《论语》中对弟子和其他人所说的话都是为了纠正他们的某种病痛而说的,这种解释就是药病说。
三、对药病说的否定
王夫之的所谓“药病说”正如上面所说的,就是认为《论语》中孔子的话是为了纠正包括孔子弟子在內的某个人的病痛而说的。举一个例子: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对此,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引用了范祖禹的话。范祖禹解释:“子贡之患,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故告之以此。”B27而《朱子语类》中朱子也对此这样解释:“只为子贡多言,故告之如此。”B28朱子和范祖禹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是说,孔子的话是为纠正子贡的病痛而说的。
对此,王夫之则批判说:“非言之艰而行之艰”是人们的通病,并非子贡一个人的病痛B29,不能像范祖禹的解释那样,认为孔子的话是为纠正子贡的病痛而说的。B30而且王夫之认为,类似范祖禹的这种解释是源于对子贡的误解。通常学者们根据《孟子》中子贡“善为说辞”的句子B31,认为子贡善于言辞,而“善为辞命”和“善为说辞”是完全不同的层次。结果王夫之认为,说子贡“以言语著”是没有根据的,子贡只是善于交际而已。B32
反而,王夫之考虑到孔子门下如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皆有论著,而惟独子贡没有,而且对孔子之道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B33等等,认为子贡是一个非常慎重且不“轻置一词”的人。那么就没有像子贡那样寡言的人了。王夫之主张:这样看来,不但不能说子贡有某种病痛,而且不能说孔子看出他的病痛,使用了适合其病痛的药。B34
先行后言,自是彻上彻下、入德作圣之极功,彻始彻终、立教修道之大业,岂仅以疗一人之病哉?B35
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语括圣功之始末,斯言也,固统天、资始之文章也,而仅以药子贡之病耶?B36
根据以上引文,王夫之主张,孔子所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不是为纠正子贡的病痛,而是为引导人们彻上彻下而成为圣人。换句话说,是一句不受时代和地域限制,能被所有人接受的普适的话。
王夫之的批判,后代的学者说因为与孔子交谈的弟子们都有这样那样的病痛,所以孔子为他们下了这样那样的药方,就连对这些病痛的见解本身也是错误的。如: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對此,朱子解释:“樊迟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B37朱子的这种解释,按照王夫之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适用药病说的解释。然而,王夫之却认为朱子对樊迟的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虽然后代学者们以为樊迟有“粗鄙近利”的病痛,但是王夫之下的诊断是:“其沉潜笃实、切问近思者,莫如樊迟。”B38既然诊断有误,所谓对其下的处方,即孔子的话也只能导致曲解的结果。王夫之对此批判说:“屈圣言以从己。”B39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子游为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对此程子说:“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B40程子也是接受所谓“药病说”,即孔子对其三个弟子所说的话是为了纠正他们的病痛的见解,来解释《论语》的这一句子。
然而王夫之却批判说孟武伯“轻身召疾”、子夏以不温和的脸色对待父母,完全是一种臆测、毫无根据的诬陷。B41即是说,对所谓病痛的诊断都已经错了,还主张孔子为他们开了处方,这是强词夺理。
而且王夫之认为,药虽然能起到治疗的作用,但是也能造成伤害,同样为治疗某个人的病痛而说的话,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毒药,由此他否定药病说。B42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解释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反而会把意义无穷的孔子之语束缚在狭隘的藩篱之中。因为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良药,而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毒药的话,这些话就很难说是真理。
总而言之,王夫之对“药病说”持批判的态度,他说:“论语一书,先儒每有药病之说,愚尽谓不然。”B43即是说,圣人之语本来是圆满而广博的,如果把它解释为“治疗某一个人病痛的话”,就会缩小它的涵义。
四、理一分殊
在上一部分,我们探讨了王夫之否定药病说、主张对《论语》中孔子的话进行普遍解释的内容。但是王夫之并不是认为可以超越时代和空间,机械地运用《论语》中孔子的话。王夫之说:“圣人一语,如天覆地载,那有渗漏?只他就一事而言,则条派原分”B44,将它表述为“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
(一)“敬”与“简”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雍也》)
对此,程子解释:“居敬则心中无物,故所行自简,居简则先有心于简,而多一简字矣”B45,将“居”属于心、“行”属于事来看。B46王夫之却认为这是荒谬的。因为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解释,仲弓给予肯定的“居简而行简”就能解释为“以尧、舜兢业之心,行伯子不衣冠之事”,这是不可以的。B47
因此,王夫之将“居”解释为“所以自处”,“行”解释为“行之于民”,“居敬而行简”则解释为“自治敬而治人简”B48。“自治”包括治理自己和恭敬他人。“敬”与“简”,不解释为一个人的内心和行为,而解释为所有人对自己、他人的“敬”和治理者对百姓的“简”。按照王夫之的这种解释,治理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敬”是属于所有人的普遍事,而治理百姓的“简”则属于治理者,即天子或诸侯。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不以居敬为德,敬者非但南面之所有事也。行简则唯君道宜然。唯君道为然,则仲弓之语,于行简上进一步说居敬,实于君子之学,居敬上更加一法曰行简也。B49
就是说,从天子到庶民,虽然在“以居敬为德”上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天子负责治理百姓的政事,所以不得不在“敬”上加一个法则“简”。在王夫之看来,“居敬”虽然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德目,但是 如果因为治理者本身居于敬,就要求百姓也居敬,不但百姓很难做到,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因此,王夫之主张:“欲得临民,亦须着意行简,未可即以一‘敬字统摄。”B50
就个人而言,一个人以“敬”对待别人是应该的,别人也应该这样对待他。但是如果站在治理他人立场上的人制定一个“以敬待人”的原则,强加给所有百姓的话,这个原则是难以实行的。同样,王夫之也说:“若君人者必使其民法冠深衣,动必以礼,非但扰民无已,而势亦不可行矣。”B51
而且,王夫之主张:“谓自治敬则治人必简”,亦是有“躐等”的。B52也就是说,并不是“自治敬”,就自然能“治人简”。那么,和为“自治敬”而努力一样,为“治人简”而努力也是向人们要求的一种层次。
居敬既不易,行简亦自难。故朱子以行简归之心,而以吕进伯为戒B53。看来,居敬有余,行简不足,是儒者一大病痛;以其责于己者求之人,则人固不胜责矣。且如醉饱之过,居处之失,在己必不可有,而在人必不能无。故曰“以人治人”,不可执己柯以伐人柯也。B54
如果是孔子,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B55,自然会以敬治理自己,以敬、简治理他人。但是,仲弓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孔子对仲弓说,对待别人和百姓时,“出門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B56,体现出“敬”的必要性;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B57,体现出“简”的必要性。B58孔子这样说是为了让仲弓知道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道理。
正是这样,“敬”一方面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法则(理一/同道),而另一方面又是不能站在治理者立场上以“敬”强求百姓,而是需要“简”的一种实践方法(分殊/殊途)。
(二)“孝道”与“几谏”
在东方社会里,孝敬父母(孝道)是从庶民到天子,作为子女的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理。没有尽到子女责任的人,不但会受到社会的谴责,甚至还会受到处罚。天子也要不断地向臣民们表现出尽孝道的姿态。《孝经》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B59即对于所有人来说,孝道是“理一”“同道”。但是王夫之却认为,这个“理”和“道”的实践会因其所处的位置而有所不同(分殊/殊途)。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对此,朱子将“几”解释为“微”,“几谏”则与《礼记·内则》相关解释为:“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B60王夫之却认为,隐微谏言是不能明确表达意思的,所以不能隐微,要明确。他主张,所谓“几谏”,并非“微言不尽”,解释为“见微先谏”才是妥当的。B61父母的过失被人揭发是羞耻的,所以要在那之前“见微先谏”,不让这种事情发生。B62王夫之认为,这一点正是“子事父”与“臣事君”的不同之处。如果像子女见到父母之微而先谏一样,臣下见到君主之微也先谏的话,就成了凡事都加以干涉,君主必然以为是臣下在诽谤自己。B63
真德秀在《论语大全》中说:“诸侯不谏,使亲得罪于国人,天子不谏,使亲得罪于天下”B64,认为“几谏”还涉及到天子和诸侯的子女。而王夫之却主张,不曾有天子、诸侯的子女“几谏”之礼。王夫之说,天子、诸侯的子女不仅是子女还是臣下,所以不能为了尽子女的职分,向作为父亲的天子或诸侯“几谏”。孔子所谓“事父母,几谏”,是针对所有子女而说的普遍性的言表,但天子、诸侯的子女还具有臣下的职分。当然,对王夫之的这一主张有人会反问:普通百姓的子女不也是君主的臣下?但是可以这样理解:王夫之的主张针对的是能直接谏言的狭义上的人群。总之,王夫之这样下结论:“圣人酌权以立万世之经,故不为天子、诸侯立以子谏父之礼。”B65
虽然“孝道”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则(理一/同道),而实践“孝道”的方法——“几谏”却因实践者是普通百姓的子女还是天子、诸侯的子女而有所不同(分殊/殊途)。
五、“学”的重要性
王夫之主张,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学”。虽然人在本能方面不如动物,但是人能通过“学”超越动物,成为真正的人。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
对此,朱子解释:“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B66
因为朱子在《论语集注》里同时引用了游酢B67和吴域B68的话,所以后代学者们把它解释为:比“学”更重视“行”。游酢说,因为“三代之学”本身就是“明人伦”,所以既然人伦已明,就可以认定已学;吴域则比“学”更重视“行”,提出子夏之言可“至于废学”的疑问。因为两个人在“子夏之言比学更重视行”的看法上是一致的。所以朱子也把后面的两句解释成“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只要做好前面的“四者”,就相当于是“已学”了。
王夫之却反驳,这不过是对朱子解释的误解。要想那样讲,就得这样说:“虽其未学,亦与学者均矣。”B69因此王夫之主张,要注意看朱子注释中的“必其务学之至”六字。可见朱子是为了强调前面所提到的“四者”是必须通过“学”才能获得的结果而这样说的。B70
总之,王夫之因为重视学问,所以不接受“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这种解释。因为他不认为“贤贤”等事能代替“学”。王夫之认为,要是按照那种方式比学更重视行,就应该说是:“虽其未学,亦与学者均矣。”王夫之解释,子夏不但不忽视学,反而重视学。他说,对“贤贤”等事,有人妄自说“不假于学”,但是我要说,如果不是“务学之至”的人,就“不足与此”B71。然后王夫之反问:“天下岂有不学而能之圣贤哉?”B72
王夫之批判,“不假于学”而能“从心所欲不逾矩”B73与佛教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没有分别的。是否重视“学”正是区分圣学与异端的界限。B74因此王夫之认为,“贤贤”等事也不是就“用力敦行”而言,而是据“现成人品”而言。B75
对于“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的解释,朱子的后学们解释:“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与此相反,王夫之却解释:“虽曰未学而已然,我必谓之其学以后方能若此。(使未学也,则亦安能尔哉?)”可见,王夫之是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的。
六、结语
朱子立足于道统说,把孔子视为圣人,曾子、子思、孟子视为贤人,认为儒学之道是由他们传承下来的。因此比六经更重视他们的著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他说,四书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存在优劣的问题。
王夫之也承认孔子是圣人,《论语》是最能反映圣人言语和见解的书。按照王夫之的主张,《论语》是“圣人彻上彻下语”。换言之,即是“广大该括,则又遇方成圭,遇圆成璧。”与《论语》相比,《孟子》《大学》《中庸》则是局限在那个济世时代的书。因此,王夫之要求读《论语》的人们,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具体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在这种意义上,王夫之所提出的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的正是被他称之为“药病说”的《论语》读法。就像对某种病症使用某种药物一样,孔子在《论语》中对弟子们所说的话都是为了治疗他们的某种病痛而说的,这种解释就是药病说。朱子及其后学们在解释《论语》的时候,大多据此来解释。
王夫之批判“药病说”时主张,孔子的话不是为治疗弟子的病痛而说的话,而是能够引导人们彻上彻下而成为圣人的很普遍的话。就是说,圣人对某一件事情所说的话,是可以分别适用到几件事情上的。例如,就“敬” “简”而论,治理自己和对待他人的“敬”是属于所有人的普遍的事情,而治理百姓的“简”则是属于治理者,即天子或诸侯的事情。而且“孝道”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则(理一/同道),而实践“孝道”的方法――“几谏”,却因实践者是普通百姓的子女还是天子、诸侯的子女而有所不同(分殊/殊途)。
而且,因为王夫之重视学,所以主张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学”。王夫之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他彻底地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 注 释 】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 第428页:“《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若不把《大学》做个匡壳子,卒亦未易看得。”
②③B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8、432、580页 。
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B13B14B15B23B24B26B35B36B39B43B44B49B50B51B54B65B7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 第214、268 、504 、260、193、193、197、197 、197、197、197、197、295、294 、295、216、215、217、214、257、272、274、273、274、256、199页。
B1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3页:“如‘学而时习之一章,圣人分中亦有此三种:‘时习则自‘说,‘朋来则自‘乐,‘不愠则固已‘君子。初学分中亦有此三种:但‘时习即‘说,但‘朋来即‘乐,但‘不愠则已为‘君子。”
B17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4页:“夫子只就其所得者,约略著此数语,而加之以咏叹,使学者一日用力于学,早已有逢原之妙,终身率循于学,而不能尽所得之深。”
B18王夫之:《讀四书大全说》, 第194页:“此圣人之言,所为与天同覆,与地同载。”
B1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4页:“异端之有权有实,悬羊头卖狗腿也。”
B2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94页:“近见一僧举‘学而时习之一‘之字问人云:‘之者,有所指之词。此‘之字何所指?一时人也无以答之。”
B2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96页:“如彼僧所问‘学而时习之‘之字何指,自可答之曰‘指所习者。”
B2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94页:“若吾儒不以天德王道、理一分殊、大而发育峻极、小而三千三百者作黄钺白旄、奉天讨罪之魁柄,则直是出他圈套不得。”
B2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94页:“凡论语中泛泛下一之字者,类皆如此。”
B27B33B37B40B45B56B57B60B64B66胡广(纂):《四书集注大全》 , 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硏究院1988年版, 第83、156、292、292、130—131、131、63—64、87、142、307页。
B2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15页:“非言之艰而行之艰,不独子贡也。”
B3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15页:“范氏固已指夫人之通病以为子贡病。”
B31胡广(纂):《四书集注大全》, 第508页:“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
B3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15页:“夫子贡之以言语著者,以其善为辞命也。”
B3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16页:“圣门如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皆有论著,而子贡独无。其言圣道也,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兢兢乎慎重于所见,而不敢轻置一词矣。则寡言者,莫子贡若,而何以云多言耶?子贡既已无病,夫子端非用药。”
B3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98页。对《雍也》篇中樊迟与孔子的问答“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王夫之说:“夫子与他人言,未尝如此开示吃紧”,强烈批判朱子云“因樊迟之失而告之”的解释是“非愚所知”。
B4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17页:“奚必悬坐武伯之轻身召疾,而亿揣子夏以北宫黝之色加于其亲,诬以病而强之药哉?”
B4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14页:“如必区区画其病而施之药,有所攻,必有所损矣。”
B4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73页:“程子似将居属心、行属事看。”
B47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73页:“假令以尧、舜兢业之心,行伯子不衣冠之事,其可乎?”
B4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73—274页:“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犹言自治敬而治人简也。”
B5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74页:“谓自治敬则治人必简,亦躐等在。”
B53有关吕进伯的故事,在《论语集注》的小注中是这样记述的:“世间有居敬而所行不简者,如上蔡说吕进伯,是个好人极至诚,只是烦扰,便是请客也,须临时两三番换食。”见胡广(纂),《四书集注大全》, 第156页。
B55胡广(纂):《四书集注大全》, 第79页:“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B5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73页:“仲弓且未到‘从心不逾矩地位,故夫子于见宾、承祭之外,更须说不欲勿施,使之身世两尽,宽严各致。”
B59李隆基(注), 邢昺(疏):《孝经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7页。
B6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52页:“以此知‘几谏者,非微言不尽之谓,而‘见微先谏之说为允当也。”
B6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53页:“亲之于己,直为一体,必待其有过之可改,则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恶,为人攻发,虽可补救于后,而已惭恧于先矣。”
B6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253页:“臣以几谏,则事涉影响,其君必以为谤己。”
B67胡广(纂):《四书集注大全》, 第64页: 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
B68胡广(纂):《四书集注大全》, 第64页: 吴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
B6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8—199页:“使其抑学扬行,则当云虽其未学,亦与学者均矣。”
B7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9页:“我必谓非务学之至者不足与此。”
B7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9页:“人有妄谓其无假于学者,而我必谓非务学之至者不足与此。”
B73在王夫之看来,假于心是没有一定标准的,必须要根据学习圣人来得到一定的标准。这正是王夫之把阳明学视为佛教的模仿物,加以批判的原因。
B74王夫之:《讀四书大全说》, 第199页:“‘吾必谓之学矣六字,是圣学、异端一大界限,破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流邪说。”
B7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第199页:“上四段原是据现成人品说,非就用力敦行者说。”
(编校:夏剑饮 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