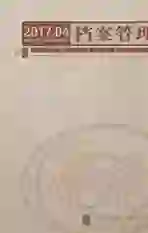档案正义论质疑
2017-08-10王笛
王笛
摘 要:文章首先提出社会正义的取向问题是档案正义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从档案留存的初衷不是维护正义、档案工作者的职责不是维护正义两方面论述了档案正义不能成为档案管理的工作准则;从档案正义理论依据不可靠、档案正义驱动力不足两方面论证了档案正义无法成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文章认为,有关“档案与社会正义”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正义无法作为档案工作的法则和档案事业的方向标被提倡。
关键词:档案;社会正义;档案正义
Abstract:The article first puts forwar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social justice is a problem that the “archives for justice” must be solved. Secondly, social justice cannot be a working guidelines a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reserving the records is not to maintain justice and the duty of the archivist is not to safeguard the justice.“Archives for justice” can not become the standard of the archive management. Social justice can also not becom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rchives since the theory of “archives for justice” is unreliable and the driving force is not enough.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about “archives for justice”,that justice can not be promoted as a rule of archives and archivists.
Keywords: Archives;Social justice;Archives for justice
“档案与社会正义”是近年来档案伦理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档案在社会正义的维护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档案工作者在社会正义的维护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等问题引发了许多档案学者的思考与讨论。维恩·哈里斯(Verne Harris)作为“档案与社会正义”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认为无论是否处于面临压迫和转型时期的社会,档案工作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反抗压迫、追求民主的政治活动,以正义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1]。兰达尔·吉莫森(Randall C Jimerson)也认为档案的保存服务于维护社会正义、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并提出档案工作者应该承诺自己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符合社会正义的需求[2]。一些档案学者支持他们的观点,并开始从档案应从哪些层面追求社会正义、档案工作者如何参与到社会正义维护中去等角度进行研究和探索。我国档案学者付苑[3]、罗亚利[4]对“档案与社会正义”的代表人物和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丁先存对我国档案正义的缺失和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述[5]。
同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现。国外学者马克·格林(Mark A. Greene)对“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档案工作者就是在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追求正义”这种观点表示不认同,他认为无论档案工作是否以正义为目标,都可以为自己保存了社会真实面貌而骄傲[6]。理查德·马修(Richard J. Matthews)则从解构主义出发,认为“档案正义”和“档案行动主义”的观点是对德里达思想的误读[7]。
笔者认为,“档案与社会正义”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对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体和个人来说,档案的确可以成为他们争取自身权利、追求社会公正的重要工具,但档案正义是否应当成为整个档案事业的方向标,档案正义是否能够作为档案工作的最根本法则被提倡,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
1 社会正义的取向难以界定
“档案正义”(archives for justice)来自“档案”与“社会正义”的结合,这就使得“社会正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概念。正如温迪· 达夫(Wendy Duff)等人在文章中所承认的那样,社会正义的概念是复杂、多样且难以定义的,而在档案与社会正义的研究中,对“社会正義”进行界定又是十分必要的[8]。那么,如何界定“社会正义”就成为档案正义的一大难题。
首先,正义本身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词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在于人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做自己本分的事就是正义[9];同为古希腊伟大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将正义与法律相连,认为法律的运作是以对公正与不公正的区分为基础的,法律是判断正义的标准[10]。近代则有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关于正义的争论。罗尔斯的正义是一种“程序正义”,他提出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二是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责任和义务联系在一起[11],第一个原则体现了“自由”,第二个原则体现了“平等”。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进行了批判,他主张正义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协商、交流、谈判之后达成的公式所决定的,公平的对话程序是达成正义原则的基础[12]。从古至今,无数思想家、哲学家对“何为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正义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那么,档案所维护的应该是柏拉图的内在和谐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是罗尔斯的自由与平等还是哈贝马斯的公平对话呢?
其次,社会正义没有固定的取向。如果说,公平是目前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一种正义取向,但对公平本身又有不同理解。一方面,许多事物的价值很难被衡量。例如一份档案的价值就很难界定,它不仅仅是一份纸质记录,还可能是个人资产的凭证、家族记忆的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28条规定,“损毁、 丢失或者擅自销毁档案馆保存的国家所有的档案和单位保管的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造成损失的,可以根据档案价值和数量,责令赔偿损失”,那么一份关乎个人利益的历史档案应该责令损害人赔偿多少才算是对双方公平公正,这是值得讨论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甲之砒霜,乙之蜜糖,一群人认可的公平正义对于另一群人来说可能是剥削压迫。如果将时代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正义的判断也是不同的,例如报仇雪恨这种在古代被视为正义之事的行为在当今社会显然是不可取的,作为要流传于后世的档案,如何保证今日所维护的社會正义能够迎合后代的正义取向呢?
既然正义本身概念难定,社会正义又没有固定取向,那么档案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又从何入手呢?
2 档案正义难以成为档案工作准则
2.1 维护正义不是多数档案被留存的初衷。无论是结绳、刻契,还是文书、信件,都是形成者为记录事物、表达思想而作,为留存信物凭证、备以日后查阅而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就形成了档案[13],所谓伸张正义、申诉社会不公并不是大多数形成者进行记录的初衷。即使是如司法档案这类记载着诉求自身权利、维护公平正义内容的档案,其形成的出发点也是作为案件的记录、审判的凭证以及对司法的监督。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意味着无论档案与弱势群体有没有关联、其内容是否有关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它都会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国家宝贵的资源被留存,这也是档案资源丰富多样、档案价值无可比拟的原因。
档案不是为正义而生,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能够为社会正义出力。在一些档案应用于社会正义申诉的实际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正义起到实质性贡献的是一些特定的档案资料。例如《记忆、正义与公共记录》(Memory,justice and the public record)一文讲述了挪威“战争儿童”为自己因特殊身份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做抗争,要求获得身份认同和经济赔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有证明“战争儿童”真实身份的个人档案、“生命之源”计划挪威指挥部的文件记录[14];《打破规则,拯救记录:东帝汶人权档案和正义研究》(Break the rules, save the records: human rights archives and the search for justice in East Timor)一文以东帝汶独立斗争为例从历史和政治层面探讨了档案在东帝汶人民追求自决权利中的角色和作用,其中被运用到的是记录违反人权情况的档案文件[15]。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更多的是记录常规性业务活动、有关普通公众的生平经历的档案资料,类似“战争儿童”档案、人权档案等关乎受害群体、不公正待遇的档案只是众多档案文件中的一小部分。不可否认,这类档案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如果过分追求档案正义,以正义作为档案工作各环节的判断准则,是否意味着只有对维护社会正义、支持公平公正有用的档案才会被保管,而与正义无关的一些日常性信息资料就不再受到重视了呢?
在正义准则下的档案工作是有目的性的,其目的就是维护社会正义,这样的目的性会带来选择,有选择就会有舍弃,有舍弃就不可能全面完整。而对于一些学者将档案正义与档案资源的完整保存相关联,认为丰富馆藏、保障公民平等利用档案就是实现档案正义的观点,笔者并不认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应该是对反抗不公、追求公平等活动的主动参与,而丰富馆藏、提供利用是档案工作的本职,只能算作对社会正义行为的被动支持,没有弱势群体、受迫害群体对档案的利用,档案所谓的正义价值就没有体现,因此被动的期待并不能作为档案事业对社会正义的主动追求。
2.2 维护正义不是档案工作者的主要职能。从社会层面看,档案职业的首要责任不是维护社会正义。
职能的专业化趋势来自分工的影响,社会分工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同时也会被当作一种责任[16]。每个人在自身的分工内各司其职、各行其是,构成了社会机器的有序运转。现代社会中法律与正义的关联最为紧密,英文中“justice”一词既表示“正义”“公正”,也有“法律制裁”“法官”之意。西方法学认为法就是正义的代表,正义是衡量是否符合法的目的的准则[17],从这一角度看,法律的制定工作是与社会正义有最直接关联的工作。在我国,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体察民情、反映民意,讨论和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监督并推动法律法规、决定决议的有效实施,他们的工作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切实推动,反映不公、呼吁平等是他们的责任。而档案工作的核心职责是管理档案,如历史记录的保管者、社会记忆的建构者等角色和责任都是围绕“档案”这个工作对象产生的。从档案的收集、整理到档案的保管、鉴定再到档案的编研、利用,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都有既定的工作规范,做好这些工作是对档案工作者的最基础要求,也是档案工作者最基本的责任。
诚然,如马克思所说,人应该追求全面发展,但这种全面发展不应该影响到其本职工作的开展。也就是说,正义可以作为档案职业伦理道德的一项要求,但不应该以档案工作者本职的弱化为代价。档案职业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种幕后工作,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常要求走到台前,正面冲突与争端,这需要参与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管理国家档案资源工作的档案工作者既没有维护正义的职责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担当这项工作。
从个人层面看,普通档案工作者缺乏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
回顾上文所举的挪威“战争儿童”、东帝汶人权斗争的案例,再加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著名运动,不难发现反抗不公正对待、追求公平正义通常是受迫害群体中的组织或个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对这一群体有特别关注的人。二战时期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发起了一个秘密文档项目,其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带领收集并归档了包括科研人员、作家、教师、公共部门工作者以及无数普通犹太人在内的众多犹太居民记录,为后世了解当时犹太居民的艰辛生活提供了资料[18]。南亚裔美国人数字档案馆(South Asian American Digital Archive,SAADA)的两位创始人中,Michelle Caswell是一名优秀的档案学者,她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学院档案学专业的助理教授,拥有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图书与情报科学博士学位,在多本档案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文章[19],另一位创始人Samip Mallick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图书与情报科学硕士学位,曾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南亚收藏的助理书目员,也曾为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南亚和国际移民项目(South Asi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grams)工作[20]。
我们能否期待或要求所有的档案工作者都具备与这些人相当的学识与素养呢?笔者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哈里斯提出档案工作者应该成为支持或反对社会压迫的记忆活动家,他认为档案工作应摆脱政治权力的束缚以维护正义[21]。笔者认为,档案的确为社会正义维护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工作者一定要成为社会正义维护者或研究者中的一员,要求档案工作者成为政治参与者或行动主义者(activism)而不只是利用者获取凭证资料的提供者实有难度。
3 档案正义尚不能成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
3.1 档案正义理论依据尚不可靠。以哈里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档案正义与雅克·德里达的后现代思想结合起来,试图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寻找档案正义的理论依据。但美国档案学者理查德·马修(Richard J. Matthews)指出,后现代档案理论将德里达的“档案热”(archive fever)阐释为“公权力”(archontic power)理论是对德里达“档案热”的误读,这种对解构主义的误解将档案工作者错误地引向了对正义的呼唤。马修进一步指出,应当认识到正义是不可判定的,“档案热”与权力和非正义无关,而是德里达通过对档案本质的研究来解释弗洛伊德“死本能”(death drive)理论化的问题[22]。
笔者认为,“正义”与“非正义”相对,是一个有限定范围的词汇。追求正义这一行为本身是一个封闭性建构的过程,它将“正义”当作为人行事的标准,把事物圈定在“正义”的框架之内,以社会正义为指导原则的档案工作是在“正义”的准则下去建构档案体系、结构化档案事业。档案正义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都圈定在“正义”的栅栏内,这与解构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相悖的,从解构主义中寻找档案正义的理论依据只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德里达对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等政治斗争的投入和支持,其出發点在于对“结构”的批判,而不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哈里斯等人只看到德里达对政治事件的参与,没有深究其行动的初衷,就将德里达的思想观点套用于“档案与社会正义”并试图用以指导档案工作实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3.2 档案正义驱动力不足。笔者认为,哈里斯对档案正义的提倡是因为其所从事的档案事业处于特殊地区的特殊时期之下,而在矛盾冲突复杂多样、正义取向并不明确的社会环境中,档案还能否在正义的维护中发挥如此显著的作用、取得世人瞩目的功绩,是存疑的。哈里斯在《终结阶段的档案伦理:雅克·德里达遇见纳尔逊·曼德拉》一文中承认,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政治转型的今天,档案正义的力量正在消散,正义已经不再是南非档案事业的驱动力,取而代之的是缓慢而无聊的社会“正常化”进程,档案部门不再是变革的工具,南非档案工作者中也少有人成为他所说的“支持或反对压迫的记忆活动家”[23]。必须看到,他所谓的“缓慢而无聊的社会‘正常化进程”正是任何一个处于平稳发展环境下的社会的常态。
放眼世界范围,尽管如种族歧视这样的不公正问题是存在的,但一个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是多样的,这种多样同时意味着分散和弱化,因此,将档案正义从个体实践升华为档案事业的整体目标是不合适的。档案正义只能作为档案事业的一个宣传方向,通过对档案工作支持世界各地边缘化群体或受压迫群体反抗不公、追求平等的案例的宣传,让人们看到档案的价值,使人们认识到档案身为真实记录的意义:档案是非正义事件发生过的证据,是少数群体寻求身份认同的依据,并借以提高档案事业的社会地位。但,社会正义无法成为整个档案事业发展的驱动力。
档案正义似乎为档案事业指出了一条积极向上的光明道路,但深入思考后不难发现,这一理论存在许多漏洞与缺陷,在这些问题尚未探讨清楚之时,档案正义不宜被过多提倡。
参考文献:
[1]Harris V. The archival sliver: Power, memory, and archives in South Africa[J]. Archival Science, 2002, 2(1):63~86.
[2]Jimerson R C. Archives for All: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 American Archivist, 2007, 70(2):252~281.
[3]付苑. 档案与社会正义:国外档案伦理研究的新进展[J]. 档案学通讯, 2014(4):4~9.
[4]罗亚利. 社会公平视阈下国外档案价值实现研究概述及启示[J]. 档案与建设, 2014(9):4~7.
[5]丁先存. 试论档案正义[J]. 皖西学院学报, 2007, 23(6):29~31.
[6]Greene M. A Critique of Social Justice as an Archival Imperative: What Is It We're Doing That's All That Important?[J]. American Archivist, 2013, 76(2):302~334.
[7][22]Matthews R J. Is the archivist a “radical atheist” now? Deconstruction, its new wave, and archival activism[J]. Archival Science, 2016(3):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