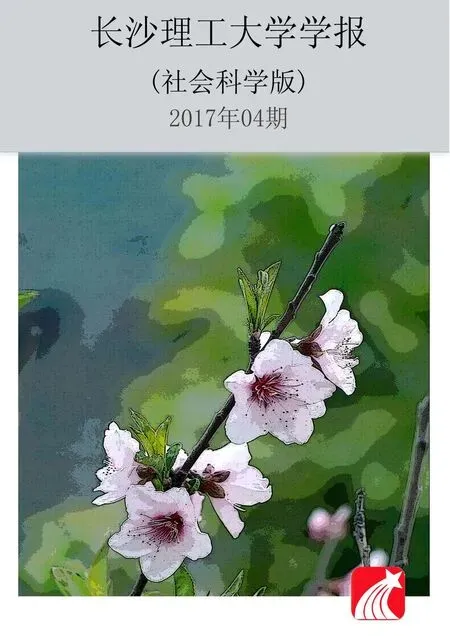科学民主化的两种研究进路
2017-07-07白惠仁
白惠仁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系,美国 纽约 10027)
科学民主化的两种研究进路
白惠仁1,2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系,美国 纽约 10027)
科学民主化的研究是由一系列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所推动的。关于科学民主化的研究一般由两部分构成:民主化理由和民主化限度。由此,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研究进路:STS的进路和科学哲学的进路。在民主化理由方面,STS的研究进路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真理与客观性,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为民主化打开大门;而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以一种温和实在论保留了科学真理,而反对科学自治。在民主化的限度方面,STS的研究进路允许公众对科学活动的全面参与,而科学哲学的进路将公众参与限于议程设置和知识应用阶段,把知识生产活动留给科学家自主决定。此外,STS的研究进路关注的是现实的民主化实践,而科学哲学的进路试图提供一种理想的民主模式。
科学民主化;STS;科学哲学;良序科学
一、科学民主化的实践与辩护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在应用层面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使得科学与公众愈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参与科学成果应用、科学决策乃至知识生产的科学民主化实践渐成趋势。然而,在规范性层面,要为科学民主化提供合法性辩护,需要挑战传统的科学自治理念。这种理念预设了自由探索与发现真理之间的必然联系,即科学揭示了关于自然的真理,而科学家不受社会政治利益干涉的自由探索为其提供了保障。
(一)科学民主化的社会实践
在科学及科学政策领域中呼吁民众参与的声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的几场社会运动起到了重要催化作用,如女性运动、反核运动和环境运动。具体而言,这些社会运动有着广泛的目标,如社会公正、改善民主实践、改变公众的观念等,它展现自己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如质疑专家知识、重新塑造科学、提出政治要求、动员科学资源以及促使知识生产更民主化[1]。
真正将公众参与的社会运动推向高潮的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艾滋病运动。鉴于当时美国政府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和对艾滋病治疗的轻视,这一被称为“艾滋病治疗行动主义运动”的组织,开始关注艾滋病的科研情况,他们从街头抗议者转变成新型专家,开始与科学共同体对话。该运动也逐渐得到NIH的支持,艾滋病临床试验小组的大多数会议也开始向公众开放,并且病人代表享有充分的投票权。在如何从事研究,如何评估研究结果,应该资助哪些研究方案等方面,公众开始享有发言权,此外还参与决定科研资源的分配。
与类似的草根运动相呼应,自20世纪70年代始,许多国家政府开始为公众参与传统上由官僚精英主导的政策领域提供新途径。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组织了第一次关于生物技术的共识会议,然后很快传播到了欧洲国家。开始,共识会议只包括了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后来也包括了代表公众的参与者。与参与方式的浮现并行的是科技政策中新的治理形式: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及协商民意调查等制度性实验,已将一些随机选择的外行公众团体纳入复杂性议题的协商过程中。其中许多的努力集中于新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管理,还有一些则试图通过将外行视角引入科学知识自身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而走向“上游参与”。
(二)科学民主化的理论辩护
可以说,科学民主化的研究是由社会运动的实践所推动的。基于对一系列科学民主化社会运动的反思,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经典考察: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对美国艾滋病行动主义者进行了研究[2];温尼(Brian Wynne)对英国坎伯兰牧农对核辐射对羊群的影响的评估案例进行了研究[3];卡龙(Michel Callon)等研究了法国的一个肌肉萎缩症患者的组织[4]。然而,科学民主化的社会运动或经验层面的社会学考察都不足以让我们在规范性层面接受科学民主化的理念。从直觉出发,科学民主化这一称谓对那些传统科学形象的捍卫者而言总是不甚悦耳。这种“直觉”即是一种科学自治的理念,它被一般的表述为:科学家自由的选择研究方向、开展研究工作,以发现关于自然的真理,期间不受任何社会、道德、宗教及政治价值的介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们纯粹、自主的活动。
基切尔(Philip Kitcher)将这种状况描述为:“科学知识与被我们当作是民主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它们应当是的样子,这一观念虽然可能不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真理,但已经被广泛认同了。对于一些评论者来说,问题在于科学的骄傲试图罔顾来自民间的价值观和智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麻烦来自于公共偏见,它们干扰了既定知识向明智政策的恰当转换。不论焦点是进化理论的地位、分子生物学的药物应用、转基因生物的安全问题、还是全球变暖的威胁,那些对应该相信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持不同理念的人们总是预设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5](P11)
从职业化科学诞生的第一天起,科学家们就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边界与纯洁性将遭受侵害的危险,并尝试着用“自治”的策略去化解。一开始的危险来自神学,到了20世纪初,宗教已不再对科学构成威胁了,但是接踵而来的却不是科学唯我独尊的时代。在二战前后,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划界、通过认知与社会的二分法,在政治面前保持“自治”。我们要为科学民主化提供合法性辩护,所面临的困难就是挑战科学自治的传统理念。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科学”与“自治”在本文的具体含义。从普朗克(Max Planck)、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到布什(Vannevar Bush),所维护的和要求避免政治介入的始终都是“纯科学”,即基础研究,而技术应用至多被他们用来作为划分科学中立与政治渗透的缓冲地带。对于科学自治,是针对科学家而言的,因为在科学研究中他们是真实的道德责任人,从而享有自治权。具体而言,科学家的自治权包括对研究方向和项目的自由决策,和自由开展研究活动的权利,即关于“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的决定权。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指的科学自治就可以被表述为:科学家在基础研究中拥有对研究方向(项目)和研究方式的自由决定权。
对于以上所界定的科学自治理念,其辩护分别来自科学性质和政治合法性两个方面。第一个辩护认为,科学自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科学研究以中立、客观的方法发现关于自然的真理,而干扰科学活动和科学方法的社会、政治或道德因素会给科学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带来负面影响。这一来自科学性质自身的理由受到包括普朗克、波兰尼及波普尔(Carl Popper)等人的支持。第二个辩护则稍显复杂,其基于现代科学的深刻转型:国家支持的科学研究活动在二战之后凸显出来,使得科学家获得大量公共资金,并从政治管理制度中获得广泛自由,而作为交换,科学为社会提供持续的、满足国防和消费需要的知识。由此,支持科学自治的第二个理由可以表述为:保障科学家在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才能保证科学的持续繁荣,而持续繁荣的现代科学对公共福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布什在他的著名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给出的理由。
以上的两个对科学自治的辩护也分别指向不同的侧面:第一个来自科学性质的辩护为科学家对“如何研究”的决定权提供了支持;第二个来自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则为科学家对“研究什么”的决定权提供了支持。同时,科学性质的辩护也构成了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基础。由此,我们要挑战科学自治理念以便为科学民主化提供合法性辩护,就要反驳以上的至少一个支持理由。相应的,本文中所讨论的“民主”就是指公众对基础研究中“研究什么”和(或)“如何研究”的决策过程的参与。
二、STS的研究进路
有关科学与民主的研究并非新生事物,它在20世纪40年代贝尔纳(John Bernal)与波兰尼关于“计划科学”的论战中已初露端倪。艾杰(David Edge)在1995年版《科学技术论手册》中指出,对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科学技术论(STS)而言,民主是重要推动力,“在越南战争以及同时发生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影响下,探索科学民主化的可能性成为一项迫切的要求”[6](P11)。在后续发展中,STS始终对这一主题保持着关注度,这一领域最核心的研究者包括:贾撒诺夫(Sheila Jasanoff)、温尼(Brian Wynne)、瑞普(Arie Rip)、柯林斯(Harry Collins)、埃文斯(Robert Evans)、克莱因曼(Daniel L. Kleinman)、彼得森(James C. Petersen)、埃尔文(Alan Irwin)等。
柯林斯与埃文斯于2002年发表的《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总结了STS学界对于科学民主化研究的三波理论,也就是科学民主化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波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一个学术运动被搁浅了的实证主义。科学的权威无可质疑,科技决策是科学家的专有领域,柯林斯称其为“权威时代”。第二波秉承了SSK社会建构论,在第二波看来,科学真理和知识客观性不再承担评判与科学相关事务的权力,民主原则被引入,使公共领域中科学争论的决策权更多的诉诸于公众。柯林斯认为,第二波理论较好地解决了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普遍发现了蕴涵在公众中的地方性知识。但柯林斯又强调,第二波研究对合法性问题的诠释又走过了头,因而出现了扩展问题:专家和公众的界限被取消了,导致了“技术决策权力的无限扩张”[7]。在第三波中,柯林斯在改变传统关于科学能够提供真理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专家知识”概念,试图重新区分专家与公众间的界限[8]。可以说,第二波理论更强调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辩护,而第三波理论更强调科学民主化的可能性及具体方式。
(一)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研究
STS的第二波主要关注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者们从反思科学技术的性质、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及科学与社会的交汇这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第一,在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一部分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专家对于问题的界定、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科学技术的责任性问题上。专家对问题的界定总是有一定狭隘性的。因而,专家体制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是先天不足的,不可能诉诸更多的研究或更好的技术来克服它们。贝克(Ulrich Beck)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还可能体制性地放大风险,而且系统地否认其造成现代风险的责任,而公众参与有助于对科学技术引发的不确定性的治理。另一部分研究者从科学政治学的角度着重反思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而论证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9-11]。杰西卡(Jessica Wang)梳理了194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与民主关系的研究视角,认为20世纪40年代科学的权威性帮助了以纳粹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的形成;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根据罗蒂(Richard Rorty)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观点,由于科学实践与自由民主规范的并行及科学家们可以在任何政治形态中形成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公共空间,科学自身开始成为一个民主力量。冷战之后,以埃兹拉西(Yaron Ezrahi)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历史和社会维度探讨科学在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系统中的角色[12]。
第二,在社会形态的变化方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了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异质力量的科学技术日益侵入社会以及个人生活,特别是带来大量的风险,引起了对于专家、专家体制等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性是现代性动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公众参与有助于积极的反思和选择。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提出了现代性的可选择性,技术的社会选择是其中一条进路,这也为公众参与指示了一个有希望的前景。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成为关键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知识生产、分配的权利意味着相应的社会权利,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给予公众以认识的权利并且更公平地分享知识的利益[13]。卡龙提出了“混合论坛”的科学治理模式,专业知识和外行知识也不是在分开的情境中被独立地生产出来而后再相遇,而是在一个“混合论坛”中共同发生的[14]。协商民主是治理的一种实现手段,它超越了代议民主的一些局限性,被很多STS学者接受为比较适合对存在知识隔阂和广泛的价值、利益诉求的科学技术议题的公众参与[15-16]。
第三,埃尔文认为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公众的社会身份和民主权利,并且和上述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冲突[17]。因此,在科学与社会交界面上,就形成更多的社会动力,引起更强烈的公众参与诉求。信任危机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怀特(Kyle Whyte)从规范概念上讨论了公众与专家的信任关系,讨论了后常规科学中公众在何种层面上可以信任专家[18]。斯莫尔(Bruce Small)认为,在科学民主化的既成事实下,科学家是可以接受与公众的对话及公众参与讨论的。公众参与有助于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更民主、平等、稳健的基础上,从而舒缓信任危机[19]。
(二)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研究
柯林斯认为,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建构论已经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即它展示了诸如利益等因素进入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合法机制,科学共同体成员并不具有相对于普通公众的认知优势,因此后者可以参与到公共科技决策过程中去。但它却没有解决“扩展问题”,即科技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参与限度是什么。柯林斯指出,第二波过于强化民主概念,使科技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无限扩大化。为此,他认为必须开展对专识和经验的研究,即STS的“第三波”,来为参与设置限度。参与限度问题的提出标志着研究者们开始将科学民主化研究的焦点转向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问题上。在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问题上,学者的工作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知识的性质及专家与公众的知识差异方面讨论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温尼认为公众与专家不同的认知方式得到理解与尊重,从而公众被认可为能动的认知者。此前这种差别被认为是公众非理性的表现,而公众参与引入了“常人视角”(lay perspective)有助于弥补专家视野的狭隘性。与此密切联系的是,凭借大量的案例研究,费舍尔(Frank Fischer)认为公众的地方知识得到了充分肯定,从而至少在理论上享有了参与知识生产的权力[20]。斯蒂尔(Nico Stehr)认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转变,其特征正是扩展了的公民行动的形式以及市民社会与专业知识之间简化了的通道[21]。卡罗兰(Michael Carolan)则结合当下的环境问题,批判了列维兹(Jerome Ravetz)和温伯格(Alvin Weinberg)将科学封闭起来的做法,讨论了环境问题中的专业知识,认为这种专业知识的开放将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22]。帕塔萨拉蒂(Shobita Parthasarathy)认为在科学决策中存在一个“专业知识障碍”(expertise barrier),要打破这一障碍可以从四个方面努力,即“发布已确定的专业知识,引进新的事实,引进新的决策逻辑,攻击官僚政治的规则”[23]。
第二,从科学民主化带来的科学实践乃至政治与社会的改变讨论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强调了对参与目的的认识不应太过局限在功利的、即时的、具体的目标之上。温尼认为,应同样关注公众参与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和界定、科学传播、政治文化的改变等方面[24]。博拉(Alfons Bora)统计并分析了七个欧洲国家有关转基因食品的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的相关数据,经过分析认为扩大的公众参与将有助于提升具体科学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效果[25]。从这些角度来看,公众参与的能力问题几乎就是个伪问题。
第三,对于公众参与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于具体的参与机制设计的讨论,这是当下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道森(Emily Dawson)比较研究了美国与英国在公众参与科学方面的不同机制,认为一个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要能够维持一个良好的协商氛围和过程,但又不应过分追求理想化的协商机制;要有助于克服外部世界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对于协商过程的影响[26]。皮吉昂(Nick Pidgeon)指出,公众参与并没有最优的模式,因此要防止将政府与研究者的各种观念强加在参与实践之上。必须通过参与过程给参与者赋权,给予他们一定的控制整个协商过程的权力,并允许参与过程按照内部的动力自由发展,而不应试图将其限制在既定的目标和议题上[27]。克莱因曼(Daniel L. Kleinman)强调从组织理论和科学政策角度分析参与式协商的制度和组织机制,主要是为了修正科技政策中的决策这个实际目标[28]。
三、科学哲学的研究进路
科学民主化研究的另外一条进路来自于科学哲学,当代理性主义传统下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的基切尔(Philip Kitcher)第一次尝试关注这一问题。基切尔的科学民主化研究集中体现在《科学,真理与民主》一书中,该书开篇即表达了当代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社会问题的集体失语。“有很多次,当我向一个新认识的人介绍我是科学哲学家时,对方总是欣然点点头,认定我一定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地位、科学对我们价值观的影响、或者科学在当代民主中的作用这些问题感兴趣。这种通常的看法尽管与职业科学哲学家在过去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事情并不相符,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重大问题的确存在,是值得提出和回答的,聪明人当然会认为科学哲学家正是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人。”[29](Pxi)
基切尔为科学的实在性和对其发生影响的社会因素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互贯通的契合点,即科学的秩序,提出了一个称为“秩序良好的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的科学研究的理想图景。良好的科学秩序并不是要否定科学对真理的追求,而是要把科学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一个民主的框架中来进行,以民主的方式对关于科学研究的政策进行决定。
总体看来,可以说良序科学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科学民主化理论。一方面,根据上一节的分析,STS的研究进路或侧重于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问题,如贾撒诺夫、温尼、古斯顿等;或侧重于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问题,如柯林斯、费舍尔、博拉等。基切尔完整的论证了一个科学民主化的理想模式,他通过对一种温和实在论的论证恢复了已被过分滥用的真理概念,进而指出科学的目标是发现“有意义的真理”(significant truth),这个发现过程有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介入,正常运行的科学应当顺应更广泛的价值,因此科学探究为了服务于集体的善就应当以一种民主的方式被决定,从而论证了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问题。基切尔将理想的科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议程设置、知识生产及成果应用。基切尔着重关注了第一和第三阶段,认为科学研究的这两个阶段应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并为这两个阶段提供了一个“理想协商”(ideal deliberation)的民主决策程序,从而论证了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问题。
另一方面,根据上一节的分析,STS的研究进路或侧重于“科学”问题或侧重于“民主”问题,如卡龙的科学的“混合治理”、列维兹的“后常规科学”关注于科学技术形态本身,以及柯林斯和帕塔萨拉蒂对专业知识性质的讨论,而另一部分研究则侧重于广泛的社会政治形态或具体的政治参与机制,如贾撒诺夫的“公民认识论”及克莱因曼的参与式科技决策的组织理论。相比之下,良序科学则完成了从科学到民主的哲学论证:在批判两种科学神话的基础上,细致论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的目标、科学与技术的区分以及科学的自由探索的组织方式等核心问题,从而为科学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进而批判了现实科技决策的“内部精英主义”和“外部精英主义”模式,区分出了“庸俗的民主”与“启蒙的民主”,为一种“理想协商”的科学决策的民主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辩护。
(一)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论证
良序科学的民主化方案是建立在一种实用主义的温和实在论基础上的,这与STS研究领域中对科学的建构论的倚重是相当不同的,良序科学的方案避免了科学民主化所遭受的来自理性主义者的质疑。著名科学哲学家朗基诺(Helen E. Longino)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基切尔的观点标志着科学哲学的一次重要转向,“它开启了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即使是在认识论上持保守观点的思想家也能够将科学和科学知识理解为一种公共财富。它建立了一种哲学空间,使得涉及科学的价值与政治理论,甚至是必要的主观因素的考量具有了合法性。它展示了在一种相对规范的认识论基础上,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考虑可以达到一种怎样的范围。成为一名真理的怀疑论者并不是对科学自治发起重大挑战的必要条件。这样,基切尔为科学哲学家们拓展了一个重要的舞台”[30]。朗基诺的评价揭示了良序科学在论证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问题时与STS学者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即将科学的实在性与自主性区分开来,在保留科学知识的实在性的基础上限制科学自治。
基切尔首先批判了当下思想界关于科学的两种神话,一种是“科学的热情支持者写书撰文颂扬对客观知识的探索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之一”,另一种是“科学的诋毁者则否认科学的客观性,质疑我们获得真理和知识的能力,认为科学是压迫的工具”[29](Pxi-xii),针对第一种神话,他要求承认知识的客观性,但我们对客观性知识的寻求并不总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针对第二种神话,他要求恢复已被过度滥用的真理概念,认为“科学有时候告诉我们独立于人的认知的世界的真理,并且让我们知道那些远离人类观察的世界由什么构成”[29](P28),提出科学应该发现的是“有意义的真理”,即对科学实在论问题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而在论证他的温和实在论时,基切尔区分两个层次:一是提出科学有时候告诉我们关于自然的真理,即科学知识仍然来自于对自然的描述而非建构;二是我们对科学理论的接受不受道德、社会、政治和宗教价值的影响,即科学理论仍然具有客观性。
面对自由探索与科学真理之间的紧密关系,基切尔恢复了科学对真理的发现作用,但希望驳斥自由探索为科学民主化提供规范性基础。对于科学自治,基切尔认为其价值基础是假设自由探索的价值可以超越其他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关切。基切尔对科学自治的批判即是针对后果主义传统对言论自由的辩护,他提出,科学研究应该促进的价值并非仅仅局限于近代科学出现以来科学家们所仰仗的密尔式的言论自由,还应该促进“基本自由的公平分配”,他用一种平等的自由为支持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的存在提供了道德辩护。基切尔对科学民主化合法性辩护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表明探索自由可能与一些更根本的自由相冲突,更广泛的自由才能促进实现公民更大的集体福利,因此公民自由参与已深刻影响到自身利益的科学决策是必要的,并且为了避免在研究议程的决策中少数人的愿望被忽略,公民应该平等的参与到决策当中。
我们要从科学中得到符合我们的利益与兴趣的“有意义的真理”,科学的客观性与实在性可以为这种需求提供保证,但是,这种需求也决定了科学必须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物而存在,科学的意义应当是社会决定的。因此,与作为科学传统形象的学院科学相比,良序科学同样肯定科学知识的实在性以及科学对真理的发现作用,不同的是良序科学与后来出现的科学的新形象——“后常规科学”或“后学院科学”类似,否定科学的自主性。基切尔将自己的焦点集中于科学政策,尤其是公共科研资源的分配问题,这又延续了二战后布什的核心论题——即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
在基切尔看来,现有的科学政策方案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一个足够清晰的目标,即没有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希望通过科学探究所促进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实际上,政府通过科学政策与创新政策形成了一种科学与公众利益相联系的合理机制,这样一种机制要做到“合理”,需要保障两个方面的问题:科学研究促进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和科研资源分配的公正。长期以来,关于科学政策始终是以第一个问题为中心展开,即更好的促进科学活动中对公共利益实现的最大化。而忽略了科研资源分配中对公众利益的公正体现,这一问题正是20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科学民主化运动的主要诉求[31]。
(二)科学民主化的民主模式
温尼曾指出,柯林斯的科学主义和基础主义立场,使他们的观点是还原论的和去语境化的,是向STS的第一波倒退。他们都要求在建构主义立场下,在科学决策中贯彻民主原则。从而,STS领域中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化的研究便陷入关于参与限度的争论,两个阵营分别以柯林斯、埃文斯与贾撒诺夫、温尼为代表。这一争论反映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如果说科学的民主化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科学应当置于怎样的民主框架之下?STS的研究进路着重关注于科学本身,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主的地方性、民主理念的适用性,在民主化方面过于草率地沿袭了现成的民主理念,缺乏深刻的反思究竟何种民主模式适用于科学这样一个关乎真理和知识的特殊事业的民主化问题[32]。
基切尔将理想的科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针对具体项目决定需要投入多少资源;二是考虑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项目;三是决定各种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实践性后果。这其中能够被民主决定的是第一和第三阶段,而涉及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二阶段仍然交给科学家,这与STS领域的研究相比,就为民主化设定了更先在的限度,即研究议程的决策而非科学知识生产活动。
那么,理想的民主模式应当是怎样的呢?良序科学所要求的民主决定方式是一种被基切尔称为“启蒙的民主”(enlightened democracy)的代议的协商民主,“假定由接受过科学专家辅导的群体来做出决策,并把社会中相对广泛的所有看法都纳入进来”[29](P133),其能够理想地决定对社会中需要进行的研究项目的选择,而参与这种协商的人,“应当包括各种观点的代表,不应仅仅来自科学团体内部,也不应仅仅来自支持科学研究的人群,而应来自整个人类社会”[29](P129-132)。这些代表由社会中的各个利益群体选举产生,参与商谈的代表的比例应当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一致,他们应当能够十分透彻地掌握自己所代表的群体需要对科学研究项目所做的投入,以及要从这些科学项目中得到什么等方面的问题。
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被协商科学项目的专家需要针对这些项目的相关知识对代表作出详尽的解释,以形成对这些项目的“指导过的偏好”(tutored preference)。接着,代表们相互交流他们指导过的个人偏好,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以某种程度想要某个后果,并且倾听其他人给出的解释。基切尔假定,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尊重其他人的偏好并想着达成一个共识清单,其中没有任何人没得到充分考虑。在这样的交流之后,理想代表的偏好又会再次得到修正,这一次吸收了他们对其他人的需要的认识。对他们而言,下一步则是在研究可能产生的结果中列出偏好的优先序。在这一阶段,代表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希望科学研究去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并且指出了这些问题的相对权重。此时,无私利的专家需要赋予已形成的集体愿望清单中每一个项目以可能实现的概率值。在下一阶段,政府利用这些已得出的概率的信息,再加上集体愿望清单,草拟出研究的可能议程,挑选出一个或一组最有利于实现理想代表们集体愿望的科研项目的资源分配方案。最后,决定权再次交回到代表们的手中,他们对合适的预算水平以及这个预算水平上的研究议程给出最终的判断[29](P134-143)。
当实际的决策过程的结果与这种理想的商谈过程的结果达到一致时,科学就可以被认为达到了一种良好秩序。因此“秩序良好的科学”是基切尔提出的一种可以使科学研究符合我们对它的真正需求的理想状态。而这又涉及到良序科学方案与其他民主化方案的第三个重要区别,即良序科学是关于科学民主化的理想图景。基切尔在《民主社会中的科学》中对于良序科学的补充说明中明确指出:“良序科学是一个理想。它似乎应该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一种哲学讨论而给科学的现实解释留有很少的余地。”[5](P125)在此,作为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乌托邦理论,良序科学为人们提供了审视所有可能制度的标准和应该为之努力的理想。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发现,对于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问题,STS的研究进路建立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打破了科学真理,取消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从而反驳了对科学自治的第一个辩护,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为科学的民主化打开了大门。相应的,在这种合法性辩护基础上,对于科学民主化的制度设计,STS的进路允许公众既可参与研究议程的设置也可参与具体的知识生产活动,从而达到“上游参与”,这就意味着在“民主化”方面,STS的研究进路要求公众对“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的双重参与。
然而,STS进路对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辩护由于损坏了科学真理和客观性,而招致了理性主义者的极力反对。因此,如果说传统理性主义科学图景不能应对现代民主提出的挑战,而基于建构论的STS的科学民主化方案否定科学真理的做法无异于釜底抽薪,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在真理与民主之间为科学寻找新的定位,即“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应当具有怎样的形象”,良序科学则尝试回答了这一问题。
从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出发,基切尔试图结合民主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问题,提供一个科学民主化的系统方案。这一方案对科学民主化的合法性辩护在保留了科学真理的基础上拒斥了科学自治,即保留了对科学自治的第一个辩护,而反对第二个辩护,从而将民主化限于议程设置和成果应用阶段而非科学知识生产的参与实践。也就是说良序科学的“民主化”只限于“研究什么”,而将“如何研究”的决定权仍留给科学家。此外,良序科学不同于STS研究进路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其民主程序是一种关于科学政策的理想模式。二者对比结果如下图所示:

科学哲学的进路STS的进路民主化理由保留真理反对自由探索反对真理与自由探索民主化限度议程设置与成果应用议程设置、知识生产及成果应用理论性质理想模式制度实践
[1]McCormick S. Democratizing Science Movements: A New Framework for Mobi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7, 37(4):609-623.
[2]Epstein S.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3]Wynne B.Sheep Farming after Chernobyl[J].Environment Magazine, 1989,31(2):10-15,33-40.
[4]转引自:Lengwiler, M.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urrent Practice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8,33(2):186-200.
[5]Kitcher P. Scienc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M]. New York: Prometheus, 2011.
[6]艾杰. STS:回顾与展望[A]//贾萨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M].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7]Wynne B. Seasick on the third wave: Subverting the hegemony of propositionalism [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3,33(3):403-429.
[8]Collins H, Evans R.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02, 32(2): 235-296.
[9]Latour B.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M]. Cambridge, MA, 2004.
[10]Brown M B. Science in democracy: Expertise, institutions, and representation[M]. MIT Press, 2009.
[11]Taverne D. The march of unreason: science, democracy, and the new fundamentalism[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Wang J. Merton's shadow: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democracy since 1940[J].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1999:279-306.
[13][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Callon M. The Role of Lay People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 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1999,4(1):81-94.
[15]Sung K. The Gatekeeping Paradig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Alternative: Science Governance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D]. Queen’s University, 2012.
[16]Fischer 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in a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The good society,2004,13(1): 21-27.
[17]Irwin A. Citizen eng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 commentary on recent UK experience[J].PLA notes,2001(40):72-75.
[18]Whyte K P, Crease R P. Trust, expertise,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J]. Synthese,2010,177(3):411-425.
[19]Small B, Mallon M. Science,Society, Ethics, and Trust: Scientists' Reflections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2007,37(1): 103-124.
[20]Fischer F. Citizens,exper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21]Stehr N, Mast J L.The Modern Slaves: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J]. Society,2011,48(1):36-40.
[22]Carolan M S. Science,expertise,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J].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6,19(7): 661-668.
[23]Parthasarathy S. Breaking the expertise barrier: understanding activist strateg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omains[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0,37(5):355-367.
[24]Wynne B.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ing and Obscuring a Political-Conceptual Category Mistake[J].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7,1(1):99-110.
[25]Bora A, Hausendorf H. Participatory science governance revisited: normative expectations versus empirical evidence[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06,33(7):478-488.
[26]Dawson E. Mediating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EU and UK: From information-transmission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J]. Minerva,2010, 48(4):429-461.
[27]Pidgeon N,Rogers-Hayden T. Opening up nanotechnology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s: risk communication or ‘upstream engagement’?[J]. Health, Risk & Society,2007,9(2):191-210.
[28]Kleinman D L. Sha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research[M]. Univ of Wisconsin Press,2006.
[29]Kitcher P. Science,truth,and democrac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Longino H E. Science and the common good:Thoughts on Philip Kitcher’s Science, Truth,and Democracy[J].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2, 69(4):560-568.
[31]白惠仁.科学政策与全球正义——一种资助埃博拉疫苗研发的道德辩护[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5):48-54.
[32]白惠仁.STS科学民主化争论的还原与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6(8):1121-1130.
Two Approaches to Research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BAIHui-ren1,2
(1.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49,China; 2.DepartmentofPhilosophy,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10027,USA)
Researches 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have been promoted by social movements from "bottom-to-up" and policy arrangements from "up-to-bottom". Generally there are two basic aspects of the researches on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the reas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limit of it. Based on these two aspects, two approaches have been applied- STS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the reason of democratization, the approach of STS denies truth and objectivity of science and welcome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with an absolute way. Depend on a modest realism, the approach on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tains scientific truth and opposes science autonomy. For the limit of democratization, the former approach allows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all aspects of science; but for the latter, public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agenda setting and knowledge application, and let the scientists reserve the phras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Besides, STS focuses on real democratizing practices and the latter mainly provides an ideal democratic mode.
democratization of science; STS; philosophy of science; well-ordered science
2017-05-1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等资助(2017M610642)
白惠仁(1988-),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讲师,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科学民主化研究。
G301
A
1672-934X(2017)04-0012-10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