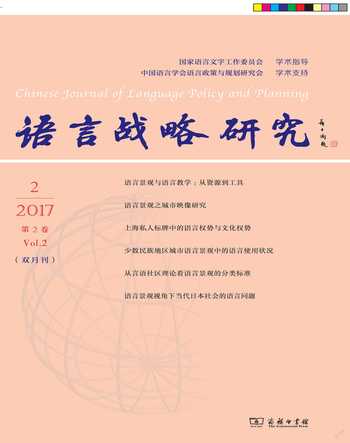旅游专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2017-05-30
散心按语: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动,旅游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流动和文化传播。语言既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媒介和工具,又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如何解读、呈现丰富多样的地域语言文化景观,从而科学合理地进行旅游规划和开发,成为当今旅游学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本期,我们邀请四位旅游专家畅谈语言和语言生活,以飨读者。
语言是最有价值的地域人文景观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 吴必虎
作为一名曾经的理科生,我却一直没有放弃对语言学的兴趣。
1980年9月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因为一些文史知识积累,后来硕士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地理方向的人文地理专业,师从褚绍唐教授。褚先生是《徐霞客游记》研究专家。我在学历史地理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古代旅行考察的重大意义,为后来我转向旅游研究埋下了种子。在广泛的阅读兴趣中,我很关注语言地理学这一小众领域。我撰写硕士论文《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时,在分析地处江淮之间的苏北平原的文化景观演变过程中,专门探讨了苏北方言景观的分布,尝试着用地图表达方法,描绘出在旧黄河(古代淮河)北侧的入声线(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吴语痕迹线(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错地带最北端)和吴语线(江淮官话与吴语的分界线)在苏北平原各地的分布。对方言的兴趣后来扩展到对地名的研究方面。
把语言作为一种区域范围内的人文景观,是我对语言地理和人文地理观察理解的一个混血产物。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我逐步把研究兴趣从历史地理转移到了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在旅游研究的道路上不管走多远,对一个新到访地区,始于当地的语言或方言,且很敏感,这样的体验感受从未消失过。我把对语言的这种感受,不管是表现于物质载体上的印刷物、楹联、牌匾,还是从日常社会交流中听到的口语表述的地方话,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语言景观。通过这个概念,可以系统地表达或阐述一个地区的语言地图、方言地图、地名景观、文学艺术景观……在语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过去主导力量是各种原因产生的人口迁移,而现代社会更为常见的动力无疑来自规模宏大、速度快捷、频率高发的跨文化大众旅游。
语言景观首先是旅游者出游过程中一道不可忽略的靓丽风景。行走在异国的大街小巷之中,街头巷尾悬挂的或霓虹灯闪烁的,或许是我们从未见过的语言文字;耳旁飘过的路人的对话,也许是从未听过的天书。离开导游或接待我们的东道主,我们可能会寸步难行。行走在祖国从未亲临的城市、小镇或边陲村寨,造访一座古典园林、一处名胜古迹,你可能会阅读龙飞凤舞的楹联和书法景观,也可能听到吴侬软语或“南蛮雀舌”之类的客家方言。在云南、贵州或藏羌地区的民族村寨里,伴随着独特的民族乐器的旋律,翩翩起舞之中爆发或涓涓流淌出来的是一段段或优美、或幽怨、或洪亮、或低沉的天籁之声。
语言景观数据分析是研究旅游文化形成过程的一个工具。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中国山地景区文化沉积过程的研究,其中运用到最多的数据搜集及分析角度是历史典籍。特别是文学作品,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语言信息并呈现出旅游景区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在电子化数据还没有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我依靠手工阅读统计,寻求五岳、四大佛教名山、道教三十六洞天在各种文学典籍中出现的频次,统计古代诗人是如何通过入山、游山、寻山、登山、咏山、看山、出山、下山、忆山、思山、爱山、居山、怜山、买山、耕山、烧山等行为与山岳发生丰富的交流活动的,细分出在山地景区中古人构筑的山门、山桥、山井、山阁、山窗、山廓、山堂、山驿、山院、山寺、山居、山斋、山舍、山馆、山亭、山房、山村、山店、山观、山宫、山郭等各式各样的建筑空间。通过以上种种语言沉淀,可以细致观察分析名人赋值和山地诗化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语言(方言)的分析还是进行区域旅游战略和产品规划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对方言、地方戏、地方音乐的观察和谛听,可以了解到福建闽文化所具有的中原文化活态档案馆与汉文化核心元素体验区的特点,从而为区域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与体验提供宝贵的学术理论支持。在闽语系统之内,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都有浓郁的唐宋或之前的中原地区古典文化的基因,特别是闽南语蕴含了古代河洛话丰富的传承。闽剧、南音、梨园戏、莆仙戏、木偶戏、芗剧、高甲戏等闽戏,闽南乐曲、十音八乐等闽乐,也同样保留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元素。用闽南话来朗读或吟唱诗经的《周南·关雎》《召南·摽有梅》《邶风·静女》,才能更有独特而愉悦的文化穿越之感。诗经十五国风分布的地区,基本上以今河南为核心,包括陕西、山西、山东、湖北等与河南接壤地区。当年《诗经》中所描述的景象或意境在当地很多已经荡然无存,但在福建五江(敖江、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二溪(交溪、木兰溪)流经的八闽地区,仍然可以隐约体验到上古民歌的明亮率真之风。
地理考察中的语言密码
《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 单之蔷
我对语言研究的兴趣起源于一次考察。那次我和四川省社科院民族所的李星星教授一起在横断山考察,在怒江峡谷中有一处名为“东坝”的小村庄,我们住在一户藏民家中。李教授问起了他们怎样称呼山、河、牛、火塘等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东西。然后李教授告诉我他们是从丹巴那边迁徙过来的。因为他们说的常用词与丹巴的基本一样。我这才想起李教授一路走来,不停地询问和记录当地人的语言。原来他在借用语言来研究民族的迁徙。此后我开始学习一些语言学的著作,也在考察中用语言学的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
一、可可西里:地名勾勒民族历史沿革
在野外考察探险中,收集和分析地名会让你收获很大,在考察中我发现,地名的分布会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范围或者说民族影响力的范围。
我曾随科考队深入可可西里与长江源,这趟行程穿越新疆塔里木盆地,跨過阿尔金山随后进入西藏,再由西藏进入青海,又沿青藏线再次进入西藏。在考察中接触了大量的地名。这些地名蕴含着大量的信息。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处西藏、青海、新疆交界地带,同时也是藏族和蒙古族两种文化的交会区。这里被称为中国三大无人区之一(另两个是羌塘高原和阿尔金山),但是这些无人区周边是有人类居住和活动的,而真正的无人区,尤其是历史上真正的无人区的范围多大?边界在哪儿?还没有人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地区是多湖地带,湖泊率较高,不亚于江南水乡。我从这些湖泊的名字入手,试图划出真正的“无人区”的范围。我们手中拿着1∶100 000的大比例尺地图,边看图,边考察。
首先我发现从这些湖泊的名字,我们能将历史上藏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的活动范围大致勾勒出来。在西藏与青海交界处分布着很多“错”(在藏语中是湖的意思),如赤布张错等。湖名为“错”的地方,历史上显然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越过两省交界向东北方前进,依然有大量的“错”,比如长江源头姜根迪如冰川附近的雀莫错。再往东北方向推进,就见不到“错”了。有的湖名出现了“诺尔”(在蒙古族语言中是湖的意思),如海丁诺尔、库塞诺尔,有的湖名虽然没有“诺尔”,但是出现了“乌兰”,如西金乌兰湖等。这说明藏族文化的辐射力至此已经减弱。历史上蒙古族的文化影响到了这里。
当我们把这些“错”和“诺尔”一个个标记出来后,我发现还有一些湖的名字划不到上述两类湖泊之中。比如太阳湖、月亮湖、桃湖、荷花湖、仙鹤湖、胜利湖,这些名字没有任何藏族、蒙古族文化的痕迹。这些名字有些是当年的地图测绘者进入这一地区时起的,有些是当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考察队起的。它们原来是没有名字的无名湖。今天可可西里地区还有一些无名湖。
这些湖的名字如此扎眼,它们在历史上不归属任何一个文化辐射区,没有人为它们命名。由此我推断,这些湖所在的区域是历史上真正的无人区。用湖的名字勾勒出真正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范围,这是我考察地名的一大收获。
二、黑戈壁:地名记录人文地理环境
有时,根据地图上的名字就可以分析出那里的地理环境特征。有一次,我去甘肃一个叫“黑戈壁”的地方考察。我摊开一张甘肃省的地图察看,发现甘肃西北部肃北县的一个区域的地名让人感到惊讶。那上面地名并不很多,现有的不多的地名全是××泉、××井。从这些地名我至少可以读出如下信息:(1)这里是干旱威胁到生命的荒漠地区,因为只有泉和井的地方才被命名。(2)这里是无人区,否则地名就不会仅仅是与水相关的泉和井。
后来我们进入了这个干旱区,发现情况果然与我们从地名中读取的信息很相似。我们从敦煌出发走到了边境。那里真是一片干涸之地,见不到一汪水、一条河。途经一个边防军驻地,发现士兵只能依靠打井取水。打井很费劲,不到两三百米深不出水,即使千辛万苦打出水,水的味道也是苦涩的。这里人迹罕至。我很快明白,那些名字里带井或泉的地方,是驼队和商旅的途经之地。他们经过荒漠,唯有依靠这些罕见的水源才能走出去。他们不是沿着两点之间的最短直线走,而是有明显的弯折。这些曲折就是为了找水。
我在地图上发现了几个不是泉和井的地名,其中一个竟有十个字,叫“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后来我了解到“布拉格”在蒙古族语言中也是泉的意思。
对一个地方的命名并非随心所欲,地名的顽强生命力不容小觑。它是人们为自然景观、地理环境打上的深刻烙印。地名一旦形成,便不易更改。甚至入侵者也拿它没办法,当入侵者踏上一片新大陆,也唯有借助当地已有的地名询问、标记和探访。
三、中原:地名坐标凸显国家意识
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在什么地方,周边的人民是否认可,地名在这时体现出人们内心的国家意识。
中国人认同中原是中国的中心,“逐鹿中原”这个成语一方面表达的是各个族群各种集团对中原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原作为中国中心的认可。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来透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黑龙江人、吉林人、辽宁人自称东北人。“东北人”这个称呼,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潜意识都是对“中原是中国的中心”这样一个命题的承认,这里面暗中体现的是一种向心力。
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南方人”和“北方人”这两种称呼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它们都反映了对对方的认可,潜台词是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互补的两个部分,没有了北方人,何来的南方人,反过来亦如此。他们通过对方反证了自己是中国人。
新疆人、甘肃人、青海人自称他们所在地区为大西北;浙江人、福建人、江苏人、上海人认为自己的家乡在东南沿海……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意象地图,即一个划分空间的框架,类似一个坐标系(有时是用二分法: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有时是四分法: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心中这个坐标系的中心也就是原点(这个原点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几何中心,而是文化、政治的中心)在哪里?这是一个国家内在凝聚力的关键。这个心中的坐标系在用语言进行表达时,有显性的部分,有隐性的部分。人们在表达他心中的国家意象空间时,西北、东北、东南、西南,或者說东部、西部、南方、北方这样一些词是说出来的,但是那个原点是不说的,是在心中深藏着的。我把这个国民心中的原点或者说中心称之为国家意识。
地名变更的文化与经济之争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保继刚
地名是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也是独特的文化现象。它蕴含着人类对地理实体的感悟和寄托,是地方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表征了某类社会群体的情感认同。因此,地名承载着区域发展的文化基因,其拟定与变更往往也透视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轨迹。
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地名是一种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用。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调整、追求知名度、发展旅游经济等因素,导致某些地区出现改名争名热,如徽州改为黄山、大庸改为张家界、中甸改为香格里拉、思茅改为普洱、灌县改为都江堰、崇安县改为武夷山市、南坪改为九寨沟县……到头来几城欢喜几城忧?殊不知,中国的地名往往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急功近利的改名可能带来一时的名声大噪乃至经济腾飞,但给文化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旅游经济的收益来补偿的。有个别成功案例,但更多是切断历史文化、扰乱传统的败笔。
在这些改名热中,一部分是为了开发旅游,以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景区(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其中最遭诟病的是黄山市的命名。安徽省名得自安庆府和徽州府的缩写。徽州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藏文化、敦煌文化并称为中国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自北宋正式建徽州府治,其一府六县的格局沿袭了近900年。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这一名称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徽商纵横明清五百年,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派盆景、徽剧、徽菜等影响深远,徽州还是朱熹、胡适、陶行知等中国重要思想家的故里。“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代表了国人对徽文化的认同与想象。
20世纪80年代,黄山进入开发高峰。1983年在黄山北的太平县设黄山市,辖黄山风景区周围。1987年,黄山市扩大至大部分徽州地区,市中心搬至屯溪(原徽州行署所在地),徽州易名为黄山市。从此,关于徽州更名黄山的激烈争论持续至今。
徽州改黄山将徽州文化的载体改没了,黄山只是一处与原徽州仍有相当距离的风景名胜,何以承载徽文化的厚重历史!徽州改黄山不仅改掉了文化,还在空间上造成了混乱。黄山市、黄山区、黄山,游客很难分辨三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没有徽州的徽文化,没有黄山的黄山市。游客对此很有意见,“皖南处处皆黄山,只见牌子不见山?”明明握有“徽州”“黄山”两张牌,却偏偏只打一张“黄山”牌!改名之功过,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
在这些改名大潮中,两种利益驱动不言而喻,政绩的和经济的。有了“名气”更能引凤入巢发展经济,于是各地为了争夺品牌地名乃至名人故里大动干戈。比如,“香格里拉”就是一块跨区域乃至跨国争夺的金字招牌。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畅销,文中“香格里拉”这个虚构的地方成了所有人都希望寻找到的理想王国。最初的寻找可能是某种精神的需要,后来则是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的诉求。印度、尼泊尔,中国的云南和四川都曾为了这个眼球经济概念而争论不休。
“香格里拉”最后落户云南与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洛克密切相关。他曾在丽江研究植物26年,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9篇文章介绍丽江、迪庆、甘孜、木里等地,还写了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的人类学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詹姆斯承认他受了洛克的影响,把小说的背景放在了中国西南。据此,2001年国务院批准将云南省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品牌从此归属云南,旅游收入扶摇直上。四川觉得很吃亏,2004年把亚丁的日瓦乡改为香格里拉乡。这样的改名均缺乏论证,日瓦乡的名字很好听,同时承载了藏族文化的内涵,中甸县也一样。
诚然,有些地名的更改对某个区域的整合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如大庸更名为张家界就显著提升了当地的美誉度和旅游效益,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需要警惕的是,更名并非地方全方位发展的灵丹妙药,如果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传统、历史和文化,无异于杀鸡取卵。作为国家与区域的历史坐标,地名通过地方记忆的再现传承着族群与个体的认同感,倘若丢失了这些基因图谱,乡愁又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而通过地名打造旅游景点,更要并重考虑旅游的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两者乃唇齿相依的关系,忽略文化属性的旅游开发,只会让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面临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语言是中外交流的桥梁
安徽省旅游局原局长 张脉贤
“语言以思维为根据,思维以语言为外壳。”语言,是人们交流、交换、交往、交融的桥梁。没有语言,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发展。在社会上,人类语言是最活跃的因素。语言,在人类进化与发展中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不断传承、不断发展的古国。语言随文字的发展变化而发展,文字也同样随语言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决定了中国语言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曾讲到,“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包容的”。他引用了莱布尼茨的话,“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我们努力吸取各民族的优秀部分才更加优秀,各种语言,也是在各民族交流中得到发展的。中国语言,以其稳定性与继承性、表达内容的丰富性及语调语气的生动性等特征,受到广泛的热爱与赞赏。
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让中国面向世界,国家的飞速发展使得各国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深入中国。语言这个桥梁,也在新的角度与深度,引起各国的重视。四百多所孔子学院,正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
我在部队25年,从事行政工作25年,后半生从事文化与旅游事业。1992年,国家旅游局组团,在欧洲四国进行旅游宣传。在慕尼黑时,城市观光汽车导游通知懂英语的上A车,懂其他语言的上B车。我们促销团,除了我不懂外语外,4个懂英语、4个懂德语,就分别上A、B车。哪知女导游却说“你们中国瞎上……”,驻欧办事处主任据理以驳,说是按你要求上的车,她还不服。上车后打开了译意风,有多国语言,但没有中文。主任问导游:“你知道联合国有几个常任理事国?”导游不作答,主任告诉她:“中、美、英、俄、法。”“你有英语、俄语、法语,为什么唯一没有中国语言?”导游说不出所以然。主任为了她乱批评我们,小小“报复”了她一下。其实,那时中国旅游才起步,国家的主要精力在解决吃饱穿暖上。世界旅游国家排行中国列第104位,根本谈不上国际旅游。后来,中国逐步发展到第41位,继而第13位、前5位,现在,不管是国内游还是国际游,中国都稳居总量第1位。1992年,我去奥匈皇宫参观,只记下了美泉与茜茜公主的电影摄制相关,其他一无所知。当时既没有中文说明,也没有中文导游。2016年4月,我再次去皇宫,无需导游了,既有中文说明又有中国语音录音解说。这样我能更多地了解欧洲历史,奥方也更好地宣传了自己。这样的交流,才有广泛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是语言表达的,为了了解世界,努力掌握语言工具,就成为人们一种自觉行动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软实力强大。在语言运用上中国有非常特殊的条件:有无数首古诗词可借用,有几千年文明史中许多古代名人言论可借用,有一代代人不断创新出来的警句、俗语、俚语可应用。其中,最突出的是智者名言,表达生动,外象多彩,内涵深刻,往往在中国人的讲话中自动涌出。我很喜欢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欧洲的四次讲演,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古为今用,使听者从他讲话中学习“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借此说明了中国人對待战争的态度,大大增强了语言说服力。
汉语经过数千年积累,为今人创造了精确表达与情感表达的条件。我们做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旅游,更是一种人间友谊传递的事业。因此,唤发情感,以情入理,更有作用。我从芜湖调到黄山,首要任务是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开发黄山的旅游价值,把旅游作为产业做起来。黄山,传说是黄帝升天的山,得名与老祖宗轩辕黄帝有关系,是文化山。我推介黄山,就凭借中国文学的助推力。黄山奇、险、俊、秀,但关键在一个“变”字,“他山以形胜,观可止;黄山以变胜,观无穷!”自古黄山云为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云遮雾罩,虚虚实实,若有若无。有时千帆竞发,有时渔舟点点,有时乱云飞渡,有时彩云追仙。黄山年均雨量是全国年均雨量的两倍,更凸显了少女的羞涩之美,再加上立体性气候,一山分三带,上下不同天,“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中国语言的修辞格如拟人、排比、起兴等,也都有助于提高语言的感染力、穿透力。一次,日本四个记者来,一见面就要我写诗。我们在花溪宾馆会面,我即用嵌头诗予以回应:“花溪水涟涟,岛上语绵绵。尧舜正犹在,春风满人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语言表现力强,强在于精粹、形象、感性,而且富有音乐性。借用诗句,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来往中语言上的极大个性。
当中国面向世界之后,世界也在面向中国。中国人会以自己更具人性情感,更能诠释文明古国的内核与外在的语言,向世界传递一种生活、一种交往、一种欢乐。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