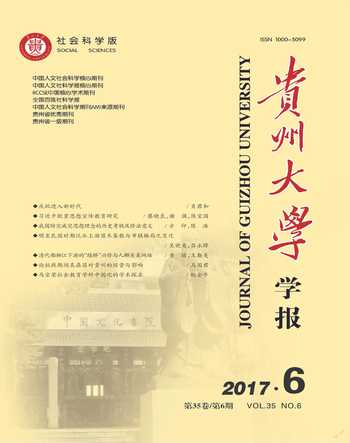清代都柳江下游的“路桥”兴修与人群关系网络
2017-05-30黄瑜王勤美
黄瑜 王勤美
摘要:
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开辟贵州东南部苗疆以来,都柳江流域河道得到进一步的疏通与修治。随着黔桂粤之间水运贸易体系的逐步形成,大量外来商贩和资源涌入都柳江沿岸山区,不但对水、陆交通的连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促进当地士绅家族势力的兴起以及跨地域村寨人群关系网络的建构。本文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峒地村寨“五百和里”内具有象征和实用功能的“路桥”兴修为切入点,去透视山区村寨中的个人及其家族,如何围绕“路桥”的兴修与管理,逐步突破家族世系成员“功德”传承的控制与象征观念,而成为凝聚不同姓氏与村寨人群跨地域的人群关系的网络联结,来因应更大区域之间经济活动的渗透和政治事件的冲击。
关键词:
都柳江;“路桥”兴修;人群关系;网络联结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6-0065-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6.13
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开辟贵州东南部苗疆,逐步设置古州厅、八寨厅、丹江厅、都江厅、清江厅、台拱厅等“新疆六厅”。都柳江水道随着清王朝军事行动和政治控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开辟与疏通,航运的便捷使得黔桂粤三省之间的商贸往来更为频繁。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随着大量外来商贩和商品涌入都柳江沿岸山区,不但对水、陆交通的连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促进当地士绅家族势力的兴起,以及跨地域村寨人群关系网络的建构。
外来商贩与地方士绅家族成员既密切合作又相互竞争,在改善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的交通状况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都柳江沿岸村落中大量的石桥和石板路的兴修。本研究考察都柳江下游峒地村寨“五百和里”,发现其连接水路与陆路交通的“路桥”网络由沿河地带逐步向高坡山地村寨延伸,这一方面得益于外来商民不断涌入山区,外来商品与山区土产的交易活动及影响不断深入高海拔地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经历了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河运经贸繁荣时期,“五百和里”地域社会采取家族继嗣关系凝聚人群力量,抵挡且抑制住外来商业势力的渗透与掌控,而在遭受咸同年间黔桂交界“苗乱”冲击之后,该地域内部各村寨人群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模式,也努力突破以村寨家族的亲缘关系为主体,而逐步走向更广阔的跨家族、跨村寨、甚至跨族群的人群关系网络的沟通与联结。
一、都柳江水道的疏通与黔桂粤经贸的繁荣
都柳江—融江河道是沟通黔桂之间的三条主
要通道之一①
,是珠江水系西江干流黔江段支流柳江的上源河段,都柳江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流经三都、榕江、从江后进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溶江口,与源出湘桂交界金紫山南麓的寻江汇流入融江
(图1)。这条通路不但将贵州东南部与广西中北部紧密相连,而且由于连通珠江水系,使得黔桂粤之间的经贸往来自北宋中期中央王朝“开边拓土”之后就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与联系。
都柳江下段含支流四寨河,北宋时称王江,王江下游为融江,宋代属于广南西路的融州。以融州为中心的融江流域,早在北宋中期,中央王朝积极
向西南地区“开边拓土”之时,就已经通过柳州至梧州之间的西江干流水道与珠江流域的商贸活动产生联系,输出商品以木材、茶叶等土产为主,此外还有朱砂、水银及马匹等等。由于融江流域林木、土产等资源丰富,宋元丰七年(1084),广西经略安抚司得到宋朝廷的同意,于当时隶属于融州的王口寨(后置怀远县)设置博买务,以通“蕃汉互市”。
“(元豐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广西经略安抚司乞于融州王口寨置博买务,通汉蕃互市,乞度僧牒三十道为本,从之。”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影印本),食货38,中华书局,2006年,第5 483页。
宋代王口寨博买务的设置,促进了山区人群以当地土产换取外来商品,使得杉木(也称“沙木”)早在宋代就成为山区人群与外地商贩交易的重要产品。《岭外代答》就有载:“沙木与杉同类,尤高大,叶尖成丛穗,小与杉异,猺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负以出,与省民博易,舟下广东,得息备称。”[1]过去由融江流域采伐而来的大宗木材,主要由水路扎排放运至柳州城中市场集散。[2]茶叶也是融州重要土产,广南诸州可以土茶经商,不受当时榷茶制度的限制。而外地输入的商品则以米粮和食盐为主。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诏令辰州试销粤盐,于是粤盐得以由西江水道上运,经柳江至融州的融江口,再经陆路运至靖州分散贩卖各地。大观四年(1110)编纂的东南盐法,规定辰、沅等州归靖州武冈军官卖盐。[3]
然而,由宋至明,都柳江沿岸的山区资源长期限于本地人群的衣食住行所需,并没有得到更大规模的开发和贸易,当地物产资源与外界市场的交换与流通,也长期限于乡民将日常消费所余带到最近的墟市,进行初级农产品的买卖。如明代隆庆年间怀远旧县治老堡附近的村民就经常到县城贩卖禾苗
〔明〕郭应聘《查参怀远失事人员并议剿处疏》:“缘各猺近县居住,时常徃来卖禾等项”,载《郭襄靖公遗集》(影印本),卷1,第33页,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或是零星的外来行商通过走私食盐以换取山区的木材、土产等物品
〔明〕郭应聘《查参怀远失事人员并议剿处疏》:“有二人贩盐经过,被马知县搜岀,痛责三十重拟,罪罚坡头、板江一带猺人,亦以刑罚,各怀异心。” 载《郭襄靖公遗集》,卷1,第33页。。
明代万历年间“怀远猺乱”平定之后,广西地方官员针对“怀远旧有浔、溶两江,木植盐货等税,往时猺人占据,阻失道,今已退出”的状况,提出“酌定江税,以通商贾”的政策,“奉详请允,该县起抽一年余矣,江滩险阻,舟楫至容江而止,非从轻取,难乎商贾之来集也。”
参见〔清〕龚一清:《善后六议》,载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577页。
这一地区水运贸易的快速发展,还是要等到清代雍正初年,中央王朝欲将都柳江上游当时被“生苗”人群聚居、处于化外之地的“古州八万”纳入版图,派鄂尔泰调集黔桂两省官兵疏通萦绕“生苗区”的都柳江河道。
关于清初都柳江河道的疏通情况,详见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第89-102页。雍正七年(1729),清军进入古州之后,鄂尔泰认识到“都江一水来自黔之都匀,直达广西之柳庆”,为加强对都柳江控制,鄂尔泰“乃调广西官兵克之。平定后,檄文武员弁通勘上下两江,上自三脚屯至三洞,下自诸葛洞至溶洞,
浅滩,辟险,伐巨林,凿怪石,舟楫邮递往来如驶,盖唐蒙故道闭塞数千载,至我朝凿江开道,从古化外之域,今为水陆康庄矣。” [4]乾隆三年(1738)八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又上奏朝廷,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各处修治河道,凿开纤路,以资□运而济商民。”
参见《清高总实录》,卷七十四,乾隆三年八月上辛卯。朝廷不但批准了他的奏请,还下令河道沿岸官民实施疏浚。都柳江下游溶江沿岸的重要商业市镇富禄河段上游河岸边的巨石上,就有乾隆三年(1738)修治当地河道的石刻记录。
参见赵冬莲:《三江文物:三江侗族组织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汇编》,第46页:“此处去平机头巨石,并下川门滩,具已修过。乾隆三年冬。”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鄂尔泰开辟古州“新疆”之后,黔桂之间的都柳江至溶江河道通暢便捷,两省之间的河运贸易也渐趋繁荣。到了乾隆年间,不但有大量的闽粤湘赣等外省商人聚集于西江中上游的桂平、柳州、长安(今属融安县)等贸易集散地,更有不少流动性较强的行商小贩溯融江而上,进入怀远境内都柳江下游的溶江和浔江流域经商往来。[5]
此外,明代中期开始的两广米粮贸易的不断增长,也进一步刺激了山区木材和土产的大量生产、交换和流通。明代中叶以后,已经有不少广东商人前往广西采买米谷,当时“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6]到了清代,两广之间的米粮贸易更是发展迅速,康熙年间广东已“全赖西米接济”
参见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广西巡抚陈元龙奏”,中国第一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94-96页。,而乾隆年间编纂的《广州府志》称:“广东一省,非山即海,田地本少,烟户繁庶,每年食米全仗广西运贩接济。”
参见乾隆《广州府志》,卷五十五,《艺文五》。到了18世纪中后期广西每年向广东供应稻谷可达300万石,粤东商人前往粤西采买米谷的同时,也会将广东的日用百货和手工业品运到广西出售,逐步形成一种两广市场一体化的趋势。[7]由此也刺激粤东商人在返程时能够购买更多当地盛产的米谷和山货土产。林木和土产成为山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如怀远县出产的杉木、茶油、桐油、江南竹都在清代至民国时期成为该县最为大宗的出口产品。
参见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第429-458页。而上游古州境内的场集,在清代咸同“苗乱”爆发之前,“各以其地所出桐、茶、油、棉、布、蜡、靛、果、竹之类交易,而退生计甚饶。”
参见〔清〕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古州厅志》卷一,页十八,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据光绪十四年刻本影印,巴蜀书社,2006年,第300页。
二、清代“五百和里”峒地村寨的“路桥”兴修
五百和里位于都柳江下游河段的溶江
溶江,为今都柳江下游进入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至老堡镇以上河段。宋代文献称为“王江”,明清两代文献称为“溶江”或“容江”,至老堡镇与寻江汇流后始称“融江”。与支流寻江
寻江,又称浔江,源出湘桂交界的金紫山南麓,经龙胜各族自治县向西北流入三江侗族自治县,至今老堡镇老堡口汇入融江。宋代以来,历代文献均将“寻江”与“浔江”混用,为与西江中游干流“浔江”相区别,本文除了在引用文献原文作“浔江”外,在论述时统称“寻江”。交汇旁的山间谷地之中,北面被天鹅岭环抱,南面则背靠南寨山,与老堡乡漾口村洋洞屯隔山相邻,整个聚落内有两条由山间溪流汇合而成的小河——王段河由西南流向东北、和里河则由西北流向东南,两条小河交汇之后再流入寻、溶两江汇流之处的三江口(见图1)。这是中国南岭山脉以南、都柳江沿岸的高原山地中散布的、因河水侵蚀山体而逐渐形成的山间谷地,汉文献中常称之为“峝”“峒”或“洞”,这些“峒”地的地势相对平坦、水源较为充足,因此可以容纳较多人群在此定居,并且从事水稻耕种。
端纳(G.B.Downer)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在多种华南语言(粤语、瑶语、云南话、国语)中,“洞”都是指种水稻的高原山地。转引自薛爱华著,程章灿、叶蕾蕾译:《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三联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我们今天见到的“五百和里”村落内分布着广阔的水田、旱地和山林,虽然海拔较高,但地势相对较低,能够蓄积山间溪流,水利灌溉资源较为丰富,稻田之间散落着多处水塘,适合大量放养鱼、鸭,村民长期以来在山上种植茶子、桐子和杉木等传统经济作物。这些山岭、河道、溪流、水塘的开发与利用,都与当地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溶江和寻江不但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最主要的两条灌溉水源和航运河道,也是沟通湘黔桂三省的重要交通水道。 “五百和里”正好位于两江交汇的水陆交通要道上,从寻、溶两江经水路而来的行旅、商贩或移民,可以在此处停船休息、获取补给、甚至买卖商品,外来的商品和物资也可以在此停留、转运,改由陆路进入到沿岸以及山区的村寨中(见图2)。明清时期,这里就已被视为进入都柳江下游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而且作为商旅、货物的转运点,更成为外来人群与“峒”地、山地人群沟通往来甚至是冲突交融的地带。该地从明代中期“怀远猺乱”被平定之后,逐步发展形成和里(旧称“河里”
“和里”旧称为“河里”,因民国十四年设团务总局于河里,团副徐楞以“河”字未协,更“河”为“和”,因此,民国十四年之前的官方文献都写“河里”。参见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第212页。)、南寨、欧阳、寨贡等四个主要的村寨(见图2)。明末清初以来,这些村落中的各姓氏家族在信仰、婚姻、经济、公共建设、地方防卫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复杂而多元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跨村落共同体,在当地民众中有“五百和里”之称(“五百”即五百户之意)。
寻、溶两江流域在唐宋时期为“古州蛮”所控制,并不在王朝国家的统辖之下,直到北宋崇宁四年(1105),“王江古州蛮”向北宋王朝纳土称臣,这一地区才得以设置怀远军,后来得名怀远县。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影印本)(中华书局,2003),卷114,页3383载:“怀远县,去州治□□□里,本王口寨,皇朝至和初置,崇宁四年三月,因工(王)江古州蛮人纳土,赐名怀远军,八月改为平州,仍置倚郭怀远县。”明朝县令苏朝阳实施“开江通商”政策,
详见〔明〕郭应聘:《征复怀远》,《郭襄靖公遗集》,卷17,第376-381页;〔明〕苏朝阳:《建置怀远始末记》,载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第549-550页。以及清代雍正年间疏通黔桂之间的水运航道,都对都柳江下游地区水运贸易的蓬勃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清代中期之后,大量外来商贩和商品涌入沿江两岸山区,对水、陆交通提出更高要求,当地士绅家族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兴起。外来商贩和地方士绅家族成员既合作又竞争,不但在改善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的交通状况上发挥重要作用,也对村落当中联结新型人群关系的信仰活动的兴起到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村落中大量的石桥和石板路的兴修,以及关公信仰祭祀场所的营建与扩展上。
当地最著名的桥梁就是坐落于和里河与王段河的交汇之处的人和桥,这里是“五百和里”村寨与外部世界往来沟通的水陆交通節点,桥梁一侧就伫立着祭祀本土神明“三王”的重要庙宇三王宫(见图2)。虽然“三王”在当地的信仰体系中是本土神明,但由于在北宋时期得到朝廷皇帝的两次敕封,与王朝国家的政治权威象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8]三王宫创建于明末清初
参见“三王宫,在和里乡南寨,明末清初建,邑廪生杨植盛、庠生荣培元、杨华等,均撰有序。”载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第157页。,当地民间也流传着三王宫是在明代“怀远猺乱”之后,由于旧县城老堡附近的村寨人群被朝廷军队镇压而逃难至“五百和里”居住,而从原建于老堡对面“石门”边的三王庙迁建而来的说法。
人和桥建于三王宫旁,起初只是一座木桥,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欧阳寨杨氏家族士绅杨仁尚之父杨万朝,鉴于“木桥奈遇春夏溪水汹潋,波涛浩瀚涌涨,木桥浮流,往来行人□于阻隔,虽修之不胜修也,共叹褊溪孰能褰裳而涉,于乾隆六十年孟夏仲浣一日,设立造建石桥,功德碑记流传”。
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碑记》,三王宫内碑刻。
值得注意的是,人和桥由木桥改建为石桥的时间,恰好是都柳江中下游水运贸易繁荣兴盛的时期,在都柳江沿岸经商的外省商人纷纷于古州城内建立会馆,古州的江西会馆、广东会馆、两湖会馆、福建会馆等都兴建于这一时期。
参见〔清〕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古州厅志》。据光绪十四年刻本影印,卷之二,页十一,《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9》,第321页,巴蜀书社,2006年。当时三王宫旁的道路和桥梁,已经成为沟通寻、溶两江与黔、楚之间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之一,连当地人都不得不感叹,此处“乃浔溶黔楚之通衢,东至古宜□胜,西至黔省溶河,南至枫木高肇,北至通邑湖南路通大道矣,□地世世感沾焚香点烛,人人敬酬神主,乡村年年庇赖,四时无□,个个叩许灵签,此系神功士农商贾之要路也”。
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碑记》,三王宫内碑刻。
因此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对人和桥的修建和管理,就已经不再是聚居于欧阳寨的杨万朝家族可以单独掌控的,有不少“异姓”人士或群体也希望介入到人和桥的兴修与管理事务当中。道光十六年(1836),杨仁尚发现其父杨万朝在乾隆年间修建石桥时设立的功德石碑被毁:“原思万古不□,奈因旧岁,不知异姓,讵料人心不一,将石碑置摡丢下水,目覩不堪”,于是带领儿子、孙子和曾孙等人,“再造新碑,刻竖庙宇之左,示为久远之计”,立碑再次声明杨万朝建造石桥的功德,并且将该家族成员的子孙姓名“信士杨仁尚偕男杨万超,孙男杨永有、杨永和、杨永富、杨永堂、杨永朋,曾孙杨宏广,杨宏宽、杨宏嵩”全部刊刻在上面,以此表明该家族成员对人和桥的建造功德流传万世。
以上所引碑文见道光十六年(1836)《功德碑记》,三王宫内碑刻。那么,这些杨仁尚眼中的“异姓”究竟意指哪些人呢?而这种将修桥时设立的功德石碑丢入水中的行为,又折射出当时地方社会中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冲突?
三王宫内这一时期树立的多块碑刻,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线索。乾隆五十二年(1787),“异省远贾”联合捐资在三王宫内立碑,宣告当时官府发布的严惩当地“刁民诈逼”远省客商的禁令:
从来上谕下遵,黎民之举,辨奸察诈,客路之逼。故儆恶释良,官司悉是父母,讼朝判父,旅客咸颂皐陶。兹蒙县主奉行陆道□□,檄奉督宪钧命以救远贾,示令许各地方刻碑,以□永远。我等均属异省远贾,曷可吝惜勒石之资,由是各铺踊跃奉公,以成美举。
参见乾隆五十二年(1787)《商人立碑》。该碑现立于三王宫内。
该碑刻内共有三利店、广合店、义盛店等22家远省商贾的名号,他们联合在三王宫内树立碑刻,刊刻当时官府发布的严惩当地“刁民诈逼”远省客商的禁令。可见,当时的三王宫不仅是当地民众重要的信仰祭祀中心,更有多家外来商号的商业贸易活动以其为轴心拓展到周边地区。因此,作为三王宫旁重要通道的人和桥,其所有权与控制权问题也就此逐步凸显出来。道光十六年(1836),欧阳寨士绅杨仁尚立碑纪念父亲杨万朝建造石桥的功德且刊刻家族子孙姓名的行为,一方面显示“架桥”活动在当地人的心中有着“修功积德”的报偿观,并且他们认为此功德能够在“架桥”者的家族成员当中代代传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实已经折射出欧阳寨杨氏家族士绅在这一时期,与所谓的“异姓”人群之间爆发了对人和桥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矛盾与争夺。与都柳江流域相邻清水江流域中,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桥”在地方民众心目中的功德观念和所有权关系变化。[9]这里的“异姓”即有可能指外省客商,也有可能是指“五百和里”聚落内其他村寨的大姓家族。
人和桥所处的位置就在欧阳寨内,而该村寨的杨氏家族也是“五百和里”境内大姓之一,因此欧阳寨杨氏凭借地理位置之便,以士绅杨仁尚为首在一定时期之内控制人和桥的所有权与管理权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即便如此,从后来竖立的多块人和桥重修的捐款碑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了光绪年间,对人和桥的修复与重建已经完全突破了欧阳寨杨氏家族垄断的状况,与欧阳寨毗邻的和里寨杨氏宗族的武生杨成超、杨成杰、杨成美等宗族成员,吴氏宗族的吴振玉、吴绍德、吴朝茂等宗族成员,也纷纷通过捐资修桥的行为,进一步介入到人和桥的重修与管理事务之中。
参见《河鲤二甲捐钱》碑。现立于人和桥上。此外,该桥梁正中供奉的关公神像以及举行的信仰祭祀活动,也折射出外来商民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至今日,人和桥已经成为和里、欧阳、南寨、寨贡四村民众共同捐资维护与管理的对象。
参见1985年《政通人和》碑。现立于人和桥上。
除了人和桥之外,乾隆年间兴建的石桥还有南寨村内的利民桥,其所在位置是王段河流经南寨寨尾一带,即目前南寨下南甲杨氏家族人群聚居之地。据仍存留在南寨戏台下的一块《石桥牌记》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当时由南寨寨尾的十几名杨氏族人共同合力修建了石桥:
建修石桥信士,今我同心乐助共捐出□□□□而做成此桥,以便行人来往万载。寨尾信士杨□□、杨□□、杨□□、楊□□、杨□□……福有攸归。大清乾隆四十六年岁次辛丑二月二十四日立。
参见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桥牌记》。现保存于南寨村“文明台”戏台旁。
该碑文的落款者姓氏共刻为杨姓,下列名字十几人,虽然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但是从碑文内容上分析,应该是目前仍居于该地的南寨下南甲杨氏家族的祖先们合力共同修建了这座石桥。该石桥目前名为“利民桥”,之后也曾得到多次重修,至今仍横跨于流经南寨下南甲(即碑文中提及的“寨尾”)附近的王段河上。
与南寨寨尾的利民桥兴建密切相关的就是旁边的一条商业街——长胜街的修筑(见图2)。据南寨当地老人口耳相传:清朝初年,这里兴起了一条由广东商人居住和贸易的长胜街,就在南寨寨尾的利民桥附近,为了方便转运货物,广东商人还特意在上游的河岸边修建了专门用于卸货的码头,但后来广东商贩与当地居民由于利益问题发生冲突,当地人不再允许外来商贩在此经商,而由本地兴起的商人继续经营,因此在清朝末年,广东商贩逐渐搬离,一部分搬到溶江上游的富禄,一部分则搬到下游的长安口。
据南寨村村民吴XY、杨SY口述。可见,借助对利民桥的修建与控制,南寨寨尾的杨氏家族族人已经积极介入到长胜街的商贸活动之中,外来商贩对地方桥梁十分依赖却难以控制,这使得当地士绅大族能够凭借对桥梁的掌控,而在后来最终取代广东商人在该地的商业地位。
虽然利民桥仍在,但长胜街已荡然无存。而与这条商业街的兴起相关的,还有附近不远处上南甲另一条石板街的兴修,笔者也在南寨村上南甲杨氏家族成员保存下来的《修路碑》中找到一些与当时这条石板街修筑相关的记载:
路通往来,名曰盘乐底,上通南地、下至容江,以及往来黔楚之行,人农商贾莫不径此而旋往。昔之父老不过锄平土而容步,或雨降而坭(泥)滑似油然而难趋,或高下崎岖难以衡步。今有南寨村信士杨传智,目睹往来行人苦于趋步,即捐修银设石板为街,即?造石桥以就地以便,往来行者,人人欣欢儿(而)至,劳辛自休之后,福赐天申。聊俱俚言,永远传序。道光七年岁次丁亥三月谷旦立。
参见道光七年(1827)《修路碑》。南寨杨盛玉藏。
碑文记载南寨村人杨传智,于道光七年(1827)捐银修路,用石板铺设了一条街道,并在旁边也建造了一座石桥,以方便农商行旅往来。据该碑刻的保存者杨传智的后代杨盛玉所言,这条石板街在南寨村的寨头,旁边就建有一座石桥,是南寨通向贵州方向的重要道路。由于20世纪90年代321国道的修建,石板街和旁边的石桥目前都不存在了。但据碑刻所载,此石板街和石桥的修建年代虽然晚于利民桥,但应该仍是在当地商业贸易活动繁荣兴盛之时,为方便村寨内外行人往来、货物运输而修建的。南寨上南甲的杨传智之所以会积极参与南寨村内道路与桥梁的修建,也必然与当时聚居于南寨上南甲的另一支杨氏家族介入到当地兴起的商贸活动中有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在道光年间增修三王宫的活动中,杨传智也是主要参与的“择师”之一。
参见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碑记》,三王宫内碑刻。通过笔者田野调查得知,这些被称为“择师”的人,就是那些在乡村民众的各类拜神、祭祖、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当中,懂得选吉时、看风水、主持仪式或指导当事人完成整个仪式过程的人。当地父老相传,杨传智曾经中过五品武举,但并未外出做官,而是留在家中主持家族及地方事务。作为懂得汉字且熟悉官方礼仪的武举士绅,杨传智及其家族后人对“五百和里”当地“三王”神诞仪式的形成与传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10]
与欧阳寨、南寨两村早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就因河运商贸繁荣而兴起修建桥梁和道路的风潮不同,和里村的杨、吴两大姓氏人群,要迟至光绪年间才在流经其境内的和里河上陆续兴建起两座路桥。
一座是位于和里村头大路旁的玉带迴桥,初建于清代光绪四年(1878),由和里村杨氏宗族的杨金旺、杨成材、杨植长、杨植隆、杨成林,吴氏宗族的吴啟祥、吴永和、吴永德、吴绍礼、吴永昌,覃氏家族的覃广财等倡建。然而,这座桥的兴建不仅得到和里村中杨、吴、覃、程、陈、蓝等各大、小姓家族成员的乐捐和支持,也得到“五百和里”境内的欧阳、南寨、寨贡、寨稿、归斗等小寨,以及溶江流域的光唐、燕子岩、南江、楚南、岑周、良口、寨福、步勾、寨夏、老堡等村,甚至溶江支流猛江(今苗江河)流域的光里、寨大、归洞、地保、铜锣(今同乐)等村民众的捐款资助。
参见光绪四年(1878)杨植盛撰《玉带迴桥》和《百世流芳碑》。此二碑现立于桥内。
玉带迴桥恰好建于和里村口,从它所处的位置和以上碑记来看,其于清代光绪年间得以兴建就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河运交通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浓厚的文武教化和人群关系网络象征。捐款建桥的人也不仅限于该村的大姓家族,而是涉及到周围十几个村寨民众的参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架桥”活动不仅已经完全突破某一大姓家族垄断和掌控的观念,而且允许并且鼓励更多不同姓氏与不同村寨的民众共同参与进来,这一“共修”架桥的行为也折射出和里村的绅民与周边其他村寨村民日常交往的密切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撰写碑文的和里廪生杨植盛正是于清代咸同年间“苗乱”爆发之时在当地倡办团练、抵御“匪患”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1862),“苗匪”由贵州黎平一带兴起,进入从江高曾一带,沿溶江进入广西,烧杀梅寨,扎驻葛亮,杨植盛率领团练一千二百多名,与其他三路团练同至葛亮攻打“苗匪”。
参见(清)杨植盛:《邀集黔粤大团剿匪请发粮弹禀》。载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卷5《文化》,第583页。与此同时,“五百和里”民众还与寻江上游的林溪河、武洛江,以及溶江支流猛江流域的“狪人”村寨以“合款”的形式组成“大款”
“款”是主要流行于黔桂交界地区土著村寨之间的一种联盟关系,可以因为婚姻、政治或军事等多种原因组成不同规模的“款”组织,不同的款组织因为某些突发事件而需要组成新的联盟关系时称为“合款”。关于“款”的历史研究,可参见邓敏文、吴浩:《侗款的历史变迁》,《民族论坛》,1994年,第2期。,共立“款条”,联合抵御“匪患”。
参见《同治二年壬子,苗匪作乱,林溪河、武洛江、猛江约同“五百和里”合为大款,联防御匪序》。载民国《三江县志》,卷5《文化》,第582-583页。同治六年(1866),贵州黔东南地区爆发的“苗乱”再次波及黔桂边界地区,由“苗酋”梁陈黄带领数千人进入古州,然后一路行船由溶江而下从和里到古宜,再顺流而下攻进怀远城内。
参见民国《三江县志》,卷7《大事记》,第650-651页。由于地处溶、寻两江的交汇之地,和里不但遭受焚掳,当地的绅民杨植萃、荣培元等还奉官府之命组织团练“赴溶江征苗”。
参见〔清〕杨植萃《古风一道二十四句》《步原韵》,〔清〕荣培元《赴溶江征苗》。载魏任重修、姜玉笙纂:民国《三江县志》,卷5《杂著》,第603-604页。咸同年间的“苗乱”事件对溶江流域沿岸村寨产生了很大冲击,地方村寨已经无法独立自保,联合组织团练、共同携手抵御“匪患”,是溶江流域沿岸各村寨最终得以免于“苗乱”侵扰的重要原因,这也客观上推动了跨地域人群关系网络的强化与拓展。因此在动乱后,组织团练的和里士绅杨植盛倡建对当地村寨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桥梁,并且得到村寨内外各大、小姓氏民众的支持与帮助,实有安抚和凝聚地域民心之意。这也显示出,随着地方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路桥”也逐步突破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的控制与象征观念,而逐步成为凝聚区域内不同姓氏与跨村寨人群联合与力量的场域。
位于和里河上游竹王宫旁的六合桥比玉带迴桥初建的时间要早,但过去仅是一座供行人往来的木桥,而且早已被洪水冲毁。光绪十五年(1889),和里杨氏宗族的杨成蔚、武生杨成超,吴氏宗族的吴振宗,覃氏家族覃继发、覃继辉、覃继福等人共同倡议新建石桥。该桥现已不存,仅留下《六合桥碑》一块,放置于近年来重修的竹王宫旁,讲述了当时为便于行人渡河而重建桥梁原因。
参见光绪十五年(1889)《六合桥碑》,碑已残损,放置于新建的竹王宫旁。但曾经“代远年湮,霉烂无存”的六合桥为何能在光绪年间得以重建,还要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峒地与山地村寨之间的人群关系来理解。
六合桥建于和里河的上游,虽然远离下游三王宫附近的官商要道,但却是从和里村进入高海拔山地的布糯、燕茶等村落的重要桥梁,也是高山村寨居民下山活动、往来峒地与山地村寨之间的主要通道。而且,该桥也坐落于当地祭祀“竹王”的竹王宫旁。竹王在当地祭祀传统中与“三王”信仰密切相关,竹王是被作为“三王”之父来祭拜的。据民国《三江县志》记载,竹王宫初建于明末清初,
“竹王宫,在和里乡南寨,明末清初建,邑绅吴志能撰有序。”见民国《三江县志》,第369页。然而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河里吴顺能撰写的《竹王宫序》的说法,竹王宫则应该立于明代万历年间,
“神宗万历年间,自立祖庙以来,神恩浩荡,庇佑苍生,即英风之彰灵于故乡者,无愿莫赏其遐迩也。”见吴顺能撰,光绪二十七年(1901)《竹王宫序》,碑刻立于竹王宫内。即“怀远猺乱”平定之后。虽然无法确定竹王宫的始建年代,但是应该与三王宫的兴建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按照河水的流向,竹王宫在地理位置上座落于三王宫的上游,按照“三王”为竹王之子的传说,竹王宫在上而三王宫在下也正好体现了神祗之间的父子关系。但是,以整个“峒”地的地理空间来说,竹王宫其实偏于一隅,位于西北边天鹅岭山脚下,主要是和里、布糯、燕茶等村的民众会来经常此祭拜,而欧阳、南寨、寨贡等村的村民平时则相对较少到此祭拜,而且一直以来主要掌管竹王宫祭祀与管理的是和里村的杨氏和吴氏两大宗族。
由此可见,竹王宫和六合桥主要是联结居于“峒地”的和里村与居于“山地”的布糯、燕茶等村民众之间的往来关系。因此,虽然在神祇传说中竹王是“三王”之父,但是在整个“峒地”区域的和里、欧阳、南寨、寨贡四村的信仰体系中,其地位也只能屈居于“三王”之下。而六合桥的兴建也反映出因商貿繁荣的架桥修路风潮也由两江交汇之处的沿岸“峒地”村寨,逐步向河流上游的布糯、燕茶等“山地”村寨延伸,而和里村的杨氏、吴氏、覃氏等家族人群则成为控制和管理这一通道主要力量。
从该地域的族群区分来看,分布于沿江两岸“峒地”的和里、南寨、欧阳、寨贡等村寨居民清初之后被视为“狪人”,民国时期被称为“侗人”,到了建国后的民族识别中被划分为“侗族”,而布糯、燕茶等分布在“峒地”四周高山地带的村寨居民则长期被视为“苗人”,目前也大部分拥有“苗族”身份。而从和里吴氏宗族的族群构成来看,其目前四个主要的宗族分支中有一支系的家族人群是过去从高山村寨迁居下来的,因此这支吴氏族人与居住在高山地带的“苗人”曾经有着密切的往来关系。
参见吴天良纂修:《和里延陵堂吴氏宗谱》,第43页。和里村民吴DX收藏。而且以和里士绅为首组织的地方团练,不但成功抵御了贵州黔东南地区爆发的“苗乱”的侵扰,更与周边高山地带的“苗人”村寨维持着长期友好的互动与往来关系。这种地域民众之间跨村落与跨族群的互动与交往关系,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光绪年间连接水、路的石桥修建由“峒地”村寨向高海拔的“山地”村寨拓展的契机。
三、结语
清代雍正年间朝廷开辟贵州东南部苗疆以来,都柳江流域河道得到进一步的疏通与修治,随着两广之间的水运贸易网络体系的逐步形成,不但西江中下游的米粮产品大量供应广东,大量外来商贩与移民也开始涌入西江上游的都柳江沿岸山区谋生。以往的研究多从外来商民经商移居的材料与视角,去讨论外来经济、文化对地方村寨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本文则希望以峒地村寨“五百和里”内具有象征和实用功能的“路桥”兴修为切入点,去透视山区村寨中的个人及其家族,如何围绕“路桥”的兴修与管理,逐步突破家族世系成员“功德”传承的控制与象征观念,而成为凝聚不同姓氏与村寨人群的跨地域的人际关系网络联结,来因应更大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的渗透和政治事件的冲击。
三王宫旁人和桥的多次重修,显示出河运经贸活动繁荣促进了具有“修功积德”观念的木桥向更具实用功能的石质“路桥”的修筑,也折射出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架桥”活动引起了外来商民与当地寨民的合作与对抗。而南寨长胜街旁的利民桥及其周围石板路、石桥的修筑,则显示出面对外来商贩与物资的进入,本地家族士绅对经贸活动的积极介入和参与,甚至进一步争夺和把持当地的“路桥”资源,以控制地方的经济与政治局势,最终得以取代外来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光绪年间,以和里杨氏宗族为首倡建的玉带迴桥,以及和里杨氏、吴氏和覃氏等村民联合倡建和管理的六合桥,则显示出咸同“苗乱”之后,凭借组织团练而在地方上显露头角的和里杨氏宗族、吴氏宗族则进一步利用向山地区域修建“路桥”之机,与山地村寨的人群建立起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与联结关系。
从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具有“功德”意义和实用功能的“路桥”,不但随着峒地村寨与河流连接的上下游地区往来日益密切而得以持续兴修,并且逐步成为士农商旅往来峒地村寨、进入高山地带的重要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路桥的倡修者、参与者和捐资者也越来越突破家族、村寨等狭窄的血缘与亲缘关系,而呈现出不同村寨人群之间建立跨地域关系网络连接的需要。
这种凭借“路桥”网络由河道干流向支流推进、由水边“峒地”要路向“高山”村寨的扩展,其承载着的商品流通、人员往来、关系网络也不断由山区平原地域向高山地带不断延伸。这种延伸契机固然与雍正年间以来对都柳江河道的疏通而拉动沿江河运贸易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更与咸同年间“苗乱”之后都柳江下游流域沿岸的人群关系能够突破狭小的家族村寨之亲缘关系,而走向更广阔的跨地域人群网络的沟通与连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这种地域人群关系网络的结构性转变,则是清代雍正年间以来,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策略、区域经贸活动、地域政治事件与地域村寨个人与群体密切互动、共同形塑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4.
[2]柳江县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柳江县交通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335.
[3]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51-55.
[4]爱必达.黔南识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150.
[5]钟文典.广西近代圩镇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71-373.
[6]王世性.广志绎[M].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115.
[7]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8-46.
[8]黄瑜.国家觀念与族群认同:以广西北部“三王”形象演变为中心的考察[J].历史人类学学刊,2015(2):79-114.
[9]钱晶晶.桥:地方社会脉络下的文化符号:明清以来贵州三门塘人的修桥活动及其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1-56.
[10]黄瑜.广西三江和里“三王”神诞仪式形成与传承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31-39.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