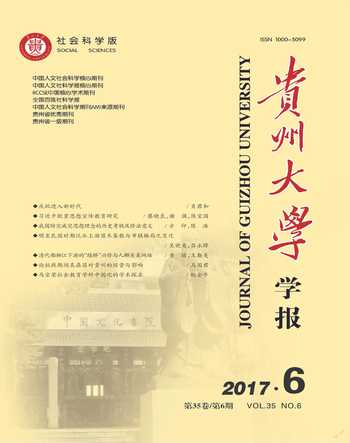“蛊镇”细读:苍生鬼神不等闲
2017-05-30杜国景
杜国景
摘要:
肖江虹的《蛊镇》《悬棺》《傩面》三部中篇,写“蛊镇”方圆数十里的人和事,内容相对独立,但人情相同,风俗相近。三部小说与过去之不同,在于苍生之外,鬼神别有开掘。《傩面》中虔恪的追逼与苟且的动摇即是一种新格磔,三部中篇对死亡意象亦有推进。苍生与鬼神的兼顾,给小说带来了新的气象。
关键词:
“蛊镇”;虔恪与苟且;死亡意象 ;苍生与鬼神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6-0145-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6.25
2013至2016年,肖江虹在《人民文学》接连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分别是《蛊镇》《悬棺》《傩面》,除2015年外,每年一部。“蛊镇”因笃信蛊术得名,讲的是镇上、街上的故事;奇异的“悬棺”风俗,流行于“猫跳河”下游的燕子峡,蛊镇在它的上游;至于傩村,则位于蛊镇往西二十里的滇黔古驿道旁,因敬傩神、唱傩戏、做傩面而得名。三部中篇写的,都是蛊镇方圆数十里的人和事。内容相对独立,但人情相同、风俗相近。最重要的是,苍生之外,鬼神别有开掘。三部小说与过去的写法有了一点不同。过去凸显生的生之艰难,死亡只是结局。现在蛊镇方圆有苍生和鬼神的交集,死就可以是升华。此中意味,可谓新格磔,旧呢喃,苍生鬼神未等闲。
一、虔恪的追逼与苟且的动摇是新格磔
“蛊镇”三部,最该推崇的是《傩面》。《傩面》的主要人物,只有秦安顺和颜素容两个,分别有一显一隐两条叙事线索,显的屬于秦安顺,隐的对应颜素容。小说最精彩之处,是虔恪与苟且这两种意识、两种声音、两种精神境界的交流与对话,类似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最终是秦安顺对傩神的虔恪,动摇乃至摧毁了颜素容患绝症后的苟且。
秦安顺七十有三,是傩村最后一个也是最老的傩师。他从小拜在东村傩师门下学做傩面,一辈子与傩为生。除了雕刻傩面,也能戴上面具为人主持傩仪,通神、通鬼、通灵、通人。整个傩村,举凡敬神、驱鬼、禳灾、祈福的一切傩事,全得靠他。秦安顺保存的傩面很多,如龙王、虾匠、判官、土地、灵童,最金贵是伏羲。每一种面具都有它独特的傩戏功用。小说开始,秦安顺又在赶制一具谷神面具。村长应允他,秋收后可唱一堂丰收傩。其他如许愿傩、还愿傩、解结傩、延寿傩、归乡傩,以及在丧葬仪式上唱的离别傩,为亡灵当引路灵童,对秦安顺来说都不在话下。颜素容是位很要强的年轻女子,因为不甘傩村的闭塞和家庭的贫穷而外出打工。她的梦想本是挣足钱以后,“就在那个能吹海风的城市过完一生”。岂知人算不如天算,自从知道身患绝症,她就有些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的意思,回到家乡自己了却残生。在小说中,颜素容的线索之所以隐而不显者,主要是她进城打工的那部分情节,全是虚写,且交待得非常简略。她在城里做小姐,挣的钱不干净之类,全是暗示,点到为止。重心是回乡之后与傩师秦安顺的交往,那时才有包括个性在内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猛烈碰撞。
因为知道死之将至,回乡后的颜素容变得十分乖张、怪僻、暴戾,不仅对小时候救过自己命的四婆,对来自己家帮父母割麦的乡邻一律恶言相向,就是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她也出言不逊。秦安顺算是爷爷辈的忠厚长者,颜素容明知道他脾气温和、敦朴友善,也偏偏要打上门去,大言不惭地将老人支过来使过去,外带盛气凌人地说三道四,羞辱老人和他已经去世的老伴。好在傩村人心向善、民风淳朴,颜素容这一系列有悖伦理,挑战乡村道德底线的行为,在睦邻敦亲看来是“撞到鬼了”,因此除了父亲,大家对她都不太认真计较。
还有一层原因:傩村人不知道这个女子已身患绝症。其实作为从傩村走出去的女子,颜素容何尝不懂做人的道理呢?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隐瞒说不出口的病情,隐瞒自己在城里见不得人的挣钱经历,用对自己的怨恨,对父母和对乡邻的乖戾,换来恶毒的诅咒,以便在万人唾骂、众叛亲离之后,可心安理得地早点告别人世。说白了,这个女子良知未泯,她这样做,也有自我惩罚的意思!
秦安顺是空巢老人,老伴先他而去,三个儿子,一个夭折,两个进城,他的晚景其实很孤独。是因傩事的缘故,秦安顺在精神上才非常充实。他一生对傩神、傩面和傩戏,可谓立节忠亮,世笃尔行,虔恪机任,守死善道,死而后已。[1]这首先体现在他做人、做事的恭谨和肃顺上。譬如做傩面,不光用料要讲究,在他看来,傩面仅完成雕刻,包括着色、上须,那还远远不够。一定不能缺少将傩面请上神龛、开光度灵的环节。用秦安顺的话说,没有神性的傩面只配称脸壳,拿到县城傩戏面具商店去销售,实际是糊弄人,通神、通鬼、通灵、通人,绝对不成。其次是唱傩戏过程中,附神的真诚与虔敬。不同的傩戏,戴面具之前,上香请神、磕头念咒,这些环节他永远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长久的恍惚依稀之间,秦安顺的错觉、幻觉与真实的生活开始模糊、混淆,阴阳两界之间,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对他已经是家常便饭。最让秦安顺神往的,是当鬼节到来,村子里要唱扫秽傩的时节,伏羲面具一上脸,他竟然可以看见过往的村庄和恋爱中的父母。想想,那是多么奇妙的情景!母亲不再是印象中那个只会站在村头扯着嗓子骂街的粗俗女人,而是由二姑刚带到父亲家相亲的淳朴少女。白天她腼腆、羞涩,夜间却悄悄爬起来,去量父亲鞋子的长度,以便回去给未来的丈夫做鞋。此中的温馨,让秦安顺无限向往。如此这般的死亡,对秦安顺而言,还会是恐惧吗?那一面的世界既然历历在目,他能舍下那副神奇的傩面吗?
与秦安顺不一样,颜素容对死亡实际充满了恐惧。她想以犯众怒的方式换来诅咒,但求速死那点心机,恰恰表明她非常怕死。这其实是个色厉内荏的女子。她的苟且,是被秦安顺的虔恪照出来的另一副面目,是色厉内荏后面真实人格的暴露。虔恪与苟且这两种人生观与人生态度的碰撞由此发生。患了绝症便万念俱灰,回家勉强地活着,过一天算一天,这是苟且的含义,也是颜素容回家后的心态。她之所以有怨结,是以为别人都巴不得她死,都知道她挣的钱不干净。既然如此,她也就破罐子破摔了。颜素容想象过自己的葬礼,也知道来给她唱离别傩的,一定是村里的最后一个傩师秦安顺。不过到过大城市见过一点世面的颜素容并不相信秦安顺的那一套,甚至连这种勾当,她都觉得早该死去才对。
然而,颜素容对傩事、傩师的态度,竟然在和秦安顺相处的过程中,渐渐改变起来。她熬草药,请傩师给她唱解结傩、延寿傩,开始也许只是试一试、闹一闹,反正人都要死了,无聊至极,无权当有,有权当无。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秦安顺对苍生、对鬼神的那种虔恪和恭谨,却慢慢地对她产生了影响。尤其秦安顺对生死的那种敞亮、豁达、乐观,对颜素容实际是一种巨大的冲击。颜素容与秦安顺讨论死亡,以为傩师是因为年过七十才不怕死。秦安顺却告诉她:真正不怕死,恰恰是在她那个年纪,天不怕地不怕,死嘛,不过两眼一闭而已。现在,秦安顺说他怕死了!因为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男男女女,日子久了,生了情了,真要死了,“扔不下,舍不得”,这是大实话。正是在这里,两种意识、两种声音的碰撞开始变得有些和谐起来,不再象开头那样扞格不入、剑拔弩张。这是不同生死观的交流,是虔恪与苟且的交锋,两种叙事的汇合势成必然。故事讲到这里,《傩面》于是便安排了一个极有抒情和象征意味的收尾:秦安顺死后,所有的傩面都成了无用之物,回家操办丧事的儿子只好把它们都烧给亡灵,但此时颜素容赶来,要下了“威严中透着慈祥”的伏羲傩。夜晚,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颜素容突然哭了,那是她回乡之后,第一次为另外一个人哭泣。哭累了,她慢慢地把乌黑的伏羲傩面戴到脸上,屋外立刻传来一个声音:“颜素容,你个砍脑壳的,天都黑了,还不回家吃饭。”那是母亲对童年颜素容的呼唤。跟秦安顺一样,伏羲傩让颜素容褪去了俗世的铅华,找回了童年的纯真。
二、死亡意象有旧呢喃
跟肖江虹的其他小说一样,《傩面》的核心意象仍然是死亡。
肖江虹的笔太硬,笔下的亡灵太多。他的小说,无论短篇还是中篇、长篇,几乎都要死人,不管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总之是各种各样的死法。随之而来的,便是各式各样的葬礼。某种意义上,《百鸟朝凤》就是冲着葬礼写的,因此先有悬念:百鸟朝凤是最难学也最神圣的一支曲子。必须要有象焦师父,或象他的徒弟游天鸣那样一支出神入化的唢呐,才能把葬礼上所有的人吹得泪流满面。而即便如此,百鸟朝凤也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吹的。只有德高望重,或有什么名分的亡灵,或者干脆就是有福气、有运气的死者,唢呐匠才会在他的葬礼上吹响那支令无数人景仰的乐曲。
除开瘟疫和战争(那只是间接交待),《蛊镇》的死者主要有四个。前面两个,一个是会讲《三国》的柳七爷,他想写一部《蛊镇志》,但未完成。另一个是来鹤村的蛊师,他是蛊镇王昌林的同道。两个都是老死,比较正常。两人的死亡只是小说的序曲。到第三个才渐入高潮,那是王四维,他死得比较冤。因為进城打工有了外遇,他老婆赵锦绣气急败坏,从王昌林那里求来一付“情蛊”药粉,以公爹生病为由,将王四维诓得回来,晚上先将“情蛊”符咒悄悄缝入丈夫的夹克衫里层,然后再将本应分三次服下的“情蛊”,一次就给他用了。药下得太猛,结果回到城里做建筑工的王四维神情恍惚,从二十层的高楼跌下来摔死了。接下来,轮到王四维的儿子细崽。这小孩子脸上长有一块神秘的红斑,不痛不痒。王昌林发现:红斑的形状竟然与蛊镇一百年前的地图一模一样,这让他很惶惑,不知是什么兆头。有一天,红斑忽然没有任何征兆就自己散了,而细崽就此一病不起,脸上还慢慢爬满了老人的皱纹。村里翻修蛊神祠,家里给他吃药打针,全没用,最后细崽以一个奇怪的姿式死在了床上。
“蛊镇”系列第二部《悬棺》中写到的燕子峡、曲家寨,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山高峡深水急,山是石漠化地区的悬崖峭壁,峡是深沟河谷,水是河谷中的激流,河滩上全是石头,种庄稼得靠崖顶上燕王宫鹰燕群的粪便。攀崖是燕子峡、曲家寨每个男人打小就必须学会的生存本领。人死了,只能放到悬崖上的棺材中去。村里每个男人都有这样一副悬棺,那是在他十四岁时就请人帮忙移上去的。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死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前两个死者一笔带过,是在燕子峡激流中接棺材时淹死的,未留下名字。来畏难见师傅曲丛水时,觉得他象一个死去的族人,也只是交待而已。悬崖上十一层悬棺里密密麻麻躺着的,是燕子峡的十一代先人。祖祠崖上穿洞中的男女老幼,是躲土匪被烟熏死的全寨亡灵。这些死亡属于历史,在来畏难攀崖过程中出现过两次,他甚至还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但这都是幻觉。唯一与死亡有关的现实场景,属于来畏难的二老祖。当下游水电站要蓄水,燕子峡将被淹没,全寨人都将迁走时,这位从崖上掉下来摔断腿的二老祖不肯走,他说自己老了,要跟祖先留在一起。靠一袭自制的羽翅,他从崖上降下,再从慢慢升高的水面上爬入属于自己的棺材。不过这不算严格意义的死亡。至少在小说结束时,二老祖只是在迎接死亡而已。
不直接写死亡,并不等于偏离死亡意象,那样的隐喻在《悬棺》中通篇皆是:攀悬崖的艰险,梯子岩、刀劈崖、祖祠崖、穿洞、燕王宫的黝黑、湿滑、冰冷,都是一个一个充满暗示的死亡意象,更别说穿洞中还有全寨的亡灵。但小说并未到此为止,一场最激动人心的死亡,是鹰燕群的殉崖,三年才有一次。在连人都不适宜居住的石漠化地区,大约鹰燕也知道用这种方式,来维持族类生命的平衡。
乌云般围着燕王宫盘旋的鹰燕群,在撕心裂肺的呜叫声中逐渐分成了两股,一股开始上升,继续盘旋;一股逐渐下降,笔直飞向对面的悬棺崖,在崖间掉了一个头后徐徐升高,一直升到崖顶。突然,突前的头燕一声尖啸,燕群对着天梯道急速俯冲过来,它们越飞越快,越飞越快,仿佛离弦之箭,在人群头顶拉出一道黑色的轨迹后,天梯道的崖壁上就响起了接连不断的砰砰声响。瞬时鲜血迸射,炸裂的鹰燕顺着岩壁往下掉,仿佛一道宽大的黑色瀑布。
崖下的人群,没一个作声。鹰燕撞崖时飞溅的鲜血雨点一样打在人们的脸上,手上,衣服上。长久满含哀伤的静默,任凭血雨漫天。
多么壮观、多么悲壮的死亡啊!哲学家冷冰冰地告诉我们: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而作家却总能够通过对生命的悲剧感与悲剧意识,剥去死亡的恐怖外衣,把它升华到审美的境界,以完成对死亡的反抗乃至超越。而这一点,也正是肖江虹近年小说一直要完成的主题。
作为“蛊镇”系列的第三部,《傩面》的核心意象仍是死亡。但它已经有了新的蕴含。在过去的死亡意象中,肖江虹主要突出生的艰难,那是属于弱者的悲苦命运,小说因此而包含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包括对人性幽暗的揭示与鞭挞。独特之处,是丧葬文化的反复融入,且各有侧重。《当大事》《阴谋》《求你和我说说话》《天地玄黄》《家谱》《内陆河》《平行线》《我们》《天堂口》《喊魂》都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犯罪嫌疑人》和《百鸟朝凤》最深刻,前者既牵动世态人情,又具有解剖人性的深度。后者的死亡意象则是双关的,丧葬不仅关乎生老病死,同时还指向了一种文化的凋敝和衰落,特别有挽歌情调。
总体上,“蛊镇”系列的死亡意象已经被注入了新的意蕴,肖江虹对生命状态、生命现象、生命价值方面的思考,逐渐超越现实批判层面,而进入到某些形而上的境界,并织入了特定地域的鬼神文化元素。《蛊镇》中,细崽脸上红斑的形状与蛊镇历史地图的暗合,指向了两者的共同命运:蛊师后继无人,那么,包括蛊神、蛊祠及“蛊蹈节”在内的蛊镇文化走向衰落的那一天,细崽也就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这是苍生的事功不力,还是鬼神的时运不济?王昌林之所以要带细崽的亡灵到“一线天”去盼归来的乡亲,或者正是对“天意”有了感悟,有了某种期待的缘故。《悬棺》最精彩,最动人心魄的死亡,是鹰燕群的殉崖,在高耸的悬崖上密密麻麻放了十一层的棺材,穿洞中的老少亡灵,更是惊心动魄的死亡警示。当水库蓄水要将它们淹没时,的确可以引起无尽的想象,毕竟那是祖先们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尽管死亡意象算是一种旧呢喃,但与过去相比,《蛊镇》和《悬棺》的死亡意象已经在修辞上有了很大变化,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到《傩面》就做得更好了。它不光是“蛊镇”系列中最好的一部,而且也是到目前为止,肖江虹最好的一部小说。首先是这部小说的死亡意象更富于哲学意味。在一辈子与傩神打交道的过程中,秦安顺不仅完成了自我的个性塑造与人格修养,而且也清醒地意识到了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真谛,所以他才活得轻松,活得充实。他牵挂人事,也坦然面对死亡,能够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将已经用不着的小石磨送给二婆,把已经答应她的小蔑筛子编妥,亲手给自己挖墓地。无论颜素容怎样出言不逊,他都不急不躁,不温不火,这是一种真性情,也是一种通达的生命哲学。颜素容的苟且之所以会被撼动,正是因为有它的烛照。其次,《傩面》的叙事比《蛊镇》《悬棺》更简洁,更明快,也更有力。小说没有太多的枝蔓,没有太多张牙舞爪的穿插,语言也更干净、更凝炼,意象的蕴含也因此而更丰富。就两个人物,两段历史,两条线索,傩面所承载的意义,在单纯中反而更显得凝重。雕刻的脸庞,写下的是沉稳的性格,凝固的表情,传达的是执着的诉求,它勾連阴阳生死,通过它回到逝去的过往,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逻辑。这样的死亡意象既包含了理性与非理性,也就可以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来去自如了。
三、苍生鬼神不等闲
明显的是,“蛊镇”系列通篇弥漫着一种原始、陌生、诡异、神秘的气息,这跟蛊术,跟奇异的丧葬,跟表情夸张、神情僵硬的傩面有关。说白了也就是跟鬼神有关,跟至今尚未被更多人所熟悉的民族历史与地域文化有关。蛊术、悬棺、傩神,这是西南少数民族典型的文化事象。蛊的记载很早就有。《周易》中的“蛊卦”即起于死难,《素问·玉机真脏论》则把“蛊”训为伤人的大虫,继而蛊即为病,《周礼·秋官庶氏》把用毒虫做的药称为蛊,蛊术由此而来。悬棺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是南方少数民族奇异的丧葬习俗,川南僰人的悬棺较早被发现,属风葬性质。后来就多了,其特点都是利用悬崖裂缝安置棺木,或在悬崖峭壁凿孔,再楔入木桩以支托棺木。名称有崖葬、幽崖葬、崖洞葬、崖穴葬等,至今未统一。“悬棺”一说,来自南朝梁人顾野王,他记的是武夷山:“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2]。傩是一种古老、原始的祭礼,南方和北方均有分布,但以南方,尤其是滇黔、巴蜀、荆楚及江西、安徽等地较为流行。傩祭的举行一般在特定的时间,年头岁尾或不祥之时,目的是驱逐疫鬼,祓除灾邪,针对的是鬼、疫、祟、恶梦、寒气等不祥之物。傩师戴假面,佩玄衣朱裳,即为通鬼神之人。
在南方很多地区,蛊术、悬棺和傩祭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谈蛊色变,悬棺常见,傩事频繁,绝非危言耸听,中国文学对此类题材早有涉及。《蛊镇》所写的赵锦绣向王昌林讨要的“情蛊”,在清代笔记小说中,一位“滇南苗人妇”为挽留与她相好的北方商人就曾用过,结果令人恐怖。[3]“苗”是那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故这里的“苗人妇”不能理解为苗族妇女,但精通此道的那位妇人,却与王昌林一样都有以蛊留人、以蛊留情的本领。据说贵州天柱县的侗族青年男女如爱慕异性,即有采摘生长于路边的“魅草”,制成粉状施放给对方,并念咒语,以俘获对方情感的习俗。[4]再一个例子是沈从文,作为从湘西走出去的作家,他的小说与傩文化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喜欢以“傩”为名。《边城》中的傩送不说了,在《阿丽丝中国游记》里,连那只兔子也叫约翰·傩喜。从文学的角度分析,蛊术、悬棺和傩祭本来就是苍生百姓探问来世、沟通鬼神之举,人、鬼、神之间,一直就被一条情感路线牵连着,只要情真意切,以今生写前世,借鬼神写苍生,无论怎么上天入地、变形幻化都是可以的。
“蛊镇”系列的核心意象既然仍是死亡,往前推进,难免就要探问来世,那是肖江虹过去的小说做得比较少的。“蛊镇”系列在这方面之所以对鬼神有所借径,或许是不再满足于现实的反思或批判,也不再满足于仅仅传达一己的悲剧感与悲剧意识。转向地域,转向民族,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隐喻,对话生命的和人性的奥义。在这里,神奇、虚幻仅属于小说修辞的范畴,重心仍是苍生,是今世,是人的精神和信仰。譬如说,民间对鬼神一直秉持两种不同的心理和态度:驱避和敬畏,前者对鬼,后者对神。“蛊镇”系列没有作这样的区分,因为那里的鬼神与祖先有关。祖先的过往不仅关系子孙的繁衍,更连结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崇拜祖先,在蛊镇周遭就是神圣的宗教。所谓苍生鬼神不等闲,就是指这其中的严肃、恭谨、崇敬说的,任何的轻易、随便、无端、平白,都不仅亵渎祖先,而且是对历史、对现实,对天地万物的不敬。这样的观念既有民族特点也有地域特点,和儒教忠孝仁义传统既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祖先崇拜曾被认为是原始宗教、鬼神信仰而受到排斥。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即以“本于精灵信仰”和“极本返始”加以驳斥,认为那是部落时代的野蛮遗风,“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因此必须彻底肃清“祭献礼拜”,崇拜祖先等陈腐观念。[5]这样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然遭到了质疑,更为流行的是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话。[7]
苍生和鬼神,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既有生,死就一定不可避免。而既然有死亡,也就会有人类对另一个世界的追问,无论它多么虚无飘渺、神秘莫测,鬼神观念由此而生。某种意义上宗教、哲学、文学也由此而生。要了解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定会接触到他的鬼神观念。东西方哲学传统与艺术精神虽存在极大不同,但以鬼神文化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思潮,一直都绵延不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神秘主义亦经历了由挫败到恢复的过程。新时期的文学“寻根”,明显有神秘主义挥之不去的幽灵。[8]19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来临后,一面是众所周知的世俗化及人文精神的失落,另一面,即是不断出现的对神秘主义的文学叩问,即便是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品,也会有这方面的内容。张承志的《心灵史》不用说了,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有此印痕。肖江虹的“蛊镇”系列或者可以汇入这一文脉。对包括鬼神在内的神秘文化,人类在哲学的、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种种分析之外,也需要有文学的阐释,不能套用固有的模式解读这类现象,更何况神秘文化的后面,往往隐含着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而这一点,也正是“蛊镇”系列的突出诉求。王昌林告诉细崽:祖先的家原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输掉一场战争才被迫迁到了蛊镇。祖先们之所以死后愿意被放入悬崖上的棺村而不愿入土为安,是期待有一天打回老家时,后人能把棺材抬回去,埋回老家的土地。这是文学想象,也可能是历史!正因为如此,当祖先留下来的制蛊手艺后继无人时,王昌林才会诚惶诚恐,才会到“一线天”去盼望乡人的重归。燕子峡悬崖峭壁上密密麻麻十一层棺材中躺著的,都是这样的祖先,每年阴历九月初三他们都要受到族人祭拜。从天梯道上跌落摔坏一条腿的来高粱,因为再也爬不上悬崖,进不了那口属于他的棺材,也就成不了未来的祖先,所以他才整日里对救他的人骂骂咧咧。秦安顺迷恋他的傩面,也是因为戴上它就能看见逝去的过往,就能与先人交流。这样的描写,既有历史意识,又有文化传承的焦虑在里头。概括起来说,“蛊镇”及其周遭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除了闭塞、艰苦,还有隐秘的历史,有原生性的信仰和崇拜,有人们自己的精神传统,正因为如此,蛊镇、燕子峡、傩村在外部世界的强大冲击下踽踽前行的身影,才会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边地文化的挽歌,不如说是对巫傩文化、鬼神文化历史境遇的现实反思。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蛊镇》《悬棺》还是《傩面》,都不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小说,不能说肖江虹是在用先锋文学的艺术观处理传统化的民俗,[9]尽管它有很多超现实的情节和场景,也有不少隐喻、借喻、象征和暗示。的确,三部中篇在写法上都有不少新的尝试,但骨子里头,它们都很现实、很传统。在肖江虹小说的死亡意象中,历史从来没有被寓言化,对象征也从来没有作整体化处理。把《傩面》当作先锋文学,大概是从人物的错觉、幻觉,以及王昌林、来畏难、秦安顺这类人物往来于阴阳两界,又有历史与现实的交错等描写中得来的判断。这是没有认真读小说的缘故,《蛊镇》《悬棺》《傩面》大量的这类描写,其实跟大荒山青梗峰,跟太虚幻境一样,全都是在理性和现实的范围内运作的,并没有意识流、魔幻、荒诞、象征那类先锋文学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汉)蔡邑.朱公叔鼎铭[M]//蔡中郎集:卷六.嘉靖二十七年序任城杨贤刊本,17-18.
[2]陈明芳.中国悬棺葬:第2版[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3.
[3](清)王咸.秋灯丛话[M].济南:黄河出版社,1990:264.
[4]刘亚虎.南方民族叙事形态的“欲求”因素与人物结构[J].民族文学研究,2004(4).
[5]周作人.祖先崇拜[M]//谈虎集.上海:北新书局,1936.
[6]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9.
[7]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6-29(20).
[8]易晖.神秘主义在当代文学的挫败与恢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5).
[9]贺绍俊.主观·信仰·先锋性:2016年中篇小说述评[J].小说评论,2017(1).
(责任编辑: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