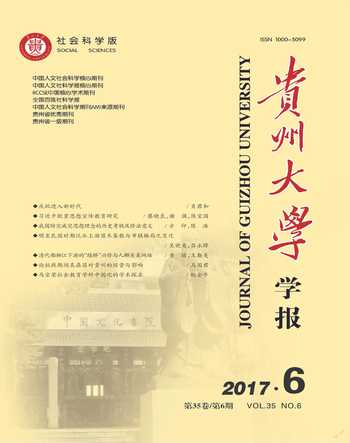肖江虹民俗小说的三重世界
2017-05-30尤作勇
尤作勇
摘要:
肖江虹民俗小说创作的深层叙事结构是自然世界、生命世界和都市世界的三元纠缠,而非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的二元对立。肖江虹的民俗小说创作展现出鲜明的生命本位意识。肖江虹民俗小说创作中生命世界的建构一方面依赖于对自然世界的不断超越,一方面依赖于同都市世界的不断角力。
关键词:
肖江虹;民俗小说;自然世界;生命世界;都市世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0-5099(2017)06-0150-0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6.26
肖江虹的三部中篇小说《蛊镇》《悬棺》《傩面》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2014年第9期和2016年第9期,是肖江虹小说创作最新的成果展示。这三部在时间上连贯而出的小说作品其实在题材、主题和结构上保持了巨大的关联性和承续性,构成了一个三部曲式的小说系列。这三部小说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民俗性征,三部小说的名字本身已经尽显而出,但民俗性无疑并不能涵盖和穷尽这三部小说的全部意蕴。正如施战军在《人民文学》 2016年第9期的卷首语中评价《傩面》时所说:“《傩面》不是一般的民俗小说,‘常之固守和‘变之瓦解已经不能概括作品的诸层面,在这条文脉上,从沈从文、汪曾祺到王润滋,李杭育再到肖江虹,恒久的极致手感的养护,所面对的是世风的粗糙度渐次变大,实情实景几乎已经框不住心神的奔突。”[1]3而透析其小说叙事的内在深层肌理以及各个叙事部件之间幽暗微妙的纠缠关系正是帮助肖江虹的小说创作摆脱简单的民俗标签、回复其本然面目的有效途径。
一、肖江虹民俗小说的三重世界
不管是《蛊镇》《悬棺》,还是《傩面》,其显在的主题都是在展示乡村世界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步沦丧的命运困境,这些民俗题材的小说创作可谓肖江虹吟唱的一曲曲贵州的乡愁之歌。《蛊镇》的主人公王昌林是蛊镇最后一个制蛊师,《傩面》的主人公秦安顺是傩村最后一个傩面师,他们是乡村世界最后的守护者。
虽然肖江虹的这些民俗题材的小说创作并没有正面去展示现代都市的生存样态,但其对乡村世界的“惘惘的威胁”却无处不在:“这几年的蛊蹈节让他窝火,每次节气来临,个个都叹气,还说什么人都走光了,搞给谁看啊?老得都要入土了,谁还有这个闲心啊?”[2]22都市世界无疑是被置放于乡村世界的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文本的潜叙事层面的,这也构筑了肖江虹民俗题材小说的基本叙事格局。
但作为显在的和主体叙事内容的乡村世界在肖江虹的民俗小说里却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肖江虹是一个具有生命本位意识的作家,却并不信奉道家的自然天成。王昌林的制蛊、秦安顺的制傩以及燕子峡男性群体的攀岩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对立于都市世界的生存样态,更是一种对乡村世界自然的、俗世的生存情状的不断超越行为。虽然,肖江虹在他的民俗小说里极为排斥现代化的滚滚浪潮,极力守护生命的纯真美好,但不管是现代化还是本真生命其实都是通过直面自然、超越自然获取到的。作家极力排斥和极力守护的东西竟然拥有一条如此一致的获取途径,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人类生命的曲折幽微。
我们在肖江虹的民俗小说里并没有看到一个像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那样的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乡村世界,相反,肖江虹提供给我们的乡村世界的色调是斑斓的、驳杂的。其实,这正是肖江虹民俗小说创作的难能可贵之处。如果人类生命的美好就是简单的回归自然,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就是白走的。对此更为全面、深刻的观照方式应该是康德式的二律背反观念,乡村与都市之间并不应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是一种需要我们去直面的复杂生命处境。肖江虹的民俗小说把乡村世界分为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极力将其复杂化的行为正可以视为超越简单的对立设置,直面人类复杂生命处境的一种努力。这样,肖江虹民俗小说的深层叙事格局就不再是乡村世界与都市世界的二元对立,而是自然世界、生命世界与都市世界的三元纠缠。
二、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对垒
肖江虹民俗小说里的自然世界和生命世界因为共享同一空间而往往被视为一个世界——乡村世界。其实,肖江虹的民俗小说对二者的区分是十分明确的。在乡村世界未受现代化浪潮侵袭之前,其自足为一个有机世界并不断获取生命依据的途径就是对自然世界的不断超越。
肖江虹的民俗小说所展示的乡村自然世界的基本境况是贫瘠的、凄厉的、粗鄙的。《悬棺》对此的书写最为全面和集中:“墨黑是这里的主色调,要见到绿色,得等到庄稼伸腰,那些大豆玉米在气势汹汹的石堆里格外扎眼,一小块一小块的,最宽的半间屋子大,窄点的八仙桌大小,还有那些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孤孤单单,在风里扭动着孱弱的腰杆,遇上狂风,呼呼几下就倒了苗,挣扎几日后,又慢慢直起了腰。”[3]88土地,因为对自然万物的孕育而几被视为生命的同义语,在这里却处处展示出对生命的拒斥。燕子峡,《悬棺》里的这个失去了土地庇护的村落只有转而祈福于鹰燕的庇护,鹰燕也最终成为了燕子峡的图腾。《悬棺》是肖江虹迄今为止写的最具寓言意味的作品,里面燕子峡的故事几可视为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征程的一个缩影。燕子峡村民一代代前赴后继的攀岩仪式成为人类进行自我超越、不断奔赴新的精神高地的生命写照。
燕子峡的村民面对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物质生存的极度匮乏,实施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救助。既然那个自然的世界无可更改,那么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就只能用人的一腔生命之血去浇筑。我们在《悬棺》里没有看到燕子峡的村民有任何为改变生存条件而直接作用于自然世界的行为,如开荒、屯田等,构成了《悬棺》主体内容的正是那带有浓郁的仪式意味的攀岩行为。不管是攀上燕王宫,还是登上祖祠崖,其实都并不能真正改变燕子峡恶劣的生存境况,却成为了燕子峡村民最大的生命信念。
来高粱,是《悬棺》重点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悬棺》所营建的生命世界的关键人物。虽然“来高粱”的名字指向了一个物质世界,来高粱的一生践履的却是一种纯然的生命意向。他二十三岁在攀岩时从悬崖坠落从而失去了双腿。他非但不感谢那些把他救下的乡邻,反而对他们的救助行为充满了仇恨。他非但不庆幸自己的肉体生命还能够苟活,反而将其视为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因为,在来高粱看来,失去了双腿就失去了继续攀登的希望,也从而失去了生命意义的终极源泉。在小说的结尾,来高粱借助自制的一对翅膀终于飞上了悬棺崖:“在山顶立了片刻,那面剪影双臂展开,鹰燕般从高处飞了下来。风鼓着翅膀,缓缓向水的方向降落。下到水面,起起落落好几回,他终于找到了水面上那口属于他的棺材。爬进棺材,他卸下那对翅膀,两手扶着棺沿,开始唱歌。”[3]116这段描写是肖江虹民俗小说最具魔幻色彩的文字之一,也是其营造的生命世界最为集中的展示。来高粱在自己的生命终结时刻做出的最后一次生命搏击,全然摆脱了物质拘囿、逻辑规范和自然限定,达至了一种最为酣畅淋漓、至真至纯的生命境界。
《傩面》里自然世界与生命世界的分野更为明晰。依仗那一张张傩面,《傩面》里的乡村世界就切分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展现在《傩面》里的自然风貌一如《悬棺》里的那样荒凉和萧瑟:“着实无奇啊!既无绕山岨流的清溪,也无繁茂翠绿的密林。黄土裸露,怪石嶙峋,低矮的山尖上稀稀拉拉蹲伏着一些灌木,仿佛患上癣疾的枯脸。”[1]4而一幅幅傩面则把我们引渡到一个个生命的洞天福地:“拍拍裤腿站起来,秦安顺发现天光悱恻,照模样推测该是黑夜和白昼开始交接的时候,四下泛著幽幽的蓝光。门口那棵死去多年的紫荆树竟然开花了,花串呈淡蓝色,拳头大小的蜜蜂在花间嗡嗡飞着。折出院门,天光大亮。阳光是橘色的,傩村浸泡在一团柔和里,像朝霞里婴儿的脸庞。”[1]7这样的文字,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过,也在鲁迅的小说《补天》里读到过。天地间的这一派祥和、澄明与华美,是人类生命初创之际独有的气象,展示了人类生命最为原初的美好与纯粹。我们虽骇然于《傩面》中那一幅幅小小的傩面使天地陡然变色的强大威力,却仍清楚无比地读到了肖江虹欲借助傩面将生命寂然的自然世界超度成一个生命盎然的生命世界的良苦用心。由此,“傩面”在《傩面》中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俗道具,而成为通达生命澄明之境的生命通道。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无我”视为一种比“有我”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仍然不过是老庄思想在美学论域的一种折光。但再本真、纯粹的生命世界,如果缺少了人的参与,缺少了人的精神意念的融入,就注定会急剧滑落成一个寂然、萧瑟的自然世界。肖江虹无疑深谙于此。在《傩面》中,天地间景色的巨大反转不过是傩面魔力的一个方面,对人之自然生命逻辑的违逆与超越才是傩面叙事的重心所在。在《傩面》的开头,傩村的那些百岁老人们本来形体已经干枯,思维已经混乱,灵性已经丧失,但一戴上傩面,一切立即恢复了元气,他们又得以重返那盎然的生命世界。这是《傩面》的一个序曲,引出的是主人公秦安顺,傩村的最后一个傩面师,在人生暮年犹自酣畅的生命之旅。
如果撇开傩面师的身分,秦安顺就是满布在中国当今农村的最为典型的孤独留守老人形象。新近丧偶,一子已逝,另外二子远赴城市打工,只有孤身一人独守乡村家园。这是一副可以让人生发多少感慨、凄凉孤寂的乡村生活图景啊。这样的乡村生活图景在那些直面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那些作品满储的对乡村文化沦丧的命运忧思更是让人动容。但《傩面》的主题立意却并不于此。《傩面》里的秦安顺面对日渐萧瑟的乡村、日渐老衰的自己已经找寻到了有效克服、全面超越的途径,那就是在由傩面制造的生命世界里沉浸和遨游。所以,秦安顺全然没有一般农村留守老人的暮气沉沉、怨天尤人,而是展现出极为舒展、从容的生命姿态。小说为此所做的一个情节设置让人印象深刻。借助于傩面,秦安顺竟然得以进入到自己父母相亲、结婚、孕育的历史场域。这是对自然逻辑的违逆,却正可以视为对生命逻辑的遵从。一个暮年老人,以对于自己的生命孕育过程的回返摆脱了死亡之神的挟持,从而达致一种原初的生命状态。依靠于此,小说的主题也更为扎实有序地走向对一种纯粹生命形态的礼赞。
三、都市世界与生命世界的角力
在肖江虹的民俗小说中,处在潜叙事层面的都市世界在小说的整体叙事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却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可或缺的。肖江虹民俗小说生命世界礼赞的主题意旨建构除了依赖于对自然世界的不断超越,更有赖于同都市世界的不断角力。肖江虹“民俗三部曲”的这三部作品对于都市世界与生命世界关系的书写依照发表时间的顺序呈现出一种逻辑上的次序性,反映出肖江虹的民俗小说创作在价值立场上渐次发生的某种变化。
《蛊镇》是肖江虹“民俗三部曲”的首篇。蛊镇的最后一个制蛊师王昌林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他也是蛊镇的生命世界最为自觉的守护者。虽然,《蛊镇》中自然世界与生命世界的分野不如《悬棺》和《傩面》那样明晰,小说仍然用了很多细节去着力建构一个丰盈的生命世界。比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王昌林对一个年老体衰的老鼠的喂养和呵护。在这样的叙述中,人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对立关系被彻底颠覆了,老鼠作为人类生存破坏者的形象也被彻底重塑。小说表现出,在作为生命载体的层面上老鼠与人类仍然是无可置疑的同胞关系,年迈的王昌林对一只年迈老鼠的友善行为正是出于一种生命与共的感慨与同情。
在《蛊镇》中,王昌林本人面对都市世界对乡村生命世界的不断侵袭是无可奈何的,他一心要培养一个接班人的计划也是以失败告终的。但小说在对都市世界与生命世界关系的处理上却展现出远超王昌林本人的力道与强度。制蛊与放蛊的本义在《蛊镇》中被刻意叙述成是为了治病救人,其担负的是对乡村生命世界的维护和延续功能。但制蛊与放蛊的行为在小说中却并不是一味和善的,在某些时候仍然会展现出一种戾气,而制蛊和放蛊偶尔展露的狰狞正是对准了都市世界。王四维是《蛊镇》都市世界的中心人物。虽然王四维更为确切的身分只是一个背井离乡、远赴都市的打工者,但却表现出对都市生存的迷恋与坚守。他对妻子的背叛行为其实指向的是对整个乡村生存形态的背叛。他也为他的这种背叛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来自他的家乡蛊镇的一次放蛊让他最终命丧黄泉。虽然小说一再强调都市生存的来势汹汹对乡村生存空间造成了无情的挤压,在这样的叙述中,乡村世界显得如此无助和落寞,却又借助乡村古老神秘的制蛊和放蛊行为对都市世界进行了极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所具有的杀伐之气让人不寒而栗。《蛊镇》的价值立场无疑仍然是守护、礼赞一个纯然、本真的乡村生命世界,只是态度显得过于峻急了,方式显得过于血腥了,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命世界的内在逻辑,以如此暴虐的方式去守护的生命世界必将走向对生命本身的叛离。
《悬棺》里的燕子峡也同样不断地受到外面的现代都市世界的侵袭,而且侵袭的力量也不再仅仅是出自乡村世界内部的一个或几个人,而是挟持着正当理由的强大的官方势力。燕子峡山高地贫,十分不适合人的生存,却是建造水电站的绝佳场所。官方给出的让燕子峡村民集体迁移的理由无疑是十分正当和不容反驳的。虽然官方要侵占的本来只是一个环境恶劣的自然世界,但燕子峡依靠攀岩建造的乡村生命世界却因为和乡村自然世界同享一片空间而受到了巨大牵连,遭遇了灭顶之灾。《蛊镇》中都市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势若水火的简单对立在《悬棺》里却呈现出极为复杂纠缠的关系,正象征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复杂进程。不管是都市世界,还是生命世界,其实都是依靠对自然世界的提升和超越而获取到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不但不是对手,还具备了因为拥有共同的对手而结盟的可能性。当然,它们最终并没有结盟。虽然二者都是在对自然世界的超越中铸就,却仍然遵循着极为不同的逻辑规则。《悬棺》中所呈现的自然世界、都市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复杂纠缠关系,征显了人类最为基本的生存真相。正是基于这样的叙事逻辑,燕子峡的村民虽然在情感上、口头上一再抵制搬迁,还是最终默默地、乖顺地搬离了燕子峡。来高粱成为全村唯一一个没有搬迁的人,他以自己最后绚烂的生命绽放完成了对燕子峡生命世界的最后守护,这也更像是对一个生命世界的祭奠行为。
由《蛊镇》里借助放蛊对都市世界的暴力一击到《悬棺》里对生命世界消失的凄美叹惋,肖江虹的民俗小说创作在对都市世界与生命世界关系的处理上所进行的叙事转移显而易见。但肖江虹对此的叙事探索并没有终止。于是,紧接著《蛊镇》和《悬棺》,又有了《傩面》。
《傩面》虽然像《蛊镇》和《悬棺》一样也没有正面展示一个都市世界,却用了明显多出了很多的笔墨去描写、叙述与都市相关的人与物。《傩面》中的颜素容是一个返乡的女性外出务工人员。在《傩面》的整个叙事布局中,这几乎是一个和秦安顺同等重要的人物形象。肖江虹的民俗小说第一次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情节叙述与人物描写展示与都市世界相关的生存观念与生存样态。都市世界在肖江虹民俗小说叙事格局中所占地位的巨大提升透露的是这样的讯息,那就是肖江虹民俗小说里的都市世界终于不再仅仅是生命世界无可奈何面对的一股生命逆流或者生命世界需要暴力反击的一种邪恶存在,也因此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抽空了所有内涵的空洞干瘪的符号。无疑,都市世界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不需要依托于外物就能够自足的世界。写作《傩面》的肖江虹已然认识到,对于一个纯然生命世界更好的守护方式,恰恰是建立在对现代都市生存足够理解和洞察的基础之上的。
颜素容身患绝症,无奈从都市归来。面对死亡的阴影,整个人陷入到一种狂躁、易怒、乖张的精神状态。虽然已经深陷绝望的漩涡,返乡之初的颜素容却处处展示她作为一个昔日都市闯荡者的优越感。她对自己的父母故作冷漠,对恩人四婆骄傲蛮横,对傩村的最后一个傩面师秦安顺恶毒嘲讽,将一个丧失了生命灵性、生命本真的灵魂尽显而出。颜素容生命情状渐次发生的变化依赖于她对秦安顺的一次次造访。这也是《傩面》在秦安顺自足的生命之旅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情节线索。在二人的交往中,虽然颜素容对秦安顺极尽嘲讽、羞辱之能事,秦安顺对颜素容却只有怜爱和呵护。在这里,生命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关系相比于《蛊镇》可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生命迷失的都市世界,生命世界不但不再欲除之而后快,而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体谅与包容。这种体谅和包容来自于生命世界对都市世界生命与共的感同身受,来自于生命世界对人类生命整体的责任承担。因为,都市世界无论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生命本真,仍然是属于人类生命的内部事件。在生命本位的层面上,都市世界与生命世界不但不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同胞。借助于此,肖江虹民俗小说创作的生命本位主义叙事终于达致一种充分和圆满的状态。在《傩面》的结尾处,颜素容在秦安顺这位暮年老人宽厚、豁达、从容的生命熏染下,慢慢消融了戾气,走向生命的达观,重返生命的本真。
肖江虹的民俗小说创作通过对自然世界、都市世界和生命世界这三重世界复杂纠缠关系的书写为中国的现代乡土叙事传统贡献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样式,也注定会在贵州文学版图乃至整个中国乡土叙事版图上踏下自己鲜明的足迹。
参考文献:
[1]
肖江虹.傩面[J].人民文学,2016(9).
[2]肖江虹.蛊镇[J].人民文学,2013(6).
[3]肖江虹.悬棺[J].人民文学,2014(9).
(责任编辑: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