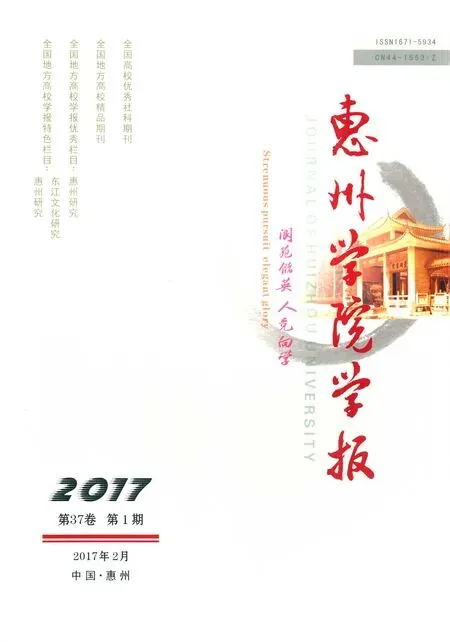论《唐才子传》的纪传体文学批评特点
2017-04-14姚瑶
姚瑶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00)
论《唐才子传》的纪传体文学批评特点
姚瑶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00)
作为第一部专门为唐代诗人立传并讨论其诗歌风格流变、评论作家作品的著作,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一书在元代文学批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其书之纪传体文学批评独具特点,主要体现在作家主体,经人纬时;传论结合,论诗为主;仙风道骨,平等包容等三大方面,而其中又包含若干小而精的内容,极具研究与探讨的价值。
《唐才子传》;纪传体;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原无“文学批评”一词,自南宋以来,刘辰翁、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评点诗、文、小说,评点之学遂兴;后《四库全书总目》列有“诗文评”一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分类于其中可见一斑。作为《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的纪昀更是被朱自清称为“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者[1]”。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则大多源于西方。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而文学包罗广泛,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古往今来的“文学”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文学总是“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各种不同的和社会有联系的现象,文学批评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探讨与研究[2]”。中国的文学批评,虽古无定名,但却实际存在,其发轫于《诗经》时代,至魏晋南北朝而趋于成熟。《唐才子传》以前的文学批评,多注重理论批评和实际批评。纵然是作家作品批评,如钟嵘《诗品》一类,也是以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很少注重作家主体。而在元代文学批评中,则出现了以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为代表的纪传体文学批评之作,创造了以作家批评为主体的纪传体文学批评样式。纪传体本是史书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的《史记》,为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文学家立传,并于传中简评其人品、文品,已开纪传体文学批评风气之先。然而,《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终究以人物传记为主,与以《唐才子传》为代表的纪传体文学批评形式有所差异。《唐才子传》作为一部纪传体文学批评著作,有其自身的批评特点与标准,下面分论之。
一、作家主体,经人纬时
《唐才子传》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批评著作,其书注重作家主体,收录了278位唐代诗人的传记,并附记120人,共计398人。其传记一般包括诗人传略、诗歌简评、诗集流传情况以及附论等内容。所记人物见于《新唐书》者仅100人,其余皆采自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唐人自传、别传、集序、行状、墓志铭等,并从传主诗文及与他人应酬赠答的作品中钩稽事迹,多为第一手材料,价值不可谓不高。辛文房学识渊博,所述颇多卓见,故《唐才子传》一书不仅辑录了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而且成为一部论述唐代诗歌风格流变与品评作家艺术成就的文学批评著作。惟书中所记人物史实多有讹误,正如卷一“引”之所言:“异方之士,弱冠斐然。狃于见闻,岂所能尽?敢倡斯盟,尚赖同志,相与广焉[3]卷第一·引:2”。此类错谬之处,后世学者多有纠正。
以作家为经线,以时序为纬线,经纬结合,共同构成了《唐才子传》的纪传体文学批评网络。在引言中,作者即自述道:“各冠以时,定为先后,远陪公议,谁得而诬也[3]卷第一·引:2”。依据时代先后排序,以求公平允当。又言“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中间大体三变①[3]卷第一·引:1”,论述唐代三百年间诗风的嬗变,大致囊括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唐末的诸多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有评:“大抵于初、盛稍略,中、晚以后渐详[4]523”,其言亦非虚。
(一)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语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5]”。孟子从修身尚友出发,提出“知人论世”之说,要求评论作品必须“知其人”并“论其世”,即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和人品操行,同时也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方法,为历代文艺批评家所遵循。清人汪师韩《诗学纂闻》云:“一人有一人之诗,一时有一时之诗,故诵其诗,可以知其人、论其世也[6]”。文学作品与作家本人的思想倾向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要真正理解并客观地评价文学作品,不可不对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及创作背景有所了解。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7]”。
《唐才子传》在其纪传体文学批评中充分体现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在论及陈子昂时说道:“子昂貌柔雅,为性褊躁,轻财好施,笃朋友之义。与游英俊,多秉权衡。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3]卷第一·陈子昂:33”。了解陈子昂的性格特征、交游情况以及当时的文坛风尚(徐陵、庾信的余风),将有助于理解其诗歌思想与内涵;同时,对陈子昂文学批评所提出的“风骨”论对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也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论及李颀时谈到他:“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3]卷第二·李颀:86”、“工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3]卷第二·李颀:86”、“故其论家,往往高于众作[3]卷第二·李颀:87”。从李颀的性格:疏放简略,对时务不感兴趣;爱好:神仙之道,服食丹砂;交游:乐于结交尘世之外的僧侣道人等特点着手,更能充分理解李颀的诗歌风格及其玄理诗的成就。在论及贾岛时又言道:“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3]卷第五·贾岛:212”、“元和中,元、白变尚轻浅,岛独按格入僻,以矫浮艳[3]卷第五·贾岛:212”。从贾岛科场失利,出家为僧的个人经历,旁及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等人变诗风为崇尚轻挑浅薄的时代风气,到贾岛独辟蹊径,将诗风转入冷僻一途以矫正浮艳风气的做法,对贾岛之“苦吟”及其清新奇僻的诗歌风格更能形成客观的认识与评价。
(二)唯“才”是举
书名为《唐才子传》,其中之“才子”,实指诗人,即引言所谓“擅美于诗”[3]卷第一·引:1者,一如唐“大历十才子”之谓大历年间齐名的十位诗人一般。而所谓“才子”之“才”,也特指诗才。辛文房在对《唐才子传》之传主进行选择时,是唯“才”是举的。辛氏并不看重身份之高低、地位之隐显、人品之高下、职业之贵贱、门第之尊卑、仕宦之穷达等,而是把是否在诗歌创作领域有挺出之才作为唯一的选取标准。从卷一的《宋之问》[3]卷第一·:28和《刘希夷》[3]卷第一·刘希夷:30中即可见一斑。宋之问巴结权贵,趋炎附势,担任科举主考官时大肆收受贿赂,被贬后仍不思悔过,人品极为不堪;甚至恩将仇报,意图将自己亲外甥刘希夷的佳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据为己有,派家丁用土袋将刘活活压死在旅馆里。在了解了这些内容后,辛文房仍为其立传,就是因为他杰出的诗才,连当时的文坛领袖张说都曾赞赏宋之问诗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3]卷第一·宋之问:28”。卷一又有《崔颢》[3]卷第一·崔颢:52小传,其中直言崔颢平时操行不佳,喜欢赌博,嗜好喝酒,娶妻专挑长得漂亮的女子,稍微不合心意随即抛弃,以至换了三四个妻子。但其所作《黄鹤楼》一诗,令李白都不禁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又卷三《苏涣》[3]卷第三·苏涣:155一传中记载,苏涣曾是一个心怀不满之人,四处抢劫钱财,危害一方,巴蜀地区的商人深受其害。后来读书学习,进士及第,却劣习难改,煽动哥舒晃叛乱,本性暴露无遗。但其诗才突出,杜甫即写有与苏涣相互赠答的诗,对其诗歌大加赞赏,称其“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殷殷留金石声”[8]卷二十三·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2014。选取宋之问、崔颢、苏涣等人入传,辛氏文学批评的择人标准可以推知。客观而言,辛文房唯“才”是举的取人标准并无不妥,但在编撰过程中,却把一些声名卓著、才华横溢的诗人弃之不取,实属一大遗憾。诸如姚崇、李邕、郭元振、张九龄等人,在当时都是声名远播的名臣,即依辛氏的诗才标准,也均是名副其实的“才子”。由此可见,《唐才子传》在文学批评的对象选择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时重科举
《唐才子传》在以时代为序的同时,对于同时代的诗人则按照登第先后为序,对其科举情况,诸如登第年份、当年榜首和主考官姓名等更是多加详记,体现出作者辛文房对科举的重视。具体而言,全书收录之诗人大体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唐末的顺序排列,而对于同一时段内的诗人又充分考虑到他们的登第顺序。诸如卷一详述杜审言是咸亨元年(670年)宋守节榜进士,其后的沈佺期则是上元二年(675年)郑益榜进士;卷二中王昌龄是开元十五年(727年)李嶷榜进士,之后的常建则特别注明是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科;卷五的韩愈是贞元八年(792年)擢第,紧接其后的柳宗元则是贞元九年(793年)苑论榜进士;卷六中朱庆馀是宝历二年(826年)裴球榜进士,其后的杜牧则为大和二年(828年)韦筹榜进士。仅此数例,初、盛、中、晚的次序井然,在同一时期内又基本按照登第顺序排列,对登科年份、榜首姓名等亦加以记录。究其原因,是辛氏文学批评重视诗歌与社会、时代的关系。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论及唐代诗歌的时代特点时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9]内编卷四:57”。所谓“气运”,即不同的社会形势、时代精神,由此形成诗歌的不同景象与风貌。在胡应麟看来,诗歌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密切,盛唐、中唐、晚唐诗歌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点,所以得出“文章关气运,非人力”的结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文学的关系或深或浅,不一定成正比,但是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文学作品多少会打上所属时代的印痕,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联系科举情况而对唐代诗人及诗歌进行论述与批评是非常必要且很有意义的。唐代实行科举取士,诗赋为考试内容之一。胡震亨《唐音癸签》言:“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咏所撰,叹惜移时。或复微行,咨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诗之日盛,尤其一大关键[10]”。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深刻影响了唐代文人士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因此,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突出传主的科考情况是极具价值的,也成了此书纪传体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
二、传论结合,论诗为主
《唐才子传》每于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等基本信息之后,论及作家诗作、诗品、诗风及诗评等内容,不拘一格,随感而发,寓文学批评于人物传略之中,可谓是传论结合,而又以论诗为主。《四库全书总目》即云:“是书……体例因诗系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即所载之人亦多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而于功业行谊则只撮其梗概。盖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4]523”。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前言中也谈道:“辛文房则是别具一格的诗评家。他虽为众多的唐代诗人立传,而其主旨却似乎在因人而品诗,重点是标其诗格,而不在于考叙行迹[11]”。辛氏论诗部分,涉及各家诗歌特点及艺术成就,多采自前人旧评,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严羽《沧浪诗话》等,也时出己见。辛文房对众多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综合,在对材料的处理中表现出其唐诗史观及文学批评观点,正如韦勒克《文学理论》所言:“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12]”。
(一)传贵生动
《唐才子传》寓文学批评于人物传略之中,又注重人物小传的生动性、形象性,这也是其书纪传体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辛文房一改对诗人生平经历的死板介绍,尽量通过一些与诗歌创作活动相关联的奇闻轶事乃至细节描写,塑造出一个个形神各异、生动活泼的诗人才子形象。以卷二《王维》为例,通过描写王维才华横溢、精通乐律、书画兼长的特性,记叙其识画、信佛等一系列故事,使王维之才子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令读者对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歌特点及“诗佛”的称号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其中记叙王维随岐王诣见九公主之逸事尤为生动有趣:“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3]卷第二·王维:70-71”。此段文字传神地展现了王维得作解头的始末,无论其事是否属实,它都达到了应有的效果:生动刻画了王维的才子形象,令读者对其诗其乐印象深刻。此事后亦多被诗人引用,几成典实,明清之人更将其事改编为传奇杂剧,广为流传。
(二)论诗尊唐,标榜兴象、风骨、格调、体制、兴趣等
辛文房身为元人而专为唐代诗人立传,并在“引”言中指出:“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于法而能备,于言无所假。及其逸度高标,余波遗韵……端足以仰绪先尘,俯谢来世”,“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以悉全时之盛,用成一家之言”[3]卷第一·引:2,其诗歌崇尚可见一斑。明人胡应麟有言:“元五言古,率祖唐人[5]外编卷六:221”,清人顾嗣立亦言元诗“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13]”,王运熙、顾易生等学者也认为:辛文房生活的时代“正是宗唐之风最盛的时代。其时元统一已近三十年,北方、南方诸种文学思潮已有充分的时间交流融会,《唐才子传》的问世正体现了这一融会的成果[14]”。可见,《唐才子传》论诗尊唐之特点当无疑议。
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5]诗辩:5”,辛文房《唐才子传》论诗以唐为宗,亦标榜兴象、风骨、格调、体制、兴趣等,并以此为其诗歌批评之标准。“兴象”作为唐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意为诗人所创造的包孕其审美意趣,又能引起读者盎然兴会的形象。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提出:“然挈瓶庸受之流……都无兴象,但贵轻艳[16]1”。并以此为标准,评陶翰诗“既多兴象,复备风骨[16]122”;评孟浩然诗曰“无论兴象,兼复故实[16]259”。《唐才子传》取殷璠之评价,谓陶翰“为诗词笔双美,既多兴象,复备风骨[3]卷第二·陶翰:69-70”,其意显然。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实质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文辞的美学要求。以“风骨”评诗论文最完备最系统的著作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其言:“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17]卷六:40”。刘勰将风骨作为情与辞的最高要求,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批评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至唐,陈子昂文学批评高举“汉魏风骨”之大旗,促进了诗风的转变和唐诗的繁荣。其后,唐人论诗多以“风骨”为标准。《唐才子传》亦多处使用“风骨”评论作家作品,如卷一谓崔颢诗“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3]卷第一·崔颢:52”;卷二称“曹、刘、陆、谢,风骨顿尽[3]卷第二·王昌龄:64”;卷三说岑参“与高适风骨颇同[3]卷第三·岑参:110”;卷五谓马异“虽风骨稜稜,不免枯瘠[3]卷第五·马异:204”;卷八称翁绶“音韵虽响,风骨憔悴[3]卷第八·翁绶:351”等等,体现出其对“风骨”的标榜。
“格调”,具体而言分为“格”与“调”两部分,其在文学批评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早以“格”、“调”论诗的是刘勰,但他在使用二者时并无确定的意义,“格”有品格、风格、法式等含义,“调”指乐律、音韵、协调等内容。至唐代,“格”、“调”合为“格调”一词使用,泛指品格、风貌,张乔《宿刘温书斋》即有:“不掩盈窗月,天然格调高[18]”等语。辛文房在其文学批评中亦标举“格调”,如卷一谓储光羲诗“格高调逸[3]卷第一·储光羲:55”;卷三称岑参“诗调尤高[3]卷第三·岑参:110”,称皇甫冉“公自擢桂礼闱,便称高格[3]卷第三·皇甫冉:135”,称独孤及“格调高古,风尘迥绝[3]卷第三·独孤及:138”;卷四说王建“格幽思远[3]卷第四·王建:186”;卷六谓清塞“工为近体诗,格调清雅[3]卷第六·清塞:259”,又谓姚合“格调少殊[3]卷第六·姚合:269”;卷七称陈上美“骨格本峭[3]卷第七·陈上美:300”,又称李群玉“格调清越[3]卷第七·李群玉:330”;卷九谓崔鲁“气象清楚,格调且高[3]卷第九·崔鲁:396”等等。其对“格调”的推崇可见一斑。
“体制”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言:“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17]卷九:57”。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曰:“体制……包括体裁及其在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也包括风格[19]”。《唐才
子传》文学批评亦注重“体制”,其于卷三评皇甫曾诗“体制清紧,华不胜文,为士林所尚[3]卷第三·皇甫曾:137”;卷一论崔颢诗“晚节忽变常体[3]卷第一·崔颢:52”;卷三谓朱湾“格体幽远[3]卷第三·朱湾:157”;卷六谓清塞“工为近体诗[3]卷第六·清塞:259”;卷七称李群玉“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3]卷第七·李群玉:330”。此类评论,不胜枚举,足可见辛氏论诗对“体制”的重视。
“兴趣”也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作为创作命题,首先是由严羽提出的。在《沧浪诗话·诗辩》中,严羽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5]诗辩:6”。“兴趣”要求诗歌创作应有感而发,反对无病呻吟,堆垛陈腐;要即事名篇,兴会神到,诉诸艺术直觉,不假名理思考;表现上要求自然天成,不事雕琢。辛文房论诗亦重“兴趣”,并以此为诗歌之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唐才子传》卷一谓张子容诗“兴趣高远,略去凡近[3]卷第一·张子容:45”;卷三谓张志和诗“兴趣高远,人不能及[3]卷第三·张志和:159”;卷五称姚系“与林栖谷隐之士往还酬酢,兴趣超然[3]卷第五·姚係:219”;卷六称姚合诗“兴趣俱到,格调少殊[3]卷第六·姚合:269”;卷八谓于武陵诗“兴趣飘逸多感[3]卷第八·于武陵:338”等等。这种高远、超然,飘逸、多感的“兴趣”,正是辛氏文学批评所追求和欣赏的诗歌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
(三)体式灵活
辛文房《唐才子传》论诗体式灵活,不拘一格,这也不失为其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总体而言,其论诗体式共有三种:总论、附论和综论。辛氏在篇中“引”言中自叙道:“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汉仙侣,幽闺绮思,虽多,微考实,故别总论之[3]卷第一·引:2”。对于高人隐士、湖海散人、天上神仙、深闺女子四类的诸多人物,于相关传主之后,加以总论。如于李季兰后总论深闺女子刘媛、刘云、鲍君徽、崔仲容等23人;于道人灵一后总论方外工文者惟审、护国、文益、可止等45人。追源溯流,概述特性,所论及之人物,有的另有小传,但仍并立总论,前后照应,避免冗杂。
“引”言又道:“天下英奇,所见略似,人心相去,苦亦不多。至若触事兴怀,随附篇末……附录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3]卷第一·引:2”,对于天下的英才奇士,于某传后心有所感,便附记于该篇之末,共一百二十人,是为附论。如卷二卢象后附论韦述,卷三鲍防后附论谢良弼,卷四畅当后附论郑常,卷五姚系后附论姚伦,卷六杜牧后附论严浑,卷七李宣古后附论李宣远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勃、刘希夷、陈子昂、王翰、王昌龄、常建、孟浩然、杜甫等44人传后另有以“Ο”与传文隔开之综论。如卷一《王翰》传后有综论曰:“Ο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侠,湮没无闻,以其义出存亡生死之间,而不伐其德,千金驷马,才啻草芥。信哉,名不虚立也。观王翰之气,其若人之俦乎[3]卷第一·王翰:40”。这些综论与传主密切相关,整体把握,涉猎广泛,挥洒纵横,各尽其宜。
三、仙风道骨,平等包容
所谓“仙风道骨”,盖指辛文房《唐才子传》之文学批评注重道教与道家思想对唐代诗人的影响。而平等包容,除指其书兼容并包,收入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诸多诗人之外,尤指此书对女性诗人群体的重视。《唐才子传》收录了数量可观的女性诗人,将她们列入“唐才子”一类,其中闪耀的平等包容之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一)道骨仙风
唐朝特殊的宗教政策使得唐代诗人无论在思想或是生活方式上均受到道教及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辛文房《唐才子传》之文学批评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唐朝奉道教为国教,老子更是被唐朝李姓贵族尊为自己的直系远祖,这种做法将道教与道家放在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社会地位上。不仅如此,道教的教义也是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唐朝科举的“道举科”主要考察道教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然要对道教及道家思想有所了解,从而使有唐一代的士子文人深受道教与道家思想的熏染,其诗歌创作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道教及道家思想的烙印。同时,辛文房所处的时代,道教宗派繁盛,全真道进入鼎盛期,茅山宗、太一道、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等符箓道派也继续发展。处在这种特定的宗教文化氛围之中,研究受到道教与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唐代诗人,故而使《唐才子传》一书充满了飘逸奇妙的道骨仙风。
据学者统计,《唐才子传》中“与道教道家有缘者就有113人之多,约占总立传才子的40%[20]”,如此之份额,足可见道教与道家思想对“唐才子”及辛文房的影响。不仅如此,吉中孚、施肩吾、韩湘、方干、陈陶、吕岩、陈抟等传主,在唐五代本就是著名道士,其中吕岩更是唐朝道教祖师、八仙之一,开创了道教全真派南派、北派、东派、西派。辛文房于《唐才子传》中为吕岩等人立传,并于传后有一段对仙道之类诗人的总论,颇为精彩,其言曰:
今夫指青山首驾,卧白云振衣,纷长往于斯世,遣高风于无穷,及见其人,吾亦愿从之游耳。韩湘控鹤于前,吕岩骖鸾于后,凡其题咏篇什,铿锵振作,皆天成云汉,不假安排,自非咀嚼冰玉,呼吸烟霏,孰能至此?[3]卷第十·吕岩:440
辛氏于此纵论仙道类诗人“指青山首驾,卧白云振衣,纷长往于斯世,遣高风于无穷”的生活方式和主体意识,认为他们留下的题咏诗篇音调铿锵,气度不凡,如星河在天上分布一样自然,又绝少雕家琢句、费心思量,然境界尤高。由此表明了辛氏之诗歌宗尚,字里行间均洋溢着道教与道家之仙风道骨,不乏神秘色彩,独具一格。
值得注意的是,辛文房《唐才子传》之文学批评亦体现出儒家与佛教思想之影响。卷中“引”言曰:“夫诗,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移风俗也。发乎其情,止乎礼义,非苟尚辞而已[3]卷第一·引:1”,明确表示自己受到儒家诗论的影响。同时,《唐才子传》一书也多处为僧人及与佛教关系密切之人立传,评论其诗歌作品等,于《道人灵一》传后更是总论诗僧45人,并直言“达人雅士,夙所钦怀[3]卷第三·道人灵一:128”,足见佛教思想之影响。鉴于《唐才子传》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道教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突出,且碍于篇幅,故本文于儒、释二家就不再详论。
(二)平等包容
《唐才子传》之文学批评表现出平等包容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其书不看重传主身份之高低、地位之隐显、人品之高下、职业之贵贱、门第之尊卑等,广收博引,“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4]523”,更重要的是其书对于女性诗人群体一视同仁,兼收并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极少论及女性,大概一方面是由于男尊女卑之封建社会制度及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女性作家之作品不易流传的情况所限。但在唐朝,政府推行较为开明的统治政策,社会风气因此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特点。天宝之前的大唐,犹如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言论的自由促进了思想的解放,独立人格的形成使得人们更勇于传播佳作。同时,唐朝的爱民、重人政策促进了平等思潮的兴起,使得平等待人、尊重女性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在武后当权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民族心态促进了女性作家作品的流传,使其后辛文房收集整理相关材料成为可能。同时,辛文房作为一位“异方之士[3]卷第一·引:2”,其人本身思想观念也较为开放。具有开明思想的辛文房作同样自由开放的唐人的诗歌批评,《唐才子传》中出现数量可观的女性作家作品批评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才子传》之文学批评对女性创作群体态度公允,评价客观,将文才突出之女子列入“唐才子”之类,客观地认识到了长期被忽略的女性群体的创作价值。此等平等包容的文学批评思想极具超越性与先进性,也成为《唐才子传》纪传体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之一。其卷六评薛涛“其所作诗,稍欺良匠,词意不苟,情尽笔墨,翰苑祟高,辄能攀附,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匪其人而弃其学哉[3]卷第六·薛涛:267”,认为薛涛是女流之辈中非同寻常之人物,不能因为她的身份而对其成就摈弃不录。卷八评鱼玄机“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3]卷第八·鱼玄机:346”,认为鱼玄机若为一个男子,一定是能大展宏图,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并于卷二《李季兰》传后总论女性作家23人,认为她们:
率以明白之操,徽美之诚,欲见于悠远,寓文以宣情,含毫而见志,岂泛滥之,故使人击节沾洒,弹指追念,良有谓焉。噫!笔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历观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锦心
绣口,蕙情兰性,足可尚矣。[3]卷第二·李季兰:77-78
对女性创作群体的积极收录和对其才华的充分肯定,无不彰显出《唐才子传》文学批评对女性群体的重视,体现出平等包容的特点,此种文学批评思想的先进性,足以使其百代之后亦能熠熠生辉。
以上从作家主体,经人纬时;传论结合,论诗为主;仙风道骨,平等包容也即纪传主体、批评实践、批评思想三个主要方面对《唐才子传》的纪传体文学批评特点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作为第一部专门为唐代诗人立传并探讨其诗歌风格流变、评论作家作品的著作,《唐才子传》在元代文学批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四库全书总目》评《唐才子传》云:“较计有功《唐诗纪事》,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传后间缀以论,多掎摭诗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艺林。于学诗者考订之助,固不为无补焉[4]523”。王宗炎《三间草堂本序》亦评曰:“继往开来,别具微旨;伸尊黜妄,体裁雅赡;评论得失,好而知恶,非徒诵其诗而不论其世者[21]”。这些评价大体概述了《唐才子传》的特点与价值,论文仅对此作了初步论述,其书之纪传体文学批评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注释:
①三变:“唐诗变体,始自二公”[3]卷第一·沈佺期:26,一变于沈佺期、宋之问;“子昂始变雅正”[3]卷第一·陈子昂:33,二变于陈子昂;“‘大历十才子’。唐之文体,至此一变矣”[3]卷第四·卢纶:161,三变于大历十才子。
[1]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2.
[2]罗志野.西方文学批评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
[3]辛文房.唐才子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251.
[6]汪师韩.诗学纂闻[M]∥清诗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40.
[7]章学诚.文史通义: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81.
[8]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81.
[1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3.
[1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33.
[13]顾嗣立.寒厅诗话[M]∥清诗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4.
[14]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049.
[15]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7]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彭定求.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295.
[1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593.
[20]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249.
[21]周本淳.唐才子传校正:附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336.
【责任编辑:赵佳丽】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graphy of Tang Dynasty's Talented People in Theory of Biograp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YAO Yao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ongqing,China)
As the first book that dedicated to the Tang dynasty poet's biography and discussed its poetry style rheological writings with commentary on writers as well as their works,Xin Wen Fang's book—The Biography of Tang Dynasty's Talented People—had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eve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ograp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Its characteristic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the writer subject and time order;biography combined with comments and comments on poetry is priority;sage-like type and equality as well as inclusiveness.What's more,there are also many small but subtle internal aspects,which are valuable fo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e Biography of Tang Dynasty's Talented People;biographical;literary criticism
I206.21.4
A
1671-5934(2017)01-0081-07
2016-10-10
姚瑶(1993-),女,湖北恩施人,土家族,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