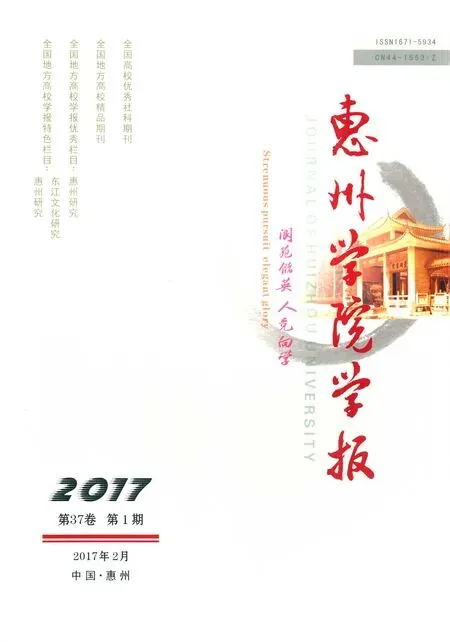清新隽永 言短意长
——《未晚谈》的艺术特色
2017-04-14周少华
周少华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清新隽永 言短意长
——《未晚谈》的艺术特色
周少华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未晚谈》是著名杂文作家林放改革开放时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专栏杂文,代表“林放式杂文”的最高成就。文章通过对《未晚谈》篇什加以梳理、分析,从四个方面归纳出其艺术特色: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拘一格,清新隽永;笔端有情,情感化人;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林放;杂文;《未晚谈》;艺术特色
“未晚谈”是著名杂文专栏作家林放(原名赵超构1910-1992年)自改革开放以后直至去世前在《新民晚报》开辟的一个署名专栏。《未晚谈》则是以在这个专栏上发表的杂文式评论为主的文章的结集,堪称林放在新时期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的结晶,代表“林放式杂文”即新闻性很强的随笔式杂文的最高成就。
林放写专栏杂文受影响最大的是邹韬奋的小言论和鲁迅的杂文。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它抨击敌人,针砭时弊,彰显正义,极具社会批判性和幽默、讽刺风格。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1]”,是“匕首和投枪[2]”。林放早在中学读书时就涉猎鲁迅杂文。作为以精深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形式成为中国政论高峰的鲁迅杂文,必然成为林放专栏杂文写作的标杆。对林放式杂文影响更直接的是邹韬奋的杂文。韬奋的小言论等杂文多为报刊撰写,都是读者第一的观念的体现。它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往往以述见评,观察精准,观点鲜明,分析透辟,平易畅快,非常符合广大受众尤其平民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水准。林放晚年回忆:“那时我经常看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尤其爱看他写的各体文章。我觉得韬奋的文笔容易学,也受读者欢迎,就学着走韬奋的路子。一日一篇,长此下去,就熟练了。写作也成了我生命的组成部分,直到现在,一天不写,好像日子就白过了[3]19”。
严秀(曾彦修)在《林放文章老更成》(1983年9月)中对林放的杂文这样评价:他的文章接触的社会问题面非常广泛,眼光是敏锐的,可以说没有一篇是清闲消遣之作。至于文笔老练,清新流利,生动活泼,思想深度等,我认为也都达到了颇高的或相当的水平[4]。而在林放盖棺论定时,严秀对他又予以高度评价:以为是达到了中国报纸上艺术性短文、评论的新高峰的。……构老文章是报刊上文学思想性短评的一个新高峰[3]109。《未晚谈》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林放曾说:“报上发的千字文,要言之有义,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味,言短意长。大处着眼,小处着笔[5]”。他的写作经验还形成十六字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放手写作,细心收拾[6]”。《未晚谈》许多文章正是成功运用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写作手法,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效果。
《未晚谈》的文章往往对重大的或者抽象的论题通过某个典型事例来论述。《若烹小鲜》说的是文化界“管得过细,统得过死”,主张为其“松绑”。这是涉及国家政策的话题,文章却借用一个生活常识来打比方。小鲜就是小鱼。“烹小鲜”表达的道理是“不扰也”。“你的小黄鱼已放在锅子里了,作料都放好了,这就是了。如果还要拿勺子抄来抄去,那小鱼一定会炒得糜烂不堪,上不了台盘。”“烹小鲜”的对立面就是“管得过细,统得过死”,要烹好小鲜就得“放宽”、“松绑”。《两把刀的比较》重申的是“知识的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承认”这个重要的话题,却是从当时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入手:“某医院里,医生为脑外科病人开刀,如遇超时,每人只补贴八角;而为脑外科病人理发的理发师,每人收费三元。”结论显而易见:“精微的脑外科手术刀取得的报酬还比不上一把剃头刀”。同时,又善于从身边发生的小事情引发大议论。《临表涕零》从一张幼儿园登记表上要求父母填写“有无重大历史问题”的栏目,看到“左”的影响仍然顽固存在于人们头脑当中;《漫画与民主》从可不可以为名流画漫画,指出这是一个社会民主的风气问题;《小仙姑不必脸红》从小仙姑的脸红,触及了小仙姑身边各色人物的嘴脸和灵魂深处;《命题作文》由一份青年工人的试卷答题,指出一种积重难返的文风;《假如茅盾不当部长》从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作家,谈到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大作家当部长,它绝不是茅盾同志的初衷,也不是合理的用人之道”。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杂文常用的表现手法。它对于晚报专栏杂谈以短小篇幅论述重要论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小处着手”,许多宽泛或抽象的杂谈论题,能变得窄小或具体,就能恰当地找到突破口,从一个角度见到全面与本质,从而容易在有限的篇幅里作相对充分的论述。否则就可能陷于“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境地。从“大处着眼”,一些单纯、具体的论题,接触面比较小,就要适当拓宽视野,也就是要围绕客观实际、社会需要来谈,从事物的联系中引出规律性认识,否则就容易沦于“以小见小”、就事论事,削弱论题的普遍社会意义。因而“小”和“大”务必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二、不拘一格清新隽永
杂文的论点除了正确、中肯、鲜明以外,还要求做到不拘一格、清新隽永。这样才能给文章增添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魅力。清新独到的论点,就是要有独到之见,言人之所未言,避免人云亦云,陈陈相因。隽永就是含而不露、耐人回味。隽永的论点往往意味深长、发人深思,能够让人们举一反三。不拘一格,清新隽永,正是《未晚谈》许多杂谈赢得读者喜爱的原因。
《包公与伯乐》就是典型的一例。这篇短论一开头就指出,包公与伯乐本来是早已过去的、应当消逝的“旧观念”,现在又时兴起来是不正常的。在当时“包公热”、“伯乐热”风行的背景下,这个开头本身就颇有点惊世骇俗。接着作者分析了包公、伯乐在旧社会为人们颂扬的原因在于“物以稀为贵”,并亮明自己的态度:我赞美清官,也赞美伯乐,但是决不羡慕包公、伯乐之所以被突出歌颂的那个时代。最后归结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醒人们,还要进一步端正党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此就可以和包公、伯乐告别,彼此相忘于无形。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它发掘出新的深度,为人们观察思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角度。
《未晚谈》中这样的篇章还有不少。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贪污受贿案件,有些人习惯性地说成是“罪犯腐蚀了某些干部”,林放却尖锐地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是在减轻受贿干部的罪责。”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受贿,一个行贿,两者是不可分的统一行为”(《受贿者如何?》)。有人冒充当时(1986年)的文化部长王蒙,写信向某杂志社推荐自己的小说。对此,有人一味斥责冒名者“这是行骗,……这是犯罪”,但他考虑到当时出版界存在的诸如“关系稿”、“认人不认文”的不正之风,而提供另一种比较潇洒一点的处理态度。“建议王蒙不妨把那篇小说拿来读一读,如果确实写得好,就写一封真正的推荐信帮他发表;如果是不够水平的,也可以指点他,劝他以后不必冒名”(《真假王蒙》)。他从《滕王阁序》的故事中,精辟分析出当年王勃之所以能留下这千古名篇,除了王勃不知天高地厚,敢于“抗然不辞”外,主人阎都督也功不可没。他“虽然开头不够大方,后来还是豁达大度”,容忍王勃写下来,“不愧为维护风雅的贤主人”。最后指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允许年轻人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权利”(《王勃不知天高地厚》)。“江郎才尽”这个老话题说的是,任何有才气的作者,脱离了生活,才思就会枯竭。而他却另辟蹊径,认为江淹才尽,是因为“他的才情都用到政治投机上去了”(《“江郎”何以才尽?》)。针对孔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名言,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天下有道庶人议”。他说,允许讨论并不是一种对群众的策略,而是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要求。呼吁形成天下有道而庶人敢议的局面(《天下有道庶人议》)。
以上杂谈都不流于俗套,而能有独到见解,读后又能耐人咀嚼、耐人寻味。这提醒人们要分析、揭示事物本质或问题实质,就应力求概括规律性认识,防止浅尝辄止、就事论事。当然,求“新”的前提是正确,离开客观规律,不顾正确与否一味趋新,那就可能成为奇谈怪论。
三、笔端有情情感化人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评论工作时曾说:“政论应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7]”。古今政论、评论作家,一向讲究文情并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务文体”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笔锋常带感情。鲁迅的随感录和杂文,嬉笑怒骂,爱憎分明。情感成为他们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思想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情感成为一切文字的作品,包括杂谈的重要构成因素,绝不是偶然的。心理学把情感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的体验[8]。它表现为或爱或憎,或好或恶,或喜或怒,或乐或忧,具有特殊的色彩。杂谈在说理的同时恰当带入情感,能拉近人们的距离,引起感情的共鸣,使道理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有些光靠说理难以为人们接受的问题,情感能起到催化剂作用。此外笔端常带感情,也可以给受众以健康、高尚感情的熏陶,净化人们的心灵。所以鲁迅先生历来强调情感的作用,提倡“有情的讽刺”,反对“无情的冷嘲”[9]。
杂文既要服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仅仅通过讲道理说服读者是不够的,还要用感情打动读者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将情、事、理、态完美糅合才能产生好的杂文。林放杂文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正是由于渗透了作者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他以饱蘸感情的笔端匡正时弊,激浊扬清,对社会丑陋现象予以无情抨击,对新事物、新风尚进行热情赞颂。
1982年,当日本某些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教科书中把侵略改成“进入”,美化战争罪犯东条英机时,林放连续写了《“精禽”与“斗士”》、《非其鬼而祭之》、《魔鬼还没有忘记“暴食”》、《还想再来一次“一亿玉碎”吗?》等饱蘸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篇章,驳斥了侵略者的种种行径,高扬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商品大潮的猛烈冲击,贵阳许多教师放下粉笔去做摊主,福建宁德地区八百多名教师弃教经商。对此林放动了真情:“禁不住要为咱们的灵魂工程师放声一哭!”他批评教师们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未能坚守师道的荣誉。但教书每月三十三元跟卖茶叶蛋三天二百多元这个收入上的巨大反差,又让他十分无奈地替教师袒护:“能怪他们弃教从商吗?”他大声呼吁:千万别再贱视知识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吧!而对值得歌颂的人和事他也满腔热情地不惜笔墨:陈燕飞舍身救人,老革命王首道带头让房子,老作家巴金的“思无邪”,老画家丰子恺在批斗声中的“恬静肃穆”,姜玉琴文明服务等。他的《迎春》以“喜看春魂化为燕,千家万户报春来”的诗句作结,抒发自己对改革之春的期盼之情。他在《杂文之春》中热情呼唤:“杂文按其迅速反映社会事象的轻武器特点来说,应当是多产的,密植的。各种报刊对于杂文,不应当搞‘计划生育’。因此还应当广开杂文园地。我们应当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百草园’”。
《未晚谈》的文章有时纵笔所至,议论风生,激起人强烈的情感;有时又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感化着读者。所以林放说“凡是能激动人心的,总是笔锋带有感情的[10]”。笔端有情,情感化人正是《未晚谈》的魅力所在。
四、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未晚谈》常常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说理,生动有趣,浅显易懂,使道理深入人心,引起读者共鸣。
一是形象生动,讲究趣味。杂文需要注重形象性,形象和议论结合得恰当,通过贴切的形象来说理,既可以节省篇幅,又利于把道理讲得透彻。《未晚谈》借助形象化的手法来说明问题的篇章不少。《小猫的屁股可以摸一摸了》是就《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刹一刹保护不正之风的不正之风》而引发感想的。作者议论到:对不正之风的斗争往往没有结果,原因何在呢?因为小猫之后有大猫。有大猫以至老虎撑腰保护,于是“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了”。这里用了“小猫、大猫、老虎”“撑腰保护”“摸小猫屁股”的形象化笔法。接着风趣地评说:“按照党中央机关报这篇文章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刹住保护不正之风的不正之风,那么,至少至少,小猫的屁股总可以摸一摸了。”在《狗年抓耗子》中写道,猫是抓耗子的能手,但也有种种例外。有的是懒猫,养尊处优,打呼噜伸懒腰;有的成了耗子的关系户,睁一眼闭一眼任由耗子横行;有的是瞎猫,只能抓死耗子;还有宠物猫,不仅不抓耗子,而且见耗子就逃。这里形象地描绘了猫儿的各种非常态,暗喻一些掌权者的“失职”“渎职”行径,进而赞美狗抓耗子,说出了“人而不如狗乎”的道理。
二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就是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通俗的论述结合起来,把道理讲得比较浅近,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深入是浅出的前提,浅出是深入后的结果。林放认为把一个艰深的问题,写得生动有趣,人人都看得懂,这是很大的本事。一篇文章,如果要读者皱着眉头,硬着头皮才能读完,那就失败了。要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说理的方式上要有针对性。把要讲的道理,同群众切身的经验,同他们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用他们熟悉的事例和表达方式进行说理论述。《昂纳克搭错了船》评论的是国际时事。前民主德国的领导人昂纳克下台后到苏联避难,德国指控他“下令向越过柏林墙的原东德人开枪”,要拘捕他。而莫斯科的主人居然下逐客令,三番五次要他离开苏联。本来作为苏联的难友、盟友和战友的昂纳克,最后竟像一只破鞋一样被遗弃而成为弃友了。作者由此想起三国时的王朗。华歆、王朗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人要求依附搭船,华歆感到为难,王朗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就让那人上了船。后来强盗追得近了,王朗就要把那人丢弃。华歆说,既然接受了人家的依托,怎么可以因为急难而相弃呢?终于把那人搭救下来。据说,当时的人就凭这件事来评判华、王人品的优劣。接着作者指出,这回昂纳克的不幸,可能就是搭错王朗的船了。进而作评:古王朗只不过见危不救、明哲保身罢了;现代的王朗不仅对难友下逐客令,而且准备拿这个79岁的老头儿作为外交上的见面礼,以便捞得一点好处。这就比得出“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了,昂纳克确实是搭错船了。国际问题一般读者不太熟悉,理解起来也有难度,但王朗的故事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文章并没有对苏联遗弃难友直接评说,但有了王朗的故事,作者的观点不言自明,读者也易于接受。
三是说家常话,亲切自然。要把杂文的内容很好地传达给读者,就必须注重语言的通俗生动。林放曾经到城隍庙泡茶馆,经常深入社会底层,和群众打成一片,注意学习和运用群众的语言。他的杂文从不居高临下,不摆出一副教训人的面孔,而是与读者拉家常话,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说出道理。如前面提到的《昂纳克搭错了船》一文中,“现代王朗”(苏联)、“老头儿”(昂纳克)、“人心不古”“像破鞋一样被遗弃”等家常白话,通俗生动,读来有趣。他在杂文中还经常用到当地方言、群众口语等。例如:把“一部分人”称为“一些些人”,把“害怕”写作“汗毛凛凛”,“受不了”说成“吃勿消”。还有像“拆烂污”、“忙煞”、“一丝丝”等。
林放杂文中还出现不少典故、古语、诗词名句,也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用自己的话说出。《应似飞鸿踏雪泥》中引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后,为便于读者理解,接着就用白话作点复述:拿苏轼的名句来概括这本集子的内容,是说在这些文章里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就像飞鸿在雪泥上印下指爪一样。还有前面提到的《若烹小鲜》,他借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来评论治国方针,希望对文化生活少些折腾,还引用韩非“烹小鲜而数扰之则贼其泽”。在引用后又以烹小黄鱼不能“拿勺子抄来抄去”的生活常识进行了解释,使读者理解起来变得容易。家常话式是林放杂文的显著特色,它使得文章通俗平易,读来亲切自然。
林放在专栏杂文创作中,努力向邹韬奋“明显畅快”的平民式小言论以及鲁迅幽默深刻、富于战斗性的主流杂文学习和借鉴,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专栏杂文切中时弊,感应现实,以小见大,明快浅近,议论风生,雅俗共赏,“栖息于寻常百姓之家[3]276”,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和欢迎。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2]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35.
[3]晁鸥,则玲.赵超构[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9.
[4]严秀.林放文章老更成[M]∥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246.
[5]晁鸥.试论林放杂文[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4):37.
[6]余仙藻.林放和他的杂谈[J].新闻战线,1983(1):35.
[7]毛泽东.组织大家写评论[EB/OL].[2016-09-08].http://www.zhzky.com/news/?13270.html.
[8]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词典[EB/OL].[2016-09-07].http://www.queshu.com/book/14505083/.
[9]王振业,胡平.新闻评论写作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376.
[10]赵超构.说“情”、“理”、“事”、“态”[M]∥探索·新民晚报研究文集.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210.
【责任编辑:赵佳丽】
Delicate and Meaningful——An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alking Before Night
ZHOU Shaohua
(Art Research Academy,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Beijing,China)
Talking Before Night was the essay published in columns of Xinmin Evening News 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t highlighted the ideas of the famous essayist Lin Fang and represented his highest achievements in ar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alking Before Night,this paper summed up it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i.e.think big,start small;delicate and meaningful;richly emotional and deeply felt;vivid and easy to understand.
Lin Fang;essay;Talking Before Night;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267
A
1671-5934(2017)01-0077-04
2016-10-11
周少华(1965-),男,江西莲花人,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剧本创作和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