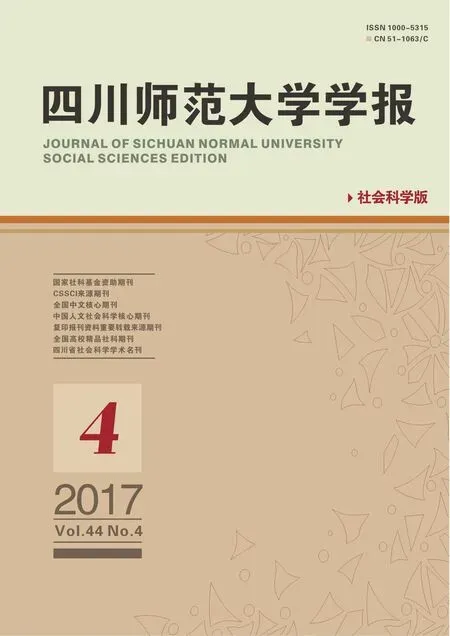教育研究中的田野研究:研究方法还是方法论
2017-04-13段会冬
段 会 冬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与心理学院,海口 571158)
教育研究中的田野研究:研究方法还是方法论
段 会 冬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与心理学院,海口 571158)
田野研究到底算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属于研究的方法论,不但在学生那里存在困惑,在研究者那里同样有着疑虑。研究方法强调的是资料收集与分析技术,并不会对整个研究的原则思之再三,且彼此间具有清晰的边界。而田野研究下辖多种研究方法,而且它强调的不仅是技术,更强调遵循整体性、长期性等研究原则,因此田野研究与研究方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人类学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的转变是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框架下完成的,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田野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又体现了田野研究的基础、开始了从实证主义方法论向人文主义方法论过渡,这两次转变都表明田野研究与方法论也不可等同。要给田野研究一个合理的定位,需要打破“研究方法-方法论”的二元认识结构。田野研究属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之外的“路径范式”,这一定位可以帮助教育学研究逐渐形成“范式思维”,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将田野研究太过“神化”。
教育研究;田野研究;研究方法;方法论;路径范式
田野研究(field research)是基于田野工作(field work)而进行的研究。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撰写一直被视为田野研究最为核心的特征。由于人类学是最有代表性的在“田野”中从事研究的学科之一,且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也普遍地是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式当中借鉴过来的,因此本文的教育研究中的田野研究,指的是我们从人类学那里“借用”过来的田野研究。近年来,田野研究在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的出镜频率颇高,尤其是教育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教育人类学在我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使得教育领域的田野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涌现。然而,笔者身边却不断有学者对田野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方法论”这一事关田野研究性质定位的问题提出疑问。有学者在私下里同笔者交流时也坦承,尽管同意学生以田野研究的方式完成学位论文,但自己仍然对田野研究该如何定位心存疑虑。而不少教育学的研究生在学习研究方法时也对田野研究的定位有着不少困惑:将田野研究视为一种方法,却发现其中包含着多种方法;而将它视为一种方法论,却又觉得它因为具有操作性而不像方法论那般关涉研究的基础。这些情况的存在表明,教育学在借用田野研究的同时对其本身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明确田野研究属于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当中的一种,还是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重新寻找其该有的定位?面对学生的不解与同行的质疑,我们非常有必要对田野研究的“身份归属”问题作出正面回应。
一 田野研究与研究方法的差异
对于田野研究是不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判定,需基于我们对于“研究方法是什么”的认识。然而,研究方法却是一个看似清晰实则被混乱使用的概念。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在翻译西方的一些研究著作时将未用“方法”(method)的许多成果也翻译成为某某研究方法,例如案例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被翻译成“案例研究方法”[1],而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则被译成“质性研究方法”[2]。可以说,不少翻译作品缺少概念的理清,使得“研究方法”这个概念显得格外模糊。实际上,研究方法是在研究中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性技术手段的概称。美国社会学家巴比认为研究方法主要是关于“如何了解事物,而不是知道什么事物”[3]5。“如何了解事物”表明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技术手段。
作为技术手段研究方法的两个特征对我们判定田野研究是否是一种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首先,作为收集和分析材料的技术,研究方法之间具有明晰的“边界”。当一些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的时候,我们无法将这些方法“合并同类项”使之成为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一项研究用了访谈法和问卷法,但不能说我们是通过访谈来进行问卷调查,因此该研究的研究方法只有访谈法或者问卷法。
基于上述特征,田野研究是一种方法的判断恐怕难以成立,因为几乎任何田野研究都不可能只用一种方法就能完成。即便是参与式观察法这一田野研究的“看家本领”,也最多只能说是“主要方法”而非“唯一方法”。在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列举了田野研究经常使用的参与式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等在内的多种方法[4]167-171。尽管作者所列举的方法同当前常见的关于方法的分类略有不同,但是田野研究下辖多种方法已经显而易见。一些经典的研究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上的研究不只限于参与式观察法,他需要不断向当地人询问仪式背后的涵义或者亲属称谓的更多内容,彼时的他势必要用到诸如访谈法之类的其他方法[5]。美国教育人类学者沃尔科特在从事关于校长的田野研究时还引入了文献法,将学校的通知、记录、报告、信件等加以复印以作为自己分析的材料[6]。与之类似的是,美国大学教授丽贝嘉·纳珊为了充分研究“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这一问题,决定自己重回大学一年级,切身体验今天大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认识。而她开展的田野工作也将访谈记录、正式文件、课堂笔记等文献资料作为自己分析的对象[7]。因此,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借助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从事的教育学研究,研究者很难只抱着一种方法而忽视其他方法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
即使我们把田野研究视作某些特定研究方法的组合,我们却发现这些方法的排列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不同研究者从事田野研究未必都会使用下辖的所有方法。例如,谱系调查法主要用来了解被调查对象的家族、婚姻、亲属制度等内容,但在学校教育的研究中,谱系调查法很难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尽管费孝通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多次到访江村、从而使得定点跟踪调查法被许多人所推崇,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事田野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选择定点跟踪调查法。总之,田野研究下辖的多种研究方法之间完全可以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者个人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排列组合。因此,田野研究非但不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也非某些方法形成的固定组合。
其次,研究方法的另一个特征对于我们理解田野研究与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不同也有帮助。通常情况下,研究方法更关注于操作层面,而不会对整个研究所需遵循的原则思之再三。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者无需思考整个研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而是说在总的原则确定下来之后才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选择与使用,因此,原则与方法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之上。例如,当使用访谈法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该在什么时间、地点、向哪些人问哪些问题等技术层面的事项,而不会还纠结于整个研究该遵循怎样的原则。换言之,当研究者的思考触及整个研究的原则时,那么此时的思考便不再停留在具体方法的层面了。基于对这一特征的认识,田野研究显然不是只对该如何操作有所要求,也有一些基本原则或者要求需要遵守。正是遵从的这些原则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将田野研究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
田野研究需要遵守的第一个原则是整体性原则。对田野的研究很容易被那些奇风异俗或者我们乐于看到的东西所吸引,然而,田野研究一贯强调从整体性的角度看待所研究的对象。田野研究应该“给出该文化现象的完全调查,而不是单单挑出那些具有轰动性的、偶然奇特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滑稽可笑、稀奇古怪的现象了”[5]57。因此,田野研究不能像曾经的旅者那样只是怀着猎奇的心态去搜集那些奇风异俗,也不能只是进入学校去寻找符合自己研究假设的证据。田野研究要遵循的第二个原则是长期性原则。要充分地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少不了长时间的介入。通常情况下,田野研究都要求研究者在不少于一年的时间从事“田野工作”。长时间的介入,不仅可以使当地人“不再为我的出现而好奇或不安或者不自然,而我对所要研究的部族生活也不再是一种干扰因素”[5]49,而且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其所研究的社会和族群的各种细节。当然,要真正理解那些地区或族群的生活,掌握当地的语言十分重要。尽管翻译的作用也许不像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常常会把文本的所有重要特点剥夺净尽”[5]89,但转译的过程中信息的遗失,或者意思表达的不到位、不传神等问题恐怕很难避免。因此,研究者能否真正掌握当地的语言也成为其所做的研究是不是地道的田野研究的重要指标,这也是田野研究必须遵守的第三个原则。
除却整体性、长期性和对当地语言的要求之外,田野研究还须遵守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原则。主位强调的是被研究对象对自己文化或社会的看法;客位则是指研究者作为局外人客观地看待所要研究的对象。在教育研究领域,主客位之间时常存在错位的情况。例如,关于民族地区学校开发的校本课程的特色,一线教师可能更加看重通过增加本民族的内容凸显课程的特色,而研究者则可能更加看重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形成学校的文化[8]135-143。换言之,只有研究者设身处地成为局内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才能在事后的分析与理论建构时不致过于主观臆断或者盲目。田野研究的上述原则,都不是某种特定的方法需要遵循的。
综合而言,田野研究既不是以单一方法完成的研究,也不是纯粹的搜集资料的技术,因此,认为田野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二 田野研究与方法论的距离
既然田野研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那么是否意味着它是一种方法论呢?同样,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首先明确“方法论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存在两种对于方法论的理解。哲学界对于方法论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认识:“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和理论体系。”[9]2换言之,世界观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认识,而方法论则更加关注“如何认识世界”。哲学界认为方法论事关“如何认识世界”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将对方法论的讨论引向科学层面。另一种是科学层面的认识,即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式,而是不同的方式何以“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法论关注的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之所以成立的充分理由,而不是“对现有方法合理性确认以后的具体运用”[10]13。当我们围绕观察时是否需要单向玻璃或者访谈时该如何追问等具体问题展开思考时,便不是在方法论层面讨论问题了。
有学者认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两种最为基本的但又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前者建立在主客二元的立场之上,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用客观、科学的方式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后者则考虑到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差别,尊重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主观性[11]6-7。在这个划分体系中,田野研究是第三种方法论存在还是某种方法论指导之下的一种研究方式呢?
从学科发展史角度看,人类学的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每一次转向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田野研究与方法论之间的距离是异常清晰的。人类学研究的第一次转向是人类学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向,即经典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的逐步确立。对人类学的发展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尽管田野研究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事,但人类学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田野研究学科,因为早年的人类学家并不从事田野研究。确切地说,早期的人类学家更像是“别人田野,自己研究”。
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素材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文明社会早期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例如希罗多德在黑海、两河流域、埃及和意大利等地长途旅游的基础上写就的《历史》被视为西方最早的民族志材料之一;二是源自那些旅行者、探险者的经历以及典籍之中关于异文化的记载,以《马可·波罗行记》为代表的文献资料为早期人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三是传教士在他乡多年传教经历基础上形成的记录异国生活与文化的作品;四是被俘或者其他某种特殊的原因被迫在异文化长期生活期间侥幸逃回后写下的回忆性文字作品[12]28-32。旅者与传道士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得人类学家们足不出户便轻易知晓来自非洲、拉丁美洲或者亚洲的妇女们用不同的锅做饭,或者祭祀祖先与不同神灵时采取不同的仪式,再或者是孩子们用何种玩具玩什么游戏。这种足不出户进行研究的人类学被称为摇椅人类学(armchair anthropology),意指坐在摇椅中翻看文献就可以得出研究结论的人类学。包括著有皇皇巨著《金枝》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内的许多早期的人类学家都算得上摇椅人类学家。
可以说,人类学研究者与资料收集者之间的分离虽然为人类学家“减少了”许多舟车劳顿之苦,甚至免除了像库克船长那样陷入族群冲突危及生命的风险,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摇椅人类学家们逐渐发现那些用别人的双眼看到的甚至用生命换来的异国风情并不总是真实可靠。摇椅人类学时期最为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泰勒,之所以选择编写引导后辈学人逐渐开始田野转向的重要文献《人类学笔记和问询》(NotesandQueriesonAnthropology),就是由于他在撰写其经典著作《原始文化》时意识到了他人民族志材料的不足[13]15。
对于早期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这种问题是致命的。当他们无法再像历史学家那样盯着别人写下的文献而构筑自己对于人类历史的体系的时候,走出书斋便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彼时博物学家的实地考查引发了人类学家的关注。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人类学家开始向博物学家学习,走出书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的人类学家虽然走出了书斋,但是并没有在真正的“田野”里待多久。他们往往只是召集当地人到住处的阳台交流一些关于当地族群的事情。因此那个阶段的人类学被称为“阳台人类学”(verandah anthropology)。这些阳台人类学家大都为殖民当局所聘,他们的居所也远离所要研究的当地族群的实际生活区域,因此,他们更像是在田野外围从事研究。尽管那些来座谈的当地人也能提供一些关于当地的素材,但是这种时而夹杂着个人情感的碎片化呈现显然无法真正满足人类学家对于异文化研究的需求。这促使以参与式观察为主要特征的真正的田野研究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
被业内称为“参与式观察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真正的田野研究的确功不可没。虽然马林诺夫斯基起初并没有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岛停留几年的计划,也没有熟练掌握当地的语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他经历短期田野调查即回到英国的计划被迫搁浅。而此后的两年时间,只能留在岛上的马林诺夫斯基,不但支起了帐篷和当地人住在了一起,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还参加了许多当地人才参加的仪式。这段时间的“偶然经历”,使得马林诺夫斯基获得了许多原来“到此一游”般调研无法获得的认识。在他看来,因为“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现象,不可能通过询问或推敲文档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不得不在完全真实的情形下去进行观察”[5]77,所以参与式观察是至关重要的。在完成了特罗布里恩岛的田野调查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在其代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开篇便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田野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且提出了前文已述的长期、掌握当地语言等一系列田野研究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自此,人类学家终于真正走出书斋,走进田野,而经典的田野研究也逐渐被众多学科所认可。
可以说,从书斋走向田野的转变,虽然改变了人类学家坐在屋里从事研究的方式,但这次转变却都是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二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方法论的差异,而是对于获得资料方式的改进。换言之,无论是摇椅人类学还是真正的田野研究,都认为凭借人类学家的研究可以形成对于世界的认知,可以寻找世界的规律,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看重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的介入,认为这样才能获得更为可靠的研究素材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阶段的田野研究并不是方法论本身,而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下位概念。
人类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大致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现象学、解释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等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开始不断反思被视为经典的田野研究是否真的足够科学。1977年,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的出版可被视为这种反思的重要标志。在这本著作中,拉比诺一改人类学田野研究事无巨细地描述研究对象的做法,转而把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加以描述,而这种转变被视为是同“实证主义主导的科学工作的决裂”以及同“‘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的决裂”[14]12。或者说,此时的人类学家开始用自己的真诚“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14]15。毫无疑问,拉比诺向人类学乃至整个学界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在研究者和当地人长期互动的过程中,我不再是原初的我,你也不再是原初的你,双方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人际形态时,我们何以认为我们的参与式观察所得到的结论便是可靠的?保罗·拉比诺在进行田野研究的时候,他的“守门人”不断向他说些什么,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守门人”的真实目的只不过是想借用自己的汽车,他何以认为此时的“告白”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15]
这一场对于田野研究科学性的反思,虽然没有从根本上促使人类学放弃赖以成名的田野研究,但却促使人类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种转向指向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改变,更是对田野研究能否真正客观地反映对象的整体情况的颠覆性思考。在这种反思中,人类学家所记录下来的民族志材料不再是纯粹客观的,人类学擅长的对于文化的分析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成为了“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6]5。伴随这场旷日持久的反思,田野研究原本遵循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也难逃质疑。既然研究者无法真正客观地研究对象,那么实证主义所坚守的一整套“合理的理由”恐怕都很难再作为田野研究的基础。既然研究者无法做到纯粹的价值无涉,既然研究者无法屏蔽自己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既然研究就是在人与人编织的意义之网中进行,那么,与其空费其力地用客观的标牌伪装自己,倒不如干脆承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进而承认田野研究正在不断向人文主义方法论这一端靠近。
总体而言,田野研究的第一次转向完成了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的统一。这次转向很显然并不是从根本上颠覆凭借素材形成对人类社会认识的基本观点。因此,与其认为此次转向表现了田野研究与方法论的一致性,倒不如认为这是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人类学研究的更新和进步。第二次转变试图在反思田野研究是否科学的基础上直指实证主义方法论所标榜的科学性。尽管田野研究和实证主义方法论都成为了反思的对象,但是由于对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反思远非局限于田野研究领域,因此田野研究充其量算是方法论反思中的一个案例或者领域。由此可知,田野研究非但不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不能说只是附属于实证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方法论,因此田野研究与方法论之间也就自然无法画上等号。
三 作为一种“路径范式”的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既不是一种方法论,也不是一种研究方法,那么,田野研究该如何定位?如果我们非得在此之间进行二选一,那无疑就会陷入前文所述的研究工作者的迷茫和学生们的困惑当中。但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在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实际上,对于“方法体系”的认识,“必须改变平面化的思维方式,构筑起相应的多层次的立体式思维模式”[10]12。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对于丰富“方法体系”有着直接的助益。
众所周知,尽管库恩使得“范式”这个概念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词汇,但由于库恩本人对“范式”有超过20种用法,加之其他学者对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个概念自从被库恩提出便陷入了异常复杂的状况。本文无意陷入“范式”一词复杂的使用语境之中,而是试图在基础的意义上借用这一概念。库恩之所以选择“范式”这个术语,“意欲提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7]8。为了强调自己对于范式的基础性理解,库恩还在后记中特意表明:“范式是共有的范例,这是我现在认为本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内容”[17]157。由于库恩是在讨论科学共同体的时候提出的范式概念,而“每个共同体都有着自己的一组承诺”,因此,“范式”即一定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如何从事研究的模型”[17]导读,15。用通俗的话讲,范式就是一群研究者共同遵循的原则、理想,抑或是在这种原则、理想的指导下展开的一种研究套路。这种套路中涉及多种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相对固定的认识框架内发挥作用。
库恩对于“范式”的理解,为我们超越方法论——方法二元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果“范式”是一种范例的话,那么实际上在研究涉及的多个层面都有可能存在相应的“范式”。或者说,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层面理解“范式”。一方面,当一种方法出现了某种经典的使用时,这种使用便呈现出“范式”的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方法范式”(method paradigm)。另一方面,如果说方法论本身反映了研究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的话,那么也应当存在相应的“方法论范式”(paradigm methodology)[18]。例如,罗斯威尔(R. Rothwell)认为存在两种“元范式”:客观主义元范式(the objectivist metaparadigm)和阐释学元范式(the hermeneutic metaparadigm),前者倾向于从主客二元对立的立场去探寻世界的规律,而后者则更加看重对主客二元的超越,从而寻求对生活世界的解读[19]21-28。这与前文所述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划分逻辑已经非常接近。
然而,问题在于上述两种划分无法准确解释共同被认可的“一种研究套路”意义上的“范式”。很显然,如果研究是由多种方法组成的,那么,单一的“方法范式”显然无法应对多种方法共同参与的研究。另一方面,“方法论范式”又同具体的研究过程有一定的距离感。因此,在多个研究方法共同介入的研究中,“一种研究套路”的存在意味着另一种层面的“范式”的存在。基于此,笔者认为介于方法范式与方法论范式之间还应当存在一种“路径范式”(approach paradigm)。这种范式并不是单一方法的使用范例,而是多种方法在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指导下的有机组合。换言之,作为一种共同体共享的范例,这种范式强调在某些共同原则指导下所形成的方法集群的整体呈现。而正是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所以这种整体呈现的过程虽带有每个研究者个人的偶然因素,但总体上是沿着某种共同的套路而展开。前文所提的整体性、长期性、主客位结合、掌握当地语言等原则,正是作为“路径范式”的田野研究所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将田野研究定位于“路径范式”层面,有助于教育学研究形成自己的范式思维。长久以来,教育学研究究竟有哪些范式始终缺乏必要的思考[20]。至少相比于人类学对于田野研究范式的不断反思,教育学的范式思维显然略显薄弱。范式思维的薄弱不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缺乏关于方法论的探讨,也表现在学术论文中围绕这一主题的探讨远不如学校发展、高考改革等热门话题更能吸引学者的关注。然而,我们都未能对以往研究的路数进行深刻的反思,又何以知道今天的研究不会重蹈覆辙?倘若我们连曾经的研究路径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又何以相信培养出的研究生真的能够继往开来?
现实中对于田野研究等研究路径认识上的误区,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学研究中范式思维的薄弱。例如,围绕田野研究最为突出的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所有对“田野”进行的研究都是田野研究。殊不知前文所提的诸多原则的存在,意味着只有遵循了那些原则对田野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田野研究。同样可以被称为属于“路径范式”的政策分析也时常遭遇误解。政策分析“最初实际上只是一种效率研究……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依据”[21]译者前言,2。然而,现实中却总有人误把所有对政策的分析都视为政策分析。甚至有的研究生在论文中赫然将“政策分析”当成是自己所使用的方法,而实际上他只是对以往的政策脉络进行了梳理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将田野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路径范式”而加以讨论时,至少我们已经开启了培育教育学领域范式思维的努力。
当然,将田野研究定位于“路径范式”,就必须对其擅长什么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很少就国家的经费投入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而经济学家也往往不会把族群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路径范式”,田野研究有其自己擅长的领域。就教育学领域的田野研究而言,课程、教学、学校文化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校长领导力、学生亚文化、薄弱学校改造等领域都可以充分发挥田野研究的优势,但是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等领域则难有田野研究的用武之地。因此,将田野研究定位于“路径范式”,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学领域的不同研究套路进行分类认知。
将田野研究定位于“路径范式”,还隐含着对其研究局限的认识。很显然,介于“方法论范式”和“方法范式”之间的“路径范式”并不限于田野研究一种,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我们从事教育研究的唯一选择。任何一种范式的典范性都无法掩盖其局限性。将田野研究定位于“路径范式”,也有助于我们警惕“神化”田野研究的风险。
从某种程度上讲,田野研究在教育学界不断兴起正是源自学者对于书斋式思辨或者走马观花式的研究方式的不满。向人类学借鉴田野研究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当我们选择用田野研究作为已有研究方式的补充的时候,似乎也顺带着把田野研究“神化”了。仿佛在研究过程中,学生只要田野研究,就万事大吉了。然而,我们凭什么认为研究教育的方法只能是在学校里住上几年,沉浸在教师、校长和学生的日常闲聊中?虽然不少从事教育研究方法研究的教师在教授研究方法时也非常重视学生对于不同方法利弊的分析,但是却对多种研究方法汇集的路径中可能产生的问题鲜有涉及。这意味着即便学生真正懂得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方法本身的利弊,却未必真正能够理解田野研究的利弊。很显然,方法的利弊与“路径范式”的利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教育研究试图借鉴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范式的时候,对于这种范式的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
前文已述,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人类学界就不断反思田野研究的局限。除却对于田野研究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反思之外,人类学对于田野研究的反思还触及许多方面。例如,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声称自己所倡导的田野研究是对当地文化的整体研究,但是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中却很难看到殖民者的身影,甚至连“殖民者”之类的表述都难得一见。这表明那时人类学家在田野研究时有意地回避了征服与殖民主义的事实[22]8。不仅如此,在北美人类学界至今仍旧认为研究者的“家乡”并不是一个好的田野点,越是“非家乡”越适合从事田野研究,越是住在“非家乡”的矮小、地道的当地的住所里的田野研究往往被视为越地道[22]16。问题是:为什么“田野”必须在异国他乡?我们何以判定异国他乡的某个村落一定比“家乡”具有更加典型的差异性和地方性?换言之,为什么白人学者去非洲研究就算得上地道的田野研究,而非洲学者回到非洲的田野研究就不够地道?
诸如此类的质疑与反思在近些年的人类学界已然成为一种常态。也许这种“选择性失明”并不是田野研究的必然状态,但借用田野研究的教育学也不该对田野研究的这一问题视而不见。库恩认为“范式”必须“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7]8。这意味着将田野研究定位于“路径范式”层面,不仅强调了对局限的关注,还保留了探索未来的开放性。总之,田野研究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路径范式”。在这种经典范式面前,我们既要谨慎地接纳范式要求的基本原则,也要对范式存在的问题保持警醒。突破方法与方法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对于重新理解田野研究的定位乃至培育教育学的范式思维有着重要的意义。
[1]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M].周海涛,等译.第3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第1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4]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5]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张云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6]哈里·F·沃尔科特.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M].杨海燕,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7]丽贝嘉·纳珊.当教授变成学生——一位大学教授重读大一的生活纪实[M].张至璋,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
[8]桑国元.文化人类学与课程研究——方法论的启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9]刘蔚华.方法论辞典[K].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10]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1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2]OSWALT W H.Otherpeoples,othercustoms:worldethnographyanditshistory[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13]STOCKING G W.AfterTylor:Britishsocialanthropology,1888-1951[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5.
[14]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C]//克利福德,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5]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6]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7]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8]孙绵涛.西方范式方法论的反思与重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110-125.
[19]ROTHWELL R.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C]//HIGGS J.WritingQualitativeResearch. Sydney: Hampden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dvancement,1998.
[20]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7-12.
[21]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谢明,等译.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2]古塔,弗格森.人类学的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M].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第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罗银科]
Field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Method or A Methodology
DUAN Hui-d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58, China)
Whether field research is a research method or a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is confusing not only for students, but also for researchers. Research methods are kinds of skill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but seldom care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whole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clear differences among them. Field research includes different methods and emphasizes on some principles such as integrity, long-term and other research principles. So field research and method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completed the first change from a study to the field in the framework of positivism methodology, and the second change which began with the reflection of scientific value was influenced by the methodology transition from positivist methodology to humanistic methodology. As a result, field research is different from methodology. It needs to break down the dual cognitive structure of “Research Method-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field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is a kind of approach paradigm which can help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to improve paradigm thinking on the premise of avoiding the deification of field research.
education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 methodology; approach paradigm
2017-02-08
段会冬(1983—),男,山东青岛人,教育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教育人类学。
G526.5
A
1000-5315(2017)04-00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