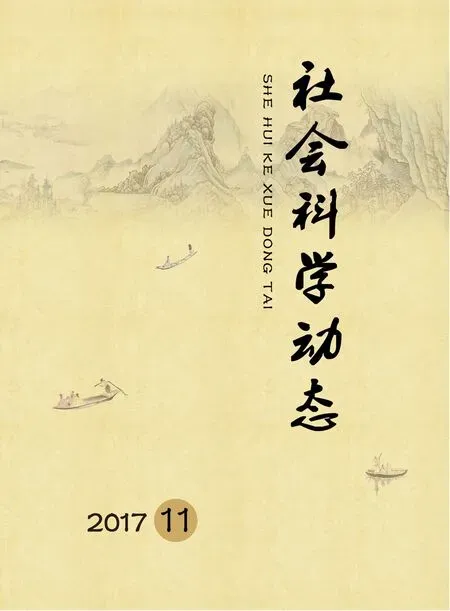天谴灾异与天道自然
——两大传统灾异观的形成及其所体现的防治方法
2017-04-10易德生
易德生
天谴灾异与天道自然
——两大传统灾异观的形成及其所体现的防治方法
易德生
中国古代先民面对大自然的各种灾害,逐渐形成了两大灾异观,本文称之为“天人感应的灾异观”和“天道自然的灾异观”。前者根植于万物有灵和神秘的天人感应思想,后者则根植于唯物主义,更多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灾害。由于灾异观的不同,防治灾害的方法和手段就会有较大不同。纵观古代中国灾害防治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两种灾异观相互交织的历史。
灾异观;灾异防治;方法和手段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农耕文明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农耕社会对各种自然灾害非常敏感。从原始社会起,中国古代先民面对大自然的各种灾害,进行了不屈的抗争。①先民们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灾异观,我们这里分别称之为“天人感应的灾异观”和“天道自然的灾异观”。②
“天人感应的灾异观”由于根植于对自然的无知,根植于万物有灵和神秘的天人感应思想,因此,表现在具体的灾害防治上,就是强调祭祀、祈祷与巫术性很强的仪式化行为,强调有意志的“天”能感应人事,人事也能影响天意,认为通过一定的人事行为(这种人事行为主要强调政治和道德行为),能够预防和克服灾异;“天道自然的灾异观”则根植于唯物主义,更多从现实的经验观察入手,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灾害,认为自然灾害主要是自然力所为,所以防治灾害要以掌握自然规律的方式去进行,要通过改造自然的手段去防治灾害。显然,前者总体上是消极迷信的,后者则是相对科学的、积极的。纵观古代中国灾害防治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两种灾异观相互交织的历史,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加深,天道自然的灾异观逐渐成为主导。
一、两大灾异观的形成及交织
1.“灾”与“异”的概念及其流变
“灾”字最初的出现可能与洪水灾害有密切关系。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根据古文字学家的隶定, “灾”字为象形字,表示洪水泛滥成灾的意思。根据《说文解字》,“天火曰灾”。《左传·宣公十六年》云:“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这样的解释应含有远古含义。实际上,至迟至东周时期,“灾”字的含义已明显变化,其所包含的范围扩大,包括水旱瘟疫等都可以称为“灾”。如《左传·昭公元年》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杇之。”“异”在《说文解字》等字典中,常常被解释为“分”、“奇”、“怪”、“非常之事”等。总体来看,“灾”主要与自然现象有关联,往往会造成经济或人员损失,如水灾、旱灾及蝗灾等;而“异”则是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或人事现象,并不一定造成人事损伤,如天象异常的日食、陨石及怪异之事等。从先秦文献如《春秋》及《左传》等来看,“灾”和“异”的概念虽然会有一些神秘色彩,但总体上并没有与政治、人事等有更多纠缠。
到了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把具有自然性质的“灾异”与“天”、“君主(政治)”及“人事”结合起来,对“灾”、“异”概念做了彻底的“天人感应”式的解读。董仲舒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③在董仲舒看来,“天”既是自然的天,有日月星辰风雨等物质表现形式,又具有人格意志,也即具有道德性、神学性和情感性,是和人的情感与精神相通的。④灾是上天给人间的谴责,异是上天给人间的惩罚;从时间上看,灾的发生要早于异;从危害程度上看,异要大于灾。班固把这段思想概况成下面的话:“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⑤东汉的经学大家何休对灾、异概念则做出了不同于董仲舒的解释。他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说,“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⑥“灾者,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⑦“异者,所以为人戒也。重异不重灾,君子所以贵教化而贱刑罚也。”⑧他认为,异是怪异的现象,兆示着灾难;而灾是随事而来,是对人的惩罚。灾虽然程度比异大,但异更值得重视,因为异有预兆性。尽管何休对灾、异概念的理解与董仲舒稍有不同,但他和董仲舒一样认为,无论是灾还是异,都是上天对人事及政治败坏的预兆或惩罚。比如《春秋》记载“大水”九次,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认为,其中六次大水是由于民众怨气太大而造成的。
董仲舒、何休等儒学大家的灾异概念与“天人同类”、“天人感应”密切相关,使先秦时期的“灾”和“异”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后世的灾异观产生了巨大影响。
2.天人感应灾异观的形成
先秦典籍中就有灾异的记载,有些也透露出某种“天人感应”的因素,如《尚书·金滕》、《墨子·尚同》等。但是,真正使天人感应灾异观成为宏大体系,大显于世,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汉的董仲舒。
上面我们在谈董仲舒对灾异概念的解释时,实际上也对其灾异观做了一定的阐述。董仲舒本是以公羊传来讲解《春秋》经的大家,他一方面吸收《公羊传》中解释灾异的观点,且更多加入天人感应方面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使灾异学说阴阳五行化⑨,把人事、自然、天象和阴阳五行等思想进行综合,形成“宇宙—天地—人事(社会政治)”相统一的宏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灾异成了天和人事、政治之间的某种中介和征兆。如果政治腐败,社会道德混乱,则具有人格意志的上天就会降下灾异;反之,如果政治清明,社会讲究道德,就会出现祥瑞。总之,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天与人之间有神秘的超物理的感应关系,“天人同类”,“天人相互感应”是董氏灾异观的核心。《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⑩《汉书·董仲舒传》在提到董氏的灾异思想时说,“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从这些话中已经明显看到,君主失德、政治腐败和社会道德沦丧会使阴阳五行失序,是灾异出现的根本原因。⑪除了灾异外,董仲舒还提到“大异”(大灾异)。他认为,如果君主极端无道,或者政治极端腐败,则上天就会降临更大的灾异,这即“大异”。比如,山崩、地震等都是“大异”,这些“大异”将是国家灭亡、王朝更迭的征兆。董仲舒的灾异理论由于体系宏大,且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现象做出了符合当时条件下的一些合理解释,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
在董仲舒之后,灾异理论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如果说董仲舒是以《春秋》经公羊传人的身份来解释灾异,其它儒家经典如《易经》、《尚书》的传人,也都以所传经典所蕴含的思想来解释灾异。例如,西汉后期的儒者孟喜、京房等以《易》经来言灾异。刘向、刘歆父子,则以《尚书》言灾异。西汉中后期以后,灾异理论还有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许多人背离正统经学,把对灾异的解释附会到孔子或神的名下,以谶纬说灾异,使灾异开始谶纬化。⑫东汉时期,由于君主的热衷和学者的上行下效,谶纬之学更加流行,弥漫到经学和政治,灾异观的谶纬化也非常盛行。例如,东汉时期的何休也是传授公羊传的大师,他受谶纬之学影响颇深,在继承和改造董仲舒等前代公羊大师学说的基础上,又大量引用谶纬以注经,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将天人感应的灾异说发展到甚至怪异荒诞的程度。
以上所述这些儒家学派的灾异观各有异同,但是总体来看,都不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灾异观影响巨大。现在看来,董氏的灾异观虽然牵强附会,很多地方荒诞不经,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神学目的论,但由于和传统的经验认识及君主专制思想相符合,因此在其形成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⑬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
另外,这里稍微提下与董仲舒灾异概念相关的所谓“符瑞”或“祥瑞”概念。符瑞在先秦时代已经流行,如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⑭这里孔子将凤鸟、河图等作为吉祥之物,作为盛世兴起前的美好征兆。董仲舒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⑮在董仲舒看来,灾异因政治无道而产生,符瑞则因政治清平而出现。
3.天道自然灾异观的形成
虽然董仲舒的灾异观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但是,一直以来即有人对此加以批评和抨击。他们把灾异现象和“天人感应”区分、隔离起来,更多从自然现象方面来看待灾异,我们这里称之为“天道自然的灾异观”。这些人中,东汉时期以王充为代表;中古时期则以柳宗元、刘禹锡及王安石等人为代表。
谈王充的灾异观,应先谈谈战国时期荀子的灾异观。因为荀子的思想应该是天道自然灾异观最重要的源头。从他对“天人关系”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荀子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与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天命主义、唯心主义相对立。他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之天,正如牟宗三所说的,是“非宗教的,非形而上学的,亦非艺术的,乃自然的,亦即科学中‘是其所是’之天。”⑯自然之天自有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⑰荀子眼中的自然灾害,“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人事活动并不能影响天的规律及灾害发生。这实质上已否定了“天人感应”思想的根本。同时,荀子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又有认知和辨析能力,能够认识自然规律。一方面,人与天各有职责与区分,要“明于天人之分”;另一方面,要发挥人的认知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认识天的自然规律,并根据其自然规律进行控制和利用,即所谓的“制天命而用之”。⑱
对“天道自然灾异观”较有体系的阐述是东汉思想家王充。东汉时期,天人感应灾异观十分流行,且谶纬化的趋势使其更流于荒诞。王充的灾异观一方面是基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批判荒诞的天人感应论及神学目的论。
首先从“天”的性质上来看。“天人感应灾异观”中的“天”具有人格神性质,有喜怒哀乐,能和人相通,能惩恶扬善,而王充则认为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实体,并没有什么意志。《论衡·祀义篇》说,“夫天者,体也,与地同”⑲,“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⑳“天道当然,人事不能却也。”㉑其次,从灾害与人事或政治的关系上看。《谴告篇》云,“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是人为,非自然也。”《明雩篇》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天并没有意识和目的,是自然自为,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灾害是自然界本身的现象,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是阴阳之气错乱所致,“风雨暴至,是阴阳乱也”㉒,人事活动并不能影响灾害过程。如当时人最关心的日食月食,其实有一定的周期。《治期篇》中说,“四十二月日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水旱灾害是“天之运气,时当自然”㉓,“云积为雨,雨流为水”㉔,与政教无关。最后,他通过逻辑和列举历史事例来说明 “天谴灾异论”、“天人感应论”为“虚妄之言”。按照天人感应的灾异观,灾异是上天对君主及政治腐败的惩罚和警告,既然如此,《自然篇》中写道,“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择才若尧、舜,授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复与知。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也就是说,既然上天能够谴责昏君,那么,天为何不直接挑选尧、舜这样的圣君来治理国家,而偏要选择一些昏君,让天那么劳累地加以谴责呢?如果说灾异是为失政而降,那么,为何“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㉕相反,尧、汤则是人所皆知的至圣之君,可是“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尧、汤恶君也。”㉖
总之,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王充否定“天人感应”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彻底地“物化”天、人,由此排除天被人感动的可能性和否定人有感动天的能力,以自然论否定目的论,二是预设“偶自然”(即自然既有自然规律性又有偶然性)为天之正道,然后以偶然论否定因果律(主要指天人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律)。㉗王充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所谓“异端”思想家㉘,对“天人感应论”和“天谴灾异论”这种极为流行的思潮做出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批判,无疑是极为杰出的,然而,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王充过分夸大自然的偶然性,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滑向了悲观消极的“命定论”㉙;同时也较为相信“符瑞说”,显示其思想矛盾的一面。
王充的“天道自然灾异观”虽然没有成为古代灾异观的主流,但是唐宋以来,其影响越来越大。唐宋乃至明清,“天人感应灾异观”仍是主流。但更多的人,如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等就对“天人感应灾异观”表现出大胆怀疑和不相信,并思索灾异形成的真正原因。
柳宗元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在哲学的重要问题上,比如自然观、天人观等,他都有重要认识和创见。他的灾异观与其哲学观紧密相连,散见于他的一些论文中,如《天说》、《天对》 (以解答屈原《天问》中提出的问题而写成的论文)、《答刘禹锡〈天论〉书》、《贞符》、《非国语》及《时令论》等。㉚他的哲学观点充满唯物主义精神,因此其灾异观也是唯物的,充满理性色彩。㉛
他的主要哲学观点及灾异观如下。首先,柳宗元继承荀子、王充等人关于天道自然及元气的一些思想,认为“元气”是天地间惟一永恒的存在。元气自身包含阳、阴二气,元气的运动及其阴阳两种属性的矛盾冲突,形成了宇宙万物及其发展变化。
从元气论自然观出发,柳宗元反对“天人感应灾异观”中“天”有意志的流行说法,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性的自然存在。“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然而中处,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天地,大果蓏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㉜在《非国语》中,柳宗元指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㉝他对天人感应论、有神论及福瑞、巫术等思想也提出质疑。他说,“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而寿者也。”㉞又说,“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卜者,世之余技也,道之所无用也。……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㉟由于天是物质实体,并没有意志和目的,所以它不可能赏功罚祸、赏善罚恶,不能主宰人世间的活动,且人事的功或祸与上天无关,都是人自己造成的。这种观点虽然是针对韩愈而发,其实很明显,也是针对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观”的批判。
在另一篇论文中,柳宗元提出了哲学史上有名的观点,“天人不相预”。“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㊱也就是说,万物生长繁殖与灾荒都产生于天,即产生于自然;而法制与悖乱则源于人类社会,两者泾渭分明,并不相互干预。这无疑有荀子“天人之分”的影子,却明显是反对“天人感应”之说的。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的天人观及灾异观,引起了其好友刘禹锡的讨论。这里顺带谈下刘禹锡的天人观。刘禹锡认同柳宗元的元气本源论,认为世界万物是元气运动变化的结果,万物“乘气而生,群分汇从”。㊲他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并且提出“数”与“势”这两个范畴来说明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颇具创新性。
刘禹锡所写的《天论》,对天人观做了新的探讨。他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天人观,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较大影响。㊳他在《天论》中说,“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自然万物及人类各有其特性,各有所长,交互作用。人类对规律认识不深时,往往是天胜人;如果人类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认识自然规律,对自然进行改造,为我所用,则是人胜天。他以舟行江河为例进行说明。船航行在较小的河中,由于风缓浪小,易掌握驾驭规律,好航行,是人胜天;航行在大江大海中,浪大风急,险滩遍布,较难以掌握航行规律,危险重重,多听天由命,是天胜人。另外刘氏还解释了人类较易陷入迷信和天人感应天命论的原因,主要是人类对“天”或自然的规律认识不够。由于无法“胜天”,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容易产生神秘的有神论和迷信的天人感应天命论。前面提到的大江大海航行的例子也表明,在不易掌握规律,认识自然不深的时候,人往往容易产生有神论和消极的天命主义。总之,刘禹锡的天人之间“交相胜”、“还相用”的辩证关系,是对柳宗元“天人不相预”观点的扬弃和深化,同时也是对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观的深刻批判。
二、不同灾异观所决定的灾害防治措施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自然灾害颇为频繁发生,所以对灾害防治非常重视。《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不同朝代,对于灾害的防治,尽管其防灾、救灾效果不一,但其大体的程序则大致相同,即灾前预防、临灾救治、灾后救济。灾前预防主要包括建立中央及地方的粮仓储备制度,如常平仓、太仓等仓储制度;另外还有改善自然条件,如进行水利与林垦建设等。㊴临灾及灾后救治,经济上而言,政府需要做的,大体上是赈济(包括赈恤、赈贷、赈粜和工赈等)、蠲免赋役、安辑流民、各级官府厉行节约等。除此之外,由于社会上存在不同的灾异观,也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灾异防治措施。天人感应灾异观倾向于用神秘的、巫术的、改变人的行为的方法来防治灾异;而天道自然的灾异观则倾向用经验的、理性的手段来防治灾异。可以说,中国古代灾异防治的历史,就是两种观点相互交织的历史。
1.天人感应灾异观指导下的防治措施
中国的二十四史等史书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在天人感应灾异观的指导下,由于其相信灾异和人事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尤其是相信君主的德能高低、政治的清明与否和灾异有直接关系,因此从防治方法上看,特别强调君主的行为,重视祈祷、祭祀等巫术性的禳灾方法。
具体而言,人们时常会用如下方法来进行防治灾异。首先,君主要以改良政治的方式防治灾异。㊵每遇到大的水灾、旱灾等灾害,社会上下便认为是政治不清明造成的,而皇帝作为天的代言人(“天子”)和国家元首,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此,皇帝往往会进行敬天与修政活动,以期减少灾害的发生。皇帝的敬天与修政活动主要包括:第一,要下诏书进行自我谴责,承担灾异责任。自我谴责的方式包括向天谢罪、避正殿、裁减后宫人数、撤声乐等。同时,官方或民间要进行盛大的祭祀、祈祷等禳灾活动。第二,要检讨施政得失,整顿吏治。包括改元(年号)、更换丞相、选举贤良、宽狱减刑等。第三,整个官僚阶层都要厉行节约,减少耗费,同时给予灾民更多的救助。西汉文、景、元三帝都曾在大灾期间诏令削减朝廷及宫廷的膳食、玩乐等支出费用,以示节约。汉元帝登基之初,关东郡国大水灾,元帝除了下诏自责外,还“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振贷穷乏。”㊶东汉延平元年,有37个郡国遭遇大雨水灾,殇帝下诏“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㊷除了皇帝本人,皇帝还常号召官僚、贵族等统治阶层节约,减少浪费,有时甚至还削减官员的俸禄。唐贞观十一年七月发生了大水灾,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说,自己因灾害而静思有没有过错,并希望文武百官“极言朕过,无有所讳”,同时命令官府减少百姓服役,“诸司供进,悉令减省。凡所力役,量事废。”㊸唐太宗是历史上公认的贤明皇帝,却也相信天人感应灾异观,可想而知,其它平庸或迷信的皇帝更摆脱不了这种观念。直到清代,君王还相信这种方法。比如顺治帝,因天灾不断,多次下“罪己诏”,并建议大臣进谏、献言,指出自己的错误。如顺治十三年,因天灾不断,顺治下“罪己诏”,指出“今水旱连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负于上天作君之心。”㊹
其次,从君主到民间,普遍流行以祈祷、祭祀及巫术的方法来防治灾异。这些方法始自原始社会,随着时代发展又有花样翻新,程序增加,仪式增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最根本出发点都是“天人感应”,都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感动上苍、感动诸神或者祛除鬼怪,以达到防治灾异的效果。每遇到水旱等灾害,皇帝往往下诏举行祭祀祈祷活动,以祈求禳灾。如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诏书曰:“自春以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洁斋齐祷请,冀蒙嘉澎。”㊺对于旱灾,一般而言其灾害程度往往大于水灾,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所以,旱灾禳灾的仪式更体现了天人感应灾异观。实际上,民间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各种舞龙活动,从根本上讲,就是从祈祷龙降雨的仪式而来,因为龙是雨神,祈祷祭祀龙神可以求得降雨。古代祭天祈雨的主要方式称“雩”,又称“舞雩”。至少自西周起,大旱之时流行雩祭。春秋时期更普遍。如《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春秋》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论语·先进》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语。《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郑玄注曰,“雩,呼嗟求雨之祭也。”《周礼·春官》之“司巫”,其职责“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后汉书·礼仪志》云:“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汉代雩礼的具体细节,在《春秋繁露·求雨》中有所保存。其重要细节包括,一年四季不论何时有旱情,举行雩礼,都“皆以水日”,同时要制作“土龙”,且“必取洁土为之”。春天求雨做“苍龙”,夏天做“赤龙”或“黄龙”,秋天做“白龙”,冬天做“黑龙”;同时,祭祀时间和方位都要符合阴阳五行的要求。另外,舞龙之人及其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汉代求雨要做龙,因为龙有行云布雨的功能。《淮南子·地形训》有“土龙致雨”,高诱注曰:“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王充《论衡》云:“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㊻
2.天道自然灾异观下的防治方法
与天人感应灾异观指导下的灾异防治方法相比,天道自然灾异观下的防治方法则积极务实理性。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人们更多以自然的角度来看待灾异,希望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方式消除、减少灾害,或者以此来缓解对灾异的恐惧。由于水、旱、虫(主要指蝗灾)等灾害在古代最为常见,因此,这里以它们为例,简述史书中所记载的防治方法。
古人在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过程中,发现兴修水利对水旱灾害防治有重大作用。因此,观察水性,兴修农田水利,防水抗旱,是每个王朝的重大政事。《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沟洫志》,足以说明人们对水利的重视。《汉书·沟洫志》说:“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阪泽,所以备旱也。”也就是说,沟渠、堰塘、堤防之类水利工程,不仅可以抗干旱,也可以防水灾。这种方法无疑会比祭祀龙王、建立龙王庙等有效得多。例如,西汉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是以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重点,当时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有六辅渠、龙首渠、白渠等。这些水利工程对于关中地区的灌溉排涝、预防水旱灾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汉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以汉明帝时期王景和王吴修筑的黄河堤防工程最为巨大。该工程耗费巨大,质量较好,能够因势利导,是黄河中下游能够安流大约五百余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代中国,对蝗灾也非常看重。每当蝗虫黑压压遮天蔽日而来,其灾害程度甚至比水、旱之灾还要严重。明代学者徐光启说:“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蟠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㊼汉代出现蝗灾时,大多是利用祈祷、祭祀等天人感应的方法来禳灾。但也有唯物主义的积极务实的办法,其中包括直接捕杀蝗虫。西汉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遣使者扑蝗。民扑蝗诣吏,以石斗受钱。”㊽王充也主张开沟灭蝗。他说:“蝗虫时至……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㊾数千年来,我国先民积累了常见的较为有效的治蝗方法,一是直接捕杀法,包括挖除蝗卵、开沟捕杀幼虫及篝火诱杀方法等;二是农业防治法。农业防治法是根据农耕技术和农事操作程序,创造不利于蝗虫繁殖的环境条件,以抑制蝗灾的发生。包括施行深耕技术、种植抗蝗或蝗虫不喜食的作物等。三是生态治蝗法。所谓生态治蝗,是指利用蝗虫天敌的方法来防治蝗灾。这实际上是从食物链或生态的角度观察到了生物相克的现象。例如,清代江南已经普遍采用蝗虫天敌(如鸭子)来防治蝗灾。
注释:
① 汤因比就认为中国古代“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些挑战“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见氏著:《历史研究》 (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2页。
② “天人感应的灾异观”在一定程上与消极迷信的天命主义思想相吻合,这种思想大致即邓拓(邓云特)提出的“天命主义禳弭论”,见氏著:《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199—204页。
③《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④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⑤《汉书·董仲舒传》。
⑥《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三年。
⑦《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五年。
⑧《春秋公羊传解诂》定公元年。
⑨ 司马迁说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见《史记·儒林列传》。另《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⑩《春秋繁露·阴阳义》。
⑪ 当然,由于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而导致的灾害,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的失德行为,但是这与古代所谓的天人感应是有本质差别的。
⑫ 《说文解字》云:“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纬,织横丝也。”在汉代谶纬之学的语境下,谶,即通过诡秘的隐语、符、图、物等,结合神启,来预言朝代更替及人事的吉凶祸福。纬以配经,所谓纬书,实质上是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术数等神秘主义思想附会、解释儒家经典的说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称:“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渐杂以数术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关于谶纬的专题研究,可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台湾“国立”编译馆1991年版;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⑬ 董仲舒思想的巨大贡献及其成为主流的原因,详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76页。
⑭ 《论语·子罕》。
⑮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⑯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第214页。
⑰⑱ 《荀子·天论》。
⑲ 以下引述王充的话皆引自《论衡》诸篇。
⑳ 《论衡·自然篇》。
㉑ 《论衡·变虚篇》。
㉒ 《论衡·感虚篇》。
㉓㉖ 《论衡·明雩篇》。
㉔㊾ 《论衡·顺鼓篇》。
㉕ 《论衡·治期篇》。
㉗ 陈静:《试论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㉘ 王充对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也充满了批判精神,写出《问孔》、《刺孟》等篇。章太炎对王充赞美有加,说“汉得一人(即王充) 焉,足以振耻。”(《訄书·学变》)
㉙ 由于王充过分强调自然世界的偶然性,所以在对待社会问题上他却陷入了悲观消极的“命定论”。他认为,“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又说:“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论衡·命禄篇》)“命定论”是王充哲学的最大缺陷。
㉚ 《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㉛ 侯外庐:《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哲学研究》1964年第6期。
㉜ 《柳宗元集·天说》。
㉝ 《柳宗元集·断刑论》。
㉞ 《柳宗元集·贞符》。
㉟ 《柳宗元集·非国语》。
㊱ 《柳宗元集·答刘禹锡〈天论〉书》。
㊲ 《天论》,见《刘梦得文集》四部丛刊本,第十二卷。以下引《天论》皆此版本。
㊳ 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认为唐代科学思想方面最大的成就乃是刘禹锡的《天论》,见氏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㊴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7—269页。
㊵ 董仲舒认为,防治灾异的德政措施主要包括“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振穷困”;“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省宫室,去雕文,举孝弟,恤黎元”;“忧囹圄,案奸宄,诛有罪。”(《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这些措施,基本上为历代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所遵从。
㊶ 《汉书·食货志》。
㊷ 《后汉书·殇帝纪》。
㊸ 《旧唐书·五行志》。
㊹ 《清世祖实录》。
㊺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
㊻ 《论衡·乱龙篇》。
㊼ 《农政全书·荒政》。
㊽ 《汉书·平帝纪》。
K203
A
(2017)11-0023-07
易德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