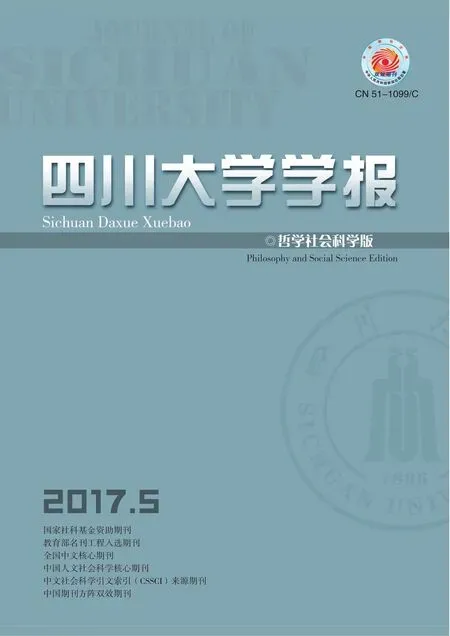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
——以儒墨关系为中心
2017-04-03,
,
§墨家研究§
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
——以儒墨关系为中心
丁四新,吴晓欣
清代乾嘉以来,墨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民国时期,墨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兼爱”一义成为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对于“兼爱”的各种讨论基本上以回应孟子的批评为出发点:学者或突出墨家对“孝”的重视,力证“兼爱”与“无父”这一标签没有关联;或将“兼爱”视为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或继承孟子的立场,对“兼爱”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个别学者在赞同孟子批评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墨家后学。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把握民国学者对儒家、儒学及对儒墨关系的基本态度。
民国学者;墨家;兼爱;孟子;儒墨关系
先秦时期,儒墨并为“显学”。出于维护儒家传统的需要,孟子指控宣传“兼爱”思想的墨家是“无父”,是“禽兽”。自西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儒林传赞》)以来,墨学逐渐式微,而孟子加给墨家“兼爱”的“无父”“禽兽”的标签也随之固定下来。在此期间,虽然韩愈、李贽以及汪中等人曾为墨家的“兼爱”作辩护,但始终未能冲破儒家正统观念的束缚。*韩愈说:“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这是通过突出儒墨之间的相同点来为墨家辩护,他就此得出结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参见韩愈:《读墨子》,载《韩愈全集》,钱仲联、马茂元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李贽说:“兼爱者,相爱之谓也。使人相爱,何说害仁?”参见李贽:《墨子批选》,载《墨子大全》(第六册),第556页。汪中说:“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参见汪中:《墨子序》,载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70页。及至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说影响的加深与传统儒学弊端的暴露,墨家的兼爱说以及孟子对它的批评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中。
梁启超认为:“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陈顾远指出:“墨子政治哲学的中心点,就是个兼爱主义。”*陈顾远:《墨子政治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八册,第486页。杨宽主张:“墨学之中心,是在兼爱。”*杨宽:《墨学分期研究》,《学衡》第79期,1933年7月,第32页。民国学者对兼爱说的关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即以此为基础,依据观点的不同而将他们的阐释分为两大组来考察。第一组学者赞同“兼爱”,反对孟子的批评;第二组学者虽然赞同孟子的批评,但对批评的对象有不同的理解。在考察这两组观点的过程中,我们还将探讨这些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儒学及儒墨关系的态度等问题。
一、关于兼爱的两点辩护
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无父”,主要针对墨家主张他人和自己的父母同观,从而忽视了“己父”在伦理关系上的特殊性。于是,民国时期有的学者即指出墨子从未否定子女对父母的孝养,承认“己父”的特殊性,因此孟子的批评站不住脚。此外,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易白沙、吴虞、陈独秀、胡适等人,不仅视“兼爱”为批判专制的有力武器,而且将其直接运用于救亡图存的运动之中。
(一)“兼爱”不等于“无父”
孟子对墨家“兼爱”说的关键批评是“无父”。对此,一些民国学者所作的第一种辩护就是试图证明墨家的“兼爱”说并未否定孝道。章太炎、吴雷川、王治心、伍非百、陈顾远和郎擎霄虽然在论证的思路上有所区别,但他们为墨家“兼爱”作辩护的初衷基本上是一致的。
先看章太炎对墨家“兼爱”说的态度及其转变。章氏是民国时期较早关注墨学的学者,他指出:“诋其‘兼爱’而谓之‘无父’,则末流之噧言,有以取讥于君子,顾非其本也。……夫墨家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孰曰无父?”*章太炎:《訄书》(初刻本),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8页。除了《訄书》初刻本,作为章太炎同一部著作的另外两种结集本,《訄书》重订本和《检论》有相同的论述。章太炎以墨家的“严父”“以孝视天下”来反驳了孟子“无父”的指控。不过,章太炎的观点并非始终如一,时有折中和摇摆。在《检论·原墨》中,章太炎说:“且夫兼爱者,人主之道,非士民所当务也。”*章太炎:《检论·原墨》,载《章太炎全集》,第441页。这是将墨家的“兼爱”看作“人主之道”,而不是普遍人所应当急行者。在《诸子略说》中,章太炎似乎对孟子的批评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他说:“夫兼爱之道,乃人君所有事,墨子无其位而有其行,故孟子斥为‘无父’。”*章太炎:《诸子略说(下)》,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15页。在他看来,“兼爱”说本身没有问题,但推行“兼爱”说则是最高统治者(“人君”)的职责,墨子无权私自推行之,因此孟子斥责他是“无父”。换言之,章太炎认为,孟子的批评不是否定“兼爱”学说本身,而是否定墨子私自推行“兼爱”的行为。由《訄书》初刻、重订两版本到《检论》,再到《诸子略说》,章太炎从为“兼爱”说辩护逐渐转变到调和孟子的批评,甚至站到孟子的立场而替孟子的批评辩护,这除了反映章太炎对于墨家“兼爱”说之理解的变化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儒家、儒学态度的转变。在《訄书》初刻本和重订本中,章太炎均专列《儒墨》一篇,将儒墨并提,这主要源于他反对儒学独尊、力求平等对待诸子的观念。在1906年发表的《论诸子学》中,章太炎即明确指出:“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章太炎:《论诸子学》,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章太炎彼时对于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平等存在、自由竞争的状态大为赞赏,而对汉代以后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却大不以为然。出于对“诸子平等”状态的向往,章太炎那时对孟子的辟墨言论就必然会予以反驳。然而,当《訄书》更名为《检论》之后,章太炎不但将原来的《儒墨》篇改为《原墨》,而且认为“兼爱”说“非士民所当务”,对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表示怀疑。到了晚年,章太炎甚至对自己早期的批孔言论表示深度的忏悔,称其为“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章太炎:《致柳翼谋书》,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63页。从而彻底转向了儒家立场。
再看基督徒学者吴雷川(吴震春)和王治心对于墨家“兼爱”说的辩护。吴氏认为,孟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无父”批评仅仅出于维护儒家正统的需要。他反驳孟子的批评道:“这种不合逻辑的漫骂式的评论,本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吴氏进一步指出,孟子这种纯主观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导致墨家被人们指斥为“异端”的后果;而事实上,在吴氏看来,“兼爱之说,并不与儒相悖”。吴氏认为,墨子同样注重“君臣上下长幼之节”,所以“并没有打破旧有阶级制度的观念”。*吴雷川:《墨翟与耶稣》,载《墨子大全》第五十册,第177、234、250页。然而,在爱的范围与程度上,吴氏认为,儒墨两家仍有不少区别,墨家的“兼爱”更接近于耶稣的“博爱”。儒墨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这并非吴氏的关注点;沟通墨学与基督教、宣传基督之爱,这才是吴氏研究墨学的初衷。
王治心更认为,孟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激烈抨击纯属一种“偏狭的门户之见”。他根据《墨子·兼爱》一文证明了“孝子”或“孝”同样是墨家的关注点,儒墨之间的关键区别不在于谈不谈“孝”,而在于表达“孝”的方式上。既然儒墨两家都强调“孝”在家族伦理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就没有理由认定“兼爱”必然会导致“无父”的后果。王治心质问道:“在儒家以为孝之道如此,而墨子以为孝之道如彼,各人的主张不同,怎能便说他无父呢?”对于儒墨两家“孝”观念的不同,虽然王治心没有通过实例作具体说明,但是通过比较《论语》和《墨子》的相关文本,可以知道王治心“主张不同”的具体所指。儒家的“孝”主要体现在对父母的生死、丧葬以及祭祀等的各项规定中,如《论语·为政》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除了在物质上供养父母,儒家还强调对父母的“敬养”,如《论语·为政》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而墨家的“孝”则是为父母带来“利”,即《墨子·经上》所说“孝,利亲也”。经过比较,儒墨对于“孝”的差别便清晰可见。不过,王治心的论述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说:“我们把他所讲的爱,归纳起来,可以见其大旨与基督相同。”*王治心:《墨子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三册,第393、410页。沟通墨家的兼爱和基督之爱,从而为在华夏宣传基督之爱寻找契机,这才是王治心关注并诠释墨家“兼爱”说的根本目的。总结吴雷川和王治心对墨家“兼爱”说所作的辩护,其基本思路及宣扬基督之爱的目的是一致的,而这两点又是由吴、王二人的基督徒身份预先决定的。
再看伍非百对墨家“兼爱”说的分析及对墨家的辩护。在伍氏看来,墨家的“兼爱”说由“爱”与“利”这两个互相联系的观念构成。他说:“爱必待周,而利不必得。故爱无差等,而利有厚薄。”“利”既然是“兼爱”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其本身有厚薄之分,那么“兼爱”与“无差等”就无法等同起来。如此,在伍氏看来,孟子的批评就失去了根基,“孟子之说盖未通乎墨之意,得乎兼而遗乎交,执乎爱而未权乎利也。”接下来,伍非百通过揭示人与禽兽的不同来为墨家的“兼爱”作进一步的辩护。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不在于爱的“兼”与“不兼”,而在能不能爱。他说:“人能爱其父,亦爱他人之父,此‘兼爱’也。禽兽不特不爱他人之父,亦不自爱其父,此‘兼不爱’也。兼爱,人也;兼不爱,禽兽也。”而孟子未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伍氏认为孟子的批评是“察类不精之过”。*伍非百:《墨子大义述》,载《墨子大全》第二十七册,第378-379页。从剖析“兼爱”的内涵出发,伍氏最后得出了“兼爱”与“无父”无关的结论,或者说“兼爱”并未否定孝道。由此,伍非百有力地反驳了孟子。
最后看陈顾远和郎擎霄对于墨家“兼爱”说的分析。陈氏视兼爱主义为墨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兼爱”的准确含义包括“兼相爱”和“交相利”两点。“爱”,指关心所有人;“利”,指利于整个社会。他拿出儒家的“大同”说来作比较,进而突出了墨家“兼爱”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墨子虽没说出‘大同’两字,这一段的意思,*笔者按,“这一段”指《兼爱下》:“今吾将正求兴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为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政,即若其利也。”就是孔子大同的境况,他却用‘兼’往前做,是比孔子学说实在地多了。”*陈顾远:《墨子政治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八册,第440页。由此出发,他针对尸佼“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则一”*陈顾远对《尸子》原文的引用不准确。《尸子·广泽》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公”只是一个空头口号,“兼”则意味着实际去行动。作为一名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陈顾远还将兼爱主义与社会主义关联起来。他说:“他这兼爱主义慢说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即就后世的社会主义,也不能逃出他的范围的。”*陈顾远:《墨子政治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八册,第519页。除陈顾远外,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将墨家学说与社会主义并提,如梁启超说:“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页)支伟成说:“试观今日俄国劳农政府之社会组织,盖可证明墨子学说之非属理想也。”(支伟成:《墨子综释》,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第17页)杨宽说:“墨学之原则,与今社会主义无二。”(杨宽:《墨学分期研究》,《学衡》第79期,1933年7月,第32页。)郎擎霄认为,墨家的“兼爱”说在阻止现代战争方面可发挥一定的作用。他说:“今日世界已成战争之场,使彼战争之邦,得闻兼爱之说,以戢其相攻之野心,而使有兼爱之同情,则不难一举战争之场,而变为和平世界。”*郎擎霄:《墨子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二册,第551页。对于孟子的指控,陈顾远和郎擎霄都予以否定,因为他们认为墨家从未否定家庭伦理中的“孝”“慈”等观念。但陈、郎二人对于“无父”的理解有所不同。陈顾远一方面坚持认为“兼爱”绝不等于“无父”,另一方面又将“无父”视为一种连墨家都难以实现的最高理想。所以他说:“孟子骂他无父无君,拿现在的眼光看来,简直是给墨子拍起马来了!”*陈顾远:《墨子政治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八册,第519页。依陈顾远之见,“兼爱”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之幸福的实现,也即是所谓“无父”,而非对自己父母的偏爱。“无父”是陈顾远极为欣赏的一种社会主义理想,在他看来,墨家尚未做到这一点,而孟子的批评实际上是高估了墨家。郎擎霄则认为“无父”是孟子贴在墨子身上的一种错误标签,他说:“孟子诋为‘无父’‘禽兽’,未免失之过当了。”*郎擎霄:《墨子哲学》,载《墨子大全》第三十二册,第547页。由此可见,同样是反驳孟子的批评,陈顾远和郎擎霄二氏的理解完全不同,而陈氏对“无父”的特殊理解主要是由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所决定的。
(二)兼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意义
面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传统儒学弊端的暴露,新文化阵营或者试图在墨学与西方文明之间找到相通之处,从而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培育适宜的土壤,或者以墨家的精神和学说来鼓舞时人的爱国救亡热情和批判专制儒学。借此,“兼爱”无论被视为一种为他人牺牲的伟大精神还是作为一种以平等为核心要义的学说,都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易白沙是将墨家学说运用于现实救亡运动的典型代表。在他的论著中,对于墨家学说,多见“益于国人”“救国”之类的说法。以此为出发点,易白沙致力于突出墨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的积极影响:“十论”中的“非攻”“节用”和“兼爱”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可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天志”“明鬼”亦可有益于普通百姓。这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从墨学中寻找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无疑是易白沙张扬墨学的出发点。”*叶宗宝:《论“五四”时期“尊墨抑儒”及其原因》,《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易白沙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各不相爱”的状态,且必然导致“尽社会之人,群起而攘夺劫掠”的混乱局面,而与《墨子·兼爱上》所描绘的情形颇为类似。于是,他大声疾呼“兼爱之说不可缓也”,*易白沙:《述墨》,载陈先初编:《易白沙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希望通过“兼爱”结束当时社会的混乱纷争状态。
除强调“兼爱”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新文化阵营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将之视为批判专制的有力武器。其论证思路包括三方面:一是明确区分儒家差等爱与墨家兼爱,以揭示专制与平等的对立;二是在反驳孟子的基础上指出儒墨思想根基的不同;三是突出兼爱与资产阶级民主道德的相通性。
首先,新文化学者对儒家之“孝”(“爱”)与墨家之“爱”作了严格的区分。陈独秀指出:“惟儒教之言孝,与墨教之言爱,有亲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鸿沟,孟氏所以斥墨为无父也。”*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任建树、李银德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胡适也认为“这种利人主义教义是对孔子厚亲而薄疏的爱的原则的否定”;*胡适:《先秦名学史》,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页。“墨家兼爱,本之其所谓‘天志’。其意欲兼而爱人,兼而利人,与陋儒之养老异矣”。*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册,第167页。陈、胡二人分别对儒墨之爱的根本区别作了界定,并认为这一区别是孟子攻击墨家的重要借口。胡适虽然未具体指出儒墨两说的优劣所在,但他提到的“陋儒”一词足以透露出他对儒家差等爱的不满。
其次,新文化学者反驳了孟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钱玄同说:“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乌得是谬说耶?”*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钱玄同此论说明了两点:其一,儒家的家族制度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其二,墨家的“兼爱”说对于摧毁家族制度的禁锢有重要作用。旧有制度既然难以维系,“兼爱”又提供了新的出路,钱玄同自然对孟子诋毁“兼爱”的言论表示出不满。新文化阵营中,对孟子的辟墨言论反驳得最激烈的,当为吴虞。吴虞专门撰写《辨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对孟子的辟杨墨予以反击。吴虞以《兼爱》篇的“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为依据,力证“兼爱”与“无父”毫无关系。对此,他说:“墨子‘兼爱’之旨,不过曰欲人之爱利吾亲,必先爱利乎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此不可斥之为无父明矣。”吴虞立足于《墨子》的文本,从中找出墨子并未忽略对自己亲人之爱的证据,继而强硬回击了孟子的“无父”说。除此之外,吴虞还把目光投向了儒家的相关论说中。他说:“孔子《孝经》之说曰,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与墨子兼爱之旨无异也。而孟子所谓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与墨子兼爱之理,仍无异也。然则孔子亦当诋为无父,孟子亦将自居于无父欤?是孟子无父之驳议,进退失据矣。”*吴虞:《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载田苗苗整理:《吴虞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9页。前面吴虞基于墨家的思想来证明“兼爱”与“无父”无关,这可以视为一种“防守型”的辩护;这时,吴虞深入儒家学说的内部,通过发掘其中与“兼爱”相类似的说法来证明孟子的辟墨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论证可视为一种“进攻型”的辩护。需要注意的是,吴虞将《孝经》、孟子的说法与墨家的“兼爱”说相提并论,只是为了反驳孟子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从中并不能推论出他将儒墨二者完全等同的结论。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一样,吴虞认为儒墨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墨子的主义,根本上和儒家绝对不能相容。孟子但攻击他的兼爱为无父,不特与墨子的学说全不相符,亦毫不合于论理。”*吴虞:《墨子的劳农主义》,载《吴虞集》,第82-83页。
最后,新文化学者肯定“兼爱”的现实意义。新文化阵营并非仅在理论层面上揭示“兼爱”说的内涵,并对孟子的批评予以反驳,他们的兴趣点还在于“兼爱”与现代民主、道德相符合。吴虞在反驳孟子时产生了如下质疑:“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已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载《吴虞集》,第11页。表面上看吴虞仍在批评孟子,实际上他突出了儒学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极其不相容,杨墨学说则可以与现代民主相契合。比起吴虞,钱玄同的观点更为直接:“帝国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民国的道德是‘兼爱’。”*钱玄同:《赋得国庆》,载《钱玄同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帝国的道德”和“民国的道德”这一对概念将儒家的专制和墨家的平等性质简练地概括出来。陈独秀的观点更加详细和具体:“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219页。陈氏的批评对象很明确,即儒家以尊卑、等差为特征的孝悌学说。他不仅指出孝悌的范围过于狭窄,差等之爱太“猾头”,还将未来社会的纷争归咎于这种学说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对此,陈独秀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即“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陈独秀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这种“全社会的友爱”的具体内涵,但不难推出,它指墨家的“兼爱”思想。*陈独秀虽然极为赞赏兼爱,但不主张过分依赖兼爱,他对兼爱所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参见陈独秀:《人生真义》,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386页。
新文化阵营对“兼爱”说进行阐释的目的很明确,即通过比较来凸显儒家有差等之爱的专制色彩,而将墨家的“兼爱”用作批判专制的思想武器。从这一点来看,儒墨两家似乎没有调和的余地,而这种看法也掩盖了儒墨之间的相通性。此外,新文化阵营在将兼爱运用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运动以及将其与现代民主道德相联系时,某种程度上也忽略了墨子所处时代与新文化运动所处时代的差异。
二、兼爱之批评及其分歧
根据具体观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批评“兼爱”的民国学者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学者对“兼爱”基本上持批评的态度,即认为“兼爱”与现实社会不符,或有违人性,因而不能付诸实践。第二类学者虽然赞同孟子的批评,却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
(一)对墨家“兼爱”主张的严厉批评
《墨子·耕柱》记载了巫马子*目前尚不能确定巫马子是否为儒者,笔者暂且将其视为子墨子的一个论辩对手。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Chris Fraser, The Ethics of the Mohist Dialogues, in The Mozi as an Evolving Text: Different Voic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edited by Carine Defoort and Nicolas Standaert, Boston: Brill, 2013, pp.175-204.和子墨子之间发生的一场对话。巫马子认为他不可能做到兼爱,因为“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435页。巫马子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力证个人对自己的爱最为可行,因为它符合一般人的情感特征。民国时期反对“兼爱”的学者同样把关注点放在“兼爱”的不可实现性上,但其所使用的论据略有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来予以概括和说明。
第一种,梁启超的批评集中在墨家的“兼爱”说无法付诸实践这一点上。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为《新民丛报》时期,代表著作为1904年发表的《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期为20世纪20年代,代表著作为《墨经校释》《墨子学案》以及《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论墨部分。梁氏将“兼爱”视为一种极端的、无差等的爱,这一看法在前后两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页。梁启超的思想极具变化,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兼爱”的认识上。在《子墨子学说》中,梁启超把“兼爱”和耶稣之爱归为同一类,并且将其与儒家有等差之爱截然二分,认为前者“仅为一至善之理论”“断不可行于实际”“不足以为道德之标准”,而后者“于维持社会秩序最有力”。*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30、34、35页。由此,梁启超认为,墨家的“兼爱”在可行性上明显不如儒家的有差等之爱。十几年之后,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除了继续肯定儒家的有差等之爱,“在旧社会组织之下,自然不能不如此”,还出乎意料地为“兼爱”作辩护。他认为孟子的辟墨言论“真能传出墨子精神,不是罪案,倒是德颂了”,认为将“兼爱”等同于“无父”“禽兽”的观点没有任何依据。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态度与前期反差最大的一点体现在如何对待“兼爱”的可行性这一问题上。他说:“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的理想之一部分。他们是否出于道德的动机,姑且不论;已足证明墨子的学说,并非‘善而不可用’了。”*梁启超:《墨子学案》,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10、70、11页。梁启超在前期仅限于在理论的层面上指出“兼爱”的不可行,到了后期,在目睹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之后,他在其中发现了“兼爱”的影子,从而认为“兼爱”可以付诸实践。然而,仅仅时隔一年,梁启超再次对“兼爱”作了彻底的否定。他不仅认为孟子的“无父”批评“不为虐”,还指出墨子的“兼爱”主张“虽善而不可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由此他重新回到了前期所持的立场上。梁启超虽然在后期曾经为“兼爱”辩护,并认为它可以付诸实践,但这应当视为他对变化了的时代环境(特指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所作的短暂回应。沟通墨学与俄国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这只是为后者寻找一个理论上的来源,其根本目的是借前者来对后者所暴露出的弊端予以猛烈抨击。*梁启超在后期对墨家的兼爱、实利以及社会组织等学说全部持否定的态度。他说:“把一切含着‘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梁启超:《墨子学案》,第10页)“墨家全不从一个人或各个人着想,其所谓利,属于人类总体,必各个人牺牲其私利,然后总体之利乃得见”;“对于社会组织方面,必使人以上所是非为是非,亦其所短也。要而论之,墨家只承认社会,不承认个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2、130页)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批评墨家学说的根本目的是揭露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种种弊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梁启超仅在一年之后便再次否定了“兼爱”的原因。
第二种,钱穆和郭沫若的论证集中在墨家的“兼爱”说具有矛盾这一点上。钱穆和郭沫若通过揭示其矛盾性而反驳“兼爱”。钱穆将“兼爱”“尚贤”视为墨子学说的“两大干”“大骨格”,认为墨子提出这两大主张的根本目的是“反贵族”。从反抗贵族阶级这一点来看,儒墨两家是相通的,区别只在两者对礼乐的理解不同。儒家通过礼乐来恢复三代以来的宗法制度,反对贵族阶层的僭越行为;墨家由否定礼乐而推翻贵族阶层的统治。对于儒墨不同的反贵族方式,钱穆评论说:“儒家只是反贵族的右派,墨家是左派。”*钱穆:《墨子》,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35页。从“反贵族”这一目的来看,钱穆对儒墨的态度似乎没有偏差。具体到墨家的学说,钱穆则基本持批评的态度。针对《墨子》中提到的世人普遍反对“兼爱”、但在关切到自身利益时又依赖于“兼爱”这种矛盾现象,*《兼爱下》云:“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拂也。”钱穆说:“世人不情愿吃自己兼爱的亏,却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这真是墨学进行上一重不可解免的难关。”此外,钱穆以《庄子·天下》篇对墨子的评价“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为依据,进一步对“兼爱”作出批评:“墨子从爱人的本意上,却转出不爱人的行为来,因此说他意是而行非。这又不是墨学上深深的一层矛盾么?”矛盾,是钱穆对墨家学说的总体评判,也是他区别儒墨两家学说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孔子只是一个调和,墨子只是一个矛盾”。*钱穆:《墨子》,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6册,第37、42页。一方面,他肯定墨家在反贵族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和品格,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揭露墨家学说的内在矛盾,这是钱穆对墨家及其学说的基本态度。郭沫若的关注点集中在兼爱与现实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上。他说:“他的最大的矛盾是承认着一切既成秩序的差别对立而要叫人去‘兼’。”在他看来,不可能在承认社会秩序之差别与对立的前提下来宣传“兼爱”这一口号。墨子的学说旨在引导社会中多数不安乐的人去爱小部分安乐的人;后者享受前者的爱,却只分享他们很小一部分的爱。对此,郭沫若断言:“这所谓‘兼爱’岂不就是偏爱!”*郭沫若:《墨子的思想》,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1页。依郭沫若之见,“兼爱”意味着取消社会中的差别与对立;否则,它就称不上“兼爱”,而只是偏爱。在《孔墨的批判》中,郭沫若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说:“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的劝人爱人,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郭沫若:《孔墨的批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114页。不少学者以“非墨”“反墨”等词来概括郭沫若对墨学的态度,蔡尚思甚至说他是典型的“尊孔反墨”。*蔡尚思:《十家论墨·要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仅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著作来看,郭沫若对墨学的态度确实以批评为主,这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结果。然而,郭沫若对墨学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尤其在早年的时候,他对墨家的兼爱、侠义精神、宗教思想和《墨经》中的科技成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肯定。*曹顺庆、聂韬:《试析“泛神论”对郭沫若墨学态度的影响——从“扬墨”到“非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第三种,柳诒徵的批评集中在墨家的“兼爱”说违背天性与人情这一点上。与上述学者相比,柳诒徵对“兼爱”的批评可以说达到了极端。他从两个层面分别论证了“兼爱”不可实行。一是在天性的层面。他说:“盖吾之老、吾之幼,以有天性之关系,故爱之出于自然;人之老、人之幼,以无天性之关系,故自然不能不生分别。”这是从人的天性层面揭示对自己亲属的爱与对他人的爱应当相区别的原因。二是在一般人情的层面。在他看来,每个人都依据自己与他人关系远近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程度的关爱:“故就人情而论,视人之室,必不能若其室;视人之家,必不能若其家;视人之国,必不能若其国。”既然违背天性与人情,“兼爱”这一学说自然陷入“无父”的危险境地中,并最终与禽兽的行为完全无异。因此,柳诒徵对孟子批评“兼爱”的做法表示强烈的支持:“世间惟禽兽不知有父,初民之等于禽兽者不知有父,故直断之曰‘是禽兽也’。”柳诒徵强烈谴责将己父与他父相混淆的做法。在他看来,对自己的父亲尽孝,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伦理道德。据此,他认为孟子对“兼爱”的批评“最为透辟”。墨家的目的只是追求物质利益,即“我之所以爱利人之亲者,即为人之爱利吾之亲。反而思之,使人不爱利吾之亲,则吾可不爱利人之亲矣”。*柳诒徵:《读墨微言》,《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第1、2、4、3页。最后,柳诒徵作出总结:儒墨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讲动机,后者则讲功利;墨家学说从表面上看与人的情感特征相符,实则有损于人性。在批评兼爱的过程中,柳诒徵表明了坚定的儒家立场。
(二)两种兼爱的区分:墨翟的兼爱与墨家后学的兼爱
与上述直接批评“兼爱”说的学者不同,还有一些学者在两种“兼爱”说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而将孟子的批评指向墨家后学。从历史上看,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墨家“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据此可知,兼爱、右(明)鬼、上(尚)同等墨家学说均以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为核心,这便与儒家伦理具有了某种相通性。虽然班固没有提及孟子对兼爱的批评,但我们很难想象孟子会攻击与儒家学说具有相同理论根基的墨家学说。然而儒墨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被严重曲解“兼爱”本意的墨家后学所破坏,班固说:“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3页。经过墨家后学的过度诠释,“兼爱”逐渐偏离了其原始义涵,而演变为一种忽略传统礼仪与家庭血缘关系的学说。班固的这一观点被唐代的韩愈所继承,他说:“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韩愈:《读墨子》,载《韩愈全集》,钱仲联、马茂元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受班固和韩愈的影响,谢无量等学者首先对“兼爱”的原初义涵表示赞同,然后将其与墨家后学的“兼爱”观区别开来。谢无量首先指出墨子所言之爱与儒家所言之爱的不同,前者“不分亲疏,不立差等,而施同一之爱”,后者则“因其亲疏之别,而为差等之爱”。从爱的内涵和形式来看,“兼爱”与耶教的博爱更加接近,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最大之幸福”。对于孟子的批评,谢无量以班固的观点为依据,坚称孟子对兼爱的“无父”“禽兽”之批评“盖指当时为墨学者之流弊而言”。*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一编下,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第49、50页。在他看来,《墨子》多处强调孝道,而且突出“爱”在结束社会纷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但这仅限于原初意义上的墨子本人的“兼爱”说。到了墨家后学这里,以上内涵被全部抛弃,以致“兼爱”演变为一个忽略父母之孝的学说。作为儒家正统的捍卫者,孟子绝不能容忍这种思想倾向,所以才“推其弊之所极而云然耳”,从而对墨家后学展开了猛烈抨击。
同属“学衡派”,孙德谦和陈柱对“兼爱”的态度较柳诒徵有所缓和。孙德谦为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兼爱之义,墨子方且教人之孝于其父矣。教子以孝,岂不与孟子无父之说,大相反乎?”围绕这一问题,孙德谦首先将关注点放在“子”这一称呼上。他认为这是孟子对墨子的一种尊称,由此证明孟子从未否定墨子其人。接下来,孙德谦继续讨论“氏”这一称呼,并将墨子从其范围中予以排除。《孟子》中两次出现“兼爱”,但表述略有不同,分别是“墨子兼爱”和“墨氏兼爱”。按照孙德谦的理解,前者反映了孟子对墨子兼爱天下之精神的赞赏,后者则是对墨家后学“无父”行为的批评。同一个“兼爱”,却被孟子区别对待,其可能的原因是“兼爱”的原初内涵被墨家后学篡改了。对此,孙德谦说:“孟子之于墨学,若不明其为末流之失,不仅墨子沉冤千古,无以昭白,亦岂孟子所乐出此?”*孙德谦:《释墨经说辩义》,《学衡》第25期,1924年1月,第6页。孙德谦的这一解释似乎既为墨家“兼爱”作了辩护,又维护了孟子儒家圣人的形象,但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仅仅将结论建立在一己之见上。*郑师渠说:“经此新解,墨子本人罪名固可以解脱,孟子亚圣的威信也不至受损,岂非两全其美?孙德谦可谓用心良苦矣,但是这样随意解说又有何说服力呢?”参见郑师渠:《学衡派论诸子学》,《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
陈柱同样将孟子的批评指向墨家后学。与孙德谦稍有不同,陈柱用“势”这一术语来描述“兼爱”在墨家后学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势”一般用来描述事物发展或变化的某种趋向,陈柱用它来表示“兼爱”经墨家后学阐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陈柱认为,“兼爱”之“势”会造成“或舍其亲而不顾”“唯利之是务”以及“唯爱其身”等后果,从而引起天下的混乱。孟子对这种“势”的弊端有清晰的认识,所以“盖惧墨学之末流,其势将为天下祸,故不得不辞而辟之”。*陈柱:《定本墨子间诂补正》,《学衡》第56期,1926年,第2页。虽然孙德谦和陈柱在论述的过程中分别使用“氏”与“势”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们在批评被墨家后学曲解了的“兼爱”时却保持了相同的立场。除了对孟子的批评对象进行界定,陈柱还简要地概括了儒墨的见解之所以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孔墨之异,在墨本于天,孔本于父母。”*陈柱:《墨学十论》,载《墨子大全》第三十七册,第151页。具体而言,儒家以孝治天下,因而更加关注人的情感,而不是追求物质利益;墨家以没有情感的天作为理论根基,这就导致过分强调物质利益,而忽略人的正常情感。这种不同,使墨家可以轻易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儒家却能长久地坚持自己的原则。陈柱将天与父母分别视为墨、儒两家的理论来源,并认为它们是决定墨、儒对人之情感和实际利益之态度的重要原因。不难看出,在这一比较中,陈柱基本偏向于儒家的立场。
三、结 语
民国墨学研究热潮是在西学冲击日益加剧、儒学弊端逐渐暴露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这一时期关于墨学的各种讨论大都涉及儒墨关系话题。孟子虽在先秦时期对“兼爱”作出“无父”和“禽兽”的批评,但在当时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孟子之后的二千多年里,虽有个别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对孟子的这一极端批评有所提及,但终究没有引起集中性的讨论。直至民国时期,在章太炎、梁启超等的带动下,墨家学说尤其是作为其核心思想的“兼爱”说才逐渐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孟子批墨,乃由儒墨两家思想主张的不同所致。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又可反映出他们对儒墨关系所持的不同态度,而这主要源于他们不同的学术或政治立场。章太炎和梁启超对墨家“兼爱”的态度较为复杂,二人虽然都对“兼爱”表示出一定程度的赞赏,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儒家立场,而放弃了墨家学说。吴雷川、王治心、伍非百、陈顾远、郎擎霄以及新文化阵营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墨家的“兼爱”说辩护,或基于宣传基督教义的需要,或出于改变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对儒墨关系或儒学传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反对墨家“兼爱”说的学者中,钱穆、郭沫若和柳诒徵的态度较为激烈,不仅对“兼爱”作了猛烈批评,还彻底割断了儒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而谢无量、孙德谦和陈柱则比较温和,一方面维护了孟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为墨家的“兼爱”说争得了某种话语权。
TheExplanationofJian'aiintheRepublicofChinaPeriod(1911-49)CenteringontheRelationshipBetweenRuandMo
Ding Sixin, Wu Xiaoxin
Mohism has been on the way of renaissance since the Qian-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1736-1820).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ozi and Mohism, especially the core idea jian'ai became the hottest topic for scholars. Discussions about jian'ai in this period basically started with Mencius' typical criticism of it. Some scholars tried to prove that jian'a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being fatherless” by showing Mohist emphasis on filial piety. Some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role that jian'ai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feudal autocracy and saving the nation. Some held on to Mencius' stance and attacked jian'ai fiercely. Others agreed with Mencius but further pointed out that his attack was only targeted at the later generations after Mozi. By analysing their discussions about jian'ai, we can learn about these scholars' attitudes toward Confucianis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 and Mo. And their attitudes were largely shaped by their background and life experience.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ohism, jian'ai, Mencius, relationship between Ru and Mo
B261,B224
:A
:1006-0766(2017)05-0032-09
(责任编辑:曹玉华)
丁四新,清华大学哲学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100084);吴晓欣,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长沙41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