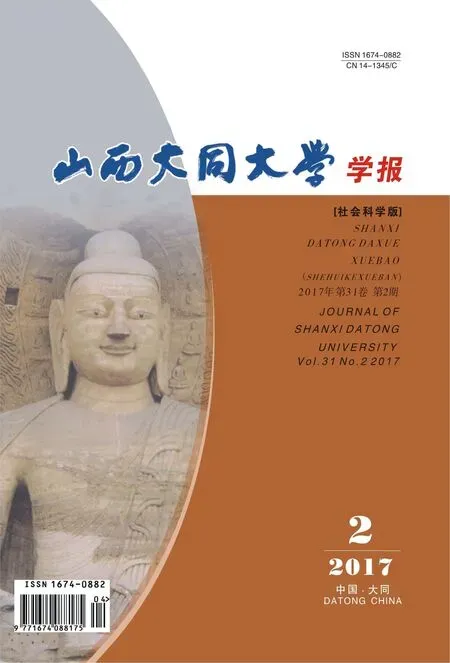王朔小说中喜剧性的表现及消退
2017-04-02崔佳琪
崔佳琪,谢 纳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王朔小说中喜剧性的表现及消退
崔佳琪,谢 纳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开创了独特的小说创作范式,他打破新时期以来典型化、单一化小说模式,以反传统、反权威的创作心理,创作出大量颇具喜感的小说。王朔小说中的喜剧性,主要源于他充满智趣的反讽语言、滑稽怪诞的闹剧式故事情节、寻求刺激和游戏人生的“顽主”形象,以及作者自身幽默洒脱的创作态度。
王朔小说;喜剧性;调侃;顽主形象
20世纪80年代,王朔凭借其独具特色的小说风格,在中国文坛获取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王朔小说中喜剧意蕴浓厚,他凭借乐观豁达、敢为人先的创作态度,通过幽默、调侃式的反讽语言,对崇高和权威进行解构,揭示伪崇高的可笑和滑稽。作者笔下一系列机智幽默、游戏人生的“顽主”形象,加之怪诞多变、违背常规的闹剧式情节,均使其小说充满个性、通俗幽默,完美迎合处于改革动荡期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从而掀起一股全新的小说创作浪潮。
一、解构传统与权威的反讽语言充满智趣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中指出:“人类最惊人的符号手段就是语言。”[1](P08)王朔对小说语言的应用有着特殊的解读,他说:“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打散重新组合,就呈现出另外的意思。”[2](P41)从这一语言观出发去解读王朔小说的语言特色,不难发现,作者对“变幻语言”和重新“组合词句”的实践。王朔小说中常常将庄严式、崇高式话语和大众化话语相结合,他为小说主人公贴上“俗人”的标签,借“俗人俗语”对崇高和权威进行调侃和反讽,使原本崇高的、不容置疑的事物在“俗人俗语”的调侃中被解构为琐碎和平庸,庄严的官方化语言和俗人的“侃话”相互杂糅,使小说中的反讽语言充满智趣。
王朔笔下主人公大都是粗俗、文化程度不高的“俗人”,他们的语言大都杂有粗话、脏话、秽语和恣意的笑骂等,这类人物与崇高和优雅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当庄严而神圣的东西作为语料在他们日常交流话语中出现时,就会产生以俗戏雅、化雅为俗的喜剧效果。在《顽主》中,一位不满自己丈夫整日只顾“乱侃”的少妇,面对临时扮演自己丈夫的“3T公司”员工马青大骂道:“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的过去,没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光,抽水马桶一拉就哗哗喷水,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少妇将丈夫的“砍(侃)瘾”比作“抽水马桶哗哗喷水”,语言本身粗俗但不失趣味,精巧形象的比喻,表现出少妇对丈夫“砍(侃)瘾”的指责和厌恶,生动还原市民生活真实场景,充满生活乐趣。“中苏谈判”本是神圣而庄严的,如今却和“砍(侃)瘾”、“抽水马桶”联系到一起,借以讽刺丈夫的乱侃行为,这种俗雅结合的语言模式,将崇高、神圣和平庸、琐碎相互混合掺杂,使庄严受到调侃和解构,同时俗、雅语言之间的调遣运用也使小说充满智趣和喜感。
王朔小说中将庄重而神圣的官方化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语言相结合,有意对高雅和正统进行调侃,在调侃中实现消解的目的。这种解构崇高的调侃式、反讽式语言,表现出作者对精英文化的强烈反叛,轻松不屑的调侃语调、充满智趣的反讽语言也促使小说趣味横生。
二、寻求刺激、游戏人生的“顽主”形象颇具喜感
王朔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文化圈内备受热议的话题,他率先打破新时期以来小说程式化、典型化创作模式,凭借轻松、另类的小说风格收获大量读者。王朔小说给读者以乐趣和欢快之感,主要原因在于“他首次让一群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痞子形象堂而皇之的闯进文学殿堂。”[3]作者笔下的“顽主”形象真诚、豁达,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生活,他们看破世态人相,通过调侃和反叛的方式,表现出对社会型塑人的不满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这一系列注重在生活中“找乐”的顽主形象,是王朔小说中喜剧因子之一。
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大都是自小生活在老北京城的各色青年,他们没有固定职业,用尽精力寻求刺激和享乐,顽主们对世人的同情、指责和不满不屑一顾,反而鄙夷那些持严肃态度对待人生、忙忙碌碌的世人。此类人物形象刚刚出现在文坛时,曾有批评家针对“顽主”指认王朔小说是“流氓文学”。事实上,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氓流,从具体行为来看,他们的确不符甚至有违社会现有的价值判断尺度和秩序,但深入挖掘顽主性格本质,不难发现,“顽主们”固守自享其乐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彻底看穿了人性的虚伪和丑恶。于是他们走南闯北,出入各大豪华酒店宾馆,不分昼夜的摸牌赌博,反对刻板无趣的生活现状,追求在生活中为自己“找乐”。
《顽主》中马青等人深知以青年人导师自居的赵尧舜是伪善的“假道士”,在莫名承受赵尧舜一番“教导”后,马青等人难以平复内心的压抑,索性就在街上以打人解恨,“三个人肆意冲撞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的毫无反应”,于是马青自我感觉良好的冲到前面,挥着拳头喊道“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只见一位彪形壮汉走近他:“我敢惹你”,马青见状喊道“那他妈谁敢惹咱俩?”毫无疑问,“头发整齐”“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是社会虚假的象征,马青等“顽主”对其是鄙夷的态度,五大三粗的汉子看穿马青等人虚伪骗术,勇敢向前挑战,反而获得顽主们的敬重。在马青这位顽主喊道“那他妈谁敢惹咱俩”时,更是鲜活的表现出顽主们的机智风趣。
王朔小说中顽主们通达乐观的性格本质、幽默机趣的处事风格、无所顾忌的人生态度均为小说增加了喜剧因子。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迫于社会环境、道德准则等压力,面对不合理现象,他们很难像顽主们一样以实际行动去表达自己的反叛。但通过阅读王朔的小说,读者可以实现和顽主们精神的契合,并受到顽主们风趣幽默、真诚、不羁的性格感染,从而暂时忘却现实压力,加入到顽主们追求人生乐趣的队伍中。
三、荒谬怪诞的闹剧式情节寓庄于谐
一般情况下,学术界和读者均愿将王朔小说视为通俗小说,事实上,王朔小说要比一般通俗小说的内涵深广很多,这是因为其小说中包含对传统和崇高、权威和反叛、自由和价值的重新估定与审视。王朔为完美再现传统和权威型塑人的荒谬后果,他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意义,往往通过组织怪诞的闹剧式故事情节传达小说主题。作者善于渲染燥热、狂欢的小说氛围,描写权威压制下的日常生活场景,借滑稽可笑的闹剧式情节彰显生活中存在的荒诞。王朔对于小说形式意义的注重,不仅有助于提升小说思想格调,而且也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喜剧性。
张健在《中国现代喜剧史论》中指出:闹剧“常将高度夸张或极其滑稽的人物形象有意识地安排在某些意外与荒唐的情节里,并以大量的插科打诨去求得喜剧效果,目的主要在于逗引观众的捧腹大笑。”[4](P302)王朔小说中故事情节以闹剧形式出现,他笔下代表权威和传统的人物常常以滑稽、另类的形象,出现在怪诞的情节中。嘈杂喧闹的小说氛围、荒谬跳跃的故事情节均让读者忍俊不禁。
《千万别把我当人》以象征权威的“赵航宇”等人煞有介事的为维护民族大义改造唐元豹为故事主线,其间穿插若干闹剧式情节,如:为获得体育竞赛胜利,赵航宇等人安排唐元豹变性这一情节。由于变性的需要,唐元豹先是被安排到女生宿舍,与女同学共处一室,以便更好地熟悉女性生活。于是小说中出现,在女性中久居的彪形大汉唐元豹穿着女士衬衣、涂着胭脂、和四个姑娘“手拉着手娉娉婷婷地走着”的滑稽场面。原为铁骨铮铮的七尺男儿,如今却扭捏的和女孩儿们一起描眉画眼,满身散香,这其间的巨大反差和荒谬,足以引发读者笑意。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继而又编织更具闹剧式的情节。赵航宇等人为增强唐元豹变性信心,竟然大张旗鼓的举办“动员唐元豹加入妇女行列全国妇女英豪誓师献技大会”,大会上“一万八千个娘们儿雄赳赳气昂昂的坐满看台”。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全场妇女引吭高歌,一个个唱的满头大汗”,随后各界妇女代表讲述她们当女人的幸福,激动之余迁怒到场上的男性主持。于是闹剧式场景出现:先是唐元豹在妇女们的鼓动下发表誓言“决心变成女性”,随后面对场上的男性主持,“妇女们发了疯似的举着拳狂吼狂喊:绞死他!绞死他!”甚至“有几个动作敏捷的已经冲了上来,揪起主持人左右开弓的扇起他耳光”。小说中“唐元豹变性”这一情节荒诞至极、变化多端,妇女们歇斯底里的喊叫促使小说闹剧意蕴浓烈。作者有意将象征权威的“赵航宇”等人置身于荒唐的情节中,通过揭示人物思维方式、行为、心理的滑稽搞笑,营造寓庄于谐的美学效果。
喜剧研究者彭吉象认为,喜剧让人笑的原因在于“喜剧性艺术具有‘寓庄于谐’的美学特征。‘庄’是指喜剧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谐’是指主题思想的表现形式诙谐可笑。”[5]从这一论断探究王朔小说中的喜剧性,可以发现,王朔小说正是通过滑稽怪诞的情节模式,表达对于权威和压制的反叛,其小说中“寓庄于谐”的美学特征,是促使读者发笑的重要原因。
四、逍遥洒脱、注重趣味的创作态度浸染作品
王朔自述小说创作观念时指出:“制造个气氛,给自己寻个小快乐也是有的”,[6](P08)由此可见,作者在小说创作中轻松达观、逍遥洒脱的创作心态,和有意为小说增加趣味性的创作心理。王朔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极具个性的作家,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日益兴起之时,他并没有追逐流行的创作热潮,而是选择忠于内心,坚守自己的创作风格。他以无所顾忌、率性洒脱的文学观念为基点,创作出一系列反映时代变革、表达自由追求、且颇具喜剧意蕴的优秀小说。
中国古代有“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之说,即“文如其人”的文学理念。文学作品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可以很好地反映作者的创作追求,同样作家的创作态度也会直接决定文学作品的风貌。王朔是一位认为写小说只不过是“码字”的作家,他认为作家进行创作并不是多么神圣高尚的事情,只是生存、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就如农民种地收取粮食一样,无非是一种职业而已。他反对精英文学,否认只有专业作家才能进行创作的观念,于是以“俗人”自居的王朔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独特的潇洒不羁、无所顾忌的创作心态。而这种创作心理反映到作品中,则使作品呈现出同作者心境一样的轻松氛围。加之王朔又是一位乐于在作品中“找乐”的作家,所以王朔进行创作时,有意以轻松氛围为小说基底,通过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的革新,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现实生活中的王朔具有幽默、洒脱、敢为人先的人格特质,当作者的这种人格特质转化为创作理念时,他的小说必然会受到幽默的浸染。结合王朔性格本质和创作理念分析他的小说,其作品中主人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和趣味性调侃,其实正是作者现实生活中的投影。《顽主》中的于观听说林蓓要和作家保康结婚时,他认为:“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一点正经没有》中的主人公提出“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我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小说中人物对于“作家”的看法和嘲弄机智风趣,事实上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王朔对于“作家”地评判。需着重指出的是这里的“作家”并不泛指所有作家,王朔调侃和嘲弄的是以职业写作自居,且排斥一切平民写作和通俗作品的作家。王朔十分反感那些仅仅倡导精英文学,将其他一切作品均视为异端的作家,当他的小说被这类作家命名为“痞子文学”时,王朔并没有与之进行唇枪舌战的争辩,他以独有的达观、逍遥、洒脱的态度,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并以无所畏惧的幽默调侃对此类作家进行嘲弄,于是便有了小说中于观等人幽默机智的“作家论”。由此可见王朔潇洒乐观、幽默豁达的创作态度和人生观,对于小说中喜剧意蕴和喜剧氛围的影响。
王朔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并不是偶然,读者对他的喜爱,大都源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幽默的人生态度,作者敢为人先、逍遥玩世的创作理念是对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学的极大冲击,也是对文学应具有庄严教化功能理念的反叛。他凭借独特个性创作出的小说,可以让倍感生活压力却无可奈何的读者,从中获得瞬间的轻松和乐趣,也可以让痛恨权威秩序的个体,在他逍遥的小说世界里得到宣泄。
五、结语:喜剧性色彩日益褪色的遗憾
王朔小说中的喜剧性在上世纪90年代日益消退,这与文学界对王朔长期以来的争议有关,也和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定位密不可分。学者黄平认为:“我们的文学史,是一部没有笑声的文学史。”[7]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留下来的大都是精英化、经典化、具有严肃教化功能的文学作品,与这些作品相比,王朔小说中的亵渎、享乐、无畏等自然被认为是异类的存在。因此王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是文学界争论的话题,各类文学史著作中对于王朔的处理有一共同特点:即以“纯文学”审美机制的评判标准,虽重视王朔小说反映社会变革中“个人”的出现,但对于解构性的“个人”如顽主,则采取规避的叙述态度。
王朔小说中的喜剧性是建立在反讽、解构、个性、荒诞基础之上的,这与当代文学史追求的建构化、集体化有明显出入。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许多作家都曾在文学史上有过短暂的“失踪”: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作家们在文坛上消声后,或转变创作方法、或在适宜的时期重新执笔、或不再从事文学创作。王朔面对文学界对自己的批判,先是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潇洒态度,无所畏惧的固守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但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史对王朔的有意隐藏,则促使他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创作。正是由于这一次自我质疑,导致王朔小说中的喜剧性日益褪色。立足当下,反观王朔小说中喜剧性的日益消退,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作者本人,这将会成为一种损失和遗憾。
王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篇自序中写道:“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包括所写的东西产生了很大怀疑”“什么生活也是百感交集莫衷一是,为什么反映在小说中却成了那么一幅面孔,譬如说:喜剧式的。”[6](P01)由此可见,王朔对于小说中喜剧性合理地位的怀疑,伴随着自我怀疑产生的是王朔创作风格的转变。90年代后期王朔创作出《看上去很美》这部小说,标志着作者开始从逍遥转向严肃,从调侃转向深沉。王朔转化创作风格后,其小说更注重还原真实生活,思想更深刻、内涵更厚重、气氛更严肃,由此引起小说中喜剧性的日益褪色。王朔创作风格的转变是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实现的,转变的出发点自然是希望作品可以更优良,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但事实上王朔并未注意到,他的作品在80年代受到疯狂追捧的原因,正是在于作品氛围的轻松、逍遥和喜剧意蕴,因此它的这一转变未能实现预期效果,反而使大量喜爱阅读他前期小说的读者大失所望。
王朔作为一个时代的神话人物,他创作风格的转变是充满勇气的,但也可谓是失败的。王朔小说中独特的喜剧性,是他开启小说创作之门的一把钥匙,但在创作后期,他有意规避小说中喜剧性的存在,无疑是封锁了自我的创作之路。对于读者而言,不能继续通过阅读王朔的小说中获得快感和趣味,这也将会是一种遗憾。
[1]朱 狄.当代西方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2]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3]刘凤芹.王朔小说中的另类形象的现实反观[J].名作欣赏,2009(03):81-82.
[4]张 健.中国现代喜剧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彭吉象.试论悲剧性与喜剧性[J].北京大学学报,2004(04):41.
[6]王 朔.看上去很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7]黄 平.没有笑声的文学史[J].文艺争鸣,2014(04):23.
The Express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Comedy in Wang Shuo’s Novels
CUI Jia-qi,XIE N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136)
Wang Shuo created a unique paradigm of novel crea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in the 1980s.He broke the typical and novelized mode of the novel since the new period,and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happy feelings in the anti-traditional and anti-authoritarian psychology.Fiction.The comedy in Wang Shuo’s novels is mainly due to his ironic language,funny absurd,farce-like plot,seeking the image of stimulating and game life,and the author’s humorous and free attitude.
Wang Shuo’s novel;comedy;ridicule;stubborn image
I207.42
A
〔责任编辑 冯喜梅〕
1674-0882(2017)02-0080-04
2016-12-25
崔佳琪(1994-),女,内蒙古通辽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谢 纳(1973-),女,辽宁沈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