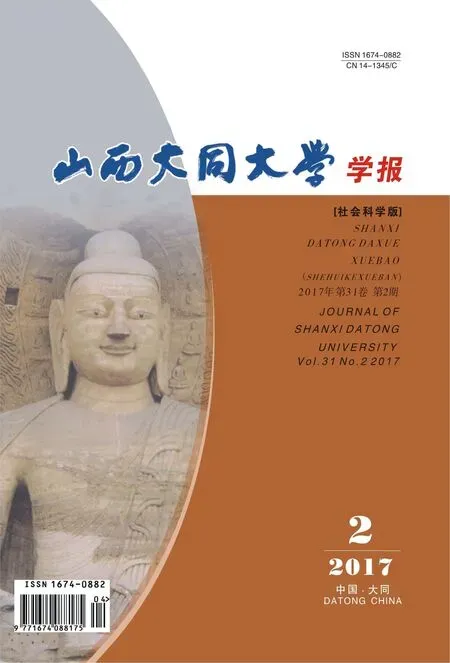北魏医学成就初探
2017-04-02李海
李海
(山西大同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北魏医学成就初探
李海
(山西大同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从医事管理、名医介绍和方剂学的发展等方面,探讨北魏时期的医学成就。结果表明,北魏医药管理机构齐全,名医辈出,特别是方剂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北魏;医学成就;医事管理;名医;方剂学
北魏时期,重视医药业的发展,设置国家医药管理机构和医官,积极选拔、使用医药人才,加强医学教育,认真收集、整理医药图书文献,使其医学成就硕果累累。
一、北魏医事管理
医事管理,是指国家医药管理机构的设置、医官的配备、医学教育的开展及相关政令的发布等事宜。良好的医事管理对促进医药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对医药业的重视 北魏对医药业非常重视,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与百姓的迫切需要。北魏时期,虽然有相对和平的时段,但总体而言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由于战争、饥荒,造成了大量的受伤、患病人员及新的病症。大量军民治病疗伤的迫切需要,必然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当时有作为的北魏帝王多关心民间的医药救助事宜。皇兴四年(470年),献文帝下诏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名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1](卷6)献文帝看到百姓有病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于是诏令天下,病人均由所在地的官府派遣医生到家中诊治,按医生处方免费给予所需药物。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下诏,令司州、洛阳两地贫穷无靠且患疾病的老人别坊居住,且“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1](卷7)永平三年(510年),宣武帝下诏,令太常寺在闲置之地设一医馆,让京畿内外有疾病的人都住在里面,由太医署派遣医师予以治疗;延昌元年(512年),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发生地震,房屋倒塌无数,百姓伤亡甚多。为救助地震造成的灾难,宣武帝下诏曰:“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外科医生),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1](卷8)
二是统治阶层的迫切需要。当时,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士人、官吏、乃至皇帝盛行吃寒石散。如果不懂医学知识,便有发病亡命的危险。如北魏道武帝在御医阴羌指导下,服用寒石散,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阴羌去世,道武帝乱服寒石散,导致中毒,神经错乱。[1](卷2)另外,北魏诸帝多笃信方术,乞求长生。天兴三年(400年),仪曹郎董谧献《服食仙经》,载有炼不死药之法。道武帝就授董谧为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1](卷2)太武帝听说高僧昙无谶有方术,便欲得之,又令方士韦文秀等合炼金丹。孝文帝也曾令侍御师徐謇试为延年之药。统治者乞求长生,自然对有名的医士、新来的仙方倍加青睐。
(二)医药管理机构和医官的设置 北魏时期,设太医署以管理国家医药事务。北魏前期太医署属尚书省。孝文帝太和改制,设置九卿,太常为九卿之首,太医署始归太常。太医署设有太医令、太医丞、太医等医官,掌管医政兼医疗事宜。唐杜佑《通典·职官》记载,太和改制后,在门下省设尚药局,置尚药典御、尚药丞、侍御师等医官,总知御药事。[2](卷38)其中,侍御师即御医,北魏名医徐謇、李修等人曾任此职。侍御师平时服侍皇帝,只有接受了皇帝敕令后,才会为重臣出诊。又在中书省设中尚药局,置中尚药典御、中尚药丞等医官。《通典·职官》又载,北齐时尚药典御正五品,中尚药典御从五品,侍御师正六品,尚药丞、中尚药丞从七品、太医正九品。北魏时医官的品阶应与北齐时相同。另外,北魏时增设的医官还有仙人博士、太医博士和太医助教。仙人博士的职责是“煮炼百药”,应是负责制作药物医官。不过,仙人博士一职仅在道武帝一朝设置。《魏书·官氏志》曰:“太医博士,右从第六品下;太医助教,右从第八品中。”[1](卷113)这是我国古代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之始,为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三)医学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 北魏时期,御医们曾多次主持、组织医家收集、整理医学图书文献,编撰医书。然后全国颁行。太和年间(477-499年),侍御师李修“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1](卷91)《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时曰:“《药方》五十七卷,后魏李思祖撰本百一十卷。”[3](卷34)李修,字思祖,其《药方》当为方剂学之类医籍,反映了当时医学的进步。宣武帝年间(500-516年),侍御师王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1](卷91)永平三年(510年),宣武帝在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1](卷8)这两项记载,时间和撰修卷数等基本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手段,备布郡县乡邑,既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又有益于百姓疾患的防治。
(四)医学教育的兴盛 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师承家传和学校教育。北魏时期,医学教育比较兴盛,但仍以师承家传为主。有的医家始于拜师(多拜沙门医家)学艺。北魏名医李修之父李亮,年青时跟随沙门僧坦学习医术。[1](卷61)北魏名医崔彧,年青时在青州向隐逸高僧学习《素问》及针灸。[1](卷91)而成名的医家往往将医术只传授给自已的子孙后代,从而产生了医学世家,如周澹父子[1](卷91)、李修家族、王显父子、崔彧家族、历经八世的“东海徐氏医药世家”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当时的医学认知、发展水平有关。当时,医家注重在名师指导下的实践,崇尚直接的诊疗经验总结,在理论上并不作深入探讨。这样,后辈学医者就必走拜师学艺之路,为医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世医现象成为医家步入仕途的捷径。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官员的选拔,均通过九品中正制而来。这种选拔制度,注重门第,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北魏时期,帝王重视医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御医往往拜将封侯。名医徐謇,年纪很大了,还升任光禄大夫,加封平北将军;名医王显,官至太府卿、御史中尉,因医术封爵卫南伯;名医徐之才,更是因医术而封王,“迁尚书令,封西阳郡王”。[4](卷33)在这种环境下,师承家传的医学教育方式必然成为主流。但这种医学教育培养出的医学人才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
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唐六典·太常寺》医博士条注云:“宋元嘉二十年(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5](卷14)据此,我国古代设置学校医学教育机构应始于南朝刘宋时期。但是,由于时局动乱,在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逝世后,这个医学教育机构遣散,仅存10年。目前,尚未发现北魏兴办学校医学教育的直接记载。但北魏官学教育发达,国家先后设置了太学、皇宗学、国子学、中书学、四门小学;地方实行郡国学制,每郡亦设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设置的学官有太学博士、皇宗学博士、国子学博士、中书学博士、四门博士等。[6]当时官学虽以教授经学为主,但必辅之以算学、医学等。上文谈到孝文帝时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这是从事医学教育的医官。因此,当时可能已在官学中增设医学教育。永平三年,宣武帝诏曰:
可敕太常于闲敞之外,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1](卷8)
太常乃是当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命其“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即在闲置宽敞之地设一医馆。其作用:一是对病人要“严敕医署,分师疗治”;二是对在学医生,“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显然,该医馆相当于一座当今的实习医院,这也是北魏时开展学校医学教育的一个例证。《通典·后周官品》记载,北周的各种职官及在校学生共“万八千八十四人,府史、学生、算生、书生、医生……等人也”。[2](卷39)医生者,医学生也。显然,北周时在官学中存在医学教育。北周教育制度沿袭北魏,进而推知,北魏时在官学中亦有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北魏名医介绍
北魏时期,社会的需要及良好的医事管理促进了医药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人数众多的名医,现择其重要者作介绍。
1.周澹 (?-419年),京兆鄠(今陕西户县)人。《魏书·周澹传》称其“多才方艺,尤善医药”。北魏元明帝中风头眩,为周澹治愈,由此受宠,位至太医令,赐爵成德侯。
元明帝神瑞二年(415年),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发生饥荒,朝议将迁都于邺城。周澹与博士祭酒崔浩表示反对,正合元明帝的心意,高兴地说:“唯此二人,与朕意同也。”于是下诏,给予周澹、崔浩赏赐。元明帝泰常四年(419年),周澹卒,赠谥曰恭。
周澹之子周驹,深得父传,袭太医令。孝文帝延兴(471-476年)年间,位至散令。[1](卷91)
2.李修 生卒年代不详,字思祖,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县)人。李修之父李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北魏太武帝时,赴南朝“就沙门僧垣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李亮后为北魏侍御师,累迁府参军,督护本郡。李修之兄李元孙,自幼和李修随父李亮学医,得父真传,但医术不及李修。成年后,在平城行医,以功赐爵义平子,拜奉朝请。
孝文帝太和年间(477-500年),李修任侍御师,后迁中散令、给事中,以功赐爵下蔡子。孝文帝、文明太后每当患病或身体不适时,多由李修诊治。为此,经常得到赏赐。是时,李修“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惜该书佚失,内容无考。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李修被封为前军将军,领太医令。李修亡故后,赠威远将军、青州刺史。[1](卷91)
李修之子李天授,深得父传,袭父职,为侍御师,又任汶阳令。但医术不及李修。
3.徐謇 生卒年代不详,字成伯,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人,祖籍山东莒县,出生于“东海徐氏医药世家”。北魏献文帝(466-471年在位)时,徐謇在青州行医,被北魏军队俘获,具表将他送至京师平城。由于医术高明,深受献文帝的宠遇,任中散大夫、内侍长。孝文帝亦深知徐謇的才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及其宠幸的冯昭仪身体稍有不适,都让徐謇诊治,并对其渐加爱宠。不久,迁徐謇为右军将军、侍御师。徐謇曾在崧高炼金丹,试图替孝文帝寻找延年益寿之法。虽历经一年,但一无所成,只得作罢。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因战事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突然病重,就派驿马急召徐謇。徐謇一天一夜赶了数百里,到达悬瓠,立即为孝文帝诊治,疗效显著。是年九月,孝文帝车驾从豫州出发,临时住宿在汝水之滨,特为徐謇设宴。让徐謇坐上席,命左右宣扬徐謇的医治之功。并下诏进其为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赐钱一万贯。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徐謇以高龄升任光禄大夫,加封平北将军。不久去世,追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定谥号为靖。[1](卷91)
徐謇之子徐践,字景升,小名灵宝,袭父爵,亦为侍御师。
4.王显 (?-515年),字世荣,阳平乐平(今山东莘县)人。王显自称祖籍山东郯城,是汉朝王朗的后代。其祖父于北魏太武帝延和(432-435年)年间,迁居于彭城(今江苏徐州)。王显的伯父王安上,在南朝宋文帝时为馆陶县令。太武帝南征,王安上归降,赐爵阳都子,升任广宁太守。
王显年轻时就精通医术。文昭太后怀宣武帝时,梦见日化龙体,追逐缠绕其身,醒后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和王显,共同为文昭诊脉。徐謇曰:“是微风入脏,宜进汤加针。”王显曰:“是怀孕生男之象。”当然王显说得对,文昭太后确实是怀孕了,而且生下了宣武帝。不久,王显补任侍御师、尚书仪曹郎。宣武帝即位,对王显非常信任,遂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但仍兼侍御师,营进御药,出入禁内。后历任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太府卿、御史中尉。是时,宣武帝诏令王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宣武帝立东宫太子时,王显又兼任太子詹事。延昌二年(513年)秋天,王显因医术封爵卫南伯。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夜崩,孝明帝连夜即位。宣武帝在位时,王显受到重用,又为御史中尉,乃执法之官,倚仗权势、显示威严,为当时群臣所嫉恨。孝明帝即位后,嫉恨王显的大臣,借口其给宣武帝治病有误,群起而攻之。孝明帝下令削去王显官、爵,并把他逮捕。值勤武官还用刀环重击王显的腋下,使他重伤吐血,第二天就死了。[1](卷91)
5.崔彧 生卒年代不详,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崔彧之父崔勋之,曾任南齐大司马外兵郎。崔彧与其兄崔相如均自南齐入北魏。崔相如以才学知名,但青年时就去世了。崔彧少年时,曾经去青州向隐逸高僧学习《素问》及《针灸甲乙经》等医书,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经患病,王显等人不能治,后崔彧用针灸疗之,抽针即愈。从此,崔彧名声大振。不久,任冀州别驾,累迁宁远将军。崔彧性情仁恕,每见贫苦人患病,好与治之。同时,还广教门徒,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人赵约、勃海人郝文法等人,亦以医术知名于世。
崔彧的儿子叫崔景哲,也以医术知名于世。先后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6.徐之才 (492-572年),字士茂,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人,祖籍山东莒县,出生于“东海徐氏医药世家”。徐之才的祖父徐文伯(徐謇之兄),在南朝刘宋时曾任东莞、兰陵、太山三郡太守。父亲徐雄,南梁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二人皆以医术见称于江南。徐子才自幼聪慧,五岁能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十三岁召为太学生,粗通礼、易,被誉为“神童”。成年后,在南梁豫章王萧综处任豫章王国左常侍和镇北将军府主簿。
北魏孝昌元年(525年),萧综投降北魏。在萧综的推荐下,孝明帝“诏征(徐)之才,孝昌二年,至洛(阳),敕居南馆,礼遇甚优”,徐之才由此进入北魏。由于其“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因此,“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孝武帝时(532-534年),徐之才被封为昌安县侯。
东魏孝静帝天平中(534-537年),徐子才被大将军高欢(北齐神武帝)征赴晋阳,常在内馆,礼遇稍厚。孝静帝武定四年(546年),徐子才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后转授金紫光禄大夫。
北齐文宣帝高洋取代东魏时,徐之才赞同,并引经据典,说明其合理性。因此,高洋即位后,封徐子才为池阳县伯、赵州刺史。北齐孝昭帝皇建二年(561年),徐之才任西兗州刺史。是时,武明皇太后患病,徐之才疗之,应手便愈。为此,孝昭帝赐其彩帛千段、锦四百匹。徐之才博识多闻,医术高明,他虽然在外为官,还是经常被皇帝召回,为皇家诊治。如为北齐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北齐后主天统四年(568年),徐子才累迁尚书左仆射、兗州刺史。武平元年(570年),徐之才任尚书令,封西阳郡王,故有徐王之称。徐之才去世后,赠司徒公、录尚书事,谥曰文明。[4](卷33)
除上述名医外,北魏尚有许多医家,如阴羌,《魏书·太祖纪》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1](卷2)
三、方剂学的发展
(一)方剂学的撰修 北魏时期,很重视方剂学医籍的收集和撰修。例如:孝文帝太和年间,李修“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宣武帝年间,王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李修、王显所撰《药方》是官颁医书,其内容即是方剂之类的实用医籍,便于“皆行于世”。当时不少医家也编撰此类书籍。如《隋书·经籍志》记载,徐子才家族著有《徐氏家传秘方》二卷、《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十卷、《徐王方》五卷、《小儿方》三卷。徐子才还详加修订《药对》等方剂医籍。[3](卷34)
十六国北朝时期,诞生于南亚的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与明末清初西方耶稣教士在华传教,同时带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西学东渐”完全类似,当时西域高僧在中土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科技知识,医学是其中之一。是时,翻译了不少的南亚和西域的方剂学医著。《隋书·经籍志》记载的此类医籍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婆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3](卷34)这些书目中分别有“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等佛教菩萨的称谓,或直接以僧人作者命名,颇具时代特征。其中,《龙树菩萨和香法》亦见于《历代三宝记》,该书卷九载有“《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并注曰:
凡五十法。梁武帝世,中天竺国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意宝。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沙门僧朗觉意,侍中崔光等笔受。[7](卷9)
正始为北魏宣武帝年号。这条文献可证《隋书经籍志》所载的方剂医籍,至少有部分译于北魏宣武帝或稍后的孝明帝时期。受翻译佛家医著的影响,西来高僧和本土医僧也撰写了不少方剂医籍。如《隋书·经籍志》记载:“《疗百病杂丸方》三卷,释昙鸾撰。《沦气治疗方》一卷,释昙鸾撰”。[3](卷34)昙鸾,北魏高僧,雁门(今山西代县)人。《续高僧传》称其“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8](卷6)昙鸾的这两种医籍,传世较久。
(二)徐子才对方剂学的贡献 我国传统医学中关于药物方剂的分类,最早有“七方”之说,即大、小、缓、急、奇、偶、复方,始见于《内经》。名医徐子才对方剂的分类贡献显著。他在其详加修订的《药对》等书中,总结了我国传统医学中方剂分类的理论和经验,提出“十剂”的分类方法,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内容如下:
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桔皮之属;
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
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
泄剂,泄可去闭,葶芷、大黄之属;
轻剂,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
重剂,重可去祛,磁石、铁粉之属;
滑剂,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
涩剂,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
燥剂,燥可去湿,桑皮、小豆之属;
湿剂,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
这种统一的按方剂功用分类的方法,既给处方用药带来很大方便,又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的药物调遣、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所以,一直为后世医家采用。
(三)一部重要的方剂学医著《小品方》《小品方》又叫《经方小品》,是我国隋唐以前医学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方剂学医籍。[9](P62)《隋书·经籍志》著录:“《小品方》十二卷,陈延之撰。”[3](卷34)陈延之,史籍无载,故难以判断《小品方》成书于何时何地。有的学者推断其为南朝刘宋时期的医家所撰,但证据不足。笔者认为,该书可能编撰于北魏孝文、宣武年间。如前文所述,其时北魏组织众多医家收集医药方剂,分别由李修、王显主持编修《药方》,或许激发民间撰修方剂医籍的热情,《小品方》应运而生。
1985年,日本学者在日本尊经阁《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了《经方小品》残卷,包含了自序、目录等内容。据此,人们对《小品方》的结构及成书有较为清楚地了解。据陈延之在自序中所言,《小品方》在撰写过程中,共参考了18种300多卷前人著作。《小品方》全书共12卷:第1卷有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第2至第5卷为渴利、虚劳、霍乱、食毒等内科杂病方;第6卷专论伤寒、温热病的诊治;第7卷为妇人方;第8卷为少小方;第9卷专论服石所致疾病之诊治;第10卷为外科疮疡、骨折、损伤等;第11卷论述了本草药性,是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增补民间用药经验而成;第12卷为灸法要穴、灸治禁忌、诸病灸法等。
陈延之反对“唯信方说,不究药性”的时弊,主张因时因地,因人因病地灵活运用。其组方用药以简单、方便为主,收录的方剂多为小方,很少有超过10味药的大方,但疗效却很灵验,而且药物的选择也体现了方便经济,以“山草中可自掘取”为原则。显然,这是适合寻常百姓使用的“救世良方”。
[1](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隋)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唐)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李海.大同府文庙沿革[J].文物世界,2011(02):66-70.
[7](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
[8](唐)释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李经纬.中医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A Discussion on Medical Achievement of North Wei Dynasty
LI Hai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s Science,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chievement of medicine of North Wei Dynasty,based on medical management,famous doctor,science of prescrip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were complete medic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f North Wei Dynasty,and large number of famous doctor appeared,in particular,science of prescription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North Wei Dynasty;achievement of medicine;medical management;famous doctor;science of prescription
N09
A
〔责任编辑 马志强〕
1674-0882(2017)02-0064-05
2016-12-25
李 海(1948-),男,山西左云人,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