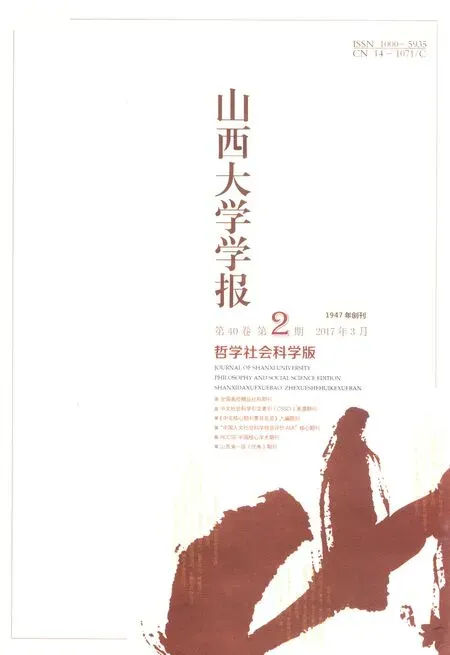北京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考略
2017-04-02孟伟
孟 伟
北京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考略
孟 伟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张家湾山西会馆,是目前所知明清时期山西商人所营建的1000多座(所、处)商人会馆之一。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张家湾,营建于晚明前清时期。它与通州城的一系列国家漕粮码头相对应,作为山西商人的专用码头而存在,并在市场管理和神灵祭祀、娱乐活动等等方面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性组织与民间性活动的中心。
明清时期;京师;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商人专用码头
通州在京师东六十里许,以京杭大运河之北码头而闻名天下。通州城偏东南十几里处,有一个叫作张家湾的古村落。村内有一座山西会馆,原坐落于京杭大运河畔,现已不存。实际上其存在的时间最短算也有300余年,可以追溯到晚明前清时期,有康熙十年重修碑可考①(清)黄成章:《通州新志》卷六《艺文》中收《重修张家湾大王庙碑记》,雍正二年刻本。。然而这座默默无闻的山西会馆,却曾作为大运河上相当重要的“地标建筑”而存在。对于中国明清经济史、商业史、对外贸易史、民族关系史,特别是山西商人发展史来说,更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标志”意义。
本文的学术追求和旨趣就在于:通过对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的学术探讨,揭示隐藏在这一会馆背后、深层次的一系列问题。既属于明清商业史中山西商人的研究,更是探究“京杭大运河”、“茶叶之路”等历史问题的一个特别视角,两者密不可分。
一 张家湾山西会馆的现存资料
针对出现在距离通州十几里的张家湾的考论,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山西会馆作为有型的建筑实体历史地出现及其存在于张家湾的情况;其二,张家湾的历史地理情况及其文献;其三,与张家湾山西会馆直接和间接关联的山西商人的相关文献。
(一)张家湾山西会馆的现状及其调查
有关张家湾历史的文献记载非常有限,其地山西会馆的建筑实体也已荡然无存。实地调查时,收集到一些居住在张家湾镇的老者口口相传的叙述如下:
张家湾山西会馆,三进大院,坐北朝南,正殿五间,耳殿左右各二间,其他房屋有百十多间;大殿有关老爷读春秋像,偏殿还有许多神像,正殿对应的是“山门倒坐戏台”,中轴线布局,占地五亩余,庭院植有对称的四棵松树,在城外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有后院,左右开门,后院可出入车马,左右偏门可入正院;门口有旗杆,一人高的大石狮子分列左右,有钟鼓楼与之对应;琉璃瓦铺盖,五脊六兽应有尽有,气势恢宏;较之通州城东的铜关帝庙,更有气派等等。
以上叙述,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张家湾山西会馆的布局造型,与运河沿线其他码头的山西会馆大同小异。
现在的张家湾成为北京城发展的重地,历史的遗存和痕迹愈来愈少。要想弄清楚历史上到底是哪些山西商人在张家湾营建了山西会馆及其目、时代特征等等,“历史文献”的方法论必不可少。
目前现存的直接资料有:(1)“山西会馆”匾额。现存于通州博物馆,很可能是目前所存留的唯一建筑“部件”。该匾额系两块长方形石合成:左为“会馆”,右为“山西”(旧式书写方式),无题名,无落款。另在《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下)中收有照片。[1]1068初步断定,此额系通州张家湾会馆门匾。抑或该会馆拆除时所留,抑或通州城另有“山西会馆”,倘若后者其情况待考。(2)乾隆四十年《重修山西会馆碑记》。此外,尚存留碑记两通,极为珍贵。两通碑形制相同,现存张家湾村委会后院。系乾隆四十年所立,题名:重修山西会馆碑记,首身一体,笏首平底、无座,碑高210cm,宽90cm,厚22cm,石灰岩质,略有漫漶。(3)康熙十年《重修张家湾大王庙碑记》。碑记明确记载为“山西商人所修”,早在雍正二年就收录在黄成章撰《通州新志》,卷六《艺文》中。由于传统的方志编撰惯例,收录该碑时直接省略了“碑阴”,因此当时的情况也无从所知。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史领域,尤其是明清山西商人历史的研究,对碑刻的利用与以往传统史学的情形不同,“碑阴”是极其重要的“细节”,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根本性“内容”。
(二)张家湾的地理区位*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目前涉及张家湾的一些基础叙述多半存在误区,即便现在的“张家湾村”和“张家湾镇”也并非是一回事。在空间地理分置布上两者分居运河两岸,张家湾村诞生较早,原是国家行为的建制,是源头,现如今其行政级别小,也即本文所述山西会馆所在地;张家湾镇则历史上是衍生,属于清代中叶以后民间社会的发展结果,现如今行政级别却高,属于“镇所在地”,如此情况需要特别注意,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张家湾在通州城偏东南十里许,明代嘉靖时期,开始筑起城垣,周长九百余丈,依照运河的弯度而修筑,习惯称之为“刀把形”城垣,开有几个城门,为的是就地势而充分利用码头。尽管张家湾是大运河的北码头,但沿运河南来北往的官绅、士子,也多在此下船起旱,赶往京师,可省去好多路程。
在张家湾,从明代开始就设有“皇木厂和盐厂”,与通州的漕粮码头遥遥相望。守城的兵丁和百姓住在城垣里边,总人口即便最多时也不过三、四千人*这一数字,系笔者赴张家湾调查时村委会所提供。按照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张家湾村人口不足2000人,直到新中国成立也没有超过此数。据此向上推演,较早时期的人口亦应不高于2000人。,因此与其说张家湾是一个“城垣”,倒不如说是一个“运河岸边的专门为皇家堆放南来木料的仓储式城堡”更为贴切。
河北岸是城堡式村庄,河南岸则是开放式的散住居民,现在称之为“张家湾镇”,两者由“运通桥”相连,运通桥也称之为“萧太后桥”。[2]213目前有关张家湾镇的历史资料甚少,其发展轨迹难以完整复原,然而镇里唯一的“清真寺”的创始年代则在道光年间。如此来看,张家湾镇的发展较之张家湾村要滞后的多,并且带有明显的回族移民特点——不难断定,张家湾镇的兴起与草原驮户转输大运河货物有直接的关系。
晚明、有清一代300多年里,有关张家湾商业职能的确切记载并不多见,除了皇家木厂、盐厂、运通桥、山西会馆等有记载之外,其他的商业机构很难稽考,甚至作为村庄标志的“集市”也无从寻觅,但据说原来的庙宇却营建不少,有十多座,只可惜现已无一幸存,相关的碑铭也不知去向。
(三)历史时期与张家湾会馆相关的山西商人的一些情况
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中,有些非常明确的关于张家湾山西会馆的一系列关联性记载。特别是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账册、书信、规程、碑铭等方面的民间文献,有效地弥补了正统历史文献稀少的缺憾。
这里谨将业已发现的、涉及张家湾山西会馆的部分资料,简列于下。
(1)乾隆十八年《祁县里村重修老爷庙碑》记载:武巨要,通州湾募化叁拾两(字号略);
(2)乾隆三十一年《通州湾立规碑记》中记载:茶叶到达通州湾的规则(参见下文)*原件收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
(3)乾隆四十四年《北京河东会馆碑》记载,共有通州二十余家商号募捐银两(字号略)[1]962-980;
(4)乾隆五十七年《口到库伦商货册单》中记载,由于通州湾到货迟,尚有茶箱未到若干的情况[3];
(5)嘉庆十八年《茶叶规程》中载,《新立碑规》——茶叶抵达通州张家湾的规则;
(6)道光九年《平遥颜料会馆新铺开市碑》中,有十一家颜料字号及其募捐银两情况[1]1047;
(7)同治六年,《西口聚升魁清单》中,开列有:疲账一项,王开源张湾丢失茶箱,折合银两肆佰伍两捌钱*原件为北京晋商博物馆收藏。;
(8)光绪十七年《东口湖广茶庄共俱信稿》中,有关于茶叶轮船运输的相关问题,涉及通州张家湾等情形*原件为民间收藏家刘建民先生收藏,笔者依据影印件整理(未刊)。;
(9)光绪十八年《安化办茶规程》,山西祁县商号抄本中,列有《通湾脚价》等②;
(10)“民国”四年手抄本,《祁县长裕川茶庄行商遗要》中,所载“茶叶转输情况”,明确记载的茶路规程之“通州码头”多项事宜。[4]481-541
二 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沿革与变迁
就张家湾山西会馆的实际,结合本文的基本问题,拟从张家湾山西会馆的诞生、发展和消亡,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稍加考论——以勾勒出张家湾山西会馆历史变迁的阶段性轨迹和脉络。
(一)张家湾山西会馆的诞生
张家湾山西会馆最迟诞生在晚明时期的嘉靖年间,当时活跃在运河沿线的山西商人,除了开中盐商持续性地发展之外*明代的开中制,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明初至“土木堡事变”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前后两个阶段对山西商人的影响不同。有关“明代开中制的问题”,目前的学术探讨并不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入。,还有更多的粮油商人、典当商人、布商、铁商、丝绸商、颜料商等。其籍贯主要是平阳、泽潞、汾州府地区的临汾、襄陵、曲沃、翼城、长治、潞城、泽州、高平、阳城、汾阳、介休、平遥等地。这些商人由于南北往来,与掌管张家湾的太监建立了商业关系甚至更为亲密的人情关系。因此按照商人群体修建庙宇的惯例与官府人员进行联合——最初的“大王庙”,“遡其始创,明御马监张诸之功德也,为三桥八庙之一,比如长寿寺之故址也”——御马监张诸即当时张家湾(镇)“最高官衔”的长官。
也就是说,在张家湾镇的山西会馆,初创时期作为四大王庙,具体位置在东偏南的“便门外”,以原来的长寿寺旧址为基础。
虽然当时是以“大王”为额,但庙中“有关圣帝君之像,梓童帝君之像,眼光圣母之像。前奉大士,后供诸天,信心罗拜,无不皈依”——则俨然已经成为一座经过改造的、符合山西商人需求的“金龙四大王庙”。或者说张家湾的“大王庙”从一开始就与运河中南端的、较为纯粹的、以“运河神”为主要“神灵”的“金龙四大王庙”不属于“一个神灵和信仰序列”了。与之相反,却明确地表现出了山西平阳、泽潞地区商人的一般性庙宇习俗和信仰追求。甚至完全能够说,张家湾的大王庙较为充分地表现出了晚明前清时期平阳、泽潞地区商人营建商人会馆的主要特征——以“四大王”、“关帝”、“财神”等为主要祭祀“神灵”。
(二)张家湾山西会馆的发展
晚明末年,战乱波及运河沿岸,张家湾的“大王庙”逾数十载亦被残破。当时有浙江商人“钟世亮,虔发弘愿,自输囊金,宜饰者绘,宜彩者金,且益之戏楼,以壮大观”。说明这一时期的“大王庙”的所有权益未必完全归“山西商人”。至少些许祖籍地的商人们也有责任和权利对大王庙实施修葺。
清入关后,虽然张家湾的山西会馆还以“大王庙”的名义而存在,但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
在雍正二年的《通州新志》中明确载明了:山西商人重修。所谓的“重修”,是指“古晋油曲善商赵运隆、宋谅等共发菩提心,劝善输资,奖众鼛工,洞开觉路,装塑金身,仍复灿然改观,焕然奋目。非赵宋二商之首倡,曷克臻此事竣功毕”。
这里的“山西商人赵运隆、宋谅”,其籍贯目前无从稽考,但依据其从事的行业行当,大致可推断,其为平阳商人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当时的京师油业,基本为平阳商人所垄断,并且分为“南油帮”和“北油帮”,而“京师油业公所”也在临汾会馆中*该会馆保存有康熙、乾隆碑记。。一般而言,营修庙宇或者会馆的“维首”,通常都是当时经营状况良好,且规模较大的字号。
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正式出现,应当在康熙雍正朝。因为到了乾隆三十五年,被大水冲毁的庙宇已经称之为了“关帝庙”,而不再有“四大王”额。并且这一次的重修,完全由与张家湾密切相关的250多家山西商人的字号完成。由此可见,张家湾山西会馆从“大王庙”到“关帝庙”的转变,或者直接地用“山西会馆”定名,在乾隆中后期业已完成。这也标志着出现在运河上的山西商人进入到了以晋中商人为主的时代。
这一点恰好也与山西商人会馆整体的发展情形相一致:(1)到乾隆中期,遍布大江南北的山西商人会馆的格局基本形成;(2)山西商人营修会馆的机制——厘金制初步确立;(3)晋中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到了山西商人的会馆营修建设中——在此之前的山西会馆营建基本上是以平阳、泽潞商人为主体;(4)山西商人会馆,包括“山陕会馆”的称谓成为普遍,会馆中的祭祀对象正式确立为了“关帝”等等。
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正式定名,还与晋中地区的商人,特别是茶叶商人、门头沟煤炭商人、旅蒙商人、皮张商人的崛起有直接关系。
以汾州府、晋中地区为主的山西商人选择距离通州城十几里的张家湾为据点,并在此安营扎寨长达200多年的情况,既可以与乾隆初年兴建在通州城里的“翼城会馆”,也可以与出现在天津、京师的会馆相对照。“宣大议和”之后,以“八大皇商”为主力的边贸商人群体异军突起,在他们展开商贸活动的早期,他们也必然地需要会馆,不可能不“效仿”。况且布匹、茶与皮张的对应性转输的历史事实,也并非是“恰克图开启”之后才出现,事实上汾州府商人所从事的民间性的草原贸易,在“多伦会盟”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因此可推断:伴随着茶叶、皮张、铁器等商品量的急剧增加,这些商品却难以象布匹、颜料等零星商品那样,再搭北上的“粮船”载运,进入通州城码头装卸、转输。一系列的不方便,甚至遭遇敲诈勒索等屡屡发生,迫使他们做出新的选择——寻找适合自己的、纯粹民间性的、属于商人专用的码头。远离国家、官府控制的通州城码头,在距离通州十多里的张家湾安营扎寨,成为最佳选择。
将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放置在明清时期的山西会馆的整体中,其个性化的特点始得凸显:
第一,乾隆年间的重修,其名称直接就是“山西会馆”,而不是“山陕会馆”。进而延伸开来:从山东聊城以北的河北、关东地区、蒙古草原地区,乃至京津,基本没有再以“山陕会馆”定名的情况出现。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仅仅在“特定的时空下”(晚明前清的黄河、江淮流域),才有一定的关联性。
第二,将出现在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与北京的全部明清时期的会馆稍作比较,张家湾山西会馆无论在功能和作用,还是实际的运营等方面都是大相径庭的。目前可考的明清时期的山西会馆(包括部分地区的山陕会馆)绝大多数与科举考试、京师官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张家湾山西会馆是标准、典型的山西商人会馆。
第三,将江苏扬州、淮安,湖北汉口、襄樊,河南赊旗、周口,山东聊城、临清,江西吴城,湖南湘潭,天津三岔口等地的山西会馆(包括山陕会馆)与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稍作比较,亦可发现这些会馆的相似性和共性——都以远距离的商品转输为“动力源”而兴建会馆,并且其地理位置均是“水陆码头”之地。与此相反,与较大城市、集镇的山西会馆则有明显的差别。进而通州张家湾的山西会馆是凭借“运河码头”而营建的渊源情况,也就自然显现出来。
第四,从《乾隆四十年·张家湾山西会馆碑》中可知:张家湾“山西会馆”最早出现的时间,至迟可以追溯到乾隆初期,这里的依据主要是“布商”与“通州城内的翼城会馆”相分离的情况——汾州府布商开启恰克图布匹贸易,而翼城会馆诞生在乾隆初年。与此同时,临清、天津卫三岔口的山西会馆则修建于晚明前清,京师前门外也至少有五座山西商人会馆修建于晚明。而当时的主要行当为布商、铁商、车铺、烟商、煤行、茶行、成衣行、钱行,这些行当的特点决定着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权益和特征”;其中,虽然目前难以断定到底哪些字号在张家湾安营扎寨,但二十多家车铺则是这一会馆的“显著标志”——这一点,是目前所有山西会馆“功德碑”上不曾有的情况。另外还需注意,这里没有山西盐商,却有成衣行,实际上“成衣”基本属于“皮衣”,是以汾州府商人为主,由草原地区的皮张加工而成,通过运河南运;
第五,从乾隆朝开始的一系列文献中,一直到民国年间的150多年里,通州张家湾山西会馆,始终是汾州皮张商人、颜料商人、烟商、祁太茶叶商人等,以及泽潞地区铁器商人、平阳粮油商人的专用码头的“大本营”,与属于国家序列的“漕运”和“官方行为”截然地划分开来。另有一通碑铭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情况,兹将《道光九年·茶叶规程》中所载:乾隆叁拾壹年立牌(碑)规开列于下(节录)*原件藏北京晋商博物馆,手抄本。。
凡货到湾,俱要轮帮,前后起卸。报信即一字号者内有伙计叁、贰位相跟进行者,货亦相继而到者为一帮,货客久隔时日,即以前后轮帮;
凡货船到湾,必许(须)系客船方许轮帮,若止(只)有肆/伍家货搭别船来者,则可卸栈,不得报信发车,务以本船到日再为轮帮;
凡发脚,勿论车驼,俱归柜上搭派分发,如本客自雇或各口庙雇来之车驼,亦要归公;
……
凡客人从口庙、来湾,截路私添脚价雇车驼者,亦要随公议价,归公分发,如脚户不随行议,原客包补;
凡发脚因要挨帮,若发小庄货存肆、伍车者,即与扫数,如大庄货有柒、捌车者,亦清庄。
由此可见,张家湾的“茶叶转输规则”,是非常典型的“民间习惯法”,至迟从茶叶贸易的“专门化运输”——有了专门的码头和运输船只,就开始成为严格的“规程”,为所有的茶叶商人所遵循。乾隆三十一年所定规则,是茶叶贸易中转输规则成熟的标志。
总结目前发现的文献史料可发现,明清以来蒙汉地区的贸易以及中俄恰克图茶叶的贸易的历史进程中,茶山由武夷山转向两湖,茶叶的生产技术由传统到机器的革命,茶叶的运输方式也升级为轮船、火车运输,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也发生本质性变化等等。然而,至迟从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民国年间的山西茶商却始终在通州张家湾实行“挨帮”的转输制度,或者一如既往地延续驮脚到东西两口,或者辗转丰台车站到张家口,其民间习惯法的基本规则从来没有本质性变化。
也就是说,张家湾山西会馆的职能和命运也保持一贯性。作为几乎是“万里茶路”的唯一专用码头,张家湾才是真正的“茶叶之路”的“水陆码头”的转换点。进而张家湾的山西会馆的特殊作用和功能,也与其他城市、集镇的山西会馆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以汾州和晋中商人为主体的“保障商品转输顺畅的商人会馆”,而不是“市场交易和发散型会馆”,更与近在咫尺的前门外的几百座科举、官绅等会馆,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三)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消失
民国初期,张家湾山西会馆开始出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往来于运河上的山西商人——张家湾会馆的所有权益人出现了大幅衰退。特别是与张家湾山西会馆有密切关系的商人,诸如茶叶、皮张、门头沟煤炭等相关行业的商人表现出急速萧条和衰落。
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消失,总体来说与其他地区的山西商人会馆的情形差不多,但也有个性化的特点:(1)运河的荒废、铁路的开通,山西商人也弃船上岸,转输商品改为火车;(2)从事西北贸易的茶叶商人、皮张商人、门头沟煤炭商人撤离张家湾,山西会馆与张家湾的萧条同步;(3)民国年间张家湾地区曾经多次遭受水灾的山西会馆,得不到及时维修,很早就成为“老爷庙”,处于了荒废状态;(4)民国时期的战乱,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调整、急速的时代变革等等,也不能忽视;(5)“文革”时期的动荡,使当时幸存的残垣也被荡为平地;(6)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建设浪潮中,遗址已无处寻觅;
三 结论
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始终以运河为“商业活动的主要通道”,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是最为重要的“水陆码头”。伴随着国家漕粮码头的紧张加剧,民间性的山西商人便将“民运码头”挪移至距离通州城十几里的张家湾,专门分流通州码头的“漕运转输”压力,集散草原地区以及恰克图贸易商品,为此营修了“山西会馆”。可以说,张家湾山西会馆是有清一代的“山西商人的专用码头”。其诞生及发展与山西商人商贸活动的专门化转输相适应、相对应,也与“国家与民间”的“大运河利用和效应”相对应。
此外,张家湾作为有清一代一个多世纪里的“万里茶路”上几乎唯一的“茶叶转输专用码头”,维护市场秩序的管理机制是通过坐落在其地、有型的建筑——“山西会馆”而体现的。无论是规则的制定还是落实,以及对违反规则的惩戒,乃至于神灵祭祀、娱乐活动等等山西商人的民间性组织活动,都以这座有型的建筑为中心。
目前通州地方文化学者不能谙熟张家湾历史真实的原因,则是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山西商人以及西北商品货物的集散转输消失的年代较早,民族贸易转型、运河淤塞、铁路开通、商路改道等等是主因;另外山西商人西北贸易衰退,返回故里;张家湾地区曾经多次遭受水灾,实体的山西会馆很早就成为“老爷庙”;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调整、急速的时代变革等等也不能忽视。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不仅直接地导致历史记载稀少,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学术范式”——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张家湾历史地位的降低(行政区划),抑或 “商人不入志”、“运河码头村庄化”,造成了“张家湾历史真实”的缺失,直到现在仍鲜为人知。事实上,类似张家湾山西会馆的情形——山西会馆的历史意义被普遍低估,隐藏在会馆背后的山西商人的作用被过度“地域化”,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因此更新和改进学术方法论是目前经济史学的当务之急。
[1]李金龙,等.北京会馆资料集成[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3]赖惠敏.清政府对恰克图商人管理(1755-1799)[J].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1):39-66.
[4]史若民.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贾发义)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n Shanxi Merchants’Guild at Zhangjiawan in Tongzhou,Beijing
MENG Wei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Shanxi Merchants’ Guild at Zhangjiawan is one of the 1000 and more guilds known to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Shanxi merchant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cated at Zhangjiawan in Tongzhou,the north end of Beijing-Hangzhou Canal,it was set up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ere were many official tribute grain transportation centers in Tongzhou,but it existed as a private dock for Shanxi merchants only,and functioned as a center for all business and other activities,such as marketing management,worship ceremonies and entertainments.
Ming and Qing periods; Capital (Beijing); Zhangjiawan in Tongzhou; Shanxi merchants’ guild;dock for merchants only
2016-11-13
2015年北京学基地项目“京师近郊山西商人会馆考察”(BJXJD-KT5051-YB01)
孟 伟(1963-),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民间文献学的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2.010
F129
A
1000-5935(2017)02-006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