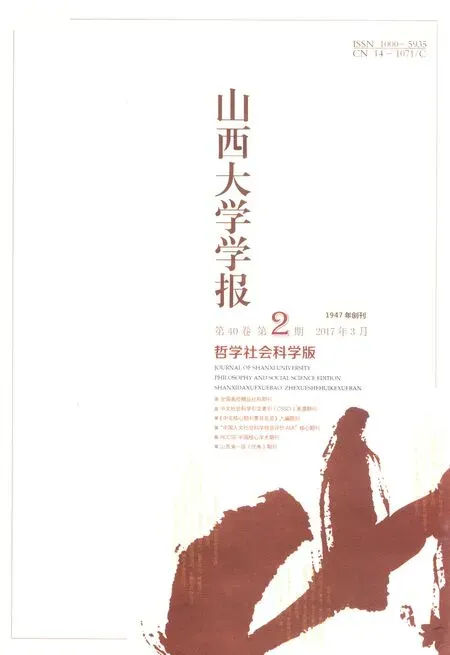空间的焦虑:文学与寻根
2017-04-02吴红涛
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空间的焦虑:文学与寻根
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空间因其外感性与实在性,在文学中常被借喻为某种家园品格。某种程度上,与人类世界相伴而生的家园品格,可视为空间元伦理属性一种。以此为基点,空间在文学抒写中所演绎出的经典情感呼之即出,这种经典情感即是“家之依托”。对于“家乡”这个空间的怀念与感知,在文学中衍化成了独有的文化寻根情结,此种情结源自作家内心失却家园的空间焦虑感,因而在作品创作中,其习惯聚焦于那类承载着家园文化和民族记忆的独特空间。在推崇时间、速度和效率的信息时代里,重审连接空间焦虑感的寻根创作,以此唤起人们寻找家园的“回家”意识,是一个极其迫切且重要的时代命题。
空间;寻根文学;家园;焦虑;现代性
一 “家”之空间与文学情感
从常识的层面出发,无以否认,在文学表达中融入“空间”的元素,是件极其寻常的事情。随处翻开一篇文学作品,我们能够轻易地找到各种有关“空间”的元素,譬如城市、乡村、河流、山川、公路、建筑、树林、长街等。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长期以来,针对文学中的空间元素而展开的研究并不十分受人重视;漫长的文学史中,我们也很少见到以“空间”为关键词的流派或思潮。当代人文学者徐岱教授曾经感慨:“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时间而非空间才是文学的基本存在方式。”[1]这句话指出了上述问题的关键,而“空间”在文学研究中的缺席,当然并非源于“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缺席,很大程度上其在于“时间”对“空间”的无声压制。某种程度上看,这与人们传统认识论中“时间优于空间”的观点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究其原因,就如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所解释的:“不知是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空间在过去就被视为僵死的、呆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则是丰盈的、多产的、有生命的以及辩证的。”[2]而在另外一次演讲中,福柯更是提到:“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累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进程。”[3]18诚然,福柯指称的“历史”,其实便是“时间”的代名词,只不过,被时间所“着魔”的时代不只是19世纪,早在17世纪,牛顿“绝对空间”观的出现,便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时间”的优势性。可以看到,传统、现代、后现代、前现代、古典、新古典、晚期、新历史、新千年等这些人类历史中的明星语词,无不源自“时间”维度的生发。同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古典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此类既往文学进程中的重要流派,也内含着鲜明的时间性元素。与之不同的是,“空间”式命名的创作思潮在文学史中似乎非常罕见。也正因此,美国学者索亚才会调侃性地将“时间性”形容为一种“万能叙事”。[4]
对于文学研究中“空间”被压抑的原因,荷兰著名女学者艾琳·德容(Irene J.F. de Jong)给出过这样的解释:其一是如莱辛所认定的那样,文学是一种时间性艺术,相反,绘画和雕塑才是空间性艺术;其二是因为在文学叙事中,空间常常只是被视为背景装置(background setting)的一种,除此别无其他。[5]从这个富有代表性的观点中我们能够看出,相比于时间,空间在文学中往往是被遗忘和疏落的一方,它或者成为默默无声的背景,或者充当黯淡无光的装衬。显然,这与“空间”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符。我们知道,“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思考和观看世界的基础维度之一,借助于“空间”,我们能够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便明确提出,“空间”和“时间”共同组成了人类的两种“感性直观纯形式”,认为“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之基础的必然的先天表象”。[6]与“时间”所倡导的内部直观不同,“空间”的外部直观显然指向了某种实在性。如果说,“时间”因其内在性和流动性,而为人类世界提供了某种“生命感”和“律动感”的话,那么“空间”则因其外感性和实在性,展示着某种“存在感”和“家园感”之价值。所以有学者总结道:“我们‘存在’,空间是我们的家。”[7]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更是将“家”形容为一种“庇护所”式的空间[8],这其实便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空间”的元伦理属性一种,即与人类世界相伴而生的家园品格。
以此为基点,空间在文学中所演绎的某种经典情感也便呼之即出,这种经典情感即是“家之依托”。古往今来,有太多怀乡或思家的作品,都会在写作中融入鲜明而独特的空间性表述。比如在中国古典文学里,无论是《诗经》中那段让人感伤的“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还是《古诗十九首》中那段令人神悲的“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都为读者呈现了一种空间的画面立体感,前者是细雨迷蒙的“东山”,后者是漫长孤寂的“道路”。而北宋诗人李觏的一首《乡思》,更是代表了“空间”与“乡思诗”的重要关系:“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这首诗巧妙地利用了“天涯”和“碧山”这两种空间背景的转换,使得读者如临其境地沉浸在虽“望极”但仍“已恨”的思家情绪中。诚然,从物质形态上来看,“家”与“乡”本身就是一种居住性空间的存在,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空间被允许进入人的居住这一事实,空间敞开了。”[9]正因此,几乎所有写到“家”或“乡”的文学作品,或多或少地都会首先加入一些空间性的抒写,以便让读者知晓家与乡的某种地方特质所在。例如萧红在其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就在开头部分交代了呼兰河这座小城的空间表征: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10]
在这部小说里,类似空间性描述的文字还有很多。萧红当然并非意在借此来向他人推销“呼兰河”这个令其沉迷的地方,而是因为在这处布满细节的空间里,承载着她的深厚情感,其不仅能为读者更真切地走进小说故事而做好铺垫,也为当时身患重病且孤独贫困的萧红带来了“家”之回忆的温暖。《文心雕龙》中有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1]因“物迁”而生“情感”,因“情感”生而“辞发”,诸多承载“家之依托”的文学写作,莫不如此。从这个视角观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大量的空间书写来转达怀乡之情的巅峰之作,莫过于沈从文的《边城》:“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12],沈从文开篇就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始了《边城》的叙述。夏志清先生认为《边城》的创作离不开沈从文的“田园视景”,[13]177他以一种“牧歌式的文体”,展现了“山水人物”[13]176的情感世界。显然,无论是“田园视景”,还是“山水性格”,都突出了《边城》中鲜明的空间感。在这样的语段里,读者也能够更真切地进入到小说故事所在的空间背景之内,实实在在地感受那个地方的风土和人情,也为正确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命运预先布置了一个无声背景。显然,《边城》之美,除了令人惆怅的爱情之美,也包括了“边城”这个地方的空间之美。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远离家乡的沈从文似乎有意要在这篇小说中,写尽他心里日思夜想的那处湘西之家,“思家”亦是爱情的一种,在《边城》中,被他化为了娓娓动人的等待。
二 空间焦虑与文学表达
当然,更多的时候,文人的思家之情总会夹带着一丝无奈的忧伤感。一方面,这源自浪迹在外,“家”难再见的感叹,如诗人王湾行至北固山下,面对“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样的空间景致,发出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式的千古喟叹,一句“乡书何处达”,更是将他的无奈之情展露无遗。另一方面,这种无奈的忧伤感也源自重回故里,“家”却早不如昨的酸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文中作者时隔多年,再次来到当年那个“杨柳依依”的地方,如今却已物是人非,唯有那条“雨雪纷纷”的“行道”,让人徒添清冷。而唐朝诗人贺知章的那句“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更像是以“门前”这处历久不变的“空间”,来暗示自己内心对“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无奈之痛。清代词学家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有言:“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吾心者”[14],岁月静然流逝,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置身于异乡的某处空间,观览景致,“动心”而思,遥想日日念及的故家,某种空间转换之后的心理落差便应然而生。正所谓:“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乡,苦身不已。”[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社会学专家涂尔干提到的这个观点的确言之成理:“空间”具有相对应的“情感价值”[16],它深刻表征着人的情感世界。
行文至此,我们已有必要点出,在诸多文学作品中,怀乡思家的情感表达,其实都共同指向了某种空间的焦虑感。诚然,在人的意识深处,“家”不仅只是一个固定而客观的物质空间,更为重要的,这处空间连接了人与环境及生活之间的重要脉纹,是人体验生存意义的一种媒介。挪威学者舒尔兹曾经提到:“人之对空间感兴趣,其根源在乎存在。它是由于人抓住了在环境中生活的关系,要为充满事件和行为的世界提出意义或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17]当长期居住或习惯的生活空间发生了改变,那条之前建立的关系链便开始发生断裂,人对环境及世界的感知也由此显得不同往常,生性渴求安居的人,自然会在此种情境下产生莫名的焦虑感。自古多情的文人墨客,其心里弥留许久的焦虑感,更是为一般常人所不能及。从学理上看,“焦虑”这个术语最初来源于拉丁语anxius,其被定义为一种“不安或痛苦的状态”。[18]而在日常生活里,作家的这种焦虑感时常难以得到有效的化解,唯有求助文学或艺术的形式使其婉转再现,方能令其“不安或痛苦”的焦虑得以舒缓。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中如是说道:“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19]
这种促成作家产生焦虑感的“空间”,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那里被称之为“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也有人将其称之为“作为再现性空间的亲历性空间”。[20]此种空间以“物质性空间”(spatial practice)为基础,但在绝对的物质属性之外,还涵包了复杂的象征性品质。[21]譬如“家宅”,从形态上看,它首先是一个由砖瓦水泥组合而成的建筑物,也即是前面所说的“物质性空间”;然而,“家宅”对于人的意义并不仅是一个可供居住的“物质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空间里,存放着人的生活与故事,寄寓着人的希望和梦想。用某位当代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家宅”是“庇护所与身份”(shelter and identity)的一种体认。[22]当代作家汪曾祺就曾在一篇名为《我的家》散文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着“家”的空间结构,诸如:“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临街是铺面。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23]这类看上去似乎稍显沉闷的罗列性文字,形象地印证了“空间感”在家之记忆中的重要性。汪曾祺的目的不是要强迫读者熟稔他曾生活的空间,而是因为那里包裹着他的童年往事,也象征美好的生命体验,让年过古稀的汪先生想起来备感亲切(该文作于汪曾祺71岁之时)。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体验被形容为一种“本源的亲近”:“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24]“本源”即是“家园”,即是“根”,因而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情感称之为“寻根”。当“根”已不在,“寻”之体验本身便会给人带来一种无名的焦虑感。这类承载着“寻根”意味的空间,在作家笔下以文学的方式“再现”,进而逐渐演绎成作品中的经典情感表达,充满了象征意味,列斐伏尔“三元辩证法”中的“再现空间”即是如此。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家对于“家乡”所蕴含的“寻根”之思,大多都还只属于某种私人情绪的抒发。陈世骧先生在著名的《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美学品格,强调的是“诗的音质”和“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25]换句话说,如前文我们所提到的很多作品一样,其由“家乡”这类空间所生发的焦虑感,大多是从作者个人情感记忆出发而建构起来的主观性感知。但我们必须明白,“寻根”远不止于这种“私下”的个体性体验,尤为重要的,它还指称了一种人类文化的共通品格。同样,“家乡”这个独特而又充满魅力的空间,也并不全然是个体情绪的单向表征,它亦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共同隐喻,是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指称的“文化空间”。在《人论》这本经典哲学著作里,卡西尔曾强调:“为了发现空间和时间在人类世界中的真正性质,就必须分析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26]卡西尔的意思非常明确:任何空间背后,都潜藏着相对应的人类文化,这种“文化”显然不单是个人主观情感的宣泄,还是人类整体文化情境的言说与象征。地理学家Jo⊇l Bonnemaisonze在一本名为《文化与空间》(CultureandSpace)的著作中,从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的视域出发,专门论证了空间与文化之间的重要交涉,指出两者的关系实质上是空间的自然属性与象征属性之间的关系。[27]也正因此,当代西方空间研究的著名学者哈维才会开宗明义地谈论,空间具有社会的属性,空间和时间概念同样都依赖文化。[28]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以古典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并未清晰地在作品中将“家乡”这个空间上升为一种超越个体的文化空间,其焦虑感大多出自主观情感的私有体验,而非人类文化的伦理思问。
三 文化空间与文学寻根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里,并不是所有思家寻根的作品都缺乏相应的文化品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这首著名的《春望》中,杜甫便将“国”与“家”连接在一起,使得个体的“思家”之情扩展到了更为深远的“家国”文化。而鲁迅在以其故乡为背景原型的小说《祝福》中,也再现了一些充满文化象征意味的空间,如这段文字:“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到沉寂。”[29]通过小说的整体语境来看,鲁迅显然是意在借此空间感的叙述,来从侧面印证“故乡”这个地方的封闭和愚昧,以及其中封建文化对于祥林嫂的吞噬与戕害。然而,这类作品几乎都是以零散的、非主流的形态存在的,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与系统的文学流派或创作思潮,我们也无法找出一个将“故乡”视作“文化空间”来进行集体写作的文学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前文所分析到的那些源自个体私有情感体验的抒情作品。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遗缺和空白,直到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才最终得以被填补。
在当前这个以娱乐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文学市场环境下,寻根文学的风采早已不复如昨,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寻根文学的确带来过极其轰动的效应。正如叶舒宪教授所评价的:“翻开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寻根文学’已经成为不容忽略的创作流派而占据了专门章节的内容。”[30]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寻根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已萌芽,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的“寻根文学”,直到1984年底才被人所熟知。在杭州举办的一场名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上,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一批日后被视为寻根文学主将的作家,共同唱出了“文化寻根”的主调。换句话说,寻根文学之所以出现,实质是出于文化反思的需要,如陈平原所指出的:“被称为寻根派的诸多作家,实际上理论见解和艺术追求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并试图通过输入现代意识与改变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来重建中国文化。”[31]为何要通过“文学”来重建中国文化?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家园”的失落和“根”的遗忘。随着“文革”浩劫的结束与改革开放的进行,面对各种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传播和渗入,面对新旧文化的交替和更新,众多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开始遭到淡忘,本国文学的创作也在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下显得亦步亦趋。一批曾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作家,对此充满着焦虑感,他们不得不开始思索文学与民族之根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深知,商业化和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会对本土文化构成一定的挑战,而要在“现代性”的时代情境下仍然保持一种文化的健康与自信,就需要重新回到我们民族深处的“根”,去寻找和发现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家园。对此,时隔多年之后,韩少功在某篇文章中重申了这种“焦虑感”:
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 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32]
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在作品中再现文化寻根的焦虑感呢?在这种情境诉求下,“空间”便进入了寻根作家们的视野,“空间”与“寻根”的联系,在其写作中得到了最为贴切的展现。通过研读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寻根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其间有着极为突出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可以从以下两个部分来看:其一直接表现在作品的标题上,代表作品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吴增若的《蔡庄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义的《老井》等;其二是作为小说故事的主题背景,比如莫言《红高粱系列》中的“高密”,郑万隆《异乡异闻系列》中的“老棒子酒馆”和“峡谷”,韩少功《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张炜《古船》中的“洼狸镇”等。可以看到,在这些寻根派小说中,“空间”当然已不只是某种无关紧要的元素,也不再是“时间叙事”的无声陪衬。相反,寻根作家们似乎有意要让这些“空间”跃居到台前,成为作品里无处不在的主角。然而,要在作品中担负重任的“空间”,并不是任意设定的,为了更好凸显文化寻根的意义,作家对于“空间”的选择可谓是用心颇深,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寻根文学中着力描写的空间,几乎都远离现代城市,或者是古老传统的山寨乡野,或者是原始神秘的自然世界。这种设定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组泾渭分明的文化关系:现代城市对应的是工业、市场、货币和全球化,而寻根作品中的“空间”对应的则是农耕、质朴、野性与纯真。后者似乎有意要与前者保持一种对峙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城市会遮蔽文明的本真,正如寻根作家张炜写道:“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33]而张炜之所以要告别城市去寻找真正的野地,正在于他从城市中看到了浮华与失落,那里缺乏家园的安居与温暖,用雷蒙·威廉斯的话来说,城市可视为“一种异化的和冷漠的体制”[34],所以“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33]正因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这句话:“自然景观和地理空间不单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过去的延续。”[35]从这个意义上讲,“融入野地”实质上也即是“寻找家园”。其次,相比于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寻根文学中有不少“空间”是异质的、落后的甚至是荒蛮的,它们鲜被关注,因此也是非主流的。比如《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它“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一脚就踏进云里”,在这里,“蛇虫瘴疟也是实在的。山中多蛇,粗如水桶,细如竹筷”。[36]再比如《小鲍庄》里的“小鲍庄”,“这里地洼,苇子倒长得旺。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弄不好,就飞出蝗虫,飞得天黑日暗。最惧怕的还是水,唯一可做的抵挡便是修坝”。[37]显然,“鸡头寨”和“小鲍庄”这两处空间,在全球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里,无疑是“落寞”的,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很难令人感到愉悦,尤其是那些久居都市的现代人。但是在寻根文学中,它们却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诸多奇异而又真实的人们生长在其中,诸多古怪而又亲切的故事生长在其内。米歇尔·福柯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寻根文学作品中的这类异质空间称之为“异托邦”(heterotopias),与极富光彩和魅力的乌托邦空间不同,“异托邦”显然容易遭到世人的忽略。然而,“乌托邦”再美好,毕竟只为虚构;“异托邦”则不同,它们皆是现实存在的空间,其身上虽有诸多令人规避与厌弃的特征,但它却属于人类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深刻表征着时代的典型症状。借用德国学者格罗伊斯的观点来看,乌托邦空间和异托邦空间的关系,犹如“美妙风景中突然发现一具腐败的动物尸体”一样,乌托邦是美妙风景,异托邦是动物尸体,“在审美价值的刻度上,尸体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要比美丽鲜活的风景要低端很多,而正是这个低端的位置使得尸体不由地成为显示内在世界的一个切实可信的、诚实的符号”。[38]因此,福柯才会将“异托邦”视为一面“镜子”:“我就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种让我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的缺席指出,看见自身。”[3]22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作家之所以刻意选择那些异质的、落后的、荒蛮的异托邦空间来表达文化寻根的诉求,原因恰恰在于它们更能完整地映射人类世界的真实面向,那里安放着人性的纯真,保留着文明的初壳,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更好地审视自我与时代,让那些迷失在现代世界里的上帝之子,重新踏上“回家”的路,这其实也更是寻根文学所要极力彰显本土传统文化的某种价值所在。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再作回首,寻根文学身上最富魅力的印记,或许便是这些承载着家园文化和民族记忆的独特空间。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寻根作品着力彰显的空间里,有一些同时也是写作者自己的故乡,如贾平凹的“商州”、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等等。当然,还有不少作家,其虽未直接在小说中书写自己的故乡,但那些背负着文化寻根意蕴的空间,何尝不是作家内心深处的精神故乡呢?如莫言说的那样:“一个作家难以逃脱自己的经历,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历。有时候,即便是非故乡的经历,也被移植到故乡经历中。”[39]所以,寻根文学从某种视角上看,其实亦算得上是怀乡思家之文学。
四 无根时代与寻找家园
作为寻根作家之一的王安忆,显然意识到了“空间”所蕴含的此种家园性品格,当她去往美国四个月之后,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表达出了这样的心境:
四个月是短短的时间,可是空间加强着时间的感觉,我觉得我去了很久。去了很久而又很远地回来了,回到了我熟悉的土地上来。我那么自然而容易地与它亲近了起来,习惯了起来。[40]
如王安忆自己所说,让她重新体验到故乡亲近感的,恰恰是那片熟悉的土地、熟悉的“空间”,它甚至会反过来“加强着时间的感觉”。但在现代性无孔不入的奠基声里,寻根文学的热潮终于还是隐退了。那些“把根留住”的文化愿景,也逐渐湮没在信息时代的高速轨道中。伤感的是,“根”依然未能“寻”到,美丽家园正变得面目全非,自命不凡的现代人,似乎依然怀抱着浩渺无根的生活。雅斯贝尔斯早有预见性地发现,当今时代“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41]因而有学者形容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虚时代”。[42]从某种意义上看,“空虚”即是“无根”,如果说“寻根”源自于某种情绪的焦虑感,那么“空虚”则源于一种自我放逐的无聊感。在“空虚时代”中,文化之根已遭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当下之享乐。就像利波维茨基所说的,“交流和享乐主义的时代纵容了健忘,纵容了对现实的‘吹毛求疵’,以前的事情都不再重要了”。[43]所以,马克思悲观地感叹道,现代生活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歇尔·鲍曼意识到了马克思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现代生活一个与生俱来的悖论:一面是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和新生活,一面是却对坚固与永恒的不断融化。鲍曼如此描述道:“现代生活既是革命的也是保守的:它意识到各种新的经验与历险的可能,它收到许许多多现代历险都会导致的深厚虚无主义思想的恐吓,它渴望创作并且抓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不管一切都在融化。”[44]
毋庸置疑,现代生活所极力推崇的新奇、进步、速率与革命,背后彰显的正是“时间”之维。与之相反的是,“空间”所代表的坚固、实在和根基则似乎被丢弃在现代性的视野之外了。列斐伏尔用他极富创建性的工作证明了,“空间生产”已然主宰当今时代,而当“空间”都在“时间”的诉求下,纷纷被批量消灭和生产的时候,家园的安居感其实便不复存在了。“拆迁”与“重建”,这对语词精准地概括了诸多空间的现代命运,它们就像过往那些堆砌在橱窗里的商品,被不断生长的人类欲求所改变。齐格蒙特·鲍曼感慨道,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战争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的壕堑战”,而“时间则是战争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远具有攻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领的力量”。[45]正如曾经定格在记忆中的美丽家乡,当生长于其中的空间风貌被时代需求所消解,“家乡”从此也便失去了往日温度。这种由空间变迁所导致的文化记忆之缺失,让作家们不由深感焦虑,他们的心灵被重重地刺痛,因为他们知道,“在我的疼痛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46]
当年那些执意寻根的作家们,面对这些“根”已渐渐崩塌的时局,如今也只剩下了“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式的喟叹。贾平凹说,“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了[47];韩少功则在一旁埋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在铲除一切旧物”。[48]而当“故乡”在人们的印象中愈来愈趋向于这种“概念”或“旧物”的话,那么它终将失去其本有的文化活力,从而沦为记忆博物馆中那一张张黯淡无色的标本,乏人问津。或许,这也便是寻根文学今日的结局所在,在讲究“飞逝的、过渡的和偶然的”[49]信息时代,它必将带着自己曾经的光荣,背离我们渐渐远去,因为“根”已流散,故乡不再。大行其道的,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网络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以及诸多讲究粉丝效应的“粉丝文学”。这类文学创作,正是一种流动的、液态的文学现象,它追求时间和速度,以信息化和快餐化作为自身的主要症候。虽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值得我们伤感的,并不只是寻根创作的行将失宠,而是与之相伴的家园意识的日渐缺失。
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指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下,人们的“时空距离”被逐步消解,一切都在提速,但这种全面提速也会导致其否定性的一面,那便是“现代人在陷入焦虑的时候,无根、怅然迷惘以及缺乏实际感受的空虚感”[50]。因此,如何在“无根”的时代,重审“寻根”的意义,不仅是一个迫切而关键的文化命题,也是当代文学亟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而所谓“寻根”,也即“意味着寻找一个本已或曾经存在而现在却失去了的‘根’”。[51]当然,我们不能借此而轻率幼稚地认定,只要重新倾力倡导寻根文学,便能成功恢复和保全人类的文化记忆,令我们再次找回家园的根基与本真。但是,寻根文学创作中对于现代空间的焦虑与隐忧,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所主张的寻根情怀与家园意识,今天看来,依然有其不可忽略的重大价值。兴许,等到我们失去“故乡”,最终都已身为“异乡人”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寻找家园”的可贵与不易。
[1]徐 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89.
[2]Michel Foucault.Questions on Geography[M]∥in Cordon C.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7:70.
[3]【法】福 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Edward W. 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M].London: Verso,1989:11 .
[5]de Jong,Irene J F.Space in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M].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2012:1.
[6]【德】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
[7]Tarthang Tulku.Knowledge of Time and Space[M].Oakland: Dharma Press,1990:119.
[8]【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
[9]【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41.
[10]萧 红.呼兰河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3-4.
[11]刘 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3.
[12]沈从文.边城[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9.
[13]【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李欧梵,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4]郭绍虞,罗泽根.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0.
[15]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792.
[16]【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 东,汲 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2.
[17]【挪威】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M].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1.
[18]【美】艾伦·T.贝克,等.焦虑症和恐惧症:一种认知的观点[M].张旭东,王爱娟,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7.
[1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27.
[20]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416.
[21]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1:33.
[22]Gerry Smyth,Jo Croft.Our Hou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Domestic Space in Modern Culture[M].New York: Amsterdam,2006:13 .
[2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12.
[24]【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69.
[25]陈世骧.陈世骧文存[M].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32.
[26]【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 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64.
[27]Jo⊇l Bonnemaison.Culture and Space[M].Josée Pénot-Demetry,London: I.B.Tauris,2004:2 .
[28]【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39.
[29]鲁 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
[30]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207.
[31]陈平原.文化·寻根·语码[J].读书,1986(1):41.
[32]韩少功.寻根群体的条件[J].上海文化,2009(5):14.
[33]张 炜.融入野地[J].上海文学,1993(1):4.
[34]【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31.
[35]【法】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M].顾 良,张泽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5.
[36]韩少功.爸爸爸[J].人民文学,1985(6):83-85.
[37]王安忆.小鲍庄[J].中国作家,1985(2):43.
[38]【德】鲍里斯·格罗伊斯.揣测与媒介[M].张 芸,刘振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7.
[39]莫 言.超越故乡[J].名作欣赏,2013(1):59.
[40]王安忆.归去来兮[J].文艺研究,1985(2):76.
[41]【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
[42]徐 岱.审美正义与伦理美学[J].文学评论,2014(2):116.
[43]【法】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77.
[44]【美】马歇尔·鲍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徐大建,张 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
[4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4.
[46]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3.
[47]贾平凹.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J].当代作家评论,2005(2):156.
[48]韩少功.山居心情[J].小说界,2006(3):13.
[49]【英】戴维·弗里比斯.现代性的碎片[M].卢临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2.
[50]William Barrett.Irrational Man[M].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1962:35.
[51]张 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53.
(责任编辑 李雪枫)
Spatial Anxiety: Literature and Root-seeking
WU Hong-tao
(SchoolofLiterature&Journalism,ShangraoNormalUniversity,Shangrao334001,China)
Space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some kind of homeland character in literature for its externality and substantiality. In a way, the homeland character which comes with human world can be regarded as one meta-ethics of space. For this reason, there is a classic emotion of space in literary works which is called 'Home-relying'. The memory and perception of homeland has evolved into a unique cultural root-seeking complex, which stems from the spatial anxiety of the writers for losing their homeland, therefore, i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they are used to focusing on the kind of space which bears the homeland culture and national mem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hich respects time, speed and efficiency, it's a extremely urgent and important proposition to review the root-seeking creation connected with spatial anxiety.
space;root-seeking literature; homeland; anxiety; modernity
2016-07-2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X034)
吴红涛(1984-),男,江西上饶人,博士,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及空间文化批评研究。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2.007
I206.09
A
1000-5935(2017)02-00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