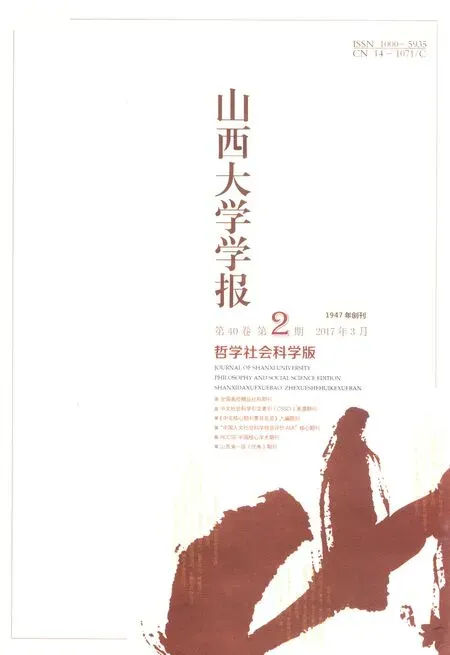庆历之际的经学新变与古文
2017-04-02方笑一
方笑一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庆历之际的经学新变与古文
方笑一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宋代经学在仁宗庆历之际的新变影响了文学,尤其是古文的观念与创作方面。士人将经书义理与社会人事相联系,推动了古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范仲淹在创作古文时引入《易》理,成为欧阳修等人的先导。孙复、石介猛烈批判当时文风,但主要不是在文章写作传统的内部展开,而是以作者的经学观念和主张为依据。
庆历;经学;新变;古文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宋代经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1]28,而“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2]1095。清人皮锡瑞由此指出:“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3]220从宋朝立国到庆历年间,已经经历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国家治理中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经学的新变,可以看作制度和社会变革在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反映,或者说,集中代表了北宋学术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宋代经学在庆历之际所经历的重要变化,使之真正开始与汉唐经学相区别,显现出“宋学”的独特面目。①以庆历为宋代经学革新的时间起点,亦屡见于今人著述,详见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1页;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庆历之际经学的新变,也影响到文学,尤其是古文的观念与创作方面。宋初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本就以尊经为前提,以六经为楷模,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的分歧,仅仅是对于应该从六经中学习什么,以及如何取法于六经的分歧。②关于宋初古文家在古文理论方面的分歧,参见笔者《宋初古文家之经学与古文——以柳开、王禹偁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收录于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9-239页。当庆历之际,在经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形下,经学与古文关系,更加引发笔者的学术兴趣。经学的新变究竟对当时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本论题的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欧阳修、尹洙身上,涉及庆历之际的其他人物时,往往将之作为讨论欧阳修时的背景。③刘越峰的《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只讨论了胡瑗、孙复、石介、周敦颐、张载、邵雍、范仲淹、刘敞、李觏的学术思想,未涉及其与古文的关系,见该书第34-161页;对欧阳修经学与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参见巩本栋:《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马兴祥和李建军则讨论了《春秋》学和欧阳修、尹洙古文的关系,参见马兴祥:《北宋经学与文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156页;李建军:《〈春秋〉义法与北宋古文运动——以尹洙、欧阳修考察中心》,《国学研究》第3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165页。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庆历之际经学与古文的关系再进行一些探索。
一 范仲淹对经学新变的推助
庆历之际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庆历新政”。这场由范仲淹等人主导的全面革新虽然没有成功,但对于北宋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而深远的。在新政诸项举措中,有与经学直接相关的内容,集中在科举和学校方面。庆历三年(1043)九月,在范仲淹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第三事为“精贡举”。对于学校措置方面,建议“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具体做法则是“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科举方面,建议“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其效果在于“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改革措施,是因为范仲淹深感当时人才匮乏,“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他认为能够通过这样的变革以求得“经济之才”和“救弊之术”[4]529。仁宗诏近臣议,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等人联合上奏,提出“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校外,其余并各令立学。如本处修学人及二百人已上处,许更置县学”,“若少文学官可差,即令本处举人众举有德行艺业之人在学教授。”[5]4273并要求改革科举制度:“进士并试三场:先试策二道,一问经史,二问时务;次试论一首;次试诗、赋各一首。三场皆通考去留。旧试帖经、墨义,今并罢。”[5]4274是月乙亥,仁宗正式下达诏令,显示之前兴学和改革贡举的建议被接纳,其中规定:“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谴,以名闻”,科举方面规定“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6]3564-3565。州县立学的举措,对宋代学术文化之发展影响尤其深远,“庆历诏诸路、州、府、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于是州郡不置学者鲜矣。”[5]2188其效果,正如南宋光宗时大臣所言:“惟我国家,内自京师,外及郡县,皆置学校。庆历以后,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矣。”[5]2186庆历科举改革的倾向则清楚表明,策、论因为能使“辨理者得尽其说”,而受到重视,讲说经书义理的“大义”比主要靠死记硬背的“帖经”、“墨义”两种方式更受重视。虽然最后由于新政失败,所颁布的这个《详定贡举条制》没有真正施行,但它预示了今后科举改革的方向。
作为庆历之际经学新变的大背景,兴学和科举改革主要是由范仲淹等士大夫倡议的,范仲淹本人也利用自己身居官位的条件,聚集起一批精通经学的士人,在其推荐之下,崇儒尊经的士人们有了进行经学活动的空间。这里有必要对范仲淹的学术经历作一概述。范氏少年就学于睢阳书院。睢阳书院又名应天府书院、南京书院,是在宋初著名儒士戚同文旧居基础上创建的。《宋会要》载其事甚详:
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二十四日,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府民曹诚为本府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故工部侍郎许骧、侍御史宗度、度支员外郎郭承范、董循、右谏议大夫陈象舆、屯田郎中王砺、太常博士滕涉皆其门人。同文卒后,无能继其业者。同文有子二人,维为职方员外郎,纶为龙图阁待制。至是,诚出家财,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令同文孙奉礼郎舜宾主之。召明经艺者讲习。本府以闻,故有是命。并赐院额,仍令本府职事官提举。[5]2188
可见当时的应天府书院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范仲淹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此前在该书院学习。关于书院的兴建缘由和培养人才的情况,范氏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也有所记述,称“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4]192,可见一时人才之盛。范仲淹在这样的环境中刻苦学习,“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7]587。而六经之中,范氏最精通的是《周易》。《宋史》本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8]10267-1026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非但于经学学有专长,而且乐于汇聚精通经学的人才,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与宋初提倡儒学者相比,范仲淹的地位有很大不同。庆历新政之前,他已经为官二十多年,兼具地方官与京官的经历,在官场有一定地位。这就为他推举人才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有几位最重要的经学家都受到范氏的举荐。他上奏荐胡瑗、李觏为太学学官,对两人的学术给予极高评价:
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又建昌军应茂才异等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搜贤之日,可遗于草泽,无补风化。伏望圣慈特令敦遣,延于庠序,仍索所著文字进呈,则见非常儒之学取进止。[4]615
景祐元年(1034)他出知苏州,兴建府学,先请孙复前来讲学:“或能枉驾,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才,是亦先生之为政。”[4]688未果后又邀请胡瑗讲学,《宋元学案》载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9]24。在饶州、润州知州任上又延请李觏来讲学[4]390,并向朝廷推荐:“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伏乞朝廷优赐就除一官。”[4]451应该说胡瑗、孙复、李觏诸人在士人群体中能产生学术影响,除了本人的经学成就之外,范仲淹的赏识和推荐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庆历新政中推出的兴学校、改科举的措施,以及主导者范仲淹本人对通经人才的举荐,为庆历之际经学新变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范仲淹举荐的经学家中,各人的学术观点和关注点相当不同,胡瑗讲究“明体达用”,孙复揭示《春秋》“尊王”大义,石介以经书为依据批判佛老和骈文,李觏从《周礼》中寻求“太平”和“富强”之道,这显示了庆历之际经学新变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经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各种异说纷纷出炉,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局面。日本学者诸桥辙次认为唐、宋经学“最主要的差异是唐代经学界有定于一尊的倾向,而宋代经学界则有强调分化的倾向”[10]120,可以说,这种“分化的倾向”正是从庆历之际开始的。
二 经学的多元化与主观性
在前述庆历四年(1044)三月仁宗所下兴学校与改革贡举的诏书中,开头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牵拘之,则吾豪隽奇伟之士何以奋焉?”[5]4276它说明了兴学校和改革贡举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学者充分阐述他们自己关于“天地人之理” 和“古今治乱之源”的各种学说,而当时注重“声病、章句”的考试方式不利于学者发表各自的见解。真宗时王旦因为贾边考试时舍注疏而立异论,而毅然将其黜落。这种不允许“立异论”的局面,到了仁宗朝就逐步瓦解。此时,士大夫“异论”纷起,再也无法遏制。对此,张方平有过一番描述:
国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说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谚曰:“水到鱼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术驭下。王文正公(旦)为相,南省试《当仁不让于师赋》,时贾边、李迪皆有名场屋,及奏名,而边、迪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迪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王文正议:“落韵失于不详审耳,若舍注疏而立异论,不可辄许,恐从今士子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曾)、吕许公(夷简)犹持此论。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11]81-82
不难看出,张方平内心是认同真宗以前“天下私说不行”局面的,也举了当年王旦“取迪而黜边”的例子,而对六科(制科)设立以来士人异议纷纭、以影响朝廷的情况深有不满,但他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宋仁宗初年以后,士人各种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绝无可能再回到不允许“舍注疏而立异论”的时代了。
事实上,各种私说的兴起,恰恰反映了当时的士人不满足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不满足于对天人关系、治乱兴衰等问题的既有看法,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力求学术的发展与创新。对此,全祖望用“学统四起”来形容,他总结道: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当作“师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9]251-252
这里提到的学者,包括泰山先生孙复一派的士建中、刘颜,安定先生胡瑗一派的“明州五子”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永嘉的王开祖、丁昌期,浙西杭州的吴师仁。古灵先生陈襄一派的章望之、黄晞,关学张载的先驱侯可、申颜,以及蜀学范祖禹的先驱宇文之邵。纷起的“学统”无疑给当时的学界吹来一股自由之风,使得人们从旧经学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事实上打破了经学一元化的格局,形成了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源于士大夫对旧经学的不满,而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经学无法担负起宋人试图通过经书来深究天人之理,探寻历代治乱之源,阐述自身价值观念,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任务。宋人对儒家之道的内涵以及传承有新的理解,对于本朝之区别于汉、唐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当士人试图在经书中寻找他们所注重的儒道时,却发现旧经学的解释问题重重。在他们看来,其中不少解释和解释的方法都是错误的。士人甚至认为,儒家经书的文本本身以及某经书为某某著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由此,疑经、疑传注成为一时学术风尚。关于宋代的疑经,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讨论,兹不赘述。*对宋代疑经的整体性研究可参见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
既然对汉唐注疏多有不满,那么宋代士人自然要对经书重新加以解释。所以“疑经”只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提供新的解释。李觏说:“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12]276朱熹也曾说过:“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13]2089李觏是庆历之际经学新变的当事人,朱熹则是后来的追述者。非常巧合的是,李觏本人也名列朱熹所称赏的学者之一。而将两人的话前后映照,正好可以看出庆历之际新经学“异于注疏”的特点,用朱熹的话来概括,就是“自出议论”、“理义复明”。也就是说,士人获得了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和观点解经的学术空间,而其解经的着眼点则主要在于经书的义理,这两点是庆历之际新经学的核心特色。
限于篇幅,这里举三个例子。
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说:
“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种使得其所,故谓之四德:言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又当以嘉美之事,会合万物,令使开通而为“亨”也。又当以义协和万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也。又当以贞固干事,使物各得其正而为“贞”也。是以圣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贞”。[14]13
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则作这样的解释:
元为乐,亨为礼,利为刑,贞为政。何则?盖元者始生万物,万物得其生,然后鼓舞而和乐。圣人法之,制乐以治天下,则天下之民,亦熙然而和乐,故以元为乐也。天下既以和乐,然而不节则乱,鼓圣人制礼以定之,使上下有分,尊卑有序,故以亨为礼也。夫礼乐既行,然其间不无不率教者,圣人虽有爱民之心,亦不得已乃为刑以治之,于是大则有征伐之具,小则有鞭朴之法,使民皆畏罪而迁善,故以利为刑也。夫天下既有乐以和之,礼以节之,刑以治之,不以正道终之,则不可也。故政者正也,使民物各得其正,故贞为政也。夫四者达而不悖,则天下之能事毕矣。故四者在《易》则为元亨利贞,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五常则为仁义礼智,圣人备于《乾》之下,以极天地之道,而尽人事之理也。[15]174
相对照之下不难看出,虽然孔颖达也以“元、亨、利、贞”为四德,也提到圣人运此四德而长万物,但其阐说的核心在于“物”,在于自然之物的生成和变化的状态,总体上恪守其所征引的子夏《易传》的解释。而胡瑗则在“圣人法之”四字之下,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新解释。概括而言,胡瑗的关注点不再是“物”,而转向“人”,他据卦辞阐说了一番圣人以礼、乐、刑、政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道理。正如胡氏最后说的,“极天地之道”目的在于“尽人事之理”。事实上,胡瑗通过对乾卦卦辞的解释,勾画出的不再是一幅万物变化的蓝图,而是一幅治国理政的路线图,其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注释者本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而在胡瑗看来,并不是他自己主观上将这些义理强加到卦辞上去的,而是《周易》经文本身就包含了这些义理,诠释者只不过将它们发掘出来而已。
又如当时《春秋》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16]289有了这样的观念前导,孙复解释《春秋》当然就带上了明确的指向性,“尊王”之义成为该书最需要阐发的《春秋》义理。如释庄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陈人杀其公子御寇”云: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此言“陈人杀其公子御寇”者,讥专杀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无天王杀大夫文,书诸侯杀大夫者四十七,何哉?古者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诸侯不得专命也。大夫有罪,则请于天子,诸侯不得专杀也。大夫犹不得专杀,况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国无大小,其卿、大夫、士皆专命之,有罪无罪皆专杀之,其无王也甚矣!故孔子从而录之,以诛其恶。称君、称国、称人,虽有重轻,而其专杀之罪则一也。[16]299
这里被杀的御寇并非大夫,而是公子,但孙复借此事讲了一大套“大夫有罪,诸侯不得专杀”的道理。因为在孙复看来,大夫虽然地位低于诸侯,可他们是由天子任命的,由此一旦大夫有罪,应该惩杀他们的也不能是诸侯,而只能是天子。假如诸侯擅自杀了大夫,就是越权行事。而孙复郑重指出:“春秋之世,国无大小,其卿、大夫、士皆专命之,有罪无罪皆专杀之,其无王也甚矣!”这里的“无王”二字,醒豁地点出了“专杀”问题的关键,也将孙复所看到的《春秋》“尊王”之义明确地阐发出来。这一层意思,无论是初唐官修之《春秋左传正义》,还是中唐啖、赵、陆学派的《春秋集传纂例》均未道及,可以看作孙复自己对“尊王”之义的大发挥。至于被诠释的《春秋》经文中到底有没有孙复所讲的意思,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又如《诗经·卫风·氓》中有一句话:“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小序》对全诗有整体解释:“《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而对于诗中此句,郑玄《笺》、孔颖达《正义》与欧阳修《诗本义》的诠释不同。《笺》云:“尔,女也。复关既见此妇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为室家矣。兆卦之繇,无凶咨之辞,言其皆吉,又诱定之。”《正义》云:“此男子实不卜筮,而言皆吉无凶咎者,又诱以定之。前因贸丝以诱之,今复言卜筮以诱之,故言又也。” 显然,两者都将此句解释成男子对女子说的话:我为你卜筮,结果是吉利的,你很适合做我的妻子。这样说目的是为了诱骗该女子,使之从己。《正义》干脆认为男子根本就没有卜筮,只是说这话来欺骗女子的。但欧阳修《诗本义》云:“《氓》据《序》是卫国淫奔之女色衰,而为其男子所弃,困而自悔之辞也。今考其诗,一篇始终皆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据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序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 他不同意《笺》的说法,认为这里的“尔”不是诗中男子指女子,而是女子指男子。他认为,“尔卜尔筮,体无咎言”是诗中女子对男子说的话,是女子被男子抛弃后,回忆男子当初如何甜言蜜语诱骗她。欧阳修和郑玄、孔颖达在解释“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这句话时的分歧显而易见。他们都想对这句话作出正确的解释,而欧阳修和郑、孔之见显然只有一方是正确的,因为这句话不可能既是用女子口吻说,又是用男子口吻说的。从经学的角度看,欧阳修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其一,他根据《小序》的说法,说明这首诗是女子被抛弃后“困而自悔之辞”,全诗是以女子责备的口吻写成。
其二,正因为如此,诗中的人称代词“子”、“尔”,都是女子称其男子,而不是相反。
其三,此句上下文中并没有男子的话,通篇都是女对男说,这里假如忽然插进一句男子对女子说的话,就显得非常突兀,不合文理。
因此,从经学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欧阳修在解释此句时,以富有说服力的推断,纠正了郑玄和孔颖达的错误之处。比解释诗句准确与否更值得关注的,是郑玄、孔颖达与欧阳修是从何种视角、以何种方式解释经文的。郑玄是从字(“尔”)的释义出发,然后用散句将诗中原句加以复述,来解释经文的。孔颖达与郑玄略有不同,认为“此男子实不卜筮”,但总体上仍遵循郑《笺》。欧阳修的解释,则是从诗歌文本整体的意义出发的。他先以《小序》对此诗主旨的概括为自己的说法张本,然后是从通篇(“一篇始终”、“上下文”)的“文理”的连贯性出发,来驳斥郑玄之说。也就是说,欧阳修认为整首诗歌的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自有“文理”。判断“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这一句是男对女说还是女对男言,不能孤立来看,而是必须将其放置在诗歌文本的整体之中来考察,用通篇的文理,也即文章逻辑的连贯性来衡量这句话究竟用谁的口吻写成。欧阳修的解释从《小序》对此诗主旨的概括出发,以自己对此诗内容的总述作结,充分说明他诠释经书的方法立足于经书文本整体意义和内在逻辑的连贯性,把一句经文放置在经书整体意义之下给予解释,充分表明了欧阳修对于经书整体性意义的重视,而不是将一章一句孤立地来看待。
庆历之际经学风气的转变,导致了各家学者都热衷于根据自己的意见诠释经书。由此而形成学者纷纭的局面。单就疑经这一点而论,据考察,宋代疑经的学者就有165位之众。[17]1更为重要的是,士人对经学相对自由的研究和思考,对经书义理的揭示和阐发,尤其是他们将经书义理与社会人事相联系的做法,客观上推动了古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般的记、序等文体引用经书并加阐发的情况开始多见。以下用范仲淹、孙复、石介三人作为代表,来讨论庆历之际经学与古文的关系。欧阳修的情况或许更具有代表性,但鉴于学界已经有较多研究,本文姑且从略。
三 范仲淹、孙复、石介的经学与古文
范仲淹之所以如此重视淹通经学的人才,除了缘于他早年在书院的学习经历之外,还由于在其本人的政治理想和理念中,尊经重文的观念本就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把经学和国家对人才的培育联系起来看待,同时也将其与文章的盛衰挂起钩来。他认为: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在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在宗经这一大原则下,范仲淹进一步将经学的重要性与文章盛衰相联系,指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4]237-238。在这里,范仲淹将经学、文章、风俗与选材四者的因果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晰。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范氏也不乏类似的阐述,并皆明确将“虞夏之书”与“南朝之文”相对立,作为正反两方面的典范。[4]200由此可见,范仲淹的态度十分鲜明,就是提倡以上古经典的文本作为典范,反对南朝的骈文。范仲淹于经学非但提倡,而且身体力行从事研究,尤擅长《易》学。今存范氏《易义》二十七则,解释了《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二十七卦,是北宋经学新变发生时期的重要经学著作。从其解《易》的路数看,当属于义理派,而要言不烦,重视用《易》来阐述天子、君臣、孝悌等儒家核心范畴的意义。其中时见范氏的寻求变革的思想。如释“革”曰:“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之时也。夫泽有水则得其宜,今泽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然而反常之权天下何由而从之?以其内文明而外说也。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无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听矣。”[4]148虽然范仲淹的《易义》将《易》的内容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显得较为直接,从更高的层面说,尚缺乏对《易》的形而上的诠释,但他的解说通俗易懂,体现解释者主观意图的地方也极为明显,这反而为《易》学对文学施加影响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如范仲淹本人就撰写过以《周易》经传文字命名的十篇赋,*这十篇赋分别题为《蒙以养正赋》、《贤不家食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才赋》、《乾为金赋》、《体仁足以长人赋》、《制器尚象赋》、《天道益谦赋》、《圣人大宝曰位赋》、《水火不相人而相资赋》,对它们的详细分析参见李凯:《范仲淹与〈易〉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同时他也是北宋时期较早将《易》理融入古文创作的作者。除了在奏章中引用《周易》为自己张目外,范仲淹还将《易》语引入杂记文中。如宝元二年(1039)知越州时所作《清白堂记》,记述了作者在州署边废井中重获嘉泉之事,照例这是极为平常之举,可文中除去描写清泉之甘洌外,在最后点题时不忘引用《周易》:
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4]193
作者从身边之井联系到《周易》的“井”卦,并据《周易》经文概括出“井”的两大象征意义:“所守不迁”、“所施不私”。很明显,前者对应了士大夫所应具备的人格操守,后者对应了士大夫良好的道德品质。作者最后所说的“清白而有德义”,显然不是单就井水而言,而是指向了其对士大夫理想人格的理解。这样一来,这篇寻常的杂记文就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在宋代士大夫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作者借《易》理来呼唤一种“清白而有德义”的士大夫人格楷模。作者之所以在文章中如此应用《周易》,和他的《易》学本身是分不开的。在其所撰二十七则《易义》中,恰好有一则对“井”卦作了解释:
水为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迁惠之时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无所不利。君子居于德而不可移,其惠之迁也无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穷,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于人而不见其亏,独善于身而不见其余,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4]148
这里就将作者对卦义的理解讲得更明白了,而与《清白堂记》对“井”卦意义的发挥完全一致。其中讲到君子的“居德迁惠”,正与《清白堂记》中“所守不迁”、“所施不私”相对应,只不过《易义》中解释得更为具体而已。
而在《邠州建学记》一文的末尾,作者也同样引用《周易》:
予尝观《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谓其道未通,则畜乎文德,俟时而行也。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谓相说之道,必利乎正,莫大于讲习也。诸生其能知吾君建学,圣人大《易》之旨则庶几乎!故书之。[4]196
作者将建学讲习的意义,用“小畜”和“兑”两卦之义来阐发,可谓别出心裁,又相当贴切。我们今天仍可从《易义》释“兑”卦时所云“上下皆说之时,必内存其刚正”[4]151,来返照文中的“相说之道,必利乎正”一语,证明范氏引《易》理入文章,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以其对《易》理的重新诠释为基础的。
在评论古文时,范仲淹也时以儒家经书为标准。最为著名的是其对古文家尹洙的一段评论:
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4]183
在这里,范氏不但精到地总结出尹洙古文“辞约而理精”的特点,并且把这种特点的形成与其人“深于《春秋》”联系起来,可见其将《春秋》的行文视作文章典范的倾向。
范仲淹的经学著作不多,古文观念和创作中涉及经学的内容也比较有限,但庆历之际著名士人兼擅经学与古文的特征,在范氏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加上他积极推荐经学人才,对北宋经学新变与古文发展可以说厥功甚伟。他在古文创作时引入《易》理的写法,也为欧阳修等人频繁用《易》提升古文立意的做法提供了先导。
在范仲淹向朝廷推荐的经学人才中,对经学贡献甚大而又兼备古文造诣者,当数孙复。而孙复弟子石介,虽然没有受到过范氏的直接举荐,但在庆历新政中,对于范仲淹等革新派的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孙复、石介在当时颇有学术声望,又都曾担任过国子监直讲。孙复在经学上地位更高,所撰《春秋尊王发微》是北宋新经学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石介对于儒家学说和经书的推崇不遗余力,见于文章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继范仲淹之后,将对经书的尊崇和对当时文风的批判更为具体地联系起来,经学本身成为他俩批评声律对偶之文的重要理论资源。
读孙复、石介的著述,不难发现他们对于当时的文风相当不满,曾经给予非常猛烈的批判,这样一种批判往往并非在文章写作传统的内部展开,而是与学术文化相联系,尤其是以作者在经学上的观念和主张为依据的。虽然孙复本人的经学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与其文章观念似乎并不直接相关,石介也没有专门的经学著述,但他们以经学为依据,对当时文风展开的批评,是观察庆历之际经学与古文关系不可忽视的历史维度。
孙复对文章的性质和功能有明确的表述,他在《答张泂书》中说: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是故《诗》、《书》、《礼》、《乐》、《大易》、《春秋》之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18]293-294
在孙复看来,文章并非是抒发主观情志的作品,而是“道之用”,也就是“道”的器用、应用。文章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功能:“适其用”和“张其教”。在对文章的性质和功能作出如此认定之后,作为“道”的文字载体的六经当然是地位最高的“圣人之文”,而后世所有的写作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只是“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高举起“斯文”的概念,他这样教导张泂:
明远无志于文则已,若有志也,必在潜其心而索其道,潜其心而索其道,则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则其所言也必远,既深且远,则庶乎可望于斯文也。不然,则浅且近矣,曷可望于斯文哉!
噫!斯文之难至也久矣。自西汉至李唐其间,鸿生硕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言杂乎其中,至有盈编满集,发而视之,无一言及于教化者,此非无用瞽言,徒污简册者乎?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18]294
孙复所说的“斯文”,主要指文章而言,他认为文章作者必当潜心索道,写出的文字才能意蕴深远。他检视了西汉以来的文章,认为其在内容上夹杂了很多异端思想,而文章形式上已被南朝的骈文家们所污染,所以前代纵然留下大量文章,但对于教化是毫无作用的。他只推崇董、扬、王、韩四人,因为只有他们能做到思想上“不叛”,行文上“不杂”。
对于“斯文”的衰落,孙复是极其痛心的,他说:“国朝自柳仲涂开、王元之禹偁、孙汉公何、种明逸放、张晦之景既往,虽来者纷纷,鲜克有议于斯文者,诚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18]293我们发现,他在这里所推崇的柳开、王禹偁、孙何、种放、张景五人,背景虽然不尽相同,但都隶属于宋初同时热衷于经学和古文的士人群体之中。显然,孙复要将复兴“斯文”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兼擅经学与古文的文化前辈身上。
斯文的颓坏,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原因的,孙复对此作了分析。总括他的说法,从历史上说,非儒学的异端思想充斥于文章,“战国迨于李唐,空阔诞谩、奇险淫丽谲怪之说,乱我夫子之道者数矣。非一贤殁,一贤出,羽之翼之,则晦且坠矣。”[18]292-293假如以儒家为时间参照,这里的异端,既包括“乱之于前”的杨朱、墨翟思想,也包括“杂之于后”的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更指向至今“横乎中国”的佛老思想。孙复认为,异端横行,实为“儒者之辱”[18]309。而孙复眼中,驱除异端的办法,无外乎董仲舒式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熄灭邪说”[18]303;从现实来看,斯文的衰落,则与取士制度有关。孙复对当时所施行的辞赋取士制度深为不满,他曾向范仲淹指出:“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徇世俗之士,则孰克舍于彼而取于此乎?”[18]290在给范仲淹的另一封信中,孙复更为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经学主张。首先,他提出,虞夏商周之治,皆在于六经,而“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其次,对前代的注疏,尤其是官方颁行天下、作为考试标准的汉唐注疏,孙复持明确的批评态度。在逐一评述后,他进而轻蔑地反问道:“彼数子之说,既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而可藏于太学,行于天下哉?”最后,他向范仲淹郑重提出重新注释经书的建议:
执事亟宜上言天子,广诏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覆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大出王(弼)、韩(康伯)、左(氏)、穀(梁)、公(羊)、杜(预)、何(休)、毛(苌)、范(宁)、郑(玄)、孔(安国)之右者,重为批注,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复矣,不其休哉![18]291-292
应该说,相对于孙复本人文章所受经学的影响,他的经学观念和文章观念更值得重视。他的论述虽然不多,但所提出的变革经学、取士制度、文风的要求,都针对并切中了他那个时代学术文化之弊端。并且,这些要求又是相互关联的,背后则是面对佛老思想挑战而产生的深刻的危机意识。
由这种危机意识所触发,在言论上更走向极端的,是孙复的弟子石介。石介尝撰《怪说》三篇,反对佛老和杨亿,在上篇中,石介斥佛老为“汗漫不经之教”、“妖诞幻惑之说”,认为其严重冲击和扰乱了“礼乐”、“道德”、“五常”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中篇则集中反对杨亿的文风,其中对这种文风特征的概括,如“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等等表述,常为文学史家所征引,但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石介批判杨亿文风是以儒家经书为标准和依据的,在石介看来,杨亿的罪状在于对儒家经书的破坏,这里不妨完整引用石介的文字:
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十翼》,而为杨亿之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19]62-63
显然,石介首先以《书》、《诗》、《易》、《春秋》这四部儒家经书的文字作为文章的最高标准,然后指斥杨亿所追求的文风,表面华丽,实质是对以上经书内容和文字形式的毁坏,所谓“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更为严重的是,杨亿的文章,竟被作为新的典范,妄图或者已经取代上述儒家经书所树立的文章典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亿文风对于儒家的危害,对于经书正统地位所构成的挑战,并不下于佛老,故而被石介拿来与后者相提并论了。
经书之所以被石介视为文字的典范,除了作为圣人之道的载体之外,其文辞的确富有深意。如《周易》是圣人救乱而作,“乱有深浅,故文有繁省”,“文王、夫子非以衒辞,明易也”[19]78-79。《春秋》的编纂主旨在于“明帝王之道”,故“其文要而简,其道正而一”[19]81由此看来,经书的文辞并非随意而为,其形式背后有圣人的旨意存焉,因而它的典范性是不容动摇和毁坏的。
不难发现,无论是石介对当时文风进行激烈批评,还是他在给“文”下定义时,其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经书。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在两处重复引用了某些经书中的相关论述。其《上赵先生书》云:
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正,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传》曰:“经纬天地曰文。”尧则曰:“钦明文思。”禹则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则曰:“郁郁乎文哉!”汉则曰:“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19]136
在《上蔡副枢书》中说:
文之时义大矣哉!故《春秋传》曰:“经纬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刚健。”《语》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三王之政曰:“救质莫若文。”尧之德曰:“焕乎其有文章。”舜则曰:“浚哲文明。”禹则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则曰:“郁郁乎文哉!”汉则曰:“与三代同风。”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19]143-144
上述两段话中,非但引用了《周易》、《左传》、《尚书》、《论语》等经书中对于“文”的论述,而且其中引《左传》“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郁郁乎文哉”、《尚书》“文命敷于四海”这三句话还是重复的。虽然以上经书所言之“文”有时指文化、文献,并不能简单地完全等同于文章,但石介对于文章性质、功能、形态等方面的理解,无疑深受儒家经书中关于“文”的这些论述的影响,经书中的表述可以说是石介文章观念的主要来源。
由于文献留存的关系,以上三人古文创作中所受经学具体影响的痕迹还比较有限,在欧阳修的古文创作中,经学尤其是《易》学的影响就更为明显[20]。需要特别补充的是,欧阳修之所以能将经学成功地化用于古文的写作之中,与其观念上摆脱了对经书语言形式的机械模仿有关,更与其对经书内容和义理的体认有关,对于儒家经书,他关注的重心很大程度上从道德转向了情感,这种转向使得经书义理不再是抽象的原则和道理,而与士人人生命运与情感世界连结为一体,在欧阳修的古文写作中,最终落实为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之间的某种张力,欧文招牌式的“感慨”很大程度上便即由此而生。关于这个问题,这里只能浅尝,容另文详论。
[1](宋)吴 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宋)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5](清)徐 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宋)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元)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日)诸桥辙次.经学史[M].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
[11](宋)苏 辙.龙川略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宋)李 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唐)孔颖达.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宋)胡 瑗.周易口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6](宋)孙 复.春秋尊王发微[M].//通志堂经解:第8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17]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曾枣庄,刘 琳.全宋文:第19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9](宋)石 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方笑一.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J].人文杂志,2010(5):112-117.
(责任编辑 魏晓虹)
The Innov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and the Ancient Style Essays in the Qingli Period of Song Dynasty
FANG Xiao-yi
(InstituteforChineseAncientBookStudies/Si-mianInstituteforAdvancedStudiesinHumanitie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The innov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in the Qingli period of So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the concepts and the ways of writing of the ancient style essays. Literari developed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writing ancient style essays by relating the moral principles in classics with the society and human affairs. By introduc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Book of Change,FAN Zhongyan became the guide of OU-YANG Xiu,etc.. SUN Fu and SHI Jie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style of essays in their time mainl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oncepts and views on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riteria of the writing of essays.
Qingli;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innovation;ancient style essay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7.02.005
2016-12-2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试策与策文研究”(11CZW033);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策论与经义:宋代科举考试文体比较研究”(14PJC028)
方笑一(1976-),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I207.62
A
1000-5935(2017)02-0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