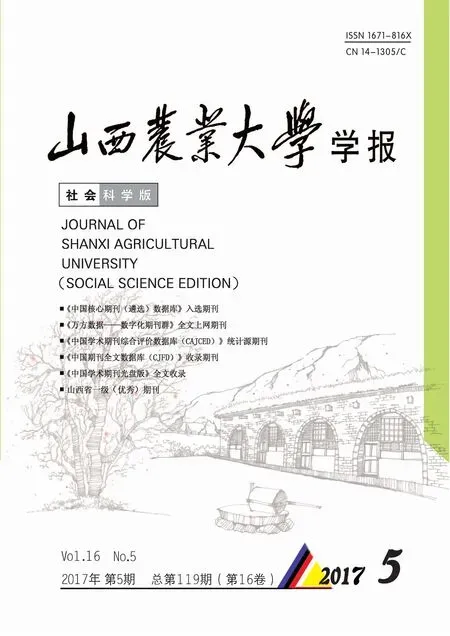阿尔都塞“总问题”的解构新视角
2017-04-02张政
张政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阿尔都塞“总问题”的解构新视角
张政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通过“总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将马克思分为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引起了广泛反响。虽然阿尔都塞的分期理论对明晰不同阶段马克思思想特点是具有理论意义的,但是再从提上陷入了无法自洽的逻辑迷阵。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分期的理论,遮蔽了马克思首先作为一个自然人,有其自身精神成长连贯性这一基本事实,对于理解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成长并不适宜。通过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反思,借助《荷马史诗》的比附手法。澄清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解遮蔽。
马克思;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分期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经典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对其的研究主要是限于资料整理和经典文本阐发,并着眼于当下的阶级斗争,所以在早期共产国际、各国共产主义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者中,很少有对不同时期马克思思想进行分期比较的著述,也未成体系。卢卡奇从马克思思想中引申出“物化”和“阶级意识”,葛兰西在马克思思想基础上提出“文化霸权”等,都没有指出这些思想本身有分期上的差别。直到阿尔都塞,对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分期的重要性论述才被学界广泛关注,对此的研究逐渐形成体系化。因此对阿尔都塞的研究成为研究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分期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阿尔都塞提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直接分属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两个总问题,因此两个思想分期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这种“断裂”不是“超越”,而是毫无关联的自成一体的存在,绝不能混淆。基于此,阿尔都塞对青年马克思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指出青年马克思的话语和问题仍然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仍然流连于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但是这种批判也有其严重缺陷,存在不合理性,使其学说备受争议。通过批判阿尔都塞的分期思想,重新理清对马克思的理解理路,指出马克思作为人的在先性,应尊重其思想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一、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本人何者在先的问题
按照阿尔都塞的逻辑,任何哲学家都可以被统摄于不同的总问题之下。“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 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 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1]然而,一位哲学家,如果他的思想是可以被断裂、被完全划分为不同阶段的,那么这就包含了一个前提,即这位哲学家是隶属于他自己的思想的。从时间上说,一个人是无法与其自己的任何时间段相断裂的,也不能断裂式地发展,对他自己而言,没有断裂只有“更新”。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们会首先看到这个哲学家的思想而不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如果他的思想被分裂为前后期两部分,那么相应地作为人他也会被分成前后期两部分,例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那么一个哲学家、思想家隶属于他的思想,或者说相对于思想家本人,他的思想是否具有在先的合法性呢?我们必须从阿尔都塞框架内进行探讨,这样才能保证与阿尔都塞思想对话的有效性。阿尔都塞在提出总问题的断裂论时,他自认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问题的框架下进行思考的,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隶属于他的思想必然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正如马克思创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概念,他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显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是基于现实的,而现实与概念之间只能通过马克思自身的活动和他接触到的其他主体的现实的活动才能够得到联结。阿尔都塞如果基于思想家属于思想的假设,那么他的体系内部是完整的,因为他的总问题就是作为规定哲学家的自我意识而先在的,思想在先是他的一贯思维。但是这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现实是思想产生之根源的基本原则。
如果承认“马克思的思想隶属于马克思”,问题就变化了。一个人的的思想隶属于他这个人吗?阿尔都塞比较典型的论述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下(而他并未真正自觉认识到自己所处的费尔巴哈理论背景)专注于“非实在的目标,它包含的对象不是实在的对象。”[1]这似乎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学者张一兵认为,“讨论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论断裂”,这有一个特定的语境,即认识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3]从认识的发展史来看,一个人应当是基于社会关系这个包含众多人的共同实践中的,思想属于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学院式的思辨和冥想。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必然是首先属于这个人的,没有两个人会拥有完全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身体机理和思维方式也会有差距,所处身的社会实践亦不会完全相同,那么思想首先必然是在个人烙印和框架下出生的,而且它也必然会永远带着这个人的烙印。马克思的思想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恩格斯的思想或者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马克思的思想。这种被他人完全的理解和把握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思想,必然是有其先后顺序的,如果把之前的思想完全去除,就不可能有之后的思想了。因为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有历史的,这种历史不单纯指社会历史,还有个人独特的思想发展历史和他个人思想发展史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人”看作是一个不彻底的费尔巴哈式的词语有其合理性,但是,“人”依然存在。思想不是人的造物主,而人是思想的造物主。阿尔都塞在总问题上坚持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这是否认了马克思作为人的个人思想史的连续性,否认思想的产生依赖于作者本人的实践和其他的实践,否认一个“特定的思想”依赖于产生它的、有个人思想成长历程的人。国内学者周珍银在《无前提的断定》中提出,“阿尔都塞所批判的折衷主义的做法, 也即主观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进行肢解从而导致断裂。”[4]因此,青年马克思成为了成熟马克思的必然开端,那么两个总问题之间就存在着逻辑顺序,所以总问题使用断裂才得以划清自身与其他问题的边界的可能性就难以成立。
在此需要重申的是,笔者并不是认为从青年马克思里找到成熟马克思的某些思想片段或者某些相似部分就断定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不能产生断裂,而是针对关于基本的个人思想发展的探讨我们得出两者连贯性的结论。现在我们会面临一种反驳,即一个人的思想难道就不能分期了吗?思想家的思想分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不能经由这种分期得出两者断然分裂的结论,所谓“断裂”的结论明显忽视了个人历史连贯性的简单事实。对这个问题阿尔都塞有过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个辩论的总题目是“青年马克思是否已经是马克思的全部。”[1]首先,说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全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宗教式的思维或柏拉图式的回忆说。结果不像阿尔都塞认为的 “承认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由于一个人的青年思想不是自己整个人生的所有思想,因此自己的青年思想不属于自己的思想,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想反,对于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所谓的马克思的思想,而只有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和不同著作里的思想,所谓马克思的思想史是非马克思本人能把握到的。对于自身而言,一个人因为自身的历史和所处社会的历史,他只拥有一个流动的连贯的思想,而他人的思想则是一个精致的有着完整结构的思想。例如,在评价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优缺点时,这个人之外的他人往往可以对他有一个抽象的评价,说明他有哪些优缺点。这个抽象的评价之所以能够形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只能通过事件发生关系,一个事件结束后,直到两人之间再发生下一个事件之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是维持在静态中的。但作为被评价者本身,这个人完全可以选改正缺点或者放弃优点,他作为变化着的人处于同自己相关的无限多的连贯事件之中,行为是不断发生的,他时刻都在改变着自己。从而反观自身,他自己只拥有着一个流动着的连贯的思想,而没有抽象结构化的评价。阿尔都塞其实也有相关思想,恰如他在评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所说:“非抽象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如果把这句话当作完整的定义,单从字面上解释,他却说明不了任何问题。”[1]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思想隶属于马克思。一个近乎常识的结论却要经过分析得出,这并不是稀奇的事情,因为哲学家在考察思想时习惯于从思想史出发而不是从思想着的人出发,这已经是痼疾了。
对于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关系,俞吾金教授的观点比较能代表国内大部分学者的意见:“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重大的差别。就主要之点而言, 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点的历史唯心主义,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则体现为以实践活动为基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着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关系。”[5]所以说,关于马克思思想隶属于马克思还是马克思隶属于他的思想的问题就变得清晰了,马克思的思想隶属于马克思,从起点上说,如果真的存在认识论断裂,必然先有认识主体的断裂,但认识主体是一个连续生存、实践和反映社会的主体,那么认识论断裂便在主体与其思想的关系层面上被废除了。但是认识论断裂和总问题却无法分开,事实上,认识论断裂不过是总问题独立化的分界工具,它确定了总问题自身独立的可能性,保证了总问题的边界,因而也是总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总问题有了某种程度的意义实现,那么认识论断裂仍是可能的,而总问题的意义实现是否可能呢?
二、逻辑顺序与时间顺序的两种考量
从逻辑上讲,总问题为区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而设定,它作为一个形式化的标志,像一个照片一样将阿尔都塞所认为的两个阶段的结构和截然不同的组成概念呈现出来,根据上文,两者的区分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否可以有意义还是值得考虑的,虽然总问题无法在逻辑上成立,但是总问题可以在意义领域成立。
时间顺序不等于逻辑顺序,马克思的思想从思想史总结的角度上说,是逻辑顺序的,但在直观现实中,他的文本是时间顺序的。一个思想家的青年与成熟之辩,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直线上的,时间顺序的,预设为两部分,进而在其中找到关联或者不关联,这是阿尔都塞式的;第二种是荷马史诗式的,这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但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荷马史诗》是在圆圈内的,包含在先的向外的伊利亚特和在后的回归的奥德赛,这一种我们在最后一章讨论。我们秉承在文章一开始所确立的原则,即对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概念要从阿尔都塞框架内进行探讨,这样才能保证与阿尔都塞思想对话的有效性。那么本节我们只从直线式思维角度,先分析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思想的青年和成熟之辩。
阿尔都塞关于思想家的青年和成熟之辩,我愿意把他表述为直线情形下的青年和成熟的分野。学界对阿尔都塞的分期的批判虽然很多,但是他们的批判不过是在继续随着这种直线式思维而进行的批判,他们的批判路径大都集中在两者的内在联系、青年马克思作为马克思思想开端的必然性(这恰恰是阿尔都塞所认为的反对分期学者的通病),没有跳出这种直线思维而只是从外边进行整体的批判。即使是阿尔都塞,借助于斯宾诺莎进行自我反思,仍然建立在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直线发展基础之上的。学者安启念就指出:“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确实意味着新的哲学思想已经形成, 但是马克思的新思想究竟是什么,阿尔都塞并没有全面准确地把握。”[6]斯宾诺莎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只是在证明了意识形态概念后,破坏了阿尔都塞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的意愿,破坏了阿尔都塞的核心概念之一,从而引起阿尔都塞的反思。但阿尔都塞真正应该反思的倒是自己连接这些概念的逻辑理路本身,这才是他的致命错误所在,而不是单个的概念。我们在这里,不是一场辩论,不是破坏对手的核心概念,不是击倒对手就可以了,而是一场讨论,一场针对阿尔都塞的思路问题的讨论。这种思路就是把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看做直线型。
从常识上,以及从前文所有的论证而言,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应当是直线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家本人会接触更多的实践和理论,从逻辑上思想家不断在旧的问题上拓展新的问题,这些都是直线型分析,因为这种思路的真正基础是,这些思想在文本上、时间上、或者逻辑上是有顺序的。这种思维是符合常识但却有严重危害的。第一,直线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导致一种暗示,即后来的思想往往是超越、包含前者的,处在明显优越位置的。从成熟与否来说,思想家永远将后期看作是对前期的俯视和超越,所以很容易得出后期是更成熟的结论,但是对于很多哲学家的思想而言,前期可能更有突破性和更有真正的价值。谢林就是个著名的例子,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里,称赞青年谢林是“真诚的青春思想”,谢林后期的启示哲学很难超越其前期的思想,但在谢林本人看来,自己在晚年是更成熟的。正如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特别是最高层次的《精神哲学》,虽然包含着《精神现象学》的正反合思想,但其僵化程度和犀利程度远逊于《精神现象学》。相对于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区分,青年黑格尔和老年黑格尔的区分反而更恰如其分,我当然并不是要求将马克思思想分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而是在使用直线型思维时不要带上后者更优越的暗示。第二,直线思维并不能反映真实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直线仅仅存在于日常经验的时间和空间中,这不代表逻辑也一定遵循着直线的发展,逻辑的发展和推演是穿插曲折、错综复杂的。一个人可能在自己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陷入同一个逻辑中,一个逻辑链完全可能是封闭的,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当然,不可否认这个思考过程在时间上确实是直线发展的。其实阿尔都塞所谓的总问题不就是如此吗?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永远是在同一个结构下对时代问题进行回答,不论面对何种问题,思想本身的逻辑是不动的,思想家的逻辑本身永远是封闭和循环的,没有随着他的年龄而呈现必然的顺序性发展。所以,直线顺序对于思想来说不是必然的,特别是对于复杂思想更是如此。当然也有人会质疑,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分期不必然是直线的,而是体系各自特点的区分在先,然后才被以青年和成熟命名,这不象征着直线顺序。对于这种质疑,我认为,直线顺序是必然的在这种区分中被象征的。凡是前后相继的都可以理解为直线顺序的,而凡是断裂都意味着思想分属于不同时期,即使不用青年和成熟,而是用其他区分方法,两者也是直线顺序的,凡是摒弃相交的可能性的必然只能象征着直线顺序,不相交的两者必然只能以相继的方式出现,所以必然是直线的。
是否青年和成熟之分是没有意义的?即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思想分期是否可以在意义领域成立。如果说一直坚持对思想家,特别是对马克思这样一个强调历史性的哲学家的思想采取直线式的思维方式的解读,并且直线上的每个节点是相互断裂的,这必然是错误的。无论是青年和成熟、前期和后期还是青年和老年等等言词上的改变解决不了直线性思维方式的根本错误。直线思维下的分期要想提供意义,那么它必然首先在逻辑上可行的,其次才能在意义上是可能的。我们在本节一开始提出的:两者的区分是在逻辑上不成立的,但是否可以是有意义的,这个问题在直线思维下不能解决,但是分期的可能基础还有另一个,即荷马史诗型的,类似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分期模式,在这里或许可以寻得意义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节中予以探讨。
三、马克思思想分期与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分期
在前文中,我们探讨了马克思的思想隶属于马克思还是马克思隶属于他的思想的问题,以此为基础,我们来重新认识到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第二篇中提出的一个经典命题,他说“他们不再是马克思身上找到青年马克思的影子,而是在青年马克思的身上找到马克思的影子。”[1]真正的问题,不是在青年马克思中能否找到马克思(这是阿尔都塞已经批判过的学界的错误),而是在成熟马克思中能否找到青年马克思;也不是青年马克思是否对成熟马克思有开端意义,而是青年马克思本身就是马克思本身。
阿尔都塞这句话是否正确,决定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思想应采取的基本态度。但我认为问题可以稍加转化。阿尔都塞认为只要不认可他的“认识论断裂”,就等于承认“青年马克思的本身就是马克思本身”,其实,这是一个逻辑陷阱。既然阿尔都塞视域中的总问题作为一个体系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有严格区别,那么只要证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可以作为成熟马克思的一部分就可以了,不需要证明两者的全同就可以破坏阿尔都塞的体系,并建设一种通达两者的新思路。当然,阿尔都塞提出的马克思思想的两种思路有其独特意义,对于很多学者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是有警醒意义的,但在这里也可以找到阿尔都塞自身的错误。
第一种,在青年马克思中找到马克思。这是很多学者所沉迷的研究方式,我认为其中原因如下。第一,对于任何一个思想家,从他的青年时期思想中找到他成熟思想的组成部分、萌芽和碎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是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必然。为思想家作传,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史,这项工作的可能性就是建立在个人思想发展的必然的前后相继的基础上,即使前后期的思想是绝对对立的,那么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也是可以在其前期思想中找到的,例如这个思想家在其青年思想时期经历了重大的时代事件或者思潮冲击等,致使其之后的思想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可以说,在一个思想家的青年思想中找不他成熟思想的任何蛛丝马迹是不可思议的。对于学者而言,从一个人青年思想中找到其成熟思想是简单易行的,因为总能找出前后思想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否认前后两个思想之间的联系会更难(所以阿尔都塞的努力至少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即使否认这种联系,也仍改变不了两种思想作为同一个人的产物而具有的天然联系。所以阿尔都塞在《青年马克思》中对这一类学者的轻蔑与批判也是源于对学术极负责任的态度。第二,马克思的思想本来是建立在同一个实践序列之中的。从方法上来说,马克思坚持一贯的方法论品格。例如马克思很早就树立了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即使他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抑或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时,也保持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方式。从社会实践上来说,马克思投入于分析和现实社会实践的工作中,从早期的《莱茵报》到后期参与的各种工人组织和流亡组织,还有一系列论战性的文章(如1844-1845年《神圣家族》)和关注时事的文献(如1841年《评普鲁土的书报检查令》、1843-1844年《论犹太人问题》等),都证明了马克思一贯的工作旨趣和活动重点。所以无论理论品格还是社会实践重点,马克思前后都有其连贯性,某些前期活动甚至可以看做是对后期思想的某种积累,所以从实践角度看,由青年马克思中找到成熟马克思的蛛丝马迹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从青年马克思中找到成熟马克思的影子,是一个必然正确然而并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如果沉迷于种种成就,青年马克思就不过成了成熟马克思的材料库,根本不能充分论证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是成熟马克思的思想的必然开端,如果陷入这种理论僵局,这种联系反而昭示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属于成熟马克思的思想。
所以,正如阿尔都塞所说,要在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青年马克思。这样,问题就变得有意义了。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成熟的马克思代表着成熟的总问题,代表着成熟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那么如果在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青年马克思,那么青年马克思也就在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之内,也就在成熟的总问题之下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存在,而不是在成熟的总问题之外需要被抛弃的。因此,合理的推断是,青年马克思本身就是成熟马克思的一部分。但是,这似乎陷入了一种不可接受的悖论,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期就了解到了他之后所做的一切,除非马克思是神,否则这个结论不能成立。任何一个思想家前期思想作为后期思想的部分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的思想是一贯的,那么前期思想就能是后期思想分步骤的建构。但是,马克思前期陷入人本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思想的历史是不能抹去的,即使我们不承认阿尔都塞的“断裂”,也要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分期”。马克思无法预见到自己之后所做出的转变,所以他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就不能作为成熟时期整体思想的组成部分,因为两者不是互相连贯和支撑的。
至此,让读者费解的是,为什么我在前文中的开始声称阿尔都塞的要从成熟的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青年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推到最后又变成了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要在成熟的马克思思想中找到青年马克思这一问题,是在面对马克思思想时而不是针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这个人而言时,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上一节随之而来的分析是在阿尔都塞的体系内继续的(正如我一开始所说要直面而不逃避我们所讨论的人的思想,这是负责任的态度),问题就落入到了阿尔都塞的话语中,就变成了结构化的成熟马克思怎样把青年马克思当成部分的问题。这是阿尔都塞的解决公式,认为成熟的马克思,有一个结构化的总问题,青年马克思只有成为其中一部分,才能算做成熟的马克思,才能否认掉两者的断裂。只有超出他的框架,才能有新的突破。
四、马克思思想的延续性
比附是哲学解释的一种方式,例如马克思经常饮用莎士比亚拙作以扼要表述资本主义生活现状,给人直观的感受,在《巴黎手稿》中尤为突出。《荷马史诗》的介入既是一种直观的比喻,也是对西方思想家思想发展脉络的一种象征。《荷马史诗》分为两个部分,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利亚特》讲述了一个因愤怒而出征,鏖战特洛伊并最终取胜的故事;《奥德赛》则讲述了奥德修斯突破全知和永生等等诱惑,最终返乡的故事。在阿尔都塞的视域中,成熟的马克思思想才是马克思的思想,正如奥德修斯的返乡,更像是一个逐渐磨炼精华的过程,逐渐形成自己真正的信仰,从而到达自己的精神家园。
青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囿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路,所以他的整体思维是“德意志式”的。而德意志恰恰代表着行动的软弱和思想的过分强大,这也是青年马克思所面临的类似于奥德赛的“全知”的诱惑,只有退回现实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奥德赛只有退出具有全知诱惑的岛屿重返现实归乡之路才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面对理论无法满足现实的困境,马克思没有像很多思想家一样提出返回更古老的思想家那里去寻找智慧的学院式的解答方法,而是直接回到现实。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退回到现实,把握住真实对象,摒弃继续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挖掘,是真正断裂的动机所在。
阿尔都塞认为通过以上努力,马克思才真正进入了转换后的新问题——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把这种退回现实后的新发现结构化,将其设定为马克思以及之后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发和进行思想活动的框架,认为这个总问题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这双重的发现,—方面在歪曲了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此岸,发现了意识形态所涉及的现实,另一方面在不了解现实的当代意识形态的彼岸,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而且因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总问题统一起来,抽出其中任一成分,整体就会改变意义。”[1]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行动上的重回现实使得思想上成熟马克思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任何一部分上都抛弃了青年马克思思想。
我们这里要重新介入《荷马史诗》的探讨以便例证笔者的观点。首先,对《伊利亚特》的考察。第一,思想家思想的“触发点”必须是符合体系的吗?《伊利亚特》始终贯穿着阿喀琉斯的愤怒。毫无疑问,思想和诗的出发点是情绪化的,是人本学意义才能解释的,一个思想往往不能有一个科学的开端。阿喀琉斯因为对阿伽门农的愤怒而退出联军,导致希腊联军在特洛伊战争中处于守势,寸步难行,岌岌可危,又因为阿喀琉斯对战友死亡的愤怒,重新投入希腊联军,所以势如破竹,杀掉对方主将赫克托尔而奠定胜局。但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如何表达,我们如何像描述一个故事结构的方式来描述情绪结构从而“科学地”表达?然而,我们是否排出了任何情绪化原因,就能够真正得出这场战争的真实原因?整场战争的发起、战争过程中的战略战术、不同将领之间的协调,都是理性的,但是仍逃脱不了希腊人的愤怒和阿喀琉斯的愤怒两个情绪的终极支配。我们反过来看看马克思的前期活动,包含更多的是伦理学上的关怀,这从更直接意义是他的“触发点”。我们以《莱茵报》时期为例,《莱茵报》代表着青年马克思非常重要的思想成长阶段,如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著名评论文章,和莱茵省总督沙培尔论战的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这些文章表现出青年马克思主要是一名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中贯彻着关怀和同情等伦理意义。然而,这些文献都不能说青年马克思符合了后来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方法。那么,不符合体系是否就必然不是体系的部分呢?愤怒不是战争,但是愤怒是战争的核心。青年时代马克思不是成熟马克思,并不代表他不是成熟马克思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属于成熟马克思,两者是不可分开的部分,而是不可分的思想之流。当我们看《资本论》这样一个成熟马克思代表作时,关于“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秘密的剖析和当年《莱茵报》时期批评森林法对农民捡拾果实和树枝的价值取向是一样的。区别是可以从体系上区分的,反过来看是在马克思关怀的总价值取向的视域下,采取了不同述说方式。第二,人本学的起点是否有意义。如果把青年马克思当作成熟马克思的一部分,那么人本学看似是不恰当的。但是成熟马克思主义脱离了费尔巴哈的“人”了?这似乎是阿尔都塞非常隐蔽的一个假设,不在费尔巴哈的语言框架中说话的马克思不等于不谈论“人”,这之间是缺乏必要的论证的。其实,马克思抛弃了费尔巴哈的人,但是建立了自己的人,所有成熟马克思的概念,都是有其承担者的。所以,马克思始终没抛弃人,区别只是使用怎样的人的概念而已。正如之前讨论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虽然也投入实践,深入农民生产生活现场,但还是在最感性直观层次去“整理”这些材料。这种层次就是他的人性关怀的层次,那时候的马克思还是处在一种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层次看待人,他就当下论当下,聚焦每一个具体个体的人的具体生活环境来寻找材料,当然也达不到更广的联系,从而在这些材料中看到社会制度、经济等因素。因此,人的关怀问题贯穿的是马克思的长期理论取向的动力,即使成熟马克思不在从人或者人性出发,但是还是以人的关怀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的。
那么基于以上论述,我想通过以上两点提出一个断言,阿尔都塞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马克思是个有价值取向的人,只是把马克思当作生产思想的机器。《伊利亚特》中,海伦被抢、特洛伊城墙的来历,众神的恩怨和木马计,不过以希腊联军情绪化的主线,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始终以一种情绪化的东西作为自身的主线,但不能因为体系的转化就忽视了马克思作为人的价值取向。
经过对《伊利亚特》的分析,我们看到离家太久、走的太远的奥德修斯如何返乡的历程。《奥德赛》隐喻着一个思想家经历理论、信念和追求真理后的沉淀过程。第一,成熟马克思思想与《奥德赛》能够类比的原因。《奥德赛》是一个归途的故事,是一个摒弃和祛魅的故事,这似乎非常适合阿尔都塞关于成熟马克思与以往错误思想决裂的逻辑。思想经历了“伊利亚特”,收集了丰富的材料,经历了无以伦比的盛景,到达了真理的彼岸,但是曾经支撑自己走到这一步的东西,如何才能抛弃。征战的生活和信奉的东西已经成为习惯,如何回到过去的生活已经成为挑战。而且只要不回去,就会有女巫许诺“全知”和“享受”。马克思如何断裂自己与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他已经能够窥探德国古典哲学体系的奥秘,可能成为一名不亚于前辈的哲学家,他也无限接近于费尔巴哈的“爱”,这种“爱”支撑着他关怀人的理念。一个近乎于神父遇见天启的神圣图景无限接近他。但是,马克思选择了决裂和转向,这是一个没有哲学、宗教神圣之光的悲惨的工人阶级生存现状和冰冷的制度。但是马克思投入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中,又退出来,祛魅之后,是否一无所获?其实,重回实践,不断祛魅本身就是成熟马克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伊利亚特》如何必然成为《奥德赛》的开端。奥德赛随军出发,是一种整体时代的命运,是全希腊人对于海伦叛逃希腊转投特洛伊的愤怒。这是一种原始的感情,一种不需要真理的出发。愤怒支撑着远行,去收集所看到、所经历的一切,出行之后才有奥德赛再次剥离这种远行中的诱惑,只把更高的智慧和荣耀带回家乡的故事。我们在青年马克思中,看到的是对普鲁士这个具体国家的愤怒,对德国哲学软弱的愤怒,对时下农民工人生活困苦的愤怒,但是没有对国家制度、哲学和阶级状况进行纯粹的、脱离具体国家而放眼世界历史的角度的分析。马克思首先作为马克思这个具体的人才就有马克思的思想,早期的马克思需要不断的伦理方面的原因驱使马克思的行动和思想的成长,这也促使他在理论上更接近费尔巴哈,因为人本学是一种更直观的学说。人一般直观地将善人、恶人当做善恶的来源。一般的文学作品最终是喜剧还是悲剧决定于是人还是恶人最终获得胜利。这种解释方法更为大众接受,更适合使用“人性”等词语直观感性地呈现善恶的原因。阿尔都塞将成熟马克思结构化以便于呈现、讨论和应用是值得借鉴的,这种结构化的表述马克思会有诸多的逻辑错误,但其本质错误将这种成果向前一步,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分开。第三,马克思思想是《荷马史诗》而非《奥德赛》。所以,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作为伴随着马克思这个人的生活之流而形成的思想之流,既是因关怀、悲悯和愤怒而开始思想远征的伊利亚特,看到人家具体纷繁的疾苦和不平等而对具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批判的过程,又是冲破材料堆积而整理材料,剥离具体的情绪而回归到对根本的制度、经济基础、阶级状况等根本因素,从而形成共产主义智慧,建构无产者精神家园和支撑的奥德赛。把马克思思想放到共产主义生成和成熟的整个历史视域中,它又像早期傅里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式的幻相和民主主义者限于对具体统治者反叛的始点,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推力和马克思本人的学术品格又必然从这个始点突破各种诱惑(如成为新一代德国哲学家或某民主主义政党的参与者)到达共产主义归宿的必然性。马克思的回归是带着智慧的回归,所以他不再是回归成一名犹太教徒、律师或者宣扬民主主义的编辑,而是回到了社会现实的最基础层面。
五、结语
伦理意蕴从未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被剔除,科学的马克思思想同样包含着青年马克思的热情,改造流亡者组织,支持巴黎公社、关注雾月十八的时局等等,仍然是和早期马克思维护工农利益的做法异曲同工。如果不从伦理层面开始,那么马克思思想又要从哪里开始呢?阿尔都塞将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都置于结构化的处理之下,他看到人所能建构的存在,却看不到人所不能建构只能生成的存在,更关键的是,这种建构的结构化存在(总问题)只能置于生成的思想之上,而不是生成的思想置于结构化的最终表述上。
[1][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杜章智校.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8,128-131,128-131,38,70,48.
[2][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93.
[3]张一兵.认识论断裂:意识形态与科学[J].天津社会科学,2002(1):4-12.
[4]周珍银.无前提的断定[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4(4):5-10.
[5]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J].学术月刊,2006(4):43-53.
[6]安启念.阿尔都塞马克思哲学思想“认识论断裂”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2016(1):18-25.
(编辑:佘小宁)
An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from spiritual growth: reflections on Althusser's general question
Zhang Zheng
(InstituteofMarxistPhilosophyandChina'sModernizationandDepartmentofPhilosophy,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After the death of Marx,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increasingly presents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rapid chang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researchers' knowledge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s. Among them, Althusser has divided Marx into the young Marx and the mature Marx in theForMarxthrough the “general question” as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which caused widespread reaction. However, there is a misreading of Marx, which obscures Marx's traits as a natural person who has his own spiritual growth coherence.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Althusser 's theory,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 s thought.
Marx; Althusser;ForMarx
2017-02-22
张政(1988-),男(汉),山东潍坊人,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早期文本方面的研究。
B565.59
A
1671-816X(2017)05-004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