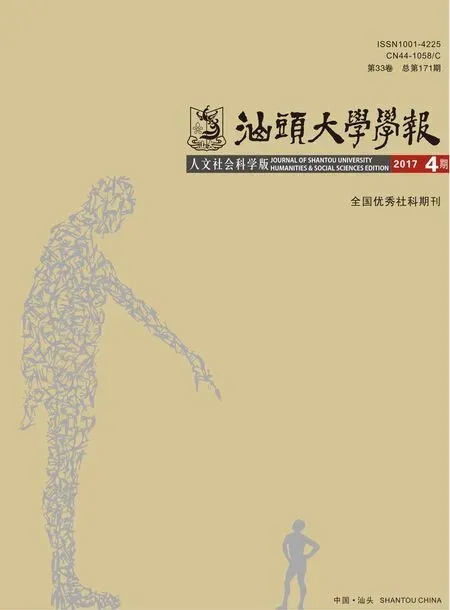晚清历史人物方耀功过论评
2017-04-02燕世超
燕世超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晚清历史人物方耀功过论评
燕世超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方耀作为我国近代于文治武功多有建树的历史人物,他修筑炮台、防卫海疆,重教办学,广设善堂,浚江围垦、兴修水利,打击地方黑恶势力及整顿社会治安,为抵御外敌入侵,为潮汕地区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他参与围剿太平军余部要做历史分析,他建造德安里有案可稽。评价方耀要摈弃极左思维,实事求是,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方耀;围剿太平军余部;“办清乡”;建造德安里
方耀为晚清名将,曾两次出任潮州镇总兵,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其重要事迹有:参与围剿太平军余部;“办清乡”;建造德安里;修筑炮台,防卫海疆;重教办学,广设善堂;浚江围垦,兴修水利。其中前三件颇具争议。对于方耀的是非功过,一些学者早已撰文论述,笔者谨在此略述一孔之见。
一、参与剿灭太平军余部有其合理性
关于方耀参与剿灭太平军余部兴王陈金缸、康王汪海洋、侍王李世贤等的活动,《清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潮州志补编》等史书记载颇为详实,且无大的出入,论争双方争议也不大,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举是非功过。笔者认为,只有把它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出恰当的评价。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一方面是清王朝走向腐朽衰落,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也很快蜕化变质。“有称太平天国建立的为‘农民政权’‘革命政权’。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说,太平天国的前期是属于农民的或革命的政权,那么,定都天京后,就不符合事实了。洪秀全为首,其他诸王都以改朝换代的姿态,极力营造新的帝王生活。他们的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完全蜕化变质。从太平天国的官制看,最能反映政权的性质。它已失去原来的兄弟之义,而变为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僚化的制度。……太平天国的后期已不再是农民政权性质,而变成为与清朝一样的封建政权。”[1]1673可有些人受极左思潮影响,一提到农民起义,就笼统地、无条件地认为是进步的、革命的,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此分析和思考,从而陷入误区。在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和评价方面,马克思树立了光辉的范例,这就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论证和评价。从1853-1859年,马克思连续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恩格斯也撰文《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他们从人类正义与公理出发,愤怒地谴责英法美俄等国对华输入鸦片、残杀无辜百姓、蓄意挑起战争、欺骗国内舆论、迫使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量领土(俄国)、引起中国大量白银外流、经济频临破产、民生凋敝以致终于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1-2从清政府自身来说,起义的内部原因在于,“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2]26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无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马克思称赞它是一场“强大的革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马克思透过许多罪恶的事实渐渐看清该运动的性质。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即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分析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原因后,尖锐地指出:“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之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3]545在列举了太平天国杀人、抢劫、强奸、制造恐惧等种种恶行后,马克思总结道:“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3]548这就是说,太平天国非但没有改变封建政权的性质,反而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给人民群众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在此情况下,方耀平定太平军余部有利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国家统一,因而有其合理之处。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太平天国的所有人物、所有事件一概否定,有些军事将领如李秀成在其占领区,曾经颁布一些法令,采取一些进步措施,使得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受到他们的爱戴和拥护,再如石达开在极刑面前,大义凛然、英勇就义,表现出感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办清乡”于民有功
要正确评价方耀“办清乡”,先要了解“清乡”前潮州地区治安状况。据《清国史》:“潮属风气强悍,抢掳械斗,习以为常,甚至负隅筑寨,据兵抗粮,良民胁于凶焰,莫可如何。”[4]314《清国史》可能是最早记载有关方耀的详细史料,由手写而成,其权威性非同一般。《清史·列传》与《清国史》所述语句完全相同,可能是摘录后者而成。《清史稿》载:“潮俗故悍,械斗夺敓以为常,甚且负隅筑寨,据兵抗粮。”[5]12678曾国荃《奏疏》云:“查潮属民情夙称犷悍,抢掳械斗之案层见迭出,甚或连结会乡,霸占田产,抗粮拒捕,戕杀官兵,法纪荡然,几同化外。”[6]109《明清实录潮州事辑》更是多次强调:“广东潮州府属,素有抢掳械斗之案,……潮郡民风素称强悍,……潮郡匪徒,抢掳械斗,积案甚多。……广东潮州府属潮阳等县匪徒,抢掳械斗,积案甚多。”[7]288-290《明清实录潮州事辑》由《明实录》和《清实录》中有关潮州的文字综合而成,这两部实录是明清两朝皇帝执政时期的旨谕日记,是皇帝处理事务的编年大事记录,其权威性可想而知。《潮州先贤象传》亦云:“潮俗好斗。土豪每筑堡聚众。占田产抗官租为常。吏不能禁。”[8]84由此可见,此时潮州治安积重难返,社会黑恶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方耀如何“办清乡”及其结果如何呢?有史为证:“耀以为积匪不除,民患不息,遒创为‘选举清乡法’,先办陆丰斗案,明正其罪。潮人始知有官法。陈独目结会戕官,谢奉章恃险擅命,并捕治之,潮民遂安堵。”[5]12678“已办之著匪郑锡彤、郑锡位、谢昆冈、谢普屿等,均系抗官拒捕、残杀多命,罪恶昭彰,供证确凿。”[6]109“办陆丰斗案,诛负险阻兵之谢奉璋、谢昆冈、郑锡彤、郑锡位等。遂清历年逋赋,归之官;理积踞田产,还之民;民乃大和。”[8]84《潮州志补编》有关方耀清乡的叙述多来自《清史·列传》,而《清史·列传》的记载又与《清国史》完全相同:“耀以为不除积匪,其患不息,而发兵剿办则元气伤,而患更大。乃创为选举清乡法,择豪族正人为乡约正副,任以稽查,分别良莠,准予自新,以为纲领。先办陆丰县斗案,明正其罪,潮人始稍知官法。其拜会戕官之陈独目,恃险据兵之谢奉漳等,俱次第就擒,治如律。访获悍匪无算。清查强占民田,悉归本户。仍会同文武勾稽积欠钱粮,使民自完。从前占久未经升科之沙田,至是皆丈量赋税,潮关税额亦岁增巨万。创设书院义举,风气一新,潮人颂之。”[4]314这些史书说法相似,可相互印证,应十分可靠。这说明,“清乡”后,潮州治安状况得到明显好转,方耀此举得到潮州民众拥护。
方耀“清乡”是否个人行为呢?《明清实录潮州事辑》载:同治八年即1869年,“该督(瑞麟)因派总兵方耀、道员文星瑞带兵先赴惠州所属之陆丰,再赴潮州,相机办理,自系为整顿地方起见。……即着妥筹机宜,饬令方耀等严申军律,相机办理,俾潮郡良民无稍扰累,匪徒知所儆惕,将抢掳各凶犯交出惩办,以遏乱萌,仍不可一味逞威,激成变故。”[7]288同治九年重申:“经该督抚派委总兵方耀,道员沈映钤等赴该郡查办。……仍着饬令相度机宜,认真整顿,务令匪党悉除,舆情帖服,以副去暴安良至意。”[7]289这说明,方耀“清乡”是广东总督瑞麟委派并得到朝廷支持的。
方耀在“清乡”中杀了多少人?据方耀《复张香帅书》:“数年间,审结积案千余起,惩办著匪三千余名,征收旧粮百余万两,起获炮械数千余件,均经奏报有案。”[9]33“惩办”即处罚,除了处死,还应包括监禁、罚款或打板子等刑罚。又据上述曾国荃《奏疏》云:“核计该总兵方耀在海阳、揭阳、潮阳、惠来、澄海、普宁等县,先后获办匪犯实共一千余名,并无数千名之多,俱系先查县案、采访舆论,尚无报复私仇、汪杀无辜情事。”[6]109“获办”也不能理解为全部杀死。再如《普宁县志》:“经过数年,办理积案数千宗,杀戮不下3000名,为清廷搜刮税银100余万两,收缴炮械数千件。”[10]676《普宁县志》为1990年代出版物,相比之下,曾国荃《奏疏》更为可靠。由此可推测,方耀惩办著匪可能是3000余名,其中1000余名被杀掉。处理数千宗积案,且对方拥有炮械数千余件,当时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杀掉1000多人应不为多。
方耀惩办的多是些什么人呢?《普宁县志》云:“被清办的有农民起义军、抗官抗租者,也有土豪海盗。”[10]676但笔者没有发现在方耀“清乡”期间,清代史书记载潮州一带曾爆发农民起义。《普宁县志》载有1854年大长陇村陈娘康和北山村许阿梅分别聚集农民万余人起事,当年起义就被镇压下去,而方耀“清乡”是在其起义失败15年后的1869-1871年。《明清实录潮州事辑》载:同治十年即1871年,方耀等“先后将惠来等处著名匪犯陈独目、谢漮品、谢奉漳、谢昆碙、郑锡彤及陈老仔汰等缉获正法,该郡赖以安谧,办理尚属奋勉。”[7]290此处所言,方耀惩治的皆为地方豪强、劣绅、恶霸。联系《清国史》《清史稿》《清史·列传》《潮州志补编》《潮州先贤像传》以及《曾国荃奏疏》等史书可推断,方耀清乡惩办的应该没有农民起义军。窃以为,那些负隅筑寨、戕杀官兵、残杀多命、抢掳械斗的社会黑恶势力,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允许其存在,联系潮州地区上述触目惊心的现实,方耀“清乡”是完全必要的。至于那些抗粮税者是否属于贫苦百姓,在缺少具体史料的情况下,不能妄加猜测。抗粮税不能简单理解为反抗清王朝统治,即使清王朝此时正在加速衰亡,农民上缴粮税也是应该的。因为倘若没有这样一个政权存在,就会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军阀割据、民族分裂、生灵涂炭;没有充足的粮税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就无法抵御外来入侵。事实上,正是在清王朝与太平天国殊死搏斗时及其后,才出现“边疆危机”:沙俄乘机侵占我东北、西北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英、葡强行“租借”港、澳,美国、日本先后侵台,法国发动侵越、侵华战争,英国进犯西藏。
对于方耀“办清乡”,也有相反的意见,有称屠杀群众上万名,仅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发现其据主要有四:一是《大南山苏区史料汇编》:“他(方耀)两任潮州镇总兵达十三年之久,操‘自由杀戮’大权,先后借‘办清乡’为名,杀戮潮汕人民万人以上。”[11]2对于属于书中“概述”部分的这段话,笔者心存疑虑:清廷也有法律和监察制度,决不会放任其“自由杀戮”,否则就不会让曾国荃“奏为遵旨查明总兵被参各款”,并“据实复陈”,且皇帝一再要求方耀“严申军律”,更没有授予其“自由杀戮”的权力,因为“自由杀戮”等于蔑视清朝法律并会激起民变,加速清朝灭亡。二是《中共普宁党史》:“他(方耀)任潮州镇总兵十余年间,以办‘清乡’为名,胁迫农民交还欠租欠债,清偿40余年战时之损失,又硬勒农民加租,农民无法交租,被其杀戮焚掠者数以万计。县内农民土地几乎全为方耀占夺。”[12]4三是《普宁史学·掌故》:“为追究陈娘康农军抗官攻城事,同治十年(1871)农历正月十四日,方耀带兵清剿大长陇,把近万人的大长陇乡夷为平地”;“方耀之女探亲路经此地(上庵村),被盗贼劫去金手环一只,方耀便以‘乱贼’的罪名,施以抢、杀、烧,上庵村丁口殆尽。”[13]19笔者感到不解的是:方耀“把近万人的大长陇乡夷为平地”根据何在?“夷为平地”时有没有死人?是否这近万人都被杀死了?四是《普宁县志》:“因积案牵连乡村,被烧杀抄毁者,有陈娘康、许阿梅农民起义首领的家乡大长陇、北山乡等。甚至他的女儿探亲路过城东5公里处的上庵村,被盗贼劫去金手环一只,便以‘乱贼’的罪名,连夜烧杀,使七八百人的上庵村丁口殆尽。”[10]676《普宁县志》并没有说杀掉上万人,但杀上庵村人与上述《普宁史学·掌故》表述也如出一人,不知是何原因。一个七八百人的村庄突然被杀光,无论在什么朝代都会是惊天大案,但在清代史书中却没有发现任何记载。无疑,它没有原始资料作支撑,仅属于当代人的表述,其可信度不高。上述引言所出的著作均出版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南山苏区史料汇编》没有注明出版时间,其“后记”写于1987年,出版时间应在其后;《普宁史学·掌故》为非正式出版物),距方耀“清乡”已经120年左右,那就要引用具体、确凿的原始资料,譬如,方耀到底胁迫哪些农民交还多少租债?“被其杀戮焚掠者数以万计”中潮州各县、乡分别占多少?都是些什么人?清史或其他典籍中是怎么记载的?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被杀人数、物证等,方能支撑方耀当年“杀戮潮汕人民万人以上”这一论断。论者可对方耀“办清乡”所杀人数及人员性质存疑,“办清乡”也有可能出现冤假错案,但若拿不出确凿的史料,这种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建造德安里有案可稽
围绕方耀建造德安里,同样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德安里是方耀驱戮当地村民所建。主要论据一:“普宁县以方耀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是潮汕地区最大的封建堡垒,其子方十三(方廷珍)仗势压迫剥削农民之残酷,闻名东江。……还以驱赶杀戮驻马院桥村的农民,建造起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德安里’大院。”[14]4论据二:“方耀的官邸及属村德安里、和安里、福安里,就是马院桥、寨仔内、水龙寨、赤髻鸟等4村村民被其在‘清乡’时诬为‘乱匪’置于死地,村址夷为废墟而建成的。”[12]4-5论据三:“同治七年(1868),方耀调任潮州镇总兵,便决定在家乡洪阳营建府第,地址选中城郊东南面马院桥村。当时马院桥村住着王、吴、陈、周、姚等姓,丁口七百多,该村曾在咸丰年间联合北山许阿梅起义。方耀采用软硬兼施手段,先强迫村民把土地卖给他,迁徙他方。有不愿卖地搬迁的,则以‘通匪作乱’的罪名捉拿,杀人烧屋,把该村夷为平地,然后建起府第‘德安里’,格局成为‘百鸟朝凰’。”[15]12论据四:“清同治七年(1868)潮州镇总兵方耀告假归乡,选中城郊东南面马院桥村这块地方营建府第。当时马院桥村住着王吴陈周姚等姓,丁口七百多,土地肥沃,绿野平畴。咸丰年间,曾联合北山许阿梅起义,……方耀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先强迫该村农民把田地卖给他。部分农民被迫迁移他乡,另置家园;部分农民拒不搬走,方耀则以‘通匪作乱’的罪名杀人烧屋,将马院桥村夷为平地。方耀遂在这废墟上面建筑府第,定名为德安里。”[13]23这四个论据中第一个语焉不详,观其语意,似乎是方耀儿子方十三“驱赶杀戮驻马院桥村的农民”、建造德安里,但这明显违反史实。第四个属于非正式出版物,与第三个在表述上大同小异,不知是何原因。第二、三个论据共同点在于,方耀把当地不愿搬迁的村民以‘通匪作乱’的罪名杀人烧屋、村庄被夷为平地后在此建造德安里。不同的是:前者指方耀的官邸及属村德安里、和安里、福安里是马院桥、寨仔内、水龙寨、赤髻鸟等4村被夷为平地建成,后者单指马院桥村被夷为平地建成德安里。笔者曾亲往实地考察,发现方耀的官邸其实就在德安里内,而非与德安里并行的两个地方;据有关材料,和安里(现名“和安”)、福安里(现名“水龙寨”)和新福里(现名“赤髻鸟村”)是方氏族人住地而非方耀所建府邸。德安里与其他三里建寨的时间前者在1871年、后者在1885年,地点相差有的一公里,有的二公里。由此看来,第二个论据与事实不符,第三个论据同样没有注明其史料来源,难以置信,同时“百鸟朝凰”仅属于老寨格局,而非整个德安里格局,把“百鸟朝凰”等同于整个德安里的格局无疑与事实不符。研究一座建筑物,最好去实地考察,否则可能会犯常识性错误。另据《普宁县志》:“同治十年,在洪阳强行买地,驱散马院桥村村民,把该村夷为平地,建起府第德安里。”[10]676这一论据把方耀建德安里对村民“驱戮”改为“驱散”,应稍为接近史实。其实,早在方耀生前就有人以其种种罪名上奏朝廷了。据《明清实录潮州事辑》载:1882年即光绪八年,“有人奏,署广东潮州镇总兵方耀,办理积案,枉杀甚多,创立花红名色,勒捐潮属富户,不下数百万元,半归私囊,包庇命案,擅受呈词。又广引其族人,分官汛地。……普宁县属向有马耳桥永安乡二村,居民以旧怨尽被驱戮,将马耳桥村名,改为德安里乡,聚族霸居,该总兵拥资数百万,开设当店、糖行,罔利营私,请饬查办等语。所奏是否属实,着裕宽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庸徇隐。”案件查办的结果是:“寻奏,方耀督办潮州,任劳任怨,不避艰险,筹办善后,悉和机宜,全潮一律粗安。所参各款,逐一访查,均无实据。报闻。”[7]297而《曾国荃奏疏》则详细说明了“德安里”由来:“原参普宁县属向有马耳桥、永安乡二村,居民以旧怨尽被驱戮,将马耳桥村名改为‘德安里’乡,聚族霸居一节。查普宁县属向有马耳桥、永安乡二村,自咸丰四年兵燹焚毁,遂成丘墟。其时方耀并未在籍带勇,两处居民非该总兵所能尽行驱戮。其永安乡地方,向系方耀族人方高鸣等在彼居住,嗣以避乱移居,贼平后始行迁回复业。至马耳桥乡,系由业主林、姚等姓凭中转卖与方耀本支六房之方燕贻堂建屋居住,确有印契可凭查勘。”[6]113这两份资料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军机处奉旨着裕宽查明,并派密委候补知府张赓云驰赴潮属各县,逐一访查后向曾国荃禀复,再由曾向朝廷恭折据实复陈的结论。朝廷也准了曾国荃的奏疏,还方耀一个清白。”[9]52可见清朝监察机关并非形同虚设。它在调查被检举人的材料时,连调查这一事件的官员都不知道检举人的个人信息。由此可知方耀在世时,关于他驱戮村民、建造德安里一事,就已被查明纯属诬告。同时,在死人之处建造府第是很不吉利的事,潮汕人尤其忌讳,方耀若照此办理有违常理。其实,德安里三寨并非方耀一人所有,老寨为方耀六兄弟共建,中寨为方耀四弟方勋及其儿子所建,新寨为方耀所建。把德安里三寨一概说成是方耀府邸,是不符合事实的。
方耀“办清乡”,无疑会触犯当地一些土豪、官绅、恶霸的利益,他们上书诬告势所必然,不以为奇。当然,今人对清廷早已查明的案件可以质疑,但一定要有当时的史料为证。如果在正史中查不到,能够发现一些物证或野史记载形成一个证据链也行,否则其可信度还不如上述《曾国荃奏疏》中提及的诬告信。
四、研究历史人物要客观全面
围绕方耀功过发生论争,根源可能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
(一)要实事求是
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但都要遵守起码的准则,那就是尊重历史,要有充足的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治史需要严谨、客观的态度。它首重原始资料,还要形成一个证据链,才有说服力,决不能以作者的一厢情愿取代史实,决不能以当代某些人的言论作为定评,更不能因为方耀的负面资料不足就把方耀后代或方耀家族与方耀等同起来,因为方耀与方耀后代或方耀家族虽有联系,但他们毕竟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不能相互取代。聚族而居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常见的农村居住形态,而每个家族中的人可能鱼龙混杂、善恶并存。以方耀家族混同于方耀,以达到借批判方耀后人来批判方耀的目的,张冠李戴,其实是以血统论取代历史研究。遗憾的是,上述凡是对于方耀的负面评价,譬如清乡杀死上万平民百姓、驱戮村民建造德安里等,笔者没有发现一项有清史或其他原始资料作为依据,不知其持论何据。实事求是,就是不要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评价历史人物,好就一切皆好,坏则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实,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无一人没有缺点错误,反之,那些历史罪人也有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应该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环境中去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上述马克思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列宁评价普列汉诺夫时既指出他才华卓越及其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同时又指出其某些错误,他们分析历史人物的辩证方法值得我们效法。
(二)论述要全面并分清主次
就上述方耀生平六件大事中,清乡、办学、兴修水利和修建德安里无疑属于地方事务。当然,国家事务也离不开地方事务,但保卫国家在当时无疑是重中之重(这里要强调的是,国家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卫国家不等于保卫清王朝)。所以,方耀一生所为,最重要的当属修筑炮台、防卫海疆。他主持修建的汕头崎碌炮台,特别是他在虎门主持营造的20多座新式炮台、炮械,建构了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法国侵略军被迫改变进攻广东的企图,转攻福建,以至于钦差大臣彭玉麟巡视粤海防后复旨奏称:“粤有方耀,可高枕也”。如果抛开这最重要的一点不谈,无疑是以偏概全。就史迹而言,汕头崎碌炮台改革开放后先后被广东省政府和汕头市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达濠的“方大人公”神庙,潮州金山书院大厅的方耀塑像,虎门、潮州等地给方耀所立祠堂,方耀主持修筑的韩江水道、丰顺白流沙溪、潮州府南堤及其督建督修的几十所书院和上百所乡校、私塾等都可为证。在潮汕历史上,若就其兴文重教所做出的贡献来说,方耀无疑无人堪比。若视方耀为历史功臣、民族英雄,当不为过。
(三)评价历史人物避免泛政治化
正如评价一座建筑物,也不应泛政治化或政治庸俗化。否则,北京故宫早就应该毁掉了,因为它是明清两代封建皇帝发号施令之处;颐和园更应该烧掉,因为它是慈禧太后作威作福之处;那些寺庙都应该推倒,因为僧尼利用宗教腐蚀民众的灵魂;许许多多的碑记更应该让其消失,因为它们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不为平民百姓立传。照此推论,历史上的许多文物都要毁灭,这岂非文革时期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重演?其实,除了政治角度,还可以有其他角度,如文物角度、艺术角度等。诚然,艺术不能与政治脱节,但艺术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德安里作为一部多种艺术结晶的巨作,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的美学理念。据《德安里》一书介绍:其“装饰工艺涵盖面广,有各种木雕、石雕、壁画、潮汕嵌瓷、灰塑等形式;就艺术手法而言,有通雕、平雕、半浮雕、泥金漆画、水墨浅绛、大绿设色等;题材有戏曲、人物、神话故事、山水花草、虫鱼鸟兽等。不胜枚举的细部装饰或精工细琢,或粗犷质朴,或深沉含蓄,就整体风格而言,富丽雅致,匠心独运。”[9]21这些都颇值得珍视和研究。对前人创造的艺术不加维护,任其毁灭,无疑是对艺术与历史不负责任。
[1]李治亭.清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7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嘉业堂钞本.清国史:第1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第45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曾国荃.曾国荃全集:第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历明.明清实录潮州事辑[M].香港:艺苑出版社,1998.
[8]饶宗颐.潮州先贤像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9]广东历史学会,普宁市市场物业管理局.德安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10]普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普宁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1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等.大南山苏区史料汇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12]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普宁党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13]汕头市历史学会普宁县分会.普宁史学·掌故[M].普内出准印证字第05号,1990.
[14]刘纪铭,蔡超.中共潮汕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5]陈竞飞.方耀传奇[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佟群英)
K207
A
1001-4225(2017)04-0038-06
2016-04-27
燕世超(1954-),男,安徽涡阳人,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