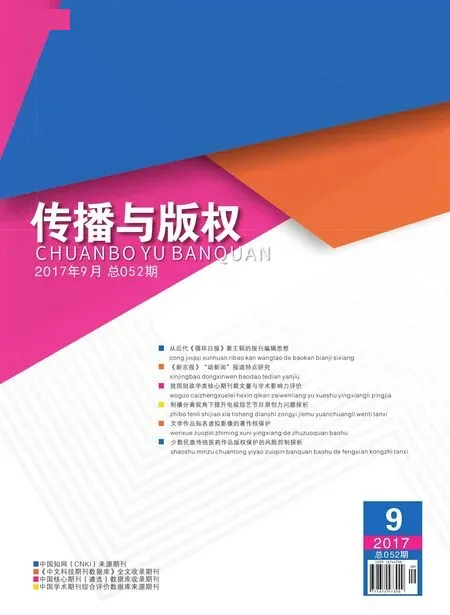天宝十四载中华帝国印刷术之“升”与“回”
2017-03-28朱政德
朱政德
天宝十四载中华帝国印刷术之“升”与“回”
朱政德
大化播扬,沧漭宏广。语言奠立后,文字创辟是一起不闻烽鼓的战役:符号化信息革命自此触启,刻就中国传播史惊崖裂岸第二笔。千载以继,造纸、印刷双峰迭起,信息传播、贮存再揽胜绩。时值雕版让鼎活字之际,印刷术却迟迟无力进驱,传播革命于中华帝国滞入僵局。究其病因,物议多指明清;而笔者认为,印刷传媒于中华帝国由“升”至“回”的轮替乃中华帝国文化架格“反现代性”之应然,与文化沉疴累世不愈之必然。
中华帝国;印刷术;信息传播;文化架格;反现代性
宕开中华帝国文化脉络,天宝十四载是一枚句号,却被故作嘲弄地补上一笔,为帝国史诗勾出一枚欲抑先扬的逗号。
彼时,霓裳羽衣的谰言被渔阳鼙鼓戳穿。“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安史二人匆匆跳梁的闹剧,谱下一阕文化衰变的序曲。文化独具惯性,盛唐气象死而不僵,流泽两宋;赵宋之世,虽有彩色套印、活字印刷等技术新秀为传播史屡制新词,但传播技术所负载的“文化本体”,却无时无刻地吐纳暮气,这为印刷术后劲乏力暗拟了牓题。
诚然,如若天宝十四载是中华帝国无计规避的宿命,倘若帝国文化架格终必沦为“循环的超稳定”,那么印刷术由“升”至“回”并于近代化前夜见陵于“反现代性”而赍志凋萎,似乎必是一种不可补缀。
所谓结局,何尝不在开篇便预埋了伏笔?
一、中华帝国文化架格之先天隐疾
返视先秦,前帝国时代亦是建构帝国文化架格的“轴心时代”。其时,化成天下的人文信息多呈拉斯韦尔式线性传递。纵有“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的舆情抓取,抑或“学在官府”的文教藩篱被“有教无类”取缔,但信息传播之宗宰无出剥削阶级其外。移步帝制,该传播方式虽连遭自下而上的冲击,却无损大体。其以“学而优则仕”的诱惑使天下草民“被主动”地涌向“精英至上”的传播视域。经社会流动反哺,帝国传播格局渐被铸成“超稳定”的铁壁。
致命的矛盾就此蠢蠢欲动。它造就了印刷术的荣耀,却又迫不及待地将其毁掉。
外儒内法的帝国精英默许着传播技术、语言文字的世俗普化,其本心绝非对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更无涉“启蒙民智”的社会使命。于彼看来,信息传播与阶级流动是互为表里的双面,二者归流于至大无外的阶级利益。防民甚于防川,与其“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乃至诱发屡禁不绝的板荡、起义,不如撬动利益壁垒的一架吊桥,将庶民魁首招安为“辅弼”。如此,心有不平的庶民群龙无首,而民之能人被精英同化、掌控,并以身作则为天下人布道“释褐”的一线天窗;如此,社会仿若植入代码的计算机,数以万计地循环着一个名为“稳定”的程序。
这组程序需要一个求解的算法,意识形态便当仁不让地成为首选。
二、隐疾未发的帝国文化进阶期
随着帝国疆界及物质活动的扩大,秦至唐成为封建主义的进阶期,亦是文化传播的进阶期。技术领域,契随不断简化的象形文字,丹青竹帛、造纸术直至雕版印刷使一度被贵族专享的信息资源开阀下泄。与之如影随形的是民间语文经士人“归于雅驯”,以及世卿世禄、九品中正向科举取士奔赴。大行李唐的雕版印刷铭刻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价值取向,将天下英雄载入“朕之彀中”,为精英集团注入源头活水。统治阶级以组织资源下放为工具,通过阶层流动削弱阶层固化诱发的不稳定。四万九千首诗歌流馨枣梨,无不咏叹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时代里“知识就是权力”的真理。作为知识传播、存储的中间介质,雕版为帝国壮年刻出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春秋[1]。
三、讳疾忌医的大唐精英与权力控制下的传播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教化传播的边界是制度(“事”)。缺省制度把关,民主意识觉醒的庶人将不再安全。
帝国精英深谙此理。这恰恰旁证了举国能诗的唐宋盛世里,文化却仍是精英的玩具。
因而,防波之堤不许信息洪流无限上涨,无论是“异端”思想抑或传播技术,其活动半径已被“祖宗之法”封顶。更有甚者,举国庶民醉于“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晋身大梦,“准精英”的自我认同使他们将万般术业贬为下品,一旦精英阶层对读书之外的任何一种抛下否定,他们鲜少逆流而上。这就解释了活字印刷异军突起后非但未能斩获主流认同,甚至民间匠人也无心使其更上一层;直至1450年古登堡将这项失落已久的技术为其所用,十三万块《大藏经》仍不改当年滞重。
文字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天宝十四载,沦为招安工具的封建帝国文化在昙花一现后与外强中干的封建主义帝国同其式微,而根柢封建社会形态的“文化本体”及其派生的“文化架格”,使以此二者为内驱的传播技术在风雨寒暑间无可奈何地伤悴。
四、“反现代性”与印刷术病入膏肓
宋元明清,文化架格由开放趋于内敛,相应地,活字印刷在庆历初年电火行空后渐次暧黯。崛起的商品经济与市民阶级一度萌发懵懂的民主诉求,取味民间的词曲、杂剧、传奇宣言着世俗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挑战。与此同时,垂死挣扎的封建阶级使专制压迫登峰造极。进退维谷的自我诉求在严酷政治生态下变异。于是,“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的泰州学派等一众市民化士大夫于掊击理学淫威之余,却矫枉过正,使具有前现代性进步因素的个人主义思潮以“朝不虑夕,恬不知耻”的香软馋猾面目示人,并一定程度速就明亡清兴的革鼎之难。
清初,遗民文人痛斥明季携有前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为“束书不观”无根游谈,而存此执念的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吴伟业等巨擘又相继荣登“汉学”“虞山派”“梅村体”等导平清朝三百载学术、文艺界先路的宗匠人物,因之,其经世致用或“诗有本”等文艺主张使帝国文化架格初步肃清明季前现代性文化因素,而稍后蜂起的文字狱以生民未有的强权使文化传播沦为专制权力的附庸。如此,上自魏阙,下至学林;前者有意,后者无心,两股“反现代性”思潮合流,使文化架格臣屈帝座之下,风骨不敌媚骨的文化架格,岂能衍育拥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现代公民?由此,印刷术等技术文明徒然鸿渐于时文、制帖诗、布道书、杂剧传奇等传统形态或“羼以懵懂的前现代性”等文化载体的刻印实践,而商业化刻印因“重本抑末”的阻遏及对匠商无所底止的捐税终无力、无心投资新技术以扩大生产,这使活字印刷作为包蕴现代性潜力的母体,终然子嗣艰难。明清二代,雕版印刷及配套技术已臻于至善,其应对传统农业社会稳定、有限的精神文化需求可谓得心应手,传统社会稳定的惰性使印刷业界对有待试错、略显冗余却实为现代性传播推手的活字印刷不屑问津。
五、对“反现代性”文化架格之追问
吞噬活字印刷远大前程的“反现代性”文化架格确属印刷革命悲剧之一幕。雕版刻下一个盛世,而活字却徒然抱璞。在冷落的幽愤中,它见证着超稳定的中华帝国,在不知其反的循环运动里,直至耗尽最后的力气。读书至此,可堪追问,为何古登堡诞生于莱茵左岸的美因茨而非雄踞江河五岳的中华帝国?
信息是不确定性的削弱。窃以为,文化架格中信息不确定性愈强,文化架格所衍育的传播方式愈加趋向现代化。信息是人对环境变化发射信号的解码所得,是客体对主体的正负反馈,主体掌控信息而详究他者本末,进而对环境中的自我产生自觉的掌控力。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自然科学、人文理性呼唤着成见、习常、偶像等一切确定、稳定性权威被日新月异地质疑、重估,此谓不确定性之一;官僚政治、市场经济诱发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频仍的阶层流动打破农业帝国乡土模式的熟人社会——陌生社会的匿名性谓之不确定性之二;升沉于现代性风险社会的个体,面对偶然性高于稳定性、随时有偏离最初设定之虞的异度空间——此刻,实时传播、即时反馈的信息资源俨然跳脱文化架格,它睥睨能源、材料,跃居重构社会秩序的鼎足之一。罔顾风险性至上的语境,一切传播都无以汲取现代化进阶的原动力[2]。
文艺复兴前后,欧洲爆发著名的“古今之争”,此番论辩肇开欧洲现代性先声,一种线性、进步的时间观率先敲碎哥特教堂祭坛上“永恒”的静定,民族国家、重商主义下的欧洲,可谓风起云涌,异军突起。其空前不稳定性呼唤着现代性传播手段为其所用,以应变局。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第二幕第三场写道:“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誓言和麦秆一样,人们的承诺就是薄脆饼,诚信才是唯一可取的。”近现代传媒作为匿名性风险社会公信力代言者,催生了古登堡活字印刷机腾如骏奔地为市民传递讯息。信息传播被目为国之公器,传媒专业主义使信息传播成为职业精神支撑下的体面行为,而庞大的市场需求倒逼印刷商投产效率高超的活字印刷机以自由竞争[3]。
相反,此时的中华帝国迫于自然经济、东方专制主义,遂止步于近代化前夜。帝国文化架格内一再掀起“古文运动”等反现代性逆流。乡土中国,家国同构——熟人社会宗法制度下,“过去是时间的原型,也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式”,致君尧舜等上古理想被集大成地尊崇,并被寄以士林清望,而一切新思潮、新技术或被斥为“三风十愆”或被贬为“奇技淫巧”而罹患排挤。循环的时间模式,稳定的“敬授民时”,日复一日地循环、静窒,使千秋万岁如出一家之手,治乱分合如诉隔日之事,民人耕读传家,唯叨一饱,唯捧四书,唯希一官,唯事一主,岁岁年年还相似的社会动力机制,鲜有“兵燹、苛政”等中世纪风险外的现代风险形态。信息之于人民,无外乎上传下达之政令,坊间闾里之风言,可有可无,以为谈资。需求匮乏引致信息市场疲软既久,供给层又受主客观多方抵牾,雕版印刷的高位裹足、活字印刷的后继乏力可谓题中之旨,必有之义。
六、让天宝十四载结束
江宁缔约,国将不国。在屡试不爽的招安后,以文化为诱饵的帝国精英,玩尽权力铁蹄下枪弹论的传播把戏,却再也无力承担最终的结局。
天宝十四载开启了帝国天命的潘多拉之盒。体被痼疾的中华帝国,踬蹶文化架格千岁之久,却无计自愈,无剂以医。终然,泰西利舰燃放现代化烈焰,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黑手将古中国遗骸推入全球化渊薮。被迫的现代化使中国传播革命始终带有半殖半封的时代烙印。
思视当代,百年国耻悉以湔雪,自由民主深入人心;而天宝十四载镌刻的前车之鉴使后车中人不得不式毂怵惕。天宝十四载及其后千载之文化架格,其痼疾所依凭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已荡然无存;而其作为一种传播思维,仍使当代传媒界人皆侧目。如何使天宝十四载彻底终结?唯有打破似正实邪的招安循环,唯有开辟上下公议的双向回路,唯有取缔皮下注射的线性灌输,唯有“表里如一、明暗同度”的彻底现代化,文化传播才得以人为本,印刷术等文化传播技术,才不会乐此不疲地搬演“升”“回”的两难。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张昆.中外新闻传播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作 者]朱政德,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