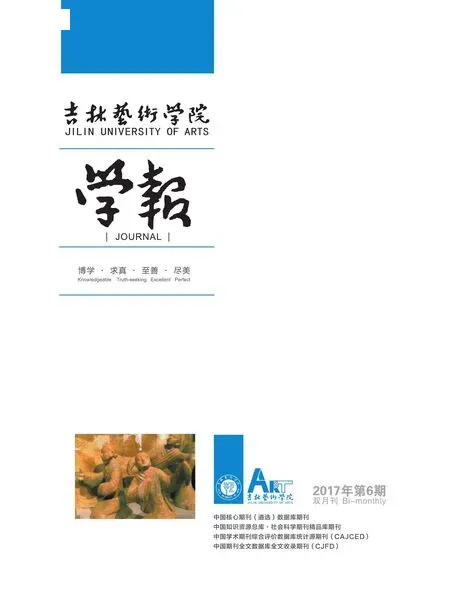颤栗的延宕与视觉的振荡
——关于电影《敦刻尔克》的节奏分析
2017-03-27蒋东升
蒋东升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
颤栗的延宕与视觉的振荡
——关于电影《敦刻尔克》的节奏分析
蒋东升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
取材于二战史实的诺兰新作《敦刻尔克》是一部异于其以往作品风格的“非商业的商业电影”。影片采用多线叙事并配合交叉剪辑手法营造反复式节奏,用错落有致的音效锻造生死逃亡之速的隐喻性节奏,巧设悬念所带来的负向度情感的延伸呈现出绵延性节奏。颤栗的音效、IMAX摄影机拍摄等所带来的沉浸感使《敦刻尔克》在中国引起一番观影热潮,并且这种沉浸式观影与影片内外节奏的配合所给观众带来的颤栗感和视觉冲击效果是对战争的反思,是一种不反思的反思。
克里斯托弗·诺兰;敦刻尔克;电影节奏;绵延
克里斯托弗·诺兰最新作品《敦刻尔克》(以下简称《敦》)虽然没有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顶配技术(3D/4K/120帧),但延宕的音效、大量的主观视角、IMAX摄影机拍摄等手段所达到的沉浸感,让观众身临二战战场体验战争真实的时间维度。简单的情节、历史的群像、寥寥的对白、消隐的敌人等诸多非商业电影元素似乎与观众的视野期待相背离,但诺兰却给观众奉上了一场肆意饕餮的视听盛宴,影片更被中国观众赞为“最好的战争片”。那么,《敦》靠什么赢得观众呢?毋庸置疑,《敦》最大的特色就是节奏鲜明。法国先锋派电影理论家莱昂·慕西纳克谈及电影时说:“是节奏,不然就是死亡”[1]。节奏之于电影的重要性由之可见一斑。电影自一诞生,便以节奏为存在前提。正如罗西里尼所说,电影“至为重要的是节奏,而它偏偏又是无法言传的,只是人们身上固有的禀性”[2]。“节奏只有在被感知之时才成其为节奏”[3]。虽然不同主体对于客体的感知上存在差异,无法量化,但不能因此就避开观者心理谈节奏。让·米特里认为“电影中没有‘纯粹’的节奏”[4],纯形式的节奏是不存在的。我国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节奏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5]。可以看出,电影节奏是观影主体的感知、视听语言运动变化与戏剧冲突相统一的,即电影节奏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显现。本文主要从叙事、音响、悬念等角度着手结合其所给观众带来的心理起伏对《敦》一片进行节奏分析。
一、多线叙事:被拉长的“最后一分钟营救”营造反复式节奏
“最后一分钟营救”即交叉蒙太奇,是由大卫·格里菲斯在摄制《党同伐异》时创造的,所采用的平行剪辑法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中的情节进行交叉剪辑,增强了叙事节奏与悬念,创造了新的电影时空,至今仍是电影创作中的惯用手法。这一经典的电影叙事手法被诺兰赋予了新意。《敦》采用三条故事线交叉叙事,陆地一周、海上一天、空中一小时。影片一开始就进入大营救的场面,直到结尾士兵成功撤回英国,“最后一分钟营救”变换为最后一小时营救,长达100多分钟的交叉剪辑。在时间上,一周、一天、一小时,不对等的三条故事线,使用交叉蒙太奇很容易使观众对情节之间的关联陷入迷茫。这部影片的特点是“有故事无情节”,情节的弱化给诺兰在时间不对等的情节叙事上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严格来说,《敦》的交叉蒙太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因此,诺兰在故事中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时间的重合点,也即是空中一小时。实际上,在对敦刻尔克防波堤撤退的时间一周、海上民船受英国政府号召或自发营救的时间一天,与空中掩护英军撤退的飞行员与敌机战斗的一小时交叉剪辑。防波堤和海上的时间被大大压缩或省略。
故事的核心聚焦于撤退,溃败求生,核心之核是士兵在一周中等待救援的无助,在漫长的等待中,死神步步逼近,却见不到一丝曙光而产生的恐惧感。海滩空间中,因被敌机轰炸一次次撤退失败,士兵对死亡恐惧的时间被无限绵延。诺兰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所营造的逼真效果使观众与摄影机的视角统一,将观众强行拖入战场,此一做法的效果是将影片的客观节奏与观众的主观心理节奏合二为一,加之三条线的交叉剪辑营造出一种反复式节奏,增强战争对人的心灵的狂暴摧残。在影片叙事时间的第8分钟左右进入第二个时空,道森准备出海营救(第15分钟处正式出海),随后进入第三个时空,三架英国飓风战斗机入画。战斗机飞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敦刻尔克需要40分钟的时间,直到影片的结尾掩护撤退的战斗机、营救民船才到达敦刻尔克,长达100分钟的交叉剪辑呈现营救撤退士兵的过程,这让观众屏住呼吸直到最后一刻,无形中增强观众的恐惧感,与之产生了心理共鸣。
在《敦》的叙事时间行进至一半、海上道森的营救船只与空中战斗机第一次出现在同一画面时,影片才真正进入交叉蒙太奇阶段。此前的平行剪辑只是单纯因叙事而为之,因此,三条叙事线时间的不对等,使得此前的平行剪辑乍看起来具有任意性,但并非随意、无章可循。这种叙事方式不仅仅给观众带来了错落有致的视听节奏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蒙太奇句式成功地呈现出撤退所带来的颤栗感。正如岩崎昶所言,“把蒙太奇的任务仅仅局限于通过画面的变化和连接来创造节奏,这种想法无疑是形式主义的……这种理论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电影就变成完全脱离了精神内容,而陷入纯感觉的形式”[6],因此,诺兰绝不是借助二战故事之壳在炫技。回到影片,前8分钟讲述第一条叙事线——防波堤士兵等待撤退,并不时被敌军轰炸的场景;第一次被敌军轰炸后,交代了撤退士兵的处境,场景转向第二条叙事线——道森的船只和其他民船被政府征用——准备海上营救;场景再转向第三条叙事线,飓风战斗机前往敦刻尔克掩护英国士兵撤离;将三个场景具体状况交代清楚后,再次回到第一个场景——防波堤撤离,汤米与“吉普森”抬伤员等撤离船的悬念。与海军即将登陆道森的船只、空军即将迎敌状态交叉剪辑,三者面临的态势具有相似性。整部影片通过这种相似性的交叉剪辑,来体现不同时空中紧张的节奏态势。
这种衔接所带来的节奏韵律也是有故事比例上的考量的。“电影作品正是从节奏中体现出它本身的布局和比例关系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具有一部艺术作品的特征了”[7]。《敦》的故事主题是撤退,所以重点是海岸上士兵的撤退情况,其次是海上的营救过程,再次是空中的掩护,因此诺兰在安排故事时防波堤撤退时间是一周,海上营救时间是一天,空中掩护时间是一小时。那么在交叉剪辑的叙述时间中,防波堤撤退的用时最长,其次是海上营救的叙述时间,最后是空中掩护的叙述时间。通过这种叙述时间由长到短和占据全片比例的能指,其含蓄意指是撤退的困难、营救的艰辛、掩护的紧迫,三者的交叉剪辑整体体现出的特点是由疏到密的反复式节奏,从而建构了影片的紧张、恐惧气氛。
据此不难看出,在常规的多线叙事中,有意被拉长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结合导演所营构的沉浸式观影手段使恐惧感被无限延宕。诺兰许是无心插柳,但确有对战争变相反思的意味。
二、颤栗音响:错落有致的音效锻造生死逃亡之速的隐喻性节奏
让·米特里在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电影符号学质疑》中认为“电影节奏归根到底是一种音乐结构”[8]。普多夫金、莱昂·慕西纳克、多宾等诸多电影理论家在电影节奏的研究中也多借用音乐的节奏进行类比分析。此种类比合理与否暂且不论,但不可否认,音乐在制造电影节奏中确有一席之地。电影声音作为符号,其表意功能不仅在于能指所简单对应的直接意指,更在于其与画面的匹配关系所产生的含蓄意指。大众传媒传递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就是含蓄意指,罗兰·巴特将这种含蓄意指称为“隐喻”。“隐喻是意味着将一种视觉内容同一种音响元素相并列(在同一画面或两幅画面的连接中进行),此时,音响便通过它所包涵的形象与象征价值而去突出画面的意义。”[9]《敦》中的音效的形象是心跳声、秒表声,用这种音响的象征性来突出士兵与死神赛跑的隐喻。
《敦》的配乐是由好莱坞配乐大师汉斯·季默一手打造,本片中的音乐与电影的常规配乐不同,是将音乐做成了音效并塞满全片,令观众时刻屏住呼吸,似乎有张无弛。一部好的电影作品,节奏要张弛有度,似乎《敦》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做法自然会超越观众对商业类型电影的期待视野。影片一反常规战争片的套路,一开始就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的戏码,主人公死里逃生。影片叙事似乎并没有开端、发展而直接跃至高潮,并且高潮不断,直到最后一刻成功撤离。与这一连续性高潮相附和的是颤栗音效。独具特色的音效是《敦》的一大特色。错落有致的心跳声、秒表声几乎贯穿全片。这种音效实际上传达了时间的迫切与神经的紧张。撤退时间的紧迫性,隐形敌人随时的轰炸以及军船与民船的抢时性营救,似乎整部影片都在与时间进行较量。面对生死每位士兵的生本能被激发,都在与时间赛跑,并在上演一幕幕分秒必争的生死大逃亡。《敦》的视听语言的内在张力所呈现的是悬疑和惊悚。正如诺兰所说,“我不是把它当作战争片来拍的,而是当成关于生存的悬疑惊悚片来拍的”。惊悚源于对对象的未知,基于此,全片德军始终未露面。
《敦》的超真实音效制作可谓独具匠心,能引发听力错觉的谢泼德音调(Shepard tone)令人毛骨悚然,如坐针毡。另外影片中的心跳音效不是生命处于常态的心跳声,而是人遇到危险本能产生紧张时的快速心跳,并且心跳音效始终处于一个频率上,但振幅却有强有弱,秒表声也有同样的特点。纵观全片,似乎音效与台词互换了角色。戏剧化的音效成为推进故事和表情达意的手段,寥寥的台词却成了故事情节的点缀,不至于让观众如欣赏默片一样乏味单调。在德军空袭来临时,特别是指挥官抬眼望远方时的寂静,汤米和“吉普森”抬伤员上撤离船的争分夺秒;撤离船被德军炸毁后士兵跳入海中逃生;撤离船被鱼雷轰炸后士兵被封闭在船舱内;英国飞行员迫降海面后被困机舱内;德国战斗机轰炸道森的营救船;空中飞行员与德军战斗机正面交火等等。这一系列生死场面和空中战斗场面所匹配的音效皆处于强节奏状态。音效的强弱更替直接配合了小情节的跌宕起伏。强弱有力的音效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位士兵每一次面临敌机轰炸所引起的恐惧与逃生上。作为战争中每一位士兵内心恐惧情境的变相描摹的颤栗音效,加之IMAX摄影技术,在视觉真实与听觉真实的交织所呈现的电影艺术感官中生、死与时间的节奏隐喻性上,可使观众从中“体验或感染到那种思想和情趣,从而引起同情和共鸣。”[10]视觉与听觉节奏的匹配使观众始终沉浸在敦刻尔克的战场中,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并在这种恐惧状态中去反思战争的残酷,以及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与肉体的伤害。
三、巧设悬念:负向度情感的延伸呈现出绵延性节奏
“悬念是由创作者通过对某些信息(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危险、令人期待的欲望等有关)予以隐藏或强调的叙事技巧,在虚构叙事性文本中所预设的,使得接受者在接受活动产生期待(正向度情感)或恐惧(负向度情感)等不确定性情感反应的叙事活动。”[11]“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历史事件放置在电影中似乎并无悬念。但是诺兰却说,“敦刻尔克这个故事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悬疑感”。事实上,诺兰的悬念并非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结果,而是撤退中的细节。中国对具有史诗性的历史正剧创作准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用在《敦》中。诺兰制造悬念的手段,除却上文提及的音效之外,便是常规的故事悬念。《敦》的故事悬念体现在战争中个体生命的升降沉浮之细微处,让观众在士兵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情境中体验战争的残酷而产生悬疑感。如影片开场,英国士兵在敦刻尔克街头找水喝时被敌军发现,一个个士兵在敌人极强扫射时接连倒下,短暂的时间之内汤米能否成功脱身;汤米跳过一个大门之后,子弹又被卡住;在海滩一场中,敌机接连轰炸的恰好的汤米卧倒的方向,汤米是否会被炸;开场的两个场景汤米可谓是死里逃生。由于遇到敌机轰炸,原来抬伤员的两位军人被炸死,为了混进撤离船汤米和“吉普森”借机乔装抬担架人员赶往撤离船,但此时指挥官已经下令准备出发,二人能否成功登上撤离船;随后二人通过隐藏,不但躲避了敌机的轰炸还成功上了撤离船,但随后撤离船却被敌军的鱼雷炸毁,士兵被困船舱内;空军飞行员柯林斯由于战斗机被敌机射中不得不迫降海面,但成功迫降后舱门卡住能否成功脱离;被炮弹轰炸受到惊吓的士兵失手推了乔治,致使乔治磕破脑袋血流不止,乔治能否坚持到返航。空中战斗机油量不断减少最后能否击退敌人并成功返航;被困敦刻尔克海滩的士兵在飞行员法里尔的掩护下成功撤回英国,但法里尔的战斗机已经油量耗尽无法返航,不得不迫降敦刻尔克海滩;由于老式战斗机的机轮需要通过手摇才能从机身中显露出来,法里尔能否调正机轮安全迫降。诸多不确定情境皆是诺兰精心设置的悬念。《敦》中悬念横生,但其设置与解除相连,情节跌宕起伏,负向度情感受到积压而逐渐升级。正是这种扣人心弦的连续性悬念,使观众在体验战争的残酷、生与死的边界陷入恐惧的绵延。
故事的悬念“建立在观众对主人公处境的怜悯和恐惧之上”[12]。导演通过制造念将观众拉入意义建构的活动中,通过缝合机制,让观众对银幕角色产生认同,获得想象性满足。同时产生内在共鸣,并对战争中的冲锋陷阵与生死逃亡产生恐惧。如前文所述,全片似乎没有常规戏剧叙事的开端、发展,直接跃至高潮,让观众直面战争的生与死,这种负向度情感一直延宕至影片结尾。诺兰所采用的IMAX摄影机拍摄和特殊音乐的渲染,以极其震颤、压抑、焦虑的心理感受和身临其境的视觉冲击将一个历史事件呈现给观众。
四、结论:颤栗节奏的伦理诉求——不反思的反思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极具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但战争的基调却是悲剧色彩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而战争的悲剧能够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伦理反思——战争给个体生命所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是不可想象的。
《敦》作为一部“诺兰式”战争片,全片除了一些轰炸与机枪对决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血腥画面,但有战争就会有奉献和牺牲。有论者简单地认为《敦》是一部非英雄主义的电影,空中飞行员法里尔在油量即将耗尽时决定继续追击敌机以确保海滩士兵安全撤退而无法返航,最后迫降于敦刻尔克的德军防区后被俘虏,这种大无畏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彰显了英雄的气质。正如片尾士兵在接受盲老人赠送的衣服时说,“我们只是逃亡”,老人说“这就够了”。言外之意,为正义而战的每一位士兵,无论成败皆是英雄。另外,还有论者认为诺兰的《敦》并未对战争做出任何反思,纯属于个人风格的实验电影。相反,导演通过主观视角、声画语言的变化组合和IMAX摄影机拍摄等手段营造的颤栗节奏效果将观众缝合在“真实”的二战战场中所带来的视觉振荡和极度恐惧,正是对战争的一种变相反思。
[1][7][法]莱昂·慕西纳克.论电影的节奏[J].电影艺术译丛,1963(05):166-172.
[2][意]罗贝托·罗西里尼.罗西里尼论电影[J].电影艺术译丛,1979(01):291-302.
[3][4][8][法]让·米特里.电影符号学质疑:语言与电影[M].方尔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219,229,219.
[5][10]朱光潜.谈美书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64.
[6][日]岩崎昶.电影的理论[M].陈笃忱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80.
[9][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105.
[11]陈瑜.电视悬念的叙事分析[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15.
[12]陈瑜.电视悬念的叙事分析[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7.
Trembling Delay and Visual Shock--The Analysis of the Rhythm of the Film Dunkirk
JIANG Dong-sheng
(Shanghai Film Academy,Shangha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72, China)
Nolan’s new work Dunkirk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World War II. The movie is a "non-commercial commercial" movi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yle of his previous works. The film uses multi-line narration with cross-editing techniques to create a repetitive rhythm, using patchwork sound to forge the metaphorical rhythm of the speed of escaping from life and death, and exaggerates the suspense caused by the negative degree of emotional extension showing a continuous rhythm. Thriller sound,IMAX camera shooting which bring the immersion so that Dunkirk in China causes some watching craze, and this immersive film and film with the rhythm bring he thrilling sense and visual impact to the audience,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war, a reflection of no reflection.
Christopher Nolan; Dunkirk; movie rhythm; extension
胡子希)
J951.1
A
CN22-1285(2017)046-051-06
10.13867/j.cnki.1674-5442.2017.06.08
本文系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62400410441)阶段性成果。商丘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16GGJS19)阶段性成果。
蒋东升(1985- ),男,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与影视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商丘师范学院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