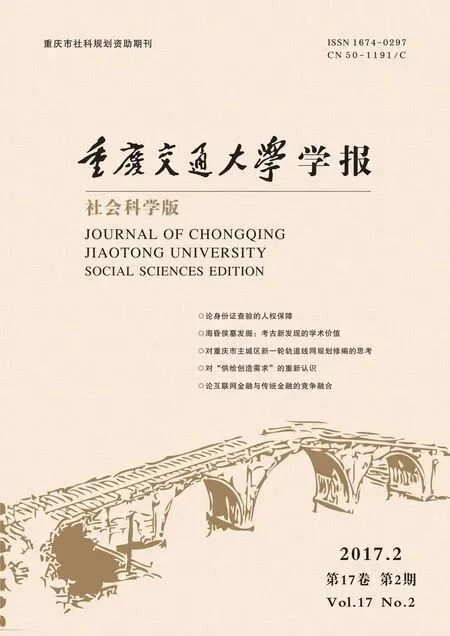另类的“文革”想象与叙述
——评王小妮《1966年》
2017-03-27徐翔
徐 翔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西安 710125)
另类的“文革”想象与叙述
——评王小妮《1966年》
徐 翔
(西安培华学院 人文学院,西安 710125)
“文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回避的重大事件,亲历其中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更多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内,出于倾诉内心痛楚和反思历史的需要,文革被无数人不断地言说。文革因此进入了文学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标识,不同的作家都对那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注解。王小妮的《1966年》别具一格,以举重若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百态,描绘了历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王小妮; “文革”想象; 个人叙事; 浪漫诗意
“文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回避的重大事件,亲历其中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更多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那段历史有着强烈的倾诉、宣泄、批判和反思的情感需要。作为影响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出于倾诉内心痛楚和反思历史的需要,文革被无数人不断地言说,因此就进入了文学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标识。“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和影响,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很少能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1]面对这样的题目,不同的作家对那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注释,加之文学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革时代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无论以何种态度来书写文革,作品中的历史大多是作者亲历的,与自我的文革记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作家,王小妮自然是文革的亲历者,但她并不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对自己作为“亲历者”的那段历史反复书写。读过《1966年》,会发现王小妮既没有问责那段历史,也没有借那段历史缅怀自己的青春岁月,相反,作者的态度是与文革拉开距离。“一个人离自己的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作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想要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加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2]作者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让小说《1966年》发掘了历史洪流遮蔽下的另一种真实。作者在小说序言里讲到:“热衷于大历史的,始终还把它当做一个极特殊的年代,或褒或贬,我倒觉得它更像罗生门,未来会持续出现新的无限的讲述空间。”[3]作为书写对象的“文革”,在王小妮笔下因为视角的特别具有了另一种颜色,小说以举重若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百态,描绘了历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发掘了文革叙事的新的讲述空间,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一、轻松的沉重
《1966年》这个书名会让很多亲历者感到沉重、壮烈和悲伤,对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们来说,那是一段苦难岁月,是永远不想回忆的梦魇,新时期之初的很多小说就描写了十年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创伤,这样的书写方式是作家们在政治解压后急于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压抑的情感所致。这些小说从不回避那个狂乱年代的社会景象:漫天的大字报、整日响彻耳边的口号和革命语录、如火如荼的武斗和大批判,以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伦悲剧。先锋文学的文革书写更是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暴虐场景和狰狞人性,血腥和暴力、权力的争夺与厮杀,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暴虐。
《1966年》会让人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让人似乎感受不到那个年代的沉重。小说中没有出现文革中惨烈的武装斗争、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也没有出现传统文革叙事作品中那些脸谱化的反面角色,甚至没有出现文革时代的惯用词汇“大字报”“红卫兵”等,出现的只有“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很多“戴红箍”的人。小说写到了游行、惊慌,但那只是作为背景影影绰绰的;写到了死亡,但没有描写惨状,也没有家属的嚎啕大哭,一切都平平淡淡,王小妮似乎在既定的写作轨道上出了轨。小说笔法疏淡轻盈,叙述语言平淡,情节几乎是寡淡的,我们无法通过作品感知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不可否认,文革时代是荒诞并且沉重的,以往的小说在面对文革历史时,或者将其当作一个政治寓言去解读,或者着力去书写敢于与荒诞时代对抗的“大写的人”。《1966年》是独特的,十一个片段式的简单故事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全部。
小说用简笔画式的手法勾勒了1966年几个普通人的生活图景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人物皆不是个性鲜明的人,甚至面容也是模糊的,而且没有名字,只以父亲、母亲、儿子、老太婆、水暖工、年轻人为代号。但仔细阅读小说,会发现作品在很多细节、人物的心理行为刻画和很多不经意的描写中泄露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压抑和恐惧。作品举重若轻的描绘背后,确是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生命中无法承受之恐惧与伤痛。尽管没有任何暴力的描写,这些人却被笼罩在一种山雨欲来的恐惧中,谁也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更无从预测下一分钟的生活,即使没有被剧烈的洪流裹挟,生命也变了色彩,变了温度,变了声音,充满问号,这也许是人所经历的最大恐惧。
《普希金在锅炉里》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文革的到来让平静的家庭生活离一家人越来越遥远。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也无法理解突如其来的另一种生活,如同小说里他们不理解为何住在日本人建的房子里是一种罪过。父母给四个孩子正儿八经开了会,告诉他们:“我们家才这么几口人,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干活是不对的,不应该,非常错误!”父母告诉孩子们以后得他们自己烧锅炉,并给孩子们分了工,而且因为爸爸妈妈随时可能“不在”,又告诉孩子们:“从今天往后,万一家里大人不在,这个分工也不变。”小说中的父亲每天都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灾难,“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像一段折子戏,紧张而短促,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已经在父亲的脑海里彩排了无数次”。主动来帮这家人烧锅炉的年轻人也活在恐惧中,他的书包里装着摘抄的普希金的诗集和苏联姑娘的照片,“那个书包给他带来的危险比定时炸弹还大,比几辈子的财主的变天帐还心惊胆战”。为了安全销毁这些,他主动来帮这户人家烧锅炉,却让这个家庭担惊受怕,宁可受冷挨冻也要避开他。《新土豆进城了》讲述一个小院里住了三户人家,其中一户是穿着埋汰的收废品的老头老太,在这一年收废品的老头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心颤了。有一天,老太太被人喊了20年前当妓女时候的名字,她慌了,知道大祸临头,转身找老伴,却发现相伴20年的人不见了,是多么深刻的恐惧让这个男人断绝了夫妻情分。
小说中的很多人都活在惶恐中,锅炉工把他抄的普希金诗选和苏联姑娘的照片藏在床板底下,出租小人书的母亲把小人书烧了,把满洲时期的邮票藏在米袋子里,有过风月生涯的老太婆把一对金耳坠埋在刺玫底下,有军功的医生也因少年时曾读过日本学校而惴惴不安。小说里文化大革命并未像一列横冲直撞的列车闯入每个人的家门,把他们的生活硬生生地分成两截,历史的巨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突兀,相反,那种变化是一点点浸入家常的日子里的。他们发现这个社会变了,原有的秩序被打乱,生活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变得不可理喻,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过去熟悉的世界渐渐崩塌,变得面目全非,只能被动或主动地陷入政治的狂热之中。社会氛围变得压抑沉闷,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再被自己掌握,明天变得不可捉摸。从城市到乡间,从大人到孩童,每个人都压力重重,惶惑不安,惊惶失措,甚至性格扭曲。王小妮用若即若离的笔触,用平静如水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1966年无数人的噩梦,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压抑、恐惧和疯狂,给当下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对历史的感知方式,让读者在轻松中感受历史的沉重。
二、从集体记忆到个人叙事
面对“历史”是无数作家在写作中都要面临的命题,文学如何对“历史”作出回应,是无数作家在面对文革记忆时都无法忽略的。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反思”文学关于文革的书写被填充了过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反思的内容,但无论是沉重的政治批判还是冷峻的文化反思,文革书写都被纳入了“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作家们尽管是在写个人的伤痛,但这些伤痛超越了个人,成为了整个国家和国人的伤痛。“在这里,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已经被自然地连为一体,或者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行程和未来发展。”[4]王小妮并不想以宏大视野去回顾那段历史,小说中很难看到对文革史诗性、全景式的叙述,作者关注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历史中的个体”,是属于他们的个人记忆。
从小说来看,历史的巨变似乎并不是剧烈突兀的,反而不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似在一瞬间就完成了新旧交替。尽管很多人面对变化惶惶如惊弓之鸟,但这些变化在更多人的眼中仅仅是新土豆进城了、天凉了、叶子黄了,昭示着老百姓生活中本应有的普通,日常市井中普通的人们在那特殊一年里依然重复着往日的生活。他们也许发现了街道没有人打扫,街角的垃圾堆成了山,街上多了很多戴红胳膊箍的人,但并未过多思考,他们都是活在当下的人,心里想的还是新土豆该怎么做,今年的菜窖要挖多深之类的琐碎问题。这些小人物行进在历史之中,却又仿佛在历史之外,时代的大浪潮在表层整合着他们的生活,但表层之下依然是个人的生活细流在涌动。“当历史与个人相遇时,历史的社会意义与价值被抽空,历史萎缩为个人生存时间,甚至淡化为个人存在的氛围。”[5]在那个特殊年代,宏大历史往往凭借强大、不可抗拒的力量规范着市井民间的生活,但市井民间往往能突破宏大历史的异己力量的约束。小说试图去挖掘被宏大历史遮蔽的民间生活和个人体验。
《两个姑娘进城看电影》中的主角是一对年轻乡下女孩。一天早上,她们梳妆打扮换上最好的衣裳,骑上自行车去城里看电影,一路上憧憬着电影院的神奇。她们骑着自行车如马飞奔地进入城市。她们发现城里变了,“红砖墙上有粉笔写的大字”,“沿着街的楼房从上到下都被大张纸糊满”,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看电影的好心情。两个姑娘最后没看成电影,电影院在开大会,她们美丽的辫子也被红卫兵莫名其妙地铰掉。事实上她们并没有太苦恼辫子的问题,头发终究会长起来,辫子还会再有,她们只是遗憾这次进城怎么就不给演电影了,她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背后的沉重。
小说里大部分故事平平淡淡,都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呈现那个狂乱的年代。小说呈现的是时代边缘被人忽视的场景,本该是处在运动中心的那些激烈的红卫兵运动、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残忍的暴力场面在小说中反而缺席了。如果将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家比作电影导演,王小妮的镜头偏离了时代的大轨道,却瞄准了容易被人忽略的小轨道,记录了一群迟钝的人和他们对于这个敏感时代的迟钝的感受,重绘了那个年代的另一种真实图景,时代的苦难和创伤因为旁逸斜出的琐碎生活画面被淡化了。作为一个作家,在触及历史的时候应该先要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不必是庞大的,相反,一件小事、一个小人物就足够,一个片段、一种情怀便触及到了那段沉重历史的内里。“普通人的感受,最不可以被忽略和轻视。任何真实确切的感受,永远是纯个人的,无可替代的和最珍贵的。”[3]小人物们对生活的感受和他们普通但恒常的生活方式化解了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其实是由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构成的,他们的眉眼里藏着历史的另一种质感。
《1966年》的个人叙事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民间意识形态的体现,它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接近历史真实的途径。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巨变而出现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也没有被巨大的历史激流荡涤干净,小说也因此跳脱了以往文革叙事惯常的写作模式。王小妮用从容的文字、含蓄的方式,还原了那一年中北方小城的真实生活图景,触碰了历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故事简单,但蕴含深远的情感。
三、苦难中的诗意
王小妮是一个诗人,诗人的思维方式注定了她总是以诗意的笔法来记录生活的点滴。在她的作品里,读者会发现生活既平庸又浪漫,如同她小说里的那些故事,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背后隐藏着淡淡的诗意。《1966年》里的那些平淡故事在诗人笔下也就有了诗的特质,王小妮以细腻的笔法仔细编织着生活的每一个画面,诗人特有的细腻笔触缓缓展开了1966年大变局下的生活画卷。小说尽管写到了那个年代的沉重和压抑,却也轻轻拨开历史沉重的一角,透入永恒与温暖的光芒,让人在沉重中也能看到人性的善和美,收获些许希望和诗意。
《钻出白菜窖的人》里,年轻的医生因为上过日本学校,会说日本话整日惴惴不安,工作组上门调查他已经过世的老师是否是特务的时候,尽管自己已是岌岌可危,在百般逼问下他仍然要保护他的老师。《一个口信》中年轻的工人无意中听到组织在调查同厂的一名女工,尽管他和这个女工三年间没有说过话,但他决定要冒险给这个几乎陌生的姑娘带一个可能并无太多帮助的口信,因为他觉得“明是听见,不能去递个信儿,不能去说一声,做人不能这么不仗义”。《火车头》里有个“戴帽子”的人以组织的名义每月给无依无靠的小男孩送来五元钱,并告诉他要当一个好人,这个男人还叮嘱自己的儿子,“你到某街某胡同某号去看看,有一个孩子,看他是不是还在家,暖气热不热,有没有吃的,要对那孩子好一点”。在1966年这个混乱的年代,很多人都会变,很多人的道德观价值观都被颠覆,但在小说里,读者会看到人性所不曾泯灭的善良之光。在那个政治观念裹挟一切的时代里,大部分人往往是以政治地位来判定个体的道德品质,但这些人有着他们的善恶是非观念,有着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意识,这是开在苦难中的善之花。这些饱含着情谊的画面尽管微不足道,只是历史长河中不为人关注的一个点滴,却为沉重的历史注入了极具力量的永恒人性之美,让苦难中多了一丝温情和诗意。
小说中很多故事是以孩子的视角来写的,这又让小说呈现出了童真的色彩。1966年在成人和孩子心目中是完全不同的。对成人来说,这一年是残酷的红色风暴,让他们无时不在恐慌和恐惧中;但对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个狂欢的时代。政治运动的到来让所有既定的秩序都被打破,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却为不少孩子带来了欢愉的时光。孩子们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他们有无数的方法让自己在物质供应短缺的时代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在烟囱上》是让人读起来感觉一丝开心的文章。小男孩被母亲关在家里,但他有自己的乐趣,他用吃过冰棍剩下的小木棍搭房子和桥,然后拆掉基座上的一根,看整个建筑物一下子塌掉。他家是开小人书店的,为了避免迫害,小男孩的母亲关闭了书店,并且把小人书都烧掉。小男孩偷偷藏起了小人书的封面,尽管被母亲责骂,却依然没有说出它们的下落。后来小男孩不再是一个人了,五个小学生和他成了好朋友,最终小男孩说出了他的秘密,所有的小人书封面被他藏了起来,这个秘密成为了六个人的秘密。这是一种纯粹的快乐,孩子们都是单纯的,在那一瞬间,谁还记得外界是怎样的环境,他们只记得那干净的快乐。
事实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着自己的秘密花园,有着自己的梦幻空间,这内心的一角是灵魂深处最柔软的所在,它不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只忠于个人的心灵。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尽情地幻想,尽情在诗意中飞翔。《普希金在锅炉里》写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纯情和梦幻的世界,小说尽管也写到了压抑和恐惧,但小女孩依然有着属于少女的梦幻想象空间。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喜欢看雪,她希望每天都能下雪,她喜欢一个白色的世界,“这是一个被白雪公主之类的童话蒙骗的孩子”,这样的蒙骗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烧锅炉的年轻人触动了少女的心扉,“她的心里涌现出一种随着雪片倾斜着飘舞的感觉”,“女孩觉得她并不在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她自己有另一个世界,暖和又有好看的颜色”。因为对年轻人好奇,女孩偷看了他的本子,普希金的一行行炙热的情诗让女孩子吓坏了,这也导致了本子被扔到锅炉里化为灰烬。年轻人不再出现,女孩感到一丝遗憾,女孩甚至想象“那些诗,也许就是他写给她的”。一切好像童话一样,仿佛是一个梦,小女孩在梦中成了公主,遇上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尽管结局有点遗憾,但让沉重的生活有了一丝亮色。
传统关于文革的叙述大多是悲情的、控诉的、情绪化的,《1966年》则是舒缓的、绵密的,带着淡淡的诗意,这诗意不是作家刻意营造的,而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真实的生活,来自于人内心深处隐秘的一角。这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诗,有人能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中找到自己的童真乐园,有人能在人性泯灭的年代保存内心的善,有人会在那个苍白的年代中保留对生活的梦幻想象。出于诗人的敏感,再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王小妮心里也能激起波澜,小说中的诗意正是来自于一些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但正如她所说:“在平淡中,在看来最没诗意里,看到‘诗意’,才有意思,才高妙。现在的世界太现实。人天生就应该有奇思怪想。”[6]王小妮用诗人般飘忽的笔来写史,让黑白的年代里多了一层彩色,让苦难中多了些许诗意。
四、结语
小说《1966年》并不是要还原作为“集体记忆”的文革时代,而是提供了对文革时代的另一种叙述。作者对那个时代的描述渗透了自己对个体命运的思考,历史中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是王小妮倾注了感情的写作对象。作者在书写文革时与历史拉开了一段距离,但小说并没有因为淡化的历史情境而使写作失去意义。王小妮的历史讲述是人的命运,是历史时空里亘古不变的人性,是独特的个体生存体验,这在个体诗学意义上展现了个体在面对历史时的选择的自由。小说呈现了小人物在历史大潮面前的真实反应,有怯弱和恐惧,有人性的善和美,有自己的诗意的空间。这些人面对历史巨变的不同反应,让小说具备了类似罗生门一般的多重空间,同时,这种多样性的叙事改变了人们对文革历史的单一刻板的记忆和认识,展示了一段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1] 许子东.叙述文革[J].读书,1999(9):12.
[2] 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1-32.
[3] 王小妮.1966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11.
[5] 周新民.生命意识的逃逸[J].小说评论,2004(2):34.
[6] 王小妮.半个我正在疼痛[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222-223.
(责任编辑:张 璠)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and Narr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 Review of WANG Xiaoni’s 1966
XU 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710125,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significant event happened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bringing people endless disasters and the trauma difficult to heal.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the need to pour out the pain and reflect the histor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always the speech topic of countless people.Ther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has become a unique literary identity in the new period. Different writers have made different annotations of history. WANG Xiaoni’s 1966 is more unique. In order to ease the brushwork, the novel depicts the living beings in the special bigotry and the little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tide of history and experience, which shows an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and narr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NG Xiaoni; imagin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onal narrative; romantic and poetic
2016-08-23;
2016-09-06
徐翔(1981—),女,河南南阳人,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2
A
1674-0297(2017)02-00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