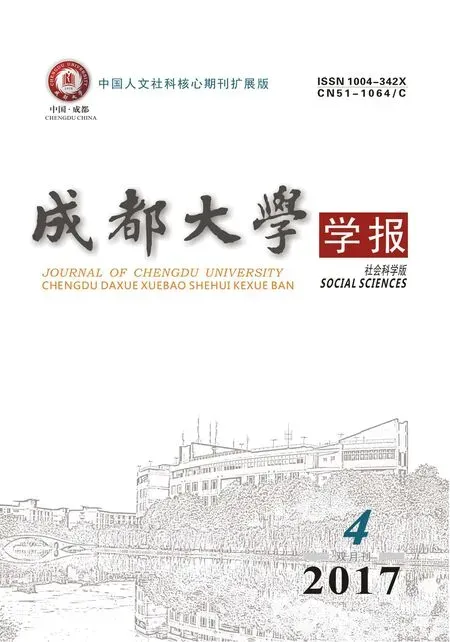论析傅雷画论对译论的影响
2017-03-24李丹丹
李丹丹
(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语言文化·
论析傅雷画论对译论的影响
李丹丹
(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傅雷是我国杰出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同时还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他对于绘画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鉴赏力。傅雷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绘画的真知灼见在“神似”说、傅译风格、创作者的素质、融合和谐观念四个方面,对他翻译思想的形成和翻译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傅雷;画论;译论
傅雷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法国文学翻译家,译著宏富、译艺超绝,同时还是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他通晓建筑、绘画、音乐、雕塑等各个领域,尤其对绘画的评论更是精湛透彻、见解独到。翻译和绘画在傅雷的艺术人生中相伴而行,傅雷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绘画的真知灼见对他翻译思想的形成和翻译的实践活动都有着深远影响。
傅雷出身书香世家,聪颖刻苦,传统文化功底颇深。19岁考入巴黎大学文科,专攻艺术理论。留法四年,傅雷阅读大量文学、绘画、音乐方面的书籍,与良师益友谈学论道,欣赏观摩艺术作品,游访名胜古迹,这样的经历使傅雷对中西方绘画都有深刻的见解,造就了他高雅的艺术品位。1931年傅雷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史和法语。1933年傅雷离开美专回到书斋,以翻译为职业,开始长达33年的译者生涯。本文从“神似”说、傅译风格、创作者的素质、融合和谐观念四个方面比较傅雷画论和译论,分析其画论对译论的影响。
一、“神似”说
在我国传统绘画理论领域,“传神”理论由来已久。东晋顾恺之在人物画中首先提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1];唐代张彦远在画论中提到“古之画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2]。“传神”论逐渐“成为我国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3]15。傅雷在《观画答客论》及与友人论画的信件中多次提到绘画“传神”的重要性,如“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4]190,“艺术始于写实,终于传神”[4]226。中国画不满足于模拟事物外在的形似,而是大胆取舍,保留最能体现事物精神的形象特征,尽力表达出内在的风神、神韵。之后傅雷又做了“形神之辨”:“神似方为艺术,貌似徒具形骸”[4]229,“倘或形式工整,而生机灭绝;貌或逼真,而意趣索然;是整齐即死也。……取貌遗神,心劳日绌,尚得谓为艺术乎?”[4]190傅雷认为中国画讲究以抽象的线条传达内在的精神,笔、墨、章法的运用产生内在气韵,“气韵生动”则是绘画所追求的境界。若只取形式而遗失神韵不可谓之真正的艺术。
“传内涵之神”直接促使翻译上“神似”说的形成。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开门见山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5]3在与罗新璋信中重申“愚事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5]56。“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使傅雷成为“神似”的代表人物,“神似”也成为傅雷最重要的翻译观点。不难看出,“神似”二字是从绘画理论借鉴而来,以绘画作比,傅雷生动地揭示了翻译的内涵。傅雷在翻译中也常受原文“形”的桎梏,“通常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傅雷是怎样解决的?傅雷要求“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把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同时“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5]23。抓住神韵、放大胆子和“最大限度保持原文句法”恰恰体现了“形”“神”辩证统一的关系,求“神似”却并不放弃“形似”,是保持“形似”基础上的“神似”。从时间上看,傅雷绘画思想早于其翻译思想,我们说傅雷翻译思想受到绘画思想的影响似乎确是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这样,傅雷借助绘画领域内的“传神”理论成就文学翻译中的“神似说”,将翻译与绘画联系起来,把文学翻译纳入了文艺美学的范畴。
二、傅译风格
傅雷把“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作为自己的“预定目标”[6]270,通过傅译实践,这十二个字也成为了鲜明的傅译风格。研究傅雷的专家金圣华给这十二字做了注释:“所谓的行文流畅,应指译文读起来犹如用中文写成的文章,既不拖泥带水,又不佶屈聱牙;用字丰富应当指翻译时,‘遣词造句’都精辟恰当而有文采;色彩变化……指原著文字上修辞色彩,一旦翻译时,也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手才能掌握得到。"[7]56
(一)行文流畅
傅雷主张绘画要“师法造化”、臻于自然。何为“师法造化”?傅雷道:“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沃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为我有。”[4]191傅雷称赞黄宾虹为石涛之后绘画造诣上第一人,是因为“黄公游山访古,阅数十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傅雷认为大画家塞尚“绝对忠于自然”,“大凡一件艺术品之成功,有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即要人格和自然合一”[4]174。“天人合一”也是中国画的最高审美境界。傅雷又道:“理想的艺术总是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即使是慷慨激昂也像夏日的疾风猛雨,好像是天地中必然有的境界。露出雕琢和斧凿的痕迹,就变成庸俗的工艺品,而不是出自肺腑、发自内心的艺术了。”[8]203由此可见,傅雷认为理想的艺术恰如大自然一般行云流水、不事雕琢,在绘画上,唯有“师法造化”才能“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4]192。
对于翻译,傅雷以为“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归一”。“原作”岂不就是绘画所讲的“造化”?傅雷又提到“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痛的大毛病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可见对待译文,首先要求“行文流畅”,傅雷也坦言“要将原作的声韵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5]29。
(二)用字丰富
译文中“遣词造句”犹如绘画的“线条(用笔)”。傅雷认为:“从线条(中国作家所谓用笔)的角度说,中国画的特色在于用每个富有表情的元素来组成一个整体。正因为每个组成分子——每一笔每一点——有表现力,整个画面才气韵生动,才百看不厌。”[4]220翻译时,傅雷生怕“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用字不够广”[5]37。在写给儿子傅聪的英文信中提醒“……别毫无变化地说‘多妙’或‘多了不起’,你大可选用‘宏伟’,‘堂皇’,‘神奇’,‘神圣’,‘超凡’,‘至高’,‘圣洁’,‘辉煌’,‘卓越’,‘灿烂’,‘精妙’,‘令人赞赏’,‘好’,‘佳’,‘美’等等字眼……”[5]170傅雷在自己的翻译活动中更是以“用字丰富”来要求自己,如aimer是极常见的法语动词,即“爱,喜欢”之意。傅雷根据具体语境和人物身份译为“心爱”,“疼爱”,“只求”,“拥护”,“爱戴”,“迷着”,“留恋”等。据傅雷看来,“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技术分歧之一是我们的线条的表现力的丰富,种类的繁多,非西洋画所能比拟”[4]218。在翻译上却正好相反,因为“刚从民间搬来”,“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5]23。傅雷深谙线条丰富有生机使得“画面气韵生动”,在翻译上也采用丰富的用字使译文自然洒脱,避免“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5]31。“线条丰富”和“用字丰富”可谓一脉相承,傅雷将绘画中“用笔丰富”引申为翻译的“用字丰富”,标新立异却又水到渠成。
(三)色彩变化
当一幅画摆在眼前时,扑面而来的便是其色彩。傅雷认为“色彩”是绘画最动人的工具。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傅雷用整个篇章讲述了天才画家鲁本斯比别人更善运用色彩;傅雷赞美塞尚“是一个大色彩家”,并分析他“成功之秘诀”在于“中间色”[4]174。学贯中西的傅雷又道“用墨在中国画中等于西洋画中的色彩”[4]221,“笔犹骨骼,墨犹皮肉。……干黑浓淡湿,谓为墨之五彩;是墨之为用宽广,效果无穷,不让丹青”[4]189。色彩变化使得画面或遒劲或柔媚或平淡或富丽。然而翻译比绘画更难,因为“译本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5]3,傅雷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教养、心理,所处的场合、环境进行翻译,译文真正做到了“色彩变化”。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众多作品经过傅雷翻译,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书中经典人物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译文完美地再现原文甚至超越原文,赋予每个人物鲜明的个人特色:爱财如命的欧也妮·葛朗台,痴愚可怜的高老头,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克……傅雷将绘画用语“色彩变化”直接引入到文学翻译领域,为读者奉上了色彩丰富、富于变化的高品质译文,不管在翻译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属创新之举。
三、创作者的素质
傅雷将翻译和绘画作为神圣崇高的事业,不愿被急功近利或欺世盗名之辈随意对待或践踏。他谦虚自持、严以律己,对待自己的译作认真到近乎严苛的地步,始终认为自己学识不足、修养不够。他也犀利地指出“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道路”[5]32;在美术界,“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9]219。在傅雷眼里,创作者须具备以下素质:
(一)创造才能是首要素质
“任何学科,中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不若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创造才能是艺术家的生命,对于绘画来说,创造才能尤为重要,“若创造,则尚需有深湛的基本功,独到的表现力”[4]243。“深湛的基本功”是绘画的基础,“独到的表现力”是绘画的关键。傅雷批判“扬州八怪”没有“真本领真功夫”,“四王”则“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真正的笔,无一线条说得上表现力”——这都是创造才能缺乏的表现,也因此无法梦见艺术的真天地。至于翻译,傅雷道:
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像极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无论如何弹不好Schumann。朋友中很多谈起来头头是道,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歪曲,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5]32
译者的“文学天赋”犹如画家的“创造才能”,是与生俱来的,后天仅能“挖掘和培养”。没有文艺素养很难深刻理解原作内容,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全摸不到,更加无法恰如其分地用中文表达,正所谓非诗人决不能译诗,没有文学天赋很难搞好翻译。
(二)专业能力和个人修养是必要素质
傅雷认为画家有三种必要素质:“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4]229“鉴古功力”和“审美卓见”属于创作者专业能力范畴,“高旷心胸”属于个人修养范畴。译者须具备五种必要素质:“敏感之心灵”,“热烈之同情”,“适当之鉴赏能力”,“相当之社会经验”,“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5]57此五种素质也属于“专业能力”和“个人修养”两方面:“鉴赏能力”、“社会经验”、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属于专业能力,“敏感之心灵”和“热烈之同情”属于个人修养方面。
重视创作者的专业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傅雷特别看重创作者个人修养的培养。他不厌其烦地教导傅聪“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次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10]262。“我始终认为弄学术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家××家以前,先要学做人”。[8]216在翻译上,傅雷同样要求译者具有普遍的人间性,因为“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5]10。
(三)艺术修养是根本素质
无论绘画还是翻译,傅雷认为艺术修养是根本。“读书养气,多闻道以启发性灵,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自当为画人毕生课业”。傅雷崇尚“师法造化”,提出“师法造化,不徒为技术之事,尤为修养人格之终生课业”[4]229。绘画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技术层面的摹画,是徜徉山水之间的陶养性情,而是思想修养方面的终生修炼。翻译上,傅雷更是直言以艺术修养为根本,傅译作品《艺术哲学》、《约翰·克里斯朵夫》、《人间喜剧》涉及美术、音乐、建筑、戏剧等方方面面,如若傅雷不是艺术修养深厚、学识渊博的通才,决无可能传神地翻译此类大作。
四、融合和谐观念
傅雷极为钟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因为它们处处体现了协调、融合、和谐的精神。傅雷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的第一讲就高度赞扬了文艺复兴先驱乔托,他认为:
乔托全部作品,都具有单纯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与其他美一样,是一种和谐:是艺术的内容与外形的和谐;是传说的天真可爱,与画家的无猜及朴素的和谐;是情操与姿势及动作的和谐;是构图、素描与合乎壁画的宽大的手法及取材的严肃的和谐。[9]110
傅雷还谈到达芬奇的绘画和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无不展现了融合和谐的精神,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超凡脱俗,成为不朽的杰作。绘画上融合和谐观念也同样影响了傅雷的翻译活动。对于翻译,傅雷以为:
首先译者要与原作者“气味相投”。傅雷将选择原作作者比作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5]8傅雷选择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因为他与罗曼·罗兰性情气质相似,而巴尔扎克与傅雷表面上各走极端,但“剖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与不羁,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毅力、自律与执着;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与含蓄,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与狂热”[5]79。正是因为气味相投,傅雷才选择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也正是因为气味相投,译作与原作才能丝丝入扣,成就翻译史上的佳话。
其次,译者与原作的融合。“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5]57译者要充分理解原作的思想、感情和神韵,才能在译文中将其准确表达,也才能让读者理解、感受、体会原作。为翻译巴氏作品,傅雷大量研读有关巴氏及其作品的书籍;为解决书中疑难,傅雷驰书国外请教专家。傅雷真正做到将原作化为己有,才能用纯粹中文表述原文,既忠于原文又符合大众审美,展现了翻译艺术的精髓。
第三,译著中文白和谐。傅雷认为“我们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形,没有准则”,译文纯粹用普通话,则“淡而无味,生气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5]10;若译文中过多使用文言或方言,则要考虑文言在译文中是否水乳交融,方言会否影响原作的地方特色。在傅译本中,我们看到叙述文字往往“文”一些,对话往往“白”一些,甚至是方言俚语。这样便很好做到“文白分野”、“文白和谐”。
第四,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的肖似。对于文体风格,傅雷“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傅雷对于翻译巴尔扎克也颇有自信,“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感情,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5]27-28;面对伏尔泰“句句辛辣,字字尖刻,而又笔致清淡,干净素雅的寓言体小说”[5]9,傅雷难免逡巡畏缩,《老实人》八易其稿,傅雷仍不甚满意。译文要再现巴尔扎克的健拔雄快、伏尔泰的辛辣简括、罗曼·罗兰的质朴流动,“真正要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是无法兑现的理想”[5]29。正如傅雷所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5]4再回想傅雷呕心沥血两次重译《高老头》,力求遣词造句精辟恰当、译文风格神似原文,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傅雷一生都未停止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深厚的艺术修养使其画论和译论独具一格、成大家之言。傅雷的画论深刻影响着其译论的形成和翻译实践活动,画论与译论息息相通,交相辉映。无论是在翻译领域还是艺术理论领域,傅雷的名字永远闪耀光芒。
[1]罗立斌.浅谈傅雷翻译思想的艺术内涵[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67-369.
[2]马宾.东晋顾恺之与现代傅雷之跨时空对话——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文学翻译“形神观”之对比研究[J].考试周刊,2008(43):229-231.
[3]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傅敏.傅雷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10.
[5]傅敏.傅雷谈翻译[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6]傅敏.傅雷书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7]金圣华.江声浩荡话傅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8]金梅.傅雷艺术随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9]傅敏.傅雷谈美术[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10]傅敏.傅雷家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晓红)
TheInfluenceofFuLei’sPaintingTheoryonHisTranslationTheory
LI Dandan
(Zhongbei Colle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Fu Lei,one of the prominent translators of French literature in China,was also an excellent artist with high attainment.As to painting,Fu had his own unique insights and appreciation which had profoundly influenced his translation work.In this paper,the author compares Fu’s painting theory with his translation from four different aspects(spiritual resemblance,style,personal attainment and harmonious concept)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his painting theory on his translation concept.
Fu Lei;painting theory;translation theory
2016-10-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文学汉译经典研究”(项目编号:12BWW041)。
李丹丹(1988-),女,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法语讲师,硕士。
J205;H059
:A
:1004-342(2017)04-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