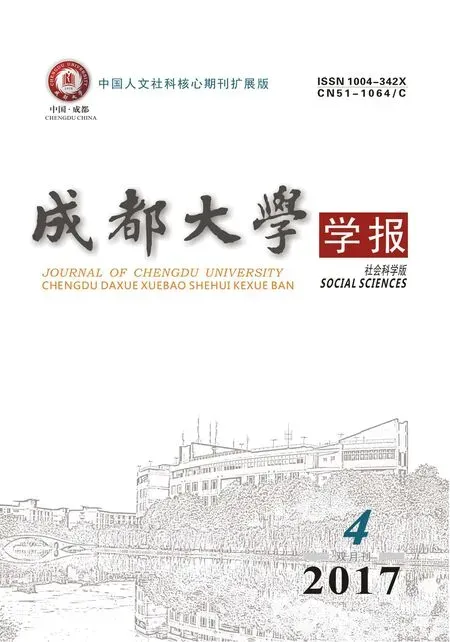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
——博尔赫斯《马可福音》之解读
2017-03-24李亚飞
李亚飞
(成都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文艺论丛·
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
——博尔赫斯《马可福音》之解读
李亚飞
(成都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马可福音》中表达了其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在小说中,博尔赫斯试图建构一组理智主义对直觉主义的矛盾,旨在呈现两个主体间的互动与对抗。故事中代表理智主义的埃斯比诺萨运用修辞、表演向代表直觉主义的古特雷一家讲述“马可福音”的过程是二者关系发生蜕变之过程;同时,埃斯比诺萨与古特雷一家讲者与被讲述者关系的最终破裂则暗示了博尔赫斯对于理智主义在把握世界认识方面的质疑与忧虑。
理智主义;《马可福音》;博尔赫斯;直觉主义
博尔赫斯小说探寻主体多样,从对人生和宇宙的冥想到对时间永恒和存在荒谬的探寻,极具个性。[1]博尔赫斯犹如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借助其丰富的文学想象,将复杂深奥的人性生存主题进行编码,以小说的形式加以呈现,最终成就其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独特的地位。在短篇小说《马可福音》中,博尔赫斯正是借助圣经故事的原型,交汇荒诞、死亡、神秘等小说元素,以极强的故事性呈现了理智主义者埃斯比诺萨的人生悲剧。具体来讲,在小说中,博尔赫斯建构了一组理性主义对直觉主义的矛盾和对抗,以这两种矛盾的互动和拉锯作为推进整个故事发展的动能。在小说中,这组矛盾主体之一的埃斯比诺萨运用修辞、表演向主体之二的古特雷一家讲述“马可福音”的过程是二者关系发生蜕变之过程;同时,埃斯比诺萨与古特雷一家讲者与被讲述者关系的最终破裂则暗示了博尔赫斯对于理智主义在把握世界认识方面的质疑与忧虑。
一、诗学中的理智主义与直觉主义
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的主导方面。[2]理智主义哲学思想强调对于理智的运用、发展和实践,它肯定认识的确定性和价值的普遍性,以及历史的进步性;然而传统的理智主义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例如它坚持绝对的真理观,因为传统理性主义坚信人们能够凭借理性来认识外部世界,达到对知识的确定性把握。[3]然而,这种理性的思维逻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便受到质疑与挑战,人们越来越怀疑理智主义式的线性思维逻辑,并对此开展反抗。
直觉主义哲学便是这种反抗力量的一个表现。直觉主义哲学思想由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所倡导,其哲学的基本观点是直觉是一种能力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这种认识能力和方式,世界的本质能够得到认识。[4]也就是说,跟理智一样,运用直觉可以达到对本质的把握。同时,伯格森对于理智主义在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方面提出了怀疑与批判,对理性世界的线性逻辑提出了质疑,呈现出一定的“反理智主义”倾向,因为在他看来,理智主义在对事物产生认识和探究时会划定事实的界限,故理智主义只对认识属性稳定的物质事物起作用,然而对于认识抽象而精神的存在本质则显得有些无力。
这种直觉主义哲学对于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从乔伊斯和伍尔夫的“意识流”写作到后来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后者已经明显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文学的形式到风格等方面,都受到了伯格森哲学的影响。博尔赫斯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早期开创者,其文学作品充满了“幻想”(fantasy),具有较强的哲学性,所以博尔赫斯的一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在实践直觉主义哲学。
二、博尔赫斯实践中的直觉主义
博尔赫斯本人是直觉主义的实践者。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总是借助其丰富的想象和直觉,将大量离奇而荒诞的文学元素杂糅进文学创作。博尔赫斯讲述的故事,几乎都以非现实作为表现的对象,其小说中的故事很少基于现实中的真实故事和真实人物,他关注的是“现代人的感觉和情感体验”[5]。在故事的叙述中,博尔赫斯倾向于“在心理时间基础上追求叙述的感觉化,将叙述导向主观化和非现实化的自由境地”[5]。在小说《马可福音》的创作中,博尔赫斯更是实践了这种直觉主义。
在小说《马可福音》中,博尔赫斯对于直觉主义的实践体现在其对荒诞、离奇故事情节的编织上。博尔赫斯的《马可福音》极具“原小说自觉性”和“原意识”。[6]在小说中,博尔赫斯将一种普世化的、口耳相传的宗教文化传统融入到了小说的叙述体中,小说中的故事以圣经《新约》中的“马可福音”福音书为原型,与“马可福音”中对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存在不言而喻的互文性,故小说的创作极具元意识。小说《马可福音》讲述了一位名为埃斯比诺萨的医学院学生,他来自大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暑假受邀去表哥的农场度假。由于连续大雨导致河水上涨,农场的出口和入口均被洪水阻挡了,埃斯比诺萨不幸被困在了农场,而此时表哥出差在外。同时,农场内的古特雷一家也被困。古特雷一家由“文盲”领班父亲、“极其粗野的”儿子和“不确定其生父”的女儿组成。古特雷一家房屋漏雨严重,埃斯比诺萨伸出援手,将其一家换到农场主房屋后面的屋子居住。起初,埃斯比诺萨为古特雷一家诵读小说,然而这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不经意间,埃斯比诺萨获得一本《圣经》,出于消磨时间的打算,他便给古特雷一家阅读《圣经》里的故事。古特雷一家对《圣经》中的“马可福音”很感兴趣,且对福音书中的故事信以为真,将《圣经》中的故事情节带到现实,在向埃斯比诺萨确认耶稣被钉死的意义——耶稣用自己的牺牲去拯救他人——之后,最终将埃斯比诺萨钉死在十字架。[7]
故事读来离奇而怪异,极为荒诞。《马可福音》中埃斯比诺萨的死亡主题在叙述上充满了感觉化、主观化和随意化,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荒诞。通过文学想象,博尔赫斯直觉地讲述在读者看来极其不可能的故事。所以博尔赫斯对于《马可福音》的叙述实际上是其一种直觉主义的实践。
三、博尔赫斯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
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马可福音》中表达了对理智主义的怀疑和某种程度上的担忧。在小说中博尔赫斯试图说明,直觉主义对于理智主义存在超越的可能,前者甚至会造成后者的颠覆和破灭。具体来讲,博尔赫斯首先建构了“逻辑”与“文盲”的二元对立关系,并暗示着逻辑的理性本身的矛盾性;其次,通过呈现代表“逻辑”的“讲述者”与代表“文盲”的“被讲述者”之间互动的权力关系,博尔赫斯表达了“被讲述者”的直觉化认知对于“讲述者”叙述实践的非理性想象和回应。最后,随着“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关系的破裂,以及“被讲述者”运用直觉主义暴力对“讲述者”的颠覆,博尔赫斯表达了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
(一)“逻辑”与“文盲”的对立
在博尔赫斯的《马可福音》中,用以探索和理解存在和真实的本质的理智主义与直觉主义信仰之间存在一种分离和对抗。具体而言,博尔赫斯首先建构了一组“逻辑”与“文盲”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逻辑”与“理性”的代表埃斯比诺萨与代表“文盲”与“无知”的古特雷一家之间形成对立。首先,埃斯比诺萨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同时“善于演讲”、“有口才”,“他父亲和同时代的绅士们一样,是自由思想者,用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教导他”,[7]深受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
然而,总管古特雷一家则“几乎不开口”,同时“对乡村的事情知道得很多,但是不会解释”,[7]“日期概念模糊”,这些导致了埃斯比诺萨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很困难”。从传统的文化社会权力观点来看,埃斯比诺萨的“逻辑”与“理性”似乎对古特雷一家的“文盲”与“无知”有合法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依照传统的线性思维逻辑,代表“理性”和“逻辑”的埃斯比诺萨能够运用其掌握的文化能力与资本对“文盲”的古特雷一家加以权力控制,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其进行调动与摆布。
但是,博尔赫斯在小说一开始便对这种“理性”与“逻辑”存在质疑,建构了一个“埃斯比诺萨矛盾体”。埃斯比诺萨虽然接受了现代意义上的“逻辑”教育,也深受其父亲“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埃斯比诺萨自身却是个矛盾体。小说开篇对埃斯比诺萨的描述就显示了他的矛盾性,“他虽有口才,却不喜欢辩论,宁愿对话者比自己有理。他喜欢赌博的刺激,但输的时候多,因为赢钱使他不快。他聪颖开通,只是生性懒散;年纪已有三十三岁,还没有找到对他最有吸引力的专业,因此没有毕业。”[7]同时,受其父亲“斯宾塞”学说教导的埃斯比诺萨每天却被母亲要求“念天主教经,在身上画十字”,且“多年来他从未违反过这个诺言”,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使得埃斯比诺萨的矛盾性随着其成长而加强。这些性格和家庭教育经验中的矛盾因素导致了埃斯比诺萨价值观和行为的矛盾性:
他生性随和,有不少见解或习惯却不能令人赞同,比如说,他不关心国家,却担心别地方的人认为我们还是用羽毛装饰的野人;他景仰法国,但蔑视法国人;他瞧不起美国人,但赞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盖起摩天大厦;他认为平原的高乔人骑术比山区的高乔人高明。当他的表哥丹尼尔邀他去白杨庄园过暑假时,他马上同意,并不是因为他喜欢乡村生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扫兴,因为他找不出适当的理由可以拒绝。[7]
所以,博尔赫斯建构了一组“逻辑”与“文盲”之间的对立;同时,博尔赫斯也对这种逻辑的理性充满了质疑,认为其存在固有的矛盾性。
(二)“讲述者”与“被讲述者”的互动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代表“理性”和“逻辑”的埃斯比诺萨能够运用其掌握的文化能力与资本对“文盲”的古特雷一家加以权力控制,在思想和行动上对其进行调动与摆布。小说中,埃斯比诺萨正是借助其文化资本,运用演讲、翻译、修辞等文化手段,给古特雷一家讲述《马可福音》,而古特雷一家则“全神贯注地倾听,默不作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二者之间形成了“讲述者”与“被讲述者”的权力关系。
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且来自大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埃斯比诺萨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代表着科学、技术、逻辑、理性、分析,以及说教者。同时,其出色的演讲能力和“无尽的和蔼”(unlimited kindness)都是作为理智主义精英应该具备的典型特质。相反,古特雷一家的“文盲”(illiteracy)以及他们在表达和交流上体现出的无能都是只能使其处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在现实的生存中扮演被说教者的角色。相反,古特雷一家更加倾向于运用直觉主义来理解和把握周围的事物,逻辑与理性对他们而言既值得敬仰又无法企及。从表面上看,埃斯比诺萨运用其占有的文化资本实现了对缺乏宗教信仰和毫无读写能力的古特雷一家文化上的支配。他运用翻译、演讲与修辞等文化能力进行社会实验,测试古特雷一家是否有理解能力,并发现“重复比变化和创新更加有趣”[8]。
当然,“讲述者”与“被讲述者”之间的关系绝非只是单向的文化控制关系;“被讲述者”对“讲述者”的叙述实践进行了其观念系统范围内的回应,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作为“被讲述者”,古特雷一家对埃斯比诺萨的《马可福音》讲述表演很感兴趣,并在他们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对埃斯比诺萨的讲述内容加以理解与阐释,对“讲述者”埃斯比诺萨的个人加以权威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变化:“他在房间里和走廊转悠时,古特雷一家仿佛迷途的羔羊似的老是跟着他。他朗读《圣经》时,注意到他们把他掉在桌子上的食物碎屑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一天下午,他们在背后谈论他,言语不多,但满怀敬意,被他偶然听到。”[7]此时,“被讲述者”古特雷一家对“讲述者”埃斯比诺萨的叙述行为和叙述中的内容直觉地关联起来,埃斯比诺萨成为古特雷一家精神崇拜的对象。
(三)“直觉”对“理智”的颠覆
埃斯比诺萨对于古特雷一家的文化支配自然导致后者对于前者的想象和意念崇拜。然而,古特雷一家对于埃斯比诺萨的文化崇拜和想象出自于毫无理智基础的直觉,这也使得这种处于直觉的崇拜的深层次埋伏着毁灭性的危机。古特雷一家对于埃斯比诺萨所讲述的《马可福音》进行直觉化的解读,将福音书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与故事中的现实相联系,最终将其非理性的情感冲动和直觉联系转化为毁灭性的力量,将埃斯比诺萨当成故事现实中的耶稣基督,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埃斯比诺萨向古特雷一家诵读“马可福音”的过程实则是其与古特雷一家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过程。两个主体之间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则是埃斯比诺萨用药丸让古特雷女儿的宠物羔羊的伤口止血:“总管的女儿有头羔羊,特别宠爱,还给它扎了一条天蓝色的缎带,一天给带刺铁丝网刮伤。他们想用蜘蛛网给羔羊止血;埃斯比诺萨用几片药就治好了。这件事引起他们的感激使他惊异不止。”[7]这之后,古特雷一家对埃斯比诺萨产生了敬畏,奉其为权威的拯救者。如果说埃斯比诺萨给古特雷一家诵读圣经是他们间关系发生稳定而持续变化的驱动器,那么埃斯比诺萨与耶稣基督外在和行为上的类似则是进一步地加快他们间关系的蜕变的催化剂。同时,古特雷一家的直觉主义生活哲学也导致他们不能够去区分埃斯比诺萨讲述中引用的圣经叙述和个人对神学的观点,[9]最终酿成埃斯比诺萨的悲剧。
这种极具离奇和荒诞的死亡发生仿佛阐明,科学和理性虽然在表面能够对直觉形成文化支配,然而直觉主义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和能力,能够产生反作用,甚至对理智主义加以颠覆和毁灭。所以,博尔赫斯运用两个主体间关系的发生、发展、蜕变来推进故事的情节,并将直觉主义和理智主义这组矛盾的对抗交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最终力图阐明其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
三、结语
博尔赫斯《马可福音》中的故事充满了故事性,也不乏荒诞性。理智主义者埃斯比诺萨凭借其占据的文化资本,运用翻译、表演、修辞等文化手段,向“文盲”且缺乏宗教信仰的古特雷一家诵读《圣经》中的“马可福音”,并试图对其进行文化控制。然而,古特雷一家对于埃斯比诺萨表演内容加以直觉化的解读,将后者所讲述故事中的修辞话语与故事中的现实相结合,在一系列故事现实类比的强化下,最终演化出了其直觉主义的暴力,至此埃斯比诺萨的悲剧成为必然。过渡到故事的暗流中,两个主体间的互动与对抗,实则是理智主义与直觉主义这组力量的较量与拉锯。而埃斯比诺萨讲述“马可福音”的过程则是其与古特雷一家关系发生蜕变之过程。二者间“讲述者”与“被讲述者”关系的最终破裂则暗示了博尔赫斯对于理智主义在把握世界认识方面的质疑与忧虑。
[1]陈平.智者的心灵世界——博尔赫斯文学透视[J].江苏社会科学,1999(3):146.
[2]邓晓芒.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现代哲学,2011(3):46.
[3]文兵.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1):22.
[4]王晋生.略论伯格森的直觉主义[J].东岳论丛,2003(1):93.
[5]王永兵.“故事的闯入者们”——博尔赫斯与马原的影响和接受关系[J].山东社会科学,2012(7):170.
[6]赵毅衡.后现代小说的判别标准[J].外国文学评论,1993(4):15.
[7]Borges,Jorge Luis.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M]//In David Rampton & Gerald Lynch (eds.),Short Fiction: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Second Edi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mpany,2004:437-438.
[8]Levinson,Brett.Technology,aesthetics and populism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J].Discourse,Spring,2005,27(2):4.
[9]Timmons,Nathan.John,Paul,Jorge,and Ringo:Borges,Beatles,and the Metaphor of Celebrity Crucifixion[J].Journal of 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2011(3):392.
(责任编辑:刘晓红)
Borges’sAnxietyandDoubtofIntellectualism:AnInterpretationofBorges’s“TheGospelAccordingtoMark”
LI Yaf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Borges expresses his anxiety and doubt of intellectualism in his short story “TheGospelAccordingtoMark”.In the story,Borges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ism and intuitionalism so as to present the interact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these two forces.In the story,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tellectualism, Espinosa articulates the “TheGospelAccordingtoMark” to the Gutres,who represent intuitionalism,by employing rhetoric and performance.This process,in depth,is a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Meanwhile,the final breaking-dow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y-teller and story-listener actually reveals Borges’s anxiety and doubt of intellectualism’s valid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ism;TheGospelAccordingtoMark;Borges;intuitionalism
2017-02-15
李亚飞(1990-),男,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
I783.074
:A
:1004-342(2017)04-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