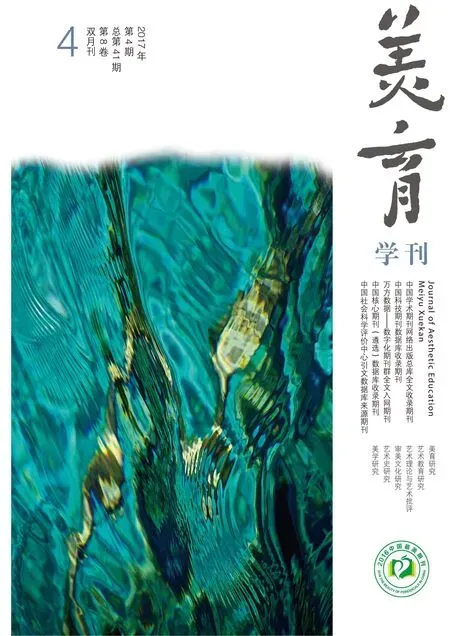文学美育的可能:在人与世界的审美把握中形塑健全人格
2017-03-24叶继奋
叶继奋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文学美育的可能:在人与世界的审美把握中形塑健全人格
叶继奋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当下社会功利化、世俗化以及学校教育的唯知识化倾向,对青年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文学将视界投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多个层面,是对人与世界的审美把握。文学美育为形塑健全人格提供了可能:在尽享自然的博大精深中诗化和强健了人类自身;通过阅读更新视界得以认识、否定和超越自我;补偿与满足人的虚拟性体验并以此形式联结他人;将想象的翅翼自由地伸展于历史与未来及个人、民族与人类的多维时空,并通过具体的生活图景昭示人生的意义,回答人类普遍的存在困惑和价值追询。
文学美育;可能;人与世界;审美把握;形塑;健全人格
所谓“健全人格”,包括健康强壮的体格、自由充实的心灵、 充沛丰盈的感性、清朗明澈的理性、富有教养的意志力以及奉献人类的情怀等要素,也即在生理、心理方面发展良好的并能协调平衡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一种优化人格。 “健全人格”是人类个体全面发展的理想标准。但当下社会的功利化、世俗化以及教育的过度理性化等因素影响了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审美教育为之开辟了通途。“如果说以感性教育界说美育是偏重于美育的根本特性,那么,以人格教育界说美育,则是偏重于美育的根本目标。”[1]文学对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学艺术“将自己的视界投注在人与世界的整个体系,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类)、人与自然四个层面上”,这个体系几乎囊括了人与整个世界的丰富而复杂的层面,能够最广阔而深刻地展示人性。不仅如此,文学艺术通过审美体验的方式能够对人产生深刻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本质特征——“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完成作品,而且更在于完成人的灵魂的铸造,从而改造人的个性心灵,影响他的感觉、情感、理智和想象”[2]。 教育的人文价值在于:通过学习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达到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而最终实现健全人格的形塑。文学特有的美育功能以及作为教材载体的文学作品,为形塑青年学生的健全人格提供了可能。
一、人与自然:“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人与自然具有最为天然密切的关系,人“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也必死于斯”,自然是人的襁褓和归宿。爱默生在《论自然》中,以其诗性睿智的笔调阐述了自然给人类带来了诸如美、语言、纪律(理性)、精神等种种恩惠,将自然尊称为人类的“慈母”“舒适甜蜜的家”,认为大自然之于人类的真正地位在于,“所有正当的教育都力图在此位置上确定人类的存在价值,并且依此树立人类生活的目标,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3]。《课程标准 》提出要在文学阅读中“体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发珍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即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达成个体人格的和谐发展,旨在致力于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均衡发展。
文学书写的“第二自然”给我们带来了有关人与自然的诸多启示。文学使人领略到自然的“不言之言”:在荒原落日中,我们感受到它的仁慈、眷恋以及死亡的壮丽神圣,甚至历史的昨日和未来;文学启示我们生命短暂、自然永恒:“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济慈、雪莱的华彩诗篇中,人们在山林鸟鸣、田野草原、清晨黄昏、秋风冬雪中,聆听来自天堂的启示,感悟生命如随四时转换而生生不息,放声讴歌理想和自由。我国“京派文学”则以淡雅疏朗的笔墨虚拟了一个宁静单纯的理想家园。富有意味的是作者偏要把人物安置于偌大的山水中,而主人公的故事总要等到美景风情铺叙之后才舒缓而适时地推出,自然与人的亲切关系在此得到了生动演绎。文学还生动地再现了人类开发自然的历史情景,并同时启示人与自然如何保持适度关系。当人类从迫于生存之虑开垦拓荒及至无节制的占有和攫取时,在瓦尔登湖享受慵懒阳光和无忧青春的梦幻结束了:“这恶魔似的铁马,那震耳欲聋的机器喧嚣声已经传遍全乡镇了,它已经用肮脏的工业脚步使湖水浑浊了,正是它,把瓦尔登湖岸上的树木和风景吞噬了。”(梭罗《瓦尔登湖》)而狼的“从一个山崖荡到另一个山崖,回响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的“一声深沉的、骄傲的嗥叫”,以及它被大量捕杀之后山林的荒芜、草原的疲惫、沙尘暴的降临等种种灾难,留给人类有关人与自然的无尽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隐忧并非杞人之忧,但足以令他安慰的是,这个来自荒野的隐藏在狼的嗥叫之中的启示已被人类所领悟:人类学会了“像山那样思考”。在利奥波德离世半个世纪后,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当代文学刮起了一阵急遽强劲的“狼风”,标志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学”的兴起,它同时也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深化。总之,文学不仅以神奇的语言将人们见所未见的优美、崇高的山川风光摄入笔端,而且还立体地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相互间的对立与融合、依存与抗衡等多种关系。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领悟到来自天地宇宙间神秘超然的哲学启示,得以从容地再度打量人类自身留下的历史足迹。
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优美自然使我们如沐春风,不知不觉地培养起对于自然的感情,人们从文学作品提供的间接世界中感悟人与自然的真谛。欣赏自然的人坚信:“大自然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审美心胸,对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怀,对于我们健康人格的形成,大自然都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4]欣赏自然的人也必然是一个追求“诗意的存在”的人。 但由于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功利原则以及分工细化,使人在智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导致人格的畸形与残缺。“人文”与“工具”的对立,“感性”与“理性”的失衡,已经成为现代教育必须正视和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对大多数青年学生而言,想象力、闲情逸致是一种奢侈的追求。一些事实表明了他们与自然的隔膜及感性的缺失:他们漠视明丽的春光与飘飞的杨花;他们惊喜于冬日的初雪却因表达的无能而尴尬;他们无法破译大自然千姿百态的表现形式的密码。过度发达的抽象理性和务实功利的价值取向挤压了人的感官和情绪。 “在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西方现代美育理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对现代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揭示和批判,从而使得现代美育理论成为了一种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资源。这种批判是从‘理性压抑感性’这一历史现实出发的,其正题是人的感性生存和个性的完整。”[5]
如果说文学以其生动形象的描述使人感受自然,那么,通过审美“移情”则有助于恢复人的感性。威廉·沃林格“把移情解释为来自在机体和生命中发现的一种合理的快感,它不仅想模仿自然对象,更要‘把原初生命的线条和形式投射……出来,进入理想的独立自在和完美之中(并因此)在每一次创造中为人自身生命感知自由无阻的行为提供一个舞台(竞技场)’”。[6]206-207由于“内摹仿”作用,审美“移情”使人不自觉地根据自己喜好有所选择地摹仿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移入个体生命中以滋养精神提升气质——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此外,“移情”并不只是人的情感“外射”到自然万物,而是人与自然万物“情感投射”的互动游戏,即人在“移情”于万物的同时,也在自然万物的濡染中得到种种恩惠:抚慰、美感、愉悦或者启示等。总之,“优美的山野令人心旷神怡,它使我们的精神从人生的忧愁中解脱出来,赋予我们以勇气和希望。奔流不息的大河,使僵化的思维活跃起来,得以扩展死板的思维范围。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还诱发出对万象之源——生命的神秘感谢,唤起对生命的尊重意识。”[7]此外,审美“移情”的心理机制是“同情”,它能改善人的德性。“移情”已“无法成为今天艺术理论的一个有用的或描述性的词汇”,“但它被精神分析学挪用过来,指‘某一个体感受他人的需要、渴望、挫折、欢乐、悲伤、焦虑、伤害以及真正的饥渴的能力,似乎这些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一样’(阿恩海姆语);因此,‘移情’是一种超级同情”。[6]203-204然而,即便不是因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证明,“移情”本身具有的广泛的同情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移情”消除了主客体之间的存在界限,主体完全投入到客体中去,在对象中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为一体,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移情”就是“宇宙的人情化”,它有助于养成人对世间一切事物博大的仁爱同情之心,从而达到健全人格之目的。通过“移情”,“我们这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同情,还可以扩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把自然草木鸟兽都当成人的眷属和同胞,这样就能发生极高的美感。[8]我们也可以把通过审美“移情”而提高的同情心广施于整个社会和人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之,“移情”不但能恢复人的“感性”,而且还具有伦理价值。它是心灵的艺术体操,有助于柔化被理性压扁了的感性“结节”;它以神奇的力量使人投入到“第二自然”中,从而在尽享自然的博大精深中诗化和强健了人类自身。
二、人与自我:从“自己所是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前提。但认识自我是困难的,尤其对于人生阅历及理论修养不深的青年学生而言。人如何认识自我?在克里希那穆提看来:“‘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我’无法透过抽象的思考来认识自己,‘我’必须在我的具体存在中,认出我之为我,而非理想的我。”[9]因此,观察“我”自己在关系中的表现,会发现自己的真相。克里希那穆提的描述无疑是睿智的。但是,实际生活又会在不同时空和独异的体验场景等方面给人带来限制,从而使人局限于个体自我的单方面了解,而无法对真正的自我获得真知。
文学给人提供了得以突破局限的广袤时空,以它整体的、感性的、可体验的形式,将一切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仿佛置身其中,从而获得了在多维关系中认识自我的可能,因而 黑格尔认为欣赏就是“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自己”。此外,文学所描绘的生活是一种“应然性图景”, 作家的生命意识与人生态度自然地流泄或包孕在场面、细节之中,包含着“应该如此”的价值取向。优秀的文学典型集中体现着人类的至善至美,散发着人性光辉,是人类精华之集萃。文学给读者以清澈的眼光,用来分辨高尚与卑下、崇高与滑稽、善良与丑恶;使读者养成规范而优雅的情感,从而使灵魂超越庸常升华到纯净而美好的境界。因而文学不但是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参照团体”,而且还有判断和选择功能。
文学给读者提供了“陌生世界经验”,从而可以通过阅读更新视界打量自我。 伊瑟尔在解释读者自我提高的内部活动时这样表述:读者在接近文本所显示的陌生世界的经验时是向文本敞开的:当他适应对象(本文)的召唤结构时,他疏远和超越了先前的经验和期待视界,这时“区别就不在主体和对象之间,而在主体和自身之间”,这种吸收陌生的经验而更新主体的视界,仍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的提高”。反过来说,自我意识的提高来自于主体视界的更新,主体视界的更新需要吸收陌生世界的经验,而“吸收”的关键是主体向文本“敞开”。如伽达默尔所言,审美理解的基本模式是“对话”,“理解是在对话中进行的”。让文学作品进入自己的生命中,通过文学典型反观自己,发现自己,并通过扬弃达到“超越”。“否定”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对此,伊瑟尔在《隐含的读者》中这样论述:读者发现文本的意义,以否定来作为他的出发点:“他通过一部分至少是部分不同于他即己所习惯的世界的小说而发现一个新的现实;他在流行的规范中和他自己受约束的行为中发现了内在固有的缺陷。……发现是审美愉快的一种形式,因为他提供给读者两种独特的可能性:第一,使他自己——即使是暂时地——从他自己所是的东西中解放出来,逃离他自己社会生活的束缚;第二,积极地操持他的各种官能——一般是情感的和认知的官能。”文学阅读使人浸润于文本特定的审美氛围并寻找到一个新的世界,在欣欣然向往与渴慕中与旧的自我告别。“告别”,即“否定中的超越”。青年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形阶段,且激情充沛易于感动,文学阅读使他们在审美愉悦中不知不觉地认同了作家倾向,并通过对这个艺术世界学会了对于自身的理解和自我提高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就是认识。通过文学阅读,人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和社会,最终实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三、人与他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一些调查表明,由于激烈的学业竞争,青年学生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相当有限,情感态度也比较淡漠。此外,经济发达带来的物欲追求导致人的价值取向趋于自私功利,而由于人对网络的依赖和网络对人的控制,也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得个体逐渐疏离群体而陷入孤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关爱日渐丧失。文学阅读以审美体验的方式成为联结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
文学能够拓展人的视野,补偿与满足人的虚拟性体验,认识他人和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为人们拓开着一个广阔的“第二世界”,它使人超越时空,追溯荒古又展望未来;它启迪人们领略各色人等,体验生活百味。从人与他人的关系而言,文学能帮助人突破自身对人生体验的有限性,根据人“从人生经验、精神(包括情感)体验两方面产生的延展要求,分别在时间的过去与未来、空间的天地与异域等维度上全面展开,从而构成了文学内涵的巨大丰富性”[10],补偿和满足了人对未曾亲历生活的虚拟性体验。
文学通过情感体验联结他人和世界。“善是通过行为和行动,在关系中体现的。”[11]30仅凭理性认识,人与世界的交往就停留于“我与它”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彼此处于陌生隔膜状态。仅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作品中描述的人和事冷眼相看,那么,文学阅读也不会使我们与之产生密切关系,我们在作品中读到的一切,与路过某地碰巧目击了一起事件几乎没有二致。文学阅读以审美体验和想象的特殊方式,产生一种推己及人的作用,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读者与主人公之间原本彼此分离的关系,它以一种强劲的力量把你拖曳进去,与书中人物一起经受甜蜜与痛苦、欢乐与忧伤,从而体验他人的生存状况。“情感生活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使人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人格,而在自己身上实现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统一。”[12]反复多次的感受和体验可以使人的心灵变得细腻敏感。这种柔弱的力量使人通过想象体察陌生世界,感受他人精神上的痛苦,推己及人,以心比心,沟通自己与他人情感上的联系。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而恰恰是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的。那些河流、山川、森林属于人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存于广袤的土地上。尽管每个人在生理和物种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人类对于喜怒哀乐的感受大致相同。“一个人就是整个人类。他不只是代表人类,他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全部。本质上,他就是人类的整个心智。……你对整个人类负有责任,而不是作为个体对自己负有责任,那是一个心理上的幻觉。作为整个人类物种的代表,你的反应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于是责任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11]17人与世界联系的思维方式,可以使我们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深刻的爱,从而逐渐养成博大深厚的挚爱情怀,形成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3]这在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及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人与社会:“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每天机械地做题和频繁的测试,几乎是高中学生的生存常态,做题的最终目的指向升学,之后是“就业”。生存空间狭窄化,人生目标短期化,价值取向功利化,等等,捆绑了理想的翅膀,让人往世俗的地面下坠。如何脚踏实地地筹划事务又坚定地超拔出来,让心灵指向“无限”与“自由”;如何挣脱自我外壳的束缚,即使身处斗室也能与大千世界息息相通;如何解放学生的心灵,使学习成为自我塑造与审美享受的“自由自觉”行为?“文学与人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文学必然涉及“人与社会”这个深度命题。
人与社会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这两种互相依存关系。人与社会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宗教乃至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都附着和载负于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的人的身上。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这些关系中”[14]。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人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人对存在现状的不满是社会革命发生的直接动力。文学生动地展示了社会的人如何以其睿智、雄心和强劲的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态画卷。文学展现了革命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掀起巨澜轰毁旧社会根基创建新社会的恢宏图景,使人领略到通过社会的人的努力如何推进社会的迅猛发展,从而创造了更适合于人的生存的社会,使人在这个合理的生存状态中得以提升人的社会属性,促进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的人的双重发展。
与历时性动态的时间角度相对应,文学还从共时性的静态的空间角度,在更广阔的界面上展现了自然宇宙、历史文化、道德风俗、战争苦难等宏大景象,把人的视野引向大千世界,思考有关区域经济、人口爆炸、全球一体化等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更深刻层次上观照人性、本原与社会人生,引导人对自然、人类、宇宙萌生出一种大关怀。文学展示了不同肤色的人种、不同文化信仰的民族、不同政治主张的国家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不同区域的全方位生态图景,这使我们得以置身于世界大格局中,审视和思考一系列问题:我们自己得以生存其中的民族、国家所处的地位;我们作为其中一员身负的责任;我们如何把个人发展和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同步发展结合得更好。
与科学阐述和历史记载不同,文学更深地触及人的灵魂,多层面地展示了不同社会地位、阶层、身份的人在社会巨大变革中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细腻地刻画了人的迷惘、痛苦、焦虑、矛盾和挣扎的复杂心理,经历大浪淘沙后把正确答案告诉人们。文学总是以具体的人生故事演绎普泛真理:人生道路的选择以及对人生价值的确认,并不纯粹属于个人私事,人的社会属性已不由自主地把单个的人与社会整体紧密而又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宏观地讲,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筹划、忙碌并决定着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而社会发展的同时又提升了人类精神新的质态,社会的人的发展是与人的社会的发展相同步的。唯其如此,文学感人的力量及其对人的心灵发挥着如此巨大而又持久、深刻的影响。
总之,“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个人的发展、个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受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支配的,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中的一切又都是发展着的个人创造和改变的。社会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和推动个人的发展,个人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适应、配合社会的发展,即在自由全面地发展个人中发展社会,在充分发展社会中发展个人,并尽可能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从而达到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展的目的。”[15]文学以强大的艺术感召力引导人进入历史与未来。每一个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也往往是伟大文学家诞生之时。他们以其高尚的艺术良知和崇高的使命感,采取积极介入的人生姿态,向着时代和社会进言呐喊,他们的政治观点、态度和倾向,以及自身体认到的对民族、国家、社会以至人类的认同感,以审美表达的方式渗透在字里行间,喷射出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人们满怀豪情勇敢地投身时代洪流,在为民族解放和人类和平的伟大事业中书写壮丽的人生诗篇。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是深刻的思想家,能够预测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文学能以其特有的浪漫引发人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使人即便处在艰难困厄的逆境中也始终抱持光荣与梦想。文学自由地将想象的翅翼伸展于过去、现在、未来,伸展于你、我、他也即个人、民族与人类的多维时空,并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图景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回答人类普遍的存在困惑和价值追询,引导人在社会历史的时空中确立自身的人生坐标。文学拓宽了人的精神视阈,提升了人的生存境界,使人立足于大地又坚定地超拔其上,翱翔在“自由”与“无限”的辽阔天空,从而将仅仅满足于生存所需的卑微劳作上升为表现人的尊严的自由自觉的审美创造。
我们处在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一个古老的民族怀着青春的梦想正在大步向前。它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更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中国人投入生命与激情,点燃熊熊的理想之火。因而,通过文学审美形塑健全人格在今天就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别的现实意义。
[1] 杜卫.美育三义[J].文艺研究,2016(11):9-21.
[2] 胡经之.文艺美学[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1-132.
[3] 爱默生.论自然·美国学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3.
[4] 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5.
[5] 杜卫.论中国美育研究的当代问题[M].文艺研究,2004(6):4-11.
[6] 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0-441.
[8] 宗白华.美与人生[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20-121.
[9] 克里希那穆提.重新认识你自己[M].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0:23.
[10] 朱寿桐.文学与人生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6.
[11] 克里希那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灵[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12] 王元骧.拯救人性:审美教育的当代意义[M].文艺研究,2012(3):5-12.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4.
[14] 陆贵山.人论与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5-76.
[15] 刘远碧,税远友.论人与社会的关系[M].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3-16.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ture as Aesthetic Education:Forming a Healthy Personality in the Aesthetic Grasp of Man and the World
YE Ji-fen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t present, social utility, secularization and the knowledge-only tendency in school education have brought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young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Because literature is the aesthetic grasp of man and the world, which focuses on multiple levels of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elf, man and others, man and society, lite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 healthy personality by poeticiz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human self while enjoy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nature; recognizing, denying and overstepping the ego by updating one′ s vision via reading; compensating and satisfying man′s virtual experience to connect with others; stretching the wings of imagination freely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space-time of history and future, individual and nation; revealing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hrough the unfolding of concrete life and responding to man′s pervasive existentialist bewilderment and quest for values.
lite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possibility; man and the world; aesthetic grasp; form; healthy personality
G40-014
A
2095-0012(2017)04-0049-06
(责任编辑:紫 嫣)
2017-04-26
江守义(1972—),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