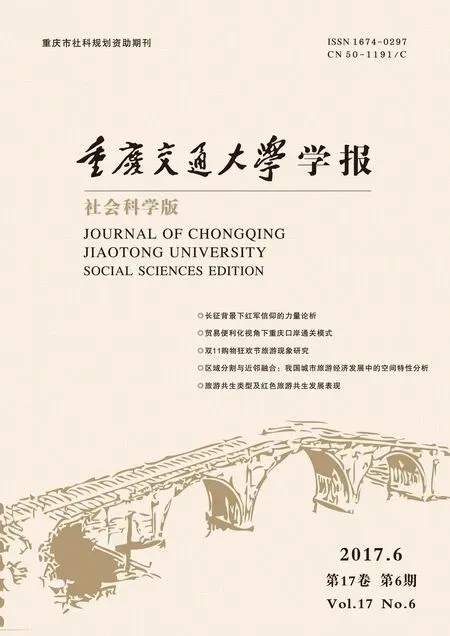晚明工程技术典籍的传播与翻译
——基于《园冶》与《天工开物》的共性考察
2017-03-22陈福宇
陈福宇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晚明工程技术典籍的传播与翻译
——基于《园冶》与《天工开物》的共性考察
陈福宇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作为工程技术典籍的代表,晚明著作《园冶》与《天工开物》在国内的遭遇、对外传播及翻译的时间与空间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等方面高度相似。考察二者对外传播和翻译的过程与主导力量,不仅有利于推广中国古代工程技术成就,而且有利于典籍自身的保护与传承,对当代典籍翻译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工程技术典籍; 翻译; 对外传播; 共性
工程技术典籍是我国工程与技术领域的经典著作,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哲学与技术成就,其对外传播和翻译是汉籍外译的重要内容。尽管此类典籍反映出领先于西方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科技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却没有得到他国的公认,古代科技典籍外译不发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1]70。从《中国翻译通史》《中国科学翻译史》及《汉籍外译史》有关中国科学著作外译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工程技术典籍对外翻译并不多见。成书于明朝末年的工程典籍《园冶》和技术典籍《天工开物》却被系统地翻译成外文,并在国外广为传播和研究,足见其重要性与代表性。此外,二者在国内的遭遇、对外传播及翻译的时间与空间、所产生的国际影响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
一、晚明时期工程技术典籍的命运:成书与禁毁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为晚明四大科学巨著之一。计成著《园冶》集我国古代造园文化与经验之大成,为世界最古老的造园书籍,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巨著。它们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工程技术水平。
《园冶》成书于崇祯四年(1631),《天工开物》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然而,此二者成书后不久即遭受了被禁毁的命运。
据考证,《园冶》是由阮大铖资助刊印,他还为此著写了《冶叙》。阮大铖为明末清初“为士人所不齿”的奸臣[2]49。由此,《园冶》在清代成为禁书,到了近代在国内已罕为人知。故而长期以来对《园冶》的研究都基于流失海外的版本。
清初曾整理《四库全书》,《天工开物》被认为存在反满思想而被排除在外,不再刊行,理由是书中涉及火枪、火炮等兵器的制造,不利于清朝统治。著者宋应星的尊法反儒思想也是《天工开物》被禁毁的重要原因。
二、晚明时期工程技术典籍的对外传播与翻译
(一)概述
《园冶》与《天工开物》的对外传播和翻译,根源在于中国直到明清依然领先世界的科技水平,亦得益于康乾时期中国的强大国力,其外传外译符合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即由强势文化输出至弱势文化。同时,与明朝至清初频繁的中外交流密切相关,如中日文化交流和欧洲传教士在华活动都促成了此类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
《园冶》与《天工开物》的对外传播与翻译在时间、空间和形成的国际影响等方面都高度相似。二者的外传外译始于17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当代,大体上经历了东传、回流、西渐等阶段。空间上,《园冶》与《天工开物》都首先东传至一衣带水的日本,而后到达朝鲜半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回流中国之后,很快就西传至欧洲,最远到达北美和非洲,南至澳大利亚。二者都在海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研究。
(二)东传与回流
1.东传
在国内命运多舛的两部典籍不约而同地首先东传日本,并“墙外开花”。究其原因有三:其一,中日在地理位置上仅一水之隔且同属汉字文化圈;其二,明末至清中期,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而书籍交易占据重要地位;其三,日本历来重视学习中国文化,江户时代尤其重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的引进。
《园冶》在日本畅销,即便在国内成为禁书之后,仍有印刷和出口日本。1701年(康熙四十年)—1735年(雍正十三年),先后有三个不同版本输入日本[3]。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先后出版了桥川时雄的《园冶》、上原敬二的《解说园冶》、佐藤昌的《园冶研究》等日文版本。
日本对《天工开物》的最早文字记载为1694年本草学家见原益轩所列《花谱》和《菜谱》二书的参考书目。1771年,日本出版了《天工开物》汉刻本与翻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4]42。
《天工开物》在18世纪日本哲学界和经济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兴起了开物之学。1952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现代日本语。
18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到朝鲜半岛。1783年,朝鲜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随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开物之学亦在朝鲜半岛兴起,许多重要科技作品都曾引用该书。此著一直未被译成朝鲜语,概因朝鲜亦同属汉语圈,且朝鲜学者多精通汉文。直到1997年,韩国汉城外国语大学崔炷出版了双语译注本《天工开物》。
2.回流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园冶》和《天工开物》才回流中国。彼时,清政府的文字压制与闭关锁国已让二典在国内近乎销声匿迹。而清末以“师夷长技”为目的的留洋活动对此类典籍的回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1年,时为留学生的著名园林学家陈植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发现了《园冶》明刻本,此后回流中国。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刊行《园冶》铅印本,拉开了国内大规模研究《园冶》的帷幕。
20世纪初,地质学家丁文江查《云南通志》始知《天工开物》一书,后偶见此书日文版,并发现英、俄、德等选译本和法文全译本[5]。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丁文江、章鸿钊等科学家的努力,《天工开物》才从日本传回翻刻本。
(三)西渐
现有证据难以确切表明此类典籍向西方传播是源自中国本土还是直接由日本传向欧洲。分开来看,《园冶》向欧美传播在回流中国之后才开始;《天工开物》虽在回流之前(18世纪)就已传入欧洲,但最早入藏巴黎皇家文库的系明刻本,而欧洲最早翻译该书的儒莲此前就翻译过儒学经典《孟子》,其后又系统地翻译了中国多种典籍。这或可说明此类典籍的西渐乃始于中国本土。
1.《园冶》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1936年,中国建筑学家童寯(Chuin Tung)于《天下月刊》发表文章“Chinese Gardens: Especially in Kiangsu and Chekiang”(《苏浙之中国园林》),第一次以英文提及计成和《园冶》,并认为“造园知识的系统化始于计成”[6]227,232。刊物发行于上海,并未引起西方过多注意。
瑞典美术史学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 1949年出版GardensofChina,此著为《园冶》节译,真正引起了欧美对《园冶》和计成的关注。
英国园林设计师玫萁·凯瑟克 (Maggie Keswick) 于1978年出版著作TheChineseGarden:History,ArtandArchitecture介绍中国园林,让英语读者认识了《园冶》及作者计成。英国汉学家夏丽森(Alison Hardie) 1984年开始翻译《园冶》,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法籍华人建筑学家邱治平(Chiu Che Bing)1997年出版《园冶》法译本(Yuanye,letraitédujardin)。
荷兰学者鲁克斯(Klaas Ruitenbeek)1993年出版著作CarpentryandBuildinginLateImperialChina(《中华帝国晚期之木工与建筑》),使西方学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明代建筑技术,为理解《园冶》有关建筑的篇章奠定了基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中国遗产季刊》(ChinaHeritageQuarterly)刊发了不少研究《园冶》和中国园林的文章,而且收录了1935—1941年发表于《天下月刊》上的部分文章,包括前述童寯一文。澳大利亚华人建筑学家冯仕达(Stanislaus Fung)研究了计成的设计思想,深化了对《园冶》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他认为《园冶》是复杂的,对这一丰富、复杂的历史文本的翻译工作,其难度已经超越狭义的翻译本身[7-8]。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有关中国园林的外文出版物渐多,欧美多所大学都将中国园林包括在中国文化课程内,增加了西方对计成《园冶》和中国园林的了解。在纽约,《园林历史学刊》(JournalOfGardenHistory)现名StudiesintheHistoryofGardensandDesignedLandscapes(《风景园林设计历史学刊》),组织发表了不少有关《园冶》和中国园林的论文和英译文。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仅开设中国园林课程,还组织编辑了中国园林翻译集。
2.《天工开物》在欧美的传播
早在18 世纪,巴黎皇家文库即入藏明版《天工开物》。从19世纪30年代起,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先后把《丹青》《五金》《蚕桑》等卷摘译成法文,其后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英文、俄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刊于欧美和非洲[4]43。1869年,儒莲还将有关工业各章合并起来出版法文单行本,但仍不是全译本。
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汉学家蒂洛(Thomas Tilo) 着手翻译《天工开物》前四卷,并于1964年完成此四卷之德译本。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E-Tu Zen Sun)博士与其先生孙守全(Shiou-Chuan Sun)将《天工开物》全译成英文,题为T’ien-KungK’ai-Wu:ChineseTechnologyintheSeventeenthCentury(《天工开物:17世纪的中国技术》),1966年在宾夕法尼亚和伦敦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文全译本,使宋应星的著作在欧美获得了更多读者,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明提供了重要文献。
1980年,《天工开物》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才得以出版,即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的英译本Tien-Kung-Kai-Wu:ExploitationoftheWorkofNature—ChineseAgricultureandTechnologyintheXVIICentury。此译始于1950年,先后由物理学家李熙谋和化学家李乔苹主持,共有冶金专家沈宜甲、地理学家张其昀等15位先生参与。由于种种原因,该译本的正式出版晚于任以都译本,且其影响力远不及任译,但同样在《天工开物》外译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三、工程技术典籍传播与翻译的意义
(一)对典籍传承与保护的作用
考察此类典籍的外传与回流可知,其对外传播对于典籍自身的传承与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历史原因,《园冶》和《天工开物》在国内一度只剩残卷。目前所见到的版本以及所进行的有关研究大多基于海外回流的版本。若非其对外翻译与传播以及后来的回流,恐已失传,或至少无法复原完整的版本。
(二)巨大的国际影响
始于17世纪的工程技术典籍对外传播与翻译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在中国由强入弱又再度崛起的数百年间,为推广中华优秀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园冶》的东传对日本造园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朝鲜半岛的古典园林有深远影响。欧美各国的园林发展也深受《园冶》的影响,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园冶》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甚广,不仅影响了欧美的园林建筑艺术风格,甚至改变了部分大学的课程设置,以《园冶》和中国园林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愈发频繁。
《天工开物》作为科学经典早已在各国广为流传并受到高度评价,书中的许多技术都曾应用于亚欧美非多国的生产实践,如采矿、冶炼、造纸、船舶制造等。儒莲称之为“技术百科全书”,达尔文阅后称之为“权威著作”,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其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4]43,视之为最杰出的科学家。
四、对当代典籍外译的启示
进入21世纪,典籍外译在国内再度兴起,一百多年来以文化输入为主的局面正逐渐改变。工程技术典籍的对外传播与翻译对于当代典籍翻译可以提供几点启示。
其一,典籍翻译及其研究不应局限于哲学和文学经典,而应更广泛地覆盖我国多学科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贴合西方人科技著作认知的典籍”[1]70。其二,在当代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中,国内译者可以有更大贡献。回顾工程技术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不难发现,主导此过程的基本是外籍学者,他们不仅翻译典籍,还对有关的工程技术知识及背景深入研究;而国人的参与和贡献相对有限。一方面,这是由当时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和彼时的历史背景、对外政策、国内外语水平等方面有关。诚然,外籍译者在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9],但在当代典籍外译和传播中,本土译者已责无旁贷。其三,跨学科协作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译者不仅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研究典籍外译,还要“从其他学科汲取养料”[10],并积极探索跨学科协作的机制与模式。观察工程技术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可以发现,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例如,翻译和传播《园冶》的有园林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等,而《天工开物》的外译外传多由汉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科学家共同推动,这对于当代的典籍翻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梅阳春.古代科技典籍英译[J].上海翻译,2014(3):70-74.
[2] 夏丽森.计成与阮大铖的关系及《园冶》的出版[J].中国园林,2013(2):49-52.
[3] 韦雨涓.造园奇书《园冶》的出版及版本源流考[J].中国出版,2014(3):62-64.
[4] 费振阶,曹洸.从《天工开物》外译情况谈科技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1988(2):41-43.
[5] 肖克之.《天工开物》版本说[J].古今农业,2001(2):82-83.
[6] TUNG C.Chinese gardens:especially in kiangsu and chekiang[J].T’ien hsia monthly,1936 (3):220-244.
[7] FUNG S.Word and garden in Chinese essays of the Ming Dynasty:notes on matters of approach[J].Interfaces:image,texte,langage,1997(11):77-90.
[8] FUNG S.Here and there in Yuan Ye[J].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1999(19):36-45.
[9] 佘烨.中国翻译史上外来译者的作用与贡献[J].上海科技翻译,2001(4):57-60.
[10] 谢柯.模因论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英译及传播[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37-140.
TransmissionandTranslationofEngineeringandTechnicalClassicsofLateMingDynastyA Commonness-Based Study ofYuanYeandTianGongKaiWu
CHEN Fuyu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Representing China’s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classics respectively,YuanYeandTianGongKaiWuof late Ming Dynasty are highly similar in their domestic experi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 courses and routes of their overseas transmission and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n inspection of the courses and leading forces of their translation and overseas transmission reveals that, while popularizing th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of ancient China, these activitie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such works,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classics; translation; overseas transmission; commonness
张 璠)
2017-03-23
陈福宇(1978—),男,福建三明人,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H059
A
1674-0297(2017)06-01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