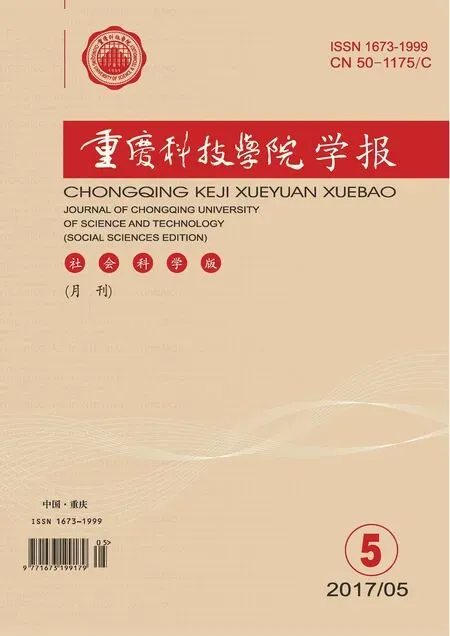历史的隐喻与反思
——再读《索菲的选择》
2017-03-22杨友玉
杨友玉
历史的隐喻与反思
——再读《索菲的选择》
杨友玉
美国新历史主义作家威廉·史泰伦在《索菲的选择》中将被忽视、被边缘化人物的“小历史”编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历史”背景之中,把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虚构、虚构与梦境交融于一体。威廉·史泰伦让他的形象代言人即故事的叙述者斯汀苟结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索菲,“重返”二战中的奥斯维辛纳粹大屠杀现场,探寻生命存在的双重性、历史的隐喻性和邪恶的“绝对性”。通过对“小历史”的关注与反思,威廉·史泰伦最终找到了一个普遍的颇具后现代主义意义的文学主题。
新历史主义;《索菲的选择》;历史的隐喻;历史的反思
人类历史有两种:一种是由各种事件构成的自然发展的历史;另一种是由某些人叙述出来的历史。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被阐释的对象,历史本质上是语言的阐释,这种叙述话语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而许多已经出版的历史书或是统治阶级的文人所写,或是经统治阶级的专设机构审查通过,代表了统治阶级的观点,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者把目光转向那些被统治阶级边缘化的阶级和群体所说的或所写的奇闻、轶事、传说、野史、歌谣等。美国新历史主义作家威廉·史泰伦在《索菲的选择》中书写了3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历史”:一是非犹太人索菲的纳粹集中营经历;二是年轻作家斯汀苟的成长与成熟的蜕变过程;三是大屠杀幸存者索菲的战后美国生活。威廉·史泰伦将这几段“小历史”完美地交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历史”背景之中,把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虚构、虚构与梦境交融于一体。当历史悲剧犹如一个梦魇消失之后,人们步入现实、现代、后现代时代,开始日常生活、爱情和娱乐,开始有意忘却那段曾难以名状的悲壮历史。然而,历史的阵痛所造成的苦难是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这是索菲和斯汀苟的宿命,更是人类的责任。作为一位负责的现代作家,威廉·史泰伦有意“重返”历史现场,审视那巨大的苦难所在,诉说人性被扭曲、被异化的无奈,探寻生命的多重密码、历史的隐喻性质以及历史在阵痛与消长沉浮后的后现代意义。
一、历史的隐喻
威廉·史泰伦惯用一种“部分脱离”式的旁白(即事件亲历者的叙述)过滤相关人物的强烈体验以传达他所肯定的道德观。叙述者参与故事中的灾难性事件,他(她)的人生也因此发生改变,或更糟或更好。例如,在《索菲的选择》中,威廉·史泰伦让叙述者斯汀苟结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索菲而“重返”二战中的奥斯维辛大屠杀现场。这一血腥、惨烈的现场令很多非直接参与者或因害怕而不敢靠近,或因悲痛而不愿触及,或因敬畏而保持缄默。但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威廉·史泰伦却是个例外。
在小说中,威廉·史泰伦首先介绍了这个名叫斯汀苟的年轻人,一位和威廉·史泰伦自己颇为相似的正崭露头角的作家。1947年夏季,在斯汀苟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或许与索菲的奥斯维辛经历一样重大,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重大。当索菲坐着拥挤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要在她的2个孩子中作出可怕的选择时,斯汀苟正为了达到海军陆战队入伍的最低体重要求而暴食香蕉;当索菲在华沙躲避纳粹的时候,斯汀苟正在听格伦·米勒的音乐,喝着啤酒,沉溺于寻欢作乐。威廉·史泰伦比较了这两类事件的差异性以及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的双重存在性:当一类人被命运诅咒时,而另一类人则被命运祝福。像斯汀苟这类人永远不会感到另一个世界里的彻底堕落或嗅到奥斯维辛燃烧尸体的气味。通过对比,索菲的恐怖生存状态得到了突出和强调。让索菲讲诉她自己的二战经历和斯汀苟回忆他自己的幼稚行为,威廉·史泰伦实际上是试图寻找这两类生存之间的关联和生命的多重密码。
通过一种曲折迂回的双重节奏,年轻的斯汀苟在倾听索菲的二战及战后的人生经历中成长、成熟。斯汀苟滑稽而平凡的经历弱化了中心事件的恐怖和严峻,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抵消了人性被疏离、被异化的严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包括索菲和斯汀苟在内的所有的“小历史”都是由成熟的斯汀苟回忆而讲述给读者的。这时的斯汀苟已经读过很多哲学著作和关于纳粹德国的第一手回忆录,他的成长史只是他创作的一种心智背景。毕竟,威廉·史泰伦不能假装轻易地理解纳粹暴行,与悲剧事件保持一种距离感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将恐怖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是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
威廉·史泰伦要解决的另一个历史问题是关于索菲的死亡之谜。奇怪的是,索菲在集中营里不惜任何代价,一直努力活着,而在去奥斯维辛之后,她却几次企图自杀。在奥斯维辛,生命的本能使她把自己和儿子的福祉放在所有事项之上,她以一种虽生犹死的存在嘲笑生命的魔咒。而去奥斯维辛之后,只有有意地逃避那段历史,她才能带着内疚和自我憎恨继续活下去。她爱上内森·兰道是必然的,她与斯汀苟的关系也必然如此:一个是她的救世主和刽子手,另一个则是听她忏悔的“神父”。实际上,索菲不仅对爱人内森·兰道隐瞒了很多实情,对倾听她忏悔的“神父”斯汀苟也保留了很多无法言说的秘密。斯汀苟后来坦言:“那年夏天索菲对我撒了不少谎。也许我应该说她沉迷于某些逃避,以此保持她的镇静。”[1]97索菲频繁地撒谎或逃避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自我麻木、自我疏离,尤其是当野蛮和残暴已不能被其他人所感受或理解时。
在小说中,索菲最难以启齿的经历由索菲自己零零碎碎地给斯汀苟讲述,她有意的遗漏或撒谎使她讲起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她只能慢慢地讲述自己的可怕行径。例如,她(尽管不情愿)曾为仇恨犹太人的父亲工作,为他打印和分发他的狂热的小册子以加速犹太人的灭绝;她还把反犹册子藏在鞋里,假装自己是反犹人士,企图获得纳粹分子的优惠待遇。“帮凶”感是索菲对斯汀苟讲述二战经历的最大困难,她也因此对犹太爱人内森·兰道保持缄默,只字未提。还有她那个最恐怖的选择(在2个孩子之间的选择),一直“逃避”到故事的结束:她的生命结束,也是小说的结束。因此,历史的谎言或秘密,无论多么的异同和隐晦,终究要被揭穿或暴露。作者威廉·史泰伦所要揭示的历史隐喻,在笔者看来是历史阵痛中的人性的异化和双重性,是一种生命的交替体验:欲望与绝望、亲密与分离、愤怒与祥和、幸存与灭亡。
二、历史的反思
威廉·史泰伦对历史的哲学性思考说明了揭示历史隐喻和历史谎言的必要性,这一必要性尤其体现在当人类卑鄙地活着并企图逃避或疏漏某些往事的时候。谎言也是某种讲故事的方式,这种方式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造成实际的伤害。而编故事则犹如编织生命,有助于人们在创伤和悲剧中苟活下来。在《索菲的选择》中,内森·兰道所讲的科学突破的故事让斯汀苟和索菲听得如痴如醉;索菲给内森·兰道所描绘的已故父亲的形象则光鲜亮丽。威廉·史泰伦对这对恋人(内森·兰道和索菲)的兴趣逐渐转变为对揭示历史隐秘的兴趣和对历史隐喻的反思。
首先,斯汀苟是威廉·史泰伦在小说中的形象代表,他将索菲对二战经历的回忆和她在战后的美国生活交织于他自己的成长及成熟的蜕变岁月之中。对斯汀苟来说,索菲不仅“遥远却真正的像玛丽亚·亨特”,而且还是一种“绝望的……精疲力尽的,随着某个前兆性的、悲伤的阴影,迅速地奔向死亡的”[1]46形象。年轻的斯汀苟发誓:“有一天我会写索菲的生活和死亡,以证明绝对的邪恶从未在这个世界上消失。”[1]513为了研究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邪恶的平庸和大规模屠杀的心理,斯汀苟还查阅了很多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的作品,甚至大量引用奥斯维辛司令官霍斯的自传陈述。这些都有助于成熟的斯汀苟在间或的“岔离话题”和冥思苦想中缓缓地靠近奥斯维辛(大屠杀),慢慢地接近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陋现实。当数百万人正在欧洲被宰割被屠杀时,其余的世界则照常运转日常业务。尤其令斯汀苟震惊的是:这个世界仍在忽视人类历史上被屠杀的成千上万的非犹太裔的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以及像索菲一样的波兰人。因此,威廉·史泰伦指出:“大屠杀是一团熊熊烈火,这种火焰仍在继续威胁着整个人类。 ”[2]
其次,内森·兰道作为索菲在新世界里的拷问者,是奥斯维辛的镜像或延伸。在《索菲的选择》中,成熟的斯汀苟在忏悔的自传伪装下对年轻的自己未能完全理解索菲和奥斯维辛这两大奥秘方面经常夸大其词:“我原以为可以通过试图理解索菲来尝试理解奥斯维辛……”[1]219他不理解索菲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索菲的缄默和“难以言表”,部分是由于他那特有的美国人的天真。而且,年轻的斯汀苟未能领会到内森·兰道在索菲的生命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治愈她的救世主和折磨她的恶魔。后来,索菲告诉斯汀苟内森·兰道吸毒成瘾的秘密,斯汀苟才恍然大悟:“我是多么盲目啊!”他痛苦地重新解读内森·兰道的过去行为[1]311。的确,在获悉内森·兰道疯狂的原因之后,我们只得重新理解内森·兰道与索菲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索菲的未来命运所起的作用。是内森·兰道代表纳粹集中营的延伸?还是集中营代表一种集体疯狂?答案神秘而隐晦,但内森·兰道最终成功地引诱索菲自杀,至少他们死在了一起。
第三,索菲作为小说的情感担当,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一个害人者,她的身上承载着我们对她的所有喜欢和不喜欢。没有人会否认索菲是二战纳粹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绝对的邪恶”[3]夺走了她的家、她的家人、她的自由和尊严、她的一切,而更糟糕的是,她在奥斯维辛的第一天就面临在2个年幼的孩子之间作出选择。一个母亲如何在死亡和生存之间选择孩子?一个母亲怎能送她的孩子去灭绝室?残酷的命令让索菲在精神恍惚中选择了儿子简,女儿夏娃哭喊着、尖叫着,立即被处死了。因此,索菲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个施害者,一个杀害自己女儿的刽子手,虽然她自己已经受到了最大的伤害。
此外,索菲还是个骗子、受虐狂和酒鬼,是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帮凶。她十分害怕被毒瘾发作时的内森·兰道称为厄玛·格里泽(一个在奥斯维辛专杀犹太人的金发美女),因为她承认他的指控属实。他越是折磨她,她越是接受他,甚至爱他,渴望对她的种种罪行进行惩罚。我们很容易把索菲在新世界里的恶魔情人想象为超出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绝对的邪恶”。威廉·史泰伦在文中引用了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对“邪恶的真正本质”的描述:“灰暗,单调,乏味”[1]149。 但是,不管它是乏味的还是浮夸的,邪恶似乎就是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无情利用,利用纳粹集中营,利用对人类完全的、毫不掩饰的统治,以阐明邪恶的终极或“绝对”的形式。
三、结语
在当代美国小说中,索菲是极少数具有悲剧气质和自我挫败感的一位女性,与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得》中的苏·布赖德海德等这样的经典女性十分相似。她的被毁、自毁、悲凉、短暂的美丽人生承载着太多的历史阵痛与沉浮,她的悲剧形象不仅有效地强化了作品的文学质地和认识价值,而且充分显示了作家威廉·史泰伦的艺术成熟和审美品质。而通过对小人物的历史关注与反思,威廉·史泰伦最终找到了一个普遍的颇具后现代主义意义的文学主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威廉·史泰伦的关注和研究,这一主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1]STYRON W.Sophie’s choice[M].New York:Random house,1998.
[2]STYRON W.The message of Auschwitz[G]//CASCIATO A D,WEST J L W.Critical essays on William Styron.Boston:G.K.Hall,1982:285.
[3]WEST J L W.Conversation with William Styron[M].Oxford: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85:253.
(编辑:文汝)
I106.4
A
1673-1999(2017)05-0064-02
杨友玉(1974—),女,硕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2017-01-19
2017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历史本真与文学本位的完美契合:从新历史主义视角重识威廉·史泰伦”(2017-ZZJH-32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