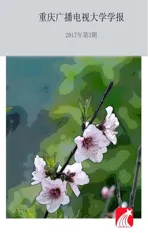毛姆《面纱》的叙述学解读
2017-03-21梁慧琦
梁慧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毛姆《面纱》的叙述学解读
梁慧琦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毛姆的小说《面纱》是一个关于主人公凯蒂在出轨受到良心谴责之后寻找救赎并最终获得心灵平静的故事,而非是表面上看起来的爱情故事。作者通过对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恰当选取,弱化了对于凯蒂的道德谴责,还原了人性的复杂和幽微。通过对《面纱》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毛姆对于“寻找与皈依”主题的偏爱,他试图证明每一个在世上漂泊的旅者都在寻找心灵的栖息地。
毛姆;《面纱》;小说;叙述学
《彩色的面纱》(ThePaintedVeil,又译为《面纱》,以下统称为《面纱》)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凯蒂因为赌气嫁给细菌学家瓦尔特,婚后与风流倜傥的查理发生了婚外情,瓦尔特带着报复和自虐的心理带凯蒂来到了瘟疫横行的梅潭府。凯蒂在环境恶劣的异国他乡踏上了一条寻找与发现的道路,最终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又回到了家乡。
评论家一般因为毛姆过于重视小说的故事性,不重视小说的艺术性,而将毛姆归为二流作家,但毛姆的小说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和追捧,百年来魅力不减。毛姆一生创作众多,以《月亮和六便士》《刀锋》《人性的枷锁》为其长篇小说的主要代表作。《面纱》比起《月亮与六便士》《刀锋》等小说而言,知名度并不算很高,但近年来,《面纱》中的一段描写爱情的话在网络上流行起来:“我明知你愚昧无知、水性杨花,可是我仍然爱你;我明知你孜孜以求的是低级庸俗的东西,可是我仍然爱你;我明知你平庸浅薄,可是我仍然爱你。……我从来没有期待着你爱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你爱我。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只要你允许我爱你,我就千恩万谢了。”[1]人们感动于瓦尔特的深情与卑微,《面纱》也因此提高了知名度。但实际上,《面纱》真的是一部爱情小说吗?通过《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和《人性的枷锁》,我们发现,毛姆小说中的主人公尽管境遇不同,但都在寻找一种挣脱枷锁的方式,寻找通向自由与平静的“道”。那么,在《面纱》这个披着爱情表皮的故事下面,传达的是否也是这样一种思考?笔者尝试从叙述学的角度来拨开小说的“面纱”,探寻它的本来面目。
一、情节如何吸引人
毛姆不仅创作了众多优秀的作品,还有着自己的文学观。毛姆认为,小说创作的目的是愉悦读者,“小说应津津有味地读,如果它不给予乐趣,对读者而言,它就毫无价值”[2]。因此,毛姆的创作不论在主题选择或者情节编排上都会考虑如何才能吸引读者。
小说能否吸引读者,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一是选择的事件和主题是否有“可述性”,二是故事讲得好不好,三是读者的理解方式和认知满足[3]。作家在创作时的“显性”工作则是要布置小说的“可述性”和“叙述性”。语言学家莱博夫认为,“可述性”是事件等待被叙述的潜力,是否“值得说”是事件本身的特征,而是否具有“叙述性”,则是文本进行叙述化的成功程度之别,是叙述化在不同的叙述中实现成功的程度[4]。因此,“可述性”关涉到选择什么样的事件和主题进入小说。有不少论者认为,事件选取的标准和其违反常规的程度有关,“人咬狗”才值得被写进故事。但实际上,小说吸引读者很大程度上靠的不是猎奇,读者“期盼某种体裁,完成社会文化规定的表意程式,这也是一种常规性心理满足”[3]169。
毛姆认为,“一本好小说,它的主题应该具有广泛的和持久不衰的兴趣,即不仅使一群人,不管是批评家、教授、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酒吧侍者感兴趣,而且有更广泛的人性,它对普通男女都具有感染力”[2]32。因此,“作家探讨的应是那些永远吸引着人类的主题:上帝、爱情、仇恨、死亡、金钱、野心、嫉妒、骄傲、善良和邪恶”。“总而言之他们谈论的是我们大家普遍都有的那些激情、本能和欲望。……正因为他们探讨的是那些对一代一代的人都很重要的主题,一代一代的读者也就会在他们的书中找到某种合乎他们意愿的东西”[2]32。
在《面纱》中,没有多余的陈述和铺垫,作者开篇就利落地呈现给读者一个婚外恋的故事。毛姆将凯蒂与查理之间的激情、迷恋,查理的懦弱和道貌岸然以及凯蒂失恋后的痛苦情形描写得入木三分。当我们以为这是一个与出轨有关的爱情故事,并同情可怜的瓦尔特的时候,作者笔锋一转,将故事引到了梅潭府。读者发现,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在梅潭府,凯蒂忍受着失恋和良心谴责的双重折磨,在痛苦中丢失了自我和平静,于是她开始寻找一种东西。为了寻找这种东西,凯蒂去修道院和修女们一起工作,去见沃丁顿的中国女朋友,祈求瓦尔特的原谅。虽然最后她没有成功,瓦尔特染病身亡,她独自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但是,她曾经犯下的过错、做过的蠢事和遭遇到的种种不幸,终于使她依稀看到了那条通往宁静的道路。
毛姆选择了凯蒂这样一个普通的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虚荣、肤浅、漂亮,从个人角度看,她的经历有一些传奇性,可从人类普遍经验和历史角度来看,她的故事就具有长久的启示性和吸引力。
二、情节的否定性推动力量
“情节是叙述中发生的事物情态变化。情节之所以有变化,是因为某种事物的状态被否定了,而这种否定导致了新状态的产生。”“对事物旧有状态的否定,是情节推进的最重要动力,没有否定,情节不会往前走。”[3]198在《面纱》中,沃丁顿对凯蒂说:“有人在鸦片里寻道,有人则求教于上帝,有人在威士忌里寻找,还有人求助于爱情。凡此种种,追寻的都是同样的道,而道则通向虚无。”[5]这段话点明了凯蒂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因此笔者选择“道—非道”这一对可能的关键概念,在无尽的语义场中进行多次否定,尝试找出叙述运动路线*文一茗.不可靠叙述的符号研究[J].符号与传媒,第4期.。
凯蒂童年的生活天真简单,可以假设那时她内心基本是平静的,因此是“得道”的。在《面纱》中,毛姆不仅讲故事,还探寻因果和逻辑的关系,寻找凯蒂最初的悲剧源头。作者将笔触伸向了凯蒂的母亲,凯蒂一直被寄予着“嫁的好”的期望,但恰恰由于母亲的野心,这种期望落空了。凯蒂为了逃避原来的生活,草率地嫁给了瓦尔特。自此,凯蒂开始陷入“非道”的循环当中。希望落空,这是对原有情节的否定,也是故事接下来发展的推动力。由于凯蒂并不爱瓦尔特,所以引得使凯蒂迷恋不能自拔的查理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查理的出现同时否定了凯蒂与瓦尔特的婚姻生活。瓦尔特发现了凯蒂与查理通奸以后,凯蒂本以为终于可以破釜沉舟,跟查理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没想到在凯蒂的质问之下,查理露出了他虚伪懦弱的本来面目。爱情的迷梦告吹后,凯蒂被迫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去了梅潭府。在梅潭府,凯蒂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痛苦使得她无法平静,“非道”的状态达到了一个顶峰。此时,瓦尔特同样是处于“非道”之中的。“就因为他给一个玩偶穿上了华丽的服装,并把她放进神殿加以崇拜,然后又发现玩偶体内填充满了锯末,就既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玩偶。他的心灵受到了伤害。过去他一直是活在假象当中,一旦真相将假象打碎了,他就以为现实本身被打碎了。”[5]159按照情节的发展,读者以为通过凯蒂的不懈努力和寻找,这次救赎能够成功,但是期望被再一次打破了。凯蒂始终没有办法爱上瓦尔特,而瓦尔特却在治理瘟疫的过程中不幸染病身亡。面对瓦尔特的死亡,凯蒂并没有悲痛欲绝,甚至带着解脱的感觉回到了香港。面对查理的诱惑,她再次迷失了,但是她终于否定了那样的自己:“我并不感到自己是人。我感到自己是个畜生,是一头猪,一只兔子或一条狗。……那种兽性像恶魔一样令人可憎、可怕,我痛恨它,鄙视它,还要摒弃它。从那以后,每想到这种兽性,我就感到作呕。”[1]210-211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她回到了家乡,此时母亲已经去世,“非道”最初的源头被打破了。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凯蒂终于知道了自己想要寻找的是什么,并且怎样得到。她要她的孩子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她请求跟父亲一起去巴哈马群岛,她看见了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至此,凯蒂在绕了一大个圈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得道”的道路上来。但是,我们意识到,毛姆给的结局其实是开放性的,我们并不知道凯蒂是否真的跟父亲到了巴哈马群岛,到了之后的情况又会是怎么样的,凯蒂孩子的情况会如何。倘若作者愿意,整个叙述运动还可以回向源头概念,进行又一轮的否定。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选取“道—非道”这一对概念,可以使小说沿着否定性情节的推动不断前进。
三、读者的接受与认同
一次叙述产生于文本的创造过程中,二次叙述发生于文本的接受过程中。赵毅衡教授在《广义叙述学》中按照二次叙述“还原”文本意义的复杂程度将其分为:对应式二次叙述、还原式二次叙述、妥协式二次叙述、创造式二次叙述。《面纱》以凯蒂为主人公,但实际上,凯蒂并不是一个具有道德优势的人物。瓦尔特待她一心一意,她却婚后出轨伪君子查理,导致瓦尔特心碎而死。按理来说,凯蒂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面纱》不仅以凯蒂为主人公,而且并没有反讽的意味,读者反而到后来也有些同情甚至理解凯蒂,这与二次叙述不无关系。当文本叙述的“因果—逻辑链”混乱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使用创造式二次叙述。“某些叙述明显违反道德和文明准则,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之,此时就必须找出文本的‘代偿价值’。”“二次叙述必须创造新的道德理由来接受之。”[3]113凯蒂虽然犯了错,但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能够理解凯蒂犯错的原因。这一方面与文本的叙述方式有关,另一方面,凯蒂虽犯了错,但内心挣扎痛苦并且经受了磨炼,算是付出了寻“道”的代价,结合小说的主题,读者也就可以理解了。
虽然毛姆一般被认为是一位不太注重“技巧”的作家,但他在小说叙述者和叙述角度上仍有自己独特的选择。美国小说理论家路伯克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6]可见,叙述角度在小说写作中是非常重要的。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将叙述视角分为全知视角和选择性全知视角[7],《面纱》中的视角属于选择性全知视角,虽然是全知视角,但仍限制观察范围,仅揭示凯蒂的心理活动情况。
“她对瓦尔特要笑脸相迎,友好相待,但态度要坚定。他们两个用不着吵架。即使分道扬镳以后,她也乐意见到他。她衷心希望,他们在一起度过的这两年将成为最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他的脑海里。”[1]40
“当然,她绝对相信查理。查理对她的爱情跟她对他的一样深厚。她觉得,查理绝不会不欢迎这样的天赐良机。她决不能那样去想,哪怕自己头脑里有一闪念的怀疑,那也是对爱情的不忠。”[1]62
以上两段是凯蒂在准备跟瓦尔特摊牌时的心理活动,毛姆以这样的视角将凯蒂的心理活动展示出来,反而让读者看到,凯蒂虽然有些天真,但不至于邪恶,于是对凯蒂就有了几分同情。
“凯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远处小山顶上有一座牌坊。……看到这座牌坊后,她不知为何感到心神不安,觉得它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含义:她弄不清楚究竟是一种威胁呢,还是一种嘲弄?”[1]81-82
“一座高大、威严的城堡这时突然从天空的白云中钻了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不仅能够看到它,而且,它像是一拍魔棒就突然出现了的一座建筑物。……凯蒂微张着嘴,屏住呼吸望着远处的美景,激动得一只手捂住胸口,另一只手捂住嘴,两行热泪滚下面颊。她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一身轻松;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变成了躯壳躺在自己脚旁,留下的只是灵魂。”[1]88
这两段文字以凯蒂的视角观察了梅潭府这座神秘、美丽、又恐怖的异域之地。凯蒂的视角敏感、忧愁又充满预兆和魔力,她的感情都是真实的,她甚至是可怜的,通过她的视角来看书中的世界,读者自然会对主人公产生理解和同情。
“瓦尔特那样悲惨地死去,她感到难过,但这种难过纯然是常人的感伤,正像一位熟人去世时她也可能感到的那样。她承认瓦尔特有许多令人倾慕的品质,但是她却不爱他。”[1]190
“她看出了父亲想要掩饰的是什么。那是他所感到的精神上的解脱,一种极大的解脱。他怕流露出自己的这种情绪。……如今如果由于一个眼神或一个不慎的举动稍微流露出一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在居丧期间不应有的感情,对他来说可是件极糟糕的事情。”[1]217
失去亲人,本来应该悲痛欲绝,但作者却让凯蒂极其冷静、诚实地承认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以及她所看到的事实。她如此坦白,反倒让读者没法指责她了,因为读者也明白,人心不总是高尚的。毛姆的小说一向以抒写人性著称,他写出了人性的幽深、复杂和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四、神话模式与毛姆小说的主题
乔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总结了众多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提出一种“单元神话”模式。“从其日常所居的茅棚或城堡出发的神话英雄,被引诱到、挟持到,或是自愿地走到冒险活动的入口,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守卫着一条通道。这位英雄可以击败这个势力,或者设法赢得其欢心,从而活着走出这个黑暗王国……他也可能被对手杀死,降入冥世。越过这一出口后,这位英雄开始了在一个充满了陌生的而又奇怪的熟悉的势力的世界中的旅程,其中某些势力严重地威胁他,某些则提供神奇的帮助。在他抵达这一圆形神界的中心低点后,他经历一次最大的磨难,并得到了报偿。……”[8]将这种类型的故事描述为一个从“出发”到“返回”的圆圈,表现为“召唤—启程—历险—归返”的基本框架。
在毛姆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模式。《月亮与六便士》中,中年的思特里克兰德受到内心的召唤,抛下家庭和舒适的生活,迷恋于绘画创作,东奔西走、披荆斩棘、刻苦磨炼,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生活和创作的乐土,创作出了杰出的艺术作品,留给世人无尽的精神财富。在《刀锋》中,拉里由于目睹好友的死亡而内心受到触动,抛下了现有的正常生活,到世界各地学习、思索以及探险。终于在印度的神秘宗教中找到了平衡心灵的办法,并用自身的精神力量去影响身边的人。在《人性的枷锁》中,菲利普经历了学业、事业、爱情的种种磨难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使内心平静的道路。在《面纱》中,主人公虽不是受到神秘力量召唤的苦行僧或殉道者,但凯蒂经历了爱情和婚姻的失败,受到了痛苦的折磨,打破了内心的平静。她一直在寻找的,同样是一条能使内心平静的道路。以上几部小说的主题确有相同之处。
毛姆对于这种“找寻”主题的钟爱,或许也与他终身漂泊和动荡的经历有关。在工业和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人由于生存和发展的原因不得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漂泊着。旧的价值观被毁灭,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也是精神上不断在漂泊和寻找的流浪者。毛姆的小说在当下具有了它的启示性意义,这也是这位标榜传统叙述手法的小说家所具有的现代性。
[1]毛姆.彩色的面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59-60.
[2]毛姆.巨匠与杰作[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
[3]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69.
[4]William L.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2:4.
[5]毛姆.彩色的面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95.
[6]路伯克.现代小说写作技巧[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96.
[7]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45-246.
(责任编辑 周 骥)
10.3969/j.issn.1008-6382.2017.03.003
2017-05-07
梁慧琦(1993—),女,云南曲靖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文学符号学与叙述学研究。
H0
A
1008-6382(2017)03-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