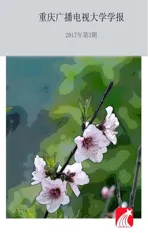论格非《望春风》的符号叙述与主旨内涵
2017-03-21王娟
王 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论格非《望春风》的符号叙述与主旨内涵
王 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望春风》在叙述上既采用先锋小说的叙述手法,又融入了传统小说的叙述风格,呈现出先锋与传统相融合的叙述风格。在人物塑造上,格非延续了他一直以来坚持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但是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赋予到普通农民的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物的断裂之感。在小说的主旨内涵上,《望春风》是格非对乌托邦叙述的进一步探索与回答。
格非;《望春风》;符号叙述;主旨内涵
从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到近作《望春风》,在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格非既有其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内核,也有不断追寻的创新之处。小说《望春风》以“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讲述了“我”重返故乡之后,对故乡的人与事的回忆与记叙。这部小说不仅在叙述方式上一改往日先锋叙述的晦涩,而且在先锋手法之中融入传统小说的叙述风格,使得小说在叙述上更为流畅自然。格非自创作之初,便始终专注于知识分子写作,其作品之中带有浓厚的精英意识。在《望春风》这样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人物的断裂之感。而在主旨内涵上,《望春风》这部小说也是对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就一直在探索的乌托邦叙事的进一步追寻。
一、先锋手法与传统风格的融合
《望春风》在叙述上既有其一如既往的先锋叙述手法,也融合了传统小说的风格,深刻地体现出先锋手法与传统风格相融合的叙述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先锋手法
格非以先锋小说步入文坛,同时也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其早期的作品在形式上都极具先锋性,比如《迷舟》《褐色鸟群》《锦瑟》等。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先锋小说的落潮,许多先锋作家也开始逐渐转型。格非的早期作品如《迷舟》等,其对空符号的运用让人着迷,而《褐色鸟群》《锦瑟》等采用了重复叙事的手法,也体现着 “深刻的重复”。因此,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等作品,很多人认为格非的小说也进入了转型期。但是,在笔者看来,格非的小说一直伴随着先锋的影子,“所谓‘转型’只是力求与现实、大众和解的造作表象”[1]。格非早期的先锋小说常用的叙述手法,在《望春风》中依然有着诸多体现。
(1)元叙述因素
“元”(meta-)这个前缀是希腊文“在后”的意思。由于哲学被认为是对自然科学深层规律的思考,因此meta-这个前缀具有了新的含义,指对规律的探研。根据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的总结,关于X的X,被称为“元X”[2]。所以,所谓元叙述,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叙述的叙述,而在小说中的元叙述,主要是指那种暴露出小说叙述方式的叙述行为,这在先锋小说中是极为常见的一种叙述方式。虽然很多人认为格非的小说已经成功转型,但是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在他的小说中依然有所保留。在小说《望春风》中,格非也运用了这种元叙述的方式。
在《望春风》的最后一部分,“我”重新回到故乡,面对随时将会消失的村庄,“我”决定将村庄里的人与事都写下来。当我写完初稿进行抄录的时候,每天傍晚都会将当天抄录的部分一字不落地读给春琴听,而作为听者的春琴,不仅“对我的故事疑虑重重,甚至横加指责”,“竟然多次强令我做出修改,似乎她本人才是这些故事的真正作者”[3]。在春琴的干涉与威胁下,“我”不得不对文章中许多地方进行了删改,比如对于更生这个人物,因为春琴的干涉,“前后删改七八处,删掉的内容,大约在七千字上下”。“这样一来,更生从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被降格为一个次要人物。”[3]384而小说对于更生这个人物的描写,不仅着墨甚少,而且很多地方也的确写得模糊不清,这种作者在文中直接说明自己如何创作,叙述自己如何叙述的叙述方式就是元叙述手法。
(2)空符号
空符号是格非小说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根据赵毅衡先生对符号的定义,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4],而作为符号载体的感知,它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当符号载体是非物质性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空符号,比如画上的留白,音乐中的停顿等。用皮尔斯的观点来说,符号、对象和意义形成了稳固的三角关系,对象决定符号,而符号又决定意义[5]。在格非的小说中,他常常喜欢在创作中造成符号的缺失,一旦符号缺失了,也就没有办法指出一个明确的对象,更没有办法生成一个确切的意义,而读者在阅读中,也就常常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
在《望春风》中,关于父亲的死因一直为作者模糊其词,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父亲究竟是为何而死,真的是因为远在南京的母亲的一封检举信吗?那么,那个报信的女人是谁?父亲在死前离开了整整五天又是去了哪里?而最后他又为何选择在便通庵悬梁自尽呢?一系列的谜底等待被揭开,然而正是因为作者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空符号,所以读者难以找到明确的对象,更难以找出一个明确的意义,于是读者探寻真相的愿望落空。可是与此同时,读者却又能在这种落空之中生出无限的解释,使得原本缺失的意义又生成出无限的意义,从而丰富了整个小说的内涵。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空符号并非是一种全然的“无”,它是“介于‘0’到‘1’之间的部分之无”*杨锦芬.论空符号的在场形式[J].符号与传媒,2013年秋季号(总第7辑):32-42.,因为它并不能单独地以“无”的形式存在,它是在有之间的“无”。因为有作者对于父亲的种种描写,有明确的符号来指明对象,让我们在意义的解读中产生了对父亲这个人物形象的理解,所以其后的空符号也才能够得以形成,否则全部的“无”也就完全没有办法表达意义了。因为有了前面明确的符号,所以后面的空符号才会产生出作者预期的意义。
2.传统风格
(1)古典诗化的语言
《望春风》所描写的场景虽然是农村,但是格非笔下的农村与同时代的贾平凹、阎连科等笔下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格非笔下的农村更接近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笔下的农村,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是一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因此,作者在对这样的环境进行描写的时候,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充满古典诗化意味的语言,这在文中也是处处可见的。
比如,有一次“我”在王曼卿家的天井边睡着了之后,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阒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3]74短短几句话所描绘出来的山中小院,恍然间让人觉得其就是陶渊明笔下那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比如,“我”到赵锡光的家里,看到“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3]27-28这完全是一幅安闲静谧的农家院景。再比如,有一次“我”独自走在雨中,看到“肥硕的杏子和梅子在雨中悄然发了黄,看到斜雨在河塘里腾起一片蒙蒙轻烟,看到远处田野里雪白的麦花向天边伸展”[3]126,这分明就是贺铸笔下“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情景。作者用这种古典诗化的语言来描写记忆中的故乡,营造出一幅世外桃源一般的乡村图景,这也正是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追求的——沿着记忆的河流逆流而上,最终走入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地方。
(2)指点干预
中国传统小说中常常会有许多的指点干预。所谓指点干预,指的是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对叙述形式进行议论,而中国传统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指点干预,是因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常规叙述方式是制造一个假性的口头叙述场面,仿佛是叙述文本在书场中把说书人的叙述照实记录下来写成的”。“为了制造这种效果,叙述者(他自称为‘说书人’)一有机会就想显示他对叙述进行的口头控制方式,其目的则是诱使读者进入书场听众这叙述接收者地位,以便更容易‘感染’读者。”[6]发展到后来,在逐渐形成了一种程式之后,则变成了一种风格特征了。《望春风》在叙事上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也体现在小说中多处存在指点干预。
在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常常跳出所叙述的内容,直接与读者对话。比如,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3]74-75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指点干预,叙述者“我”在叙述的过程中,突然跳出来对叙述的形式进行议论指点,而在紧接着的文本中,则自然而然的是对“我”的妈妈的一段叙述。再比如,作者在对赵锡光进行介绍的时候提到,村里人当面会客气地尊称他一声“赵先生”,但是背后大都称他为“刀笔”这样一个颇有贬损之意的名字。紧接着,作者写到“若不嫌我饶舌啰唆,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3]24,接下来便叙述了赵锡光在写合同的时候如何坑了唐文宽的事情。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跳出了叙述者的位置,直接与读者对话并告诉读者下面这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村里人为什么会称赵锡光为“刀笔”。这样的指点干预在文中还有许多,不过《望春风》中的指点干预有其自己的特点,其目的更多的是试图追求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而不是真的要去指点读者,或者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3)预叙悬疑
所谓预叙悬疑,是指提前预叙一部分情况,而让后文在事件的正常位置上说出全部的情况,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一种叙述方法[6]204-205。在传统白话小说中,预叙是时序变形最主要的方式,“实际上所有的长短篇小说,楔子中都点出了故事的结局,故事尚未开始已知结果”[7]。在小说《望春风》中,作者也常常运用这种预叙悬疑。
“我”在小的时候非常讨厌梅芳,甚至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厌恶,而父亲在教育了我一番之后,无不同情地告诉“我”说这个人的命不好,紧接着便出现了一段预叙:“很多年以后,到了梅芳人生的后半段,当霉运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到她头上,让她变成一个人见人怜的干瘪老太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过的这句话。”[3]10对于梅芳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作者在这里先提前预叙了一部分,用以印证父亲对于梅芳命运的推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说明父亲作为算命先生对于命运推算的准确。而梅芳人生的后半段所要遭受的霉运,则会在后文事件发生的正常位置上加以说明。再比如,在赵孟舒死的时候,关于他的古琴的下落也有一段这样的预叙:“一直要等到十五年之后,‘枕流’和‘停云’才会重新出世——高定国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从他们家床底下偶然发现了这两件稀世珍宝。”[3]109对于高定国去抄红头聋子家的原因和过程,则要等叙述到十五年后的事情时才会说出全部的情况。
这样的预叙在小说中并不算少见,而作者用这样的预叙,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通过预叙一些情节来吸引读者阅读的兴趣,同时也是为了行文方便。比如,关于赵孟舒的古琴的下落的预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赵孟舒一生的总结。赵孟舒是整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而他一生挚爱古琴,所以古琴其实也是他的一种象征,他最为珍贵的“碧绮台”在他的葬礼上被王曼卿付之一炬。而后来我们会知道,另外两张琴虽然被藏了十五年之久,却仍然免不了被烧掉的命运。其实,这样的预叙也是为了追求传统小说的这种叙述风格。
二、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格非本人是文学专业出身,毕业后就一直留校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其自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作家,其作品也散发出浓厚的知识分子写作气息。他的作品“对历史境遇的求证,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对人性的探寻,对人的存在意义的不断追问,都让我们体味到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之感”[8]。比如,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是对乡村知识分子启蒙神话的一次颠覆,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如《初恋》《紫竹院的约会》《凉州词》等,关注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可以说,格非一直在重复着知识分子的题材,虽然对于这样的重复,格非认为“随着创作的持续,作家一旦找到了某种相应的形式,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这种形式加以规定,有些作家一生都想超越自己(比如列夫·托尔斯泰),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超越仅仅意味着一种‘深刻的重复’”[9]。但是,如果说这种知识分子抒写是格非小说的一个创作内核的话,那么,以此来观照《望春风》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可以说这应该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重复。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农村生活,主要的人物也几乎都是农民,但是当作者将这种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赋予到一个普通农民身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人物形象所产生的断裂感以及其不可靠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对主要人物德正的塑造上。
德正是一个孤儿,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而他的酒鬼父亲在德正五岁的时候也病死了。因为舅舅、舅娘不肯收留他,所以德正只好被安排在祠堂里,靠着村里人的施舍过活,成年后的德正成了一个轿夫,也为村里的人做一些力气活儿。按理说,像德正这样一个不识字更没有上过学的轿夫,是不可能走上仕途的,然而,革命掀翻了传统的定义,将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轿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上。在1950年的土改中,德正被推选为农会主任,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从此,这个目不识丁的轿夫也如这变幻莫测的时代一般,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心怀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德正在成为农会主任之后,不仅一改往日的形象,而且也开始了他人生的三件大事。德正曾经对“我”的父亲说过,他的一生有三件大事要干。在他儿子的满月宴上,小木匠赵宝明重新提起这件事,他以为德正的三件大事,是像一个普通农民一样的心愿:建房子,娶妻,生子。谁知听到此话的德正却正色道,他要办的三件大事一件都还没有办完。由此可以看出,德正的心里还有更远大的理想。
在“我”即将离开儒里赵村,去探望早已离开政治舞台且身患绝症的德正时,才彻底弄清楚他所说的三件大事到底是什么。第一件事是要在儒里赵村修建一所小学,而在德正的不断努力下,儒里小学也在1971年的秋天正式落成了。第二件事便是要推平磨笄山。德正用自己的足迹将磨笄山丈量了无数遍,画了百十张图纸,精准地计算如何将磨笄山推平,用余土填平沟壑,以此来为村里增加可耕种的土地,解决春夏之交的饥荒问题。而这第三件事,便是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死。可以看出,德正的这三件大事不是追求个人享乐,而是启蒙式和奉献式的,这完全不像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贫困轿夫所想要追求的目标,而他在办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魄力,也完全不像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所具有的。德正在离任后,燕还旧窠,重新回到祠堂当一名仓库保管员,过着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涯,正如德正自己说的,“好比做了一个梦”[3]170,而这也确乎像是一个梦,在这个梦里,德正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可是,在笔者看来,小说对于德正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可能并不是成功的。将这种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安排在德正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轿夫身上,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了一种明显的断裂。在成为农会主任之前的德正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轿夫,成为农会主任之后的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心怀天下、有勇有谋之人,而在失去了职位之后,又瞬间回到了一个农民的位置之上,这样的断裂也难怪让人产生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而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不妥,所以在德正完成了第二件大事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之后,一种怪病缠上了德正。他总是梦见同样的事情,而且一闭上眼睛,就会感觉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躲在他背后朝他冷笑,可是这个离奇的怪病在德正被人设计陷害失去职位之后,却又奇迹般的好了。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德正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以这个人物的身份与形象,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作者以这样一个颇有迷信意味的方式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
三、乌托邦叙事的破产
《望春风》表面上看是作者对故乡的追溯与回忆,是对正在消失的村庄的一种缅怀,但其实是作者对一直以来都在探索的乌托邦叙事的一种延续。所谓乌托邦叙事,在中外文学史上都由来已久,这主要来自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永不停息的乌托邦冲动。在格非的一些作品中,特别是他回归之后的作品中,比如《人面桃花》等,可以看出格非对所谓的乌托邦叙事所进行的探索。而此后的《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乌托邦意识的进一步探索。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人面桃花》写出了古典江湖乌托邦的破产。
《望春风》这部小说,看似在写“我”对故乡的回忆以及成年之后的返乡之路,但当“我”顺着记忆的河流逆流而上的时候,“我”回到的其实已经不再是现实中的那个故乡,那个故乡早就在轰轰烈烈的拆迁热潮中消失殆尽,“我”回到的是我记忆中的故乡,或者毋宁说是我幻想中的故乡——一个乌托邦式的所在。作者正是怀着对正在消失的村庄的一次深切的缅怀,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重新回到故乡的土地之上,在这个只剩下骨架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境。小说中,“我”在同彬和莉莉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回到了故乡,和春琴住进了曾经的通便庵。这座幸存于拆迁大潮的庵庙在同彬和莉莉的努力下焕然一新,而“我”和春琴在这个没有电视、报纸、自来水、煤气和电冰箱的地方,回到了我们的童年时代,回到了最初的出发地。可是,这个看似美好纯净的乌托邦,却时时显现出一种即将破产的摇摇欲坠的态势。“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3]387由此可见,这种美好如乌托邦一般的生活,不过是时代缝隙下的一个短暂的停顿,它终将会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而去。虽然“我”在不断地安慰春琴,也安慰自己道:“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3]393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的“那个时候”可能是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时候。
总的来说,《望春风》这部小说既有其成功之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格非在对先锋叙述手法的探索上,融合了传统小说中常用的一些叙述手法,以一种更加娴熟的叙事策略来叙述文本。在主旨思想上,延续了他对乌托邦叙事的探索,并叙述了这种乌托邦终将破产的结局。在人物刻画上,也延续了格非一直以来坚持的创作内核——对知识分子的抒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物造成了一定的断裂之感。
[1]李丹梦.文学的现实态度——聚焦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J].文艺研究,2015(4):5-16.
[2]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292.
[3]格非.望春风[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6:381-382.
[4]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
[5]柯尼利斯·瓦尔.皮尔斯[M].郝长墀,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101.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33.
[7]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39.
[8]孙萍萍.桃源梦尽——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J].当代文坛,2012(6):165-168.
[9]格非.故事的内核和走向[J].上海文学,1994(3):70-76.
(责任编辑 安 然)
10.3969/j.issn.1008-6382.2017.03.002
2017-05-07
王娟(1992—),女,四川德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H0
A
1008-6382(2017)03-0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