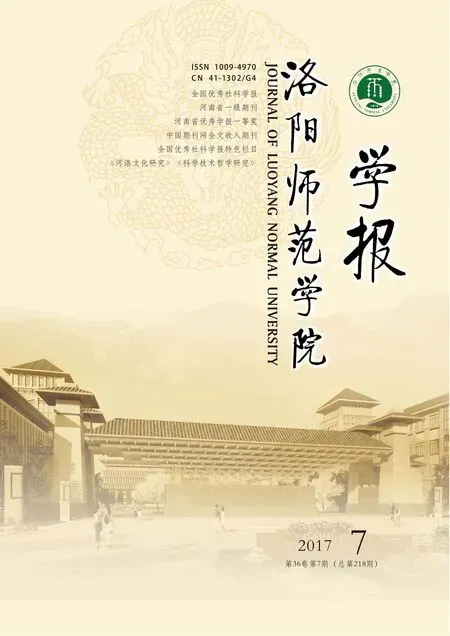流行音乐“中国风”解析
2017-03-12辛颖
辛 颖
(洛阳理工学院 教育科学与音乐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流行音乐“中国风”解析
辛 颖
(洛阳理工学院 教育科学与音乐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新世纪以来, 中国大陆流行乐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风”热潮。 这种流行音乐风格将西方流行音乐中最具潮流代表性的音乐体裁融入中国古典文化的不同侧面, 形成极具中国传统特色并饱含时代音乐气息的全新艺术形态。 跨越历史和音乐种类, 从多重视角主体形象、 音乐技巧和目的性思考, 中国风音乐并不等同于我国流行音乐发展中的“民族化”音乐。 它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 五四时期艺术歌曲、 80年代港台流行乐曲有相同处, 它们的主导力量、中西文化的融合继承都具有相似性。 中国风音乐应当克服审美和创作缺陷, 将其提升为与蓝调、 摇滚并存的体裁样式, 并稳定发展成为一种专属于中国的流行音乐新体裁。 关键词: 流行音乐; “中国风” ; “民族化” ; 中西结合 ; 古今融合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从无到有, 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漫漫长路, 由最初的懵懂与非主流, 逐渐成长为在商业化包装和营销机制下的繁荣与鼎沸。 经历了模仿与学习的艰辛过程之后, 中国大陆的原创流行音乐也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即便近有港台乐坛比邻, 远有日韩欧美风潮侵袭, 但中国大陆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始终不减, 并努力勾勒着一种带有东方标志和民族气质的独立音乐形态。 在“民族化”的感召下, 曾经灵光乍现的“西北风”“亚运风”“红太阳热潮”都在创作中竭尽所能地主动加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但偏偏事与愿违, 这些求索的成功还未来得及开花结果, 便被湮没在浩瀚的歌坛新思潮中。 直到新世纪伊始, “中国风”的称谓悄然降临在华语歌坛, 新的东方音乐审美观再度与西化的流行音乐产生碰撞, 而这一次绝非昙花一现。
不久前落幕的《中国好声音》第四季节目中,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选秀歌手张旸凭借改编的《菊花台》得到评委的青睐。 对本属于“中国风”的原作进行二度创作, 使其具有了浓郁的河东大鼓韵味, 京腔京韵的调门儿, 配上儒雅考究的歌词, 在电声乐队现代感十足的配器中演绎。 霎时间, 中西、 古今、 土洋、 雅俗, 多种多样的矛盾体交织一团, 纷繁却不杂乱。 而也就在这一瞬间, 不禁使人对“中国风”的称谓与内涵有了新的思考, 甚至对原有的理念共识产生了疑惑。
一、 流行音乐“民族化”不等同于“中国风”
“民族化”的概念和理想是每一位音乐人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也是创作中情不自禁的有感而发。 流行音乐在20世纪70年代末初传到大陆时, 并非从欧美直接袭来, 而是通过港台乐坛的消化与转换, 将其过渡为国人易于感知和接受的曲调与辞藻, 这一过渡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觉的“民族化”转换尝试。 在熟悉了流行音乐曲式风格之后, 本土音乐人在创作中开始加入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内容, 传统文化情怀在流行音乐的创编和演绎中逐渐渗透, 并在一些时期集中迸发。
“民族化”的基本理念在于将外来文化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转化, 从而将“他”文化转变成为自主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一理念中, “操控者”主体是我们自己, 而进行转化的客体目标是外来文化, 转化的结果是据为己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 在租界中唱响的《夜上海》与《何日君再来》被称为流行音乐“民族化”的第一次尝试。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状态下, “民族化”虽是主动创作的结果, 但技法的生涩与审美上的献媚造作, 从“酒不醉人人自醉, 胡天胡帝蹉跎了青春”中可见些许端倪。 这次“民族化”尝试的遗作证明了流行音乐有可能为东方文化所服务, 但短暂的哗众取宠过后便烟消云散, 也证实了民族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顺其自然。[1]
20世纪80年代, 当流行音乐以风卷残云之势再度袭来时, 中国文化在接纳并融合的过程中开始了一轮对于传统音乐文化自省与反思的高潮, 随之而来诞生了前所未有的原创歌曲热潮“西北风”。 此次流行音乐“民族化”进程攻势强烈, 大陆乐坛当时曾出现“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般的一家独大。 然而, 急功近利也并非“民族化”之上策, 强势的席卷被快速的审美疲劳所摧毁, 仅仅不过两年时间, “西北风”也一阵风似的刮过, 从此再无人问津。
屡屡失败的教训不禁使人疑惑, 究竟流行音乐是否可以被“民族化”, 需不需要被“民族化”, 又如何操作才能够成功呢? 也许, 草率的叫嚣使流行音乐如何“民族化”, 未免有些不自量力。 即便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我们的流行音乐产业发展已日趋成熟, 但距离“自成一派”还为时尚早。 与其费尽心机地思考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 不如思考如何为流行音乐贡献素材与生机。 在我们看来, “民族化”不应是生搬硬套的“东施效颦”, 更不应是盲目傲慢的妄自尊大。 当时机不成熟, 能力不足以为之的时候, “民族化”稍有不慎便会沦落成为噱头或笑柄。 在漫长的华夏音乐历史中, 我们运用“民族化”的“武器”, 成功地将外来乐器、 舞蹈、 音律转化成为民族艺术的一部分, 历史的成功可以当作经验来继承, 却不可作为财富来炫耀。 欧美流行音乐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就默默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流行音乐风格体裁, 如今依旧执世界流行乐坛之牛耳, 这样的地位并非我们追赶过程中的灵光一现就可以撼动, 学习与理解还需漫长岁月。
“中国风”这一称谓出现在新世纪伊始的流行乐坛。 周杰伦的一曲《东风破》, 配合MV中古典气质十足的水袖、 古琴、 红烛, 将欣赏者拉入遥远的古文化意境中。 不多时, 随着《发如雪》《兰亭序》《千里之外》的出现, 以及陶喆、 王力宏、 林俊杰等歌手的纷纷效仿, “中国风”的基调确立, 风格模式也形成了审美的共识。 人们不禁会问, “中国风”是否又是新的一轮“西北风”? “中国风”是否标志着“民族化”的成功? 在仔细思考之后, 我们认为, “中国风”与“西北风”绝非同类, 而与“民族化”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代沟。 “中国风”的本质是对东方文化的缅怀与致敬, 以现代的音乐手法继承发扬。 但行为主体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运用的技法是完全西化和现代的音乐语汇, 而其结果是为了塑造新的音乐风格路径, 而不是为了谁吞噬谁。[2]
首先, 主体的形象不同是流行音乐“中国风”区别于以往“民族化”的最重要的显性标志。 在以往的中国原创音乐中, 将传统文化与流行音乐相互结合的创作成果不胜枚举, 徐沛东的创作, 刘欢的演绎, 无论是曲调中的京腔京韵, 还是歌词中浓郁的传统辙韵, 都透露出彻头彻尾的新曲“做旧”。 但这并不能被纳入到“中国风”的行列, 只能被称为“戏歌”或“跨界”。 “中国风”的主体是具有欧美生活经历, 或被欧美流行音乐风格所深刻浸染的新生代流行歌手, 他们往往具备创作能力, 在意识形态中存在现代音乐与古典韵律的双重审美心得。 无论周杰伦、 王力宏、 林俊杰, 或者他们背后的方文山、 陈镇川、 李瑞洵, 都存在这样的共性特点。
其次, 从运用的音乐技巧来看, “中国风”的音乐语汇擅长以流行音乐元素中的R&B、 说唱、 民谣等风格为依托, 并未因歌词内容和曲式结构的复古化而一味地迎合, 而是通过矛盾对立的方式, 在一首歌曲中展现出古今与中西的鲜明反差。 这样的创作思路不仅完整保存了现代音乐的全貌, 又以当代人乐于接受的视角提炼出古文化的精彩点滴。 这样的解构方式和音乐自信, 在以往“民族化”的实验中是不具备的。
再次, “中国风”的音乐理想并非功利地达到某种目的, 而更多的是在随心所欲中渗透审美的多样情怀。 如《烟花易冷》中“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的古典爱情, 《青花瓷》中“天青色等烟雨”的优雅江南水彩, 《在梅边》中“春水望断夏花宿残妆”的生死离别。 种种对于传统文化的观察包含了人文、 历史、 传奇、 典藏。 看似杂乱无章, 但却在松散的随笔中勾勒出传统文化神采的精绝。 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风”的自然随性无意中完成了“民族化”的寄托, 并去除了其中的急于求成。 而随着“中国风”的渐行渐远, 它已超出了音乐种类或中西文化的隔阂, 化索取为给予, 为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更精彩的通途。
“中国风”没有被禁锢在“民族化”的“瓶子”中, 而是以“老酒新酿”的方式将传统文化全新表达出来。 “中国风”的自由清新使其并没有将古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作一种负担累赘, 反而化腐朽为神奇, 成就了以小博大以柔克刚的美谈。
二、 音乐历史中的流行音乐“中国风”
虽与流行音乐发展中的几次“民族化”进程不同, 但“中国风”的成功也并非史无前例。 翻阅近代中国音乐的历史, 发现曾经的过往中有过许多异曲同工之妙, 而这些音乐事件与成果, 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塑造和影响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学堂乐歌”是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开端, 受“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 中国的新式学堂中引入了音乐教育内容, 其主要创作与代表人物是沈心工、 李叔同、 曾志忞、 柯政和等人,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过留洋经历。 在他们的创作中, 美国歌曲《罗萨·李》被改编成《勉学》, 法国民歌《一个半小时的游戏》被改编成《话别》, 美国流行歌曲《梦见家和母亲》被改变成家喻户晓的《送别》。 这些创作举动并非为了功利化的目的而投机取巧, 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助推的“灵机一动”。 西化的音乐旋律与“维新运动”的时代进步不谋而合, 而被置换植入的中式歌词, 除了顺应时局, 也彰显了动荡时局下音乐人不屈不挠的民族自尊。 “学堂乐歌”的成就在于, 它迈出了中西音乐在近代结合的第一步, 并将理论上的可能性成功付诸实践。[3]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音乐创作与传播的又一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基础。 在此之前, 虽欧美旋律音调在中国不绝于耳, 但并未形成真切的认识与研究, 也许就没有进一步的融会贯通。 直到萧友梅、 黄自、 赵元任、 青主等“学院派”音乐家崭露头角。 这些大家有着留洋国外多年的共同经历, 不仅将国外的优秀作品介绍到国内, 还将歌唱理念、 作曲理论、 配器技法一并引入, 开创了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 《长恨歌》巧妙借用了西方清唱剧的体例和配器方法, 而意境却随传统文化而动, “仙乐”“长生殿”“渔阳鼙鼓”等主题元素, 融于“山在虚无缥缈间, 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写意抽象之中; 《教我如何不想她》营造出复杂多变的调式环境, 在严谨的旋律体系中描绘出专属于东方的四季美景, 平淡却不失风韵, 简洁而不乏儒雅。 “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使东西音乐文化的融合更进一步, 合理的取长补短以科学的音乐理论和声乐技巧辅以中国化的内涵构造, 看似素不相识的结合却并行不悖, 自然而然。
80年代的港台流行乐坛被誉为最鼎盛时期, 不仅刘文正、 邓丽君、 罗大佑、 “四大天王”接踵而至, 更有无数被奉为经典的流行音乐作品相继诞生。 而作品高产的背后, 其实蕴藏着中外音乐创作结合的大量案例。 如张学友最具代表的《李香兰》《每天爱你多一些》, 王菲的《梦中人》《黄昏里》, 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山茶花》, 等等。 几乎当时所有大红大紫的歌星都或多或少演唱过这类歌曲, 就是在日本流行音乐作曲基础上填词翻唱或改编。 当然, 在特定时期以如此搭配音乐创作, 不免有政治因素, 但这样的流行音乐创作尝试, 早于大陆的“西北风”, 并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口碑。
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五四”艺术歌曲, 再穿梭到80年代的港台流行乐坛, 一段段历史缩影至今仍历历在目, 它们对于中外音乐文化的结合探索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方式, 与今天流行音乐的“中国风”热潮有着如出一辙的相似。 首先, 引领这些历史风潮的主导力量, 都是感于时代而动的音乐弄潮儿, 他们饱有国学与西学的双重阅历, 了解国际音乐发展的最新风向, 并愿做中西音乐桥梁的搭建者。 其次, 无论“学堂乐歌”或艺术歌曲、 “中国风”音乐, 都成功找到了中西音乐结合的合理对接点, 恰到好处的融合使双方的文化精髓得到互补, 基于优势基因的结合并没有产生音乐审美中的隔阂。 置身中国文化的生态群落中, 一辈辈音乐人虽身处的境遇不同, 但都对传统文化充满敬畏、 尊崇, 并深感任重道远。 再次, 同样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提炼, 不同音乐人的视角各有千秋, 并没有被圈禁在某一狭隘的语境中, 也没有贪图面面俱到的海纳百川。 细致、 深入、 感同身受, 很小的音乐动机就可以勾起欣赏者对民族文明的肃然起敬, 而内心的自豪和归属感也随之油然而生。[4]
传统音乐文化这坛“老酒”已在华夏文明的孕育中酿造了几千年, 即便在今天工业现代化主宰的文明中已不再身居台前, 但它却根植于民族历史, 昭示着东方文化的别样精彩。 正如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音乐思潮一样, “中国风”就像音乐浪潮中的一朵涟漪, 每每翻腾出不同的形色, 反射出不同时代的镜像, 但对于母体的眷恋从未有过半点消退。
三、 流行音乐“中国风”的机遇与挑战
在几十年的拼搏奋斗中, 中国的流行音乐人始终在追赶中前行。 原本起步就晚的中国大陆原创音乐, 不仅与港台音乐竞争市场, 还要抵御日韩风潮的愈演愈烈, 而欧美流行音乐风格的多元和新潮更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度。 多年来, 中国大陆音乐人都曾试图通过努力, 寻求到一种属于中国流行音乐特有的声音, 能够与摇滚、 嘻哈、 爵士等风格并驾齐驱, 以此来慰藉多年的劳苦与自尊。 但无奈, 为了迎合市场, 取悦观众, 不得不随波逐流, 飘摇中求得生存契机。 对于传统音乐元素与流行音乐潮流的结合, 在求索中也曾多次尝试, 但始终“叫好不叫座”, 虽得到赞许, 但很难引发年轻人的共鸣, 也不能形成持续的深化创作。 究其原因, 一则是视野狭窄, 流于形式表象, 不足以深入人心; 另一则大概是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融合方式, 导致音乐形态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
“中国风”的出现, 成功开辟了技术领域的新天地, 但所引发的创作与审美缺陷问题却更值得推敲。 首先, 欧美流行音乐中的R&B和说唱等风格已存在许久, 引入中国的时间也很早, 为何国内的音乐创作者并没有将其转化成为“中国风”的面貌; 其次,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多可以表现的素材, 为何在以往的民歌和音乐创作中始终标榜轮廓, 而不能形成多元的微观具象存在; 再次, 中国流行音乐人原本手握大量的一手资料, 并占据绝对有利的文化高地, 但“中国风”的创作和演绎为何总是“海归”创作人能够先知先觉。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 恐怕最为贴切的便是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现代音乐创作者时常以时尚与潮流来炫耀自己, 总试图通过脱离文化束缚来表达自己的独树一帜, 而对于传统文化和艺术, 要么采取避而不谈的冷漠, 要么便是浅尝辄止的敷衍。 然而, 音乐是有灵魂的, 是有根源的, 那些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律动, 虽然随时代发展可能越埋越深, 但其能量却是深入骨髓, 挥之不去的。 国门开放, 文化交融, 使我们的创作动摇了信念, 以模仿和追随潮流来诠释自己的与时俱进, 恰恰忽略了手边最宝贵的资源。 殊不知, 再高明的模仿也是“二手”的仿品, 只有立足本质的原创才是无可撼动的资本。[5]
也许对于“海归”音乐人来说, 在技术层面上更易于把握得得心应手, 但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热爱与主动衔接, 绝非物质领域的时机成熟, 而在于“海归”音乐人寻根意识中更迫切的渴望。 也许在置身“他”文化的境地中时, 那种浮萍般的感伤尤为突出, 而自我证明与寻找存在感的心绪自然而然地会倚靠在传统文化的脊梁上。
自“中国风”起, 新世纪歌坛对于民族文化的自省与反思变得深入许多, “中国风”也刮得愈来愈猛, 成为华语乐坛原创音乐风格的重头戏。 大至故土河山, 小至瓦檐滴雨; 柔至汉服水袖, 美至胭脂粉黛; 远达西汉初秋, 近及昨日掠影。 “中国风”音乐创作中洋溢着浓浓的温情, 厚重的儒家哲理, 丝丝入扣的细致妥帖。 但当音乐变得熟悉而美好时, 我们生怕这一切会再度丢失, 害怕如各种各样流行风潮一样会转瞬即逝, 变成过时与陈旧的代名词。 作为当代流行音乐创作者, 作为具有责任感的音乐人, 我们实在有责任以“中国风”为里程碑, 将其风格长久保持并上升为与蓝调、 摇滚并立存在的固定体裁样式, 以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成长证明, 为传统音乐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在一些理论学者谴责流行音乐对于传统音乐的破坏时, 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歌剧与摇滚乐的并行不悖, 看到美国百老汇歌舞与说唱饶舌音乐的同生同长。 音乐的发展不一定必须此消彼长, 不同音乐形态之间的雅俗高下之争更荒诞无稽。 传统音乐在当今时代的继承弘扬必须学习现代音乐的成功经验, 而现代音乐脱离了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传统也会变成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历史赋予的文化瑰宝随时间的迁移变成芬芳醇厚的陈酿, “中国风”的出现正如一把钥匙, 开启了历史酒窖的大门。 愿现代音乐的智慧能够成就历史回响的生生不息, 续写民族文化新的乐章。
[1] 王思琦.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 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72-206.
[2]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48-55.
[3] 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266.
[4] 姚艺君.中国传统音乐基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239-253.
[5]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9.
[责任编辑 杨 倩 尹 番]
An Analysis of Chinese-Style Popular Music
XIN Ying
(EducationandMusicCollege,Luoyang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Luoyang471023,China)
The Chinese-style popular music,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opular music style of western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culture, has gain increasingly interest in the new century.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style and national-style music through different genres of music in multi-point views.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style popular music to the famous event occurred in history. At last, we analyze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Chinese-style popular music is leaded by overseas returnees and how to make the Chinese-style music become a real music style in a sustainable and stable way.
popular music; Chinese-style; national styl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2017-02-17
辛颖(1983—), 女, 河南洛阳人, 助教。
J605
A
1009-4970(2017)07-008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