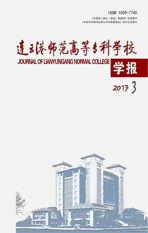《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差异及影响因素
2017-03-11赵建国
赵建国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
《红楼梦》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差异及影响因素
赵建国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6)
《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霍克斯英译本在用词、句式、翻译风格、民俗风情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审美观念、语用习惯和翻译策略。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找到原著与译文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译者应掌握双语基本功,夯实语言基础;遵守目的法则,活用翻译方法;秉持文化翻译观,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红楼梦》;译本;差异;影响因素
《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有多种,代表性的译本当为中国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英国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分别简称“杨译本”和“霍译本”)。杨宪益生于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有深入的研究;霍克斯生于英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致力于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翻译则成为跨文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和交际工具。两位译作者生活、成长与接受教育的背景迥异,分别受到中国、英国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自然带有鲜明的个人及民族文化的印记。本文对两个译本中的译文差异进行对比,并对造成译文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赏读、品析英译本《红楼梦》,同时为提高古典名著翻译的质量提出建议。
一、杨译本、霍译本译文差异的具体表现
杨宪益的翻译多是从中文直译过去,力求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霍克斯的翻译多考虑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感受,行文更符合英语的话语方式。笔者主要从用词、句式、风格和风俗民情角度分析两个译本的翻译差异。
(一)用词差异
《红楼梦》中存在许多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词汇,而杨宪益、霍克斯各自选择了认为最合适的词语与之对译,现举数例如下。
例1 贾瑞一把抓住,连叫“菩萨救我”。
杨译本:When they complied,he seized hold of the Taoistand cried:“Saveme,Bodhisattva!Saveme!”
霍译本:“Holy one.Saveme!”He cried out again and again.
杨宪益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将“菩萨”译为“Bodhisattva”,保留了原文用语的宗教内涵;霍克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将“菩萨”翻译成“Holy one”,增添了基督教色彩。
例2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杨译本: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without rice.
霍译本: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原文中的“粥”,杨宪益、霍克斯二人分别译为“rice”“flour”。显然,前者的翻译更符合中国人所说的“粥”的概念。
例3 怡红院
杨译本:Happy Red Court
霍译本:Green Delight
在本例翻译中,杨宪益将“红”译成“red”,而霍克斯则将其译成了“green”。相比之下,前者符合原文。
例4(王熙凤道:)“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杨译本:Iforgetourold ancestress.
霍译本:Iquite forgetaboutyou,grand dear.
杨宪益翻译的“old ancestress”强调年高位尊,称呼比较庄重;霍克斯将“老祖宗”译为“grand dear”,显得亲切自然。
(二)句式差异
汉语、英语的代表性差异之一就是句式的差异,从杨、霍的译本中,读者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一点。
例5昨宵庭外悲歌发。
杨译本:Last night from the courtyard floated a sad song.
霍译本:Last night,outside,amournful sound was heard.
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在翻译本句诗时,霍克斯的被动句型翻译更符合西方人的行文特色。
例6 恰好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见紫鹃之言,都赶着来看。
杨译本:Just then,the old lady arrived with Lady Wang,Li Wan and Xifeng who had hurried over after hearing Zijuan’s report.
霍译本:Itwasat thismoment thatGrandmother JIA,LadyWang,LiWan and Xifengarrived on the scene.
杨宪益的翻译将人物置于句首,内容中心安排在语句的前半部分。霍克斯的翻译使用了不定代词“it”做形式主语,句子的内容中心偏向语句后半部分,且省略了有关紫鹃的内容。
例7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杨译本:Lin Ruhai Recommends a Tutor to His Brother-in-Law.
The lady Dowager Sends for Her Motherless Grand-Daughter.
霍译本:Lin RuhaiRecommends a Private Tutor to His Brother-in-Law.
And Old Lady Jia Extends a Compassionate Welcome to theMotherlessChild.
杨译以并列的分句相连,以前后顺序暗示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霍译偏重句子的内在结构,使用严谨的连接词揭示事件的逻辑联系,以“and”点明两个事件的并列关系。
(三)风格差异
总体来说,杨译本与霍译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杨译本倾向采用直译、异化等翻译方式,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霍克斯则遵循文化交际的翻译策略,采用归化等多种方式使译文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与接受,能使目的语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颇为相似的阅读感受。
例8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
杨译本:Her close-fitting red satin jacketwas embroidered with gold butterfliesand flowers.
霍译本:Her dresshad a fitted bodice and wasmade ofdark red silk damask 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and butterflies in raised gold thread.
由此可以看出审美因素对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影响。霍克斯将王熙凤穿的袄译成了“dress”,充分展现了女性的妩媚美,而杨宪益的译文“jacket”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显得普通和呆板。再如:
例9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坛子打个稀烂!
杨译本:One of these days when I really losemy temper,I am going to give that vinegary bitch a good beating.
霍译本:One of these days when Igetmy temper up,I am going to lay into that jealous bitch and break every bone in herbody.
例10 贾芸笑道,“虽那么说,叔叔屋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
杨译本:Imustn’t forgetmymannersbefore the sisters in yourapartments,uncle!
霍译本:“Iknow,”said Jia Yun,“Buta body-servant!Idon't like tobe presume.”
例9、例10集中体现了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时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杨宪益追求译文需忠实于原作,再现原作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因而更多采取直译的方式,如例9中的“醋坛子”和例10中的“姐姐们”,杨宪益分别译为“vinegary bitch”“sisters”;霍克斯则采用意译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分别译为“jealous bitch”“ body-servant”,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原文。
(四)风俗民情差异
杨译和霍译在处理一些体现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词语翻译中也有差异,如:
例11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杨译本:But poor ill-fated little cousin,losing your mother so young!
霍译本:But poor little thing!What a cruel fate to have lostAuntie like that!
对于“妹妹”一词,杨宪益直译为“little cousin”,直接点明了王熙凤和林黛玉之间的关系;霍克斯巧妙地将它翻译为“little thing”,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刻画出了王熙凤善于人际交往的人物形象。
例12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杨译本:I’m late in greeting ourguest from afar!
霍译本:Oh dear!I’m late.I’vemissed the arrival ofour guest.
霍译本增加了“oh dear”一句,拉近了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与西方人奔放的处世方式一致。中国人则相对含蓄,很少以“dear”互称,因此杨宪益在译文中仅仅用“guest”一词代指黛玉。
二、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差异探因
杨译本与霍译本的差异是两位翻译者不同的成长经历、所处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具体地说,造成两种译本差异主要有以下诸方面的因素。
(一)社会文化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大不相同,而宗教信仰对人们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有很大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两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不断得到发展,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派别之一。生长在中国的杨宪益熟稔佛教文化,如“菩萨”是佛教中的神仙,因此他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将“菩萨”译为“Bodhisattva”,保留了《红楼梦》原文体现的宗教观念。霍克斯生长在英国,英国的主流教派是基督教,因而他受基督教的影响较深。在翻译“菩萨”一词时,霍克斯将佛教中的“菩萨””译为基督教中的“上帝”即“Holy one”。这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是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较好体现。
人情风俗也能导致翻译的差异化选择。古代中国的大家庭中,年长者处于权威地位,备受尊重。而西方国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平等,有时可以直呼其名以表达亲切感。因此翻译《红楼梦》中的人物称谓时,杨宪益和霍克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如对“老祖宗”一词,由于贾母在贾府最受尊重,杨宪益将其译为“old ancestress”,以体现尊贵的地位;霍克斯仅将其译为“grand dear”,淡化了尊贵色彩,增加了亲近的意味。再如,对王熙凤所说的“妹妹”一词,杨宪益译为“little cousin”,直接表明了王熙凤与林黛玉之间的亲缘关系;霍克斯将其翻译为“little thing”,霍克斯似乎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认为“little thing”带有亲切色彩,但在中国人看来,将人称为“thing”却带有轻蔑的色彩。对“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杨宪益将其译为“Bathed in tears”,形象地表现了贾珍把所有痛苦和辛酸都写在了脸上而不加掩饰的情态;霍克斯则将它译为“well-nigh chocked with tears”,披露了贾珍有泪往肚子里咽却不愿别人知道的心态。其原因在于中国人重视社会性,乐善好施。邻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认为个人的事就是家庭的事乃至集体的事,所以他们很关心别人的欢乐与痛苦,也愿意向他人说出自己的喜悦与不快[1]。这一点对于西方人而言恰恰相反,西方人历来以个人为中心,注重对自身隐私的保护。
此外,不同国家的人们对颜色的偏爱也不同,对颜色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爱红色,这个喜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的民族,钻木取火加速了先民对火的认识,培养了华夏子女对红色的亲近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寓意兴旺、喜庆、热烈。但西方人并不喜欢红色,红色的引申义在英语中贬多褒少,经常使西方人联想到残忍、灾难、战争、死亡等,如“red battle”意为“血腥的战斗”,“red vengeance”意思为“暴力复仇”。绿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绿色代表着生机,另一方面绿色又代表着低贱。而在西方,绿色蕴含着积极的文化内涵,代表着和平、希望和生命力。因此,杨宪益遵循中国文化传统,把“怡红院”翻译成“Happy Red Court”;但是英文读者对此会一头雾水,无法将“Happy”和“Red”联系在一起。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可接受性,霍克斯将“怡红院”翻译成了“Green Delight”。同样,对《红楼梦》书名的翻译,杨译本传递了书名的字面意思,即“红楼中的一个梦”,因此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而霍克斯先生则考虑到了红色一词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含义,放弃了《红楼梦》这个书名而采用了另一个书名《石头记》,将它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二)审美观念
中国人注重婉约美,外国人则欣赏豪放美。《红楼梦》刻画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女子形象,她们是中国古代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杨宪益和霍克斯在描绘她们的形象时必然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美学策略。例如,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一句,杨宪益将“袄”译为“jacket”,这一翻译使人物的美丽形象大大受损。众所周知“jacket”一般指“短上衣,夹克衫”,穿“jacket”的女性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中性,少了几分温婉和柔情。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散发着妩媚的女性,因此用“jacket”这个词无疑会影响王熙凤在读者心中的形象。相比之下,霍克斯将“袄”译为“dress”更胜一筹,较好地再现了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保留了原作的美学效果[2]。
(三)语用习惯
英汉两种语言不仅在词汇层面存在着诸多不同,而且在句式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汉语多主动句,英语多被动句;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语重名词,英语重代词;汉语偏头重句,英语偏尾重句等。汉英句式的不同特点也导致了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文表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3]。如例5中,霍克斯使用了被动句型进行翻译,符合西方人的行文方式;杨宪益使用主动句进行翻译,偏向中文的行文方式。例6中,霍克斯使用了不定代词“it”做主语和倒装句型,符合英文喜用代词和尾重的句式结构;杨宪益则使用了名词做主语,没有最大程度地体现英文的句式结构特点。例7中,两位翻译者对章回目录的翻译体现了汉语重意合、英文重形合的特点。因为,汉语多以意思连接的积累式分句或独立单句相连,以句序之先后暗示其逻辑关系,英语则要通过增加连接词等保持语言的逻辑性。所以,杨宪益严格按照原文的短句特征将其译为两个独立分句,霍克斯先生则按照英文的句式特点添加连词“and”,将两个独立的分句连接起来。
(四)翻译策略
总体来说,杨宪益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杨宪益遵循“文化翻译观”,即译文需要忠实于原作,故而采用直译和异化等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原作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目的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而霍克斯先生则持“交际翻译观”,认为译文应该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习惯,因此采用意译和归化的翻译策略,用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翻译原文,使译入语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感受原文读者的阅读体会,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如例9中,“醋坛子”指“心眼小,爱嫉妒的人”,在《红楼梦》中,“醋坛子”意指王熙凤不允许丈夫在外面有其他女人。杨宪益用的译文与原文严格对应,却可能让外国读者不明白为什么女人是酸的。因此,霍克斯照顾到外国读者的感受,将它直接译为“爱嫉妒的女人”。例10中“叔叔屋里的姐姐们”一词,并非指有血缘关系的姐姐,而是指宝玉屋子里的丫头们。杨宪益忠实于原文字面意思,将它直译为“sisters in yourapartments”,这容易导致外国读者误认为这些丫头们和宝玉是有血缘关系的;霍克斯并未逐字翻译,而是意译为“body-servant”,点出和贾芸戏谑的那些丫头们与宝玉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三、从译文差异看翻译的优化策略
通过阅读译作、分析差异,我们可以看出杨译本的表达更切合古典名著的中国文化内涵,而霍译语言表达更为流畅,贴近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这些体现出译者对源语言、目标语言形式和文化的精准把握,以及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的读者群而采取的贴心、精巧的翻译策略。《红楼梦》翻译属于文学翻译,跨文化特征尤为明显。从杨译本、霍译本的差异来看,为了提高翻译质量,文学翻译工作者应具备以下语言素养,并形成有效的翻译策略。
(一)掌握双语基本功,夯实语言基础
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是翻译的基础,因此优秀的译者需要熟练掌握源语和目标语,以便对两种语言进行准确传译。比如,在词汇使用上英语和汉语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即英语呈静态,汉语呈动态。简而言之,英语倾向使用名词来表意,而汉语则更多使用动词。名词是英语的优势词,在英语中大量被使用,特别是常用抽象名词来表达各种动作概念;动词是汉语的优势词,在汉语中随处可见,可以充当句子中的各种成分。如果译者在平时的翻译训练中善于对两个语种的词汇使用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并通过恰当的词语表现作品的内容,就可以避免中式英语在翻译中出现,从而使译文更加地道。
(二)遵守目的法则,活用翻译方法
翻译中的“目的法则”决定了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对中西翻译史上的归化、异化之争,乃至近二三十年译界广泛讨论的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目的法则”均能做出很好的解释。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时,对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采取了直译的方式,目的是使西方读者能够最大程度地接受中国特色文化,领略其原汁原味的语言魅力;霍克斯先生则更多采用意译的方式,用西方文化中具有同等意味的词语来表达《红楼梦》原著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希望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与中国读者产生同样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当然,不同翻译方法本身无可厚非,译者也无需厚此薄彼,因为没有最优的翻译策略,唯有根据翻译目的灵活选择翻译策略才能使译文具有其应有的价值。
(三)秉持文化翻译观,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实质上是文化交流,既包括文化内部的交流也包括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文化而不是传统的词句或者语篇,应走出语义等值的局限,实现文化中的功能等值[4]。显然,这种文化翻译观重文化交流,视文化为第一位,而视信息为第二位。因为文学作品基于大众生活,最能集中反映一国独具特色的国情和民风习俗,在翻译成另一语言时不易找到直接对等的意象,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若没有特殊的翻译目的,应尽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间寻找翻译意象的平衡点,既减少源语文化特色的损失,又便于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促进文化内部交流和文化间交流。优秀的译者需一头连着古老的历史,一头连着异质文化的读者,不仅要掌握两国的语言文字,具备广博的知识,还要熟谙两国之间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和文化常识,才能准确恰当地表现源语和目的语,让不同民族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对方的经典文学作品,为民族文化传播和相互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
[1]戴清娥,杨成虎.《红楼梦》英译本饮食名称翻译的对比研究:以杨宪益和霍克思的英译本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4):80-84.
[2]张碧云.对《红楼梦》杨、霍两个译本的对比赏析:以第三回为个案研究[J].新西部,2011(9):152-153.
[3]蔡小红.英语与汉语:静态与动态的转换翻译[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4):124-125.
[4]段峰.苏珊·巴斯内特翻译文学思想评述[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8-92.
The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Dream in the Red Mansions
ZHAO Jianguo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Lianyungang Normal College,Lianyungang 222006,China)
The Dream in the Red Mansions has two representative translations respectively done by the Chinese couple YANG Xianyi and DAINaidie,the English man David Kawkes.They two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using words,sentence patterns,translation styles,and folk customs and so on.Themain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clude social cultures,esthetic senses,pragmatic habit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So in order to reach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translation,to promot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translators mustmaster bilingual basic skills,strengthen linguistic foundation.In translation,translators should obey the target-language principle,make flexible use of the translation methods,hold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thus we can best promo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 Dream in the Red Mansions;translation;differences;influential factors
I046;H315.9
A
1009-7740(2017)03-0027-05
2017-06-20
赵建国(1966-),男,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