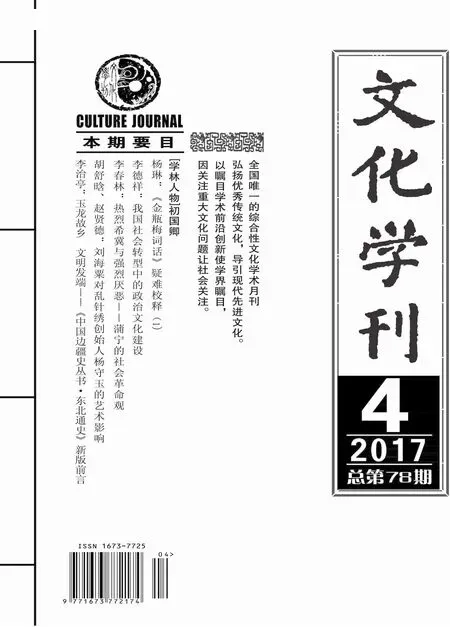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
——兼谈我国《物权法》106条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2017-03-11梁汪洋
梁汪洋 凌 晶
(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法律文化】
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
——兼谈我国《物权法》106条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梁汪洋 凌 晶
(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我国善意取得制度见诸于物权法106条,立法直接将其统一适用于动产与不动产的所有权领域引发了颇多争议。依体系解释来看,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需立足于无权处分基础之上,因此在不动产领域,合理地理解无权处分的内涵关乎善意取得制度目的的实现。本文就主要探析不动产领域内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善意取得;不动产;信赖保护
善意取得制度滥觞于日耳曼法的占有制度设计,后又吸收了罗马法短期时效制度的善意构成要件。厘清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首先必须从整体端视善意取得制度的理性基础。依笔者看来,其理性基础在于通过立法拟制技术简化现实交易占有所有时常分离的复杂情形来保障交易的安全和便捷,[1]换言之,其制度设计的基础在于市场交易中经济自由、安全和便捷效率的价值导向。以此可见,如果没有现实中无权处置他人之物的交易常态,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余地则完全无从谈起。依我国《物权法》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动产或不动产于受让人,所有权人皆可予以追讨,但符合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的除外。该规定简化了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将动产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做一并规定,但现实的问题在于不动产和动产在无权变动规则中存在明显差异,这势必要求二者在适用上有所区别。基于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的适用规则上争议不大,但在不动产上的争议颇多,因此笔者试就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的相关问题,以及我国物权法106条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予以分析和讨论,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希盼对于未来司法解释的出台和立法的重构有所裨益。
一、无权处分的概念确定
无权处分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就标的物的所为的处分行为。[2]在此,该如何理解“处分”二字?从学理来看,最广义的处分可分为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一般而言无权处分中的“处分”系指法律上的处分,即通过买卖、抵押、质押等行为使得所有权转让或者权能发生分离的情形。[3]何以具备处分之能力,在笔者看来,应当从两个维度来看:第一,具备处分权应当有内部的法律事实关系作为支撑;第二,处分资格的具备需满足物权变动的外部形式要件。[4]按照此两种进路可对不动产中无权处分的内涵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处分人即使具有登记权利人的形式要件,但其不具有真实的法律事实的支撑,其亦属无权处分人;第二,处分人是实际的有权处分人,但不具有外部的形式登记要件,其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
如何理解不动产领域中无权处分的内涵,学界目前主要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登记错误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登记错误与无权处分实属上下位阶关系,对无权处分应作限缩解释,即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对无权处分的解释仅应限定在不动产登记权利人登记错误的情形下,行为人以登记权利人之名义处分不动产。二是学者们认为登记错误和无权处分应当属同一位阶,是并列关系,其共同的上位阶概念是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的要件。[5]依笔者之见,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应采用第一种“登记错误说”,具体来看:善意取得制度系为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而设立,其存在的逻辑前提应当有一个使相对人得以信服的、产生信赖的“标记”,即立法上所表达的使买受人产生所谓的“善意”,《物权法司法解释(一)》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其立法原意即在于此。因此,对于物权法106条的解释脱离此“标记”,则与立法精神的原意相背离。在正常的不动产交易中,实际权力状态和形式所登记的权利状态应当一致,但试想如果处分人没有登记权利的“标记”,相对人所谓的善意和信赖之说实属勉强,因此对于不动产无权处分应当采用笔者之前所言的第一种维度予以思考,即在登记错误情形之下,处分人虽没有内部的法律事实支撑,但其具有登记的外部形式之外观,其亦属无处分权人。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限缩解释至“登记错误”还远不能解决理论实务中的诸多争议,其还需进一步的界定理清。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是否所有的登记簿错误都可以致使不动产善意取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登记错误具体可分为登记簿上的权利事项错误和非权利事项错误。[6]权利事项的错误是指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关乎不动产权属和纠纷与真实的物权不一致的登记错误,非权利事项的错误则一般指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事项与不动产的自然状态不一的错误,诸如房屋实际的楼层、位置和登记簿上登记的不同等情况。在此,登记错误应当进一步限缩解释为权利事项的错误。因为权利事项的错误与非权利事项的错误在文意上虽差之毫厘,但在法律效果上却差之千里。一方面不动产登记簿的功能在于实现交易明细的清晰化目标,其具有事实上的推定效力,但推定效力的范围却仅仅限于不动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而这些权利都是不动产登记簿表现,皆属权利事项。另一方面非权利事项错误也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性基础不相协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买受人不可能仅因为不动产登记簿上房屋面积的登记错误对处分人产生实际所谓其具有处分不动产权能的“信赖”。因此可以进一步地理清不动产善意中的无权处分,即应限缩解释为权利事项的登记簿登记错误。
至此,似乎从学理上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的界定已予明晰,但颇为吊诡的是,在私卖夫妻共有财产的类型案件中,对于夫妻一方“无权处分”夫妻共同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还存在颇多争议。在笔者看来,首先应当讨论是否夫妻一方只要处分共有不动产财产,就都属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如果其并非之前所界定的权力事项的登记簿错误,那么其也不应由善意取得制度所调整。因此,对此问题如果不能予以明确,显然对于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有百害而无一益。笔者试结合案例分析和解答这一现实问题。
司法实践中,关于夫妻一方擅自处理共有不动产财产的类型案件依笔者之见主要可归类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夫妻双方均为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人,其中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不动产;第二,不动产登记簿上仅登记一人,夫妻另一方没有登记,但是没有登记的一方擅自处分了共有不动产;第三,此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类似,区别在于处分人是登记的夫妻一方。针对以上三种情形,在笔者看来,虽同属广义上的“无权处分”,但其并非都属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限缩解释后的“无权处分”。仔细分析来看,只有在第三种情形下才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因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在于有一个外部信赖的“标记”,此标记的表现在于登记簿上的权利事项错误。前两种情形虽也使相对人产生了“信赖”,但此信赖非彼信赖。相对人在此产生的信赖标记并非基于登记簿上的错误,而是由于其相信基于夫妻关系,夫妻一方有“代理权”代表另一方处分财产。需要明确的是,夫妻关系并不当然地附随产生代理关系,其实际处分共有不动产财产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7]而无权代理和无权处分之间却是个性大于共性,其有本质区别,[8]切不可将二者混淆替用。
另需补充的是,是否前两种情形之下私卖夫妻共有不动产财产买受人的交易安全就不再受保护?其实不然,保护相对人的交易信赖安全乃现代民法的基本理念,只不过保护此等信赖的制度非善意取得制度,而是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避免混淆使用各种民法制度,发挥各制度的特定功能方能实现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的初始目标。
三、《物权法》106条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似乎所有问题的症结皆在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将善意取得制度统一于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领域之上,事实上自《物权法》颁布以来,学界对于此条的质疑和批判就不绝于耳。其主要论点基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采用严格区分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立法模式,着眼于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在架构基础、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的不同,明确善意取得制度仅应适用于动产,在不动产所有权领域的信赖交易安全则应由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机制予以规范和保护。[9]依笔者之见,其论点指明就不动产和动产应当分别构建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两种架构迥异的交易保护制度,分别调整的立法方向值得称道,但仔细推敲此论点,还需讨论以下几点问题:第一,立法者将《物权法》106条统一规定适用不动产,究其原因是对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示力区分认识不够,还是另有他义?第二,善意取得制度是否绝无适用不动产领域之可能?
针对第一个问题,可从我国《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看出些许端倪,在王利明教授和梁慧星教授分别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都提出了要分别建立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区别在于王利明教授提出可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做特别规定,但在最后通过的《物权法》中却对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条文只字未提,而是将善意取得制度扩张至不动产所有权领域,中国“特色”的《物权法》106条就由此形成。
仔细分析王利明教授和梁慧星教授的建议稿,就会对我国立法机关对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区别了然于胸。但我国依旧反其道行之,唯一理性的解释在于立法者是在考量我国的实际国情后,对于我国建立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未有充足信心,需可知我国自建国以后长期实行房屋分配制度,且执行男女有别的分房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期实行房改时,更有单位明确要求唯有本单位人员才具有登记房屋登记簿之资格。[10]而这一现实国情与德国严密的不动产登记簿制度差别甚大,此贸然借鉴分立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制度无国情基础做支撑,实非立法之上策,可见对于《物权法》106条绝非立法者理性缺失之产物,而实属权衡国情利益之规范。
此外,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能扩张至不动产所有权领域的争论也尤为激烈。坚持善意取得制度仅能限于动产的学者主要因为两点。第一,不动产交易中往往以登记作为公示的方法,买受人在实际交易中一般不会误将房屋占有人误认为所有权人,并与之交易。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几无适用之空间可谈。第二,基于比较研究的法域经验,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皆采用分离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立法模式,其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促进商品流通效果显著。因此,我国需以之为立法范本。然而笔者却不敢对此苟同,首先,不动产实际交易中确以登记作为所有权认定之标准,但却存在登记错误之常态,实际所有权人和登记簿上的权利人往往并不一致,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无适用空间之谈显然站不住脚。其次,先进的域外经验的确是一国法制进步发展的重要资源,但其还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否则只会结出“南橘北枳”之果。我国与德国国情差别明显,受制于我国建国初期房地产分配和“特色”的登记簿规定的历史遗留问题及我国地域之大、调整之难的现实,“照抄”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实非理性之举。因此,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领域井水不犯河水的论调则显得过于绝对。
讨论至此,还需回归到《物权法》第106条之上,笔者之前所言皆是在对《物权法》106条的批判予以回应,似对其持赞许态度。其实不然,对于《物权法》第106条的理解需从两点出发,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物权法》106条之规定,乃立法机关基于国情将善意取得制度扩展至不动产领域的“权宜”之策,但问题在于其并未明确对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的限度,善意取得制度即使能适用于不动产,但也并不意味其在遇到不动产所有权领域的争议皆可适用,其还必须考虑合理限度,并需明确区分与其功能相似的制度。因此,这还需司法机关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进一步明确界定至权利事项的登记错误,方可发挥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交易安全的初始目标。其次,《物权法》106条对于将善意取得制度扩充至不动产领域并非立法之上策,其只是临时的过渡办法,我国未来的立法方向应当是遵从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明确区分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立法模式,只不过我国还需进一步整治和规范我国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之建设,这一艰巨的工程还需法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1]郭志京.善意取得制度的理性基础、作用机制及适用界限[J].政治与法律,2014,(3):14-28.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0.
[3]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8,(10):2-10.
[4]辛正郁.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J].民商辛说,2016,(5):2.
[5]施蒂尔纳·鲍尔.德国民法典(上册)[M].张双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97.
[6]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J].法商研究,2010,(5):74-84.
[7]刘贵祥.论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冲突和协调—以私卖夫妻共有房屋时买受人的保护为中心[J].法学家,2011,(5):99-113.
[8]王泽鉴.债法原理(第2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99.
[9]朱广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J].法学研究,2009,(4):40-61.
[10]孙若军.论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以遏制夫妻共有房屋被一方擅自处分为视角[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3):46-51.
【责任编辑:王 崇】
D923;D922.181
A
1673-7725(2017)04-0172-04
2017-02-15
梁汪洋(1993-),男,安徽合肥人,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猜你喜欢
——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