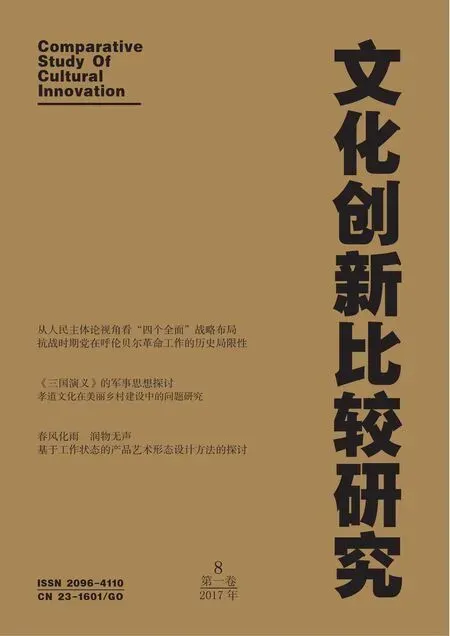踏雪寻梅:基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思考
2017-03-11谢红萍王欣
谢红萍,王欣
(1.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2.山西省侯马市第一中学,山西侯马 043000)
踏雪寻梅:基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思考
谢红萍1,王欣2
(1.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2.山西省侯马市第一中学,山西侯马 043000)
学者刘锡城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第一部学术史。它以“丰富的史料,卓越的史识”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概貌。这部具有拓荒性质的“大度而厚重”的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著作的空白,也为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下,该著作的再版对当下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锡城;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学科建设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旅程,其发展有其历史延续性。而 “从学科建设来说,民间文艺学是由民间文学理论(包括原理体系和方法论)、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学术史三者构成的”[1]。目前,在民间文学理论和民间文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颇丰,在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诸如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民间文艺学原理》,李惠芳的《中国民间文学》,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等著作;在民间文学体裁方面,有袁珂的《神话论文集》,刘守华的《故事学纲要》、《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程蔷的《中国民间传说》,吴超的《中国民歌》,潜明兹的《史诗探幽》,张紫晨的《中国民间小戏》等专著;在民间文学学术史方面,有祁连休、程蔷主编的 《中华民间文学史》,刘锡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十年》等。而民间文学学术史方面,学界却鲜有人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自从刘锡城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2006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该著作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14年12月再版,2015年8月又进行了第2次印刷,足见这本巨著在学界的重要价值,以及社会各界对其的认可程度。《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第一部学术史。它以“丰富的史料,卓越的史识”[2]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概貌。这部具有拓荒性质的“大度而厚重”[3]的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著作的空白,也为民间文学乃至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把握时代脉搏的奠基之作
该著作从唯物史观出发,将民间文学的发展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展现了文化对抗与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的特殊性”[4],它将百年民间文学发展史分为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歌谣运动的兴衰、学术转型时期、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共六个时期,体现了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民间文学是作为激发民族精神的思想工具登上历史舞台的。作为民众心理的集中体现,民间文学对于认识民族心理,进一步改造国民性,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产生萌芽于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运动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早期的启蒙主义者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政治目标的首要任务在于唤醒民众的觉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借助民间文艺作品进行政治宣传、启蒙民众。这一时期,在梁启超、章炳麟、陈独秀等人利用民间文学的各种样式用以“开风气、倡革命”的同时,蒋观云、鲁迅、刘光汉等人还将传统的国学与新兴的西学结合起来对民间文学的体裁进行了溯源探究,进而揭开了研究民间文学的序幕。随后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旨在反帝反封建,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1918年2月由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兴起。这些知识分子纷纷走向民间,认为歌谣能够反映 “国民心声”。可以说,五四时期掀起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热潮,有着唤起平民自觉意识和与民众结为一体的双重作用,这为后来延安时期与建国时期借用民间文学来实现知识分子向劳动群众身份的转换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民间文艺学的政治功能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时期被日益强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向已被歪曲,最终步入歧途,这与五四时期倡导的“到民间去”的意图严重背离。20世纪80年代,在“实事求是”方针的规正与思想解放的宽松环境下,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重新回归五四时期开创的学术传统,沿着“到民间去”的正确方向重返民间。1984年,由文化部、中国民协、国家民委三部委组织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撰工作,包括《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民间文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搜集采录工作,堪称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万里长城建设。近30年来,随着国外相关理论的不断引进,加上中国学者的本土实践,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日益活跃,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纵观民间文学发展的历程,学科建设的每一次推进都伴随着社会转型,是现实社会的产物。同时,该著作也对民间文学学科发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整理,如学科归属问题、学者队伍不稳定、概论思维、运用西方理论教条化等,客观地指出了学科建设有待完善的方向。进入21世纪以来,正当学科发展在上述问题中遭遇窘境、踟躇不前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掀起的热潮再次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带来机遇,使之日渐成为一门显学。21世纪以来,现代化发展的同质性与文化发展的异质性并行不悖,许多民间文学因失去文化土壤而濒临危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为此带来了活力,为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后集成时代对各门类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如何在后非遗时代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的保护与传承,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探索民间文学发展变异的轨迹,都是时代主题赋予当下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显性议题。
2 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石之作
刘锡城在著作中指出,“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上,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5]。”他明确了民间文学兼有文学和民俗的学科性质,而民间文学的这一学科特点既为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养料,也为其在学科体制下的定位带来困扰。
一方面,将民间文学置于文学话语的框架内,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自周代以来受“陈诗以观民风俗”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民间文学被视为平民文化而一直被当作正统文学的对立面,因而作为颠覆正统文学的思想利器,刚健清新的民间文学肩负着推翻陈腐雕琢的贵族文学以实现文学革命的重任。与早期的启蒙主义者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识到民间文艺除了有助于宣扬启蒙思想外,还可以用来实现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为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帷幕。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文学革命”的一次具体实践,它将民间文学的研究推向高潮。之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北大歌谣运动的学者们转而南下。这一时期,随着广州、杭州、厦门、福州等地民俗学会的成立,民间文学研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下,不仅提高了采录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还引进了相关的西方理论著作,拓展了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自此昔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受到瞩目,民间文学研究也开始迈进学术殿堂,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群体创作,与人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一方面以民众自己的立场认识生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与民众生活形态(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可分割,有时甚至就是生活形态本身[6]”。可见,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是与民众的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的,是民众的生活文学,而民俗学的着眼点正是民众的生活世界,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民间文学学科被置于民俗学领域,运用民俗学话语进行表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学科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学科间的疆域被打破,在以问题意识为主导思想的引领之下,“知识共享、方法互用”逐渐成为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潮流。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被置于文学语境中,学术取向上偏重人文学科,而民间文学是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的,应当关注民间文学的生存、发展情境,将它回归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探究其生成、发展与演变的动因与规律,看民众是如何应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看他们是如何面对外部条件进行适宜的选择,进而保持民间文学永久的生命力。对民众生活方式民俗的调查正是为研究民间文学的生存情境提供了语境基础,对民众风俗的田野作业与研究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因此,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取向应从注重文史的人文学科向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领域拓展。
此外,民间文学的双重属性也容易使学界对民间文学学科的认识产生偏差,并在学科体制之中,将其排除在学科目录外。1952年教育部将民间文学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下,是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后,民俗学被置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下,成为与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并列的二级学科,而民间文学只是被包含在民俗学中成为三级学科。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下降,不仅影响了高校课程的具体设立,也使该专业人才在就业问题上遭遇危机,严重制约了该学科的继续发展。如何使民间文学摆脱当下的困境,广大的民俗学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3 强化学科意识的拓荒之作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刘锡城先生在步入古稀之年时的著作,为了了结在民间文学岗位工作四十年的心愿,为这门学科做出点事情,先生不顾年迈,历时三年,躬身耕读,查阅史料,“一件件、一桩桩地翻阅、梳理、阅读、摘抄”。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态度,无不表现了一个民俗学者的情怀和强烈的学科意识。尽管如此,他还谦逊地说,“在步入古稀之年,决心写作这部规模如此之大的、带有拓荒性质的学术著作,实在是件自不量力的事情。”“由于这项研究,犹如开垦一片处女地,学科积累和基础甚是薄弱,有些方面几乎没有前人涉足过,加之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涉及面广,在论述中,时段、人物、学说、体裁等不同领域,可能出现轻重、简繁、详略失当的弊端,评价上也可能出现有欠准确的地方”。同时,他还遗憾地表示,“由于我的研究和写作,始终为个人独立完成,没有助手,借阅资料也颇困难,虽尽力而为,但眼界受限,疏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加上三年来夜以继日工作,到最后已感筋疲力尽,体力难支,故有些章节段落,未能做到完善,只好留待日后继续深入的研究[7]。”
在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百年历程中,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员专业背景多元化,涉及的学科有文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如文学领域的鲁迅、周作人、胡适、茅盾、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何其芳等;历史学领域的董作宾、顾颉刚、杨宽等;哲学领域的容肇祖等;人类学领域的杨成志林惠祥等;民族学领域的芮逸夫等,都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卓有建树。而他们都是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是兴趣使然。所以,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缺乏专业人才,表现出先天不足的劣势。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招收民间文学研究生,一些高校成立了民间文学教研室,民间文学的人才培养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文革时期被一度停滞后,1978年,民间文学又重新回归高校课程,随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民间文学课程。但是至今为止,能招收该专业研究生的高校为数寥寥。再加上就业的压力,也是导致学科队伍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许多专业人才面对就业时的窘境,被迫转向其他领域,致使人才流失严重,由此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缓慢的主观因素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刘锡诚先生坚定的学术信念为每位民俗学人树立了榜样。
4 结语
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学术历程折射出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图景。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尽管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囿于学科体制的束缚和人才匮乏的局限,发展较为缓慢,但广大的民俗学人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秉承学科肩负的社会使命,在这条漫漫其修远的道路上,上下求索。诚然,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艰难之路,但踏雪寻梅,在广大民俗学人的不断探索中,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定会香飘满园,硕果累累。
[1]刘锡城.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991.
[2]李丽丹.丰富的史料,卓越的史识——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J].湖北民族学报,2007(5):157.
[3]高有鹏.一部学术史的大度与厚重——读刘锡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N].文艺报,2007-05-08.
G633.6
A
2096-4110(2017)03(b)-003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