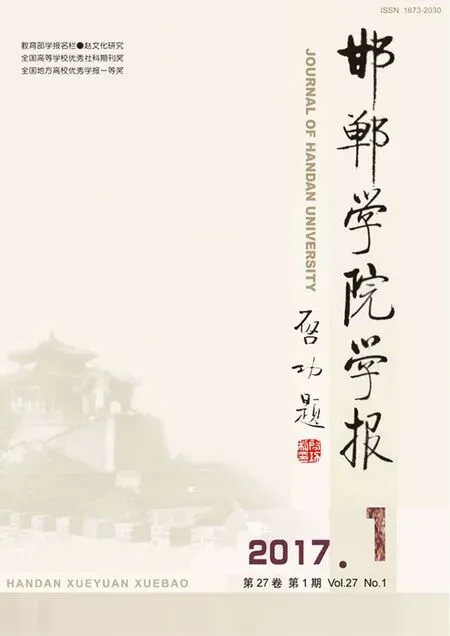论汉代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的发展及其政治功能
2017-03-10甄尽忠
甄尽忠
论汉代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的发展及其政治功能
甄尽忠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46)
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是中国古代星占学分野理论的核心模式,在汉代基本成熟和定型。其主要用途是用来占卜所对应地区的吉凶祸福,尤其是集中在诸侯国的兴衰和国君死亡、战乱、少数民族反叛、讨伐四夷及自然灾害等方面。在刘邦创立汉朝、光武中兴及魏文帝曹丕受禅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充分反映了汉代的宇宙观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十二次;二十八宿;分野;汉代;政治功能
分野学说是中国古代星占学中的重要理论,“占星家把天上的某一部分星宿只与地上的某一地区相应,那个部分星宿中发生的某种变异,指示他相应的地上区域内发生某件大事,这种把天上的星宿对应于地上的区域的分配法,就是所谓分野。”[1]419分野学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至两汉时期基本定型。虽不具有科学性,但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对天地关系的朴素认知,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目前有关汉代星土分野说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星土分野说的起源及分野模式的考证等方面①,而对于其政治功能极少论及。其实,在天人感应思想极其流行的汉代社会,以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为核心内容的星土分野学说首要目的是根据天象变异来占测、比附所对应区域人事的吉凶祸福,即通过“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2]3215,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认真分析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在汉代的发展及其政治功能,对于更好的认识汉代社会的特质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在汉代的发展与定型
分野观念在古代中国来源已久,“可以说是起源于原始时代。”[1]421李勇先生将中国古代的分野模式概括为三种学说八种模式。即干支说,包括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和十二月分野;九宫说,即九宫分野;星土说,包括单星分野、五星分野、北斗分野和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3]22-31。在这八种分野模式中,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是分野体系的核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尤为显著,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对象。
十二次分野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岁星纪年。岁星纪年是中国古代“以木星(即岁星)在十二次中的位置记年的方法。木星约12年行一周天,古人划周天分十二次,将木星每年行经的星次记下,便成了自然的记年资料。”[4]220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最亮的一颗行星,较早地为人们所熟识,经过长期观测,发现它约12年(现代测定为11.86年)运行一周天,古人将木星运动的周天路线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次,自西向东依次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和析木,以次来记年,故木星又称岁星。
《周礼·春官·保章氏》载:“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星土”,郑玄注:“星所主土也。封,犹界也。”“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今其存可信者,十二次也。”[5]819“分星”,就是地域分野所主之星。
十二次分野说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有关该方面的书籍虽然在郑玄时代已经亡佚,但仍可从有关文献中得到印证。《国语·周语下》载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伶州鸠论律时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岁在鹑火”,韦昭注:“岁,岁星也。鹑火,次名,周分野也。从柳九度至张十七度为鹑火。”“岁之所在”,韦昭注:“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6]86多数学者认为伶州鸠这段话是根据岁星纪年法推算而得的,或认为是后人加入的。
但根据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利簋”铭文,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旜公宝尊彝。
“岁鼎”,张政烺释读为:“岁,岁星,即木星。鼎,读丁,义即当。”“‘岁鼎’,意谓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商国。”[7]58-59
张政烺先生的释读得到徐中舒、戚桂宴、马承源、黄怀信等先生的认同①。据此,伶州鸠之说是有一定史实依据的,基本上是可信的。由此推算,十二次分野说的源头可上溯至商周之际。钱宝琮先生指出:“除鹑首、鹑尾、寿星、析木四次外,其八次之名俱见《左氏传》,确系春秋时代之天文家言,其名义及分野可得而详也。”[8]337其实,析木之次曾出现在《左传·昭公八年》,史赵对晋平公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9]1305鹑尾、寿星二次虽未见于《左传》,但在《国语》中亦有提及,《国语·晋语四》载子犯曰:“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6]222
秦汉大一统之后,二十八宿分野成为秦汉时期及其以后较为流行和占主导地位的分野模式。《银雀山汉墓竹简·占书》《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都是以二十八宿配封国和州,而不用十二次名目。只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将二者部分地融合在一起。
二十八宿,或称二十八舍、二十八星,名称在文献中始见于《周礼·春官》“冯相氏”一职:“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5]818《周礼·考工记》“辀人”云:“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5]914《吕氏春秋·圆道》亦云:“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10]1721977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公元前433年)出土的圆拱形漆盖上,“盖顶中央绘有一个篆书大斗字,象征北斗。绕斗字篆书二十八宿全部名称,两边配画青龙、白虎图象。”[11]66这是迄今关于二十八宿之名的最早发现,也说明二十八宿体系最迟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就已形成。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亦列出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并按方位进行排列和划分:
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
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
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
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
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
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参、东井;
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
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10]657-658
《银雀山汉墓竹简·占书》和《淮南子·天文训》是将二十八宿与先秦时期的诸侯国相对应:
《占书》:
角、亢、抵(氐):郑
房、心、尾:巍(魏)
箕、斗: □
牵牛、婺女:□
虚、危:□
营室、东壁:□
奎、娄女、胃:鲁
昴、毕、觜巂、参:□
东井、舆鬼:秦
柳、七星、□:周
翼、轸:楚[12]242
《淮南子·天文训》:
角、亢:郑
氐、房、心:宋
尾、箕:燕
斗、牵牛:越
须女:吴
虚、危:齐
营室、东壁:卫
奎、娄:鲁
胃、昴、毕:魏
觜嶲、参:赵
东井、舆鬼:秦
柳、七星、张:周
翼、轸:楚[13]166
将二十八宿与封国相对应,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吕氏春秋·制乐》篇载,宋景公时,出现“荧惑守心”这一极凶天象。宋景公甚为恐惧,就咨询当时著名的星占家子韦:“荧惑在心,何也?”子韦回答说:“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10]347-348已将心宿视为宋国的分星。《占书》残简只能看到6个古国的分野,从上下文来看,是11国的分野,这应是战国时期最初的分野模式。《淮南子·天文训》的13国分野与《占书》略有参差,显然是对这一分野模式的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同时也反映出西汉初年,去战国不久,先秦时期的封国畛域观念仍然浸润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是将二十八宿与州相对应,这既是对先秦时期九州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秦皇、汉武拓地开疆的反映。”[14]573可以说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局面在地理格局上的体现。
二书的对应模式完全相同,分别是:
角、亢、氐,兖州。
房、心,豫州。
尾、箕,幽州。
斗,江、湖。
牵牛、婺女,杨州。
虚、危,青州。
营室至东壁,并州。
奎、娄、胃,徐州。
昴、毕,冀州。
觜觿、参,益州。
东井、舆鬼,雍州。
柳、七星、张,三河。
翼、轸,荆州。[15]1330
《汉书·地理志》将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分野模式进行部分的整合。该部分是辑录刘向的《域(地)分》和朱干的《风俗》,说明在西汉后期已将二者合而为一。但该篇只列出四个具体地区的分星、度数与对应的次分,分别是:“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也。”“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也。……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也。”“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自东井六度至亢六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野,与韩同分。”“燕地,尾、箕分野也。……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16]1641-1659
至东汉末年蔡邕在《月令章句》中将二者完全融合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确的分野体系。其对应模式为:
自危十度至壁(八)[九]度,谓之豕韦之次,卫之分野。
自壁(八)[九]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鲁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毕六度,谓之大梁之次,赵之分野。
自毕六度至井十度,谓之实沈之次,晋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鹑首之次,秦之分野。
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鹑火之次,周之分野。
自张十二度至轸六度,谓之鹑尾之次,楚之分野。
自轸六度至亢八度,谓之寿星之次,郑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谓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须女二度,谓之星纪之次,越之分野。
自须女二度至危十度,谓之玄枵之次,齐之分野。[2]3080-3081
蔡邕的分星次度数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有所不同①。《帝王世纪》成书于魏晋之时,在此不作讨论。
二、汉代的分野占验与事应
《后汉书·苏竟传》载苏竟曰:“盖灾不徒设,皆应之分野,各有所主。”[2]1044分野理论完全是因为占星术的需要而存在的,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根据天象变异来占测所对应地域的吉凶祸福。汉代的分野占验主要保存在《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后汉书》的“天文志”中,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天文星占家的占卜和预言,又以诸侯国兴衰及国君死亡、战乱、少数民族反叛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事应”,不仅直接提供了汉代分野占测的资料和讯息,同时也反映出汉代社会“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一)诸侯国兴衰或国君死亡
这是分野占测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星占家最为关注的内容。
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癸酉,金星、水星相合于婺女。占辞曰:“为变谋,为兵忧。婺女,粤也,又为齐。”七月乙丑,金、木、水三星又合于张,占辞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张,周地,今之河南也,又为楚。”次年七月丙子,“火与水晨出东方,因守斗。”占辞曰:“其国绝祀。”根据分野,斗所对应的地区为吴,“又为粤。”[16]1303这一系列的天象变化预示着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等七国叛乱,后被大将军周亚夫率军平定。吴王刘濞败逃至越,为越人所杀。楚王、赵王、胶西王皆自杀。胶东、淄川、济南三王被诛。齐王一度与叛兵议和,在七国之乱平定后,亦畏罪惧诛自杀。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四月乙巳,水、火二星合于参宿,占辞曰:“国不吉。参,梁也。”[16]1305次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阳王、济阴王死。
汉武帝元鼎中,“荧惑守南斗”。荧惑(火星)是一颗著名的灾星,其占辞多与叛乱、残贼、疾、丧、饥荒、战争相连。①古代占星家认为,荧惑守哪一颗星宿,就会对该星宿所主的分野地区或该星宿所对应的人不利。对于此次天象,占辞曰:“荧惑所守,为乱贼丧兵;守之久,其国绝祀。南斗,越分也。”南斗为越之分野,其后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攻杀南越王、太后及汉使,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任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分兵四路进攻南越,杀掉吕嘉,“灭其国。”[16]1306
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七月壬子,月犯心宿,占辞曰:“其国有忧,若有大丧。房、心为宋,今楚地。”[16]1310十一月,楚王刘友薨。
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牵牛,长八尺,历建星至房南,灭见至五十日。”牵牛的分野为吴、越,房、心的分野为宋,“后广陵王荆与沈凉,楚王英与颜忠各谋逆,事觉,皆自杀。”[2]3230刘荆的封地广陵属吴,楚王刘英的封地在彭城,先秦时期属宋国。
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十月,岁星、荧惑、太白三星合于虚,“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为丧。虚,齐(也)[地]。”[2]3259次年,琅邪王刘据薨。
分野说在占测方面以凶居多,只有极个别事应是关于立国的。如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填星在娄宿,还居奎宿。奎宿的分野为鲁,占辞曰:“其国得地为得填。”[16]1304该年鲁国国立。《汉书·景十三王传》载,鲁恭王刘馀于汉景帝前元二年被封为淮阳王,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徙封为鲁王。
(二)战争和地方叛乱
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轸。且灭时,分为十余,如遗火状。”柳宿于分野为周,轸宿为秦和蜀,“大流星出柳入轸者,是大使从周入蜀。”该星象预示的是此时光武帝派大司马吴汉率兵三万从南阳乘船溯江而上,讨伐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同时“又命将军马武、刘尚、郭霸、岑彭、冯骏平武都、巴郡。”[2]3220
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年)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气长二尺余,西南指,色苍白,在牵牛六度。”据汉代星占理论,“客星芒气白为兵。”牵牛于分野主吴、越,预示着该地区将要发生战乱。后一年,“会稽海贼曾于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扬州六郡逆贼章何等称将军,犯四十九县,大攻略吏民。”[2]3244永和二年(137年)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南斗于分野为吴,次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拒守并杀掉羊珍等人。同年,九江蔡伯流等数百人攻打广陵、九江,杀死江都长。永和四年(139年)七月壬午,“荧惑入南斗犯第三星。”南斗于分野为扬州,“荧惑犯入之为兵丧。”永和六年(141年),九江、丹阳周生、马勉等起义,“攻没郡县。”[2]3246
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十月,荧惑入犯南斗中,占辞曰:“荧惑所守为兵乱。”南斗分野为吴,十一月,会稽人许昭聚众起义,自称大将军,“攻破郡县。”[2]3258光和三年(180年)冬,“彗星出狼、弧,东行至于张乃去。”张于分野为周地,时指东汉的都城洛阳,后四年,黄巾起义爆发,“京都大发兵击黄巾贼。”[2]3259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十月,“有星孛于大梁”,“大梁”的分野于先秦为赵国,时为冀州。十一月,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于建安七年夺取冀州。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2]3261鹑尾的分野于先秦为楚国,时为荆州。次年秋,荆州刺史刘表卒,其子刘琮继立,曹操征伐荆州,刘琮投降。
(三)少数民族反叛或讨伐四夷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辞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16]1304该年汉高祖亲自带兵32万迎击匈奴,结果在平城白登山陷入冒顿单于的重围,受困七天,经贿赂匈奴阏氏乃得以突围。平城位于先秦赵国。
按分野说本来只限于传统的华夏区域,并不含周边少数民族。《史记·天官书》曰:“昴曰髦头,胡星也。”为西北方少数民族之星。又曰:“昴、毕间为天街。”正义曰:“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15]1305-1306为北方少数民族和华夏民族在天上的分界线,故在此占测为匈奴。
汉元帝元初五年(公元前44年)四月,彗星出现在西北,“赤黄色,长八尺所,后数日长丈余,东北指,在参分。”参宿于分野主益州,后二年,“西羌反。”[16]1309西羌当时主要分布在四川、青海、甘肃一带。
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正月,“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轩辕右角稍灭。”“昴主边兵”,又主匈奴,后一年,东汉王朝派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耿忠、开阳城门候秦彭、太仆祭肜等率兵攻打匈奴。永平十六年(73年)四月,“太白犯毕。毕为边兵。”[2]3231毕宿于分野为冀州地区,后北匈奴侵犯边境,进入云中,直至渔阳。
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长二尺所,稍行入牵牛三度,积四十日稍灭。”[2]3231—3232
太白(金星)在星占学中是一颗罚星,《史记·天官书》曰:“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15]1322其占辞以兵事和杀伐为主,太白在昴“为边兵”。彗星也是一颗著名的灾星、妖星,其出现多与战乱相连。《荆州占》曰:“彗星出,必有反者,兵大起,必有乱亡。”[17]882彗星出现在天市垣“为外兵”,牵牛于分野为吴、越,“是时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蕉)[嶲]唐城。永昌太守王寻走奔楪榆,安夷长宋延为羌所杀。”[2]3232《史记·大宛列传》正义注:“其西南滇越、越巂则通号越,细分而有巂、滇等名也。”[15]3167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四月,“有流星起斗,东北行到须女。”须女,于分野为燕地,该年,“辽东貊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2]3237-3238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八月,“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东井、弧皆秦地。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2]3238弧星虽不在二十八宿之内,但《史记·天官书》云:“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正义曰:“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15]1346所以也是占测秦地吉凶的重要星宿。
《后汉书·马融传》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时任武都太守的马融在上疏中根据星象观测指出:“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建议朝廷及早加强西北地区的边防军备。不久,“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2]1971
此外,还预测分野地区的自然灾害。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五月壬午,火星、金星“合于舆鬼之东北,不至柳,出舆鬼北可五寸。”占辞曰:“为铄,有丧。舆鬼,秦也。”丙戌日,“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16]1305虽然没有指出具体的地域,但《史记·孝景本纪》载:“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15]447据《汉书·地理志上》,上庸属汉中郡,为先秦秦国的分野范围。
三、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在汉代皇权政治中的运用
董仲舒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18]286“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18]319按照天人感应学说,帝王(尤其是开国帝王)都是应运而生的真命天子,拥有“受命之符”,非人力所能强求。班彪在《王命论》中曰:“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16]4209“受命之符”包括各种所谓的祯祥嘉瑞。分野学说是为占卜服务的,而预测军国大事尤其是王朝更迭则是其最为重要也是最受关注的内容。为帝王提供受命于天的天象依据和证明,增强皇权的神圣性、权威性和合法性,以此来主导舆论、凝聚人心、巩固统治,是包括分野学说在内的星占学的首要目的,也是受到统治者和社会各个阶层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
在两汉时期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进程中,十二次及二十八宿分野模式的政治功能被得以充分的发挥,成为各派政治势力都争相使用的神学工具。
(一)“五星聚于东井”与刘邦建汉
《汉书·高帝纪上》载,汉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16]22《汉书·天文志》又载:“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侯。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崇义,东井为秦之地明效也。”[16]1301-1302
对于此次“五星聚于东井”天象,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经过回推当时的天象,“发现在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根本不聚在一块。而在高祖二年四、五月间(公元前205年5月11日至6月15日),则确曾发生一次颇为接近该叙述的天象。”[19]64张健先生经过用现代天文计算也表明,在天气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肉眼能看到这一天象只有在“公元前205年5到6月间(即汉高祖二年四月前后)”,“汉高祖元年十月(公元前207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并没有五星会聚的天象,只有土星逆行在井宿中。”[20]184-197
对于此次天象,《史记·天官书》只是略记为“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15]1348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时间。那么,班固和续写《汉书·天文志》的马续为什么都刻意将这一罕见的天文奇观记在汉高祖元年十月西入咸阳之时呢?其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为秦灭汉兴提供天象依据,是刘邦将获得天下的“天命之符”。
第一,“五星会聚”是“中国星占学上最吉的天象。”[19]49是难得的天文祥瑞,具有圣人降世、改朝换代等重大的星占意义。《史记·天官书》曰:“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15]1321《海中占》的占辞与《天官书》同:“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荆州占》亦曰:“五星合于一舍,其国主应缩,有德者昌。”[17]199
第二,《汉书·天文志》又专门强调:“以历推之,从岁星也。”即其他四星皆从岁星(木星),以进一步加强汉高祖刘邦获取天下的正当性。岁星在星占学中是一颗吉祥之星、仁义之星。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载:“岁星所久处者有卿(庆)。”[21]177《史记·天官书》曰:“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15]1312《春秋合诚图》曰:“岁星主含德。”[17]223五星会聚本已是难得的吉兆,今又皆从岁星,更是吉中之吉,说明汉高祖非徒靠武力而是凭借仁德和义举获得天下。《宋书·符瑞志》在记载此事时指出:“高帝为沛公,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岁星先至,而四星从之。占曰:‘以义取天下。’”[22]767
第三,五星会聚的星宿为东井。东井是秦国分野的主星,汉高祖元年十月,刘邦率军先入关中,驻军霸上,秦王子婴投降,这一重大的吉兆只能是应验到刘邦身上。所以《史记·张耳传》记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15]2581
(二)“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与光武中兴
《后汉书·郅恽传》载,地皇元年(20年),各地反莽起义不断爆发,精通天文历数的郅恽对友人说:“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2]1024
司马彪在《后汉书·天文志上》中亦有一则关于星象的史料: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2]3218
这两则有关星象的材料虽然时间、内容各不相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从天文星象的角度来论证光武帝刘秀光复汉祚是天命所归,早有兆示。
第一,这两次星象都是发生在翼、轸之域,而翼、轸二宿的地理分野是楚。后刘秀起兵舂陵,转战南阳,都属楚地,与星象契合,说明刘秀起兵是顺天应人的举动,从而为刘秀集团自一开始就笼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
第二,郅恽指出:“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分翼、轸之域。”《汉书·天文志》曰:“三星若合,是谓惊立绝行,其国外内有兵与丧,民人乏饥,改立王公。”[16]1287五大行星三三组合,有八种组合方式,其占辞都是兵丧和改立王公。如《汉书·天文志》载: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7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于东井。占曰:‘外内有兵与丧,改立王公。东井,秦也。’……是岁诛反者周殷长安市。”[16]1303
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岁星、荧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谓警位,是谓绝行,内外有兵丧,改立王公。’其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歆大逆不道,牂柯太守立捕杀歆。”[16]1310
对于地皇元年这次三星相合的星象,兵丧是针对王莽而言,后郅恽还西至长安,劝说王莽还政刘氏,“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2]1025
“改立王公”指刘秀而言,此当引申为改立天子。《荆州占》曰:“三星合于一舍,其国可复,修德者强,无德者受殃。”[17]203据此占辞,三星合于“汉分”,则预示着汉朝将再次复兴,即“必再受命”。刘秀出生、起兵皆在南阳,即“汉分”,当然是应验此次星象的不二人选。
第三,“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星孛(即彗星)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中为除旧布新的象征。《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鲁国大夫早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9]1390汉文帝前元八年(公元前172年),“有长星出于东方。”注引文颖曰:“大法,孛、彗星多为除旧布新。”[16]122同时也是改朝换代和战乱的征兆。刘向《鸿范传》曰:“彗星者,天所以去无道而建有德也。”《黄帝占》曰:“彗扫同形,长短有差,殃灾如一,见则扫除凶秽,必有灭国,臣弑其君,大兵起,国易政,无道之君当之。”[17]879-881预示着旧王朝灭亡和新王朝的建立。
此次彗星先出现在张宿,又东南行至翼、轸之分。张于分野为周,即周、楚地区将发生战乱,为光武帝起兵南阳、定都洛阳的天象预兆。光武帝“复都洛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2]3218洛阳,于分野属于周之分域。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曰”指出:“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2]86这两则天象资料,都集中于光武帝刘秀一身,这就进一步加深对刘秀“于赫有命”、受命中兴的神化色彩。
(三)“岁星在大梁”与魏文帝曹丕受禅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太史丞许芝为劝进曹丕废汉称帝,在罗列一系列的祥瑞、谶语符命之后,又说:
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23]65
这是从分野说的角度说明“皇天将舍旧而命新”,汉室气数已尽,曹魏当获天命。按此时曹丕尚未称帝,许芝还是东汉献帝时的太史丞。该论所据的是汉代的十二次分野说。
许芝说:“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查看汉代的分野资料,多数天文星占学家是将大梁的分野划为赵地,且十二次分野所对应的封国中也没有提到魏国。但《淮南子·天文训》提到:“胃、昴、毕,魏。”[13]166《尔雅·释天》曰:“大梁,昴也。”[24]405而且一提到大梁星次,人们首先就会联想到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大梁,“很显然,大梁星次之名源于胃昴毕配属魏的分野观念。”[25]76-80
随后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在上表中又详细阐述道:
天有十二次以为分野,王公之国,各有所属,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岁星行历十二次国,天子受命,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岁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故《春秋传》曰:“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武王始受命,(为))[于]时将讨黄巾。是岁改年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23]70
苏林、董巴所用的分野理论及星象与许芝完全相同。主旨都是为曹丕受禅制造舆论,论证曹魏代汉“符瑞著明”,与文王受命、武王伐纣一样有“受命易姓之符”,是皇天之意,万民所望。
除以上这三则典型的天象事例之外,分野说在汉代政治运作中的事件还有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十月,“客星从紫宫西行至昴为赵。”后一年,汉和帝驾崩,刚满百日的汉殇帝即位不到一年又夭折。邓太后遣使者迎请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皇帝,即汉安帝。“清河,赵地也。”[2]3237《后汉书·方术列传·董扶传》载,东汉末年,董扶私下对太常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2]2734刘焉信以为真,遂谋求出为益州牧。但最后却应验到刘备身上。
总之,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分野模式及其理论体系在汉代已基本成熟和定型,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其后西晋时期的“陈卓分野”、北周庾季才的《灵台秘苑》、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撰写《晋书·天文志》《乙巳占》提到的“十二次度数”和“州郡躔次”及瞿昙悉达编辑的《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分野略例》等都是对汉代分野模式的沿承、增补和进一步完善。不仅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极其特殊的作用,而且渗透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处,在其后王朝嬗替、争夺正统和权力角逐的过程中被不断拿出来运用,成为皇权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天文因素。
[1]陈遵妫. 中国天文学史:第2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李勇. 对中国古代恒星分野和分野式盘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1).
[4]徐振韬. 中国古代天文学词典[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5]郑玄注,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韦昭注. 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张政烺. 《利簋》释文[J]. 考古,1978(1).
[8]钱宝琮. 论二十八宿之来历[A]. 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9]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陈奇猷校释. 吕氏春秋校释[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11]谭维四. 曾侯乙墓[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3]赵宗乙. 淮南子译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4]顾颉刚. 州与岳的演变[M]//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5]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瞿昙悉达. 开元占经[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8]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钟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
[19]黄一农. 社会天文学史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0]张健. 中国汉代记载的五星运动精度考查[J]. 天文学报,2010(2).
[21]席泽宗. 《五星占》释文和注解[M]//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2]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4]管锡华译注. 尔雅[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5]李维宝,陈久金. 论中国十二星次名称的含义和来历[J]. 天文研究与技术,2009(1).
(责任编辑:李俊丹 校对:苏红霞)
①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十二章《分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25页;李勇:《对中国古代恒星分野和分野式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22—31页;崔振法:《分野说探源》,见陈美东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6页;(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307页;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第三章《恒星与分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224页;陈久金:《中国十二星次、二十八宿星名含义的系统解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81-395页。
①徐仲舒认为:“岁是岁星。”“武王伐纣而必以甲子朝至于商郊,可能还是采纳占星家的建议。”戚桂宴认为:“‘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见《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1978年第6期,第77-84页。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完全采用张政烺的观点:“岁鼎,岁星当前。是说征商的时间与岁星照临的位置相当。”“鼎,与当同义。这是说武王征商的时间与岁星运行的位置相合。”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黄怀信认为:“关于‘岁鼎’的诸说中,惟有以‘岁’为岁星之说可以相信。”“‘鼎’,应当读为‘中’”,“所谓‘岁鼎(中)’,就是岁星中天。”见黄怀信:《利簋铭文再认识》,《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59-162页。
①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的分星次度数详见《后汉书》志十九《郡国志一》,第3385-3386页。
①《史记·天官书》曰:“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第1317页。
The Development ofPattern of Twelve Star Orders and Twenty-Eight Mansions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s in the Han Dynasty
ZHEN Jin-zhong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 Zhengzhou, 450046, China)
Theof Twelve Star Orders and Twenty-Eight Mansions was the core pattern intheory of Chinese ancient astrology, this pattern had formed basically in the Han dynasty. It was used mainly to divine the good and bad luck,fortune and misfortune with corresponding regions, particularly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and the death of duke,war,the rebel of minority and crusading against minority, and natural disaster,etc. Thepattern played extremely unique role in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Liu Bang established the Han dynasty, Guang-Wu(光武)restoration, Emperor Wei Wen(魏文帝) Cao Pi accepted demise. Thepattern had fully reflected the cosmic viewpoint and the idea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kind”in the Han dynasty.
Twelve Star Orders; Twenty-Eight Mansions;The Han Dynasty; Political Functions
K234
A
1673-2030(2017)01-0068-09
2017-03-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星占学与汉代社会研究”,项目批准号:15YJA770023
甄尽忠(1968—),男,河南封丘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