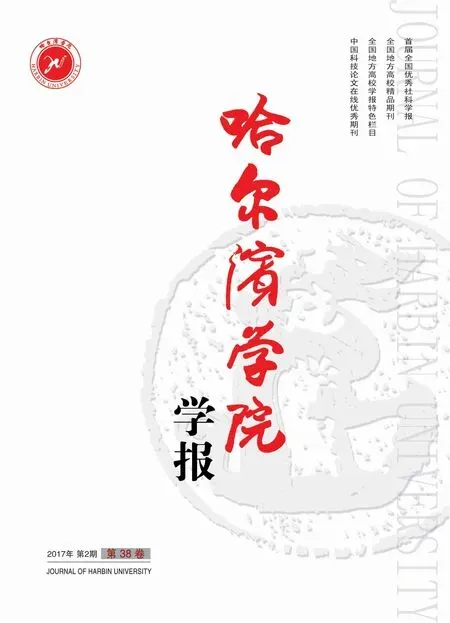论《消散》和《最蓝的眼睛》中精神殖民的异同
2017-03-10胡宗锋
刘 晶,胡宗锋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论《消散》和《最蓝的眼睛》中精神殖民的异同
刘 晶,胡宗锋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戴维·达比丁的《消散》记述了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和英国房东卢瑟福太太的对话,从中折射出殖民统治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带来的巨大影响。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渴望拥有白人的蓝眼睛的悲剧故事,展现了殖民统治对被殖民的黑人造成的精神伤害。现有研究多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最蓝的眼睛》,但是鲜有对《消散》的研究,更没有对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虽然《消散》和《最蓝的眼睛》都是叙述精神殖民的影响,但是它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文章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中体现的精神殖民的异同,旨在探究作品中蕴含的后殖民主题。
《消散》;《最蓝的眼睛》;精神殖民;后殖民主题
《消散》(Disappearance)是圭亚那作家戴维·达比丁(David Dabydeen)的长篇小说,它叙述了发生于1966年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故事。1966年,圭亚那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生长于圭亚那独立后的新世界。从小接受的英国式教育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诩为“工程师”的他随后去英国的顿斯米尔村庄进行海域工事的建设,在此期间,与白人房东卢瑟福太太的交谈改变了他对自身和对英国的认知。殖民统治带给黑人男主人公和白人卢瑟福太太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殖民统治早已结束,但是“精神殖民”和“殖民后遗症”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中篇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剧命运。20世纪40年代,新婚的波琳和乔利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俄亥俄州的洛兰镇。然而,这个北方的小镇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期望的幸福。相反,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在这里随处可见,以白为美的审美观深深地“毒害”着黑人。佩科拉就深受其害,扭曲的审美令她日夜期盼得到一双蓝眼睛,最后却陷入疯癫。虽然在故事发生的年代,美国白人对黑人的“内部殖民”早已结束,法律上明令禁止种族歧视,但是白人殖民者对黑人被殖民者的“精神殖民”依旧存在,对黑人造成的精神戕害也从未真正停歇。
《消散》和《最蓝的眼睛》都反映了殖民统治结束后,“精神殖民”对人们的侵害,都彰显了后殖民主题,但是它们体现的精神殖民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笔者首先从文化霸权对黑人的戕害,“他者”地位与“白化”两个方面分析两部小说反映的精神殖民的相同之处。其次,从两部小说对精神殖民的不同的剖析角度,传统对于黑人的重要性以及塑造的不同的白人形象三个侧面探讨它们反映的后殖民主题的不同之处。旨在剖析精神殖民在两部小说中的异同。
一、《消散》和《最蓝的眼睛》的相同之处
(一)文化霸权对被殖民者的戕害
“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起初由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在“文化霸权”理论中,“霸权”实指一种“领导权”。[1](P38)在圭亚那和美国社会中,白人统治者依靠政治和经济的霸权地位,在文化领域依旧具有领导权和话语权。白人殖民者大肆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对黑人被殖民者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消散》和《最蓝的眼睛》都反映了在白人殖民者的文化霸权控制下,黑人被殖民者的艰难生存环境。
1.传媒对被殖民者的冲击
殖民者是大众传媒的主导力量,把持着大众传媒的价值导向。被殖民者从殖民者操控的传媒中获取相关的信息,因此被殖民者的观念很容易受到各种传媒的冲击和影响。殖民者通过大众传媒来宣扬主流观点,从而实现对被殖民者的“精神殖民”。
《消散》中,男主人公由于在独立后的圭亚那长大,对自己民族的奴隶领袖古菲其人和事迹所知甚少。圭亚那的传媒完全被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所控制,“我们对其身世了解不多,而且是从英国人的杂志中看到的”。[2](P17)对本民族的英雄人物的了解都是通过殖民者的传媒报道,可想而知,大英帝国对圭亚那的大众传媒的控制程度。通过殖民者的视角来了解自己种族的历史,这无疑十分有害。其次,殖民者通过操控大众传媒来传播自己的文明,灌输自己的价值观。《消散》中的男主人公是“读着英国故事书长大的”,[2](P89)而故事书中描绘的是英国国泰民安,人人幸福安乐的场面。其实,英国的社会同许多社会一样,同样也有“黑暗”和“疾病”,但是英国的书中大力鼓吹殖民者幸福安乐的生活,散布英国人的价值观,这对被殖民的黑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男主人公受其影响开始崇拜英国人的美好生活,认为英国绅士都是谦虚稳重的,认为本族同胞“爱吵闹,喜吹牛;警察承诺多,兑现少”。[2](P89)大英帝国的殖民者对书籍、杂志等大众传媒的操控左右了殖民地人们的价值观和对自身的判断,成功地对被殖民者实行“精神殖民”。
《最蓝的眼睛》中,美国白人也同样牢牢地掌控着大众传媒,宣扬白人殖民者高贵美丽而黑人低贱丑陋的审美观念。大众传媒传播着白人价值观,建构了白人神话。以白为美成为主流审美观,迫使黑人承认自己的丑陋,不断地进行自我厌恶和自我歧视。小说中,波琳就深受电影这一大众传媒的毒害。初到美国北部生活之时,波琳受到周围黑人女性的种种歧视,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在电影中找到了自我安慰。电影中的白人男性对自己的妻子百般体贴,他们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电影对白人家庭的童话般的描述给波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她在看电影时既感到了莫大的欢乐,也对现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厌恶。电影场景和现实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致使波琳更加厌恶自己的丈夫和黑孩子。正如K·苏·朱尔(K.Sue Jewel)所言:“在维护种族划分的社会阶级结构上,大众传媒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们是意识形态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在像美国这样技术发达的社会中,主要是通过大众的认同来形成一个不平等体系,获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3](P33)因此殖民者借由大众传媒之手,对被殖民者造成冲击,以此来实行“精神殖民”,影响被殖民者的价值判断。
2.教育对被殖民者的洗脑
学校教育是殖民者传播价值观,对被殖民者进行洗脑和实现“精神殖民”的又一途径。《消散》中的男主人公是典型的英式教育的产物。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人民的教育中宣扬的是和平安乐的英国社会,完全抹去了对圭亚那历史的教育,致使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对本族的历史全然不知,盲目地崇拜英国人的教养和生活。英式的教育美化了殖民者对殖民地入侵的这一史实,将其称为对未开化的殖民地带来光明和文明的举措。英式教育把男主人公变成一位有着黑人躯体和白人思想的人,把他对白人殖民者的“所有恐惧和憎恨都掩藏起来了”。[2](P114)殖民者的教育为被殖民者成功洗脑,不仅意识不到殖民者给其带来的巨大侵害,而且一味地标榜殖民者,自己又陷入自我厌恶的境地。《最蓝的眼睛》也反映了这一令人痛惜的现实。美国学校小学课本的第一课是《迪克和简》,课本呈现的是美国白人家庭的幸福美满生活,这对黑人学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得黑人学生无比向往白人小孩的美好生活,而对现实生活心生不满,造成他们自卑自怜的心理。“教育的作用就是压制它的这些牺牲品,并教导他们通过内化指令性的审美标准来压抑黑色的自我。……开场的序言告诉我们,通过阅读一个简单易懂的课文,就可以教会黑人女孩们如何进行自我压抑。”[4](P160)由此可见,被殖民者被教育洗脑,盲目尊崇殖民者的文化和价值观,轻视本族的文明,这无疑是可悲的。
3.宗教对被殖民者的奴化
宗教不但在白人殖民者的文化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殖民统治时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宗教用于麻痹被殖民者的精神,使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死后进入天国,而不是对现状的反抗,宗教进一步奴化了被殖民者的精神和意志。
《消散》中,大英帝国的殖民者在殖民统治的同时,将自己的宗教带入了圭亚那。“在传教士带着印有陌生文字的《圣经》来了以后,他们弑杀了非洲神”,[2](P12)自此之后,非洲古老的宗教文明遭到破坏,殖民者运用基督教来控制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奴化他们的思想,泯灭他们内心深处的反抗意志,以至于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顺时,第一反应不是通过反抗来改变现状,而是怀疑“(上帝)很早就遗弃了我们这一块土地,出国或是回英国去了”。[2](P70)这样一来宗教就成了奴化被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的有效手段。
此外,在美国社会中,宗教还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沟通。教堂成为人们彼此联系,互相交流的场所。《最蓝的眼睛》中,波琳为了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同,试图通过“去教堂”[5](P133)来融入白人社会,并以此来“与那些曾经瞧不起她的女人分庭抗礼,而且比她们更有道德”。[5](P133)由此便可以看出宗教对黑人被殖民者的重大影响。
(二)“他者”地位与“白化”
“他者”的概念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西方人称自己为主体性的“自我”,而把西方以外的世界统统视为“他者”。《消散》和《最蓝的眼睛》这两部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被殖民的黑人“他者”地位,以及黑人为融入白人社会而不断地消除自己的黑人特征,“白化”自己的种种行为。
1.自卑和自我厌恶的“他者”
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的影响,被殖民者都会产生自卑和自我厌恶的心理。《消散》中,年轻的工程师在圭亚那修筑海坝时,工人们都觉得这项工程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没有自信,不敢相信……我们也可以办成事”,[2](P135)从中可以看出被殖民者的自卑心理。《最蓝的眼睛》中,波琳受到白人主流审美的影响,渐渐地开始厌恶自己的黑躯体,厌恶黑人丈夫和自己的黑孩子。而佩科拉在学校受到老师同学的各种冷潮热讽,迫切地需要一双蓝眼睛,其实也是她身为黑人自卑的体现。
2.企图“漂白”自己的“他者”
被殖民者为了摆脱“他者”的身份,不惜采取各种方式“漂白”自己。《消散》中,年轻的圭亚那工程师从小受到英国文明的浸染,除了身体方面具有黑人的特征外,其他方面更像是一个英国人。他头脑中装的是英国的工程学,每天都在忙于思考如何筑海坝的问题,他“拥有的一切是白人的思想和白人科学的陷阱,对其他的一无所知”。[2](P40)他通过不停的“漂白”自己,讲地道的英语,期望借此摆脱“他者”的地位。然而,正如卢瑟福太太所说的那样,他“毕竟在精神上仍是一个非洲人”。[2](P115)长期的殖民统治造就的“他者”身份并不可能轻易摆脱,男主人公“漂白”自己,最终使自己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者创造的“一个拥有白人灵魂的黑人”。[2](P115)
《最蓝的眼睛》中,肤色较浅的有色人种杰拉尔丁为了不沦为“黑鬼”,时刻警惕着。她不停地“漂白”自己,希望融入白人社会,并竭力与同样处于“他者”地位的黑人同胞划清界限。她在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着《圣经》,像白人一样保持着整洁,就是为了显示她与肮脏、懒惰的黑人不同。她让理发师把儿子朱尼尔的“头发剪得贴近头皮,免得让人联想到黑人的卷毛”。[5](P94)一到冬天,她就会给朱尼尔的“脸上涂上杰根斯乳液,让肤色不至于变成灰白”。[5](P94)虽然他们的肤色较浅,但是一到冬天还是会跟黑人一样,肤色变成灰白色,而有色人种本来就和黑人区分的不是太过明显,所以必须避免沦为黑人,而是要“漂白”自己,向白人靠拢。
二、《消散》和《最蓝的眼睛》的不同之处
(一)从不同的角度剖析精神殖民的毒害
虽然《消散》和《最蓝的眼睛》都反映了后殖民的主题,但是两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精神殖民的残害。《最蓝的眼睛》从被殖民者的角度反映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对黑人的身心造成的种种危害,也展现了“精神殖民”给黑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小说中,白人的审美观深深地毒害着黑人群体。佩科拉将自己在学校不受欢迎,在家里得不到母亲疼爱的根源归结于自己没有一双蓝眼睛,最终不堪生活的重压疯了,致使她整日幻想自己有一双全世界最蓝的眼睛。这种“精神殖民”对被殖民者而言是致命的。波琳也深受其害。她全然不顾自己的家庭,以在白人家里做佣人为荣,她崇拜白人的一切,终于迷失在对白人的尊崇和对黑人的鄙夷之中。《最蓝的眼睛》从被殖民者的角度呈现了殖民统治对被殖民者的精神摧残。
然而,《消散》虽然体现了精神殖民对被殖民者的危害,但是也体现了对殖民者的伤害。小说的男主人公是受精神殖民毒害的一个典型例子。殖民教育硬生生地割裂了圭亚那的年轻一代与本族历史的联系。男主人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可谓是一无所知,看到非洲的面具时,他感到的并不是亲切,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殖民使得被殖民者割断了与古老文明的联系,成为无本之木,漂泊无依。这无疑是对被殖民者最惨痛的戕害。但是小说并没有局限于此,小说最大的亮点是从卢瑟福太太身上折射了大英帝国的没落对殖民者的精神危害。殖民统治不仅仅会对被殖民者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同样会给殖民者造成心理创伤。大英帝国对圭亚那长达两百余年的殖民统治于1966年结束,但是殖民对殖民者造成的精神迫害却未自此终结。卢瑟福太太终日停留在大英帝国的辉煌往事中,不肯走出昔日的阴影,不愿接受大英帝国败落的现实,过着几乎与人隔绝的生活。她根本“没法让自己摆脱历史”,[2](P198)由此可见,殖民对殖民者造成的精神创伤。这也是两部小说最大的不同,亦即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精神殖民的毒害。
(二)传统对于被殖民者的重要性
两部小说都涉及了被殖民者的传统,但是两位作者对古老传统对于被殖民者的重要性的解读却截然不同。
1.秉持黑人传统方能幸存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中提出黑人只有秉持本族的传统,方能在白人社会中幸存。佩科拉一家是抛弃黑人传统、盲目崇拜白人文化的代表,最终这家几近家破人亡。乔利死了,佩科拉疯了,吉米离家出走了,而波琳却还在为自己是一个称职的白人仆人而骄傲,并兢兢业业地帮白人打理家务。他们一家的命运是可悲的。莫里森通过这一家的遭遇,阐明在白人社会中背弃黑人文化是难以立足的。相反,小说中的克劳迪娅一家却能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幸存,这与他们一直恪守黑人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所有的黑人小女孩都喜爱白人洋娃娃时,克劳迪娅却将其拆解,这也意味着她与白人的审美彻底决裂,而对自己的黑人身份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自信地接受。克劳迪娅的母亲也是坚持黑人传统的代表。她时常哼着布鲁斯曲调,生活虽然艰辛,却没有自我放弃,而是乐观地生活。从他们一家的故事中,莫里森强调了秉持黑人传统方能幸存的观点。
2.现代文明对非洲传统的碾压
与《最蓝的眼睛》不同的是,《消散》中展现了另外一番坚守传统文明的景象。小说中的苦力斯瓦米是非洲传统的典型代表。男主人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斯瓦米却不同,他不仅知晓本族的古老传统,而且一直在延续着这一传统。然而,代表非洲传统的斯瓦米却被代表现代文明的机器碾了个粉碎。男主人公“曾一度认为(斯瓦米)他身上有一种了不起的东西,像我们面前的大海和身后的丛林一样难以想象”,[2](P41)“了不起的东西”即指斯瓦米坚守着的非洲传统。但是并不像《最蓝的眼睛》中那样,遵从传统并不能确保在现代社会中幸存。现代文明无情地亦是轻易地就可以将古老的非洲传统碾碎,而掌握现代工程学的男主人公虽然对本族的历史所知甚少,但是依旧可以凭借着现代知识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生存。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传统对于黑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少?
(三)塑造的白人形象不同
1.白人趾高气昂,歧视黑人
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的白人殖民者的形象都是趾高气昂的。他们认为白皮肤、金头发和蓝眼睛是美丽的象征,而黑人是懒散、肮脏和贫穷的代名词。白人根本瞧不起黑人,就连糖果店的满口啤酒味的白人老板都不屑于正眼瞧一下佩科拉。而且白人在看黑人时,他们的眼睛里“透出嫌恶”,并且明显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5](P55)因此,小说的叙述者克劳迪娅才会说道:“我甚至认为那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怀有敌意。这片土地对某些花卉来说,生存条件太过恶劣”,[5](P216)白人歧视黑人是整个美国的社会大环境使然,这无疑造成了黑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
2.白人房客友好热情地对待黑人来客
《消散》中塑造的白人形象不都是充满敌意,颐气指使的。虽然也会有白人殖民者在看到这位圭亚那的工程师时,“以貌取人,看到的是他的肤色和打扮质地”,[2](P146)但是也有白人殖民者热情对待这位黑人来客,这就是卢瑟福太太。她并没有因为男主人公是黑人或是非洲人而瞧不起他,而是和他促膝长谈,十分友好热情。虽然“黑人生活在英国很多方面都受人歧视”,[2](P146)但并不是每个白人都是如此。卢瑟福太太呼吁“通过立法平等对待黑人,因为他们毕竟也是英国国民”。[2](P146)因此,达比丁塑造的白人形象和莫里森的有所不同。
三、结语
《消散》和《最蓝的眼睛》这两部作品都精彩地描绘了后殖民主题,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它们都讲述了精神殖民对被殖民的黑人的身心造成的伤害。本文从文化霸权和“他者”地位这两个层面论述了白人殖民对黑人心理和精神的迫害。尔后,又阐述了两部小说的不同之处。从对精神殖民的不同的剖析角度,传统对于黑人的重要性和塑造的不同的白人形象进行分析。虽然两部小说都展现了被压迫和被奴役的民族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留下的创伤,但是它们的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旨在探究两部小说中的精神殖民异同,展现它们蕴含的后殖民主题。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戴维·达比丁.胡宗锋.消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
[3]Aoi Mori,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1999.
[4]Louis Gates,Jr.,and K. A. Appiah(ed.).Toni Morrison:Critical perspectives,past and present[M].New York:Amistad Press,1993.
[5]托妮·莫里森.杨向荣.最蓝的眼睛[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责任编辑:张 庆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piritual Colonization in “Disappearance” and “The Bluest Eye”
LIU Jing,HU Zong-feng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Disappearance”,by David Dabydeen,is about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young Guiana engineer and British landlord—Mrs. Rutherford,from which the impact of colonization on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is reflected. “The Bluest Eye”,by Toni Morrison,tells a tragic story of the little black girl—Pecola who is eager to have bluest eyes,which reflects the mental injury of colonization on the black people. “The Bluest Eye” is mostly studied from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ly,“Disappearance” is rarely studied,let alon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novels. Although the impact of spiritual colonization is showed in those two novels,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mparing the two novels,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spiritual colonization. It aims to study the postcolonial theme in the novels.
“Disappearance”;“The Bluest Eye”;spiritual colonization;postcolonial theme
2016-07-15
刘 晶(1991-),女,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研究; 胡宗锋(1962-),男,陕西凤翔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与翻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1004—5856(2017)02—0087—05
I106.4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