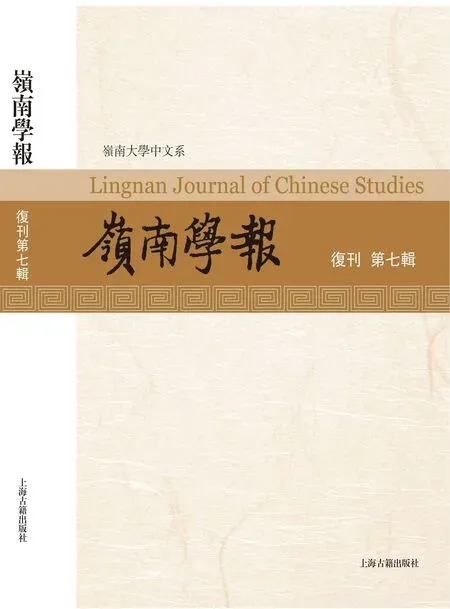詞與樂府關係新論
——關於詞與樂府關係的綜合考察
2017-03-10錢志熙
錢志熙
文體與流派
詞與樂府關係新論
——關於詞與樂府關係的綜合考察
錢志熙
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詞與樂府關係作新的考察: 一、唐宋時期詞稱樂府的實義;二、詞作爲新興樂章系統與前此的古樂府系統的關係;三、詞作爲新聲樂府與唐宋時代已經不能實際入樂的古樂府的消長倚伏的關係,即詞與唐詩中各種新舊樂府體的關係。
詞 樂府 燕樂 聲詩 唐樂府 詞與樂府
詞與樂府的關係,常被詞史家所忽略,甚至否認二者之間存在關係。其中兩種觀點最具代表性。一種觀點是籠統地説詞即樂府,是繼古樂府而生的一種“新樂府”,兩者不僅體性相同,而且在脈絡上也不能截然分開。這種觀點比較廣泛地存在於古代的詞論中,一直延至近代之初。這種觀點的價值,在於啓示我們在中國古代詩樂關係的整體上認識詞的特性,其理論的根據往往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以儒家爲代表的樂教思想,但容易忽略詞體特殊的音樂性能,以及其作爲“我國詩樂關係的新傳統”的事實*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頁。。另一種觀點,是從音樂的類型與文體的特點上嚴别詞與古樂府之不同。其核心的觀點是認爲詞乃隋唐燕樂所生,爲倚聲之體,與樂府不僅音樂母體不同,而且兩者在詩與樂的關係上也是不同的。在與音樂的結合方式上,詞爲倚聲之作,詩與樂密切配合,詩因樂而生;古樂府則或采歌謡入樂,或因金石而造新詩,詩與樂的關係是比較寬疏的。這種看法,在現代詞學中趨向成熟並成爲主流,而且對前一種看法是帶有明顯的否定性的。或者説,從籠統地將詞與樂府混爲一談,到强調詞與樂府之不同,向來被視爲現代詞學的一種進步,一種科學化的推進。從後一種較現代的觀點來看,好像詞與樂府的問題已經清楚,不須再作過多的討論。所以,現代的詞史建構往往完全截斷詞與樂府的關係,將力量主要集中於尋找詞樂與詞體的發生上。古代詞學家的詞即樂府的看法,以及從古歌、古樂府中尋找詞體淵源的探討方法,也基本上被放棄了。
但是,詞與樂府的關係,仍然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上述兩種看法,各自强調事實的一個方面,應該結合起來探討。
詞與樂府的關係,存在於好幾個層面上: 一是詞稱樂府義,即詞爲唐代新聲樂府之一種,且其源出於教坊,至宋詞本質仍爲入樂歌詞,故沿用唐人稱詞爲樂府的習慣。唐宋人稱詞爲樂府,即據此義。二是詞作爲一個新興的樂章系統與前此的樂府系統的關係,明清人認爲詞也是樂府,或詞源出樂府,即據此義。詞是在隋唐燕樂的大背景中發生的,而隋唐燕樂是接替漢魏六朝的新舊清商樂系統而興起的。所以詞在音樂背景上,與前面的樂府有一種代迭的關係。三是詞作爲新聲樂府與唐宋時代實際上已經不能入樂的古樂府的消長倚伏的關係,即詞與唐詩中各種新舊樂府體的關係。這是詞史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的一個問題。這三個層面的問題,都是本着這樣一種基礎性的認識,即詞與古樂府從音樂與文體上看是兩個能够清晰區分的系統。但在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學者已經建立了一種牢固的觀念,即詞是整個廣義樂府範疇中的一種,所以,必須在廣義的樂府的整體中,纔能完整地把握詞史,並對詞體文學作出準確的評價。近代的一些詞學家,也多有沿著這種思考方式來認識詞史,不就詞而論詞,而是從中國古代詩歌史的整體中來認識詞史中的各種問題。如夏承燾對婉約正宗論的批評,就代表了這種認識方法的成果*參考夏承燾的衆多詞史論文,尤其是《瞿髯論詞絶句》。筆者另有論文《夏承燾詞史觀及詞史建構》對此有專門論述。。
某種意義上説,上述認爲詞與古樂府從音樂與文體上看是兩個能够清晰區分的系統,也只是我們的一種假設,即認爲存在一種與舊的樂府音樂完全不同的、全新的詞的音樂。實際上這個問題並没有得到一種科學的、全面的論證。在實際的音樂與文體兩方面,詞與樂府可能存在著這樣三種承續關係: 一是詞在音樂上與前面的漢魏六朝樂府音樂有接續關係,詞繼承着古樂府的音樂成分;主張詞爲燕樂之體的學者,也多同時承認詞樂中有清樂的成份,且認爲清樂與燕樂並不能完全區分。如夏承燾即認爲“詞淵源於周隋以來的胡樂及魏、晉六朝以來的民間歌曲(清商樂)”*夏承燾《夏承燾集》,第8册,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頁。。二是從詩樂關係來看,在前面的樂府時代也存在類似於詞的倚聲、倚樂的作法。三是詞的長短句體制,與前面的樂府長短句在文體上可能存在繼承的關係。結合上述六個層面(包括前文所説的三個層面)的問題,則詞與樂府關係就能得到全面的梳理,而傳統的詞爲樂府説及詞出樂府説這兩種詞史觀點的是非利鈍,也能得到一個科學的審視與評判。
一
“曲子詞”之外,樂府也是詞的一個正名。這是宋元人的常言,其例甚多: 如李清照《詞論》:“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黄墨谷《重輯李清照集》,濟南: 齊魯書社1981年版,第56頁。劉將孫《新城饒克明集詞序》:“樂府有集,自《花間》始,皆唐詞。《蘭畹》集多唐末宋初詞。”*劉將孫《新城饒克明集詞序》,《養吾齋集》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册,臺北: 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4頁。元好問《新軒樂府引》:“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也。”*姚奠中主編《元好問集》,卷三六,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65頁。至於宋元人詞集多以樂府爲名,如《東坡樂府》等,則是學者所熟知的事實。但是,我們這裏提出一個問題,宋元人稱詞爲樂府究竟根據何種理由,體現何種名實關係?其情況應該有這樣兩種: 第一種情況是宋代的士大夫根據詞的樂歌體性,用了古代的樂府作爲雅稱,以擡高作爲當代俗樂歌詞的詞的地位;事實上,明清人稱詞爲樂府,就是這種情況,是一種托古之稱。第二種情況是,詞在當時的本名就是樂府。稱詞爲樂府,並非文人托古之稱,而是唐宋聲歌本身的名稱。我認爲,宋元人稱詞爲樂府,主要是體現後面這一種名實關係。這裏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唐人仍稱朝廷掌樂機構爲樂府,唐宋人因此稱當代的聲歌爲樂府。其例甚多,不煩贅舉,如《舊唐書·音樂一》載永徽二年太常奏白雪琴曲,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辭》,並以侍臣奉和爲送聲。“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六年二月,太常丞吕才造琴歌《白雪》等曲,上製歌辭十六首,編入樂府。”*《舊唐書》卷二八,第4册,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47頁。而段安節《樂府雜録》所記的即是宫廷樂府的音樂。宋代也仍稱教坊爲樂府,《宋史》“樂十七”:“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宫調皆不正,皆俚俗所傳。”*《宋史》卷一四二,第10册,北京: 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344頁。這些都是專治此學的學者已經清楚的。由於唐代宫廷音樂機構仍稱樂府這個原因,唐代的新聲歌曲,也統稱樂府。這與漢樂府詩歌得名於樂府所奏是一樣的。只是漢代的樂府,特指屬於少府令(或黄門鼓吹署)掌管的俗樂機構,與屬於太常令掌管雅樂的太樂令不同。所以,漢代雅俗歌詞分流,樂府詩主要是指俗樂歌詞的相和清商曲,即使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文人擬樂府,擬的也還是漢代的俗樂歌詞,而諸如鐃歌十八曲、郊祀及雜歌謡之類,並不在樂府所擬之列。唐代樂府新聲中最活躍的部分仍屬配合燕樂的聲詩與曲子詞。而且我們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唐人將預備入樂的詩歌直接稱爲“樂府”。如李頎《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中説道:“新詩樂府唱堪愁,御妓應傳鳷鵲樓。”*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一二二,第1册,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978頁。《唐才子傳》卷四記載康洽事蹟:“洽,酒泉人,黄須美丈夫也。盛時攜琴劍來長安,謁當道,氣度豪爽。工樂府詩篇,宫女梨園皆寫於聲律。”*(元) 辛文房著,王大安校訂《唐才子傳》,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頁。戴叔倫有《贈康老人洽》:“酒泉布衣舊才子,少小知名帝城裏。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宫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之盡相識。”*《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二六三,第2册,第800頁。康洽所工之“樂府詩篇”,其體裁究竟是什麽?我們尚不能考。依上所叙,康洽寫這些詩,就是將它們當作樂府詩篇來創作的,换言之,這裏稱它爲“樂府詩篇”是它未入樂前的名稱。那麽,這種樂府詩篇究竟屬於什麽體制呢?有一點是確定的,它們不是沿用漢魏以來舊題的擬古樂府,而是新體的詩歌。而我們知道,唐人能够入樂的,除了後來的曲子詞外,就是當時流行的齊雜言新體,其中五七言律絶是大宗。五言稱短調,七言稱長調,見李賀《申鬍子觱篥歌序》。序謂朔客李氏:“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又對李賀説:“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葉蔥奇疏注《李賀詩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頁。可知唐人稱五言爲短調,七言爲長調,故唐人入樂之詩,也可直稱爲樂府。而五七言絶句,尤其是其中樂府體、歌曲體五七言絶句,則更多直著樂府之名。我們看《全唐詩》所收,有些七言絶句是直接冠以“樂府”之名的,如劉言史《樂府雜詞》三首,其體即爲七絶:
紫禁梨花飛雪毛,春風絲管翠樓高。城裏萬家聞不見,君王試舞鄭櫻桃。
蟬鬢紅冠粉黛輕,雲和新教羽衣成。月光如雪金階上,迸卻頗梨義甲聲。
不耐簷前紅槿枝,薄妝春寢覺仍遲。夢中無限風流事,夫婿多情亦未知。*《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四五七,第3册,第734頁。
徐凝《樂府新詩》:
一聲盧女十三弦,早嫁城西好少年。不羨越溪歌者苦,採蓮歸去緑窗眠。*《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七七二,第3册,第772頁。
此稱樂府新詩,亦爲七絶體。我們知道,唐人的絶句,有一部分如王昌齡《從軍行》是用古題的,而《長信秋詞》則用新題,都可歸爲樂府一類中。但像上面這四首詩,只是一般的絶句,卻直接地用“樂府雜詞”、“樂府新詩”這樣的名字,它的理由是什麽呢?又如曹鄴《樂府體》:
蓮子房房嫩,菖蒲葉葉齊。共結池中根,不厭池中泥。*《增訂注釋全唐詩》卷五八七,第4册,第312頁。
這是唐人稱五絶爲“樂府體”的例子。陸龜蒙《樂府雜詠六首》,也全是五絶體,有用仄聲韻的,如《樂府雜詠·雙吹管》:
長短裁浮筠,參差作飛鳳。高樓微月夜,吹出江南弄。*《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二一,第4册,第589頁。
有用平聲韻的,如《樂府雜詠·東飛鳧》:
裁得尺錦書,欲寄東飛鳧。脛短翅亦短,雌雄戀菰蒲。*《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二一,第4册,第589頁。
從上述例子,我們發現一個文體方面的事實,即唐人有時直接將五七言絶句稱爲樂府,這當然是因爲這兩種體裁經常是入樂的。又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弦。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樂人輒以重賂購之,樂府稱爲二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外國乞文”條,《四庫全書》本。
此處“李賀樂府”之“樂府”是指歌詞體裁,“樂府稱爲二李”之“樂府”是指音樂機構。李益樂府,就是指他那些入樂的七絶,李賀同時也作古樂府,但這裏的“樂府數十首”,應該主要是指其律詩、絶句。由此我們再看皮日休《七愛詩·李翰林白》“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六二,第4册,第424頁。這一首,他所説的李白醉中草樂府,是指傳説中玄宗召他作《清平樂》一事,所用體裁也是七絶。則這裏所説的李白樂府,非指其擬古樂府一類。
唐人採爲聲詩者,當然不止絶句一體,這一點我們從任二北《唐聲詩》中已經可以觀察得很清楚。但是唐人最常用爲歌曲的,的確是絶句一體。絶句有兩類,一類是從晉宋人的聯絶體來的,如杜甫集中自爲絶句的諸首,這一類,當然不屬樂府。但另一類從吳聲歌曲中發展過來,就是樂府體了*錢志熙《論絶句體的發生歷史和盛唐絶句藝術》,載於《中國詩歌研究》第5輯,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12月版。。而這一類發展出來的大量的準備入樂的絶句體,在唐人那裏,頗懷疑常常直接稱它爲樂府。换言之,即唐人絶句的樂歌類,其正名即爲樂府。唐人對於詩歌體裁的稱呼,並不像後來宋元明人那樣注重形式,而是更多地側重於其功能與性質,如同是五言古體,有稱爲古風的,有不稱爲古風的。同樣,同是今人所説的絶句,有稱爲“絶句”者,有稱爲“樂府”者,蓋體裁雖同,而功用不一也。唐李益、施肩吾都是作樂府體絶句的好手,孟簡《酬施先輩》:“襄陽才子得聲多,四海皆傳古鏡歌。樂府正聲三百首,梨園新入教青娥。”*《增訂注釋全唐詩》卷四六二零,第3册,第764頁。這裏所説的樂府正聲,就是施氏所作的以絶句體爲主的擬入樂歌詩。我們考察施肩吾所作,如《帝宫詞》、《歎花詞》、《杜鵑花詞》、《曉光詞》、《春日美新緑詞》、《效古詞》、《侯仙詞》、《修仙詞》、《金吾詞》、《望夫詞》、《少婦游春詞》、《惜花詞》、《抛纏頭詞》、《夜笛詞》等凡以“詞”標題者,以及《襄陽曲》、《將歸吟》、《折柳枝》,實即所謂樂府正聲。可見唐之歌曲,即唐之樂府,以絶句爲主要體制。亦因此,當時的絶句亦稱樂府。後來清人王漁洋稱“唐三百年以絶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王士禛著,吳鷗點校《唐人萬首絶句選》,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1頁。,雖是後世揣摹之論,卻正合唐時的實際情形。唐人使用“樂府”一詞,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也因此,唐人的某類絶句曾直接冠以樂府之名的事實,就被淹没掉了。當然,並非所有絶句唐人皆稱爲樂府,只是其中作爲聲歌之體來創作的稱樂府,其餘皆爲徒詩。如何辨認其聲歌之體,仍須從其題名上判斷,如上述施肩吾之作,即多用“詞”標題,他如吟、曲、歎、歌及用專門之曲名如《楊柳枝》、《結襪子》來作題目的,都可以説就是唐樂府、唐歌詞。
歌曲而稱樂府,進而入歌曲之詩歌體裁也稱樂府。長短句的曲子詞,由聲詩的唱法和作詞法的改變而來。故聲詩在唐代稱樂府,詞自然也稱樂府。宋明以來,沈括、朱熹等人就提出“泛聲説”,至胡震亨《唐音癸籤》則爲此説之全:
古樂府詩,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難以入歌,中間必添和聲,然後可歌,如妃呼豨、伊何那之類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絶句,律詩亦間有采者,想亦有賸字賸句於其間,方成腔調。其後即以所剩者作實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復别用和聲,則其法愈密,而其體不能不入於柔靡矣,此填詞所繇興也。*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五,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頁。
我們現在知道,在唐代,預備入樂的五七言絶句習慣就稱爲樂府,那麽由五七言絶句變化出來的曲子詞,當然也沿用了樂府這一名稱。所以,詞稱爲樂府,應該是其來甚遠的,並非宋人的托古之稱。
事實上,唐宋人的習慣稱呼,單説“樂府”二字,主要是指當代的新聲歌詞,至於漢魏六朝的樂府及其當代擬作,則稱爲“古樂府”。古樂府在唐宋時代屬於詩體,而新聲歌曲纔是真正的歌曲一體。這一點,王灼《碧雞漫志》裏有比較清楚的記載。其論古歌曲與當時流行的倚聲曲子詞之區别云:
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制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王灼《碧雞漫志》卷一,《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一集,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05頁。
這裏所説的“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一句中的“詩”,指傳統内涵的詩,包括五七言古近體及古樂府之類。所以古樂府當時是常稱爲詩的,只有“以詞就音”的詞,“始名樂府”。没有比這一例更能説明樂府二字,是當時曲子詞的正名。甚至流傳已久的古樂府體,也頗有讓此專名於新興的詞體的趨勢。如黄庭堅《小山集序》中説晏幾道“乃獨戲弄於樂府之餘”*黄庭堅著,劉琳等校點《宋黄文節公全集·正集》卷一五,《黄庭堅全集》第1册,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頁。,又自稱“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黄庭堅著,劉琳等校點《宋黄文節公全集·正集》卷一五,《黄庭堅全集》第1册,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頁。,陸游《跋後山居士長短句》中説“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陸游集·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八,第5册,北京: 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247頁。後一例直接稱唐末詞爲樂府詞,尤堪玩味。唐人稱五七言絶句爲樂府,詞的體制變於此,自然也稱呼詞爲樂府。《全唐詩》“詞一”下小序最能明唐宋聲詩、曲子詞俱爲樂府之義:“唐人樂府,元用律絶等詩雜和聲歌之。其並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揚州詩局本,第2161頁。此可謂樂府爲唐宋詞之正名的一言定論。唯清人尚不知唐人有直呼入樂之律絶等體爲樂府者。而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合隋以來的聲詩與曲子詞爲“近代曲辭”一編,正是反映了宋人對於詞體性質的一般認識。
以上是詞與樂府關係的第一層,即詞稱樂府的名實關係,乃其原爲沿聲詩(五七言絶句)稱樂府而來。
二
詞與樂府關係的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詞作爲一個新興的樂章系統與前此的樂府系統的關係。詞與《詩經》的國風、雅、頌以及漢樂府、南朝吳聲西曲都是樂章歌詞,並且都有源於民間謡曲而後進入宫廷、並爲文人紛起模仿的發展歷史。所以,歷來詞論的一種,即著眼於樂章的共同體性及詞與前此各樂章系統的淵源關係來立論。現在可知的最早詞論——五代歐陽炯《花間集序》就追溯了歌曲、歌唱的歷史:
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效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謡則金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自合鸞歌;響遏行雲,字字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後蜀) 趙崇祚輯《花間集》,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本1998年版,第1頁。
歐陽炯認爲詞是豔麗新聲,所以追溯它的歷史。《穆天子傳》載:“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謡曰:‘白雲在天,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郭璞注《穆天子傳》卷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諸子百家叢書”本1990年版,第10頁。所謂“唱雲謡則金母詞清”即指此事。20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早期曲子詞集《雲謡集雜曲子》,以“雲謡”名集,正與歐陽炯此處同一意思。可見早期詞家,無論是民間還是文人,都是將新興的曲子托體於古代的歌曲。而且從以“雲謡”名集,可知早期曲子詞源出民間徒歌,是一種新穎、流行的歌唱藝術。至於《花間集序》中的“楊柳大堤之句”,應該是指清商曲辭《讀曲歌》中的“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以及《襄陽樂》中“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之類。“芙蓉曲渚之篇”,則似是《子夜歌》中“高山種芙蓉,復經黄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之類詠到芙蓉的歌曲,唯“曲渚”不詳何篇。或者“芙蓉曲渚”指薛道衡《昔昔鹽》中“花飛芙蓉沼”這一句。這就將詞的淵源,直接地追溯到南北朝的樂府新聲那裏了。
宋代樂府是詞的正名,而古樂府則稱爲詩。宋人的基本看法,自然是推崇古樂府,而貶低詞這種當代的俗樂歌詞。所以,我們考察宋人詞論,多是批評詞不合古樂府的格法,而少有將詞與古樂府相提並論的,這在一定意義上,正説明詞是一種新興歌樂。如宋人的一種普遍看法,認爲古詩及樂府都是因情志而發爲詩,又由詩而配爲樂;而詞則是先有樂曲而作詩。他們將《堯典》中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奉爲原則,認爲先有言志,然後纔永言,而後發爲歌聲,而附以音律,認爲詞曲將這個順序完全倒過來。《唐音癸籤》卷一五引王安石之言:“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歌永言,聲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胡震亨《唐音癸簽》,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頁。原出處爲趙令畤《侯鯖録》。王灼《碧雞漫志》則據王安石此論作了更專門的闡發,並且爲樂府之名爲詞所獨佔而辨析古是今非。所以,在詞與古樂府的關係上,宋人詞論是持一種詩尊詞卑的觀點的,認爲相對於古樂府,詞是音樂文藝的一種卑靡化。但是,南宋以降,崇尚蘇軾一派以及復雅論者,開始力求提高詞品,其中的一種論調,就是認爲詩詞同源,詞與國風、樂府,原本一脈,甚至認爲詞出於古樂府。胡寅爲向子諲作《酒邊詞序》就是較早發表這種論調的一家:“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流也。詩出於《離騷》、《楚辭》。而騷辭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頁。上面我們論述過,宋元間樂府是詞的專名,凡稱漢魏六朝樂府者,必加古字。胡寅這裏也是一個顯例。胡寅在序的後文專門推崇蘇詞,而貶抑柳永一派的婉約詞。可見詞論裏面的這一派,是屬於復雅的論調。又如張鎡爲史達祖作《梅溪詞序》即説:“《關雎》而下三百篇,當時之歌詞也。聖師删以爲經。後世播詩章於樂府,被之金石管弦,屈、宋、班、馬,由是乎出。而自變體以來,司花傍輦之嘲,沉香亭北之詠,至與人主相友善,則世之文人才士,遊戲筆墨於長短句間,有能瑰奇警邁,清新閑婉,不流於沲蕩污淫者,未易以小伎訑。”*《詞籍序跋萃編》,第263頁。這裏不僅推尊詞體於國風、樂府,而且認爲變體之詞,始於隋唐之際。王炎《雙溪詩餘自序》:“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詩至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爲清脆,如厶弦孤韻,使人屬耳不厭也。”*《詞籍序跋萃編》,第302頁。王炎認爲詞出於樂府中以曲爲名的一種,不免望文生義。但可見宋人在推尊詞體、追溯詞源時,其中的一種看法,是認爲詞出於古樂府的。他們的基本看法,是認爲詞爲樂府之變。至於張炎《詞源》通論樂府、聲詩、詞體之延承關係:“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粤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他認爲至周邦彦,八十四調之聲稍傳,“作詞者多效其體制,失之軟媚而無所取”,也是曲終奏雅之論,反映詩莊詞媚的看法*張炎著,夏承燾校注《詞源注》,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9頁。。雖然他們喜愛曲子詞,但在整體的文學地位上,又不能不將它們置於古樂府之下。張炎此書題爲《詞源》,全書講的都是樂律與作法,真正溯源於古的,卻只有這開頭一句。可見宋人的托體樂府,大半都是一種空洞之論。他們對於詞與古樂府的真正關係,也是缺少考察的。
關於詞與樂府之遞嬗歷史的探討,宋人以王灼最具專家之學的卓見。王灼首明詞爲歌曲之體。並因此而述歌曲之體,稱漢以前爲古歌,漢至唐爲古樂府,詞爲今曲子。三者都是入樂之詩,然古歌是先有詩,而後以詩入聲律;而曲子詞則先定音節,而後作歌。此今曲子之變於古,失古法者。其引《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及《詩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諸論,並作結論云:“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謡,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於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碧雞漫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一集,第105頁。此言樂府與詞之别,宋人作爲詩體的樂府,是指古樂府,以古字别於今曲子稱樂府。所以宋代樂府之名,實又讓位於今曲子。這就是王灼所謂“今人於古樂府,特指爲詩之説,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其實,唐代就已經以“古樂府”稱謂詩之一體的漢魏以來的樂府,而新聲歌曲則直稱樂府。《宋書·鮑照傳》稱其作爲“古樂府”。則在宋齊時代,漢魏樂府及其擬作已帶“古”字。其義一直沿用到宋代。宋元稱詞爲樂府,其例舉不勝舉,皆用此義。明此,則於曲子詞在詩歌體制發展史上的位置得一定位,它的基本性質,是隋唐之際出現的一種樂府新聲。
關於詞與古樂府的區别,王灼認爲古歌是先有詩而後入樂;詞爲先有音節,後製歌詞,是樂府之變: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絶。西漢時,今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絶。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碧雞漫志》,第106頁。
何爲詞體,其最先的性質爲倚聲的今曲子,後世則爲倚調填詞的徒詩,從倚聲到倚調,其文體功能性質已發生根本的變化,即樂章與徒詩之别,但因倚聲與倚調,詞體文學作爲一個詩歌體裁系統纔得以成立。拿樂府來比較,樂府也是先爲樂章,並有曲調名,後又發展爲不入樂的文人擬樂府;但一個樂府的曲調,即使在入樂的當代,就是文體不定的,詞體所具之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的特點,是樂府體所没有的,不但文人據古調名(古題)所擬的樂府詩没有這種情況,即使是原始的漢魏樂府,也是没有的。我們看建安時候的樂府,常常是同一個曲題,篇體卻很不一樣。這種情況的原因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大概是樂府的歌曲,是只有調而没有譜的,尤其是相和歌詞這一類。但有一種情況,似乎與曲相似,即漢鐃歌十八曲與後來的魏、吳、晉歷代的據曲擬作,我們看其篇體,雖然不是完全的前後劃一,但大體是差不多的。另外,如有些特定的樂府調,如三、五、七配合的一種雜言歌行,其篇體前後大體是劃一的。這種情況,可以視爲詞體倚聲、依音節填詞的前例。當然,我們没有必要直接視其爲詞體淵源,只可以視爲詞體倚聲方法的淵源。王灼也從這方面爲詞體尋找過淵源,他在指出古歌主要是先作詩、後入律入樂的同時,也提到幾個特例:
然中世亦有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碧雞漫志》,第106頁。
作爲一種入樂的方法,我們不能不説,詞的倚聲法,淵源於“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的一種,而廣義的倚聲法,是古已有之的。正因爲存在着這種方法,纔有大量的倚聲方式出現的可能。但在詞體之前的古歌、古樂府時代,這種倚聲的作法不是主流的,並且事實上並没有達到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這樣嚴格的程度。但話説回來,詞的如此嚴格的倚填方法,也是到了後來纔完全定下來的。在曲子詞的早期發展階段,一個詞調出現篇體、句字、聲韻的不同,還是很常見的,敦煌詞中就存在這種情況。所以,詞的倚聲與古樂府的倚聲,還只是嚴格程度的不同,而非性質的根本不同。在考慮詞體起源時,完全忽略古樂府時代的倚聲關係,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明白了倚聲法的歷史演變,我們就不能對詞的起源作非此即彼的簡單處理。應該看到詞是開始於古樂府時代的倚聲、倚樂方法的一種發展,也可以説是這一種入樂方式的定型。
元明清時代,詞樂失傳,詞完全成了詩的一種,這時期將詞溯源於三百篇、古樂府的托古派的詞論更多。如元延祐間葉曾作《東坡樂府叙》:
今之長短句,古三百篇之遺旨也。自風雅隳散,流爲鄭衛侈靡之音,不能復古之淳厚久矣。東坡先生以文名於世,吟詠之餘,樂章數百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真得六義之體。*《詞籍序跋萃編》,第61頁。
同時,一些詞學家也開始從曲調與體制等方面探尋詞與樂府的淵源關係。此時形成一種詩詞同工異曲、共源分派的詞史觀,其中的一種看法是認爲詞與樂府相接,出於南朝後期的樂府之體。楊慎就持這種觀點:
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詞之體具矣!*楊慎《詞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1頁。
楊氏博涉窮覽,其《詞品》卷一搜集了一大批南朝及隋時期的長短句樂府曲,甚至包括《丁都護歌》、《白團扇歌》等早期吳聲曲中的長短篇,並且一一指認後世詞體與這些歌曲的淵源關係。可以説是詞出南朝樂府之説的集成,後來爲此説者,率不能超過他的範圍。於是就有人進一步從《詩經》中搜尋長短句的起源。如清初丁澎《藥園閒話》,就從《詩經》中搜尋三五言調、二四調、疊句調及所謂的“换韻”、“换頭”之例,提出了三百篇爲詞之祖禰的看法*徐釚著,王百里注《詞苑叢談校箋》卷一,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3頁。。
詞的曲調,有出於樂府的一種。如楊慎《詞品》卷一稱“《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詞品》,第14頁。又鄒祗謨《詞衷》稱“沈天羽云:‘調名多本樂府,然去樂府遠矣。南北劇又本填詞,去填詞更遠。’”*《詞苑叢談校箋》卷一,第89頁。就是論詞與樂府及後來的曲之間,存在着調名沿用的關係。徐釚《詞苑叢談》引梨莊之論:
又曰:“徐巨源云: 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黄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以下逮於詞焉,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予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是詞貴於言情矣!”*《詞苑叢談校箋》卷四,第251頁。
又曰:“宋人詞調,確自樂府中來,時代既異,聲調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纖麗,《子夜》、《懊儂》之遺也。歐、蘇純正,非《君馬黄》、《出東門》之類歟?放而爲稼軒、後村,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則漢帝《大風》之歌,魏武‘對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詞苑叢談校箋》卷四,第252頁。
這是明清時期認爲詞源於樂府這一派比較典型的觀點,主要是從曲調的淵源、文體的遞嬗與風格的繼承這幾個方面來着眼,在以燕樂區斷詞與樂府之界限的現代詞史觀流行之前,詞出於樂府無疑是明清近代的主流看法。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名義上,明清時期的詞已經失去了樂府的專名,樂府作爲一個專名,又歸還給漢魏六朝的樂府詩歌了。
20世紀初,新型的文學史學引進,學者開始以近代學術的方式建構詞史。最初的幾家,如劉毓盤、吳梅、王易等,仍然繼承南宋以來逐漸流行的詞源於樂府之説。劉毓盤《詞史》,歷考周漢以來詩樂關係及樂府的發展,其基本的看法是認爲漢樂府詩樂合一,至魏晉諸家擬樂府,逐漸脱離音樂,多爲徒詩五言,後來又逐漸進入近體格律。“論者以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詩》四首,字句相同,若填詞然,謂即詞體之初起云。”*劉毓盤《詞史》(193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頁。漢魏與南北朝樂府曲調相繼淪亡,唐人所作樂府,皆不入樂。唐樂的主體爲采詩入樂,而詩樂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這就爲一種新的音樂文體的産生提供了歷史的機遇。劉氏根據上述的事實,提出“論詞之初起由詩與樂府之分”*劉毓盤《詞史》,第9頁。的觀點:
古樂府在聲不在詞。唐之中葉也,舊樂所存,其有聲有詞者,《白雪》、《公莫舞》、《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凡三十七曲。有聲無詞者,七曲而已。(原注: 見《碧雞漫志》)唐人不得其聲,故所擬古聲樂府,但借題抒意,不能自製調也。所作新樂府,但爲五七言詩,亦不能自製調也。其采詩入樂,必以排調、有襯字者爲詞體。(原注: 見《樂府解題》)。蓋解其聲,故能制其調也。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於是一衍而爲近詞,再衍而爲慢詞,惟小令終不如唐人之盛。*劉毓盤《詞史》,第23頁。
雖似求源過遠,但卻從音樂文體發展的大背景上,將詞視爲漢樂府、南北朝樂府音樂功能消失後産生的一種新的音樂文體,在歷史事實與邏輯關係兩方面都説得通。但劉氏的論述方式比較陳舊,以至後人在討論詞源時,多將這種詞出於樂府之説視爲迂遠之論。但無論哪家哪派,在追溯詞的音樂與文體起源時,都不能完全抛棄樂府前段。
吳梅《詞學通論》也承楊慎等人詞出南朝樂府長短句之説:
詞之爲學,意内言外,發始於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調有定格,字有定音,實爲樂府之遺,故曰詩餘。惟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已亡,而一時君臣,尤喜别翻新調。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沈約之《六憶詩》,已爲此事之濫觴。*吳梅《詞學通論》,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其書《概論一》亦持詩餘之説,歷述《詩經》以來詩樂興廢之跡,認爲周衰樂亡,經秦亂古樂胥亡,於是有漢樂府合樂之歌詞的興起,但魏晉以降,文人依曲作新歌,開直抒胸臆的文人擬樂府一途,樂府又一次失真。“一時君臣,尤喜别翻新調,而民間哀樂纏綿之情,托諸長謡短詠以自見者,亦往往而有。如東晉無名氏作《女兒子》、《休洗紅》二曲,梁武帝之《江南弄》,沈約之《六憶詩》,其字句音節,率有定格,此即詞之濫觴。蓋詩亡而樂府興,樂府亡而詞作。變遷遞接,皆出自然也。”*《詞學通論》,第46頁。其説較序論尤廣而詳。
現代詞學,尤其是詞出隋唐燕樂之説流行之後,學者們所强調的主要是詞與樂府在音樂上屬於兩個不同系統的事實。而現代諸家叙詞樂,都斷自隋唐之際前後相遞承的七部樂、九部樂及十部樂。而自敦煌石室曲子詞發現後,得以窺探詞的前期發展的某種真相,於是現代的詞源説開始形成,其主要的結構就是論樂溯自隋唐之際十部樂的形成,而論作品則溯自敦煌曲,傳統的溯自南朝齊梁之際的詞源説不再流行。如梁啓勳《詞學》一書《詞的起源》一節,即認爲:“詞起於唐,於敦煌石室發見有所謂雲謡曲子者十八闋。”又云:“大中以後,詩學浸衰,而貞觀之十部樂,上承清商曲之遺音,旁及西涼、龜兹之樂與吳歌楚調。蓋自永嘉以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爲世所尚,開皇仁壽間,南北樂府,同入於隋。大業中,定中原清樂及西涼樂等爲九部樂,入唐則定爲十部樂,燕樂分爲坐部伎與立部伎,其歌曲有所謂破陣樂、聖壽樂等。舞曲則分健舞與軟舞,其曲調有所謂涼州、甘州、蘭陵王、烏夜啼、柘枝等,皆後世詞調之名,可想見其歌拍舞容,已屬倚聲矣!是則詞之所以繼樂府而興,其痕跡固歷歷可尋也。”梁氏此論,大體上已經範圍了後來諸家的詞起於燕樂説。於是古代形態的廣義的詞起源於樂府、爲樂府之變的説法,就不再流行。而探討詞源於國風、楚辭者,更被視迂闊的托古之論。
三
詞與樂府關係的第三個層面,就是詞作爲新聲樂府與唐宋時代已經不能實際入樂的古樂府的消長倚伏的關係,即詞與唐詩中各種新舊樂府體的關係。這個層面的關係,歷來的詞史研究者基本上没有注意到。
唐代詩歌與音樂的關係,是體現在多個層面上的。第一層是朝廷郊廟、燕射的雅樂歌詩,它在音樂與歌詞上,主要是繼承前代的,新舊《唐書》的《音樂志》中對歷朝這種雅樂歌詩有詳盡的叙述。但這一部分的歌詞在詩歌藝術上陳舊而缺少個性,與唐詩藝術的實際關係不太大。第二層是與各種燕樂新聲配合的聲詩,主要採用文人創作的五七言律絶詩。這部分與唐詩的關係最大,其淵源實可追溯到梁陳君臣的采詩入樂,如陳朝何胥采後主君臣之詩,製爲歌曲,實爲唐代入樂大宗之聲詩的前導。於是唐代歌曲的主體,轉爲文人創作的近體詩歌,這也是促使近體定型並流行的重要動力。第三層即曲子詞的流行。前面已論,詞體興盛的事實,是原本非主流的由樂以定詞的倚聲、新翻曲的一種,到開元之後漸成主流,至大中之後而漸興盛。古代學者中流行一種看法,認爲詞的興起與律詩的衰落遞代。如果從近體作爲歌曲之主體讓位於長短句的詞成爲歌曲的主體來説,古人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除了上面這三層唐代詩歌與音樂的主要關係外,唐詩與音樂的關係,實際上還有第四層,即唐代詩人的擬古樂府、新題樂府的創作。這個問題,應該放在唐代詩樂關係的整體中來把握。唐人的古樂府創作,不僅寄託了唐人崇尚漢魏的詩歌審美理想,同時也寄託了他們在音樂上的復古理想。樂府體是唐代詩人從漢魏六朝詩人那裏繼承下來的一個詩歌品種,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樂府之興,肇自漢魏。歷代文士,篇詠實繁”一語*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上,《歷代詩話》上册,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4頁。,是對這個詩歌品種的簡當的概括。樂府系統在唐代的延續並發展,不僅是唐人繼承漢魏及六朝詩歌傳統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唐人復興古樂的音樂理想的表現。在南北朝後期,梁武帝、隋文帝都曾有過復興古樂的行爲。《隋書·音樂志》記載漢魏清商三調云:“《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帝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在於内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吕,更造樂器。’”*《隋書》卷一五,第2册,第378頁。這就是漢魏清商三調的遺留,其歌詞文本完整地記載在沈約《宋書·樂志》中。但這個曲調系統與晉宋以降文人的擬漢魏樂府卻並没有音樂上的關係,後者完全是作爲一個徒詩系統存在的。漢魏舊樂到武則天時代猶存三十六曲,見《舊唐書·音樂志》,正是從隋代的樂府中傳承下來的,與唐代詩人的擬古樂府也没有關係。但是唐代詩人的擬古樂府,雖然已經失去了實際的音樂依藉,卻因此而更加激勵起文士對古樂的嚮往,以及對燕樂新聲的一種蔑視。這在一定的程度上壓抑了詞體在文人詩壇上的流行,而詞體開始興盛的時期,也正是古樂府創作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唐初詩壇上已有新聲歌調的出現,如長孫無忌《新曲二首》、《堂堂詞二首》、沈佺期等《回波詞》。尤其是《回波詞》,儼然已經是倚曲拍之作。但是這類新聲倚曲,在文人中並没有太多的流行,文人流行的樂府詩的風氣,正如盧照鄰所述,仍以沿襲古題爲高:“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徐明霞點校《盧照鄰集》卷六,北京: 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74頁。同時的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也批評了晉宋以來文人擬樂府的失去古意。陳陳相因與失去古意,成了初盛唐之際樂府體創作上的兩大問題。儘管如此,具有濃厚復古思想的詩人,仍然没有放棄古題樂府而轉向新聲樂府的創作。李白擺脱了齊梁擬古樂府近體化的僵局,大量使用自我作古的歌行體、雜言體來賦漢魏以來的樂府題,開創出古樂府創作的新局面,並直接爲中唐的元白、韓孟兩派所繼承。可以説,李白對詩歌音樂理想的追求,主要是通過樂府歌行體來實現的。他爲新聲樂曲所作《宫中行樂詞》、《清平調詞》,以及尚處於傳疑狀態的《菩薩蠻》、《憶秦娥》等曲子詞,主要是受到當時流行音樂的影響,並不體現他個人在詩歌創作方面的音樂理想。曲子盛於開元、天寶之際,這是宋代李清照、薛季宣等人的共同看法,應該是符合事實的。李白出入玄宗宫廷,經遊南北各地,平生多攜伎賞歌之事,他對新聲樂曲,應該不缺少欣賞的機會。他這樣一位重視詩歌音樂性的詩人,之所以没有創作曲子詞,或者説没有更多地染指曲子詞的創作,從根本上説,仍然是受到復古的音樂思想的支配。元結曾據湘中歌謡作《欸乃曲》,有“停橈細聽曲子意,應是雲山韶濩音”之句,劉禹錫據建平地方歌曲所作《竹枝詞》,也是托意於屈原作《九歌》之事,杜甫的三峽絶句,據説也受到巴中歌曲的影響(夏承燾説),這都説明,唐代詩人願意吸收民間歌曲並托於古,對於宫廷及都市的流行新聲,卻完全是另外的態度。其在歌曲的創作方面,始終堅持以擬古樂府、歌行之體爲正宗。白居易、元稹等人有鑒於古樂府創作的困境,採用杜甫開創的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同時也吸收元結的擬《詩經》古風謡的作法,撰寫小序,並且交代創作宗旨,表達貢於朝廷樂府的意圖:“曰: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篇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卷三,第1册,北京: 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2頁。白居易是曲子詞的早期嘗試者,又是六義思想的實踐者,其曲子詞只是個人的娱情之作,而真正的歌曲創作理想,卻是寄託在新樂府方面。所謂“篇無定句,句無定字”,正是相對於曲子詞“篇有定句,句有定字”的作法,也就是説,是有意與流行歌曲的作法相對抗的。從韓孟、元白到唐末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這一派,正是處於新興的倚聲歌曲流行的時期,他們卻都抵制這種新曲,仍然以古樂府、新題樂府爲主要的體裁。所以,雖然燕樂新聲一直在宫廷與都市流行,卻始終没有成爲文人詩歌創作的一種體裁。這個原因,首先就是由於唐人執持古樂府的體制,其次則是唐代詩人堅持通過聲詩入樂的方式來尋求其詩歌在音樂中的傳播。後一問題,我們在討論詞與聲詩的關係時再作具體的分析。
但是,詞的興起,也反映了樂府創作與聲詩入樂方面的困境。其中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近體詩方面,流於千篇一律化與瑣碎、雕鐫兩種習氣;二是元白、韓孟一派力圖復興古風、古樂府的意圖也陷入了困境,尤其是他們不顧古樂實際已經消亡難復的現實,欲以古體、歌行體入樂章,與當代的燕樂格格不入。結果這一場復興古樂章的工作,雖然就詩歌藝術來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就音樂的復興來講,卻不能不説是失敗了。唐代部分詩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受了新興的詞體,這也意味著他們對於曾經長期抵制的隋唐燕樂的一種接受。事實上,作爲一種現實的音樂生活,唐代文人是一直在享受著這種當代音樂的,這方面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但文人詞一直到中晚唐纔興起,而且當時的重要詩人,如李賀、李商隱、杜牧等人,都未見參與,這裏面,其實不能不説有一種文體觀念上的紛歧。從整體上看,我們前面説到,唐人與漢人一樣,對於其當代的新聲俗樂,觀念上一直是拒棄的,恢復古樂一直是他們的願望。不考慮這一點,無法解釋唐代古樂府、新樂府創作的興盛。這樣看來,詞體不僅取代了聲詩的功能,同時也取代了樂府詩的功能。古樂府和歌行體的真正衰落是在五代時期,而這時正是文人大量採用詞體的時期,兩者之間有明顯的消長關係。進入北宋以後,首先是聲詩入樂之法完全衰落,詞體完全承擔起當代詩歌的音樂功能。與之相應,則宋詩更加文人化,其與音樂的關係較唐詩更加遥遠。這無疑是唐宋詩風格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而宋代的歌行與古體雖然在復古的美學理想的支撑下再度盛行,並且形成自己時代的風格,但是終有宋一代,擬古樂府的創作在詩體系統中所佔的比重是陡然下降了。可以説,在唐代仍是重要體裁的古樂府詩到了宋代,已經成爲無足輕重的一種體裁。這裏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宋代詞體興盛,文人在詩歌創作方面的音樂追求完全由詞體所承載,宋代古題樂府已經失去了承載文人復興古樂的審美理想的功能。
2015年10月16日初稿
(作者單位: 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