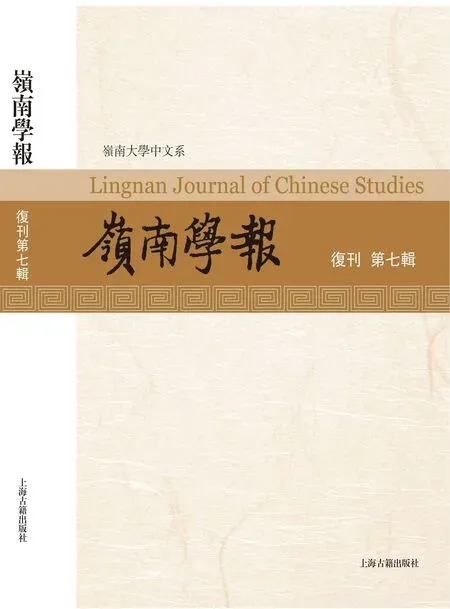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離合
2017-12-18陳才智
陳才智
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離合
陳才智
拙著《元白詩派研究》將晚年與白居易唱和的劉禹錫劃入元白詩派,曾引發異議。確實,歷來文學史對劉禹錫的定位,都是視其爲中唐元白與韓孟兩大詩派之外的優秀詩人,自具風格,别有個性。但劉禹錫晚年的詩歌創作,因爲與白居易交往唱和而有所變化,也同樣是不爭的事實,只是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視而已。二人詩風因交互影響而不免有趨同傾向,歷史上也屢有劉冠白戴的誤判,其中還包括方虚谷、王漁洋和袁隨園等赫赫有名的詩評家。本文擬在詳細排比劉禹錫與白居易交遊唱和詩基礎上,論述他們詩歌創作上的交互影響之跡,以求辨析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離合。
劉禹錫 白居易 元白詩派 交遊唱和 影響 離合
劉禹錫與白居易同年而生,惺惺相惜,二人晚年交遊、唱和甚密,生前即並稱“劉白”,所謂“四海齊名白與劉”*白居易《哭劉尚書夢得二首》其一,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册,第2541頁。,而身後這一齊名狀態則不復存在。早在晚唐批評家張爲的《詩人主客圖》中,二人地位的改變已見端倪,一爲廣大教化派之“主”,一爲瑰奇美麗派之上入室,一主一客,雖不至雲泥而分,但軒輊之别顯然已濫觴於此。儘管也有人曾推崇劉禹錫,説:“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楊慎《升庵詩話》卷一二,見《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册,第889頁。但二人名家與大家之别,今日已成公認。按説劉禹錫登進士第比白早七年之久,出仕亦早,在貞元、元和詩壇上亦聲名早著,當日,“劉、白並稱,中山(劉禹錫)未必甘也”*紀昀批劉禹錫《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之語,見李慶甲《瀛奎律髓彙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9頁。,但論今時之聲名地位,白卻後來居上。乃至焦袁熹(1661~1736)《論詩絶句五十二首》更聲稱:“香山只是憐同調,老子韓非作一家。”並自注云:“夢得詩非求則忮,忮尤可惡,不特玄都二詩也。劉白并稱,是知詩而不知所以詩也。”*《論詩絶句五十二首》(其二十),《萬首論詩絶句》,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册,第278頁。百年人物有誰在,千古聲名無盡時。在文學史上,聲名的指認固然難以量化和定論,但品第甲乙從來没有停止。這裏無意評騭二人聲名高下,只想由此説開,結合二人的交遊、唱和等,探討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離合。
一
元白詩派的領袖是白居易,向無疑義。詩派成員衆多,而晚年與白居易交往密切、唱和頻頻的劉禹錫,因爲身份、地位較特殊,創作上又自具風格,别有個性,所以一般文學史多將其單列,並無歸入元白詩派者。因此,當拙著《元白詩派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將晚年與白居易唱和的劉禹錫劃入元白詩派,曾引起異議。確實,一般而言,甘入某流某派者,多爲二三流,罕有名家大家,尤其是明清詩壇,所謂拉大旗作虎皮也。劉禹錫豈能與之同列?何況,與活躍在詩壇中心的白居易不同,劉禹錫一生大半在窮僻荒遠的貶所度過,苦悶哀怨與執著不屈交織,成爲他詩歌的底色,同香山優遊林下的閑適沖淡形成對比。從詩風上看,一豪邁俊爽,一平易淺淡,迥然有别,劉之高華與白之通俗之間,亦難以混同。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稱:“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洵爲知言,正以慧眼道出夢得“詩豪”的特質。但耐人尋味的是,樂天自己也曾屢爲後人稱作“詩豪”*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一:“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68頁)王逢《讀白寓齋詩》:“太白南流昴漸高,樂天退隱擅詩豪。”(《四庫全書》本《梧溪集》卷四)夏之蓉《讀白香山詩集》:“一代詩豪孰與儔,最清微處費冥搜。”(《半舫齋編年詩》卷一九,《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夏味堂等刻本。),可見其詩風之廣大,之多樣,之與夢得有趨同之處。
劉白之趨同,歷史上曾引起白冠劉戴或劉冠白戴的誤判,其中還包括方回、王士禛和袁枚這樣赫赫有名的詩評家。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寄贈類”收録《寄李蘄州》七律一首:“下車書奏龔黄課,動筆詩傳鮑謝風。江郡謳謡誇杜母,洛陽歡會憶車公。笛愁春盡梅花裏,簟泠秋生薤葉中(蘄州出好笛,並薤葉簟)。不道蘄州歌酒少,使君難稱與誰同。”歸爲劉賓客之作,何焯點評:“寄詩卻切蘄州事,春秋二句點化固妙,然章法又不甚緊,所以七言四韻須教夢得獨步也。”*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4册,第2352頁。紀昀批曰:“前四句太庸濫。”許印芳議道:“四句用六箇古人,太堆砌,亦太猥雜。”*李慶甲《瀛奎律髓彙評》,第1506頁。實際上,正如馮班所辨:“此首白居易作”。方回心目中:“劉夢得詩格高,在元、白之上,長慶以後詩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曉,不吃氣力,别無暗昧關鎖。”*李慶甲《瀛奎律髓彙評》,第1740頁。但這還不是他將這首詩白冠劉戴的具體原因,具體原因應該是開成三年(838)李播赴任蘄州刺史時,劉、白均有七律之作送行,劉詩《送蘄州李郎中赴任》云:“楚關蘄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薤葉照人呈夏簟,松花滿碗試新茶。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北地交親長引領,早將玄鬢到京華。”*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21頁。其中寫蘄州特産的“薤葉照人呈夏簟”一句,與上引白詩“簟泠秋生薤葉中”出典用語均略相似,因此致誤。相比之下,劉詩頸聯“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爲晚霞”,一用庾亮,一用謝朓,但讀之使人不覺,儘管也受到“纖巧”*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二十九,杜維沫校點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頁。的批評,但較白詩《寄李蘄州》前四句堆砌六個古人確實更有詩味。
再來看劉冠白戴的誤判,白居易《劉白唱和集解》曾激賞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號稱“一代正宗”*袁枚《隨園詩話》卷二:“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 俱爲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其《論詩絶句》:“一代正宗才力弱,望溪文集阮亭詩。”王士禛門人史申義《題帶經堂集後柬程聖跂》亦曾云:“鴻文一代仰宗師,心苦編摩愛者誰。”鄭江《拙隱齋集序》:“我朝王漁洋先生集宋元明人之大成……詩人之詩惟漁洋先生爲孤詣、爲正傳。”(沈廷芳《拙隱齋集》卷首,《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98册)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卷四十六:“本朝詩家以漁洋爲正宗。”沈廷芳《研精齋詩序》:“新城王尚書獨標此旨,世稱正宗。百餘年間,流派既殊,踵武者罕。”(《拙隱齋集》卷三八,《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98册)李元度《王文簡公事略》:“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公以詩鳴海内五十餘年,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之爲泰山北斗。”(《清朝先正事略》卷六)胡薇元《題周誠甫江左三大家集虞山集後》:“一代正宗王貽上,瓣香私淑只虞山。”(《夢痕館詩話》卷四)、“一代之宗”*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二稱許王漁洋:“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爲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今家有其書,户習其説,蓋自韓、蘇二公以後,求其才足以包孕餘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别裁僞體,六百年來未有盛於先生者也。”(臺北: 廣文書局1971年影印本,第112—113頁)、“一代宗匠”*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王新城詩,一代宗匠,總是風騷絶世。”(《清詩話續編》第1658頁)茹綸常《題漁洋山人詩後》:“一代文章仰巨公,瓣香爭欲拜涪翁。”(《容齋詩集》卷一)單可惠《題國朝六家詩鈔後·王貽上》:“領袖群公一代奇,生前身後九重知。”(《射鷹樓詩話》卷十七)翁心存《論詩絶句十八首》其一:“一代文章正始音,漁洋三昧印禪心。”(《知止齋詩集》卷二)、“一代宗工”*秦朝釪《消寒詩話》:“阮亭喜風調,尚標格,爲詩家一代宗工。”、“一代詩宗”*方廷楷《習靜齋詩話》卷二:“王阮亭爲一代詩宗。”袁嘉穀《卧雪詩話》卷一:“阮亭一代風雅,壇坫盟主。”金震《書王漁洋詩集四首》其二:“一代詩名推正主,落箋堂與帶經堂。”(《東廬詩鈔》卷六)的王漁洋那裏,居然被視爲白樂天的詩句。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六“表語本樂天詩”一則云:“宋任忠厚(惇)坐上書入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啓云:‘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閲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王士禛著,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93頁。而同書卷十四及《香祖筆記》卷五明明又稱,樂天作《劉白唱和集解》獨舉夢得“沉舟”一聯以爲神妙,看來多半是王漁洋意氣之餘的記憶短路。這意氣源自與趙執信的擡杠。趙執信《談龍録》載:“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葉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云:‘我所不解。’阮翁……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趙執信著,趙蔚芝、劉聿鑫注釋《談龍録注釋》,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39頁。王漁洋詩尚神韻,故薄斥以直白淺易著稱的樂天,以致劉冠白戴——即使是千古警句,沉鬱豪放,且正切己境與酬贈當下之景,王漁洋眼中亦是“下劣”,下劣之句,自然下意識就歸入自己心目中所薄斥的樂天名下。其後居然仍有以訛傳訛者——乾隆間,山東即墨學者黄立世《柱山詩話》即云:“香山‘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阮翁非之,是也。秋谷極口稱讚,何也?豈好詆阮翁,必使之無完膚耶?”*山東省博物館藏高氏辨泂居齊魯遺書鈔本《柱山詩話》。這位忙著拉偏架的學者,居然如此不學,也算罕見。
王漁洋另有一處關於劉白之詩的誤判,其《香祖筆記》載:“《丹鉛録》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絶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别,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説載板橋三娘子事即此,與謝玄輝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庵博極群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王士禛著《香祖筆記》,《四庫全書》本卷五;湛之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頁。又見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夏閎校點《帶經堂詩話》卷一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頁。此前之《池北偶談》卷十三“板橋詩”一則亦云:“白氏集有板橋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顔橋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今訛作劉夢得,而説者疑《中山集》不載此詩,蓋未考《長慶集》耳。”*王士禛著,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16頁。按,白詩題爲《板橋路》,“三十里”一作“二十里”。*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1298頁。《香祖筆記》所引楊慎《丹鉛録》云云,又見《升庵詩話》卷七,惟末尾多出一句:“然此詩櫽括白香山古詩爲一絶,而其妙如此。”*《歷代詩話續編》,第777頁。升庵《絶句衍義》卷二、《百琲明珠》卷一均收録《柳枝詞》七言絶,署名周德華。*王文才、萬光治主編《楊升庵叢書》,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6册,第229、439頁。《絶句衍義》並於詩後注云:“周德華,鏡湖妓劉采春女也。此詩櫽括白香山古詩爲七言絶,而其妙思如此,真花月之妖也。”楊升庵劉冠周戴,確有未諦,但並未如王漁洋所云白冠劉戴。白詩七言三韻,劉詩據之删削改易爲七絶,出處須注明,但版權還是劉,而漁洋恰恰忽略了升庵業已點明的“櫽括白香山”云云。櫽括削改後的“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别,恨無消息到今朝”,其實愈加凝練精彩,也更適合歌唱,原創者樂天想必也要承認其鍛煉磨礱之功。
與素來不喜香山詩風的王漁洋不同,號稱“詩學白傅”*袁枚《讀白太傅集三首·序》:“人多稱余詩學白傅,自慚平時於公集殊未宣究。今年從嶺南歸,在香亭處借《長慶集》,舟中讀之,始知陽貨無心,貌類孔子。”(《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周本淳標校本《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819頁)參見石玲《袁枚詩與白居易詩之“貌類”及内在成因》,《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的袁枚居然也劉冠白戴,可謂更令人吃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云:“唐人詩曰:‘欲折垂楊葉,回頭見鬢絲。’又曰:‘久不開明鏡,多應爲白頭。’皆傷老之詩也。不如香山作壯語曰:‘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又,宋人云:‘勸君莫惱鬢毛斑,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被風吹上北邙山!’”*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版,第332頁。按,“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並非香山之壯語,乃是劉禹錫《酬樂天詠老見示》中的名聯。“餘霞”原作“微霞”,又作“爲霞”。開成二年(837),66歲的白少傅《詠老贈夢得》云:“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澀夜先卧,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疏。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餘。”*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4册,第2236頁。劉禹錫《酬樂天詠老見示》答道:“人誰不願老,老去有誰憐?身瘦帶頻減,髮稀冠自偏。廢書緣惜眼,多炙爲隨年。經事還諳事,閲人如閲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第1261頁。四語中極起伏之勢。結句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堪與其“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劉禹錫《贈樂天》,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嶽麓書社2003年版,上册,第549頁。之句並美,實難爲樂天所掠美。袁枚的這一劉冠白戴,大概可以視爲對貌類而心儀的學習對象白香山之擡舉,好在此時香山確也英華未衰,此後“餘霞”尚比劉禹錫多了四年。其實,在上引《隨園詩話》的語境裏,香山自有“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這聯壯語,見於《洛陽有愚叟》一詩*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4册,第2056頁。,是大和八年(834)63歲在洛陽任太子賓客分司所作,明人陳洪綬還曾反其語句,書爲“任頭生白髮,放眼看青山”一副對聯,以示曠達自適之心態,不知袁枚爲何没有想起。
二
將劉禹錫歸入元白詩派,不僅源自二人並稱齊名,更因爲詩風詩境之趨同,堪稱文友詩敵。毛奇齡《西河詩話》曾分析:
白居易與劉禹錫齊名,又與元稹齊名,當時有《劉白集》,又有《元白長慶集》,而白並不辭,世亦疑之。予謂夢得與樂天原可肩並,元則卑劣抑下矣,白豈不自知,而甘與頡頏。蓋其時丁開、寶全盛之後,貞元諸君皆怯於舊法,思降爲通侻之習,而樂天創之,微之、夢得並起而效之,故樂天第喜其德鄰之廣,而不事較量。然猶自言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則亦若有不甘於並名者。夫既創斯體,已置身升降之際,使能者爲之,不過舍謐(密)就疏,舍方就圜(圓),舍官樣而就家常。而自不能者效之,則卑格貧相,小家數,駔儈氣,無所不至。幸樂天才高,縱卑貧小巧,而意能發攄,力能搏捖,才與氣能克斥布濩,而所在周給。老元短李,又何能爲!白所自言,固審耳。*毛奇齡《西河合集·詩話》卷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間書留草堂刻本,集部第420册,第566—567頁。
分析元和詩壇通侻(脱)風習的興起,指出傾向通脱之風的詩人形成創作群體,其主創爲白居易,其並起而效之的主要成員有劉禹錫與元稹,圍繞著這一詩歌群體所共同具有的通脱放達的藝術傾向,他們在詩歌創作中有三點共性: (一) 詩歌意象結構由細密而趨疏朗,(二) 遣詞造句由方正而趨圓融,(三) 主題與取材捨官樣而就家常。這是對元和詩風變化較爲準確的歸納。方世舉《蘭叢詩話》論承繼老杜五七言律詩者,“白香山之疏以達,劉夢得之圜以閎”*《清詩話續編》,第773頁。,均可爲初學唐詩之導引,與上引毛奇齡所云三點共性有相通之處。毛奇齡詩學少好宋元,後轉宗唐*參見蔣寅《清初錢塘詩人和毛奇齡的詩學傾向》,《湖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其所宗之唐,不廢中晚。他給丁克揚《琴溪合稿》所作之序云:“自夫論詩者好言初盛,遂致貞元、元和以後棄置不問,而昔有終身爲詩,始悟《長慶集》之不易爲者。”*毛奇齡《琴溪合稿序》,《四庫全書》本《西河集》卷三七。上引對元和詩風之變代表人物元、白、劉三人的歸納,可以追溯至《新唐書·文藝傳序》,其中言詩除杜甫、李白之外,即元稹、白居易、劉禹錫三人,“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新唐書》卷二一,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8册,第5726頁。。至於推尊“樂天創之”,毛奇齡《唐七律選》也有類似評説,中云:“樂天爲中唐一大作手,其七古五排,空前掩後,獨七律下乘耳,然猶領袖元和、長慶間,寶、太以後竊脂乞澤者,越若干年亦文豪也,若同時倡和,爭相摩仿,終不得似。此如東家效西家,才分懸遠。老元、短李,久在下邽嗤笑中矣,但黄鐘大吕鏗鍧已久,既降細響,則蝸吟蚓呻,自所不免,兹擇其於卑格貧相、小家數、駔儈氣不甚浸淫者,備録於篇,以厭時好之目。”*毛奇齡《唐七律選》卷三序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清刊本。詩選之評與其詩話之論正可參照。
毛奇齡爲人好辨,有時不免强作解事,如論蘇軾詩“春江水暖鴨先知”之類。上引論元和詩風之變,沈德潛曾提出異議,其雍正九年(1731)所撰《説詩晬語》卷上云:“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詘劉,每難測其指趣。”*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頁。説毛大可尊白是不錯,但他並未詘劉,只是以“卑劣抑下”詘元稹而已,稍帶也批評了江湖間元和體末流妄相仿效,卑格貧相的小家數和駔儈氣。沈德潛早年編選的《唐詩宗》卷一二及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删《唐詩宗》而成的十卷本《唐詩别裁集》卷八中,持論與《説詩晬語》相仿:“中唐七律,夢得可繼隨州,後人與樂天並稱,因劉、白有唱和詩耳,神彩骨幹,惡可同日語?”語詞亦頗爲近似。而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訂的二十卷本《唐詩别裁集》卷十五中,關於劉禹錫七言律詩的評語則訂正爲:“大曆後詩,夢得高於文房。與白傅唱和,故稱劉、白。實劉以風格勝,白以近情勝,各自成家,不相肖也。”*沈德潛著,富壽蓀校點《唐詩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頁。其實,毛大可將劉禹錫列入白居易所創元和通脱詩風的追隨者,並未屈就其地位。
Outcome analysis and reporting:according to formalized procedural protocols,a detailed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n will be created prior to study initiation.
劉、白二人地位之高下,在他們在世之日即有辯説,白居易作爲當事人表示,儘管彭城劉夢得“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但他並未服軟,稱“予不量力,往往犯之”,結果“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劉白唱和集解》),可見不相上下。當然,對《石頭城》“潮打空城寂寞回”,白居易還是服善讓能,據劉禹錫講,不僅嘆賞良久,並且説:“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見劉禹錫《金陵五題·序》,《劉賓客文集》卷二十四,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嶽麓書社2003年版,上册,第390頁。而史上盛傳的“金陵懷古”同題競賽,劉禹錫探龍獲珠,白居易等罷唱,*何光遠《鑒誡録》卷七“四公會”:“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朝興廢之事。樂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今群公畢集,不可徒然。請各賦《金陵懷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時夢得方有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劉騁其俊才,略無遜讓。滿斟一巨杯,請爲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吟詠竟日,沈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王化,兩岸蕭蕭蘆荻秋。’”(《叢書集成初編》第2843册,第51頁)參見《唐詩紀事》卷三九,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巴蜀書社1989年版,上册,第1070頁;《全唐詩話》卷三,《歷代詩話》第125頁。則因所云時間、地點多有不合之處,恐爲傳訛附會*見卞孝萱《劉禹錫年譜》,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20—121頁;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第670頁。。開成三年(838),因爲好五言詩的唐文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翰林學士推薦了名單,宰相楊嗣復聲稱:“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册,第149頁。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唐)上”云:“文宗欲置詩學士,固非急務,然非雅尚不能。李玨奏罷,未爲無見,第以憲宗爲詩,釀成輕薄之風,中間聱牙崛奇,譏諷時事,明指韓、柳、元、白諸公,此大是無識妄人。唐一代之文,所以能與漢并,正賴數君,豈俗子所解。乃憲宗興起之風,可與漢武、唐文相次。淮、蔡之勛,尚出此下,而史不略言,故余特詳著焉。樂天有諷諫詩,元稹、李紳有新樂府。”(王國安校補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頁)《資治通鑑》卷二四六:“(文宗開成三年)上好詩,嘗欲置詩學士;李玨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7938頁)可見劉禹錫聲名之盛。可惜被人聯繫起從前元白始作俑並風行一時的“元和體”,因爲擔心玷黯王化,實非小事,於是不了了之。但劉白二人詩壇地位之不相上下,已按下伏筆。官方史書《舊唐書》既在《元白傳論贊》聲稱:“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舊唐書》卷一六六,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册,第4360頁。,同時也於《劉禹錫傳》表明:“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舊唐書》卷一六,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3册,第4212頁。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九徑襲此語(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上册,第1073頁)。
分析後世劉、白二人高下的形成史,約有兩派,一派認爲劉不及白,如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一七云:“禹錫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82頁。明人楊士雲《詠史·白樂天》:“吟醉先生幾石樽,香山居士半桑門。誰言元白還劉白,只恐元劉落後塵。”*《楊弘山先生存稿》卷二,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第114册,第727頁。明人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二九云:“劉雖與白齊名,而其集變體實少,五、七言古及五言律俱未爲工。”*《詩源辯體》杜維沫校點本,第281頁。清人趙駿烈《劉賓客詩集序》云:“元和、長慶諸公,與香山唱和齊名者,劉賓客爲稱首。……大約劉之比白,邊幅稍狹,而精詣未之或遜。”*臺灣圖書館藏《劉賓客文集》卷首,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下册,第1511頁。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一云:“劉固詩豪,白乃詩仙。……在當時則劉白齊名,日久論定,劉終不能逾白也。”*《清詩話續編》,第1755頁。康發祥(1788—1865)《伯山詩話前集》云:“與香山倡和者,則有元微之稹,世稱爲元白: 後有劉夢得禹錫,世稱爲劉白。香山叙劉詩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其推崇之也甚矣。愚按: 其詩殊難與白比,其古詩亦是長慶體,而沈鬱頓挫處尚少。”另一派認爲白不及劉,如元人方回心目中,“夢得詩句句精絶,其集曾自删選,故多佳者,視樂天之易不侔也。”*《瀛奎律髓》卷二四“送别類”,李慶甲《瀛奎律髓彙評》,第1072頁。“劉夢得詩格高,在元、白之上,長慶以後詩人皆不能及,且是句句分曉,不吃氣力,别無暗昧關鎖。”*《瀛奎律髓》卷四七“釋梵類”,李慶甲《瀛奎律髓彙評》,第1740頁。紀昀批曰:“論夢得是,然以論夢得此二詩則未是。二詩乃夢得之不佳者。”二詩指《酬淮南廖參謀秋夕見過之作》、《送景玄師東歸》。明人黎民表《書劉中山别集卷首》亦稱:“中山於唐元和間有雋名,文稍亞於韓、柳,世謂之‘劉柳’,其詩則元、白諸人遠不逮也。”*臺灣圖書館藏《劉賓客文集》卷首,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下册,第1510頁。均爲上引沈德潛《説詩晬語》意見之先聲,喬億《劍溪説詩又編》以爲:“劉禹錫七言律絶,……並出樂天之右。樂天只長律擅場,亦無子厚筆力也。而當日名播雞林,後人多宗之,良由諸體贍博,盡疏快宜人耳。”*《清詩話續編》,第1126頁。同調還有《四庫全書總目·劉賓客文集提要》云:“其詩則含蓄不足,而精鋭有餘。氣骨亦在元、白上,均可與杜牧相頡頏,而詩尤矯出。”*《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整理本卷一五,中華書局1997年版,下册,第2009頁。民國間丁儀《詩學淵源》卷八《名人小傳詩品》甚至認爲:“元和詩人,(劉禹錫)自當首屈一指。韓、劉、元、白雖屬異曲,未見同工也。”*《民國詩話叢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册,第207頁。今天看來,正如瞿蛻園所云:“元、白、劉三人同開元和新派,各成壁壘。而居易能知人,能服善,此所以得廣大教主之稱歟!”*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劉禹錫交遊録》,第1606頁。知人服善,非僅詩藝也。看來,論詩之道,有時也是功夫在詩外。
三
儘管劉前期詩風之俊爽高華,後期詩風之雄渾老辣,與元白的淺切平易不相肖,但如果從交遊的密切、唱和聯句的頻繁來看,晚年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脗合之處,要多於疏離之端。劉白交遊可以按照二人唱和詩的四次結集爲綫索加以勾勒。具體的復原工作,因爲《劉白唱和集》編排以時間先後爲序,而今存《劉賓客文集·外集》之唱和詩,即宋敏求自《劉白唱和集》中裒出者,保留了原集的編次,因此給復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此後,日本學者花房英樹、柴格朗、橘英範等,中國學者熊飛、賈晉華、王卓華、王艷玲等均曾作過進一步的努力*花房英樹《〈劉白唱和集〉稿》,《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人文)12,1960年12月,第1—28頁,後收入其《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年3月);柴格朗《劉白唱和考》,《中國語文志》(京都産業大學外國語學部中國語文研究會),1961年;《〈劉白吳洛寄和卷〉中所表現的劉禹錫對政界的執著》,《中唐文學會報》(日本中唐文學會)8,2001年10月;柴格朗譯注《劉白唱和集》,東京勉誠社,2004年7月;橘英範《劉白唱和詩復原的問題》,《中國中世文學研究》(廣島大學中國中世文學研究會)20,1991年2月;《劉白唱和詩研究序説》,載《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5卷特輯號3(1995);《關於劉白的聯句》,《中國中世文學研究》31,1997年1月;《中唐唱和文學的發展——走向〈劉白唱和集〉之路》,《日本中國學會報》(日本中國學會)第60集,2008年。熊飛《劉禹錫、白居易唱和詩簡論》(《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及《〈劉白唱和集〉編集流散考》(《唐都學刊》1997年第4期);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王卓華《從幾部唐代唱和總集看劉禹錫的唱和詩》(《殷都學刊》2005年第4期);王艷玲《劉白詩人群的唱和活動及其詩歌創作——以劉白唱和詩的四次結集爲中心》(《天津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此外學位論文方面,可供參考者,還有王玫《劉禹錫白居易唱和詩研究》,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2年5月,導師鄧小軍;王曼霏《劉白唱和詩研究》,廣西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年7月,導師李寅生;付瑶《劉禹錫唱和詩研究》,新疆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6月,導師薛天緯;張育樺《劉禹錫、白居易交往詩研究》,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8月,導師簡貴雀。。筆者在博士畢業論文《元白詩派成立之研究》(2000)基礎之上,復編訂《白居易資料新編》,於劉白唱和集復有補訂。*其中劉詩繫年參照卞孝萱《劉禹錫年譜》(中華書局1966年版)、高志忠《劉禹錫詩文繫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蔣維崧等《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和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嶽麓書社2003年版)。白詩繫年參照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此毋須贅,僅列四次結集爲下表,以見其概況。

劉白唱和之結集

續 表
從《劉白唱和集》看,二人交遊始於元和五年(810),翰林學士白居易將詩作百篇寄給被貶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已有五年的劉禹錫,元稹也是在這一年開始與劉禹錫唱和,白主動寄詩當因元稹之介。*卞孝萱《劉禹錫叢考·交遊考》,巴蜀書社1988年版,第196頁;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103頁。劉禹錫答以《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吟君遺我百篇詩,使我獨坐形神馳。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102頁。此詩收入《劉賓客文集》外集,爲卷一壓卷之作,開篇第二句稱,讀白詩而坐形神馳,與劉禹錫《董氏武陵集紀》所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里,工於詩者能之”可以參觀。結尾誇白詩並世無二,大概緣於初交,不免溢美,但中間兩聯,盛讚白詩如琴韻悠揚,玉聲清越,且匠心獨運,自然渾成,如郢人運金,毫無斧鑿之痕,似仙人裁衣,不用刀尺之功,顯然出自詩友之間真切的體認。正如趙翼《甌北詩話》卷四所云:“香山主於用意,用意則屬對排偶,轉不能縱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詩,則惟意所之,辨才無礙。且其筆快如并剪,鋭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鍊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劉夢得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者,此(香山)古體所以獨絶也。然近體中五言排律,或百韻,或數十韻,皆研鍊精切,語工而詞贍,氣勁而神完,雖千百言亦沛然有餘,無一懈筆。當時元、白唱和,雄視百代者正在此。”*《清詩話續編》,第1174—1175頁。後來陸游《九月一日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即師此意。值得一提的是,何焯於劉禹錫此詩之批語留意到:“夢得别集七言律詩,大抵多效白公之體,但起結多恨其過於平直。”*卞孝萱《劉禹錫詩何焯批語考訂》,《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頁。可見在二人唱和之始,劉禹錫即有意識向樂天詩風靠攏。
長慶二年(822)正月,劉禹錫任夔州刺史時,有《始至雲安寄兵部韓侍郎中書白舍人二公近曾遠守故有屬焉》,表達對兵部侍郎韓愈、中書舍人白居易在京爲官的欽羨,中云:“故人青霞意,飛舞集蓬瀛。昔曾在池籞,應知魚鳥情。”*《劉夢得文集》外集卷一,四部叢刊景宋本;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279頁。長慶三年(823),白居易作《杭州春望》:“望海樓明照曙霞(城東樓名望海樓),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青旗沽酒趁梨花(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緑裙腰一道斜(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緑時望如裙腰)。”*《白居易集箋校》,第3册,第1364頁。次年(824),劉禹錫答以《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詩有“柳色春藏蘇小家”之句因而戲酬兼寄浙東元相公》:“錢塘山水有奇聲,暫謫仙官守百城。女妓還聞名小小,使君誰許唤卿卿。鰲驚震海風雷起,蜃鬬嘘天樓閣成。莫道騷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劉禹錫集箋證》,第1032頁。白詩中首句之“望海樓”在杭州鳳凰山。頷聯“入”字、“藏”字,極寫望中之景,伍員即伍子胥,伍員死,吳王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蘇小,指南齊錢塘名妓蘇小小,才空士類,容華絶世。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有“杭州蘇小小,人道最夭斜”。“柿蒂”是杭産綾絹所織之花紋,“梨花”是杭州美酒的名稱。落句結足春意。禹錫和詩第一句中“奇聲”,是説異樣聲名。“仙官”指居易曾爲中書舍人,極清華之選而出。“守”一作“領”。三、四句言雖有名妓蘇小小,然不許命使君以卿卿也。諧謔之語卻精極。五句“鰲驚”言刺史之雷厲風行。六句言舍人之文詞燦麗。“莫道”句説向云騷人詩思盛於三楚,故有屈原、宋玉輩,如今文星都改到吳越來了(“斗牛”間,杭與越之星野也)。這首詩通體清穩,可以和白居易原作旗鼓相當。説文星改照到吳越之間,又是何等自負!
寶曆二年(826),當時劉禹錫卸任和州刺史,經揚州回洛陽,與自蘇州北歸的白居易相逢於揚子津,一見如故,白居易作《醉贈劉二十八使君》:“爲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集箋校》,第3册,第1706頁。劉禹錫答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劉禹錫集箋證》,第1047頁。劉詩回贈接過白詩話頭,既抒寫出那一特定環境中的感情,又藴含著貶官二十多年後回鄉的深沉感嘆。那一年兩人都是55歲,回溯到貞元十九年癸未(803),他們都是32歲,禹錫在京官監察御史,居易職爲校書郎,住常樂里。二十三年過去,難免欷歔慨嘆。可頸聯卻突然振起,化沉鬱爲通達,變悲怨而樂觀,寫沉舟側畔,千帆競發;病樹前頭,萬木爭榮。在自然界的平凡現象中,暗示社會人事新陳代謝的哲理,意象新奇壯麗,寓意深長,較之樂天之“命壓人頭不奈何”確實較勝一籌。難怪樂天稱贊這兩句詩“神妙”,“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劉白唱和集解》),清人趙執信《談龍録》更推許爲“有道之言”,至今仍常常被人引用,並賦予新的意義,説明新事物必將取代舊事物的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類似閃爍著清剛的理性之光的詩句,劉禹錫還有“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秋詞》),都是對宇宙與自然沉思之後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裏,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空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的一種交融。
大和二年(828),劉、白都在長安,多有活動,與張籍同遊杏園,白有《杏園花下贈劉郎中》,劉有《杏園花下酬樂天見贈》;劉、白都參加的聯句,有《杏園聯句》、《花下醉中聯句》、《首夏猶清和聯句》、《薔薇花聯句》、《西池落泉聯句》。之後,劉禹錫在長安、蘇州、汝州等地,與白居易唱和不斷。大和三年(829)白居易歸洛後,劉禹錫有《遥和白賓客分司初到洛中戲呈馮尹》,這是白退閑後,劉、白頻繁唱和的開始,時劉在長安任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開成元年(836),劉禹錫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白居易其時已在洛陽,兩人再次相聚,因爲都以分司身份生活於洛陽,有相對自由的時間彼此唱和,交往更密,正如劉禹錫《汝洛集引》所説:“予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歡。”*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下册,第1230頁。劉、白的深契,主要是此後一段時間。如開成二年(837)夏,白居易有《分司洛中多暇數與諸客宴遊醉後狂吟偶成十韻因招夢得賓客兼呈思黯奇章公》云:“性與時相遠,身將世兩忘。寄名朝士籍,寓興少年場。老豈無談笑?貧猶有酒漿。隨時求伴侣,逐日用風光。數數遊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榮啓樂,人恕接輿狂。改業爲逋客,移家住醉鄉。不論招夢得,兼擬誘奇章。要路風波險,權門市井忙。世間無可戀,不是不思量。”*《白居易集箋校》,第4册,第2323頁。其中“身將世兩忘”,引申鮑照《詠史》“身世兩相棄”之意,與此前元和三年《偶作》“是非一以貫,身世交相忘”,元和五年《適意》“悠悠身與世,從此兩相棄”,元和七年《詠興五首》其三《池上有小舟》“我今異於是,身世交相忘”,元和九年《退居渭村寄禮部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末二句“可憐身與世,從此兩相忘”,元和十二年《閉關》“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大和八年《詠懷》“由兹兩相忘,因得長自遂”,大和九年《詔下》“我心與世兩相忘,時事雖聞如不聞”等,一脈而承。劉禹錫答以《酬樂天醉後狂吟十韻(來章有“移家住醉鄉”之句)》詩:“散誕人間樂,逍遥地上仙。詩家登逸品,釋氏悟真筌。制誥留臺閣,歌詞入管弦。處身於木雁,任世變桑田。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八關齋適罷,三雅興尤偏。文墨中年舊,松筠晚歲堅。魚書曾替代,香火有因緣。欲向醉鄉去,猶爲色界牽。好吹《楊柳》曲,爲我舞金鈿。”*《劉禹錫集箋證》,第1266頁,《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672頁。“散誕人間樂,逍遥地上仙”,説出“中隱”生活的快意;“醉鄉”、“色界”、“香火”、“管弦”、“歌詞”等,寫出“中隱”生活的内容;“處身於木雁,任世變桑田。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對白居易“中隱”思想本質特徵加以概括,相當準確。
開成三年(838)元日,白訪劉,白贈以《新歲贈夢得》,劉答以《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晚夏,白訪劉,白寄《晚夏閑居,絶無賓客,欲尋夢得,先寄此詩》,劉答《酬樂天晚夏閑居欲相訪先以詩見貽》。秋日,劉又訪白,白寄示《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夢得相過援琴命酒因彈秋思偶詠所懷兼寄繼之待價二明府》,劉酬以《樂天以愚相訪沽酒致歡因成七言聊以奉答》。舉此可以概見二人交遊之頻繁。此間劉詩不乏仿白之作,如開成五年(840),白有《楊柳枝》:“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陽橋。”*《白居易集箋校》,第4册,第2167頁。劉禹錫和詩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劉禹錫集箋證》,第858頁。范晞文《對床夜語》即斷爲“仿白”之作*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五,《歷代詩話續編》,第442頁。。寶曆二年(826),白居易《正月三日閒行》云:“緑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大和六年(832),劉禹錫《樂天寄憶舊游因作報白君以答》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楊慎以此作爲“唐人詩句,不厭雷同”之例證。此外,如前所述,劉禹錫還有櫽括白香山古詩《板橋路》的《柳枝詞》。
四
全部《劉白唱和集》,共137組唱和詩作,已超過《元白唱和集》的111組。其浩博堪稱詩史一大奇觀。劉、白唱和詩之詩體,由多至少,依次爲七律、七絶、五律、五排、五古。劉、白和韻詩詩體,由多至少,依次爲七絶、七律、五律、五排、五古。二者次序基本一致。不過,劉、白唱和在元、白之後,以律體唱和之比例,明顯超過古體,超過元白,這也是中晚唐以還律體逐漸成熟壯大趨勢的反映。劉、白和韻詩佔同體唱和詩的比例,由大至小依次爲七絶、七律、五排、五古、五律,與元、白和韻詩情況略有不同。在比例上,劉白唱和詩與元白唱和詩一樣,所占各自全部詩作之比例,都相當可觀。白居易詩2830首、劉禹錫詩884首。其中,因白集保存較爲完整,唱和對象較多,故比例稍小;而元集、劉集唱和詩有散佚,且唱和對象主要是白居易,故比例稍高。劉白唱和詩與元白唱和詩中,後者和韵詩所占比例稍高于前者。劉白和韵詩與元白和韵詩中,後者次韵詩所占比例遠遠超過前者。

劉、白唱和詩之詩體
劉、白唱和詩之浩博,足以佐證劉禹錫與元白詩派的親合度。如果細相比對,可以發現,劉白二人在詩風詩境上較量之餘,不乏相互趨同與妥協。何焯《劉禹錫詩》批語對劉白唱和詩尤其留意二人詩作同異的相互比對,如《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曾向空門學坐禪,如今萬事盡忘筌。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心知洛下閑才子,不作詩魔即酒顛。”《八月十五日夜半雲開然後玩月因書一時之景寄呈樂天》:“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清秋。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輝猶可玩,移宴上西樓。”二詩皆批云:“白公體。”《三月三日與樂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飲各賦十二韻》:“洛下今修禊,群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鷺振,歌響雜鶯啼。歷覽風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翠幄連雲起,香車向道齊。人誇綾步障,馬惜錦障泥。塵暗宫墻外,霞明苑樹西。舟形隨鷁轉,橋影與虹低。川色晴猶遠,烏聲暮欲棲。唯餘踏青伴,待月魏王堤。”批語云:“樂天固不可及,此作亦自秀整。齊韻容易窘人,非夢得幾於擱筆矣。”《題于家公主舊宅》:“樹繞荒臺葉滿池,簫聲一絶草蟲悲。鄰家猶學宫人髻,園客爭偷御果枝。馬埒蓬蒿藏狡兔,鳳樓煙雨嘯愁鴟。何郎獨在無恩澤,不似當初傅粉時。”批語云:“比樂天詩更曲折有味,三、四妙絶。馮己蒼(馮舒)極稱此詩,以爲悲涼之中,自饒才致,他人爲此而定薄矣。”《和樂天誚失婢榜者》:“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脱青衣。”批語云:“定翁(馮班)云:‘似勝白。’第三先起後半二句,直是叙得生動。”《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十萬天兵貂錦衣,晉城風日斗生輝。行臺僕射深恩重,從事中郎舊路歸。疊鼓蹙成汾水浪,閃旗驚斷塞鴻飛。邊庭自此無烽火,擁節還來坐紫微。”批語云:“其精切工假如此,樂天‘青衫書記’、‘紅旆將軍’,未免爲渠壓倒。”*卞孝萱《劉禹錫詩何焯批語考訂》,《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202頁。等等,不一而足,皆别具隻眼。
總之,儘管劉禹錫詩自具風格與個性,但晚年創作,因與白居易交往唱和而有所變化,二人在流暢自然的風格特色中找到了共通之處,尤其體現在七言律絶體中,每有異曲同工的含思婉轉之妙。正如明人許學夷《詩源辯體》所云:“考《萬首唐人絶句》,劉(夢得)實有似樂天者,故當時有‘劉白’之稱。”*《詩源辯體》卷二九,杜維沫校點本,第282頁。方世舉《蘭叢詩話》亦云:“(五七絶句)元、白清宛,賓客同之。”*《清詩話續編》,第779頁。後來唐寅、徐禎卿等吳中詩人,不約而同共同師法劉禹錫與白居易,所鍾愛者,也是二人流利自然、語工調協的七言律絶。
進一步追下去,劉白并稱也絶非僅限於七言律絶體。在元白詩派“長慶體”創作上,劉禹錫元和八年(813)任朗州司馬期間所作《泰娘歌》*《劉禹錫集箋證》,第630—631頁;《全唐詩》卷三五六;《增訂注釋全唐詩》第2册,第568頁(余才林撰)。寫作時間,陳寅恪謂作於元和九年(814),見劉隆凱整理《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講席側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頁);卞孝萱《劉禹錫年譜》第72頁和高志忠《劉禹錫詩文繫年》第81、298頁繫於元和元年(806)至元和九年(814),此據陶敏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上册,第137頁。、《傷秦姝行》*《劉禹錫集箋證》,第1014—1015頁;《全唐詩》卷三五六;《增訂注釋全唐詩》第2册,第1574頁(余才林撰)。寫作時間據高志忠《劉禹錫詩文繫年》,第84、283頁。,與元、白“長慶體”的創作時間大致平行,且符合其四個共性——(一) 詩體爲七言歌行體,(二) 内容以叙事爲主,(三) 篇幅爲八句以上的長篇,(四) 韻律上多用律句和轉韻。而且均不約而同,於詩前又加以小序,可以見出這種叙事歌行體的一種風尚。因拙著《元白詩派研究》曾有所論及,此不贅。
綜合以上,可見劉、白二人詩風,因交互影響,亦多有趨同傾向,既有異中之同,也有同中之異。比較之下,異中之同已超過同中之異。將劉禹錫劃入元白詩派,并非僅僅著眼於劉白唱和詩。在不同詩體的創作上,劉禹錫與元白詩派均有相互脗合之跡,且合大於離,這就是劉禹錫可以劃入元白詩派的主要理由。
(作者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