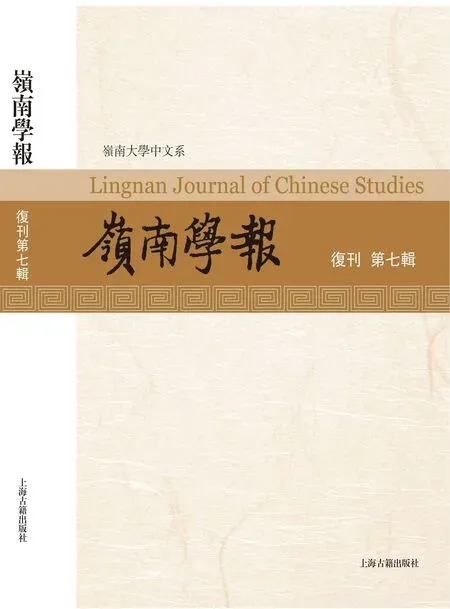仍在胡適的延長綫上
——有關中國學界中古禪史研究之反思
2017-03-10葛兆光
葛兆光
思想史論壇
仍在胡適的延長綫上——有關中國學界中古禪史研究之反思
葛兆光
本文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對於禪宗研究狀況的討論開始,探討在當時“文化熱”背景下禪宗研究存在的問題與方法,並且介紹迄今爲止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狀況。試圖指出,1920—1930年代,胡適開創了中國學界禪宗研究的現代典範,他大力提倡並且身體力行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的方法,至今仍是中國學界在禪宗尤其是禪宗史研究領域最擅長、最有希望也是最有成績的。本文在簡單介紹了日本與歐美禪宗史研究界的各種現狀,並與中國對比之後,强調中國學界關於禪宗尤其是禪宗史研究,至今仍在胡適當年的延長綫上,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至今仍是應當努力的方法。
胡適 禪宗史 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 日本學界有關禪宗史研究 歐美學界有關禪宗史研究 後現代歷史方法
引子: 從高行健説到八十年代禪文化熱
2000年的秋天,我在歐洲訪問,大概是10月12號,比利時魯汶大學的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突然來告訴我説,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給高行健,以表彰他的小説,尤其是《靈山》,對一種文化的深刻描述。這是第一位華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我當然很高興。兩天後我到荷蘭,在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看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藏書,正巧那裏有個朋友希望我講一講中國對於高行健戲劇和小説的感想,我就即興講了一段。記得當時我説的大意是,高行健得獎值得高興,但我始終有一個奇怪的感覺,就是儘管他在法國已經十幾年了,但他好像仍在1980年代的中國,他的小説中關於中國的認識、記憶和想象,好像都來源於1980年代“文化熱”。可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現在中國已經和“文化熱”那個時代不同了。記得當時我還用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典故,感慨無論是身在此山外的歐洲人,還是身在此山中的中國人,如果不瞭解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熱,也許很難體驗和理解高行健《靈山》的文化背景和靈感來源。
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感覺,經歷過中國大陸1980年代“文化熱”的人,都會覺得“記憶停滯在八十年代”*“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主潮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取經”,“至少在過來人當中,大家並没有忘掉那段歷史”。參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録》,北京: 三聯書店2006年版,《寫在前面》,第9、4頁。。爲什麽我講禪宗史研究,要扯到這麽遠呢?因爲在高行健的《靈山》裏,曾經用了很多佛教、禪宗的元素,暗示他想象中的一種荒蠻(貴州)的、邊緣(佛道)的、充滿神秘色彩(靈巫)的文化,這是和西方常識中的中國文化並不一樣的文化,高行健的文化記憶中,就包含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理解的“禪”。就在前些年,我在《明報月刊》2007年第5期上,又看到他和劉再復在巴黎對話,題目居然是“慧能的力度”。高行健在馬賽歌劇院導演《八月雪》,還説“惠能是東方的基督”,惠能“啓發人自救”,而禪是“一種立身的態度,一種審美”。可見,這個對於禪的文化想象在他心裏是很深的。這種有關禪宗的文化想象,現在已經不多見了,但在1980年代是很普遍的。因爲那個時代中國不少學者相信,對於禪宗史的興趣,有關禪文化的熱情,可以衝擊主流政治文化的一統,瓦解傳統儒家思想的固執,改變中國人的實用性格,這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中出現的特别的文化現象。
那麽,那個時代背景是什麽呢?爲什麽那時會對禪宗産生異常興趣呢?這要回頭説到當時中國出現的“文化熱”*關於文化熱,可參考林同奇《文化熱的歷史含意及其多元思想流向》(上)、(下),連載於《當代》(臺北)第86、87輯(1993年6—7月)。亦可以參考陳奎德編《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臺北: 桂冠圖書公司1994年版。。
一、 1980年代中國禪宗研究的政治與文化背景
簡單地説,中國1980年代的“文化熱”,是在一種矛盾心態中形成的。一方面,當時的人們在理智上大都嚮往現代化,因爲人們相信這樣一些格言:“落後是要挨打的”,是要被“開除球籍”的。因此,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思想世界基本上仍在“五四”甚至晚清以來“尋求富强”的脈絡之中。在這種被史華兹(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稱爲“尋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也就是奔向現代化的心情中*這是史華兹一部有關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作的書名,即葉鳳美譯《尋求富强: 嚴復與西方》,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科學、民主、自由等等普世價值,在經歷過“文革”的人看來,仍然是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因此,魯迅的“批判國民性”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批判傳統的聲音還很强。特别是,由於不好直接批判政治的弊病和追究政黨的責任,就讓文化傳統爲我們“還債”。所以,就像“伍子胥鞭屍”一樣,當時很多研究歷史和文化的人,就會發掘傳統文化中間那些導致中國封閉、落後、蒙昧的因素。這個時候,儒家、佛教、道教就統統被翻出來,重新放在聚光燈下和手術臺上。
可是,還有另一方面。畢竟都是中國的知識人,對於自身的傳統和歷史,本來就多少有一些依戀的感情,而且傳統的天朝大國心態,也讓中國人不那麽甘心或者不那麽服貼於西方文化,總覺得中國傳統還是有現代資源的。所以,對於那種符合士大夫口味的禪宗,包括那些自由的思想、反叛的行爲、怪異的公案,都很有興趣。所以,在批判的同時也不免有點兒留情,對它的好感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後門溜進來。像我自己寫《禪宗與中國文化》那本書,在談到它造成文人士大夫心理内向封閉的時候,可能批判的意味很重,但談到它追求“幽深清遠”的審美情趣時,又往往不自覺地稱讚。特别是,當時中國一批“尋根”小説家,他們在發掘中國文化資源的時候,覺得歷來佔據正統的儒家很保守,古代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很没有意思,中原的、漢族的、秩序感和道德感都很强的文化也很乏味。因此,文學家們常常去發掘那些怪異、反叛和邊緣的東西。因而佛教禪宗、道家道教、巫覡之風、西南或西北少數民族,就開始被濃墨重彩地想象和渲染。像當時韓少功《爸爸爸》、王安憶《小鮑莊》、賈平凹《臘月正月》等等,其中多多少少都有這方面的趨向。高行健也不例外地受到這一潮流的影響,所以,他的《靈山》裏面就用了貴州(非漢族)、佛教、道教這些和中原(漢族)、儒家主流文化不一樣的元素*《靈山》中寫到貴州東北部著名的梵淨山,寫到山中寺院老和尚的圓寂與火化。但是,老和尚的兩個大弟子最終也没有得到口授真傳,連象徵佛法的衣缽的“缽”都粉碎了。最後,一場大火三天三夜,一切只剩下灰燼。“浩劫之後又只剩下這一座廢墟和半塊殘碑,供後世好事之徒去作考證”。他又寫到,古廟廢墟不久又成爲土匪窩,他感慨歷史的變遷不居。高行健其實是在暗示佛教道理“凡所有相,皆爲虚妄,所相非相,乃非非相”。。
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背景刺激了“禪宗熱”。不過這個“禪宗熱”,本質上並不是歷史學或文獻學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是現實的社會關懷與文化反思下的政治批判。在這個時代,禪宗只是一個箭垛,就像“草船借箭”似地讓批判和反思的箭都射到這上頭來。可需要追問的是,爲什麽偏偏是禪宗當了這個箭垛呢?因此,我們還應當注意,“禪宗熱”背後還有一些“洋背景”。
很多人都知道,那個時候中國有一套叢書很流行,這個叢書叫做“走向未來”。聽這套叢書的名字就知道,那個時代的人對於“走出中世紀”的心情多迫切。在叢書裏面有一本小書,是一個西方人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8—)寫的,書名叫《物理學之道: 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個卡普拉是一個很有反叛性的物理學家,他大概學了一些東方思想,對西方科學有很多質疑*收在“走向未來叢書”的那個中文本,題爲《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部書流行非常廣,後來又在中央編譯局出版社重新出版,在2012年第4次印刷,並且增加了新的内容。在卡普拉看來,道家、禪宗及東方的其他神秘主義學派,如印度教、佛教等等之所以能像現代量子物理學一樣,對宇宙的基本統一性有深刻的認識,其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思維形式是渾然不分的直覺思維,而不是門類分裂的理性思維。。除了這本書外,他還寫過一本叫《轉捩點: 科學、社會與興起的文化》,兩本書裏面都引用了不少道家和禪宗的説法——當時被稱爲“非理性主義”或“東方神秘主義”——對西方慣常的理性思維和科學主義進行抨擊。《物理學之道: 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部書當時被譯成中文,就好像俗話説的“歪打正着”,也就像古話説的“郢書燕説”。他的這些很“後現代”的批判性想法,對於當時正在熱心追求科學的中國人没有形成太大的影響,但是對仍然依戀傳統文化的中國人,卻給了一個有趣的啓發: 原來,我們這裏的禪宗、道家,還是比西方哲學和科學更加時髦更加先進的思想呢,就像禪宗語録講的,“自家寶藏不肯信,整日四處尋覓”,這下可好,我們有自豪的本錢了,所以,很多人對禪宗開始另眼相看起來。
其實,卡普拉有關“東方神秘主義”的想法(包括西方人對於禪宗的理解),一方面來自歐洲哲學家或東方學家對於印度的研究;另一方面來自日本鈴木大拙的影響。這裏没有篇幅仔細討論,只是要説明的是,西方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有一些對於現代性的反思,在反思中,他們發現了可以用來自我批判的東方資源,比如叔本華、尼采,一直到海德格爾、雅斯貝斯等等。因此,這個時候歐洲哲學家或東方學家關於吠陀、佛教、道家的研究,日本學者對於佛教、禪宗的哲學詮釋,就會成爲批判資源,進入他們的思想世界。另外,我們也應當承認,日本學界在哲學和思想的反思性批判和自主性追求上,比中國學界要早得多。這也許是由於日本較早進入現代國家行列,又割不斷東方文化傳統的緣故,它很早就有所謂“近代超克”的意識,總試圖在西方思想和觀念籠罩下掙脱出來。所以有一批如鈴木大拙、西田幾多郎、西谷啓治、久松真一、阿部正雄這樣的學者,一直在努力發掘和宣傳自己的思想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禪”。因爲禪對於宇宙本質的理解,對於語言和理性的懷疑,對於社會生活的理解,對於心靈自由的另類尊重,似乎都和西方人不同。所以,從20世紀初期起,鈴木大拙就用英文在西方傳播禪思想和禪文化,後來他甚至被西方人稱爲“世界禪者”,連“禪”這個詞,現在西方人都習慣用日文的發音叫作“Zen”而不是中文的“Chan”*當然,現在歐美學界研究禪宗的學者,倒是有意識地用“Chan”來標示禪宗,特别是中國禪宗。而用“Son”來標示朝鮮禪宗,用“Zen”來標示日本禪宗。在有的著作中,還會特别採用“Chan/Zen”或“Zen/Chan”這樣的方式。。
這些傳統的佛教思想,在日本學者中用西方概念重新包裝,出口到西方,可是,又從西方的接受者那裏穿上了洋外衣,出口轉内銷回到了1980年代的中國*例如,阿部正雄撰,王雷泉、張汝倫譯《禪與西方思想》,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Masao Abe: Ze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85)。此書中譯本曾經在1980年代末出版,並且發行一萬多册。。這種西方人都承認的東方智慧,給當時强調中西思想文化差異的中國學者很多啓發,也給暗中留戀本土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重建傳統思想和本土文化的新契機。我記得那個時候,對於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曾經請臺灣學者蕭師毅給他讀《老子》這一傳聞,大家都津津樂道,覺得其中深意令人遐想。而佛教與禪宗,就是在前面所説的那種“批判”和後面所説的這種“留戀”中,被1980年代的中國學界重新發現的。包括我自己那部《禪宗與中國文化》,現在回想起來纔漸漸察覺這部書中一些思路、方法和評價的問題所在,可是,當時我卻並没有這麽明確和自覺的意識。身處一個時代潮流中,往往身不由己地被裹進去,要到很晚纔能自己反思。後來,我在翻譯鈴木大拙《禪への道》那部書前面寫的譯者序中,對這個學術史過程有一些檢討,當然這可以叫“後見之明”。
我的《禪宗與中國文化》,也許是現代中國大陸學界第一部專門討論禪宗的著作,此後,中國陸續出現了不少有關禪宗的論著。可是應該指出,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禪宗歷史和文化研究,嚴格地檢討起來,並不能算很學術或學院的。如果允許我簡單地説,中國學界的禪宗研究大致可以分三個領域。一是作爲歷史和文獻學研究領域的禪史研究,在這個領域中,研究者得先去收集史料、考察歷史、還原語境、排列時序,那是很嚴格的學院式研究。二是作爲哲學、心理學解釋領域的禪思想研究,在這個領域你得説明,在人的思想和智慧上,禪宗是怎樣超越傳統,給中國思想世界提供新思路、新認識,從而改變了中國人的習慣的,也得説明作爲一個以救贖爲目標的宗教,它通過什麽方式使信仰者的心靈和感情得到解脱?這也是很難的。三是作爲歷史和現實批判資源的禪文化研究,這當然是根據當下的需要,借助歷史和文化,來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地進行現實批判,這需要的不是歷史和文獻、哲學和心理的嚴格、細緻,應該説就比較容易。但是,這三個不同領域和三種研究進路在1980年代是被混淆的,而最後一個領域也就是現實批判,在那個時代是最受關注,也是最能够引起共鳴的。應當承認,我寫《禪宗與中國文化》,就是在這個層面建立論述和思考基礎的,所以嚴格説來它並不能算“學術的”或者“學院的”研究。可是,偏偏這一非學院或非學術式的禪宗研究,對1980年代學術界文化界的“禪宗熱”,起了最大的作用。
寫《靈山》的高行健,恰恰就是受到這一方面的影響。
二、 胡適的意義: 中國禪的基本問題與近百年來中國的禪宗史研究之狀況
現在,讓我們從禪宗的基本常識開始,重新討論中國在禪宗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術史問題。通常,在有關中國的禪宗與禪宗史研究裏,需要重點討論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靜坐的方法。在漢魏六朝時期,佛教有重視義學(就是依據經典講明道理)的一個方向,也有重視實踐(包括坐禪、苦行、造寺)的一個方向,後面這個方向中,特别以小乘禪學的影響最大。在小乘禪學中,靜坐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來源也很古老*古代印度本來就有瑜伽派,它有八個重要的方法,一是禁制(特别要謹記五戒: 戒殺、戒盜、戒淫、戒妄語、戒貪欲)、二是勸制(勤修五法: 清淨、滿足、苦行、學誦、念神)、三是位坐法(有各種坐法,包括蓮坐、勇士坐、賢坐、幸坐、杖坐、獅子坐、牛口坐、龜坐、弓坐、孔雀坐、自在坐等等)、四是調息(即呼吸法,吸入時爲滿相,呼出時爲虚相,在三時調節氣息,氣滿時人在氣中爲瓶相,就進入了所謂三昧狀態)、五是制感(控制自己的感覺器官,使眼耳鼻舌身意與外部世界分離)、六是執持(指精神與心靈凝聚於一境)、七是禪那(包括四禪階段)、八是三昧(這是瑜伽修煉最高級最純真的解脱境界)。可是,小乘的禪,作爲瑜伽八支實修法之一,“禪那”是如何被放大並凸顯成實踐的關鍵的?本來,戒、定、慧三學,都是佛教追求解脱和超越的整體方法。參看後藤大用《禅の近代認識》,東京: 山喜房佛書林1935年第三版,第七章《坐法について》。。可是,爲什麽後來有了“律師”、“禪師”和“法師”的分工?爲什麽裏面的“定”會逐漸獨立起來,並且在唐代中葉以後成爲佛教的大宗?换句話説,就是禪如何由實踐方法變成了整體理論,並且涵蓋了整個佛教關於人生和宇宙的理解和認識?——這一方面的問題,涉及在中國“禪”如何成爲“宗”的大關節問題,這是屬於禪思想史必須討論的話題。
第二,關於“空”和“無”。什麽是禪宗對於“空”的理解?它如何與道家的“無”區别和聯繫?佛教中的這一支,其核心觀念和終極追求,如何從《楞伽》的“心”轉向《般若》的“空”?所謂“佛性常清淨”,又怎樣逐漸偏向“本來無一物”?這種理論如何被詮釋和實踐爲自然主義的生活?——這一方面的問題,涉及禪思想如何“中國化”,就是它怎樣和中國原有思想的結合,以及中國禪宗最終爲何有這樣的理論和實踐走向的問題。
第三,什麽是“頓悟”?如何纔能“頓悟”?所謂“無念、無住、無相”究竟怎樣轉向了“平常心是道”?所謂“即心即佛”如何轉向“非心非佛”?在這些變化中,牛頭、荷澤、洪州各自起了什麽作用?這種逐漸趨向輕鬆修行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對於禪宗和佛教本身的宗教性,以及對於禪宗信仰者的成分,會有什麽影響?形成這種輕鬆修行的歷史和文化語境是什麽?——這個問題,涉及禪宗如何以及爲什麽能够進入上層社會,並成爲文人士大夫的精英文化。
第四,什麽是“不立文字”?其實,佛教本來是很相信文字和經典的,“如是我聞”,記録下來的佛陀説法成千上萬,有經典,有戒律,有解説的論。可是,什麽時候産生對於文字的這種不信任?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麽?它如何通過回到生活世界來實現感悟?然後,到了禪宗的手裏,它如何經由矛盾、詩歌、誤讀、模糊表達等等方式,瓦解人們對語言的信任?它是一種所謂的“反智論”嗎?如果不是,那麽,它是否像現代西方哲學一樣,是讓人回到“原初之思”呢?這關係到我們如何來理解各種看上去奇奇怪怪的禪宗文獻,也涉及我們今天如何來理解禪宗的現代意味。——這一方面,則關係到禪如何成爲文學趣味、生活方式和藝術資源,從而成爲文化,漸漸淡化了原來的宗教性。
以上這四個方面,表面看去都是禪宗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它們涉及的,恰恰也是禪宗歷史研究的幾個重點: 一是它如何從實踐方法轉化爲理論體系,涵蓋了對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二是它如何從修行傾向變成了佛教派别,使得禪師變成禪宗;三是它如何從草根階層轉向精英階層,從而使它的影響從南方到北方、從山林到廟堂。這些恰恰就是禪宗史的關節點。在這些問題裏,既涉及歷史,也涉及思想,還涉及知識和信仰,甚至還要涉及整個中國思想、宗教和文化的轉型問題,在這樣的觀察角度下,這就首先是一個禪宗史的問題了。當然,除了以上禪宗史過程之外,歷史上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對禪宗的影響和禪宗對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反影響,也仍然是需要討論的。
可是,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主要聚焦點卻在禪宗對於中國,尤其是上層知識人文化心理的影響,以及它如何影響到今天中國知識人的政治態度和社會取向。不過,從1980年代“文化熱”以來,經歷了1990年代的“學術熱”,現在禪宗研究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逐漸有了新的視野、思路和方法*有關中國學術界的這一轉變,請看葛兆光撰,土屋太祐譯《文化史、學術史、そして思想史へ——中國學術界における最近三十年の變化の一側面》,載《中國—社會と文化》(東京大學·中國社會文化學會)第25號(2010)。。關於這一方面,近年來有龔雋、陳繼東兩位合作的《中國禪學研究入門》,這是我們編的“研究生學術入門系列”叢書中的一種,對於目前禪宗研究的狀況,已經寫得很全面了*龔雋、陳繼東《中國禪學研究入門》,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我這裏想要重點討論的,是胡適開創的有關中國禪宗史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當下中國是否仍然有意義的問題。所以,我應當先回顧一下現代中國有關禪宗史研究的百年學術史。
在我個人視野中所見,沈曾植(1850—1922)應當是現代的中國禪宗史研究的開創者。他死於1920年代,生前並没有專門寫過關於禪宗的著作或文章,但是,他去世後由門人後學整理出來的劄記,也就是《海日樓劄叢》中有好幾篇關於禪宗的短文*沈曾植《海日樓劄叢》,卷五、卷六,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萬有文庫”本,特别是有關禪宗的第185、188、195—197頁。,既具有現代意味,又富於開拓意義。比如,關於早期禪宗是“楞伽宗”的説法,就比胡適早很多年,他看到了早期禪宗奉《楞伽經》的歷史;比如,像禪宗傳法系統最重要的金石資料《法如碑》,他就最先注意到了,並指出禪宗傳續過程中,並不像禪宗後來説的是東土六祖即從達摩到弘忍到惠能,甚至也不像北宗禪説的,從弘忍直接到了神秀,而是中間有一個法如;又比如,從《禪門師資承襲圖》論神會的部分,他也注意到了神會的意義,這比日本的忽滑谷快天和中國的胡適更早,他説“南宗之克勝北宗,爲人王崇重,實賴(神)會力”*他的精悍短小的研究,已經很有現代意味。比如在道教方面,像關於道教五斗米教是“拜五斗”即五方星辰,就使我們聯想到道教關於五方的崇拜,這是一直到後來還有人做的課題。在佛教方面,像關於早期佛教部派問題的討論,他就已經脱離了漢傳佛教的老説法。那個時候,沈曾植可能已經接觸了歐洲的印度學,而且還有所批評,比如他討論吠陀的時候,就批評歐洲人關於佛教否定吠陀,受自由思想影響的説法,指出佛教只是“反外道”;又比如他討論《舍利弗問經》和《宗輪論》關於十八部分離的記載爲何不同,討論了大衆、上座部的分裂的三種説法,並且考證了大衆部中的大乘思想和馬鳴與婆須密迦旃延子的關係,顯然已經超越了傳統漢傳佛教的範圍。。特别應當指出的是,沈曾植是當時學界領袖式人物,民國初年在上海寓居,儼然就是舊學世界的領袖,但開一代新風的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都很受他影響。他對古代中國和突厥之關係、西北歷史地理、蒙元史的研究,都有深刻見解,這在當時都是很前沿的學問。因此當他以學界領袖的地位來關心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就會産生不小反響*晚清民初是居士佛學興起的時代,沈曾植的佛教論述,也是這個時代居士佛學論述的代表。不過,畢竟他還是博學之士的業餘興趣,又是用傳統劄記的形式記録和表達,所以,這些研究和論述只是偶然的成就,没有在立場和方法上形成重要影響。。
沈曾植身前身後,像太虚和歐陽竟無領導的僧侣佛學和居士佛學中,也都有一些有關禪宗史的研究,學者中間也有像梁啓超、蒙文通等人的零星論述。但是,真正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禪宗研究,還是要到1920年代中期的胡適纔開始。所以現在我就轉入正題,講講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在中國大陸,有關胡適禪宗研究的評論中有三篇論文最有代表性: 第一篇是任繼愈《論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載於《歷史研究》(1955年第5期),第29—48頁。説(胡適)之所以研究禪宗,是因爲禪宗與胡適“都是反理性的,都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都是反科學的”,並且説胡適的禪宗研究“没有任何價值”。這是1949年之後,胡適批判運動下的産物,代表了政治意識形態式的評價。第二篇是樓宇烈《胡適禪宗史研究平議》,載於《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第59—67頁。指出“(胡適)以非信仰者的立場、用思想史的眼光、歷史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禪宗史的學者”,代表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的新評價。第三篇是潘桂明《評胡適的禪宗史研究》,載於《安徽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第54—59頁。特别討論了胡適對於禪宗史文獻的發掘和考證,一方面批評胡適方法論上的根本錯誤是主觀唯心主義,説“(胡適)從‘懷疑’出發,以‘考證’爲手段,提出了一些難以爲人所接受的‘武斷的結論’(柳田聖山語)”。但是另一方面也承認“在這些著述中,胡適的某些考證還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説明1980年代政治批判的痕跡仍然存在。。
我一直認爲,真正使得中國禪宗史研究有根本性變化,使它變成現代學術研究的奠基人,當然是胡適*關於胡適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意義,參看余英時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原爲1984年爲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寫的序言)以及《〈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均載《重尋胡適歷程: 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版。。胡適對禪宗史的興趣和動力,或許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於歐洲“文藝復興”的刺激,他對現代國家語言和白話文學傳統的關注*1917年,胡適(1891—1962)在美國留學回國途中,曾仔細閲讀薛謝爾(Edith Helen Sichel)的著作The Renaissance,從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極爲關注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是在各國“俗語”基礎上形成“國語”,而形成“國語”則對這些現代“國家”的形成非常重要。因此,胡適把意大利語、法語等現代國家語言(國語)和中國宋代的語録、元代的小説以及民衆口語相提並論,他認爲,這就是普及國民文化,提升國民意識,形成現代國家的重要途徑。而“白話猶未成爲國語”,正是他努力在中國推動“白話文學”以及“建設國語”最重要的思想來源。禪宗研究在胡適學術世界中佔有重要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這一思想。,因爲禪宗語録在他看來是最好的白話文學;另一方面來自他重新撰寫中國哲學或思想史的抱負。他覺得,寫中國思想史繞不開佛教,研究中國白話文學也離不開禪語録。所以,從1924年起,他下定決心研究禪宗史,現在還保存了當時他試着寫禪宗史的手稿*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册,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胡適在1924年7—11月間開始寫《中國禪學史稿》,他説:“寫到了惠能,我已經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高僧傳》裏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爲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於神會的史料。”(第570頁)又,胡適《禪宗史草稿》有關神會一段,寫於1925年3月4日,批評《宋高僧傳》“這書頗能徵集原料,原料雖未必都可靠,總比後人杜撰的假史料好的多多”。又説:“禪宗書往往把後世機緣話頭倒裝到古先師傳記裏去……我們所以借神會一傳,給讀禪宗史者下一種警告。”見《胡適全集》第九卷,安徽: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7頁;按: 手稿在《胡適手稿及秘藏書信》第8册中。。胡適對敦煌卷子的注意更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就給英國刊物寫文章,指出大英博物館敦煌文書目録的問題*胡適爲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撰文,批評1914年第3期上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編撰的《敦煌録: 關於敦煌地區的記録》(第703—728頁),指出其錯誤。見王冀青《胡適與敦煌録》,載於《文史知識》(2010年第7期)。。到了1926年,他恰好有機會到歐洲去看敦煌卷子,帶着自己的關注,便發現了禪宗史上前人很少接觸的新資料。1927年夏天,他在上海美國學校“中國學暑期講習會”講了四次《中國禪宗小史》*1931年,他給朝鮮人金九經寫信,提到他有一篇英文的《禪宗小史》,曾請Sauncers帶給鈴木大拙看,但此文我没有看到。見耿雲志等編《胡適書信集》上册,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頁。,1928年,他寫了《禪學古史考》,同年又與湯用彤討論禪宗史*1928年7月21日他和湯用彤的書信討論,即《論禪宗史的綱領》,共十三條。其中有幾個最重要的關節,一是印度禪與中國禪,中國禪受道家自然主義影響的成分最多;二是菩提達摩一派當時叫“楞伽宗”,敦煌有《楞伽師資記》;三是惠能的革命和神會的作用;四是八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很多有關禪宗系譜的僞史;五是八世紀下半葉到九世紀上半葉,禪宗的分派要參考宗密的著作和敦煌的資料;六是神會一派不久衰微,馬祖道一成爲正統,“中國禪至此始完全成立”。以上這些論述,基本上構成了六至九世紀禪宗史的大體框架。。可以看出,這個時候已經基本形成了他的禪宗史基本脈絡和評價立場*原發表在1928年8月10日《新月》第一卷6號,收入《胡適文存》三集第四卷,見《胡適文集》第4册,第221—235頁。這篇文章一開頭就强調:“印度人是没有歷史觀念的民族,佛教是一個‘無方分(空間)無時分(時間)’的宗教。故佛教的歷史在印度就没有可靠的記載。”他説他在上海美國學校講禪宗小史,對中國禪宗人物生死年代講的很清楚,這使得兩個印度聽衆很吃驚,覺得這是“中國民族特别富於歷史觀念的表現”。顯然,這已經體現了胡適對於禪宗史研究,重視時間與空間研究的現代性的方法特徵。。於是,從1929年起到1934年,他陸續發表了好幾篇關於禪宗的研究論文*像《菩提達摩考》(1927)、《白居易時代的禪宗世系》(1928)、《荷澤大師神會傳》(1930)、《壇經考之一》(1930)、《楞伽師資記序》(1932)、《壇經考之二》(1934)、《楞伽宗考》(1935)等等(分别收入《胡適文集》第3、5册),還編輯了《神會和尚遺集》,上海: 亞東圖書館1930年版。,範圍涉及了早期禪宗系譜、中古禪宗史、南宗的神會,以及《壇經》作者、惠能與神會之後的南宗禪等等,一時引起學界極大關注。應當説,他發現有關禪宗的敦煌文獻,是千年來不曾看到的新材料,他提出有關禪史的好多看法,都是石破天驚極具震撼力的。比如,關於《壇經》不是惠能的作品而是神會的作品;比如,開元年間滑臺大會是禪宗史南宗與北宗盛衰的轉捩點;比如,安史之亂中神會爲朝廷籌“香水錢”奠定了南宗的正統地位;又比如,寫禪宗系譜的傳統依據傳燈録往往不可信等等。這些研究無論結論是否正確,都使得禪宗史不得不重寫*臺灣學者江燦騰曾經質疑,胡適的神會研究,是否曾經受到日本忽滑谷快天1923年、1925年出版的《禪學思想史》的啓發和影響,所以,並不算他的原創。江勇振在《舍我其誰: 胡適傳》第二部《日正當中: 1917—1927》(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版,第661—664頁)中,一方面贊成江燦騰的意見,但另一方面又指責江燦騰“只留心出版的作品,而忽略了胡適未出版的筆記和手稿”。他認爲,胡適確實讀過忽滑谷快天的書,是“徵而不引的壞習慣”,但他又根據現存胡適手稿,認爲胡適八年前即“潛心研讀佛學或禪宗的歷史”,因此發現神會新資料是“拜他八年來用功之所賜”。因此,“胡適對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革命的意義,以及神會在這個革命裏所扮演的角色的認識,在這時(1925)就已經奠定了”。按: 胡適在1924年就開始自己思考禪宗史問題,1925年3月4日寫神會一節,主要依據是《宋高僧傳》,對《景德傳燈録》頗有批評,這有當時的“禪學史手稿”爲證。因此我懷疑,在禪宗史研究之初,胡適未必依據了忽滑谷快天的著作。在未被收録於《胡適書信集》(包括《胡適全集》)、寫於1926年10月29日一封致顧頡剛的信中,胡適提到他在巴黎看伯希和帶回的敦煌卷子,説:“發見了不少的禪宗重要史料,使我數年擱筆的《禪宗史長編》又有中興的希望了。前年(1924)作禪宗史,寫了八萬字,終覺得向來流行的史料,宋人僞作的居多,没有八世紀及九世紀的原料可依據,所以擱筆了。”(原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卷第15期,此據蔡淵迪《跋胡適致顧頡剛書信兩通》,載於《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1期,第159—169頁。)胡適的禪宗史看法的形成,應當與忽滑谷快天關係並不大。雖然1926年發現敦煌神會文書時,有可能參考過忽滑谷快天的書,受到了一定的啓發,但是,胡適從敦煌文獻入手重新審視禪宗歷史,通過整體質疑禪宗系譜的書寫,來重建一個可信歷史,在方法上他的意義更大。所以,不必糾纏於他是否沿襲了忽滑谷快天的書。當然,江燦騰也並不否認胡適在中國學界對禪宗史研究的開創性意義。。
胡適雖然並不是僅僅以禪宗史爲自己的領域,但他一輩子都在關注禪宗研究,在1930年代前後專注於禪宗史研究之後,有十幾年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政局變化,他受命擔任駐美大使,暫時放下了禪宗研究。但是,1952年之後,當他開始有餘暇的時候,又開始研究禪宗史。1952年9月,他重新拾起《壇經》的資料,檢討他自己過去的看法。那一年他到臺灣,在臺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就舊話重提,大講他發現禪宗史料的經過,可見禪宗史的興趣始終未泯。1953年1月,在紀念蔡元培84歲生日的會上,他又以《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爲題做了一次演講,這一年他還寫了《宗密的神會傳略》,這象徵著胡適再次回到他1930年代的禪宗史領域和問題。此後一直到他去世,他仍然在不斷地就禪宗史的文獻、歷史、方法進行探索。一直到他去世前的1961年5月23日,他在病榻上仍然認真地重讀1928年他曾經考察過的《傳法堂碑》,並鄭重地記下在衢州月果禪寺居然有這塊碑的原石。
在胡適的禪史研究論著出版之後,幾乎半個多世紀中,中國學術界甚至日本學術界,都深受這些資料和觀點的影響。日本的入矢義高教授、柳田聖山教授,都是佛教研究中的權威,但他們在與胡適交往通信中,不僅深受影響,也很認同胡適關於禪宗史的一些説法。柳田聖山先生還編過《胡適禪學案》一書,專門討論胡適的禪宗研究以紀念這個開創者。在臺灣和香港,一直到1960年代,圍繞胡適關於《壇經》的考證再次掀起爭論,包括錢穆等學者都捲進去了。中國大陸在1950年代重新開始禪宗研究以後,其實,大多數學院學者的研究也還是在胡適的延長綫上的。只是大陸當年把胡適當做“敵人”來批判,連胡適在禪宗研究上的成績也一筆抹殺,所以,只好在歷史學與文獻學的角度與方法之外,新增加了兩個觀察立場和分析維度,來超越過去的研究。第一個是所謂“哲學史”,這也是由於中國大陸宗教研究長期設置在大學的哲學系,並推動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研究宗教,所以,禪宗研究中增加了宇宙論與知識論層面、唯心唯物觀念角度的研究,最著名的如任繼愈及其弟子們;第二個是“社會史”,在有意無意中,繼承了傳統儒家對於佛教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作用的批判,把禪宗放在政治、社會和經濟角度進行研究,最重要的如范文瀾《唐代佛教》以及思想史領域的追隨者。可是應當説,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並没有多大起色,也没有什麽專書出版。
1980年代以後,禪宗研究興盛起來。正如我前面所説,先是出現了“歷史與文化批判”的新角度;再往後,受西方現代甚至後現代禪學研究影響,出現了新的禪學論述,這當然是後話。今天,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著作已經非常多*包括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洪修平、賴永海、麻天祥、潘桂明、蔡日新、劉思果等人的禪宗史論述。,如果不算佛教界内部的研究,而只討論學院的學術研究,那麽這些論著大體可以歸納爲三種: (一) “哲學史研究”的進路,主流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發展史的分析方法,我認爲,這是一種“反西方的西方模式”;(二) “歷史學與文獻學”進路,這方面成果不少,比如發現神會碑銘,整理敦煌本《壇經》、《神會語録》等,近年來有關禪宗的碑誌文獻大量出現,可見,以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爲主的研究方法最有成績*但是應當指出,在這一方面,方法仍然略嫌簡單,採用這一進路的學者,對歷史語境和社會背景,即政治狀況、社會生活、禮儀風俗的重建以及普通信徒觀念和知識的關注仍然不够,對文獻上的文本細讀、疊加層累、僞中之真、真中之僞的複雜方法運用仍有距離。;(三) “文化批評”進路,這包括由於對現代性的質疑而引出的價值重估,對歐洲近代文化與哲學的質疑*但是,應當指出,這一進路中,往往過度詮釋頗多,而西方擅長的“心理學”和“語言學”方法,至今中國學界仍然並未很好把握。。但是,依我的看法,中國學者最擅長,也是最有成就的仍然是歷史學與文獻學的研究,在這種史料批判和歷史評價上,禪宗史研究還是没有走出胡適的時代,想建立新典範,恐怕没有那麽容易。
我想特别强調的一點是,胡適的禪宗史研究的意義,不是對禪宗史具體的歷史或文獻的結論。如果要細細追究的話,可能胡適的很多説法都有疑問,比如前面説到的: (1) 關於《壇經》不是惠能的作品而是神會的作品,這根據是不足的*關於《壇經》的作者是神會,胡適的證據之一是《壇經》和《神會語録》裏面,很多術語和思想相近,但是這個説法並不成立,因爲學生和老師之間相似是很自然的;之二是惠能不識字,不可能講這麽深奥的思想,但是焉知惠能不識字是真是假;之三是《鵝湖大義碑》中有説荷澤一系的“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檀經傳宗”一句,胡適認爲,這證明神會炮製了《壇經》,但是,這段話只能證明神會一系用《壇經》作爲傳授時的憑信,不能證明神會就是自己撰寫了《壇經》。就連胡適自己後來也改變了看法,《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胡頌平記載説:“到了……(1959)二月二十日,先生在此文(指《六祖壇經原作檀經考》)的封面上自注説‘後來我看了神會的〈壇經〉兩個敦煌本,我也不堅持〈檀經〉的説法了’。”(《編者附記》,第2224頁)胡適論據中比較有説服力的,是《壇經》裏面有惠能説的“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這一條,所以,這段話一定是後來與神會有關係的人的説法,爲了證明真傳嫡系在神會,所以《壇經》和神會肯定有關係。但是我們相信,更可能的是神會對《壇經》有修改補充,而不是神會自己炮製《壇經》。;(2) 滑臺大會,他説開元年間滑臺大會是禪宗史南宗與北宗盛衰的轉捩點,這個説法是誇大的*滑臺大雲寺並非佛教在唐帝國的中心,没有特别大的意義,同時,辯論會在唐代相當普及,凡是有疑義,常常就會有論戰,這一次在滑臺舉行的論戰是否特别有影響?還是有疑問的。與神會辯論的“崇遠法師”不是北宗,而是義學僧人,一個法師,他敗了不等於北宗敗了,那個時代,北宗禪可能對神會很不屑,因爲當時的北宗禪正如日中天。;(3) 安史之亂中神會爲朝廷籌“香水錢”奠定了南宗的正統地位,也被證明很不可靠*關於香水錢,雖然贊寧在《宋高僧傳》説過這件事,但只是簡單叙述了一下,把它當作南北宗之爭的一個大關節,則是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纔開始的,很多人都接受這個説法,但是這是不可靠的。參看葛兆光《荷澤宗考》,《新史學》(臺北: 史語所)第五卷第4期。收入《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10世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但是,我們爲什麽要説他依然是禪宗史研究的開創者呢?這是因爲胡適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中國學術界研究禪宗的典範。爲什麽是“典範”?這裏主要指的,就是這個中國禪宗研究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範式,這個研究範式影響了和籠罩了至今的中國禪宗研究,現在中國學界研究禪宗,仍然走在胡適的延長綫上。
在這個“典範”中,有三點特别要肯定:
第一,是他開拓了禪宗史研究的新資料,特别是在敦煌卷子中發現了很多有關禪宗的新資料。1935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的時候,曾經説到能够顛覆禪宗正統派妄改的歷史的新資料,一是要從日本寺廟中找,一是從敦煌石室寫本中找*胡適《中國禪學的發展》,《胡適文集》(十二),第301—302頁。。其中,他對敦煌資料的重視是從1916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開始的,當時他曾寫過英文文章糾正過英國敦煌編目的錯誤,後來,由於對白話文學史和中古思想史的兩方面興趣,他對佛教新資料就更加關注,這纔有了1926年他去歐洲尋找敦煌文獻中的禪宗史料的事情,這可不是忽滑谷快天的影響*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傳》第二部《日正當中: 1917—1927》,第684—685頁認爲,胡適有意識去尋找新資料,是在美國讀書時受到“高等考據學”啓發,以及赫胥黎《對觀福音書》的影響,可備一説。。經由他發現並且整理出來的神會和尚的幾份卷子*1926年,先後在巴黎發現《頓悟無生般若頌》(胡適認爲就是《宋高僧傳》中説的《顯宗記》)、《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即滑臺大會上與崇遠法師等的辯論)、《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陸續與衆人的問答)、《五更轉》(南宗宣傳詩歌),見於1927年他的《海外讀書雜記》。,仍然是我們瞭解禪宗史上最重要的歷史時期的基本史料。没有這些史料,禪宗史不可能擺脱燈録系統的影響,顛覆傳統的説法,寫出新的、清晰的禪宗歷史來。
第二是他重新書寫了禪宗史的脈絡,提出了中古禪宗史研究的新方法。與古史辨派所謂“層層積累的僞史”説一樣,他有關菩提達摩見梁武帝故事爲“滚雪球越滚越大”*胡適《菩提達摩考》,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四,《胡適文集》(四),第257頁。,《壇經》從敦煌本到明藏本字數越來越多是“禪宗和上妄改古書”*胡適《壇經考之二》,收入《胡適文存》四集卷二,《胡適文集》(五),第254頁。,以及中唐禪宗編造系譜常常是“攀龍附鳳”的説法,給後人相當深刻的影響。雖然,他特别强調神會在禪宗史上的意義,把弘揚南宗禪的重大功績都加在神會身上,包括惠能的《壇經》也是神會炮製的,戰勝北宗也是神會滑臺大會的功勞,在傳統禪宗史之外重新建立起來一個以神會爲中心的中國禪史,可能這些説法並不可靠,我後來寫《荷澤宗考》就反對這個看法。但是,由於胡適的“新説”,使得禪宗史研究者一方面要抛開燈録的叙事系統,一方面又需要在反駁胡適叙事的基礎上再建構,這就像西方哲學中的“四元素”説、化學上的“燃素”説一樣,不一定正確,卻成爲一個新模式。在胡適發現神會的資料之後,他對於禪宗系譜與歷史文獻研究方法的認知越來越明晰。他反復强調,“今日所存的禪宗資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景德傳燈録》)、贊寧(《宋高僧傳》)、契嵩(改編《壇經》)以後的材料,往往經過了種種妄改和僞造的手續”*見《神會和尚遺集》自序,收入《胡適文存》四集卷二,《胡適文集》(五),第235頁;他在1952年12月6日在臺大演講《治學方法》的時候,還重新提到,1926年到歐洲發現敦煌禪宗資料的事情,指出當時可以看到的材料“尤其是十一世紀以後的,都是經過宋人竄改過的”,又以日本學者矢吹慶輝發現敦煌本《壇經》爲例,説明擴張史料的重要。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説》中評論《禪林僧寶傳》時,也説到禪宗燈録是“以理想爲故實”。,强調“中唐與晚唐有許多僞書與假歷史,都成了《景德傳燈録》的原始材料”*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臺北: 正中書局1975年版,第617頁。。主張對一切系譜與史料進行質疑,便成爲他的禪宗史研究的出發點*正因爲如此,他既對已經看到敦煌文獻的鈴木大拙“過信禪宗的舊史,故終不能瞭解楞伽宗後來的歷史”有所批評。當然,對忽滑谷快天完全依賴傳統史料叙述禪學思想史,也不能認可。見胡適《致金九經》,載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第14頁。此外,1960年2月9日胡適又在演講《禪宗史的假歷史與真歷史》中從鈴木九十歲紀念文集説起,認爲他“是有雙重人格的人,他用英文寫的禪宗很多,是給外國的老太婆看的,全是胡説。但他用日文寫的禪宗,就兩樣了,因爲日本還有很多研究禪宗的人,他不能不有顧忌了”。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172—3183頁。,他也指出了禪宗史料造僞的時代。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記載,胡適曾致信柳田聖山説到,“從大曆到元和(766—820),這五六十年是‘南宗’成爲禪門正統,而各地和尚紛紛的作第二度‘攀龍附鳳’大運動的時期”*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第630頁。1959年12月胡適致嚴耕望的信中,又談到“十宗之説,實無根據,南北宗之分,不過是神會鬥爭的口號,安史亂後,神會成功了,人人皆爭先‘攀龍附鳳’,已無南北之分了,其實南宗史料大都是假造的……”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105—3106頁。。另一方面,他也非常積極地尋找可以“穿越”禪宗譜系的真史料,正因爲如此,不僅較早的敦煌禪籍就成了他質疑禪宗譜系的重要憑據,而且唐代碑刻史料也成爲他層層剥去禪宗“舊史”的原始依據。在這一點上,他比忽滑谷快天、宇井伯壽等學者要更有貢獻,因爲他使得禪宗研究重新開闢了新的歷史學途徑。
第三,正是因爲他自覺地質疑禪宗史料,要在禪宗自我編造的系譜之外重新叙述禪宗史,因此,他對於“教外資料”,即唐人文集、碑刻資料有特别的重視。從現在留存胡適的大量筆記文稿中我們看到,胡適曾經相當詳細地做過《全唐文》中隋唐時期各種佛教、道教碑銘的目録,不僅一一記下有關隋唐佛教人物的216份碑銘、塔銘,記録了碑主、卷數、作者,而且標注出這些人物的卒年,以便對佛教史一一排比*均見《胡適全集》第九卷。。我注意到,越到晚年,胡適越重視唐代禪宗石刻文獻的重要性,在他最後的歲月,即1960—1961年中,他不僅依然特别關注各種金石文獻中的唐代禪宗碑文(在他留下的讀書筆記中有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白居易的《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李朝正的《重建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陰文》、李華的《左溪大師碑》、《鶴林寺徑山大師碑》以及《嵩山(會善寺)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等等)*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册。,而且他還特别提醒學者,對這些載於《全唐文》的碑文、詔敕要有警惕*見1960年2月11日撰寫的《全唐文裏的禪宗假史料》,《胡適全集》第九卷,第441—444頁。,要注意直接查閲真正目驗過碑石原文的文獻如《金石録》、《金石萃編》等等*見1961年1月6日撰寫的《金石録裏的禪宗傳法史料》,這一筆記討論了宋代趙明誠所見的《能禪師碑》與《山谷寺璨大師碑銘》等等,《胡適全集》第九卷,第539—541頁。。這一點他遠遠超出了忽滑谷快天,使得中國以及日本學者開始形成以傳世的文集、碑刻、方志等“教外資料”,印證新發現的敦煌、日韓古文書,佐之以教内佛教禪宗典籍的研究傳統。要注意,由於這種歷史和文獻學的研究思路,很多唐代文集中的碑誌以及石刻文獻,都統統被發掘出來,這成爲禪宗研究中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的路數。胡適一直到晚年,還在很有興趣地討論這個碑、那個碑的史料價值,在唐代文集中到處發現可以打破傳統禪宗記載的資料。這成了一個傳統,也成了一個方法,至今中國學者也還是沿著這一條路在走,應該説,這是中國學者的特長或者擅長之一。包括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杜繼文等的《中國禪宗通史》以及我本人於1995年出版2007年修訂的《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也還是走在胡適的延長綫上。
三、 與日本與歐美相比: 什麽是中國學者有關禪宗史研究的特色
在日本與歐美的禪宗史研究這一方面,我並没有資格作全面的介紹,以下所説的内容,只是用來觀察禪宗研究領域裏面,歐美和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的不同,探討一下中國的研究特長與將來出路究竟在哪里。
日本的中國禪宗研究,比中國興盛得多,研究論著也多得多,有的著作水準相當高。關於這一方面,請大家看一本很好的入門書,即田中良昭編《禪學研究入門》,這部很細緻的入門書最近又有新的修訂本問世*田中良昭《禪學研究入門》(第二版),東京: 大東出版社2006年版。。這裏我不想全面叙述,因爲日本禪宗研究歷史很長、著作太多,這裏只是就我關心的領域和問題,重點指出兩點:
第一,應當看到,日本有關禪宗歷史和文獻的研究,至今仍然相當發達。這方面要舉出有代表性的禪宗史研究學術著作,很早期的,人們會提到大正、昭和年間如松本文三郎的《達磨》(東京: 國書刊行會,1911)、忽滑谷快天的《禪學思想史》上下卷(東京: 玄黄社,1925)、宇井伯壽的《禪宗史研究》第一至第三(東京: 岩波書店,1939,1941,1943)等等*這些都是禪宗研究的名著,奠定了現代日本有關中國禪宗歷史與文獻研究的基礎。其中,忽滑谷快天的《禪學思想史》中的中國部分,可以説是第一部完整的、系統的清理禪宗歷史的現代著作,雖然它尚未參考過敦煌新發現禪宗文書,主要依賴禪宗自己的燈録和佛教的僧傳構建歷史系譜,但是他給後人留下了禪宗的一個基本的歷史輪廓。其中,特别是他以禪宗六祖惠能爲分水嶺,區分達摩到六祖是唯傳一心、簡易明瞭、只此一途的“純禪時代”,六祖之後是棒喝機鋒、分宗開派、禪法分歧的“禪機時代”,這種區分背後的價值評判,很值得注意。而宇井伯壽的三册《禪宗史研究》,則廣泛參考了更多的文獻,包括新出土的敦煌文書和散見於藏外的史料,以及各種石刻資料,對禪宗史上各種宗派和人物的傳承,作出細緻的考證,非常有參考價值。。在這以後,日本的禪宗史研究仍然有相當深入的成果,二戰之後如阿部肇一的《中國禪宗史の研究》(東京: 誠信書房,1963)、關口真大的《禪宗思想史》(東京: 山喜房佛書林,1962),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只是特别要提到柳田聖山(1922—2006),這是日本禪宗史研究的重要學者,如果要研究禪宗初期的文獻與歷史,他的《初期禪宗史書の研究》(京都: 法藏館,1967)是不可不看的關鍵性著作*前面提到,柳田聖山和胡適曾經有過交往,編過《胡適禪學案》,對於瞭解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他的這一著作對於禪宗早期的史書如敦煌發現的《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等等,有很深入的研究,至今研究早期禪宗文獻,特别是敦煌禪宗文書,都要參考這部著作。關於柳田聖山的中國禪宗史研究,可以參看何燕生《柳田聖山與中國禪宗史研究——深切懷念柳田聖山先生》,載於《普門學報》(2007年1月第37期)。。此外,如較早的山崎宏對神會的研究、鈴木哲雄對唐五代禪宗歷史的研究*鈴木哲雄《唐五代禪宗史》,東京: 山喜房佛書林1985年版。,滋野井恬對唐代佛教禪宗的地理分佈之研究*滋野井恬《唐代佛教史論》,京都: 平樂寺書店1973年版。,稍晚的,如石井修道對宋代禪宗史的研究*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東京: 大東出版社1987年版。,衣川賢次對禪文獻特别是《祖堂集》的研究*衣川賢次《祖堂集劄記》,載於《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4號(1998年12月),他與小川隆、土屋昌明、松原朗、丘山新等合作,撰有“祖堂集研究會報告”多種,發表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各期上;又,可以參看衣川賢次與孫昌武等合作校訂整理《祖堂集》,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版。、野口善敬對元代禪宗史*野口善敬《元代禪宗史研究》,京都: 禪文化研究所2005年版。、伊吹敦對唐代禪門的研究*伊吹敦《禪の歷史》,京都: 法藏館2001年版。、小川隆對神會與唐代禪語録的研究*小川隆《語録の思想史》,東京: 岩波書店2010年版。此書的中文本: 何燕生譯《語録的思想史——解析中國禪》,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还可以看他的《神會——敦煌文獻と初期の禪宗史》,京都: 臨川書店2007年版及《語録のことば》,京都: 禪文化研究所2007年版。,都相當出色,這些論著仍然延續著歷史學加上文獻學的研究路數。特别值得佩服的是,日本學者常常以研究班的方式,針對某一文獻,數年如一日地集體討論、考證和研究,甚至一再重新討論,因此常常能够拿出相當厚重的成果*比如《碧岩録》,就有老一輩的入矢義高、中年一代的末木文美士、年輕一代的小川隆的精細研究和闡發,而唐代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就有石井修道與小川隆等人對它詳細準確的注釋和翻譯,他們所採用的,基本上就是文獻學的扎實做法。。
第二,是有關傳統禪思想的現代哲學詮釋。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常常並不在行。正如我前面所説,中國研究禪宗的學者,有成績的多在歷史學和文獻學方面,除了印順之外,基本上是學院學者,與寺院禪僧不同,與有信仰的居士學者也不同,一般對於禪思想並没有多少興趣。可是日本卻很不同,一方面很多著名禪學者來自禪門宗派,不僅對於禪思想有深入體驗與理解,而且闡發和弘揚這種禪思想的立場相當自覺;另一方面他們很早就接觸西洋哲學思想,常常有意識地在日本本土思想資源中尋找可以對抗、接納和融匯西方思想的東西。因此,禪思想常常就作爲化解、接引、詮釋、對抗西方的哲學,被他們使用。在這方面,也許可以舉出鈴木大拙(1870—1966)、西田幾多郎(1870—1945)、久松真一(1889—1980)和西谷啓治(1900—1990)爲代表*(一) 鈴木大拙的很多禪宗研究著作,是有意識回應西方古代哲學和現代思想的,多是英文著作。他的有關論述,把東方的禪思想説成是主流的東方思想,又以臨濟禪作爲主流的禪思想,然後加以現代的發揮,比如“禪”超越西方A與非A的二元對立,“悟”使人們能够反身意識自身生命意義,以綜合的肯定超越分析的否定,以非邏輯性瓦解思維的邏輯性等等,在20世紀鈴木大拙與西方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和弗羅姆(Eich Fromm)互相溝通,就在心理學與宗教之間産生很大影響。其實,就是用東方思想尤其是反智(反理性)主義對抗西方理性主義和現代思維。參看鈴木大拙《禪問答と悟り》、《禪と念佛の心理學的基礎》,久松真一的著作如《禪の現代的意義》。(二) 西田幾多郎是日本很有西方哲學素養的學者,專門從哲學角度闡(轉下頁)。
毫無疑問,日本禪宗研究與中國禪宗研究,在方向、問題和重心上有很大的不同。前面已經説到,這種不同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因爲歷史原因,禪宗在中國和日本的發展不同,八九世紀禪宗由留學僧人、遣唐使傳入日本,經過日本奈良時代的發展,到鐮倉時代發展出五山禪文化,興盛一時。雖然近代曾經有過明治時期的“神佛判然”等挫折,但很快重新振作,至今禪宗不僅廟宇衆多,財力雄厚,而且開辦不少大學*(接上頁)發禪宗的超越思想與有關“無”的本體論思想,試圖通過禪宗思想的參究,弘揚東方禪思想的世界意義,由於長期在京都,所以開創所謂日本哲學的“京都學派”。(三) 久松真一則繼承這些思想,以存在主義的“無”與禪宗的“無”進行對比分析,認爲存在主義的“無”是永遠不能克服的宿命的否定性,而禪宗的“無”則是自律的、理性的,能够克服宿命的否定性(没有意義的生命)和絶對二元論(生死)的積極、肯定的智慧,一旦體悟,是“從出生的歷史到出身的歷史的大轉换”。見久松真一《禪の現代的意義》,載於鈴木大拙、宇井伯壽監修《現代禪講座》第一卷《思想與行爲》,東京: 角川書店1956年版,第319頁。這種禪思想的現代詮釋風氣,至今仍然在延續。可以參看前引阿部正雄《禪與西方思想》和《禪與比較研究: 禪與西方思想續編》[Ze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Part Two of a Two Volume Sequel to “Zen and Western Thought” (Basingstoke: MaCmillan,1997)]。*比如京都的花園大學(臨濟)、東京的駒澤大學(曹洞)等等。。而中國在宋元之後禪宗漸漸衰落,即使到了近代,也没有回到學術世界的視野中心來*這裏可以概括地從三方面講: (1) 日本禪僧可以充當國家的使者、禪宗對世俗政治領域和生活世界的深刻介入,這不是中國禪宗可以想象的。佛教在奈良時代以後就是日本的政治軍事力量,在十四世紀以後,日本武士中普遍流行禪宗,禪宗成爲日本武家社會的重要思想支柱,更因爲通曉漢文,又常常介入政治活動。比如《善鄰國寶記》就記載過足利時代的相國承天禪寺住持絶海中津(1336—1405),1392年爲官方起草過政府給朝鮮官方的文書;而豐臣秀吉準備侵略朝鮮之前,曾經在天正二年(1592)供奉禪宗僧人西笑、惟杏、玄圃,因爲他們“通倭、漢之語路”,所以,西笑終生都給官方起草外交文書,惟杏、玄圃就給豐臣秀吉征討朝鮮起草檄文,文禄二年(1593)玄圃還給豐臣秀吉起草日本和大明之間的和約文書。(2) 日本禪宗經由叢林制度逐漸寺院化、宗派化,通過對漢字書寫的語録、評唱、公案的深入體驗,漸漸形成自己的思想,比如他們對《碧岩録》和《無門關》的重視,也與中國禪宗的風氣很不同。(3) 由於宋元之際、明清之際的中國禪僧東渡和日本禪僧的西來,而刺激出新宗風,並影響社會和政治,出現了前者如大休正念(1215—1289)、無學祖元(1226—1286)、一山一寧(1247—1317),後者像榮西(1141—1215,傳臨濟宗黄龍派、並傳天台、真言,有《興禪護國論》)、道元(希玄,1200—1253,傳曹洞宗),特别是隱元隆琦(1592—1673),明清之間在日本開創黄檗宗。這些日本禪宗史上出現的傑出人物與變化現象,都不是宋元以下中國禪宗所具有的宗教現象,因爲日本禪僧對於中國文化影響很小,而中國禪僧對於日本文化影響很大。要研究日本禪宗史而研究有關日本的中國禪宗史,其實已经是很大的一個領域,它時時刺激着禪宗研究的變化和發展,如野川博之《明末佛教の江户佛教に对する影響——高泉性潡を中心として》就是一例。。第二,是近代學術背景差異。日本的佛教與禪宗研究,自從明治以來,不僅受到西方印度學、佛教學的影響,學會西洋宗教學的分析方法和歷史學的文獻訓練,還受到西方哲學的衝擊與刺激,因此才會出現所謂關於禪宗是否真的是佛教,禪宗思想與西方思想孰優孰劣這一類充滿現代意味的問題的爭論。特别是,他們中間很多是禪宗的信仰者與實踐者,因此,在西方思想衝擊下,他們試圖以禪思想來回應和抵抗的心情,就格外迫切,那種對於禪宗的超歷史的過度解釋、哲理化禪宗思想和實踐性組織活動*如鈴木大拙的海外傳播禪宗,久松真一對海德格爾、田立克的對談,他所創立的F.A.S協會,根據三個中心觀念即“無相的自我”(Formless Self)、“全人類”(All mankind)、超歷史(Supra-historically),參看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版。,就呈現了他們的努力方向。而這一種努力方向,是以歷史和文獻爲中心的中國禪宗研究者所不具備的。
再説一下歐美的禪宗史研究*1993年以前的情況,可以參看馬克瑞(John McRae)的“Buddhism: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2(1985): pp.354-371;佛爾(Bernard Faure)的“Chan/ Zen Studies in English: the State of the Field”,法文原載《遠東亞洲叢刊》(Cahiers d’Extreme-Asie, 7; EFEO, Paris-Kyoto, 1993),有蔣海怒所譯中文本《英語世界的禪學研究》;近年的研究情況,可以參看羅伯松(James Robson)《在佛教研究的邊界上》(中譯本),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89—109頁。當然,後者並不是專門介紹禪宗研究,而是包括禪宗在内的東亞佛教研究。。在這一方面,我没有做過深入研究,只能就1980年代以後,也就是過去籠罩性的鈴木(大拙)禪終結之後的一些新話題和新趨向,舉一些例子*2006年以來,英文世界有關禪宗史的著作,如Jia Jinhua(賈晉華): Hongzhou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in Eighth-through-Ten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Wendi L.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 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rio Poceski: Ordinary Mind as the Way(有關洪州宗)(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orten Schlutter: How Zen Become Zen(有關宋代禪宗史) (University of Haweii, 2008); Albert Welter: The Linjilu and the Creation of Chan Orthodox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an Cole: Fathering your Fath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首先是關注“周邊的或邊緣的領域”。一般説來,中國學者很容易一方面把禪宗看成是漢傳佛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則較多聚焦於禪宗精英層面的話題,關注禪宗的傳承系譜與思想脈絡*在較早時期,中國學者中只有吕澂、陳寅恪等少數學者例外。我在另一篇論文《預流的學問》,載於《文史哲》(2015年第5期)中説到,中國學者裏面,陳寅恪就注意並且也加入這一學術取向之中。比如1927年剛剛回到中國的陳寅恪發表的《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就是運用他對各種文字如藏文的知識,研究了一個叫作“法成”的吐蕃僧人,在河西被吐蕃佔據和張義潮光復時期,往來於吐蕃、敦煌、甘州等地的講經説法情況。。可是,近幾十年來歐美學者的研究取徑卻很不一樣,他們一方面始終對漢族中國周邊即日本、中國西藏、蒙古、中國新疆、越南、朝鮮的佛教禪宗有很多的關注,特别是對古代的吐蕃、西域和西夏,較早的學者中,無論是法國的戴密微,還是意大利的圖齊,都在這一方面相當用力。佛爾《英語世界的禪學研究》中提到的Whalen Lai 和Lewis Lancaster合編的《漢藏早期禪學》(1983)*Whalen Lai, Lewis Lancaster: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3).、Jeffrey Broughton的《西藏早期的禪學》、馬克瑞對南詔(今雲南)禪宗的研究,以及大量對日本、朝鮮禪宗的研究論著,都説明這一方向長期被堅持。這當然是由於歐美東方學對於中國“四裔”——不僅是滿、蒙、回、藏、鮮,也包括西域、南海——的地理、歷史、語言、文化的關注,對於他們來説,所謂“中國”與“四裔”,並不像中國學者有中心與邊緣的差異,因此,就像他們對中國“本土”抱有關注一樣,對這些邊緣地區的禪宗流傳也曾經相當用心。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禪宗本身的研究也不像中國學者那樣,把眼光集中在著名禪師和精英階層中,真的相信“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感悟體驗,或者是沉湎於語録、公案、機鋒之類的語言文字資料,把禪宗當作玄妙與超越的思想史來研究,而是深受文化人類學等學科之影響,非常注意“眼光向下”,不僅注意到禪宗信仰的民間傳播與滲透,而且關注形而下的問題,如禪宗的教團、禮儀、贊助與規矩。比如,我們看到一些有關禪宗的“Ritual”的討論,例如佛爾編的ChanBuddhisminRitualContext*佛爾(一譯佛雷或傅瑞,Bernard Faure): Chan Buddhism in Ritual Contex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鮑狄福(William M. Bodiford)的ZenintheArtofFunerals:RitualSalvationinJapaneseBuddhism*鮑狄福(William M. Bodiford)的“Zen in the Art of Funerals: Ritual Salvation in Japanese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32-2: pp.146-164。。他們的目的顯然是把宗教放進具體的歷史語境,從社會學角度觀看宗教的形成與信仰的傳播,考察看似破棄戒律卻遵循清規的禪宗,觀察禪宗如何在政治、社會與寺廟中實際存在。也許,這是百多年來,甚至更早的歐洲東方學就形成的傳統。正是因爲歐洲有一個廣泛的東方學傳統,又有各種語言、文書、考古的工具,因此,他們一貫相當注意研究中國的邊疆地區,發掘邊邊角角的新資料,加以新解釋,禪宗史研究領域也一樣*例如,法國學者戴密微的《吐蕃僧諍記》就是利用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書(伯4646),對八世紀後期發生在吐蕃的印度佛教和大唐禪宗爭論的一個研究。通過對於敦煌漢文文書《大乘頓悟正理論》尤其是一個叫王錫的人的序文的研究,把過去僅僅從藏文資料《桑耶寺志》中看到蛛絲馬跡的佛教論爭歷史,一下子搞清楚了。説明八世紀後期,迅速崛起的漢地禪宗,曾經影響過吐蕃,只是在與印度佛教的較量中失敗,纔退出吐蕃。後來,日本學者如上山大峻、今枝由郎等,也加入了這一領域,並且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其次,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是,近年來歐美學者對日本禪宗研究與詮釋中隱含的政治背景的發掘與批判*參看Paul Swanson: Recent Critiques of Zen,日文本《禪批判の諸相》,載《思想》,東京: 岩波書店(2004年第4期),第126—128頁。。近三十年來,像Brian Victoria、Robert H. Sharf、Bernard Faure等人已經從日本學者如鈴木大拙叙述和構造的“禪”形象中走出來,開始追究那些看上去寧靜、空無的“禪者”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取向。他們不再把現代日本禪學研究者向西方刻意傳播的禪思想和禪藝術,放在想象的純淨的思想世界,而是放回到現實的歷史世界中去*Brian Victoria: Zen at War (Weatherhill: New York, 1997);日文本《禪と戰爭: 禪佛教は戰爭に協力したか》,東京: 光人社2001年版。應該指出,他對禪宗的這一批判也受到日本京都花園大學的禪宗研究教授市川白弦(1902—1986)《佛教者の戰爭責任》(東京: 春秋社1970年版)的啓發。Brian Victoria是一個傳教士,1961年也就是越南戰爭期間到日本之後,對基督教聖戰很有懷疑,覺得佛教的和平之道很好,於是漸漸對禪宗發生興趣,因此不僅學習參曹洞禪,而且開始進行禪宗研究。但是,當他看到二戰期間一些著名禪僧的言論後,他又産生很大懷疑。這本書就從日本明治時期禪宗的動向開始,考察日俄戰爭(1904—1905)中的“護國愛教”、1913年至1930年佛教與日本軍部在“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中的合作,以及一直到二戰期間的各個禪僧與禪學者的表現,指出他們與“皇國”或“軍國主義”的關係。另外一個學者羅伯特·薩福(一譯沙夫,Robert H. Sharf)的一些論著,則考察的是鈴木、日本禪和民族主義或者帝國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他認爲,鈴木大拙在構造一種東方人與西方人奇怪的二元對立圖像時,借用禪與現代西方思想的差異,對西方進行否定,特别是在二戰中所寫的有關《日本的靈性》和《禪與日本文化》等等,其實與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確立日本精神價值的意義,是一致的。包括他對日本禪和中國禪的認識中,常常流露中國佛教衰亡没落,日本禪宗在宋代以後成爲純粹和正宗,也是同樣帶有這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背景的。。特别是,當他們借用福柯的“知識”與“權力”的理論,以及薩義德的“東方學”思路來反觀日本的禪學研究時,他們尖鋭指出,日本禪學者形塑“日本心靈”和“日本人”的時候,强調“靈性的經驗”,會有意誇大日本禪宗和西方思想之間的對立,如果放回歷史語境之中,顯然這與日本所謂“大東亞聖戰”中所凸顯的東西方對立,是一致的,日本宣傳禪宗思想和境界的獨一無二性,多少是在西方面前凸顯著日本的優越性,其實骨子裏面是一種民族主義*比如法裔美國學者佛爾(Bernard Faure)的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此書有一章譯爲日文《禪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興起——鈴木大拙と西田幾多郎》,載《思想》(東京: 岩波書店)2004年第4期,第135—166頁;這一點,現在并非僅僅是歐美學者,有的日本學者如末木文美士、石井公成等,也逐漸加入批判的行列。如末木文美士與辻村志のぶ《戰爭と佛教》,收入《近代國家と佛教》(“アジア佛教史14”·日本4;東京: 佼成出版社2013年版)第五章,第223—240頁。。
再次,是通過新理論新方法,對於禪宗史加以重新認識。歐美學者近年來,往往借用一些現代理論如福柯的系譜學、利科的詮釋學等等,對有關禪宗的傳統歷史研究和文獻考證的一般原則進行重新理解*有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未必非常可靠,也有從理論出發,爲解構而解構的作品。例如羅伯松(James Robson)批評過的Marten Cole: Fathering your Father: The Zen of Fabrication in Tang Buddhism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的研究就是一例。見James Robson, “Formation and Fabrication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Chan Buddhism”, HJAS 71.2 (2011): pp.311-349。。比如,把禪宗歷史系譜作爲後來禪宗的記憶、想象和重構,而不是把它當作信史來看待;又如,對於過去認爲是可信度較高的早期文獻、石刻文獻,他們並不承認史料真實程度會有不同等級和序列,甚至要從根本上質疑這些文獻,認爲這也許只是想象祖師或者編造歷史的“另一個版本”。這一點,下面我們還將仔細討論*這方面法裔美國學者佛爾(Bernard Faure)的《正統性的意欲: 北宗禪之批判系譜》(The will to Orthodoxy: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很有代表性。原書是作者1984年以法文書寫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成的,1997年由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現在有中文本蔣怒波譯《正統性的意欲: 北宗禪之批判系譜》,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但是這個譯本似乎有一些問題,這裏不能詳細討論。中文世界對本書的評價,參看龔雋、陳繼東《中國禪學研究入門》,第217—220頁。Faure還有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另外,近年去世的美國學者馬克瑞(John R. McRae)的《由禪諦觀》(Seeing Through Zen)也很有代表性。。
可是,無論是日本學者對於禪思想的哲學解説,還是歐美學者對於禪宗在當代的民族主義表現的研究,目前尚不是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中國學者擅長的、也是最關注的,仍然是在禪宗史的歷史與文獻學研究領域,也就是胡適當年開拓的領域。但是,看看歐美、日本學者引入後現代理論來討論禪宗歷史與文獻的流行傾向,我們不禁要問: 胡適代表的這一傳統歷史學、文獻學方法,還有用嗎?它是否要跟著新潮流一起變化呢?
四、 當代新方法潮流中: 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方法過時了嗎
法裔美國學者佛爾在《正統性的意欲》中,對過去相對研究不是很充分、並且評價相對較低的北宗禪*這裏有必要説明,我在撰寫《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九世紀》一書的時候,没有機會看到佛爾和馬克瑞的著作。同樣,佛爾在1997年出版他的英文版此書的時候,也没有看我本人在1995年出版的《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九世紀》對北宗禪的歷史與思想的一些新研究。,進行了一個新的研究。按照佛爾的説法,過去胡適接受了宗密的觀點,站在南宗神會一邊,以頓、漸分别南北,雖然胡適批判了後世各種禪宗文獻的“攀龍附鳳”,但他把南宗、北宗“誰是正統”的問題,看成是歷史的真實内容。而佛爾則不同,他把“誰是正統”這個問題,看成是禪門各個系統的“正統性意欲”,就是追求政治承認的運動,認爲這一本來曖昧甚至叛逆的運動,成爲後來三個世紀禪宗主導的和支配的意識,形成了禪宗的革命歷史。换句話説,就是禪門各種派别各種文獻,都在這種“正統性意欲”的支配下,在建構禪宗系譜。
他把這個追求正統性的過程分爲五個階段: (一) 六世紀,禪師在北方中國宣稱達摩爲祖師,試圖在北中國立足,但是不很成功;(二) 七世紀中葉,東山禪門在南中國崛起,但未曾與北方禪門建立聯繫;(三) 七世紀末,神秀逐漸接近中央政府;(四) 神秀的成功與神會的崛起,在安史之亂中成功成爲正統;(五) 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的衰落和新禪宗宗派在各地的興起,正統性轉向馬祖道一*《正統性的意欲》中文本第6頁,英文本,pp.4-5;但是,在這一段短短的禪史概述中,有不少問題: (一) 把法如和慧安當做神秀的弟子(His disciples),(二) 神秀700年被召,並非長安而是洛陽;(三) 神會並非在安史之亂中因爲香水錢達到目的,這是受了胡適的誤導。。這個禪宗史系譜我大體上可以同意。不過我的問題是,根據各種西方新理論重新建構的這個系譜,究竟與過去根據敦煌文書等新材料,由胡適以及其他人重新叙述的禪宗史有什麽區别?似乎没有。佛爾在書中,徵引了包括福柯、利科、海德格爾等等理論,也採用了很多新穎的術語,可是,是否禪宗這樣的歷史研究,就一定需要結構主義、詮釋學、知識考古及系譜學等等那麽複雜和時尚的理論?這些都值得深究*他的另一部著作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是1991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此外,他還編有一部論文集Chan Buddhism in Ritu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另一個近年去世的美國學者馬克瑞(John McRae,1947—2011),在佛爾的法文本博士論文之後、英文本著作出版之前,也出版過《北宗與早期禪佛教的形成》(TheNorthernSchoolandtheFormationofEarlyCh’anBuddhism,1986)。這部書比起佛爾的著作來,似乎比較偏向歷史學與文獻學的風格。有趣的是,他們兩位其實都受到日本柳田聖山的影響,而柳田聖山則受到胡適的影響*見《正統性的意欲》中文本,第1頁;英文本Acknowledgment, pp.1。。但是,西方知識背景和歐美學術傳統中的佛爾和馬克瑞,似乎都不太像柳田聖山那樣,恪守歷史學和文獻學的傳統邊界,對於目前可以看到初期文獻如敦煌文獻保持著尊重和敬畏,並以這些文獻爲判斷尺規。馬克瑞就批評説:“來自敦煌寫本的證據,大都只被用來在原有的傳統圖像上加繪一些更美的特點,只是在前述的系譜模式上加添知識上引人矚目的細節。”*引自馬克瑞另一篇翻譯成中文的文章《審視傳承乎: 陳述禪宗的另一種方式》,作者贈送的列印本。如果説馬克瑞的《北宗》一書還没有太多的理論表述,那麽,後來出版的SeeingThroughZen:Encounter,TransformationandGenealogyinChineseChanBuddhism裏面,就比較明顯地借用後現代理論,並且把歷史與文獻放置在理論視野之下重新考察。這部書的一開始,他就提出了所謂的“馬克瑞禪研究四原則”(McRae’s Rules of Zen Studies)*在馬克瑞贈給本文作者的《審視傳承乎: 陳述禪宗的另一種方式》文稿中,有他自己的中文翻譯,其中,第一條:“它(在歷史上)不是事實,因此它更重要”,第二條:“每一個有關傳承的主張,如果重要性越多,則其問題也就越大”。,這裏固然有他的敏鋭,但也有其過度依賴“後”學而過分之處*John McRae: McRae’s Rules of Zen Studies, 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Transformation,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xix.。在這四條原則中,第一條是“它(在歷史上)不是事實,因此它更重要”(It is not true, and therefore it’s more important);第二條是“禪宗譜系的謬誤程度,正如它的確實程度”(lineage assertions are as wrong as they are strong);第三條是“清晰則意味著不精確”(precision implies inaccuracy),據説越是有明確的時間和人物,它就越可疑;第四條是“浪漫主義孕育諷喻”(Romanticism breeds cynicism),據説,説故事的人不可避免要創造英雄和壞蛋,禪史也同樣不可避免,於是歷史將在想象中隱匿不見。
也許,這一理論太過“後現代”,這些原本只是禪宗歷史上特殊的現象,在馬克瑞的筆下被放大普遍化了,當然也要承認,我們如果回到最原始的文獻中去看,唐代禪宗史中確實有這種“攀龍附鳳”的情況。
不妨舉一個例子。以我個人的淺見,近幾十年中古禪宗史研究最重大的收穫之一,也是海外學者對於中古禪宗史研究的重要成績之一,就是法裔美國學者佛爾和日本學者伊吹敦,通過一塊碑文,即《侯莫陳大師塔銘》,證明了法藏敦煌卷子P.3922、P.2799、P.3922的《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彼岸法門要訣》*還有英藏(斯坦因編號)S.5533、日本龍谷大學藏58號等等,共有七個抄本。是智達禪師(也就是侯莫陳琰,他是北宗老安和神秀的學生)在先天元年(712)撰寫的,聯繫到另外一份敦煌卷子P.2162,即沙門大照、居士慧光集釋的《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這篇《論》原來被誤認爲是神會南宗系統的,現在被證明,其實它們都是北宗的。最令人吃驚的是,他們都講“頓悟”,比號稱專講“頓悟”的神會要早得多,於是,禪宗史就擺脱了傳統的“南頓北漸”的説法,也許還是神會剽竊了北宗的思想,反而在南北之爭中倒打一耙,使得後來形成了“南頓北漸”的固定看法*但是,還值得考慮的是,《頓悟真宗論》的作者署名中,沙門大照與居士慧光,是一人還是兩人,過去似乎都以爲是一人,最早英國學者L.Giles在1951年針對S.4286殘卷,於倫敦發表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中,就説“大照”和“慧光”是一個人,問答是自問自答。但是,從文中記載(慧光)“居士問”與“大照禪師答”的對話來看,恐怕是兩個人,因此,就要考慮大照有没有可能是著名的普寂?而裏面提到大照“前事安闍黎,後事會和尚”中的“會”,有無可能是“秀”之誤。田中良昭已經指出,老安(傳説582—709)和神會(670—762)相差了八十多歲,似乎慧光無法既跟隨老安,又跟隨神會。那麽,姓李的長安人慧光居士是誰?此外,如果大照真的是普寂,那麽,這份文書的時代,應該在什麽時候?。可是需要指出,這不是得益於後現代理論和方法的産物,而恰恰是傳統歷史學與文獻學方法的成果。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胡適當年的研究,不用後現代的理論和方法,其實也達到了這樣的認識,爲什麽今天的禪宗研究一定要弄得這麽玄虚呢?1993年,福克(T. Griffith Foulk)撰寫了《宋代禪宗: 神話、儀禮以及僧侣實踐》*Theodore Griffith Foulk: Myth,Ritual, and Monastic Practice in S’ung Chan Buddhism,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edited by Patricia B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147-208.,這篇被認爲是“過去的十五年關於中國禪宗史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據説它的意義是指出“我們對唐代禪宗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文獻的産物”*羅伯松(James Robson)《在佛教研究的邊界上》,中文本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0頁。,但是,這不是胡適早就指出的現象嗎?從胡適以來,學者們已經知道所謂唐代禪宗史基本上都是以禪宗自己書寫的燈録爲基本綫索的,這些傳燈録只是後人對禪宗史的叙述,這在中國禪宗史研究領域已經成爲共識或常識。因此,胡適纔會提倡,如果能够更多地依賴“教外”資料比如文集、碑刻和其他佛教徒或非佛教徒的記述,也許就可以看到,各種燈録和在燈録之後的各種研究著作中,究竟禪史被增添了多少新的顔色,又羼入了多少代人的觀念和心情。
中國的禪宗史研究者理應向胡適致敬。國際禪宗研究界也許都會察覺,在禪宗研究領域中,各國學者的取向與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在中國學界,類似西田幾多郎似的禪宗哲學分析並不很普遍,類似鈴木大拙那樣從信仰與心理角度研究禪宗的也並不發達,對於禪宗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分析,恐怕也還没有太多關注,倒是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檢討禪宗歷史的路數,始終是中國學界的風氣與長處,而不斷從石刻碑文及各種傳世文獻中發現禪宗歷史,把佛教史放在當時複雜的政治史背景之中討論,更是中國學者擅長的路子。
這也許正是拜胡適(也包括陳寅恪、陳垣)之賜。
結語: 在胡適的延長綫上繼續開拓
最後,我要越出“中古”的範圍,大膽地討論一下,在敦煌文書逐漸被發掘的情況下,我們在禪宗史研究上是否還可以獲得新進展?還有什麽地方可以讓禪宗史研究者繼續努力發掘的呢?我想針對中國學界説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這裏不限於“中古時期”,也不限於“中國禪宗”。
首先,對於禪宗在亞洲更廣大區域的傳播、變異和更新,非常值得研究。這一點,佛爾在《正統性的意欲》中已經提到,他説應當“打破流傳至今的中日(sino-japanese)視角所帶來的限制”。他説,要注意禪宗曾經在唐代作爲一種思想(我覺得同樣重要的是,禪宗作爲一種生活藝術和文學趣味),曾經傳播到了中國和日本之外,比如中亞、吐蕃、越南、朝鮮,所以,應當從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區域中“恢復它的原貌”*《正統性的意欲》中文本,第8頁。。雖然,所謂“恢復原貌”有一點兒違背了他這本書“後現代”的立場,不過,我們確實應當承認這個建議有道理,關注禪宗的傳播、影響、適應以及變化,並且更注意這背後的文化和歷史原因。像八世紀末北宗禪宗與印度佛教在西藏的爭論,像禪宗文獻在西域的流傳,像中國禪宗在朝鮮衍生支派,像日本禪僧對中國禪的重新認識,像明清之際中國禪宗在西南與越南的流傳等等。這方面,戴密微的著作《吐蕃僧諍記》就值得學習。
其次,禪宗在各國政治、社會、文化上的不同影響,以及它在各國現代轉型過程的不同反應和不同命運,其實是很值得討論的。以中國和日本的歷史上看,我們看到,後來的中國禪宗,雖然經過宋代的大輝煌,但是它的世俗化(從“佛法”到“道”轉向老莊化,不遵守戒律的自然主義,自由心證下的修行)很厲害,自我瓦解傾向也很厲害。所以,它一方面成爲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情趣,一方面在世俗社會只能靠“禪淨合流”以拯救自身存在,即使明代出現幾大高僧,似乎重新崛起,但仍然曇花一現,一直到清代它最終衰敗。這個歷史和日本很不一樣,日本僧侣的獨立化、寺院化與儀式化,經歷五山、室町、德川時代的昌盛,到了近代仍然可以延續。它一方面通過介入世俗生活深入民衆,一方面依靠與王權結合成爲政治性很强的組織,它不僅可以與武士道、葬儀結合,也可以充當將軍的幕賓和信使,所以即使後來遭到現代性的衝擊,禪宗仍然可以華麗轉身,與現代社會結合。後來出現很多像鈴木大拙、西田幾多郎、久松真一這樣的學者,當然也出現深刻介入軍國主義的宗教現象,更出現宗教的現代大學和研究所,這與中國大不相同。所以,這些現象很值得比較研究,也許,這就是把禪放在“現代性”中重新思考的研究方式。
再次,我希望現代學者研究禪宗史,不必跟著禪宗自己的表述,被捲入自然主義的生活情趣、高蹈虚空的體驗啓悟、玄之又玄的語言表達,也不一定要把禪宗放在所謂哲學那種抽象的或邏輯的框架裏面,分析(發揮)出好多並不是禪宗的哲理。這不是現代的學術研究方式。反而不如去考察一下,禪宗除了這些虚玄的思想和義理之外,他們還有没有具體的生活的制度和樣式,他們在寺院、朝廷(或官府)、社會(或民間)是怎樣存在的。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百丈清規》以下,有一些關於禪僧生活的規定,好像和他們説的那些高超玄妙的東西不同,可是如果你看《禪林象器箋》就會知道,禪宗寺院裏面各種器物,他們還是要維持一個宗教團體的有序生活。所以,研究禪宗不要只是記得超越、高明、玄虚的義理,也要研究形式的、具體的、世俗的生活。
最後,我們要引述幾句胡適關於禪宗史研究的話,來結束這篇論文。胡適曾經評論日本禪學者和自己的區别,説“他們是佛教徒,而我只是史家”;他又提到,“研究佛學史的,與真個研究佛法的,地位不同,故方法亦異”。在1952年他批評鈴木大拙談禪,一不講歷史,二不求理解,可是他認爲,研究禪宗“第一要從歷史入手,指出禪是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階段”*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册,第229—231頁。。
這些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2015年11月完稿於東京大學
(作者單位: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