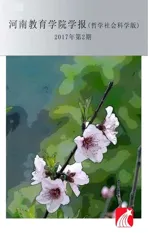周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
——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①
2017-03-10张庆善
张庆善
周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
——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①
张庆善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新朋老友:
大家上午好!
在传统的鸡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会场”,举办“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这无疑是一次很特别、很重要的专题座谈会。吸引了这么多在《红楼梦》研究上卓有成就的著名专家学者,我感觉这很有可能是红学史上非常值得记载的一次专题座谈会。在此,谨对主办单位对我的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借此机会提前向各位朋友拜个年,祝大家健康、幸福、愉快,阖府安康!
坦率地说,当接到主持人淮生兄的邀请后,要不要参加这次座谈会,是有些犹豫的,我感到有些左右为难。如果不参加,那肯定是个问题:这里离我家很近,几分钟就走过来了。你不参加是什么意思?你对周汝昌先生是什么态度呢?参加也为难:来了就要发言,谈什么,怎么谈,很费思量。谈“周汝昌与现代红学”这个题目不容易,远比谈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红学大师困难得多。这不是因为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观点有多深奥,有多难解读,而是因为现在一谈周汝昌就容易引起争议,就容易闹“意气”,很难把握在学术的范畴内,所以说是左右为难。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座谈会。我认为参加比不参加好,不管围绕周汝昌先生有多少话题、多少争论,甚至“恩恩怨怨”,我们都得面对,因为周汝昌是红学绕不过的话题。
为什么一谈周汝昌就会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总是那样愤愤不平呢?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其实,研究周汝昌,应该与研究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冯其庸、李希凡等红学大家一样,是红学史研究绕不过的话题,因为这些红学大家都是在红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他们不是简单地评价他们个人,而是研究红学史。因此,不管是怎样的观点,是赞赏还是批评,只要是认真的学术研究,都应得到尊重。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尊重你的学术权利。
周汝昌先生无疑是当代红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也是“话题”最多的红学家,谈周汝昌先生不容易。要谈好“周汝昌与现代红学”这个题目,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充分肯定周汝昌先生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充分认识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贡献;二是全面细致地梳理围绕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产生的争议,分析这些“话题”产生的原因,争论的要点,从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分析。
一、关于周汝昌先生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学术贡献
毫无疑问,周汝昌先生在当代红学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称他为红学大师、红学泰斗并不为过。冯其庸先生在《曹学叙论》中指出:“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那么,周汝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曹学叙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我想,冯其庸先生这个评价,可以说是红学界的共识。早在1953年,《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就奠定了周汝昌先生的学术地位。《红楼梦新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巨著,它的出版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多少年来,《红楼梦新证》都是红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书,几乎像工具书一样被人们所重视、所使用。《红楼梦新证》的主要价值在于文献史料丰富而翔实,其中“人物考”“雪芹生卒”“史事稽年”“脂砚斋批”“本子与读者”等章节的价值尤其大。周汝昌先生在胡适开创的基础上,把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及《红楼梦》时代背景研究更加体系化,并在《红楼梦》早期抄本、脂批、探佚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一座巍峨的红学大厦。这充分展现出周汝昌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识见,也是他对红学的最大贡献。当然,《红楼梦新证》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无论《红楼梦新证》存在多少问题,都不影响它在红学史上的地位。
除《红楼梦新证》外,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艺术,特别是《红楼梦》表现手法的研究上,也有着突出的成就。他的《曹雪芹小传》是第一部关于曹雪芹的传记,其历史性的贡献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坦率地讲,我非常喜欢看周汝昌先生的《红楼小讲》《红楼艺术》等书,他对《红楼梦》许多章回和故事、人物、艺术特色的分析是非常精彩的。
几十年来,周汝昌先生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红楼梦》研究上,他不仅是红学著述最多的红学家,也是影响最大的红学家。他的影响力,对红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科学地梳理、总结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贡献,应该是红学的重要课题。我希望能有人系统地做做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希望年轻学者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对红学的建设和发展是很重要的。
二、关于围绕周汝昌先生的“话题”
周汝昌先生贡献很大,但同时围绕着他的争论也很多,也就是“话题”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周汝昌先生的名气大、影响大,他无论说什么,都很容易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很容易形成“话题”;二是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许多观点很多学者不认可,争论也就不可避免。我的意思是说,围绕周汝昌先生的“话题”多、争论多,是由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引起的,是由周汝昌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造成的,也是由于“话题”本身具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而不是大家与周汝昌先生过不去。周汝昌先生的“孤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大家的不友好或是文化层次低,或是缺少特殊的悟性,恐怕还是与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方法、研究观点以及个人性格、想法有重要关系。
我们不妨细细地捋一捋围绕周汝昌先生的那些“话题”。如,什么是红学;关于“还‘红学’以‘学’”的问题;后四十回是乾隆皇帝与和珅阴谋的结果;曹雪芹的妻子是史湘云,即脂砚斋;贾宝玉不爱林黛玉,爱的是史湘云;“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都是指贾宝玉与史湘云的爱情,史湘云才是《红楼梦》的主角。其他还有:“曹雪芹佚诗”的真假;“《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兼凭吊雪芹》”的真伪;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是不是“震惊人类的发现”;关于曹雪芹祖籍的“丰润说”“铁岭说”;曹渊即曹颜,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等等。
这么多“话题”,哪一个都是值得讨论而又敏感的学术问题。何况这些又都是周汝昌先生提出来的,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怎么可能不争论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话题”,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争议。我认为围绕周汝昌先生的“话题”展开的讨论或争论,都是正常的学术研究,不能因为少数文章的语气比较尖锐或不怎么“友好”,就否定讨论的学术性质和学术价值。
虽然围绕周汝昌先生有那么多的“话题”、那么多的争议,但归纳起来,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观点有三个核心,即写实自传说、后四十回阴谋说、史湘云主角说。其中,核心的核心是写实自传说。
早在1953年《红楼梦新证》初版时,周老就认定《红楼梦》是作者的写实自传。他说:“我讨论过好些人,他们都不大赞成把小说完全当历史看,因为小说没有字字句句都是实话的。但我岂真是头脑简单得连这个大道理也闹不清楚?只是我看过了脂批以后,益发自信并非自己呆头死看。《石头记》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写实,那只是文学上手法技巧的问题,而绝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虚伪。譬如大荒山下的顽石,宝玉梦中的警幻,秦钟临死时的鬼卒……我虽至愚,也还不至于连这个真当作历史看。但除了这一类之外,我觉得若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账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570页)这里,周汝昌先生说得清清楚楚,《红楼梦》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写实”,也只是文学上手法和技巧的问题,“材料和立意”则是写实的,也就是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把一部《红楼梦》看成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实际上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在《红楼梦新证》中,周汝昌先生常常是“曹贾不分”“曹贾互证”,他以历史上实有的曹家的事情推证小说本事,又以小说故事情节反证历史。在他的“新证”下,历史上实有的曹家人常常与《红楼梦》中的人相会,譬如他说:“曹在二十来岁上被过继给贾母,抛开嫡亲生母,以他人之亲为亲……而曹与胞兄贾赦反较亲近。”(《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页)又说:“贾母平生只哭过五次……其余二次便都是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一次是方才所引,与贾政说,当初你父亲何等待你,何曾下过毒手?因而下泪。另一次是在第二十九回,张道士拿宝玉比曹寅……原来贾母在五十多岁上,把威扬显赫的丈夫失去,不到三四年,唯一的儿子曹颙又病死……”(《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78~79页)“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所谓旧时真本,也许是可靠的;而脂批《红楼》的脂砚斋,就可能是曹雪芹所遗的未亡人史湘云。”(《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页)这里曹寅成了贾母的丈夫,贾政成了过继的儿子曹,曹雪芹则娶了史湘云,这都真真切切反映出周汝昌先生的基本认识:《红楼梦》是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当然还包括了苏州李家的“生活实录”,甚至还隐藏着康熙废太子胤礽夺嫡斗争的“清宫秘史”。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搞清楚“本事”,他明确地说《红楼梦考证》“唯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566页)。因此,写实自传说的实质就是否定《红楼梦》是文学作品。虽然周汝昌先生后来提出《红楼梦》是“文化小说”的观点,但我们很难理解,一部“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怎么会成为“文化小说”呢?
我们都说周汝昌先生是新红学“自传说”的集大成者,但周汝昌先生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还是很不同的。他的研究方法也不是胡适的“考证”,而是“考证+索隐”。胡适倡导“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倡导“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周汝昌先生则把胡适批评的“索隐”又拿了回来,认为考证就是索隐,索隐就是考证。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猜笨谜”,周汝昌先生的索隐又何尝不是“猜笨谜”呢?周汝昌的“索隐”与蔡元培的“索隐”以及霍国玲的“索隐”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认为当下红学之争最大的焦点,就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还是把《红楼梦》当作曹家“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来读来研究。坚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研究,并不降低《红楼梦》的伟大和文化价值,也并不否认研究作者家世、版本、脂批、探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都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基础。争议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这些是为了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文化内涵,还是为了探寻曹家本事和清史秘闻,这是问题的实质。
周汝昌先生非常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强调红学的特殊性。他说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红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又说:“曹雪芹并不是一位一般的小说作者(明清以来,可谓车载斗量),而是一位中华文化的大哲士,大思想家。他的《石头记》并不是一部‘小说’,而是应当列入‘子部’的‘创教’之巨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曹雪芹〈红楼梦〉之文化位置》,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页)我认为,这些对红学特殊性的“强调”,对曹雪芹身份的“高度评价”,对《红楼梦》的“高度定位”,都不是很妥帖,不很实在,有些大而无当。说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那么研究《论语》、研究唐诗宋词、研究四书五经,算什么学呢?曹雪芹不是什么大哲士、大思想家,他只是一个小说家,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古往今来写小说天下第一。大哲士、大思想家是写不好小说的,更别说写出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文学经典了。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红楼梦》确实是“特殊”的,但“特殊”不等同于“神秘”,再“特殊”,也不能把《红楼梦》“特殊”到不是小说的地步。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这里说的就是《红楼梦》的“特殊”,说简单一点,《红楼梦》的“特殊”就在于它与以往的小说不一样。那它“不一样”在哪里呢?为什么人们总觉得《红楼梦》中隐藏了什么呢?主要原因是:(1)《红楼梦》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而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家世又成为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再加上作者的才华和创作理念,对生活细节以及吃穿住行描写得十分真实细腻,特别是对人物的刻画真实生动,栩栩如生,让人们读《红楼梦》常常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2)《红楼梦》是人生感叹、人生体验、人生感悟的结晶,作者把人生的感悟写得那样深刻,因而人们读《红楼梦》时很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人生体验的共鸣,读《红楼梦》如同咀嚼自己的人生一样,故而强化了一种“真实”的感觉。(3)《红楼梦》的叙述和艺术表现手法是“意象”的、是“诗性”的,不同于以前的叙述手法,从而常常使人们感到“言外有言”“别有意境”,似乎在《红楼梦》文字背后隐藏了什么似的,这当然是对《红楼梦》的误读。俞平伯先生就说读《红楼梦》求深反浅、求深反惑,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红楼梦》的伟大和特殊,不在于它隐藏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红楼梦》写出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物的生活、爱情、人生悲剧,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鞭笞。鲁迅说:“然而纵使谁整个地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的实有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地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借用鲁迅的话,我们不妨这样说,纵使曹雪芹家的“本事”和清宫夺嫡斗争的“秘闻”整个地进入了《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的也只是荣国府、宁国府以及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母等艺术形象,和这曾有的史事和人物倒不相干了。《红楼梦》是《红楼梦》,曹家本事是曹家本事,清宫秘史是清宫秘史。《红楼梦》永远是伟大的文学经典,而曹家本事和废太子胤礽的秘闻不过是令人好奇的奇闻秘事。无论是曹家的生活实录,还是清宫秘史,都不会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也不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非常感谢主持人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前几次开座谈会也都是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想这是对我多少有一点照顾的意思吧。如果说前几次的“第一个”发言,还比较坦然,这一次倒有些忐忑了,但我绝对是坦诚的。不管是讲了一堆“正确的废话”,还是“满纸荒唐言”;不管是抛砖引玉,还是竖了一块被“批判”的靶子,我是坦诚地说出了我的观点和看法,对本次座谈会的期待也是真诚的。我十分相信主持人淮生兄的胸怀和能力,也相信在座的各位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能力。当然我不奢望一次座谈会能有多大的学术成就,更何况周汝昌是红学的大题目,怎么可能开一次座谈会就说完了呢。但我寄希望于这次座谈会,寄希望于大家以良好的学术品格、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谈周汝昌,坦诚相见,来一场君子之争,为研究“周汝昌与现代红学”开个好头,为在红学界建设良好的学术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借此机会再一次对为红学事业呕心沥血、成就卓著的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017年1月14日
(张庆善,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范富安)
1006-2920(2017)02-0001-04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2.001
①本文在录音稿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加工,一是加了标题;二是重新核实引文,随文注明;三是座谈会规定发言不超过20分钟,发言时内容有省略,征得作者和主持人同意,发表时恢复了省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