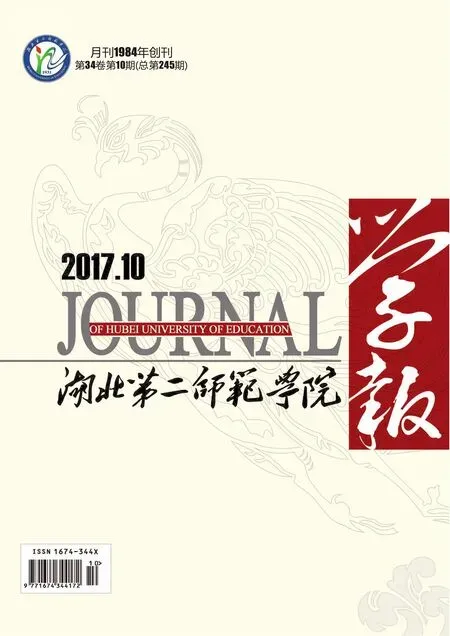阿尔比戏剧中显性与隐性的平行创伤叙事
2017-03-09洪琪
洪 琪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205)
阿尔比戏剧中显性与隐性的平行创伤叙事
洪 琪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武汉 430205)
美国戏剧家阿尔比的戏剧大多以戏谑的笔调展现现代人的心理创伤,创伤随着剧情发展一层层地剥离出来,但读者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物创伤的抚慰和治愈。本文基于创伤理论和叙事学理论,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海景》和《三个高个子女人》为例,发现阿尔比的戏剧通过显性情节叙事表现人与家庭、自然和自我关系在崇尚工具理性的现代文明中产生的集体创伤;同时,通过隐性进程叙事帮助人物治愈创伤。这两条叙事平行贯穿于阿尔比的戏剧中,使读者感受创伤获得共鸣并在无形中得到创伤的宣泄、洗涤和治愈。
阿尔比;显性情节;隐性进程;创伤叙事
“创伤”原指医学术语“刺破或撕裂的皮肤”,后由弗洛伊德代表的创伤研究发展到心理层面,拉康又将创伤研究从个人经历发展为集体创伤,之后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社会学、文化研究及文学批评领域等。由此创伤由个体的心理疾病演变为一种社会群体症候。去年辞世的美国著名剧作家阿尔比一生笔耕不倦,其戏剧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展示了在崇尚工具理性和金钱至上的现代文明中人们经历的集体创伤,如分别获得托尼奖和普利策奖、代表阿尔比早中晚期创作成就的的三部作品《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1962)、《海景》(1975)、《三个高个子女人》(1991)就很明显的揭示了家庭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疏离和人与自我的排斥。但阿尔比创作目的不仅在于揭示创伤,他更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剧中暗暗引导和帮助人们治愈心理创伤。因此形成“双重叙事进程, 一个是情节运动;另一个则隐蔽在情节发展后面,与情节进程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这种隐蔽的叙事运动称为叙事的“隐形进程”[1]48。
一、显性情节叙事展现剧中人物心理创伤
阿尔比首先用显性情节叙事展现了人物的心理创伤。由于“创伤事件在它发生的时刻没有被充分地体验和吸收,只能延迟地表现在他的持续和侵入式的返回上”[2]13,如闪回,噩梦,侵入式回忆,规避,感情麻木,过激反应,恐惧,愤怒,暴力,冷漠等,阿尔比戏剧中的人物正好符合这些创伤症状。并且创伤记忆和症状在这个程中经常发生变形和扭曲,或以伪装的形式出现,需要通过重复,非线性的,非逻辑的创伤叙事来展现人物的心理创伤。
1.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中家庭关系的异化
对家庭关系的探讨如夫妻关系和父子母子关系等是阿尔比戏剧最重要的主题,《谁》剧中尤为突出。婚姻的基础是爱和情,剧中两对夫妇的婚姻却沦为获得金钱和权力的工具,不幸婚姻带来的创伤在他们的午夜聚会中一一展现。首先是乔治的异常表现,他不断重复歌唱改编自经典童谣《谁害怕大灰狼》的歌谣,并且通过游戏来回避玛莎的讽刺和挖苦,之后还两次表现过激反应:一次拿玩具枪对着玛莎,一次企图掐住玛莎的脖子;对玛莎和尼克的调情也表现得异常麻木和冷漠,甚至说“为什么你们不去缠绵,别打扰我,我要看书”[3]271。“回避与事件有关的任何刺激并出现广泛的麻木反应是心理创伤的具体症状”[4]8。其次,学校聚会结束已是午夜,本该休息,玛莎却因丈夫聚会上相形见绌而加深她的创伤体验无意入睡,执意邀请尼克夫妇继续家庭聚会;为了刺激丈夫,发泄心中的怨愤,她用尽语言暴力和闪回乔治的失败经历,甚至采取当众给丈夫戴绿帽子的过激行为;为规避膝下无子的事实,夫妇俩甚至幻想出一个儿子和他们生活。另外,尼克的性无能和哈尼逃避成长都是心理创伤的体现。
2. 《海景》中人与自然的疏离
现代城市的扩张和文明的发展是以蚕食自然作为代价,禁锢在钢筋混凝土的中的人们被剥夺与自然的交流的机会,逐渐关闭内心情感,变得麻木和冷漠。剧中查理就算是远离城市喧嚣,来到海边享受碧海蓝天的沐浴,也无动于衷,对南希的憧憬和激情表现得极为麻木,只用一句“我啥事不想做”来回应。他这种麻木和冷漠甚至危及婚姻,让妻子怀疑他外遇而想到离婚。其次,海边前后四次出现的飞机刺耳轰鸣,打破自然的和谐,象征工业文明导致现代人的精神创伤。一向对外界事物麻木的查理对此极其敏感,每次都厌恶地说道:“这玩意儿迟早要撞到沙丘上。我不知道它们能干什么好事。”[3]373由此可看出虽然查理置身自然,但仍无法摆脱工业文明给他带来的创伤,因为“创伤具有一种萦绕不去的品质,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返回持续占有主体”[2]14。 另外,由于现代文明是靠掠夺自然,占用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来获得,人与其他生物关系敌对化。不难理解查理偶遇蜥蜴夫妇,第一反应是“找个棍子来”“给我拿把枪来”。文明使他身处自然却无法象儿时一样亲近自然。
3. 《三个高个女人》中人对自我的排斥
剧中第一幕呈现的是现实场景,ABC分别为老年的女主人公,中年的保姆和年轻的律师,A不断闪回到自己的创伤记忆,如身体的衰老、禁欲式的教育、贫穷的家庭、互为利用的和不忠的婚姻、酗酒的妹妹、同性恋的儿子等,这些记忆如此痛苦,最后说到激动处甚至中风。第二幕阿尔比让ABC扮演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主人公,并让她们同台对话。自我在不同阶段经历的创伤不同,呈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同,导致自我的相互排斥。年轻的C人生经历少,尚未有过多的创伤体验,无法理解和认同中年的自我B和老年的自我A,并信誓旦旦说“我不会变成你这样”、“我排斥你”、“不喜欢你”。其实,当B向C解释她变化的原因时道出了人成长中必经的创伤体验:“父母,老师,所有其他人。你们对我们撒谎。你们不告诉我们事情会变化的———白马王子的品行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你还得忍受,喜欢,或者假装喜欢……这些没有人告诉你”[3]372。 A进入社会后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创伤体验让她震惊和恐惧,进而启动“自我心理防御机制”,使得自我变得强大以抵御外在创伤刺激,这样导致她在家庭关系,自我认知上的排斥,她自己也说“他们都恨我,因为我太强了”[3]351。
二、隐性进程叙事帮助心理创伤的复原
从显性情节看,阿尔比戏剧将人物的心理创伤一一剥离,但读者在感受人物悲剧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创伤的宣泄和洗涤;实际上,阿尔比戏剧中隐藏一条与情节平行的叙事暗流,一条将人物和读者从集体创伤中解脱出来的道路,这就是阿尔比戏剧中的隐性进程,也是阿尔比创作的真正目的。戏剧中的创伤复原可以根据Herman提出的复原的三个阶段来体现:“第一个阶段是安全的建立;第二个阶段是回顾与哀悼;第三个阶段是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5]145。
1. 隐喻方式获得安全感
创伤主体一方面被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所萦绕,一方面由于无法正视和理解所受的心理创伤,他们往往没有安全感,而规避自己的创伤经历不愿讲述;且“创伤压抑在无意识中”,无意识常常是梦境的、非逻辑、超自然的状态,只有进入这种状态,进入创伤才可治愈创伤。
如何进入创伤并获得安全感呢? 阿尔比在他戏剧中设定各种非常规手段打破原有生活场景,以隐喻的方式进入创伤。因为“隐喻被当成一个进入封闭状况的方式…如果无法直接谈论某件事,可能就可以透过隐喻来进行,因为使用隐喻和原课题产生的距离,有助于个案谈论某件他们无法直言的事物”[6]252。 《谁》通过年轻夫妇的到访打破常规生活场景,以荒诞游戏的形式进入创伤;《海景》通过海边蜥蜴夫妇的出现打破生活常规,以人兽对话进入创伤;《三》通过过去和现在的自我同台来打破生活常规,以不同自我的对质进入创伤。这些不同寻常甚至超自然的隐喻是让人物卸下包袱,进入封闭的安全环境,为讲述创伤做准备。
《谁》剧中游戏的内容隐喻了乔治夫妇的婚姻关系。乔治给四个游戏“羞辱男主人”、“戏弄客人”、“干女主人”、“养育孩子”命名,完成安全感建立的第一步 “受创者光知道他真正的病名,压力就减轻了。经过确诊,他开始对病情有了掌控。不再禁锢于无言的创伤中”[5]147。帮助人物直接面对和确诊创伤:乔治仕途的失败、尼克夫妇无爱婚姻、玛莎的偷情和无子的痛苦。
《海景》中海边和蜥蜴夫妇隐喻自然。“风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和潜在的对抗灾难的救赎力量”[2]11。查理夫妇来到海边暂时远离代表工业文明的城市,因为“你(查理)恨城市”。在碧海蓝天的自然中,南希心情愉悦,憧憬未来;查理慢慢敞开心扉,回溯童年与自然交融的美好情景。“我精神放松,身体慢慢下沉,让双脚触到海底细沙。绿油油的蕨类植物和苔藓踏上去软软的,鱼儿缓缓游过,轻柔地抚摸你的脚趾”[3]379。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查理内心的安全感逐渐建立。
《三》的第一幕中,A表现出明显的创伤症状,时常因疾病无法掌控身体而哭泣、不断闪回创伤记忆等。她对其他人也极其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甚至说:“所有的人都想骗我的钱”[3]331。但是,第二幕阿尔比让ABC代表不同自我同台对质实则隐喻了自我的反思,让女主人公和不同年龄的自我对话,让她沉浸在自我的封闭状态,赋予她足够的安全感。
2. 碎片化的讲述
“创伤破坏了受害者思维框架,导致对创伤的经历、理解和言说分裂”[7]6。因此创伤心理的治愈需要通过讲述来恢复、整合被遗忘、被分解、被压抑的记忆,将创伤记忆转化为正常记忆。但是创伤主体的讲述从来都不是平铺直叙,常常时行时停,话语往往是碎化的。“如果创伤完全可以接受叙述的规划,那么它就需要一种与传统的直线顺序分离的文学形式”[4]6。戏剧的对话形式为碎片化,非线性、重复的创伤叙事提供天然平台。
《谁》剧中,在游戏的隐喻下,人物“就像在酒神仪式中,可以抛弃理性社会对心灵的禁锢,尽情释放自己的本能欲望 ”[8]57,能将心理创伤一一讲述。首先,乔治表达对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崇拜的厌恶,“人类将失去灿烂的多样性和不可预见性…历史的大海般的千变万化的节奏都将一起毁灭”[3]199也使得人变得极端理性和灵魂的缺失;玛莎也通过讲述表达自己由校长女儿转变为普通教师乔治的妻子的失落和通过谈论假想的儿子来慰藉无子的痛苦。
《海景》中在自然的感召下,南希第一次讲述了沉积在心里多年对冷漠的丈夫和婚姻的感受,“性爱变得…越来越少;…你知道吗?有一个星期我都在想和你离婚”[3]382。南希甚至怀疑丈夫有外遇而对她冷漠,其实查理只是因现代生活让他丧失生活的激情和交流的能力,这样的创伤回顾和交流,让查理夫妇开始了解彼此。其后与蜥蜴夫妇交流更让查理夫妇明白那些“区别我们和动物的东西”,如工具、艺术、道德等所谓的文明产物并没有让人与人更近,而是更远。查理甚至对蜥蜴夫妇说“也许我羡慕你们…在海下面,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在下面和动物在一起…死亡是一种解脱”[3]443。通过讲述,南希理解查理的痛苦,拥抱亲吻安慰他,夫妇俩慢慢开始以诚相待。
“创伤受害者在讲述关于创伤的故事时通常会混淆过去和现在,他们当下生活在怀疑和屈辱中,带着内疚和羞愧之情,这是因为过去的意义机制决定了现在的理解”[5]166。 因此,阿尔比在《三个高个女人》的第二幕让过去的和现在的自我同台对质,重新审视第一幕讲述过的故事,帮助理清创伤记忆,进而由自我排斥过渡到自我理解和宽容。第一幕A不断闪回自己的创伤体验,结尾处甚至因为激动而中风“妹妹恨我,妈妈恨我,所有其他人,他们都恨我。他离家出走了。因为我太强了”[3]351。这些未结的心结在第二幕得到舒缓。原来她的强大是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在父权社会下“当女孩不容易”,所以母亲从小教育苛刻要把她们培养成淑女,“晚上要把今天穿的衣服都洗了”,“不要轻易把自己交出去”等等,她必须睁大眼睛找个有钱丈夫,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真爱,抢走妹妹的男朋友——“只有一只眼睛的矮小企鹅”。基于金钱的婚姻必定不幸福,甚至导致儿子离家出走。通过B的讲述得知原来儿子早知道她和马夫偷情的事情并质问母亲,其实她“偷情是为了报复和自怜”。她解雇了马夫保全家庭是为了保持在婆家的尊严和帮扶娘家, B 慢慢开始释怀“好吧,我也不是那么坏,糟糕的时候有,但也有好时光”。就是她骑马摔断背特别无助的时候“一旦你自己倒下了,证明你其实也不比他们强到哪儿去,他们也不会非常恨你了,因为你并不完美”[3]377。 这种回顾让她意识到自己不再强大,卸下自我防御机制时,她的创伤也就慢慢抚平。
3. 重建关系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5]124,如《谁》中乔治夫妇的离间,《海景》中人与自然的疏离,《三》人与自我的排斥。由此创伤主体总是沉溺于过去事件,但真正走出创伤除了整合记忆,还要面对当下,展望未来,这就需要重建关系,这是治愈创伤的最后一步。
《谁》剧中人与家庭关系的重建。乔治和玛莎的角色在故事结尾发生戏剧化转变。当乔治作为游戏的制定者,设定他们假想中的儿子死去,玛莎无法承受幻想的破灭,变得失落和无助,这完全颠覆故事开始那个泼辣专横的妻子形象,反而乔治成了引导玛莎重新面对新生活的精神支柱,“乔治将手放在玛莎肩膀上让玛莎靠着,并轻轻吟唱‘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玛莎哽咽的回答到‘是我,乔治,是我…’”[3]311由此可以看出乔治和玛莎互相安慰扶持,重建关系。
《海景》中人与自然的融合。通过和蜥蜴夫妇的对话,查理夫妇慢慢和自然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该剧的结局更是发人深省。当蜥蜴夫妇进化到可以开始陆地上生活时,发现无法适应已被人类文明践踏的陆地,决定返回海洋,查理夫妇说,“你们将不得不回来…迟早的事…我们会帮你们的”。 蜥蜴夫妇的回答“那好吧。开始帮吧”[3]448让查理夫妇面面相嘘,不知所措,这其实是阿尔比号召现代人进入复原“第三阶段,准备好要更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号召人们重新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创伤经历彻底融入生活中,并采取行动,以增进力量和控制感、保护自己免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5]187。
《三》中人与自我的和解。此剧最后,A谈到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时,不再有悲哀、委屈、愤怒、无助等消极情绪,而是认为“走到人生的尽头才是最幸福的时刻,这时所有的悲哀已经被巨浪平息了……现在我可以走到一边儿,冷静地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自己”[3]383。无论她经历了什么创伤,她最终能够和自我和解,这表明她最后能够释怀,平静的看待所有经历过的创伤,从而获得解脱。“当她与自我再联结时,她感到更加镇定、更有把握来沉着地面对她的人生”[5]193。这和第一幕结尾A讲到自己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无法释怀而中风的状态不同,她已经找到自我和解之路。
三部戏剧的结尾主人公都已整合并结束对过去创伤的回忆与哀悼,开始面对当下展望未来,到这一阶段他们“已经准备好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世界了。”如乔治和玛莎不再诋毁和谩骂,而是互相安慰和扶持;查理和南希也卸下心理防御和猜疑,共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A也已释怀,平静的接受生命的终结。
三、总结
阿尔比戏剧的之所以获奖无数,是因为表现了现代人共同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创伤,获得读者的共鸣。他的戏剧通过显性情节展现人在理性、功利和物欲的现代社会下遭受的精神创伤,如《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中家庭关系的紧张、《海景》中人与自然的疏离、《三个高个子女人》中对自我的排斥等;同时剧本也通过隐形进程叙事为人物和读者提供了一条无形的疗救创伤的方法:他们通过游戏、人兽对话和不同自我对话的隐喻方式获得安全感;通过人物碎片式、非线性的讲述来疏导和重建他们的创伤记忆;通过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自我关系的调整来重建关系,通过这三条途径来治疗现代人的心理创伤。这两条叙事平行贯穿于阿尔比的戏剧中,让读者感受并治愈自己的精神创伤。
[1]申丹. 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5):47-53.
[2]Whitehead, Anne著.创伤小说[M].李敏,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3]Albee, Edward: The Collected Plays of Edward Albee(Volumn 1-3)[M].New York:The Overlook Press,2004.
[4] 薛梦婷,洪琪. 回归自然—文化创伤的复原之路——论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海景》和《山羊》中文化创伤的自然疗法[J]. 英语广场,2017,(4):7-9.
[5]Herman, Judith著.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6]Phil, Jones. Drama as Therapy: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M]. Rou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7.
[7]Adami, Valentina. Trauma Studies and Literature[M]. Frankfurt: Peterlang, 2008.
[8]洪琪.阿尔比戏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的游戏精神[J]. 现代语文,2017,(1):55-57.
责任编辑:陈君丹
On Overt and Covert Parallel Trauma Narrative in Albee’s Dramas
HONG 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China)
American dramatist Albee’s works mostly present us absurd and tragic stories of characters whose traumatic experiences, caused by material-oriented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 modern civilization, are ruthlessly exposed to the audience.However, the main characters gain hopes and understandings for life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ories of Trauma and Narrotology, finds Albee employs overt plot to present modern men’s psychological trauma, withWho’sAfraidofVirginiaWoolf?,SeascapeandTheThreeTallWomenas examples.Meanwhile, he also applies covert progression to provide the characters and readers with a therapy of trauma.These two narratives parallel in his plays to help modern men heal their collective trauma.
Albee; overt plot; covert progression; traumatic narrative
2017-08-28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Q273)
洪 琪(1977-),女, 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J834
A
1674-344X(2017)10-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