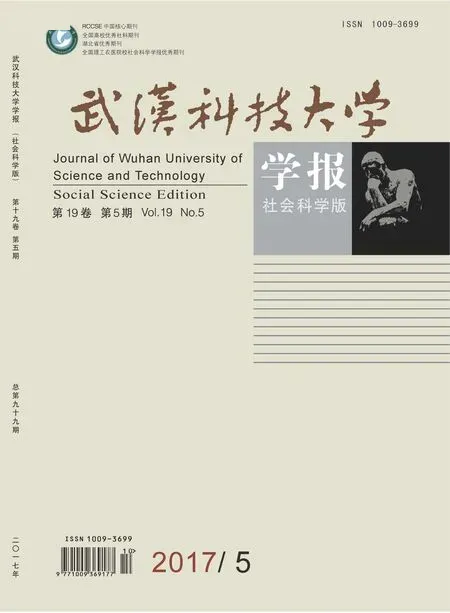当代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证明及其消解
2017-03-09张卫国马洪杰
张卫国 马洪杰
当代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证明及其消解
张卫国 马洪杰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唯物主义在西方哲学中的“当代形态”是物理主义,虽然它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但其心物同一论结论,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各种物理主义理论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即因果论证的逻辑归宿。实际上这一论证的三个前提,物理世界的因果封闭原则、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和非系统的过度决定原则,均是似是而非的命题。挽救意识独特性的方式不是完善物理主义的因果论证,而是实现思维方式的革新,推动物理主义向新唯物主义发展。
唯物主义;本体论;物理主义;因果;因果论证;因果封闭原则;过度决定
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随着脑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哲学自身的发展,作为唯物主义“当代形态”的物理主义,已成功驱逐二元论和唯心主义,逐渐成为当今西方哲学的主流。心脑同一论、功能主义、异常一元论、取消主义和解释主义等物理主义理论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心灵的本质和心身关系的认识。然而,物理主义繁花似锦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始终难以摆脱的本体论困扰,即它的心物同一论的结论,消解了意识的独特性和能动性,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这种尴尬的局面事实上是作为各种物理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即因果论证的逻辑归宿,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论证的各个前提和推导过程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并诊断出物理主义可能存在先天缺陷,从而为新唯物主义的出现指明方向。
一、因果论证
物理主义在心物关系上,坚持所有的心理事物都是物理事物,得出这一结论并非基于独断,而是基于逻辑严密的因果论证(又称过度决定论证)。David Papineau认为因果论证是支持物理主义的权威论证[1]9。Agustín Vicente宣称:“在越来越多的论者看来,支持物理主义的最好的论证,即使不是唯一的论证,就是所谓的‘过度决定论证’。”[2]149蒉益民则进一步主张:“因果辩护策略则是目前物理主义哲学家为意识物理主义化所提供的最有力的论证之一,其他非常有影响力的物理主义‘同一性论证’和‘现象概念论证’都是对因果辩护策略的运用和发展。”[3]111-112因果论证的前提和结论如下:
前提1(物理世界的因果封闭原则):每一个被引起的物理结果都是由在先的物理原因充分地决定的。
前提2(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心理事物有物理结果。
前提3(非系统的过度决定原则):由心理事物引起的物理结果不是被系统性地过度决定的,即物理结果并非总是同时有两个充分的心理原因和物理原因。
结论:心理事物一定同一于物理事物。
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如下:基于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假设心理事物m引起了一个物理结果p。根据物理因果封闭原则,p有一个充分的物理的原因p′。再根据非系统的过度决定原则,p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充分原因,由此可以得出:m同一于p。
David Papineau指出,物理主义的兴起,得益于物理因果封闭原则被普遍接受[1]7。尽管物理因果封闭原则没有出现在物理学的教科书中,但是,物理主义者普遍认为,其得到了来自于物理学的两个方面的支持。
一方面,物理因果封闭原则作为一种指导研究的方法论规范,得到了来自于科学史的归纳辩护。约翰·海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前提是假定了物质世界是一个因果闭合的系统。”[4]23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过去的所有情况似乎已向人们证明,对于任何一个物理事件,要么是由非物理的原因引起的,要么是由物理原因引起的。在前一种情况中,最终的结果是那些所谓的非物理的原因要么实际上是物理的,要么是虚假的,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物理的原因,因而物理学本身是完备的,具有解释所有现象的资源。
另一方面,物理因果封闭原则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得到了(能量)守恒律的演绎支持。从因果关系的守恒量理论看,任何类型的因果关系都是某种守恒量的转移或转化。原因和结果都根据守恒量的变化来定义:“两个事件c和e作为原因和结果关联起来,当且仅当,至少存在某个守恒量P,既受守恒律的支配,又在c和e中例示,且有确定量的P在c和e中传递。”[5]一个对象所具有的一个守恒量的值在t时增大或减小(结果),一定伴随着另一个对象所具有的守恒量的值在t时相应的减小或增大(原因)。如果物理结果是物理守恒量的值的变化,基于守恒律,那么,它的原因一定是物理的,因此物理世界在因果上是封闭的。
无论是二元论者,还是物理主义者,都承认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在绝大多人看来,否认心理事物的因果有效性,坚持副现象论,不仅是反直觉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说副现象论是反直觉的,是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人们的确体验到了思想、愿望和感受的因果有效性。说副现象论是危险的,一方面是由于心灵的存在取决于心理因果有效性,根据爱利亚人“存在就是具有因果力”的原则,如果心理事物没有因果力,就会面临着本体论上的尴尬和被取消的风险,另一方面是由于自主体的道德责任要求心理事物具有因果有效性。如果行动不是由心理活动如慎思和决定产生的,人只不过是自己身体活动的消极旁观者,因而在任何意义上似乎都不需要对身体活动负责。
对于最后一个原则,即非系统的过度决定原则,据说物理原因和心理原因对行为的过度决定关系具有难以理解的“怪异性”。过度决定关系指的是,同一个结果有两个“不同的”而且“充分的”原因。如“两颗子弹”的典型实例,一个受害人的心脏同时被两个互不相干的子弹射中,其中的每一颗都是致其死亡的充分原因。在反事实情形中,只要其中的一个原因出现了,即使其他的原因不出现,结果也不会改变。这是一种偶然的独立的过度决定关系,两个原因彼此独立,同时出现纯属偶然。基于物理主义的“最低限度的承诺”即心物随附性原则,心理事物非对称性地依赖于物理事物,金在权①金在权,英文名Jaegwon Kim.提出了否认心理因果关系是这种过度决定关系的三点理由:一是我们执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被过度决定的,都有两个不同的充分原因,这种看法极度怪异[6]247;二是在用一个物理原因取代任何一个既定的心理原因时,很明显使得心理原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必要的;三是这个方法和物理因果封闭原则是相矛盾的[7]56。
因果论证的三个前提似乎是无可质疑的真理,但是,从它们推导出来的结论,心理事物等同于物理事物,无疑褫夺了人是万物之灵的神圣地位,将人当作“惰性物质”,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丝毫空间。这一结论与人的常识观念严重不符,让人难以接受,因此,要推翻这一结论,维护人的尊严,必须从其前提和论证过程入手,重新审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事实上,这一论证的三个前提都是似是而非的命题。
二、物理域的因果开放性
科学史中的归纳记录指向的似乎是物理主义,但是许多生物学家以及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家,都不太情愿以对物理主义友好的方式来解释科学史。在他们看来,即使所有过程的基础是物理过程,在物理事物的组织中,依赖会突显出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新因果力”。
斯图亚特·考夫曼主张,物理学和化学本身不能解释生命过程,是因为分子在构成生命体和不构成生命体时有不同的行为表现,“生命,从根本上讲,存在于多种分子集合起来时那种催化闭合的品性。孤立时,任何种类的分子都是死的。合起来,一旦达成催化闭合,那个集体的分子系统就是活的”[8]61-62。在生命整体与分子部分的关系上,不是部分解释整体,而是整体解释部分,关于整体的知识能解释部分的行为。Charbel El-Hani等将这种理论直觉发展成为对下向因果关系的辩护,他们宣称,分子在构成生命体时行为会受到生命体的限制,“对分子关系的限制,源于它们是细胞结构和过程的时空形式或模式的一部分”[9]。下向因果关系实际上是因果关系的“篮球队模型”,在篮球队中,虽然运动员是球队行为的有效原因,但是忽视球员所效力的球队,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球队“选择性地激活”球员的因果力,球队是自我保存和自我组织的实在,能够限制和部分地解释其球员的行为。下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意味着,物理结果在因果上不是或不只是由在先的物理原因决定,还受到高层次原因的影响,这是对物理因果封闭原则的直接否定。
守恒律本身无法从逻辑上排除非物理的守恒量的存在。反物理主义者据此设想,非物理的特异能(如活力能或心理能)充当了物理能之间的转移或转化的中介。假设能量是全局守恒的,再假设在整个宇宙中,物理能和特异能之和是守恒的也是一条定律,即物理能每一次向特异能的局部转化,随后都有特异能向物理能相反的转化。事实可能是,神经元放电导致了大脑的特异能增大,此后,人的特异属性放电,释放特异能,引起手臂上举,这就意味着,特异能充当了物理能之间转移的桥梁,它的存在不会违反能量守恒定律。David Papineau承认非物理守恒量是物理因果封闭原则的守恒律证明的关键,但是,他从经验上否认了非物理守恒量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迄今为止未发现非物理能量存在的证据,另一方面是由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在解释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然而,“关于某个事物存在的证据的缺乏并不能表明该事物不存在……鉴于还存在大量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否认非物理能量的存在”[10]5。
Wibur Dyre Hart甚至以能量守恒律为其二元论辩护。离体的心灵本身没有能量,但它与外物发生关系时,由于外物作用于感官时必定有能量的消耗和转化,基于能量守恒原理,这些损失和转化的能量就会进到信念和愿望之内,从而使它们有能量。例如在视觉中,光线能量就会转化为信念能量,Wibur Dyre Hart认为:“这些信念之确定的量值有可能完全来自于光能。”[11]171虽然没有身体的心灵不能直接移动物体,但由于它通过知觉吸收了能量,基于能量守恒,借助能量转换可以让肢体去完成它移动物体的指令[11]173-174。
物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世界最基本的方面。物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意外惊奇,因此物理学不能对它能够研究的现象类型作出先天的限制。在Barbara Montero看来,如果有很好的证据证明世界的最基本方面包含了心理属性,如在量子力学中,根据维格纳假说,意识导致了波函数的坍缩,那么,物理主义者应当试图弄明白这些心理属性是如何运作的,将来的或最终的物理学在本体论上是一种物理主义二元论。他认为:“如果我们以物理学来定义物理事物,只要这种物理学包含了作为世界基本特征的心理事物,物理主义论题就不必与二元论相冲突,因为即使物理学可以解释心理事物,二元论也可能是正确的。”[12]179也就是说,即使物理学是完备的,在因果上也可能是开放的。
三、“物理”概念混淆与双重待解释项
虽然人们普遍坚持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但质疑因果论证对这一原则的阐述:一是因果论证的两个前提中的“物理”概念不能保持概念的同一性;二是心理事物引起的结果是行动,与纯物理的身体运动不同。
根据Scott Sturgeon的分析,“物理”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的是微观物理即量子物理,后者是微观物理和宏观物理的统称。如果第一个前提和第二个前提中的“物理”一词指的是量子物理,那么,第一个前提就变为“所有的量子物理结果都是由在先的量子物理原因充分地决定的”,这一原则可以由量子物理学确保,而第二个前提则变为“心理事物有量子物理结果”,这一论断既不从属于当前的科学,又不从属于日常经验,没有任何科学理论也没有任何常识假设了心理事物与量子事物之间存在普遍的因果关联。由此可以得出,将两个前提中的“物理”一词都理解为“量子物理”,则第一前提是正确的,第二个前提是错误的。
如果将前两个前提中的“物理”一词理解为“量子物理和宏观物理的统称”,据此,握手和量子事件一样都是物理事物,那么,日常经验和宏观物理科学都表明了心理事物有宏观物理结果。由此可知,“物理”一词若涵盖了宏观物理结果,那么心理因果性可由宏观印象保证,但是,第一个前提则变为“所有的广义物理结果都是由在先的广义物理原因充分地决定的”,这一论断不属于当前的科学,也不属于日常经验,任何科学理论和常识都没有做过如此论断,相反,宏观科学和日常经验依赖广义的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
在因果论证中,存在一个二难问题,如果“物理”指的是量子物理,因果封闭原则似乎可得到科学支持,但因果有效性原则似乎既没有科学支持又没有日常经验支持。如果“物理”意指广义物理,因果有效性原则似乎可以得到科学和日常经验支持,但因果封闭原则得不到任何支持[13]。
物理主义对心理因果有效性原则的理解,在行动哲学看来,犯了范畴错误:心理现象所产生的结果,不是作为纯物理事件的身体运动,而是人的行动。行动不同于身体运动是行动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从模态逻辑的角度讲,行动如果同一于身体运动,就“必然地”同一于身体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假设“a”表示一名医生在t时在手术室对病人实施抢救行动,“m”表示他的身体在t时处于如此这般的运动。如果a=m,那么,基于同一的必然性要求,a必然同一于m。但是,如下两种情况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第一种情况是,即使这名医生的身体在t时没有如此这般的运动,他当时也可能是在救人,也就是说,即使m不存在,a也有可能存在,例如,他救人的实现方式有多种,既可以左手拿刀右手拿钳(m),又可左手拿钳右手拿刀(m′);第二种情况是,即使这名医生采取的行动不是救人,他的身体也可能如此这般的运动,即m没有出现,a也可能存在,例如,这名医生在实施拯救的过程中,发现病人是其多年未见的杀父仇人,最终抢救失败,他是公报私仇,还是救治无效,取决于他当时的动机。既然上述两种情况在逻辑上是有可能出现的,行动就不是必然地同一于身体运动。
行动与身体运动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这一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给予了方法论指导,他认为:“让我们不要忘记下面这一点:当‘我举起我的手臂’时,是我的手臂往上去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我举起我的手臂这一事实中抽掉我的手臂往上去了这一事实,那留下的是什么呢?”[14]行动哲学对这一问题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回答:一是吉内特的内在主义观,行动就是“有行动倾向的现象性质”的心理事件,行动与身体运动有经验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与行动是否被引起以及如何被引起无关;二是密尔和塞尔的组合观,行动是由心理事件或状态(如意图)与相关的身体运动(如手臂举起)组合而成;三是德雷斯基和奥康纳的过程观,行动就是一些适当的心理事件或行动者导致适当的身体运动的因果过程;四是戴维森的因果观,行动与身体运动不同在于两者被引起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由信念和愿望构成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引起的[15]。
总而言之,行动与意向或动机等心理属性相关,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日常认为心理事物与物理事物不同的地方。如果物理主义者将行动个体化中的心理因素直接忽视掉,无视心理学所要解释的对象不同于物理学所要解释的对象,而将行动同一于身体运动,那么,他们就无需第一个前提和第三个前提,可直接推导出心理事物同一于物理事物。
四、心理因果过度决定论
物理主义反对心理过度决定关系的理由,根据金在权的分析,有三点:心理因果过度决定关系是怪异的、物理原因可以取代心理原因以及违反物理因果封闭原则[7],但是,其中的每一条理由都不充分。
过度决定关系有不同的类型,我们需要审慎地分析。根据过度决定的诸原因之间是否存在依赖关系以及二者的同时出现是否具有规律性,可将过度决定关系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1)偶然的、独立的过度决定关系:两个原因彼此独立,且同时出现纯属偶然。根据金在权的理解,这种过度决定关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两个原因在本体论上是相互独立的,“过度决定关系的一般观念包含两个及以上的独立的因果链,它们在同一个结果处交汇”[16];二是两个原因的同时出现在认识论上是偶然的、非系统的。
(2)系统的、独立的过度决定关系:两个原因相互独立,但同时出现有规律可循,如工程学中的“双保险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它们同时独立地发挥保护作用,即使其中的一个保险机制失效,另一个也能发挥保护作用。在生物学中,高等生物的器官很多都是双份的,它们同时发挥相同的功能,亦是一种“双保险”。
(3)系统的、依赖的过度决定关系:其中的一个原因依赖于另一个原因,因而同时出现是系统性的。根据依赖的种类不同,它又可分为两个子类:一是宏观/微观过度决定关系,二是迭代因果过度决定关系[17]。
在宏观/微观过度决定关系中,宏观事物由微观事物实现,在本体论上依赖于而又不同于微观事物,因而宏观事物作为原因存在时,一定存在着作为其基础的微观物理原因,但是宏观因果模式如心理因果模式在层次上要高于微观物理因果模式,此二者诸要素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不是同构的,不能将前者还原为后者,此外,高层次因果模式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对其构成要素具有下向反制作用。例如,以鸟群分布式行为的计算机模拟为例,要想出现群体模拟的结果,鸟群中的个体必须遵守三条简单的规则:一是避免与附近同伴碰撞,二是努力与附近同伴的速度相匹配,三是向附近同伴靠齐[18]。
在迭代因果过度决定关系中,一个原因在概念上或定义上依赖于另一个原因。如确定项(determinate)与可确定项(determinable)、析取或合取属性/析取支或合取支关系、一阶属性和二阶属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深红色是因果相关属性,则红色也是因果相关的。假设一只鸽子经过训练之后见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将其啄出来,对于红色之外的所有颜色,则会视而不见。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出现在这只鸽子面前,鸽子将其啄了出来,红色与其啄的行为在因果上是相关的,然而这个三角形所具有的颜色是特定的深红色。再假设这种深红色在因果上对于鸽子啄的行为是充分的,那么,红色也是一样。因此,Stephen Yablo宣称心物原因都是行动的充分原因,他说“确定物不会与它们的可确定物竞争因果影响”,相反,它们“容许并的确支持它们的可确定项的因果诉求”[19]。
如果心物之间正如金在权所说的那样存在随附性关系,心理事物在本体论上非对称性地依赖于物理事物,心理事物的出现一定以物理事物的出现为前提,因而心理因果关系必然不属于偶然的、独立的过度决定关系。但是,金在权在没有考察其他可能的过度决定关系的前提下,宣称心理因果关系不是过度决定关系,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金在权反对心物过度决定关系的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物理原因不能替代心理原因。金在权的理解是,“我们的心理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总的说来依赖于或决定于发生在身体过程上的事情”[20]14。“心理属性强随附于物理/生物属性,也就是,如果任何系统s在t时例示了一个心理属性M,必然地存在一个物理属性P,使得s在t时例示P,且必然地在任何时间例示P的任何事物在那时也将例示M”[20]33。金在权对心身关系所做的强随附性解释暗含了一个结论,即个人的生物学属性“(至少)在法则学上充分地决定”他的心理属性[20]41。金在权在心理事件个体化的问题上,坚持的是一种彻头的内在主义,即心理事件局域地随附于构成它的身体事件。根据外在主义者如普特南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和柏奇的“关节炎思想实验”,同一个物理事件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构成不同的心理事件。心理事件全局地随附于身体事件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心理原因至少不能被金在权所说的物理原因所取代。
即使物理因果封闭原则是对的,心理因果过度决定关系的存在也不一定违反这一原则。Thomas M.Crisp等假设,在可能世界W中也存在随附性,由于W世界中的规律与现实世界中的规律不同,因此M在W世界中有一个不同于P的物理基础P′。根据金在权的论证,如果P′是M的一个随附物理基础,而M引起了P*,那么P′对于P*在因果上同样是充分的。因此,Thomas M.Crisp等认为:“如果随附性存在于 W世界中,那么,P*在W世界中的确有一个物理原因,封闭性因而在W世界中并没有失效。”[21]Barbara Montero也有相似的言论:“假设强随附性在所有在法则学上可能的世界中都有效,那么,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中,具有M的任何事物同样也具有一个(不是P的)物理属性作为M的随附性基础,并且这个物理属性对于P*而言,至少的确具有和M一样的有效性。我们因此没有违背封闭性原则。”[22]
从物理主义存在的逻辑论证来看,物理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先验地构想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关于事物或因果的形而上学图景,然后再思考如何将事物纳入到这个宏大图景之中。这就导致了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物理主义坚持理论优于实践:理论是真理知识的唯一来源,从实践中获得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知识,同样也需要科学理论的证实,否则,就应坚持取消主义并抛弃。物理主义的固有缺陷是“对对象、现实和感性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物理主义虽然在西方被视作是唯物主义的“当代形式”,但仍然没有超过马克思所说的“旧唯物主义”范畴,仍坚持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未来形态的唯物主义应是以实践为出发点,来理解整个世界,尤其是意识。人的意识是从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进化而来,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物理主义缺乏这种历史的维度,遗忘了正是由于主体的活动创生了人的意识,意识是人的能力,更是人的作品。因此,对意识的理解,不仅要从客体方面去理解,更要从第一人称视角和主体方面去理解,从实践生成论方面去理解。
[1] Papineau D.The rise of physicalism[M]//Gillett C,Loewer B.Physic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 Vicente A.On the causal completeness of physics[J].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6,20(2):149-171.
[3] 蒉益民.物理世界的因果封闭性、心灵因果性以及物理主义[J].世界哲学,2014(6):111-119.
[4] 约翰·海尔.当代心灵哲学导论[M].高新民,殷筱,徐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3.
[5] Kistler M.Causation and laws of nature[M].London:Routledge,2006:26.
[6] Kim J.Supervenience and mind: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247.
[7] 金在权.物理世界中的心灵:论心身问题与心理因果性[M].刘明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 斯图亚特·考夫曼.宇宙为家[M].李绍明,徐彬,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9]El-Hani C N,Emmeche C.On some theoretical grounds for an organism-centered biology:property emergence,supervenience,and downward causation[J].Theory in Biosciences,2000,119(3-4):234-275.
[10]陶焘.物理因果闭合性与能量守恒定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6):3-8.
[11]Hart W D.The engines of the soul[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2]Montero B.Varieties of causal closure[C]//Walter S,Heckmann H.Physicalism and mental causation:the metaphysics of mind and action.Virginia Imprint Academic,2003:179.
[13]Sturgeon S.Physicalism and overdetermination[J].Mind,1998,107(426):411.
[1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44.
[15]柯克·路德维希.唐纳德·戴维森[M].郭世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63.
[16]Kim J.Blocking causal drainage and other maintenance chores with mental causation[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3,67(1):151-176.
[17]Funkhouser E.Three varieties of causal overdetermination[J].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2,83(4):335-351.
[18]Reynolds C W.Flocks,herds,and schools:a distributed behavioral model[J].Computer Graphics,1987,21(4):25-34.
[19]Yablo S.Mental causation[M]//Chalmers D J.Philosophy of mind: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81.
[20]Kim J.Physicalism,or something near enough[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1]Crisp T M,Warfield T A.Kim’s master argument[J].Noûs,2001,35(2):304-316.
[22]Raymoimt P.Kim on overdetermination,exclusion and nonreductive physicalism[M]//Walter S,Heckmann H.Physicalism and mental causation:the metaphysics of mind and action.Virginia:Imprint Academic,2003:228.
[责任编辑 周 莉]
B02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5.011
2017-06-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4CZX039).
张卫国,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心灵与行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