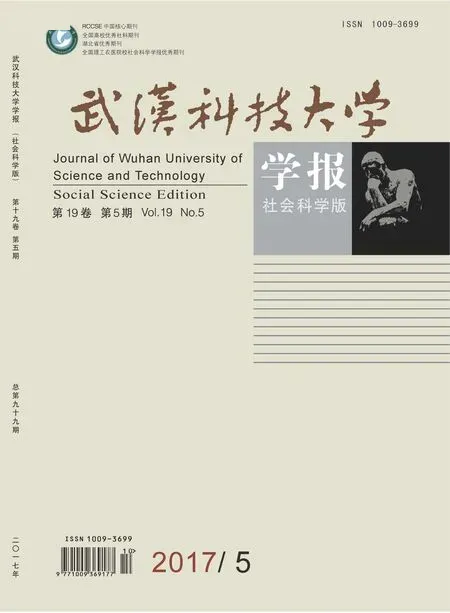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探析
2017-03-09王前
王 前
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探析
王 前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116024)
机体哲学研究在中国和西方曾沿着不同的思想轨迹发展,各有其不同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法。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视域中审视机体哲学的思想成果和发展趋势,通过相互比照,可以形成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新的机体哲学观念体系,为解释具备机体特征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启新思路、提供新对策。在中西文化交融视域中开展机体哲学研究,有助于中国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发挥应有的作用。
生机;机体;机体哲学;视域;诠释
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是从哲学角度研究各种机体的存在、演化和相互关系的哲学分支。在哲学史上,明确以“机体哲学”为标识的研究,主要是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开始的,但其思想萌芽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机体哲学在中国和西方曾沿着不同的思想轨迹发展,各有其不同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法。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视域中开展机体哲学研究的时机逐渐成熟。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的机体哲学研究思想成果进行比照,可以构建一种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新的机体哲学观念体系,这种机体哲学观念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将呈现特有的意义和价值。
一、中西机体哲学的比照与逻辑起点的新选择
西方机体哲学学派较多,它们曾经选择机体的不同特性作为逻辑起点,建构相应的观念体系。
古希腊和中世纪许多学者从目的论出发,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具有神学色彩的目的论,认为目的和终极的原因是世界真实的原因,宇宙作为理念的体系构成了“有机的精神统一体”[1]66。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因是事物的内在属性,“自然就是目的或‘为了什么’”[2]。到了中世纪,神学目的论取代了自然目的论,认为上帝在宇宙之内,存在着一种创造力使其按照自己的目的与计划去发展[3]。以“目的”为逻辑起点的早期机体哲学后来未能产生进一步影响。
莱布尼茨(G W Leibniz)以“单子”为逻辑起点展开其机体哲学体系,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单子组成的,这种单子是无因自成而不毁灭的基本部分,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1]460。作为有活力的实体,单子具有能动性,单子还具有透视性与秩序性。“一个生物或动物的形体永远是有机的,因为每一个单子既是一面以各自的方式反映宇宙的镜子,而宇宙又是被规范在一种完满的秩序中”[4]。以“单子”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比较适合说明生命现象和社会现象,但“单子”的存在缺乏实证根据,很难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效果。
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机体哲学以时间的“绵延”为逻辑起点,他认为“绵延”是生命的本质,生命作为一种本原的冲动力,是一股连续而不可分割的流,是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最深刻根源[5]。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机体哲学以“过程”为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机体都是创生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单个机体力量微薄无法直接创生自己的环境,而相互摄持、彼此“聚结”的有机体群体能够在创生过程中承前启后、聚合“共生”,从而达到机体与环境的平衡[6]。怀特海的机体哲学具有将“机体”泛化的倾向,认为“只要是有一定规律的有序结构体都是有机体”[7],这种机体哲学将近代科学中一度被忽略但在机体研究中凸显出来的“关系”“过程”“生成”等范畴视为机体的本质特征,但却取消了机体与非机体事物的界限。
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的机体哲学将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由普遍物质单元(粒子)在其结构(有机体)中通过新陈代谢作用所构成的聚集形式,并不需要其他的特殊实体,作为结构性存在的有机体是新陈代谢的功能产物[8]。美国哲学家阿尔奇·J·巴姆(Archie J.Bahm)的机体哲学将“互依”作为逻辑起点,“互依”意味着任何部分的变化将实在地引起整体的变化,而整体的任何变化也会影响其中的部分[9]。他的机体哲学以极性理论为核心,所谓极性,指的是由对立、互补和张力这三个普遍性范畴构成的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
与西方的机体哲学学派不同,中国现代哲学家受古代哲学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观念的影响,将“生命”概念作为逻辑起点。如梁漱溟提出与“绵延”类似的“相续”概念,认为“一切生物的生命原是生生不息,一个当下接续一个当下的”[10]。熊十力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发展趋势和属性就是宇宙的大生命,宇宙大生命与个体本心是一种“互既”的关系,人与宇宙大用为一体[11]。方东美认为天地之间“普遍的生命”具有育种成性、开物成务、创进不息、变化通几、绵延不朽等五种含义,有一个理性的力量支配着生命活动始于创生、止于至善[12]。
总的看来,已有的中西各种机体哲学学派的逻辑起点,或是选择生命有机体的某些本质特征,如“目的”“单子”“生命”,进而用来说明天地万物;或是选择生命有机体和无生命事物共有的某些本质特征,如“绵延”“过程”“互依”,进而将一切事物视为机体。然而,从这些逻辑起点出发,还未能充分阐释机体与非机体的本质区别,也未能充分阐释生命有机体之外的具有机体特征的其他人工物、社会组织和精神体系。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选择机体哲学研究的一种新的逻辑起点,建构相应的观念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种新的逻辑起点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范畴——“生机”,它是“生”与“机”的结合,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vitality”(意指生命力、活力),但中文的“生机”中蕴含着对机体本质特征的一种深刻理解,这是“vitality”一词中没有的。具体说来,“生”的象形字表示在土壤中长出幼苗,寓意能带来新事物、新形态的自然发展态势,生命、生活、生气勃勃等词汇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机”的繁体字是“機”,来源于“幾”,“幾”的意思为“微也,殆也”,它由两个“幺”字和一个“戍”字合成,“幺”的本意是幼小儿童,“戍”的本意是“兵守”,用两个小孩子把守城门显然很危险,这种预示危险的征兆称为“幾”,引申为各种事物变化的萌芽[13]84。对“幾”的探究可以见微而知著,及时防范风险,所以《易传·系辞上》说:“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幾”加上“木”字偏旁,就成了“機”,其最初含义是弩箭上的机关,即“弩牙”[13]123。现代枪炮上的扳机和发射导弹的按钮依据的是同样的原理,“機”(下面仍用简化字“机”)意味着对器械运动过程和结果的控制,而且以很小的投入取得显著收益,这里体现了“幾”的价值,即抓住事物苗头就能控制事物的发展。时机、商机、战机、机会、机缘、机器、机巧等词汇,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由此说来,作为“生”与“机”的结合,“生机”这个范畴应该指能够以很小投入取得显著收益的生长壮大态势。不过,“生机”这种含义需要通过词源学意义上的考察才能够发现,而这种含义揭示了机体的一种隐蔽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机体活动要体现“机”的存在。下面对这种特征做一些具体讨论。
“机体”的最初含义指所有具备生命特征的物体,而生命特征在于能够新陈代谢、适应外界变化、不断生长和繁殖。高等生物还具有一些更复杂的生命特征,特别是人类具有思维、语言、目的性、精神需求等。然而,所有这些理解都与“生”相关,还没有显露其中“机”的存在。可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生命活动没有“机”的特征,或者说没有体现出“生机”,还能够存续和发展吗?生长就是由萌芽开始不断衍生出新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过程,生产就是由较少投入产生显著效益的过程,生活就是由眼前的努力奔向更有希望的未来的过程。当人们说某一事物蕴含“生机”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事物在生长、生产、生活等过程中,由初期相对微小的状态,有希望不断发展自身,将来取得显著收益,这里包含着发展的目的指向和价值的增长。由“生机”的萌芽到其最终结果的变化,正是“生机”的展开或运行,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不断参与进来,使得事物的质和量都在不断变化,其复杂性程度不断提升,其影响不断扩大。从现代系统科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类复杂适应系统,通过系统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耦合作用,使得一个很小的输入会产生巨大的、可预期的直接变化[14],这就是机体的本质特征。所谓“有机联系”,关键在于有“生机”,即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生机”的存在和作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不仅仅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无机事物中也存在),而且还指这些事物同处于某种“生机”的展开链条或网络之中,能够传递“生机”的功能,带来事物的生长或发展,因而才具有活力。这实际上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用“生机”来解释“机体”或“有机联系”,能够充分阐释机体与非机体的本质区别。不少西方机体哲学流派之所以出现把一切事物都视为机体的“泛机体”倾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机体哲学流派的逻辑起点其实却是机体与非机体事物共有的本质特征,只不过这些特征在西方古代自然哲学中尚未得到透彻研究,或者在近代机械论世界观影响下被遮蔽,但在对机体的专门研究中被凸显出来,无论“目的”“单子”“生命”,还是“绵延”“过程”“互依”,都是如此。而具有“生机”却是只属于机体而不属于非机体事物的本质特征。已经死亡的生物体尽管还是有机物,却已经没有“生机”了,所以就不应该再属于机体范畴,这也显示出从“生机”角度划分机体与非机体事物的必要性。用“生机”来解释“机体”或“有机联系”,可以开启对机体的存在和演化、对机体的认知途径、对机体的分析和评价等方面问题的新的研究思路,开展相应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研究。
用“生机”来解释“机体”或“有机联系”,还有另一方面意义,就是充分阐释生命机体之外的具有机体特征的其他人工物、社会组织和精神体系。人类通过实践特别是创造性活动,能够将生命和人类的特征赋予自然事物(可称为“人工机体”),或者赋予社会事物(可称为“社会机体”),或者赋予精神事物(可称为“精神机体”),这些类型的“机体”所蕴含的机体特征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已往的各种机体哲学学派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关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诠释来加以讨论。
二、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诠释
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能够对涉及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给出新的诠释,获得具有启发意义的认识成果。
“人工机体”是人类将自身的生理和社会特性赋予各种自然物的结果。仿生的工具、机器、生活器物都可以视为“人工机体”,它们区别于纯粹的自然物,是因为它们具有“生机”的属性和功能。并非所有人工物都可以视为“人工机体”,彻底报废的工具和机器、工业废料、生活垃圾等等,尽管是人工物,但已经不会参与“生机”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就不再是人工机体了(废物重新利用的情况除外)。工具和机器这类人工机体看上去可能最不像机体,人们看待它们时首先想到的是其物理和化学性质,较少关注人类自身机体特征对工具、机器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实际上,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工具和机器已经被人类以各种方式赋予机体特征,如19世纪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Ernst Kapp)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投影”,马克思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延长”,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盖伦(Arnold Gehlen)认为工具是人类的“器官补偿”和“器官强化”[15]。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智能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机器似乎越来越具有“人”形,“机器”与“机体”的传统鸿沟正在缩小。人体和人类社会生活中嵌入更多的机器成分,而机器中嵌入更多的机体特征特别是人工智能成分。机器的机体特征在机器运转的时候会显现出来,有时一个零件的损毁就可能导致整个机器的报废,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就是O型密封圈失灵造成的[16],这种机制和人类生命机体的病因有很多类似之处。我们还应看到,人工机体是有“寿命”的,即有从产生、使用到老化、报废的历程。无机的自然事物就谈不上“寿命”,废弃的人工物也不再有“寿命”。很多人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往往忽略人工机体的“寿命”问题,不能及时更换即将报废的机器零件,不能及时拆除超过了安全使用期的“危房”,不能及时维修老化的管道和线路,由此造成机器损毁、建筑物倒塌、管道爆裂等恶性事故。
“社会机体”是人类将自身生理机体特征通过实践赋予社会组织结构的结果,包括家庭、社团、政党、国家、企业、学校等等。那些没有组织机构的人群,如商店里流动不息的顾客人群以至某些时候的“乌合之众”都不能说是“社会机体”。人类产生之后,其生命机体上的进化并不明显,但人类社会中各种社会机体的进化特征非常明显。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过“社会机体”概念,主要是将社会组织的特性同生命机体相类比,但对社会机体自身特有的机体特性还缺乏深入讨论。不同领域中社会机体的“生机”有着不同表现形态,在经济活动中,“商机”和“资本运作”是等价物,它们具有相同的属性,即以较小投入获得较大产出。在战争中,抓住了“战机”就能以较小的人员和装备代价消灭较多的敌人,而错失战机就会导致身处险境。在政治领域,处理国内外事务、制定政策、调整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抓住时机,利用好发展机遇,以较小代价获得政治上的显著收益。从个人的发展和人际关系角度看,“机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在教育、职业、婚姻、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要不断选择和捕捉机会,关键时刻的每一步选择都可能对后来的生涯产生深远影响。人们之所以要树立人生的目标,朝着希望的目标努力,使生活过得有意义,都是在致力于追求“生机”的展现。
社会机体的“生机”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按照一定规则运行的社会机体会相应地体现其特定功能。但社会机体的生机和活力也同社会机体成员的状态以及机体各部分之间关系密切相关。在社会机体演化过程中,有些事物特征是明晰的,但可能受隐蔽的社会因素的潜在制约;有些事物特征看起来很少变化,但长时间就会显现其不同侧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机体之间关系日益复杂化。人类社会发展在达到某些边界条件(如资源和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之后,出现结构重新调整,用传统的机体哲学理论难以解释,这就需要重新思考社会机体的新特征及其与其他类型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精神机体”是人类将自身生命机体特征通过实践赋予精神事物的结果,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各种知识体系、心理结构、语言系统、游戏规则等等,微观层面则指由个人的精神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个人在认同和信仰某种宏观层面的精神机体的同时,也会根据这种精神机体的整体目标、价值标准和行动准则来衡量、激励或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就使得个人的精神追求可能同生命机体的本能要求不完全一致,人们为了崇高的精神目标和伦理准则,可能约束自己的生理本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宏观层面,精神机体中的“生机”体现为“思维经济”,即不断追求抽象的、一般性的原理,由此推导出所有可能的推论,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少数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使得众多学生获得思想、品行和能力的进步。少数科学家和发明家将其获得的知识成果贡献给全人类,同样体现了“生机”的作用。在微观层面,精神机体中的“生机”表现为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对丰富和拓展个人精神世界的作用,以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习效果。人们在日常的思维活动中很难意识到自身精神机体的存在,但可以意识到头脑中的各种思想成分是连成一体的,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是不同的,自己的精神世界与他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同的。人们也会感受到精神机体需要动力,需要来自外界的激励,这都是对精神机体存在的间接体验。
人们对自身精神机体的体验,与三个关键词相联系。其一是“自我”。“自我”不是指“我”的肉体,而是指“我”的自主(“我”能决定自己的行动)、自立(“我”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自觉(“我”能知晓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这些都是精神机体的功能。个人的精神机体有自身的边界,并且能在整体上进行归纳、权衡、判别,融贯起来进行思考。其二是“灵魂”。人们会意识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不同于生命机体的东西,同思想、品行、气质相联系。“灵魂”有生机和活力,这同精神机体的特征相吻合。其三是“精神”,它具有自己的世界,能够活动和变化。精神机体是以人的生命机体为载体的,但不能还原为生命机体,不过这种特性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只有当两者可能发生冲突时,人们才可能意识到它们的区别的存在。比如,抑郁症患者在生命机体层面可能无异常,但精神机体层面却出现严重障碍。有些人在受到强烈的外界精神刺激和思想压力之后,尽管生命机体完全正常,也可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梅洛·庞蒂对“幻肢”的讨论,也属于此类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社团、机构都包含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不同成分,任何个人都具有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不同特点。各种类型机体的不同耦合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个性。当这些组织和个人之间出现竞争和协同关系时,其发展趋势和结果会受到各种类型机体耦合方式的深刻影响。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涉及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待深入展开。
三、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一条可能路径
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展示了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一条可能路径。中国哲学需要走向世界,需要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体现其现代价值,这一点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即讨论中国哲学史上各种思想范畴的历史意义及其对现代的启发。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学者往往用西方哲学已经定型的研究范式解读中国哲学史,这样很难发现什么新东西。而不少中国学者也在按照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解读中国哲学史,力图将古代的思想资源同现代的社会需求相联系,但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西方哲学研究范式注重逻辑分析和思辨,而中国哲学史上的思想范畴基本上是直观体验的产物,研究手段和对象之间没有很好地匹配。现代的中国哲学应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立足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形成独特的视角和思想方法,进而对世界哲学发展有所贡献,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比较薄弱[18]。要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必须增强中国哲学研究成果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开启新思路,提供新对策。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这种需要。
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中国哲学特色。这不仅是由于“生机”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机体哲学研究的丰富思想资源。各类机体都不能完全依靠逻辑分析的方法透彻地加以研究,而是需要发挥直观体验或者说直觉的作用。在注重逻辑分析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直觉的作用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直觉思维的“黑箱”一直没有完全打开。中国传统哲学在直观体验的研究方面比较深入,有一些范畴在揭示直观体验的过程和规律性方面非常重要,但在西方哲学框架里找不到完全合适的对应物,如作为思维器官的“心”,作为“心”的认知对象的“象”,以及“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等。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上可以充分吸收中国哲学这方面的思想资源。
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还具有世界哲学研究视角下的普遍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受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人们在对各种类型的机体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割裂机体内部和外部很多有机联系,因而难以获得对机体整体性质的全面理解。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注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强调明晰性、确定性、严格性,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各种机体,会造成对达不到这种标准的众多研究成果的排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近现代西方各种机体哲学流派,以及为了弥补单纯的逻辑思维缺陷而出现的解释学、现象学、实践哲学等哲学思潮,都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这些研究尚未能全面阐释机体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认识机体特性方面,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努力和海德格尔“解蔽”的工作是很有启发性的,但其表现方式较为晦涩复杂,很难成为民众普遍了解和使用的思想工具。近年来,知觉现象学和涉身认知领域的研究,已经将研究焦点日益集中在“身体”的认知功能方面[19],这种理论背景凸显了深入开展机体哲学研究的必要性,而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
就现实意义而言,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能够为解读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近年来,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去解释和预测一些涉及社会机体的现象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以此为基础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和政治方略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一些似乎不该发生的事件反而频频出现。这种状况预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展机体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现在有些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如环境污染、教育功利化、“问题青少年”增多、就业困难等等,除了制度建设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心理不稳定等因素外,对新时期社会机体特性认识的薄弱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社会管理措施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加,力度不断加大,但收效并不明显,其思想根源往往在于忽视了管理的对象是各种类型的机体,这种状况在教育、城市治理、危机防范等方面尤为突出。机体哲学研究应该提供思考现实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及时发现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避免急功近利和盲动倾向。如果用隐喻的方式,可以说很多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根源,在于将本来是“活”的事情看得很“死”,处理的方式很生硬;而机体哲学的意义在于能够让看似很“死”的事情“活”起来,正确利用其生机和活力,使人类社会生活变得更和谐、更美好。
总之,以“生机”为逻辑起点的机体哲学研究,希望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能够更清楚地解释涉及各种类型机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视域中开展这方面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有机联系,而且有助于中国哲学和文化走向世界,在处理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 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M].伍德增补,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6.
[3] 李东.目的论的三个层次[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1):20-25.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88.
[5]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8-139.
[6] 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8-109.
[7] 陈奎德.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02.
[8] Hans Jonas.Mortality and morality:a search for the good after Auschwitz[M].Chicago: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60-65.
[9] 阿尔奇·J· 巴姆.有机哲学与世界哲学[M].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4.
[10]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
[11]陈来.熊十力哲学的明心论[J].孔子研究,1992(3):81-90.
[12]李春娟.方东美生命哲学阐释[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30-35.
[1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周晓牧,韩晖,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5.
[15]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16]查尔斯·E·哈里斯,迈克尔·S·普里查德,迈克尔·J·雷宾斯.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M].丛杭青,沈琪,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2.
[17]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9-120.
[18]刘毅青.如何构建中国的理论——西方汉学家的思考与启示[J].哲学研究,2014(11):118-125.
[19]刘晓力,孟伟.认知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身体、认知与世界[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79-82.
[责任编辑 彭国庆]
B21;B5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5.009
2017-08-08
王 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伦理、技术哲学、机体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