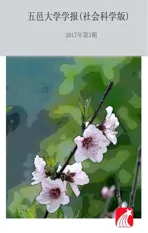白沙学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2017-03-09李晓锋
李晓锋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白沙学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李晓锋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陈白沙的文本中从没有使用过“心学”这一概念,但他提倡“心学法门”,指读书求学要自得于心。用心学来概述白沙思想的做法体现在后人对白沙学的不同解释模式中:湛甘泉等人认为白沙学是圣人之学的心学;胡敬斋等人批判白沙流于佛老,后来则出现了白沙学为佛老心学的说法;白沙学与象山学、阳明学联系起来后,其往往被认为衔接了这二者的心学。20世纪后半期以来,受“以西释中”和“以马释中”研究方法影响,白沙心学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论调。诠释白沙学应当注意回到原文,立足作者本义,避免可能带来的问题。
陈白沙;心学;圣人之学;佛老;陆王
白沙学说的主旨,有人概括为“心学”;有人概括为“自然”、“自得”、“主静”①。作为客观性的研究,我们强调白沙学的诠释应当尽量符合作者本意。但是,原始文本的诠释本身就具有众多可能性,而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后人大量地使用同一概念术语也很常见。由此带来的问题亦值得反思,比如在大量使用某一概念来阐述同一学说的时候,概念本身会经历什么样的发展?后人在不同含义层面上使用同一概念来诠释文本是否会增添文本的“价值”?以概念作为桥梁来将不同思想家相联系起来,会不会背离了作者的初衷?下面以考察白沙学被称作“心学”的历史过程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白沙提倡“心学法门”
关于“心学”概念的渊源和演变,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劳思光、饶宗颐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周炽成先生揭示“心学”这一概念大概是在南北朝翻译佛教经典时开始使用;儒家之“心学”原初意义则与《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相关;其后则出现了“圣人之学”的心学,禅或释相关的心学,陆王心学等演变意义。[1]纵观前贤之研究,可以判断的是,“心学”概念早在陈白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儒家“圣人之学”为心学的说法应当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明代大儒陈白沙是如何使用这一概念的呢?
据笔者所见,在陈白沙的著作中,他从没有直接使用过“心学”这一术语,只是在《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中有“心学法门”的说法。他称述:“予既书娄克让《莲塘书屋图后》……予赋五言近体一章,既以答世钦……颔联言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2]68-69
这一论述成为后人认为白沙学是心学的重要论据。然而,陈白沙此处所说的“心学法门”主要指的是读书、为学要自得于心,学习要有所得,必须用心体会,勿被外物所牵累。这里侧重 “以心体会” 义。而“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本为康斋早年教人之法,强调学习要主敬,从学圣人,这一点是白沙继承的先师之说。从中我们看到白沙在使用“心学法门”概念时并未赋予其特殊含义,基本上都是符合道学公认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白沙还和好友庄定山有关于“心学”的探讨。“往年白沙先生过余定山,论及心学,先生不以余言为谬,亦不以余言为是,而谓余曰,‘此吾缉熙林光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诋陈为禅者,见夫无言之说,谓无者无而无。然无极而太极,静无而动有者,吾儒亦不能无无。但吾儒之所谓无者,未尝不有,而不滞于有。禅之所谓无者,未尝有有,而实滞于无。禅与吾相似,而实不同矣。”[3]1080-1081对于好友庄定山的心学思想,白沙并没有表现出赞扬或批评的态度。而面对世人攻击自己与禅学皆以无而流入虚空,以静而归于寂灭,白沙重申自己以静见动、见活泼生机的主张,以此将自己和禅学区别开来。所以从白沙的著作和学术交往来看,他一直罕言“心学”。这说明了白沙对“心学”应该抱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世人的误解。
二、白沙学与圣人心学
最早直接用“心学”来阐述白沙学的是其高足湛甘泉。湛甘泉作为陈白沙最著名的弟子,一直被认为是白沙学的传承者,其对中晚明思想的影响很大。湛甘泉对老师学说的定位对白沙学的传承和发展亦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认为:“圣人之学皆是心学,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也,无事而非心也。尧舜允执厥中,非独以事言,乃心事合一”[3]897。
显然甘泉亦提倡心学,但他首先界定了心学的意义,认为圣人之学都是心学,并将其与《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联系起来。圣人之学为心学的说法早在宋儒时期就已形成,它更多地关心道德问题,强调心事合一、内外合一。王阳明也持这种看法:“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 ‘人心惟危……’此心学之源也。”[4]因此,甘泉和阳明的心学概念接近于今天所理解的道学或宋明理学。更重要的是,甘泉还指出了白沙心学最精彩之处是“自然”之说,他在《答聂文蔚》中说:“勿忘勿助,只是说一个敬字。忘、助皆非心之本体,此是心学最精密处,不容一毫人力,故先师又发出自然之说,至矣”[3]884。
甘泉认为白沙于心学的最大贡献是发出了“自然之说”,提出“学宗自然,归于自得”。他从白沙的学术要旨出发将其与心学联系起来,既注意到了心学的共同特点,又强调了白沙学的个性特点。
明王蓂撰写了一部《大儒心学语录》,将周子、程子、张子、邵子……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二十四家,归为心学之语也。[5]从所列之人看,除王阳明外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道学的主要学者,所以他理解的心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含义。王蓂指出传道就是传心的过程,突出了心学 “以心传心”的特点。
自湛甘泉开启了以圣人心学来阐释白沙学的做法后,这种解释模式也被很多人运用。林俊在《祭白沙祠文》中指出先生“自游康斋而心学正,友一峰而节概明,友定山而诗学大进”;“使游濂洛关闽,得其微言奥旨,侣群哲,会数圣,以肩项四之无疑也。”[2]933-934林俊认为白沙心学传承了宋代濂洛关闽的道学,还认为其心学思想在从学于吴康斋时就已形成,暗示康斋是白沙心学的来源之一。
何熊祥在《重刻白沙全集序》中也指出:“言,非圣贤得已也。自精一执中开万世心学之传……怠于舆论大同,俎豆宫墙,于是先生之心学与濂洛关闽之学并著,而先生之集与周程张朱之书不朽。”[2]901-902何熊祥将白沙与古之圣贤并举,阐述白沙心学传承了圣贤思想。黄淳在《重刻白沙子序》中也指出:“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善读者,可想见其天地胸襟、濂洛造诣。否则,等糟粕耳。神神相契,世能几人?”[2]903白沙之心学得传于圣贤,发乎于诗文,故观诗文,即可把握白沙和圣贤的要旨。黄淳认为白沙的诗文是其心学思想的集中表现。
上述论者都具有注重心学的共性,并将其与圣人之学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白沙心学是圣贤之学,对白沙学持肯定和赞誉态度,突出了白沙在道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 白沙学与佛老心学
陈白沙在世时,其思想就已经遭到攻击,其中一种是说其“流于禅学”②。白沙的同窗胡居仁(敬斋)就是最主要的批评者,这便是15世纪后半期的胡陈之辩。胡敬斋批评白沙学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其“流于佛老”,他在写给张东白(廷祥)的信中,就要求白沙“自省”。他认为“夫公甫天资太高,清虚脱洒,所见超然不为物累,而不屑为下学,故不觉流于黄老”[6]。后来在劝诫罗一峰讲学的信中,亦随带批评陈白沙“自大之言,非真见此道之精微者,乃老庄佛氏之余绪”[7]。面对胡敬斋等人强烈的攻击,陈白沙后来才写了《复赵提学佥宪》(三则)来重申自己的儒学立场,简单回应。
陈白沙去世后,这种批评的声音更甚。魏庄渠出任广东提学时期,认为白沙学乃“西方之学”[8],欲将其牌位逐出乡贤祠堂,经过阳明后学的极力挽救,此事方息。由此可见,白沙学被认为近于“佛老之学”的说法早已有之,但是胡敬斋等人尚未直接将佛老之学与心学概念联系起来。
与甘泉同年出生的夏东严也极力批评白沙之学近禅。他指出:“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备矣。吾尝恶其太严也。’此与东坡要与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盖东坡学佛,而白沙之学近禅,故云尔。”[3]67他说白沙尊崇苏东坡,并且和苏氏一同入了佛。他还尊程朱为心学正宗,批评白沙欠下学工夫。他称述:“程子云:‘与其是内而非外,不若内外之两忘,两忘则澄然无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才觉得间断,便已接续了。’此皆任其天然,了无一毫将迎安排之病,心学之妙,至此余蕴矣。”[3]75在他看来,白沙过多地谈主静,而远离了程朱主敬的要旨,流弊甚多,心学之妙离不开一个“敬”字。
由以上可推论,白沙学是否是圣贤之学的心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白沙后学持肯定的态度,对其进行护卫,同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其是一种佛老之学,非儒家传统圣贤之学。这种白沙学批评之风还一直持续下去,后来随着心学含义的多样化,出现了一种佛或老意义上的心学概念,用来专指为学中摒除杂念、虚静无欲之术,批评者自然而然地将白沙归入其列。
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这种心学概念就已经出现了。陈建(清澜)在《学蔀通辨》中就批评了白沙心学非圣贤之心学,将其称为佛老意义上的心学。他认为:“圣贤之学,心学也。禅学、陆学亦皆自谓心学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则异也,心图具而同异之辨明矣,是故孔孟皆以义理言心,至禅学则以知觉言心。……孔丛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张子韶曰觉之一字众妙之门,陆象山曰收拾精神万物皆备,杨慈湖曰鉴中万象,陈白沙曰一点虚灵万象存,王阳明曰心之良知是谓圣,皆是以精神知觉言心也”[9]。
陈建批评了禅学和象山学非心学,他指出圣贤之学和禅学皆谓心学,但是两者有着截然的不同。孔孟是圣贤心学的代表,他们以义理言心,而孔丛子、张子韶、陆象山、杨慈湖、陈白沙、王阳明和禅学一样都是以知觉言心,所以陈建认为白沙心学并非圣贤心学,而是佛老心学,应当对其进行抵触。从这里可看到,佛老心学的概念已经出现,心学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当时许多的道学者都以“心学”来阐述自身与圣贤之学的联系,故有不少批评者以白沙学为佛老心学。
四、白沙学与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心学的典型形态,这种说法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在此考察的是,白沙学是如何与象山学、阳明学联系起来的,以至后来白沙学成为了陆王心学的桥梁?
如前文所述,湛甘泉从圣人之学为心学的角度阐发了白沙学的“自然”、“自得”之说。另外,甘泉还认为象山学和白沙学皆为心学。他称述:“夫圣人之学,心学也。《记》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谓人为天地之心?人物浑然同天地之气,气之精灵者即心,心之生理即性。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别心别性,故天地人物之气之心之性,一也。如彼脂灯之火、石中之火、木中之火之光,大者如日月之光,非有别光也,乃其精灵者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10]2。
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湛甘泉对“心”的看法,他认为“气之精灵者即心”,因为气化流行,所以人同此心,性由心而生成,但两者并不是分截两物,二者是统一体。他将火比作心,光比作性,光自火来,性由心出。他又说:“象山先生立其□□□□宇宙性分之一,契道体矣,契此心也”[10]3,其指的是陆象山同圣贤一样将人心和天地之心统一了起来。他又说:“三贤(即陆象山、吴草庐、吴康斋——引者)皆天地之心也, 皆为天地立心者也。故敢叙心学之说”[10]4。如前所述,甘泉也认为白沙学为圣人心学,这说明他认为象山学和白沙学皆为心学。需要指出的是,他对道统之说有这样的质疑:
曰:“道可传乎?”曰:“可得不可传也。或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若谓有一物相授者然,而不知人人自有”[10]。
湛甘泉认为道是“人人自有”的,求道的方法是向内而非向外,所以道并非是从前贤那里传来的。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主张与其说白沙心学继承象山心学,不如说白沙心学是“自得”而来。
对于白沙学说,王阳明亦曾称赞道:“白沙先生学有本原,忒地真实,使其见用,作为当自迥别。今考其行事亲信友辞取予进退语默之间,无一不概于道,而一时名公硕彦如罗一峰、章枫山、彭惠安、庄定山、张东所、贺医闾辈,皆倾心推服之,其流风足征也。”③据此,“阳明何故不言白沙”的公案应该可以得到澄清。阳明并非不言白沙,而是多次称赞过白沙的。阳明认为白沙“学有本原”,其学问、人品和道德都是非常令人推服。王阳明对陈白沙的态度为阳明后学将其和白沙相联系起来作了铺垫。
最早将白沙和阳明两者联系起来的是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字汝中,号龙溪),他指出:“我朝理学开端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3]259后来李经纶辟王湛二家之学,在《大学稽中传》中说:“象山之学……再传而为白沙……三传而为阳明子、甘泉子也。”[3]1256这表明了象山、白沙、阳明三人联系的建立。往后就有我们熟知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视白沙开明代学风之先、阳明传承下来的说法。他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3]79。
唐伯元反对阳明学的立场鲜明,但他对白沙却抱有一种学习的态度。《明儒学案》中记载了一事。胡直曾写了一封信给唐伯元,其说:“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编》,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学,今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岂非学渐归原,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远哉?……虽然,犹幸人心之良知,虽万世不可殄灭,子思、孟子之道终不以荀氏贬。至白沙、阳明,乃蒙天子昭察,如日月之明,岂非天定终能胜人也哉!”[3]526胡直乃阳明的三传弟子,欧阳德的学生,他一直比较推崇阳明心学。他认为白沙学和阳明学皆为心学,都传承了圣贤之道,而且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他欲以此来缓和唐伯元批判阳明心学的态度。
如上文所述,明朝的陈清澜一方面批评了白沙为佛老心学,非圣贤心学,另一方面也批评了陆学、阳明学自谓心学,认为这些都是以“以精神知觉言心”,属于禅学。这也说明,白沙心学和象山心学、阳明心学相近的说法在明朝后期应该比较普遍了。
清朝的贾润也认为白沙学和阳明学皆是心学:“明初诸儒、如方正学、曹月川、薛敬轩、吴康斋,其学一本濂、洛、关、闽,未尝独辟门户。至白沙、阳明,专求心学,重内轻外,其说虽足以救朱学末流之弊,但隆、万间禅学盛行,亦二公有以潜启其端也。”[11]贾润理解的心学与前人不同,他认为心学的基本特点是重内轻外,而白沙学和阳明学都是重内轻外,后世的禅学盛行是白沙学和阳明学的流弊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把白沙心学和象山、阳明心学并列的做法已十分普遍,但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如清乾隆年间,当时很多人认为陈献章在主静上,接了陆象山宗派,陈白沙九世族孙陈世泽则认为此是诬语,并指出对方使用的“致养在我”、“终日乾乾,收拾此理”、“宇宙在我”等论据是改头换面,断章取义,和白沙原文有较大的出入。[2]916
以上梳理了明清时期象山—白沙—阳明为心学学脉的形成发展过程,陈白沙也往往被认为衔接了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后学认为陈白沙传承的是圣贤心学,另一些批评者则认为陈白沙传承了佛老心学。20世纪后,陈白沙虽也常被归属于陆王心学之列,但陆王心学的含义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侧重于心是宇宙的本原。兹由下文论述。
五、20世纪后的白沙心学
进入20世纪,有一个基本的学术背景,就是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的传入。这一时期,白沙心学的论调基本占据了学界的主流,但对心学的理解和前人有着明显差异。其中白沙心学的论调又大致有以下两种:
其一,用“以西释中”④方式来阐释白沙心学。冯友兰先生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中将道学分为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别,而朱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心学一脉则为陆象山、杨慈湖、陈白沙、湛甘泉和王阳明等。冯先生强调了陈白沙在陆象山和王阳明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认为陈白沙为陆王心学一脉。众所周知,冯先生此套《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旧瓶装新酒”,即“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12]336。冯先生以西方新实在主义的思想来区分朱陆的异同,他指出:“盖朱子所见之实在,有二世界,一不在时空,一在时空。而象山所见之实在,则只有一世界,即在时空者。”[12]217因此,他认为白沙心学所得于象山心学,其“实在”也只是一个世界,即在时空中,基本特点是主张“心即理”[12]219-221,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有别于朱子理学一脉。这种“以西释中”方式对后来的白沙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刘兴邦先生在解释白沙学时候,他着重分析了白沙之心的含义,认为白沙之“心学”是内外合一、心理合一的新“心本体”的综合与创新。他还指出此心是认知之心、主宰之心、道德之心。[13]从中可见,他运用了西方哲学中宇宙论、本体论的概念来研究白沙学中心和理的关系。这种“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在当下众多的白沙学研究论著中屡见不鲜。
其二,用“以马释中”⑤的范式来解释白沙心学。范寿康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通论》中指出:“白沙初从吴康斋所学是程、朱一派的理学,后来他自己觉得不满,实行静坐,于是遂转到陆象山心学一派的路上。……这样他和象山一样,也是一个彻底的唯心论者。”[14]范寿康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认识白沙心学,他认为白沙心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心学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由心来推出万物,而白沙不仅立足于“心之体”,还将心和外物统一了起来。他还认为理学和心学是宋明儒学的两大对举,白沙心学之源是象山心学,象山也一并是彻底的唯心论者。
在20世纪后半期,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非常大,宋明理学常常被划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对举,而心学则更多地以主观唯心主义的面貌来出现。上世纪50年代,在陈白沙的故乡江门曾有一场关于白沙心学是唯心还是唯物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尽管学者的观点有所差异,但都是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对举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
另外,把白沙学作为一种心学来研究,一些学者则强调它的岭南特色和现代价值。如黄明同将白沙学与传统的“陆王心学”区分开来,认为陈白沙创立了别具岭南特色的心学体系,“即既承认‘道’为万物之本,人‘得道’而‘天地我立,万化我出’,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又承认‘鸢飞鱼跃’、‘化化生生’自然世界的客观存在,并认定人所以能‘开万世’,令‘宇宙在我’,是以‘得道’、‘会道’,把握‘道’,即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15]她把白沙心学界定为心性之学、认知之学、涵养之学,侧重于发掘白沙心学在岭南文化中的价值意义。
六、结 语
梳理不同历史阶段人们用心学来解读白沙学的过程,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问题值得反思:
其一,基于不同的心学概念来理解白沙学,是否概述了白沙学的学术要旨?从心学的视角来认识白沙学,应当是有意义的。如上文所述,甘泉等人将心学与圣人之学联系起来,并重点论述了白沙的“自然”、“自得”之说,其不仅是对白沙学一种合理的描述,也有利于确立陈白沙在道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见,在运用一个并非作者自述的学术术语来概括该作者思想的时候,客观、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本义应当是其基础。湛甘泉和贾润都认为白沙学是“心学”,但两者的理解截然不同。湛甘泉认为白沙主张“心事合一”,贾润认为白沙主张“重内轻外”。如果仅仅用心学来概述白沙学说,那么就很容易掩盖这两种理解的差异性。因此,在白沙罕言“心学”的情况下,“心学”应当要涵盖白沙学的学术要旨。白沙学的学术要旨指的是“自然”、“自得”、“主静”三个方面。对此前贤已多有论证,如湛甘泉在《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曰:“白沙先生之诗文,其自然之发乎!……予惟自然之学,固先生始。”[2]896-897张诩在《白沙先生墓表》中说:“其为道也,主静而见大,盖濂洛之学也。”[2]883杨起元《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也说:“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2]903那么,后人在过多使用“白沙心学”一语的时候,白沙的三大学术要旨如何避免被“喧宾夺主”则需引起注意了。
其二,用心学来将白沙与其他人联系起来,是否夸大了共同性掩盖了特质性?若论心学是“以心传心”之学,其大意与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学或者理学相近,白沙学属于心学,这自然是无误的。然而,我们看到心学发展极盛的时候,彼亦心学,此亦心学,并且开始将白沙心学和象山心学和阳明心学联系起来,后来还有了吴康斋—陈白沙—湛甘泉这种心学脉络说法。白沙思想上传承了吴与弼这种观点一直遭到人们的怀疑,黄宗羲认为:“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3]14白沙自己也说:“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3]145可见,白沙在吴康斋那里求学“未知入处”,白沙学的主旨并非承继其师。另外上文指出,很多论者认为阳明心学继承了白沙心学。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密切?很多学者从逻辑上证明两种学说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论断仍缺乏一些事实上的根据。阳明推服白沙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其学问、人品和道德,但他在晚年很少提到白沙,而在自己和白沙思想的异同这一点上,他更是始终语焉未详。
其三,用“以西释中”和“以马释中”的方法来诠释白沙学,是否会增添并非文本自身的“价值”?20世纪后半期以来,心学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它更多地融入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刘笑敢指出这种“反向格义”的方法“很容易导致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导致机械地、错误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⑥。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白沙学被定义为“心学”也带来了许多白沙本人并不十分关心的论题。如认为白沙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说法,强调白沙对世界本原问题的认识——白沙主张心是世界的本原,心能推出万物。然而,我们都知道白沙本人并不十分关心世界本原这个问题,他的一生基本都是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中努力的。这说明当研究者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顶帽子来套这些道学家的时候,可能并不适用。
综上,用心学来诠释白沙学的过程体现了心学含义不断演变和白沙学“价值”不断添加的过程。然而这种诠释应当注意回归文本、立足作者本义。在对经典作品的“创造性解释”中,进一步赋予其“中国味”和回到作者的语言文字中,有利于发掘经典的永久价值和重新理解中国哲学精神。
注释:
①景海峰从倡言“自得”、学宗“自然”、“主静”的意义三方面探讨了白沙思想(景海峰:《陈白沙与明初儒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2期);周炽成认为陈白沙的三大学术要旨(自然、自得、主静)无法以心学来统括(周炽成:《白沙学非心学》,《现代哲学》,2010年第3期)。
②白沙提到其毁于时人,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自立门户者,是流于禅学者”;其二是说“妄人,率人于伪者”(陈献章:《复赵提学佥宪》,《陈献章集》第146-148页)。
③转引自邹建锋《从阳明夫子评白沙学的一段佚文看明代心学间的互动》(《浙江学刊》,2015年6期第87页)。
④“以西释中”指以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标准、尺度来衡量和解释中国哲学。
⑤“以马释中”研究范式指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读中国历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中国哲学上则表现为将哲学问题一般地内置于思想史之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郭齐勇:《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⑥刘笑敢提出了“反向格义”一说。他认为:“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反向格义’,将自觉地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反向格义自胡适、冯友兰以来成为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 周炽成.“心学”源流考[J].哲学研究,2012,(08):36-43.
[2] 陈献章.陈献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45.
[5] 王蓂.大儒心学语录:27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会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773-854.
[6] 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复张廷祥[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7.
[7] 胡居仁.胡敬斋集:卷一:与罗一峰[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0.
[8]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七:无题答或问[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会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91.
[9] 陈建.陈建著作二种·学蔀通辨[M].黎业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04.
[10] 湛若水.抚州府新创三贤祠记[M]//湛若水.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四.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万历二十三年修补本.
[11] 徐世昌.清儒学案[M].沈芝盈,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140.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3] 刘兴邦.白沙心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13.
[14] 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84.
[15] 黄明同.明代心学的开篇者——陈献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
[责任编辑 李夕菲]
2017-03-15 作者简介:李晓锋(1993—),男,广东高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B248.1
A
1009-1513(2017)03-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