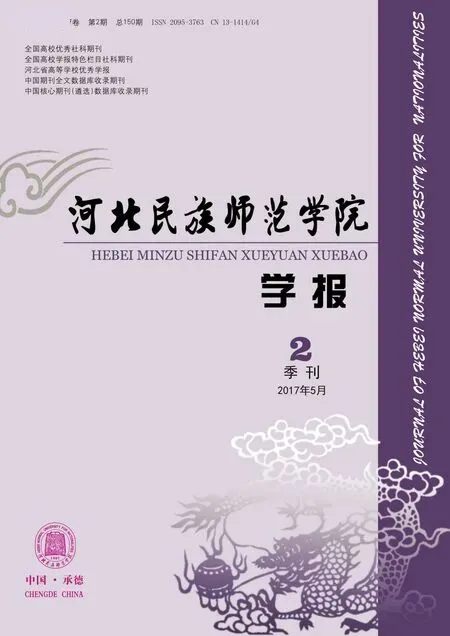承德方言词汇的文化特征
2017-03-08关志英
张 颖 关志英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语言学研究】
承德方言词汇的文化特征
张 颖 关志英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符号的使用。承德方言中有一些独特的构词和表义特点的词,凸显了地域文化的特质,其主要导源于古语词、外来语词等。承德方言词汇的形成受地理、历史、文化接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接触是显著动因,外来语词中满语词影响最大。对承德方言词汇的整理与分析进一步表明: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词语借用是异质文化群体之间接触的一种常见文化现象;方言的互相融合是一种常态,包容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之一。
承德方言;词汇;语言接触;满语;特征
一、引言
依语言学的划分,汉语方言分为七大方言区,承德属北方方言区中的华北、东北方言片。本文重点考察的是承德方言词汇,使用材料为近年来方言调查搜集收录及查阅承德各县县志所得。
“文化”是人类文明所形成的一种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种综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生活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一种能力。[1]在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中,每一地域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也存在各自鲜明的特殊性,这种不同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语言符号的使用是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和继承的工具,语言对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语言的背后是文化,文化内容的特点常常在语言中得到反映。
承德是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积淀着清王朝近三百年的文化兴衰。承德市有3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3个民族县,少数民族人口146万,占全市总人口的40%,占河北省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语言学家将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辽宁、通过承德地区一直达到北京市郊区和城区内的地域,称为北京官话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位置,承德方言词汇既属于北京官话区,与北京方言东北方言有太多的一致性,(本论文所收的方言难免在他方言中也看到)但它又有一些独特的构词和表义特点的词,这与承德地区的历史、地理、民俗文化有关,而这些方言词汇恰恰凸显了地域文化的特质。
二、方言词汇的来源
一种语言的词汇是不同来源的总和,任何一种方言都可以说是不同历史时期语言成分的累积。北方汉语词汇异常丰富,既有华夏语言的古词,来自自秦以后诸代,还有不同民族语传入的各式少数民族语词。少数民族语词使用年久,融合于北方汉语中,与固有的古词共同被调遣使用,已难寻其痕迹。承德与北部、东北诸民族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是诸民族语言相交际、相混合之地。承德方言的形成与汉语以外的诸民族语言的影响密不可分,其中蒙、满接触对承德影响最大。承德方言的词汇来源,可看出的有以下几部分:
(一)古汉语词
古语词来自秦汉开始到明清,有些方言特征词是古代原住民的语言积累,原住民的语言底层是方言形成的古代阶段留存下来的。承德方言词汇中一些词去垢拂尘,可看出是熠熠有华光的古语词,如:
䜺(《广韵·陌韵》栅小的收字:“磨豆,测戟切”。《玉篇》豆部收字:“叉白切,磨豆也”两书注音有异,释义相同,均指经过破碎的豆。)
溜(《说文》手部收“提”字,“挈也,从手是声。杜兮切”)
杌凳(“杌”《说文》儿(ren)部收“兀”字:“高而上平也……”《广韵·没韵》兀小韵收“杌”字:“树无枝也,五忽切”。可见“杌”字的本字当是“兀”字。“兀”“杌”两字含义相合便产生了坐具一义。)
累坠(累,读如雷,携带东西太多,捆系没有秩序者。方以智《通雅》有‘磊zhui’二字,与此音义皆同)
糗(读如求,上声,乱杂不清者,如做干饭,米与汤相混,不能捞者,则曰“饭糗了”《集韵》糗,去久切,音糗,食物烂也。)
抪拉(‘抪拉’即‘拨’字之缓读为二之字。《说文》抪,舒也,布散也,又击也。)
洸荡(洸,去声,摇荡也。器中水摇动曰‘洸荡’《说文》洸,水桶光也)
瘥也(《 辞海》注:差同“瘥”,病愈。《方言》第三:“差,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
褯子(《广韵·禡韵》“慈夜切,小儿褯”)
还有如:窠儿、豚儿、䝋儿、数落(落,读老,去声,数落夹杂骂词)巴巴、勾当(多作动词用)咕嘟(煮也。汤多曰煮,汤少曰咕嘟)发送(丧葬、办理丧事)面生、盹、省得、拿捏人、经意儿的(故意) 戳儿(印章)等等。
一些方言词,听起来比较土俗,但确实为古汉语的遗留,显示了古语的特点。语言使用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互借,有些汉语词被少数民族借去,后来又传入汉语。其中外族语的汉语借词,其发展不同于汉语,有可能完整或大体上保留汉语的特点,例如满语词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在读音上保留古语读音。“瀎泧Masa”《说文解字》就有这个词,释为“拭灭貌。”清段玉裁注为“今京师人语如此,音如麻沙……手上下之言也。”当然有一些古汉语词在外族人使用中也有部分变化,或多或少地被打上民族“印记”。例如满族人在满式汉语中也创造和形成了一些特殊的音位、音节和语音结构法。这就解释了承德部分词语为何会有不同于普通话的读音,如 :
早晨(tsAu214tþHin 或tsAu35þin)把(pai214介词)在家(tsai214tþi¢55)、比(pHi214)、上学(þiAu35))你们(nin214m«n)等等
(二)口语白话词
承德方言中有大部分是形象生动的口语白话词,日常交际中人们不断创造带有修辞色彩更多的是比喻义的词语,经年累月留存下来,形成了一大批语言成分丰富、交际功能生动的词语,充盈着人们的语言世界。如:
白毛风、箭杆子雨、扫帚星、闹天头、暴土、大拇哥、当家的、土包子、出门子、说媳妇、坟茔地、白果(鸡蛋)、油箅子(油饼)、面引子、手巴掌、耳房子、灶火、灶坑、风匣、铺衬、长虫(蛇)、棒子、老爷转(向日葵)、山里红(山楂)、眼气、成心的、外道、归置、挣命、做啥(tsuo51§¢35(做什么)倒粪、梆硬、鼓溜、刺痒、刺闹(tsHnAu)、花插儿(xu¢55t§HAr214间隔着)白话(pai35xu¢说空话、大话)、做瘪子、蔫土匪、犟眼子、牛儿上了(闹对立)侃大叉、挣命、诈尸、草鸡了(tsHAu214tþil«垮了) 等等。
(三)外来词
方言的演变除了纵向的传承,还同时有横向的接触和渗透。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2]是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互动或相互影响的现象。多种语言处于同一地区内,总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文化接触最直接、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借词,不同的语言,词汇丰富程度不一,各种语言总会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自己所缺少的词语,这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反映。外族语中对承德方言词汇影响最明显的是满语词。北京长期是清王朝首都,承德是北京外的清朝另一个政治中心,大量满族人口居住于此。其实满语中早已吸收并稳定了一大批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借词,还有一些其他兄弟民族的借词,尤其是满语中的蒙语借词相当多,有时很难区别清楚。这些叠置在一个空间上的不同时序的外族语借词,有的改了语音,有的改了语义,它们成了满语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满语词随着1644年满族入关而被带入,对汉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语词在北京官话区影响甚大,也在承德方言中被广泛使用。
承德人口中常用的满语词如:
啰嗦、喇乎、埋汰 勒忒、耷拉、旮旯、咕噜、伍的、划拉、嘎啦、嘟囔、虎势(xu214§)嗝嗻(满语词ɡejihesembi,北京话取其词干,说成ɡezhi)嘞嘞(lF55lF)玍古(k¢35ku又写“嘎古”,怪异)挖碴(w¢214t§H¢35)、 邋遢、胡图、察拉(t§H¢214l¢ 厉害)累赘(满语原指“笨拙”)扎古(t§¢55ku满语指“帮人调理”)央告(iAN55kF)狼乎、喀嚓(kHu¢55t§H¢义为“将物刮去一层再刮一层”,)筋道(tþin55tAu)麻应(m¢35iN)硌应(kF51iN) 嚓咕(t§H¢55ku)倒腾(tAu35tH«N“倒来倒去”) 务辣(wu51l¢)萨莫、秃鲁 、磕碜 、派邋 、 掰扯、侧棱、摩挲、磨蹭、抹布、衙门、眵目糊(也有写成“泚沫胡”)、拉忽(l¢214xu)、糊里糊图(满语读作“忽里胡图”或“胡勒巴都”)哼哼唧唧 、扎裹、哈喇(x¢55l¢,)鹅淋(F35lin 水湿后留下的印记)、塌咕( tH¢55ku )
饽饽、 萨其玛s¢55tþHim¢)、葫沓(满语原指“奶油糕”)、苦力(奶饼子。承德话:kHui214lei) ) ,指用莜面、玉米面等做成的颗粒状的食品) 饸饹、布拉儿(pu51l¢r嫩树叶搀小米面蒸的面食)锅嘎渣儿、散状儿、蛤蟆骨朵(x¢35m¢ ku55tuo也称“蛤蟆蝌蚪”)啦啦蛄 、蚂螂儿、刀螂、蛐蛐 、蛛蛛、曲蟮、屎壳郎 等。
承德地名用字和命名,如:
蓝旗营儿、扎拉营、波罗诺(蒙语波伦斯诺尔)、哈拉海(蒙语)、哈子沟、阿拉营、十二挠海、阿叱沟、乌梁苏沟、茅吉口、大布汰沟、哈巴气、扎扒营、大扎布沟、乌兰哈达、苏木营子、八达营、乌布什沟、崩布汰沟、哈拉海沟、伊玛图河 等等。
满语、蒙语词在承德地名中占了不小的成分,也说明地名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历史的内涵。
(四)满式汉语词
不同的语言群体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里,并且来往密切,互相接触引发互相影响和渗透,那么他们的语言就有可能融合成一种民族语言。满式汉语是清代流行的一种词语形式。在满汉杂居语言融合的广大地区,代表满族特征的“国语骑射”在高度发展的汉族农业经济的长期影响下,逐渐衰退或融化,而来到北京热河东北一带旗地庄屯中的汉族居民,由于长期生活在满族文化的氛围中,耳闻目睹,也必然吸收满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满族人的语言风格,于是发生方言杂交。从北京到承德一带流行着许多满汉混合语、满式汉语。
赵杰先生在《满族话与北京话》中对满式汉语作了精当解释:满族人在替换语言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中介语——满式汉语,“……清朝统治者及满州旗人在替换语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初级阶段的满式汉语(主要是东北方言)和近古汉语白话相结合,融合并发展成一种京腔北京话,逐渐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mandarin,几乎在满文基本停止使用的同时,汉语文言文的地位也在急剧下降,但它的一些成分过去也一直通过近古汉语白话不断输送给发展中的满式汉语。到了清末,满汉语言经多层数代的接触与融合,终于优化出一个公认的权威方言——高级满式汉语(主要是京腔)。”[3]151满汉语素的融合词,例如:
扎呼(“扎”满语,“呼”汉语)、马勺(满语“麻沙”)、哨卡(“卡”满语,“哨”汉语)、笨笨拉拉(“笨”汉语,“拉拉”满语“末尾”)、藏猫儿(“猫”满语“树木”)、旗袍(“旗”满语,“袍”汉语)、算盘疙瘩(“疙瘩 ”满语)、仄歪(满语词jailambi,义为“躲避、躲”,北京话加以汉语“歪”,成t§ai55uai)、乖打(满语词ɡoimbi,义为“打中”北京话为“打,拍打”) 等等。
承德地区满式汉语词星罗棋布,各个语域里都有,我们择要举例:
饮食类: 兀突水、莜面窝子、黏豆包、荤油、槽子糕等。
服饰类:兜兜(tou35tou)、哈拉盘儿(围嘴)、嘎啦圈儿(“嘎啦”满语,皮革着水变硬)、胡搭巾儿、镏子、毡疙瘩、坎肩等。
动植物类:尕尕儿、疥疤子、鸽子、鹞子、鸣鸣哇儿(miN35miN35w¢r55)等。
岁时节令类:今儿个(tþi«r55kF)、 明儿个(mi«r35kF)、后儿个(xour51kF)、夜来个(yE51lFkF也说yE51kF昨天) 、前儿个(tþHir35kF)、早曦(tsAu214þI 早晨)、头晌儿、后晌儿、 晌伙儿、黑家(hei55tþin夜里)、哄晌(xuN51§«N 后晌)、五单午儿、年五更(niEn35u214tþiN)啥前儿(§¢35tþHir什么时候)、多前儿(tuo35tþHir)等。
有关人体等生理类词:膊拉盖儿(po55l¢ kr51)夜灵盖儿(iE51liN kr51)锛楼头、哈啦子、左撇捩子(tsuo214pHiE liE214ts«)妈儿妈儿(乳房)咂咂儿(ts¢55ts¢r同前)脓带等。
动作行为类词:多是对人的行为与情态的描述。
喽一眼、搡嗒、撂杆子(liAu55kan55ts«)打嘚得、抓嘎啦、抽冰嘎儿、 拉磕儿(l¢214kHF r)捅楼子(闯祸,满语原指“祭神灵的小佛龛”为“楼子)、钉纽绊儿、喇忽、没辙、找碴、抠缩(kHou55sou )、淘登(tAu35t«N )、咋罚子(ts¢35f¢35ts«)、歇乎(þiE35xu)、訄人、皮实(pHit§ )、半吊子、二不愣(Ô51pu l«N55)玍杂子(k¢214ts¢35ts«) 夹尕头(tþia35k¢ tou35怕见生人)大列子(t¢51liE214ts«随便的人)掐巴 、添活儿(tHiEn35xuo)、 咋摸咂摸、 傻啦呱唧、撺掇、撕拉等。
性状类词:对一些事物的性状带描述色彩的词:
牢棒(lAu35pAN )、水拉吧唧、撇清拉色的、精湿呱嗒、 白不咋儿(pai35pu tsr55)稀不溜丢儿、提溜嘟噜(ti55liu tu55lu55)等。
称谓类:连乔儿(liEn35tþHiAur35)、连襟子(liEn35tþin55ts«)、妗子(tþ in51ts« )、家姑老儿(tþia55ku55lAur214未婚的老年女人 )新姐(满族人称嫂子为新姐,蒙族同)等。
物品名称类:水筲、笤帚、掸子、水瓢儿、木梳等。
以上四种是承德方言的主要来源,尚有一部分调查得来的方言词暂时没有归类,有待进一步分析确认。
三、方言词汇的文化背景
文化语言学家张公瑾曾指出,“文化是各个民族或群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4]不同的民族、历史和不同的地域特色,会形成不同的人文景观,自然会产生与之相随的民族文化。
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特征总是要在语言中留下痕迹。按照语言学的一般原理,词语的构成与当地的生活(物质的精神的)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受到历史人文条件的制约。承德方言词汇的形成原因林林总总,民族接触是其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地理
在民族心目中,神圣的文化其实就是地域特点、生存环境的产物。帕默尔说“决定语言接触的社会交际,从根本上来说,是在空间中进行的接触和运动。所以言语像一切文化现象那样,为地理因素所决定并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5]
北方地区自古就与一些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地区为近邻,古华夏族与“戎狄”不但久为邻居,而且交错而居的局面为时已久。阿尔泰语系的无声调的契丹语和女真语,如同以前各时代的匈奴、东胡、楼烦、丁零、鲜卑、突厥及其他诸族的无声调的语言一样,对汉语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对北方地区。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东与辽宁省交界,南与天津市及唐山市相邻,东南为秦皇岛市,西南紧依北京市,西接张家口市,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是诸民族语言相交际、相混合之地。承德元代以前只有少数人居住,历史上曾是游牧民族频繁出入地,处于中原与胡地的过渡地带,是历代中原王朝与漠南、辽东辽西诸少数民族的多边辖地,如平泉县为冀、辽、内蒙三省区的结合部;隆化地带曾是蒙古族繁衍、生息和游牧之地;围场县在建立木兰围场前也是蒙古人的游牧地。紧邻承德的汉语以外的诸语言对承德方言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些都决定了承德方言与东北、内蒙等地方言相近,如果站在全部汉语方言中观察,承德方言的“外貌”与北京方言、东北方言有太多的相似。环境地理对人们语言生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历史
历史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格里姆论语言的起源时说过: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是在不断应对各种各样变化和变迁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有可能通过语言材料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文化表象,探索其起源、传播和演变的踪迹。
北方地区的历史实即民族融合的历史。民族之间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伴随着语言文化的接触。宋、辽、金、元时代是北方诸民族与中原人又一次大融合的时代,北方汉语因受到极大影响而发生显著变化,为北方汉语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造成方言歧异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人口迁徙,女真入主中原后,北方发生民族迁徙的高潮,致使北方汉语与女真语相互影响以至于融合。蒙古统治时代,民族融合规模已经很大。蒙古语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创制的满族语对北方一代影响明显。
承德方言词汇亦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地处塞北历史上曾是游牧民族频繁出入地的承德,距北京224公里。自清代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修建避暑城开始,经康乾建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止,清代在承德总共建设了211年之久,正是在多民族国家巩固统一的过程中,承德从一个“名号不掌于职方”的小村庄,成为仅次于京城北京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中心,成为团结少数民族的重要活动场所。满清文化自然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汉语。
(三)文化接触信息
与文化多样性并存着的是“密切接触”的多民族差异性文化主体间不断发生的互动。共同语基础方言地位会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改变。少数民族与汉族由于长期居住在我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其语言自然相互接触,各自从另一语言里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成分来丰富自己。方言历史演变的宏观取向是弱势方言向优势方言靠拢、方言向共同语靠拢。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统治中原长达数百年,文化、语言的渗透、融合非常密切和深入,以至于进入中原的阿尔泰语使用者最终全部转用汉语。在转用汉语的过程中,由于不完全习得,不可避免地会把原来母语的一些特征带到汉语中来,汉语的一些词语便带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印记。承德方言词带有鲜明的蒙、满民族语的影响。蒙汉语言文化接触历史悠久、互补性强。在文字事物创制方面,后金也主要依据蒙古文来创制满文。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在语法上同蒙古语很相近,在词汇上又较早地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满族入关以后,从关外带来的满语词便与汉语有了更多的融合互动。满语作为京腔的一种底层,为满式汉语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满语不仅在衰落以致消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一些语音、语汇、语法等结构特点融入汉语,更重要的是,满族人把自己说母语的思维方式和目的语的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具有两种语言特长的满式汉语京腔化。”[3]159
满汉融合表现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方言的权威性主要与方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竞争力相关。满族很少的人口处在汉人极多的环境里,自然要以汉语、汉文为主。满族贵族执掌大权,军政财刑事物繁多,公文往来频繁,绝大多数不得不用汉语文,因而汉语对满语的影响日益深入,清代中后期汉语北方官话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驻防群体八旗官兵受汉语影响最大,驻防的八旗满营,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广大的汉族聚集区中,母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他们逐渐放弃使用满语,学会了当地的汉语方言。京畿地区旗人汉语和满语双语接触占主流,满人广博吸收汉文自不必说,汉人学满语文的风气也盛行,使旗人汉语成了说两种语言的人们约定俗成的产物。
在语言中,借词是构成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发现,在词汇层面,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借贷屡见不鲜,尤其在相关专业术语方面更是如此。不同时期借词内容、形式的不同,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民族特点以及语言特点所决定的。与少数民族向汉语借词一样,汉语也同样从少数民族借词,“扎古”等词原来确确实实是地道的满语词语,后来才成为汉语中的借词。语言接触对承德地区突出影响的主要事件有:
1.移民。满汉语言融合首先归因为嘉庆以后大量旗地典给民户耕种这个社会条件。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原居住东北的满族军民随着顺治皇帝定都北京,逐步向内地迁移。康熙初年,清政府以赏给官职为诱饵,鼓励地主豪绅迁徙垦荒,同时又对满族贵族迁徙人员在经济上予以优待,推动了移民的进展。承德境内大部分土地成为旗地,旗地的拥有者为八旗军政机构、旗人个人及部分驻防绿营官兵。由于清政府“借地养民”,解决灾民生计政策,清代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出关逃荒定居的汉人灾民,以及被招垦入境经商落户的商贾及眷属,移入承德本境。土地拥有者或招佃本地、外地农民立庄农耕,或自垦自种,或分兵屯田,或僻为牧场等。旗丁与民佃杂居相处,生活习惯、心理素质、语言文化愈益融合。迁居某处,慢慢培养群体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而逐渐演变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圈,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需要有一种为大家接受的公共交际语,文化扩散影响首当其冲的当为语言。
2.建围场、修行宫、设立行政机构。“木兰”本系满语,汉语之意为“哨鹿”。木兰围场,作为清王朝塞外的皇家猎苑,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初建到嘉庆二十二年(1717年)最后一次举行木兰秋狝的135年间,康熙、乾隆、嘉庆共来木兰围场百余次,举行木兰秋狝大典88次。这里成为清帝行围涉猎、演兵习武、避暑巡视、联络北方蒙古诸部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场所。
皇帝北巡这种活动规模较大,在承德境内往来驻跸、沿途行宫驿站林立、随围大臣众多,对承德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满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是木兰秋狝中主要的两种文化,作为北方新兴势力与传统势力的两个代表,满族是典型的游猎民族,自古崇尚马上骑射,因此在木兰秋狝中活动的主要内容以骑射为主,形成狩猎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另外在木兰围猎期间,祭拜祖先祭拜大兴安岭等满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也渗透其中。而豪放粗犷的蒙古族则是传统的游牧民族,音乐、体育娱乐等成了传统文化释放的主角。在这种地域文化圈里,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同化着生活期间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们涂抹上同样基调的文化背景和相互类同的意识观念,人们的生活方式、举止言谈、价值观念等无不受其文化的影响,语言的“棱镜”折射出了这种和谐共处。
四、结语
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是在相互交往相互影响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民族接触实际上就包括物质、精神、社会制度等全方位的接触。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不断地与外来文化进行接触交流,并不断吸收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通过对承德方言词汇的收集和粗略分析,让我们有了几点更明确的认识:
(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方言好似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地方文化和历史的种种信息。承德方言词汇的产生和使用与东北、北京地区的历史发展、人口迁徙、民族关系、政权更迭、文化交融等息息相关。
(二)词语借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化接触是至少一对异质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语言交往中接触双方都对彼此的语言产生一定的了解,并且都要向彼此的语言借入词语来满足交际的正常进行。没有一种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也没有一种不存在任何借词的语言。各民族相互借用的语言,成了民族自然融合的“先行者”。多民族国家的不同民族,往往会有一个民族人口最多、社会发展相对先进的主体民族语言,这种语言对其他语言的影响无论在影响力度、影响范围上,都处于优势地位。
(三)方言的融合是一种常态。如果移民与土著交往频繁,杂居在一起,两者的方言很可能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替代。包容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之一。繁荣上升的社会就该是多元化的,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多语言才能多视角,多文化才能多色彩,多包容才能多发展。这也提示我们:语言的平等、多样化与和谐共处应当成为基于人类良知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
期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一部分承德方言词汇的文化现象,或许它是一条探索承德乃至北方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重要路径,我们将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探究下去。
[1]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4.
[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86.
[3]赵杰.满族话与北京话[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151、159.
[4]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3.
[5]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17.
[6]常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7]王国平.大清皇帝在滦平[M].沈阳:白山出版社,2015.
[8]吴丽君,石东玉,李彦如.承德方言古语词探析[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4).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ocabulary in Chengde Dialect
ZHANG Ying, GUAN Zhi-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The use of language symbols is a crucial aspect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Chengde dialect, there are some words with unique formation and meaning, which highlight their regional culture. These words mainly originate from archaisms, vernacular,and borrowed words. The formation of the dialect vocabulary is in fl uenced by Chengde’s geography,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in these factors, conta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ethnicities is a signi fi cant driving force, and the in fl uence of Manchu dialect is the dominant element among the borrowed words. The collection and subsequent analysis of Chengde dialect further indicates that, dialec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regional culture, and that word borrowing is a common phenomenon when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come into contact. It also shows that the fusion of dialects is a norm, as inter-cultural tolerance and harmony is a key part of the humanism in China.
Chengde dialect; vocabulary; language contact; Manchu dialect; feature
H172.1
A
2095-3763(2017)-0099-07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14
2016-12-19
张颖(1958— )女,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词汇、语法学;关志英(1985— )新疆伊犁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锡伯语、满语。
河北省文化厅文化艺术科学课题(HBWY2014—Y—G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