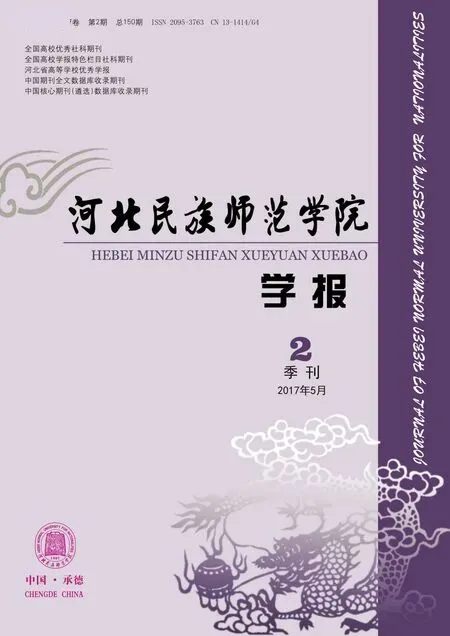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
——西田几多郎的时间阐释
2017-03-08赵淼
赵 淼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100872)
【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
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
——西田几多郎的时间阐释
赵 淼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100872)
主持人语:谈到日本的哲学与思想,西田几多郎和中江兆民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可以说西田哲学的出现,成为日本近代哲学成为哲学的标志,以西田为中心的京都学派,持续影响着整个日本近现代哲学的研究。而中江兆民作为明治初期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与理念,对于促成日本近代议会制的诞生功不可没。本期两篇论文,都是国内本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呈现当代我国学界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视角,值得大家一读。(中国人民大学林美茂教授)
本文按照西田哲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西田哲学中的时间阐释。中期西田选定时间作为其“场所”逻辑体系化中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分析说明了时间在西田哲学中作为“场所”而具有的媒介作用,极其在中期与后期哲学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本文还在批判哲学的视域下解析了西田的时间阐释对西方哲学史上几种重要时间观的批判。西田时间阐释中的特点是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使得从中期西田到后期西田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是西田“场所”逻辑体系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西田哲学在实现对西方哲学学说和立场的超越时做出的重要创见。
西田;时间;场所;媒介
一、关于“场所”“媒介”与“时间”的说明
向来讨论西田哲学时,我们几乎一致认为,中期①对于西田哲学分期,学界没有定论,两期说、三期说、四期说等都同时存在。本文沿用三期说,将西田哲学分为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早期的西田哲学初具理论形态但不够完善,并较多依赖于西方哲学的现成理论形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善的研究》(1911年)、《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1917年)。中期的西田哲学,以1926年提出“场所逻辑”为标志,这时西田哲学的理论已成熟,与德国唯心主义等西方哲学体系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从作用者到观看者》(1927年)、《一般者的自觉体系》(1929年)、《无的自觉限定》(1932年)。后期西田哲学从“从自我看世界的立场”转为“从世界看世界的立场”,从“历史现实”出发,建立了“辩证法世界”的逻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哲学的根本问题》(1932年)、《哲学的根本问题续编》(1934年)、《哲学论文集》一~七(1935~1946)。提出的“场所”逻辑代表了其学说最核心的部分。单就“场所”逻辑的内核,即对于“场所逻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或许只需定位到中期第一主著《从作用者向观者》,特别是其中“场所”一文就能得出初步的答案。西田提出“场所”逻辑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上的。当我们思考如何通过判断认识实在,即作为实在的“存在”与作为判断中系词的“存在”有什么关系时,我们才得以踏入所谓“场所”逻辑的领域。西田所谓的场所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实在性的、先验的“意识场域(意識の野)”②关于“场所”的涵义、先验性、实在性等问题,请参照西田中期第一主著《从作用者向观者》(働くものから見るものへ)。,逻辑是在作为实在的“场所”中产生的,从实在的包含性出发,逻辑本身就是实在的被包含者,而实在则是逻辑的能包含者,因此,逻辑判断中的系词“存在”必须代表某种包摄关系。进一步思考发现,这种实在的包含性首先带来的是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所谓主语逻辑的反转,即变成一种西田哲学中特有的“述语逻辑”。此时西田的想法可以说是通过扩展逻辑的范围来增强逻辑在言说和认知实在时的有效性。在后期的《哲学论文集 三》的“序”中,西田对此进行了总结式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始终是主语的逻辑。但在这种逻辑下无法思想所谓的自我,自我是不能被对象化的事物。但我们却思想着我们的自我。这里必须存在着某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我称它为述语逻辑。我们的自我作为意识的统一,不能被思想为主语性的,作为意识场域的自我限定,毋宁说它是场所性的。”(NKZ9,4)①*NKZ = <西田幾多郎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9。
“通过一反亚里士多德的主语逻辑和康德的对象逻辑,我们思想到最根本的、最具体的一般者,也可以思想到我们自我的作用。”(NKZ9,5)
西田认为能够抵达实在的判断并非形式逻辑的判断,而是“包摄判断”。即并不仅仅将述语作为对主语的述说,而将其看为主语内存于其中的场所,亦即将判断视为“特殊者作为主语而包含在一般性的述语之中”(NKZ4:240)。从逻辑的方面来看,就必须从这个问题入手,即“作为实在的‘存在’与作为系词的‘存在’有什么联系”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入手,西田对一般者进行了思索。他认为“作为系词的‘存在’(ある)与作为实在(存在)的‘存在’(ある)当然应该要区别开的,但既然‘物存在’也是一个判断,那么在两者深层的根底中,必定有某种相通的东西。”(NKZ4:229)这种东西他认为应该是“具体的一般者”。
所谓“具体的一般者”可以视为与“抽象的一般者”相区别的概念。在作为判断之根底的同时,具体的一般者本身是超越和包摄判断的。如果从作为“有限的场所”的“抽象一般者”来看包摄判断,便无法从矛盾中解脱出来。只要场所是“有限的场所”、一般者是“抽象的一般者”,那么必然还有更为一般的一般者作为其场所。总之,在“抽象的一般者”层面,无论如何都无法使判断统一于真正的实在。因此,能够将判断中的“存在”与真实的“存在”统一起来的东西必须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具体的一般者”,顾名思义它必须既是具体的东西,又是一般的东西。西田说“真正的一般者,必须是具体的一般者”,它是超越了判断并将判断包含其中,同时又蕴含于判断的根底的东西,并且它将逻辑判断产生的矛盾也一并包含其中,它本身必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而逻辑判断则是它自身的分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场所”的说法代表了“具体的一般者”的包容性,“具体的一般者”就是指场所本身。所谓“具体的一般者”也就可以看成是对早期提出的“纯粹经验”在“特殊”与“一般”意义上的指称。实际上,按照西田的想法,真正的判断的主语只能是纯粹经验,而判断则产生于纯粹经验的合理化。②参见NKZ 4,<働くもの>。“经验自身成为主语是经验作为自我同一的具体的一般者,通过限定己自身,在己自身之中使判断成立。”(NKZ4:185)
西田所说的“述语逻辑”显然不只是不断内向地扩大主观面的包摄范围的逻辑,如果单凭这种包摄方式仍然是无法真正抵达实在的,这是由于在判断内部的“主语”与“述语”之间存在着间隙。在“述语逻辑”的基础上,要弥合主语与述语之间的间隙,使之统一于实在,还需要用更为深刻的逻辑进行阐明,即在判断的根底中必须存在着用以沟通两者的媒介。西田说:
“在包摄判断中,特殊者作为主语而包含在一般性的述语中,但在能为主语而不能为述语的基体③“基体”,国内一般译为载体,是西田借用亚里士多德υ π ο κ ε ι μ ε ν ο ν(hupokeimenon)概念,用以表示指超越一切作用的作用本身,是一切作用根底中的“我本身”,是未进入一切作用中的东西,同时是“知道自己”或“观看自己”的东西,西田对亚里士多德的基体进行了柏拉图式的还原,将基体或承载者与场所或处所联系在了一起。日本学者藤田正胜对此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基体”是从早期“自觉”(<自覚に於ける直観と反省>)立场到中期“场所”逻辑之间的过渡性概念,“基体”是“场所”的前身。参见NKZ 5,<内部知覚について>、藤田正勝:<西田幾多郎の思索世界——純粋経験から世界認識へ>,東京:岩波書店,2011。中,一般者是包含在特殊者中的。但对物的判断中,成为其主语者也不仅是特殊者,相对其属性,它必须有一般性的意义。只是,能包含的一般者与被包含的特殊者之间存在着间隙的话,物与性质之间的关系就会确立,也会思想到如具超越性的物那种东西。”(NKZ4:240)
这段话除了对“具体的一般者”作出解释外,还指出,在判断中主语与述语间存在着间隙,而将这个间隙连接起来的只能是超越判断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超越性的基体,它并不进入到判断中来,却能够将判断中的主语和述语相连,它自身必须包含(是)沟通判断中主语和述语的媒介。这个媒介性的东西即是同时具有场所性的“具体的一般者”。换句话说,在包摄判断中,真正的“场所”作为能包者的同时必须包含(是)沟通能包者与被包者的媒介。这也许正是为什么西田要之后以“三段论逻辑”代替“述语逻辑”来说明“具体的一般者”连接主语和述语的作用的原因吧[1]。在论文“认知者”中,西田用三段论式的一般者来说明具体的一般者,认为具体的一般者是最完整形式的三段论式的一般者。“超越的述语面的限定”成了三段论式中“大语面的限定”,主语面成了三段论式中的小语面,而媒语则结合小语与大语来构成判断。这样的三段论式能更好地抵达作为具体的一般者的实在,而这种三段论式的判断的核心,实际上既不在小语也不在大语,而在于媒语。媒语充当了同时存在于主语和述语根底中的媒介的角色,这种媒介必须是具有包容性的、场所化的媒介。
“具体的一般者作为包含判断关系的东西,一方面思想到超越的主语,一方面思想到超越的述语,两个方向无限对立的同时,又必须是一个统一体,通过寻求两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统一,一是在主语面的方向上,一是在述语面的方向上,都能思想到相对立的两者的统一面。(将具体的一般者思想为三段论式(西田:推论式)的一般者的话,就成了大小两语面的对立。)”(NKZ4:353)
“三段论式的一般者在媒语的形势下包含大小两语。小语和大语在相对立的两个方向上成为统一面,媒语被认为合于大语而包含小语时,大小两语被认为是媒语的两端,可以认为超越的述语面包含矛盾的统一。三段论式中最能看到具体的一般者的整个结构。”(NKZ:356)
以上略陈了西田提出场所和媒介的大意,接下来笔者进入对本文主题——时间问题的阐述。在这一小节,笔者首选简要说明西田为何选定时间作为其体系构建中的关键环节,时间是如何作为场所而具有媒介作用的。在下面两节中,将更为详细地论述本节的观点。
对于试图将宏深思想转换为逻辑化的哲学语言的西田来讲,并没有止步于经过艰辛思考而提出了“场所”逻辑,而是继续由“场所”为原点展开了哲学体系的构建。在分别以中期后两部主著和后期为代表的两次体系化的尝试中①就西田对其著作的定名来看,在“场所”逻辑提出后,至少有过两次体系化的尝试,可以说分别代表着中期和后期的思想。第一次是在《一般者的自觉体系》(1930年)时期。 西田的意图无疑是根据“场所”的思想来建立“一个哲学的体系”。由此可见,“场所”逻辑的提出并不是西田哲学的终点,而恰是“荆棘之路”的开始。第二次体系化的尝试,是在所谓的后期哲学阶段。1935年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一》的副标题是“迈向哲学体系的企图”。根据西田的自序,这本书是对1933年出版的《哲学的根本问题——行为的世界》以及在其续编中收录的论文“作为辩证法的一般者的世界”所陈述的思想的进一步追究,并且试着更细致地阐明历史实在的世界的构造。而《哲学的根本问题》一书则又是对中期的《无的自觉限定》,特别是其中“我与汝”这篇论文所陈述的思想给予逻辑的基础,补充其不完备之处。参考相关著作的“序”及“題解”(<西田哲学選集>第一卷,大橋良介 野家啟一編,東京:燈影舍,1998)。,怀抱着“现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西田将哲学思考的视角从“从自我来看世界”转变为了“从世界来看世界”。②参考相关著作的“序”及“題解”(<西田哲学選集>第一卷,大橋良介 編,東京:燈影舍,1998)。这其中自然有试图逐步摆脱外界对其“心理主义”“个体主义”或“唯我论”倾向的指责的因素,更有其自身希望转向更为开阔的话题探讨的动因。在第二次系统化中,西田已经完全摆脱了所谓“个体主义”或“唯我论”的质疑,他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起点,将视角完全放在了社会、历史和世界之中。然而这一系列话题的内在核心仍然不出中期哲学所奠定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第二次系统化不过是第一次系统化顺理成章的发展,后期的西田哲学的根基仍然在中期的“场所”逻辑。
如果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将后期哲学看作中期“场所”逻辑的展开的话,那么在“场所”逻辑内部就应当包含了从中期哲学的以“自我”为出发点来看世界,到后期哲学的以“世界”为出发点来看世界的逻辑基础。而由于被观看者同是所谓的“现实世界”,这样的现实世界绝不是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凭空臆想出来的东西,在西田看来它就是“真实在”,代表了完整的实在性。因此,不论是“从自我来看世界”,还是“从世界来看世界”,所观看的世界必须是自我同一的东西,而不能是两样。显然,从逻辑上来看,所谓视角转变的关键之处实际上在于观看的出发点的转变,即从“自我”转向了“世界”。那么在“场所”逻辑的内核之中,是否存在着这种转变的基础和依据呢?西田在其体系构建中是通过那个环节来连通“自我”与“世界”的呢?正如前面已经阐述的那样,这种转变的内核在于从以述语为中心的“包摄判断”转向以媒语为中心的“三段论式判断”。而当“自我”与“世界”分别作为包摄逻辑的主语面和述语面、三段式逻辑的小语面和大语面时,沟通他们的媒语面是什么呢?中期西田给出的提案是——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期的后两部著作《一般者的自觉体系》和《无的自觉限定》中,时间成了其阐述的基础和重点。
二、逻辑化、合理化的时间:三段论式的媒语
为何选择了时间作为沟通自我与世界的逻辑媒介呢?笔者认为,这种建构至少来自如下三层理由:
1.着眼于现实世界;对人生、生死问题的关注;
2.时间既抽象又具体,具有变化性;
3.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时间可以被空间化、“场所化”。
从《善的研究》开始,人生问题就被放在了西田思索的中心位置。正如他所说:“我所以特别将本书命名为《善的研究》,是由于在本书中,尽管哲学性的研究占据了前半部分,但人生的问题毕竟还是中心和终结。”(NKZ1:3-4)人生的诸多烦恼之中,捆锁西田最深的恐怕还是生死问题。亲人的相继早逝使之饱受人生无常之苦,这种生死之际对心灵的震动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哲学思考。因此他曾感叹:“哲学源于我们自身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哲学的动机不在于‘惊诧’,而必然是源自深刻的人生的悲哀。”(NKZ6:116)人是有时限的生物,横亘在人生之中的是无情的时间之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对于个人来说,时间是与人生相伴相生的,那么对于现实世界呢?从《无的自觉限定》开始,西田就渐渐转入对“现实世界是什么”的思考,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这个阶段的思考仍然没有脱离从自我来看世界的立场,这个问题的思考无疑是晚期西田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与中期哲学不同之处在于,从《哲学的根本问题续篇》开始,他就完全站在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立场上进行哲学思索了。对于西田来说,现实世界以两种形态同时出现,它既是存在于时间之流中的历史性的世界,同时也必须是与我们人生活动合而为一的敞开的世界。作为历史性的世界,它是我们所观看到的,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发展的世界,其社会性与历史性共存;而作为与我们人生活动合而为一的现实世界,它“不仅是与我们对立的,而必然是我们在此中诞生、在此中活动、在此中死亡的世界。”(NKZ7:217)存在这两个层面的现实世界,是一方面处于历史长河之中,另一方面又包含了我们的个人历史的辩证法的世界。同时在个人和世界的根底中活动的东西是时间。
此外,时间的变化性决定了它有媒介作用。并且时间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它作为具体的一般者是真正的实在,而作为抽象的一般者又成为逻辑判断中的成分,它同时存在于实在和逻辑的根底之中。西田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认知者”一文中,他对由时间的变化性、抽象性和具体性所决定的作为媒介的可能性有这样的阐述,
“包含非合理者的、称为一般者的变化者,作为三段论式的一般者被看见。其媒语面在大语面上被限定,而与小语面接触的矛盾的统一面确立时,就能看到时间的世界。而且这种限定确立时,变化的东西得以被思想。作为三段论式的一般者而被思想的变化者的内容无限丰富时,种种时间的内容得以被思想。从大语面来看它的话,通过最为抽象的一般者被限定的媒语面即所谓时间,它包含了一切变化的东西。”(NKZ4:358-359)
但他同时指出:
“单纯在大语面上限定的东西无非是抽象的概念,作为大语面的限定的话,还不是真正的变化者,随着媒语面从小语面上限定,真正的变化者才得以被思想,才看见种种内容的时间,即通过所谓时间不能限定的东西,所谓时间之外的东西得以被思想。”(NKZ4:359)
这里所说的时间之外的东西,即非抽象性的时间的东西,其中也包含了空间性的内容。
真正的时间作为非连续的连续,它必须是可以被空间化、场所化的东西,这个观点在其有关时间的阐述中反复提到。西田认为,作为一切绝对无的自觉限定之中的东西,都是在直线性与圆环性两种意义上来限定己自身。时间的限定是一瞬一瞬消失的同时而又一瞬一瞬生起的非连续的连续,时间的运动是线性的辩证法的运动。“将时间的瞬间作为极限点来思想,总得来说就是时间的空间化”(NKZ8:109)。但时间并非只是直线性的,当时间圆环性地限定己自身时,是以己自身为中心辩证法地扩大己自身的运动。正如西田所举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绝对无的场所”看成类似于帕斯卡尔所说的那种“无边际而处处为中心的无限大的球(une sphere infinite dont le centre est partout, la circonference nulle part)”(NKZ6:187-188)的话,那么它可以看成包含了无数的围绕各自中心展开的圆球。将它化简为平面的模型,则是在无限大的平面中(无边际而有中心的无限大的圆)中包含了无数围绕各自中心展开的圆。这些无数的中心就是我们无数的自我。这样的自我是将“过现未”包含在内的空间性的自我,而当它投射在意识的所思面时就成了时间性的“现在”。
上述三个理由层面,可以看做西田时间观的逻辑部分,它是对在更深的根底上非合理的实在进行逻辑化、合理化之后的形态。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中期西田的为例,将自我、时间和世界三者代入一个三段论式中来解读一下。按照西田的想法,在这个三段论式中,作为大语面的是“世界”;作为媒语面的是“时间”;作为小语面的“自我”(真的自我、人格)。我们原引中期西田的表述,得到这样的三段论式:
大语:所有存在物都存在于时间中(NKZ4:329)。
小语:时间在我之中(NKZ6:187)。
结论:所有存在物都存在于我之中。
这个三段论式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成了:
大语:世界存在于时间之中。
小语:时间存在于自我之中。
结论:世界存在于自我之中。
在这个三段式中,大语面的时间在抽象的意义上被限定,小语的自我中包含不能被时间限定的东西,即非时间的东西。对于这个三段论式,笔者给出下述说明:
由于如西田所说的那样,中期西田是以自我的眼光来看世界,其中《无的自觉限定》一书是由内层来看外层,《一般者的自觉限定》是由外层来看内层。在《一般者的自觉体系》中,为了便于将西方哲学既有的思考方式,特别是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的“自然界”与“意识界”统一于他的“场所”逻辑之下,西田将“具体的一般者”分为“判断的一般者”“自觉的一般者”与“睿智的一般者”三个阶段,分别由外向内地对应于“自然界”“意识界”和“睿智的世界”,在最接近根底的睿智的世界中仍然存在Noesis(能思)与Noema(所思)的对立。西田认为,以往的哲学所谈论的都是Noema层面而未及Noesis层面,因此,作为对以往哲学的反省和超越,西田自然而然地着眼于对Noesis层面的探索。在《无的自觉限定》中,在阐述完“何为无的自觉限定”的问题之后,就转入对时间问题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Noema层面的必要内容是时间,在Noema层面“所有的存在物皆存在于时间中,实在必须是时间性的”(NKZ 6:P7),因此,只有通过对时间的形而上学意义,即时间与作为基础的“无的自觉限定”的关系的研究,才可以进一步完善其哲学的体系化内容。这一点在论文“永远的现在的自我限定”和“时间及非时间”以及后续论文的补充中十分清楚。
西田的时间阐释是基于“场所”逻辑和“一般者的自觉限定”的立场而确立的,在西田对时间性的阐述中,有几种基于不同层次的一般者的时间观,笔者根据中期西田的阐述整理出如下三个层次,并且,西田所说的时间的种种形态在他的三层世界结构中的位置或许应该是这样的:
1.在自然世界,我们所观看到的时间是一种“从无限的过去向无限的未来行进的无限的流,是直线进行的。”(NKZ6:182)
2.在意识界从自觉的立场出发,我们会观看到那种“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之流并非真正的时间。虽然我们仍然能够意识到过去、现在、未来(简称“过现未”)的时间之流,但我们已经能够超越自然世界的时间之流去思想它们。用西田的话说就是,“不是我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在我之中。”(NKZ6:187)西田对“过现未”的讨论中,首先是截断时间之流的过去、未来两端,而聚焦于“现在”来看,从而回到“自觉”的立场。因为无论如何,“从过去到现在是不能被限定的,只能通过现在限定现在自身来限定过去和未来。没有现在就没有时间”(NKZ6:185),“现在”是时间得以存在的根基。但这样的想法还不是在“自我观看己自身”的“自觉”的立场上来看待时间。我们深入“自觉”的立场来观看时,时间之流被看做是自我对自身的限定,因此是包含在自我之中的。我们观看到的是包含“过现未”的“瞬间”。
3.然而,“现在”事实上是无法捕捉的,时间在现在之中否定时间本身,时间被包含在某种意义中来思考便不是时间了,“时间的进行首先是行出包含者之外。时间的尖端一瞬一瞬地消失,在这里,时间永远无法返回,在这里,现在是无法被捕捉的”(NKZ6:183)。因此,在睿智的世界,我们观察到的是超越和包容了自他对立的时间。它是将无数包含“过现未”的瞬间包含在内的非连续的连续,即既有直线性限定的一面,又有圆环性限定的一面。西田认为,真正的时间并不是单纯的连续。时间的连续性并不表示每一瞬间不具有各自的唯一性,而是说瞬间与瞬间相互限定的矛盾的统一。
上述时间的形态,各自作为不同层次的一般者的自我限定的内容出现。如前所述,时间的变化性、抽象性和具体性决定了它能够作为判断中的媒语面出现。
大语:世界存在于时间之中。
小语:时间存在于自我之中。
结论:世界存在于自我之中。
这个三段式整体作为具体的一般者的完全形式,其时间的形态涵盖了上述三个层面。其中,大语面所表现的是自然界的层面;小语面表现的是自觉的层面;而结论所展现的则是睿智的世界层面。但上述的三种时间的形态,都只能看做Noema方向上被逻辑化、合理化之后的时间形态。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个三段论式中,世界作为“所有存在物”的集合,是Noema方向上的“有”,进一步讲,在西田哲学中,世界作为统一体,不仅意味着“许多事物成为一个”,而应该直接就是“多即一,一即多”的存在。而相对于“世界”,这里的“自我”则是自觉层面上的自我(真的自我①区别于“意识我”,西田所说的“真的自我”是“意识者”本身,他是超越(无数)意识我、包含(无数)意识我的“我自身”,在《善的研究》中,西田将这种“真的自我”看做一种“统一力”。),是Noema方向上的“无”。两者同被结论包含,但结论仍然只是“绝对无”②区别于与“有”相对的“无”,西田将包含有无的对立统一的“场所”称为“绝对无”。在Noema方向上的表现。至于如何认识实在在Noesis方向上的内容,中期西田诉诸“行为的一般者”,在后期哲学中发展为“行为的直观”的立场。虽然上述只是笔者根据西田的阐述、为直观起见而举的一个列子,世界、时间、自我的包摄关系并不只有这样一个方向,但从这个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时间作为逻辑媒介的合理性,还可以看出中期西田以自我的立场看世界的合理性②。
三、时间的实在性:绝对无的场所的自我限定
上述将时间作为判断中的媒语面的观点是从逻辑意义上提出的,早期西田并没有特别重视对时间性的阐述,但在中期西田中这是作为基础的重点。从中期“场所”逻辑提出之后,特别是论文“睿智的世界”中从批判哲学的视角、以三重世界的构造消解了传统哲学中的自然界与意识界的二元对立之后,西田在同一阶段转向“行为的一般者”与“表现的一般者”的讨论。自此,诸如“自然界”与“意识界”这样的传统二元对立,在西田哲学中几乎不再成为主要的论题,取而代之的是在更为接近实在的程度上,对意识底层的“睿智的世界”中Noesis面与Noema面的对立统一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中期发展成对于自他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在后期则发展为“行为的直观”与“辩证法的世界”的立场。
按照西田的看法,包括判断在内的一切对象性的认识都是对于实在的合理化,在实在的最深层根底中反而是非合理的东西。“合理化的东西无非是自我在自我之内映照自我的过程。”(NKZ6:124)因此,上述成为判断中媒语面的时间,无非是时间自身的自我限定、无限定者的限定的结果。真正的时间在其自身中还必须包含否定的、非合理的一面,并且这种非合理的一面深藏于Noesis的根底之中。时间的实在性在包含对自身的肯定的同时,必然包含对自身的否定。在西田哲学中,时间的实在性指的是:时间的成立(合理化)是绝对无的场所的自我限定,是无限定者的限定,是时间限定己自身的自我限定,而时间的根底必须是包含“有”(肯定)与“无”(否定)的正反两面的“绝对无的场所”。在这个立场中,时间性与非时间性的对立代表了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对立,同时也代表了Noema与Noesis的对立,而成为中期西田思考“绝对无”的Noesis面与Noema面的包摄关系时所借助的概念。与此同时,西田还给出了“时间——爱”的结构来阐明“绝对无”包摄下的Noesis-Noema的结构,通过这一结构的建立,为随后的自他关系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在Noema层面我们观看到的是不同层次和形态的时间。而在Noesis层面起作用的则是超越且包含时间的东西,关于它的内容,我们只能用能动性的东西来描述它,在《从作用者向观者》和《一般者的自觉体系》中,西田用来描述它是的“知”,而在《无的自觉体系》中,西田用了情态性的“爱”来阐述。在“场所”逻辑中,“认知”意味着“包含”即认知者包含被认知者。在《无的自觉限定》中,西田将“知”的意义赋予了作为在Noesis面进行限定的“爱”。他认为那些不能被知识性地认知的、所谓非合理的东西反而可以通过“爱”来认知,“爱”某个东西就意味着“认知”它,因为正如奥古斯丁所说,“我们不仅知道己自身,还爱己自身,我们不可能爱不知道的东西”(NKZ6:193)。从这个意义出发,所谓“自爱”就意味着“自觉”。
“可以认为所谓对象性的限定的东西已经在我们的自觉中,在某种意义上被认知。我们在自爱中对象性地爱着无,寻求不能知识性地认知的东西。并且被寻求者就是寻求者,被爱者就是爱者,从这里出发,自爱得以确立,作为无限定无自身的、我们真正的自觉被思想到。”(NKZ6:194)
与Noema的方向上以合理化的时间作为判断中的媒语面相对的是,在Noesis的方向上西田强调“爱”的“无媒介地自我限定”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爱”是“非时间性”的。他认为,“爱作为无的限定是飞跃的统一”(NKZ6:277)。
“我所说的场所限定场所自身就是自己积极地爱自己。因此自爱作为场所自身无媒介地自我限定,绝对的非合理得以可能,我们的自我通过自爱非合理地限定己自身。”(NKZ6,194)
爱的限定的另一个特定是它对自我(时间)①在中期西田看来,自我对于时间性的“现在”是先行的必要条件,“通过现在限定现在自身并不能使自我存在,在自我限定己自身的情况下,现在才存在。”参见<永遠の今の自己限定>,NKZ 6。的否定性。与欲望不同,真正的爱“是通过否定己自身来肯定己自身,他者通过自我之死而生”(NKZ6:288)②西田所说的“爱”并不意味着欲求的满足。他所说的爱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他认为真正的爱是自我是通过否定己自身而得到喜乐。只要含有些许自我欲求的满足的意味,就不能说是单纯的爱了。通过否定自我而找到自我之处,才是真正的爱。参见<自愛と他愛及び弁証法>,NKZ 6。
真正的时间是“现在限定现在自身”,而根底上则是无的自觉限定。时间与爱的关系在根底上就是“现在”与“爱”的关系。“现在限定现在自身被思想之处,既有时间性的意味,同时又必须有非时间性的意味”(NKZ6:269)。时间是绝对无的noema方向上的限定,而爱是绝对无的noesis的限定。①参见NKZ 6,<永遠の今の自己限定>。爱与时间分别在Noesis与Noema面限定,正因如此,爱的空间性中就包含了时间性。“在爱的自我限定中,我们接触到永远的现在(西田:永远の今nunc aeternum)的内容”(NKZ6:207)。在论文“时间与非时间”中,西田提到:“时间作为永远的现在的自我限定而成立,永远的现在的自我限定必须是绝对的爱那样的东西。时间的限定的根底必须有超越时间的东西,且必须是我与汝的关系。”(NKZ6:237)
因此,在随后的三篇论文“自爱与他爱及辩证法”“自由意志”“我与汝”中,他以这种表示时间性与非时间性对立统一的“时间-爱”的逻辑结构对“自-他”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在“自爱与他爱及辩证法”中,西田已经将现实世界表述为“历史的实在”,与从时间性的一面扩展出的历史性辩证统一的是由空间性的“爱”扩展出的社会性,这两方面是绝对无在Noesis与Noema方向的自我限定,是大的时间与空间。在历史、社会的视野下,各人的自我即转变为与他者的自我对等的人格,通过自爱与他爱的辩证关系社会得以确立。不仅如此,在各人的自我中本身就包含了人格性的社会,“我们的心之内是一个人格的社会。”(NKZ6:289)正因如此,个人的人格统一有着社会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人格统一的“真正的自由意志并非脱离现实的无内容的任意的意志”(NKZ6:297)。在接下来的论文“自由意志”中,西田对作为人格统一的自由意志进行了详细论述,真正的人格统一必须是非连续的连续。而在论文“我与汝”中,西田对自我、他者、历史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这些论述都是以这种“时间-爱”的逻辑结构为基础而确立的。
中期“从自我的立场看世界”下的“自-他”关系在后期“从世界的立场看世界”的视角下实际转变为一种“物-物”(个物与个物)关系。后期西田的立场可以看成在两个方面并行地发展,一方面是从表象出发圆环式的“辩证法的世界”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是从行为和直观出发的直线式的“行为的直观”的立场。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行为的直观成为辩证法的世界的根底,只有通过“行为的直观”,“辩证法的世界”才能够实现“自我同一”。在论文“行为的直观的立场”中,作为该立场的引入,西田亦首先对时间、空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法的表述。与中期不同的是,西田在后期更加强调媒介的意义。在“物-物”的辩证法的世界中,媒介指的是“物与物的相互关系”②参见NKZ 8,<行為的直観の立場>。,只有非连续的连续才能作为媒介而使物与物之间建立起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因为,如果媒介者是连续的话,物与物就是同一个,便没有相互作用可言,而如果媒介者是单纯的无,那么物与物就是单纯的非连续,完全无关系的东西也是不能相互作用的。③参见NKZ 8,<行為的直観の立場>。因此,真正的媒介必须是“非连续的连续”。
时间的场所化使时间通过否定自身而具有“非连续的连续”的形态。自然意义上直线性的、连续性的时间之所以能够成为判断中的媒语,是由于在它的根底中是圆环性的、空间性的场所。在绝对无的自我限定下的“时间-非时间”的结构才是“非连续的连续”式的媒介。如果时间不能够被场所化,那么时间就不能作为个物与个物、自我与他者的媒介。这正如西田所说,
“时间通过否定时间自身而成为真正的时间,空间通过否定空间自身而成为空间。内即外、外即内,主观即客观、客观即主观之处,时间与空间是自我同一的,作为辩证法的自我同一的相反两面,实在的时间及空间得以确立。时间的自我否定的肯定是空间,空间的自我否定的肯定是时间。”(NKZ8:112)
“空间不能离开时间存在,时间也不能离开空间存在。”(NKZ8:115-116)
中期西田在“自-他”关系的表述中,以自我限定意义上的“时间”作为媒介,而在后期作为表象的“辩证法的世界”中,“物-物”关系的媒介者必须是自我(时间)否定式的存在,是空间性的场所,而时间作为空间性的场所的自我限定,退居到了相对化的位置。但在“行为的直观”的立场上时间直接就是媒介者。这是由于在“行为的直观”的立场上时间与空间直接同一的缘故。所谓行为是在“我作用于物,物作用于我”的相互作用意义上来讲的,真正的现实的世界是“空间即时间,时间即空间”的矛盾的自我同一的行为的直观的世界。
“行为的立场是内即外、外即内,时间性即空间性,空间性即时间性的。并且我们通过行为观看物,物限定我的同时,我限定物。这就是行为的直观。”(NKZ8:131)
在这一立场下,西田强调“我们真正的自我是行为的自我,…只有行为的自我是真正时间性的东西。”(NKZ8:119)在行为的直观的立场下,时间就是自我。①参见NKZ 8,<行為的直観の立場>。
四、批判哲学视角下的时间阐释
如前所述,中期西田对“时间”问题的引入是在“场所”逻辑已然提出后、在哲学体系构建中作为探讨自我与世界、自他关系等内容的基础而提出的。因此,在看待西田的时间阐释时,必须将它放在“场所”逻辑及相关话题之下来探讨,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不仅如此,细心阅读不难发现,从批判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中期西田乃至早期著作也是恰当和必要的。这是因为从《自觉中的直观与反省》阶段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着手,西田在中期进入了对欧陆哲学的全面批判。西田自身的许多观点都是建立在对既有学说,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的重要立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此外,西田的逻辑展开以及概念的创造都有其对既有哲学立场的针对意义。比如在论文“睿智的世界”中,为了以他的“场所”逻辑为根基,对以往哲学中出现的种种认知体系进行重新评价,由此拓展“场所”逻辑的认知范围,他将具体的一般者区分为“判断的一般者”“自觉的一般者”和“睿智的一般者”三个层次,并由此划分出对应于三层一般者的世界。“通过将一般者区别为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思想到三种世界。”(NKZ5:123)首先,内在于“判断的一般者”中,并且为其所限定者,可以思想为所谓的“自然界”;其次,内在于“自觉的一般者”中,并为其所限定的东西,可以思想为“意识界”;再者,内在于“睿智的一般者”,并且为其所限定的东西,可以思想为“睿智的世界”。②参见NKZ 5,<叡智的世界>。这样的划分有其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的批判意义,西田将传统哲学中的“自然界”“意识界”用“具体的一般者”统一起来,并包含于最高层次的超越者“睿智的一般者”中。
在时间问题上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三种世界之间能够看到种种不同的时间形态。我们知道东西方思想传统各自孕育了各式各样的时间观,在传统西方哲学领域,自古希腊到近现代,几乎每个哲学学说都涉及对时间的认识,在众多时间观中有一类线性的时间观,以亚里士多德、牛顿等自然哲学家为代表。线性的时间观也可以说是物理的时间观,他们对时间的认识基于物理世界的运动变化的现象,在物理世界中时间成为物理运动的度量。虽然时间不是运动,但它是运动得以量化的东西,正是由于时间是关于前后运动的数量,因此它表现为从过去流向未来的直线。西田并没有否定西方传统中的任何一种时间观,而是将他们放在了其哲学体系中适当的位置。在西田哲学中,这一类自然时间观被看做“判断的一般者”所确立的“自然界”的时间形态。
与自然哲学家的线性时间观不同,奥古斯丁将时间看做神的心灵的延伸,因此过去、现在、未来都包含于神的心灵之中。持有类似时间观的还有中世纪神学家爱克哈特,他们的特点是认为过现未包含在人格性的一者之中。在论文“永远的现在的自我限定”的开篇,西田引述爱克哈特的时间观来阐释他所说的“永远的现在”。“永远的现在必须像爱克哈特所说的那样,无限的过去与无限的未来消弭在现在的一点之中。神在如同创造依始之日那样的现在,不断地创造世界,时间始终是崭新的,始终意味着结束。”(NKZ6:182)当然,与神学家将超越于人类的神作为一者不同,在西田看来,包含过现未的一者乃是我们人类的自我,自我总是与现在当下的一点直接相结合的,而过去与未来则必须通过现在与自我相接触。这类以人格性的一者包含过现未的时间观被看做“自觉的一般者”所确立的“意识界”的时间形态。
然而,实际上现在同过去与未来一样,是不可捕捉的,在更深处追寻时间的脚步的话,观看到的必然是空间化的时间。并且与物理空间不同,这里的空间反而是西田所说的绝对无的场所,因此在讨论西田的时间观时,我们在最深的程度上,必须将它看为场所化的绝对无的自我限定。但在这之前,我们仍然会观看到一种类似于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的世界那样的充满人格性的自我的场所。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把“绝对无的场所”看成类似于帕斯卡尔所说的那种“无边际而处处为中心的无限大的球”的话,那么它可以看成包含了无数的围绕各自中心展开的圆球。将它化简为平面的模型,则是在无限大的平面中(无边际而有中心的无限大的圆)中包含了无数围绕各自中心展开的圆。这些无数的中心就是我们无数的自我,如果将无数的自我放在更为广阔的的社会性的空间中来看,就成了我们无数的人格。同时,这样的人格又是包含“过现未”的一者。这样的时间观是“睿智世界”的时间观。
此外,我们还必须将西田的时间阐释纳入他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下来看待,在中期至后期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中,这部分内容反而是更为切实的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与西田有所联系的西方哲学家恐怕当属海德格尔。虽然西田对海德格尔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事实上根据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西田对这位比他年轻十九岁的德国哲学家的学说,评价完全是负面的)[2]232-25[3]526-547,但他们在人文意义上的时间阐释还是具有可比性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发表,而最初发现西田提到海德格尔是早在1924年与田边元的书信中(NKZ19:582)①书信2470。,此后在给他人的书信中也有一些评价,而在哲学论文集中为数不多的提及是在1932年出版的《无的自觉限定》以后。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西田对海德格尔时间观的不满之处在于海德格尔的时间是单纯面向未来、面向可能性的时间。正如他在论文“我的绝对无的自我限定”中评价到的那样:
“虽然可以认为海德格尔所谓的领会(西田:了解)是一种行为的限定,但它是失去自觉的行为,所谓领会(西田:了解)的世界无非仅仅是没有现在的、可能性时间的世界。”(NKZ6:165)
“海德格尔的此在(西田:存在)并非事实性的看见己自身,所谓领会(西田:了解)是不完全的自觉,所谓解释(西田:言表)是失去自我的东西的作用。真正的自我不仅仅是了解自己,还必须通过作用来事实性地认识己自身。”(NKZ6:168)
这些评价无疑是基于《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给出的。除了西田敏锐洞见到的差异性之外,事实上早期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与西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将人格性与时间性直接结合在了一起。西田将时间性的“永远的现在”与人格性的“自我”直接同一,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作为人之生存结构的“此在”的本真状态与朝向将来的时间性直接同一。不管怎样,他们的时间阐释都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观,他们共同批判的是那种以过现未的时间之流为形式的自然时间观、以超越性的上帝为主体的神学时间观、与人之生存无关的传统时间观,他们共同认为时间概念存在的意义和事实是在结合人之生存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西田并不完全否定既有的时间观念,而是将它们纳入到他“绝对无的场所”的自我限定(永远的现在的自我限定、无限定者的限定)所形成的种种体系中。他把这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观看做“生物学发展的想法的残滓”,在后期论文“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中,他对恩格尔斯的《反杜林论》中的时间观评价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叙述的那种宇宙发展的想法,其根本概念并没有脱离以我所说的永远的未来为基础的、生物学发展的想法的残滓。”(NKZ7:235)
自早期《善的研究》开始,西田就试图通过哲学上的研究来解答人生问题,中期“场所”逻辑提出后,“人生问题”在西田哲学中,以逻辑化的新形态展开,特别是在后期对“现实世界”的辩证法式的阐述中,西田亦尝试给出人之生存与现实世界之真实结构。其中与海德格尔的另一个不同是,西田虽然承认人之种种情态的合理性,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人之存在的本真状态。但西田对海德格尔的消极评价很大程度还上在于,他敏锐洞见到海德格尔这种面向将来的“此在”之生存结构的解析并不能更深层地解决实在和人生的问题,[3]526-54这其中必然也包含了两者共同关心的生死问题,毕竟人生的时间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生死问题。
以要言之,西田始终是以“绝对无的场所的自我限定”为根基来思考时间问题的,因此,人之生死问题在西田看来仍然属于一种“自我限定”。但这种限定不仅是个人对己自身的自我限定,还包括个人与环境、个人与他者之间辩证法地相互限定。在这种辩证法的一般者的限定是“一即多、多即一”的,它“不是像有机统一那种意味,而是‘一’通过绝对的自我否定而成为‘多’,‘多’通过绝对地否定己自身而成为‘一’。”(NKZ7:255-256)这种“辩证法的自我否定”的形态正是前面所说的“非连续的连续”,而在“辩证法的世界”中,“自-他”关系、个人之“生-死”以及“物-物”关系都是这种“辩证法的否定”的“非连续的连续”,只不过前两者表现出时间性,而后者表现出空间性,它们在“辩证法的世界”中都是媒介性的存在,正如西田所言:“辩证法的世界是以自我否定为媒介进行的”(NKZ7:256)。
五、结论
学者在研究西田哲学时,很少注意到作为西田哲学核心立场的“场所”逻辑中的“媒语逻辑”的面向。而黄文宏的论文“西田几多郎场所逻辑的内在转向”中注意到了“场所”逻辑的内部存在着由“述语逻辑”向“媒语逻辑”的转向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引起了笔者深深的兴趣,笔者除了在第一节沿着这个思路补充了上文未及详述的内容外,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了西田时间阐释中的特点——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并发现正是由于西田的时间观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使得从中期西田到后期西田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作为西田“场所”逻辑体系化的重要内容,在本文得以被详细分析。时间的场所化与媒介性不仅是西田“场所”逻辑体系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西田哲学在实现对西方哲学学说和立场的超越时做出的重要创见。
[1] 黄文宏.西田几多郎场所逻辑的内在转向[J].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010(1).
[2] Elmar Weinmayr: Thinking in Transition: Nishida Kitaro and Martin Heidegger(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ume 55, November 2 April 2005.
[3] Curtis A. Rigsby: Nishida’s Negative Assessment of Heidegger(Nishida on Heidegger,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0,Published online: 29 January 2010.
Time as Place and Media – Nishida Kitaro’s interpretation of time
ZHAO Miao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ime interpretation of Nishida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ishida philosophy itself. In the middle of his career, Nishida takes time as the key of his “place” logic system, and this paper has expounded its media function and its posi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Nishida’s middle and later philosophical idea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Nishida’s criticism on several important time view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philosophy. Nishida’s interpretation of time is characterized by time’s “place” and its role as media. Due to these two features, the development of Nishida’s philosophy from the middle stage to later stage has been more reasonable and logic. Time’s “place” and its role of media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Nishida’s logic system of “place”, they are also the important creations of Nishida’s philosophy in the transcending to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stances.
Nishida; time; place; media.
B313
A
2095-3763(2017)-0044-11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07
2016-12-26
赵淼(1984-),女,重庆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田哲学以及日本近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