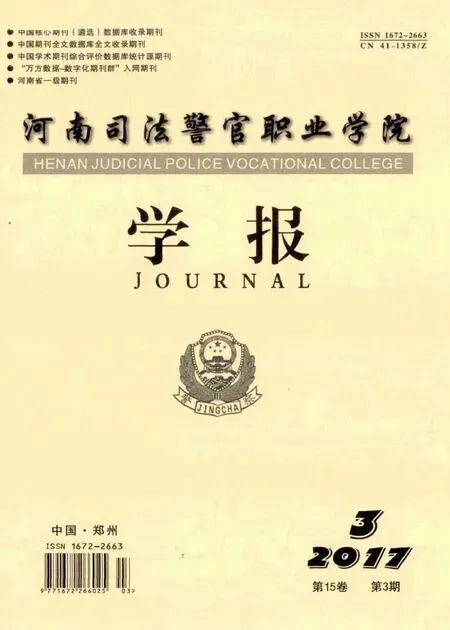美国公共信托理论的司法适用与启示
2017-03-08王灵波
王灵波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330022)
引言:公共信托资产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在美国,每个州都制定自己的规则来界定信托资产的范围。“长期以来,各个州有权界定受公共信托所保护的土地的范围,有权承认这些土地上的私人权利。”〔1〕因此,美国50个州的公共信托的资产范围,各不相同。受公共信托保护的资产,传统上仅限于以水为中心的区域。①即便是以水为中心的区域,公共信托的适用也有着逐步拓展的过程。最早,公共信托只适用于“潮汐水域”,即公共信托资产是潮汐覆盖的水域;但美国的内陆水系不受潮汐影响,故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案,将公共信托拓展适用于通航性水域中。莫诺湖案,加州最高法院又将公共信托拓展到非通航性水域。有关公共信托资产范围的变迁,参见王灵波:《美国自然资源公共信托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06页。以水为基础,公共信托的资产是否扩展,美国各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一,传统的消极保守的态度,坚守传统公共信托的范围,认为公共信托的资产,不可越过“水”的藩篱,拒绝承认任何其他资源上的现代信托利益。〔2〕之所以传统公共信托资产的范围,限于滩涂等水域,是因为那个时候水域上的渔业、通航和商业为当时社会的核心利益。其二,现代的激进扩展的态度,认为公共信托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其资产范围随着社会需求变迁而逐步拓展。〔3〕如果滩涂、河床等水域是人类在地球之上唯一所需求的资源,那么公共信托的极限则名正言顺就仅限于此。但现实是:人类需要所有的生态资源。水域上渔业、通航、商业的传统需求,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迫切需要。今天人类社会的迫切需求包括地下水保护、生物多样性、气候稳定、健康的森林、多产的土壤以及洪水的控制等等②在美国,很多州已将公共信托的资产范围,扩展到如地下水、湿地、干沙滩、公园以及非通航水道等新的资产。具体案例,参见 Alexandra B.Klass,Modern Public Trust Principles:Recognizing Rights and Integrating Standards,82 Notre Dame Law Review 707-714(2006).,这些需求在19世纪是无法想象的。“公共信托的信托资产与其所服务的社会利益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者就像是公共信托法的连体双胞胎。当一者向前迈进时,另一者也必须向前。”〔4〕
运用公共信托理论保护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是美国自然资源法律保护中最具特色且极为成功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司法适用的前提:公共信托资产的界定
尽管将所有自然资源纳入信托资产的范围,有着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在具体的个案中,无论是政府还是法院,都只会孤立地评价每一个自然资源,以确定它是否值得受到公共信托的保护。因此,有必要提炼相关的要素来界定具体资源是否受公共信托保护。我们简要地梳理了公共信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提炼了六个不同的要素。在具体的个案中,这些要素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可以适用其中一个要素,也可以组合适用几个要素,来判定资产是否具有公共信托性质。根据这些要素进行判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类别的自然资源都值得作为信托资产予以保护。
(一)是否满足公共需求
公共信托并非深奥玄妙的学术用语,而是非常务实的理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公共信托在界定其资产范围时,非常正视公众的需求。公共需求不是静止的,政府以及法院必须不断更新他们对“公共需求”的理解,以确定公共信托适当的资产范围。如果不这样做,将会导致公共信托脱离社会的需要,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怀有敌意。公共信托作为普通法上的一项法律制度,本身也非“‘固定的或静止的’,而是可以被‘塑造和扩展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和公众的需求’”〔5〕。譬如,在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案①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案被萨克斯教授誉为现代公共信托制度的北极星,具体案情参见王灵波:《美国自然资源公共信托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5页。,界定信托资产的基本框架,就是围绕当时社会的公共需求。该案发生时,渔业、通航业和商业,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涉案海滨对于这三大支柱行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公众对这三大行业的需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涉案海滨是人民主权信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免受私主体的妨碍或干扰,判决“海滨上的通航水域及其下覆土地之所有权,是本州全体人民所关注的客体”〔6〕。由此确定了一个先例:凡一个自然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所关注的客体”,就要保证其作为公共信托的一个资产予以保护。
随着社会的变迁,今天人类社会的迫切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诸如生物多样性需求、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尚美艺术以及娱乐休闲等生态需求,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公共需求。公共需求的变化,也引起公共信托资产的逐步扩展。美国很多州,以公共需求作为界定因素,将公共信托的资产扩展到地下水、湿地、干沙滩、公园以及非通航水道等新的资产之中。〔7〕
(二)是否具有稀缺性
稀缺性意味着“可用的数量不能够满足全部的需要和欲望”〔8〕。因此,“稀缺性是对特定物进行特殊法律保护并防止该领域私有权绝对化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之一”〔9〕。认定传统的公共信托财产,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公共需求的因素,对于新的公共信托财产,则还需关注稀缺性的要素。譬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电磁波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应作为公共信托财产加以保护。〔10〕稀缺性也是推动印度最高法院将天然气储量纳入公共信托保护的决定因素。印度最高法院发现“印度天然气严重稀缺”,天然气供应不断减少,证明强制保护的政府干预措施是合理的。通过政府强制干预的保护措施,达到促进社会需求和代际权益,而这些是私人市场所忽视的。〔11〕当然,稀缺性的评判,并非以资源是否可再生、是否可消耗为标准。无制度壁垒的限制下,公众对特定资源的正当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该资源就应当可以界定为稀缺性资源。譬如,土壤和空气,虽然在数量上并不“稀缺”,但从质量上看,未受污染的土壤和空气,已经成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
(三)对特定资源的习惯使用是否达到合理期待的程度
第三个要素涉及的是公众对自然资源的习惯性使用或享受,是否达到自然资源的持续存在和丰富所需的合理期待的程度。公众习惯性长期使用,主要在空气、地表水和野生动物领域。诸如国家和州公园、避难所、纪念碑以及林地等公共土地,在制度设计上都是国有。随着时间推移,公众对这些公共土地存在习惯使用,这就产生将这些资源纳入信托资产予以保护的合理预期的问题。这一要素保障了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期望。譬如,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等传统案例,已确认海滨上的通航水域及其下覆土地,是公共信托资产。沿海滨的干沙区按照这种传统的理解不属于信托资产,但公众对这类干沙区享有习惯性的通行权,如果不保证公众对干沙区的习惯性通行权,那么确认海滨的公共信托利益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从符合习惯使用的角度,毗邻海滨的干沙区,也属于信托资产的范围。〔12〕
(四)是否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共同遗产
第四个要素考量特定的土地或资源是否具有独特的或不可替代的人民的“共同遗产”的特点。哈里森·邓宁教授(Harrison Dunning)认为公共信托体现了“涉及共同遗产的自然资源,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基本理念”〔13〕。不管是出于纯粹的美学,还是美学与价值观的结合,共同的遗产资源,一直被社会所推崇。绝大多数河流就是共同的遗产资源,符合这一要素。譬如,在莫诺湖案,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河流、湖泊、沼泽、滩涂都是州的“共同遗产”。〔14〕并将莫诺湖描述为“具有国家意义的风景和生态宝藏”〔15〕,授之以公共信托保护。此外,国家公园、古迹名胜、自然景区、沼泽峡谷、森林山脉、海滩河谷等都属于这种“具有国家意义的风景和生态宝藏”,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人民的共同遗产。①譬如,新泽西最高法院也以这种方式将州的干沙滩进行了分类,“海滩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参见Matthews v.Bay Head Improvement Assn.,471 A.2d p.364(1984).内华达州最高法院认为沃克湖(the Lake Walker)是信托资产,“公众希望这种独特的自然资源能被保存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叹于这巨大的闪闪发光的水体,威严地徜徉在干燥的山地沙漠之中”。参见 Mineral Cnty.V.Nev.Dep’t of Conservation&Nat.Resources,117 Nev.235,248(2001).正如查尔斯·威尔金森教授(Charles Wilkinson)所说:“公共土地案件中使用信托语言的增加,表明联邦土地的特殊价值,像其他已被信托所保护的资源一样,已逐渐不可磨灭地铭刻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16〕
(五)是否适宜于共同使用
第五个要素考察自然资源是否适宜于公众共同使用。罗马法以是否能为个人民事权利的客体,将物分为不可有物(res extrapatrimonium)和可有物(res inpatrimonium),不可有物是不得为个人所有之物,分为神法物和人法物,其中人法物又分为共有物(res communes)、公有物(res publicae)和公法人物(res universitatis)。②罗马法中,神法物分为神用物(res sacrae)、安魂物(res religiosae)和神护物(res sanctae),神法物受法律的特别保护,侵犯损坏的,要受严厉制裁。人法物中共用物(res communes)指供人类共同享用之物,公有物(res publicae)指供罗马人共同享用之物,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也有的是属于国家的私产。公法人物(res universitatis)最主要的是市政府的财产。参见周枏:《罗马法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重要的资源是由人类共同享用的“共有物”(res communes),如空气、海岸、海洋等。为人民的生存和福利计,自然法要求某些特定的资源能够供共同使用。早在公元535年,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就已规定:“根据自然法,所有这些东西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空气、流水、海洋及海岸。”〔17〕这种共同使用的权利逐渐演化为限制政府将这些资源进行私有化的信托的观念。
资源适宜于共同使用,也持有反向逻辑:资源也适宜于私人使用。因此,还需明确适宜于共同使用的资源上各权利的优先顺位。譬如,海岸是典型的适宜于共同使用的信托财产。1667年,马修·黑尔大法官(Chief Justice Matthew Hale)认为海岸区域中分三种不同的权利:“其一,私人权利或所有权(Jus Privatum);其二,王权(Jus Regium),这是国王作为最高统治者为公众安全和福利而管理王国领域内的资源之权力,本质上是一种警察权;其三,一般公众的共同使用权(Jus Publicum),公众的共同使用权不能被骚扰或妨碍,即Jus Privatum和Jus Regium要从属于Jus Publicum。”〔18〕随着19世纪已经开始区分国王作为个人的私人财产和国王作为国家的主权者之间的财产,由此公共信托之观念得以产生。
(六)对其他信托资产是否具有辅助功能
最后一个要素涉及的是对于已被公共信托所承认的信托资产,新的尚未被承认的资产是否具有辅助功能,对于具有辅助功能的资产,也应纳入公共信托保护。有些情况之下仅保护特定的信托资产,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还应当将公共信托拓展到支撑这些已被确定的信托资产的生态环境上来。譬如,公共信托传统上适用于通航性水域,而不能及于非通航性水域。但是,在莫诺湖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将公共信托扩展到非通航水域,因为这些非通航性水域(莫诺湖的5条补给源流)对涉案的通航水域(莫诺湖)具有辅助功能,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水文联系。③莫诺湖案,即全美奥杜邦协会诉高等法院案,涉及的是莫诺湖及其5条淡水补给流。莫诺湖具有通航性,其湖床、湖岸和湖水毫无疑问是公共信托财产,但是莫诺湖的5条淡水补给流并不具有可通航性。但这些补给流对莫诺湖具有“辅助功能”。所以,加州最高法院在莫诺湖案回答了之前任何公共信托案件都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公告信托是否适用于“通航水域之不可通航的补给流”。参见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v.Superior Court,33 Cal.3d p.719—721(1983).又如,野生动物是一个经典的信托资产,其任何形式的栖息之地(如森林、沼泽、草原等),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起着辅助作用,因此凡这类栖息地也应赋予公共信托保护。再如,大气在气候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大气健康对几乎所有的公认的传统公共信托资产的保护(如河床、通航水域、鱼类和野生动物),具有辅助作用。因此,大气也值得公共信托保护。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综上,所有经典类别的自然资源,都值得纳入到信托资产之中予以保护。人类需要大自然的一切。所有的这些要素,都能在萨克斯教授(Joseph Sax)提出的一个概念中找到基础。萨克斯教授认为公共信托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的“合理期待”,“合理期待”源于但不限于私人所有权。萨克斯教授说:“公共信托的核心思想是防止社会共同的期望,失去稳定。虽然社会共同的期望,并不像私人所有权一样,获得正式的认可,但社会共同的期望支撑着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受托人的义务应着眼于防止这些社会共同的期望,免受可避免的不稳定的破坏。”〔19〕
二、司法适用的基础:成文法时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及对普通法的坚守
任何信托的基石,在于司法的执行。“重申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一种必要方式是(允许公民)向法院起诉——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法官更加聪明,也不是因为诉讼过程特别迅速,而是因为法院是一个平等地倾听公民个体和社会团体与已经训练有素以至能够操纵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的高度组织化和负有经验的利益集团的场所。”〔20〕如果信托义务在法院中不可执行,受托人就可以在受益人的财产上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它就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进自己的独特的利益。法院必须有权执行受托义务,否则所谓的信托不过是一个“恳求的劝告”而已。
美国继受英国的教义,制定普通法。然而,随着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的展开,以及上世纪70年代环境法规的大量颁布,美国环境法已经进入了成文法时代。①1970年到1980年之间,是美国联邦法律的“爆炸”时期,创造了一个“联邦监管基础”的时代。此间,美国重要的联邦环境法律,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清洁空气修正案》(the Clean Air Amendments)、《联邦水污染控制法》(the 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联邦环境农药控制法》(Federal Environmental Pesticide Control Act)、《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饮用水安全法案》(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有毒物控制法》(the Toxic Substantives Control Act)、《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综合环境应对、赔偿责任法》(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See Alexandra B.Klass,Modern Public Trust Principles:Recognizing Rights and Integrating Standards,82 Notre Dame Law Review,720(2006).与普通法相比,成文法有很多优势。譬如,普通法中法院只是通过个案解决争议,这无法跟上生态资源保护的步伐。国家需要成文法制定统一和全面的法律标准,并需要一个行政框架来执行这些法律标准。因此,成文的环境法规,比普通法更精确而似乎更具有可执行性。然而,成文法本身及其执行也会失灵。②桑斯坦教授(Sunstein)在回答“规制是如何失灵的”时详细分析了制定法本身失灵以及制定法执行失灵的原因。参见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115页。在成文法时代,纷繁复杂的成文法规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记录创设了环境管制的迷宫。法院深陷于这迷宫中,无法发挥其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不能洞悉导致政府失灵的功能性障碍。由此看来,行政国家的兴起,导致伴随而来的是司法衰弱。法院只关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失误,而不去挑战行政机关对环境的实质性保护不足的实体性问题。法官为行政机关的程序失误所提供的救济,也是程序性的:通常要求行政机关重新研究、重新听证或重走一遍行政程序。
因此,成文法时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公共信托认为仍然需要法院坚守普通法下的司法功能。第一,基于公共信托的索赔范围,是宏观广泛的。如前述,公共信托要求政府将信托资产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信托责任。相反,成文的环境法规仅要求单个或少数管制机构,对特定的信托资产承担责任,这根本无法解决系统性机能障碍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第二,公共信托要求公务人员承担实体性受托义务,而不仅仅是履行程序性手续。实体性受托义务,着眼于对自然生态资产提供实际保护,而不管政府在资源管理中是否遵循了正确的程序。第三,公共信托要求政府承担对公众忠诚的义务。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掩盖之下,政府往往会做出政治性的或自利性的决定。忠诚义务就在于应对此问题。第四,公共信托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程序,不依赖于其作出的行政记录。因此,基于公共信托,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以及环境状况,进行广泛的审查。最后,公共信托可以为法院审查立法行为提供支持。绝大多数成文环境法规诉讼仅仅涉及法规执行的问题,但公共信托诉讼可以挑战法规本身是否违反法定的受托义务。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容后文详述。
三、司法适用的技术:尊重与控制之间的选择
司法之目的主要是警惕和监管政府处置公共信托的行为。这意味着法院必须谨慎划定对政府行为尊重和控制之间的边界,并在特定的案件中决定采取何种适当的措施。一方面,法院有时会明智地拒绝侵犯政府的特权,这可称为“司法抑制主义”;另一方面,法院必须行使对政府行为的审查的权力,这可称为“司法否决主义”。
(一)司法抑制:法院对政府行为的尊重
在司法抑制的情况下,法院应尊重政府分支中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1.对立法机关的尊重:避免“反多数难题”
就立法机关而言,比克尔教授认为:“司法审查是我们的体制中一股反多数主义的力量。”〔21〕立法机关是政府中最民主的分支,由少数的法官推翻立法机关的法律,会发生反多数的难题。“非选举的法官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怎么能够具有正当性呢?在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的案件中,一部由民主的法律制定机关合适地通过的法律,为什么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有权宣布它违宪呢?”〔22〕涉及分配自然资源的政府行为,司法干预和推翻立法行为,存在“反多数难题”,使得自然资源的配置陷于法官的“少数人暴政”的影响。因此,在马克思诉惠特尼案(Marks v.Whitney)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宣称,“在立法机关的智慧和权力范围内,决定立法机关作为受托人是否尽职履行其信托义务,公共信托使用方式是否被修改或消灭,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受法院的审查。正如约瑟夫·萨克斯教授(Joseph Sax)所说:“在公共信托领域,即便是最积极干预的法院,也没有兴趣取代立法机关,把自己作为制定资源政策的最终权威。”〔23〕法官也应视自己为“以自认的最佳方式继续发展国会已开始的制定法方案的合作者”〔24〕。因此,法院应该依据能够支持立法机关“所作所为”的最佳原则来解释制定法。
2.对行政机关的尊重:“谢弗林尊重”的适用
就行政机关而言,司法对行政的尊重指“当国会对某一法律条文的含义并无清楚说明,或国会的立法意图难以确定时,法院对于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职权范围内对该法令条文作出的合理的解释应给予充分的尊重”〔25〕。由于其主要形成于谢弗林案,因此该原则也被称为“谢弗林原则”或“谢弗林尊重”。①“谢弗林尊重”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主要审查国会是否就涉及的问题做过准确的说明,如有,则法院、行政机关服从于国会明确表示的意图;第二步,如果法律就相关问题沉默或较为模糊时,法院的作用在于判断行政机关的回答是否基于一种允许的法解释之下。有关谢弗林案的评论,具体参见高秦伟:《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第142—149页。“谢弗林是行政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判决,其后十年间引用和适用这一判决的案件超过了1000余件。”〔26〕“谢弗林尊重”原先只适用于行政法规对法律的解释,后适用于审查一切法律解释。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这种恭敬的姿态,在自然生态领域,其逻辑是环境问题属于行政机关的专长,而法院缺乏技术能力,法院无法深入考虑那些预先不适当地干预监管结果的政治因素。因此,“谢弗林尊重”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公共政策形成能力的尊重,而使行政机关更加自律。
总之,在司法抑制下,法院“不能轻易地宣布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法令违宪;最高法院应当维持州政府等地方官员的决策;应当支持联邦机构——尤其是各种联邦管制委员会(federal regulatory commission)——的规章命令”〔27〕。
(二)司法否决:法院对政府行为的控制
1.对立法行为的司法否决:“反多数难题”的新解
在一个完善的政府架构中,如果立法机关能真正代表和服务于公共利益,司法对立法的干预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当立法机关处置自然信托资产而受到外部的干预和影响时,法院的作用就变得举足轻重。为了使作为受益人的公民的公共信托权利能够被有效执行适用,如果立法机关的行为违反了信托的基本义务,司法机关就必须享有推翻立法行为的权力。譬如,在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案,1869年伊利诺斯州的立法机关通过《湖滨法》(the Lake Front Act),授予中央铁路公司“挪用、占有、使用和控制”密西根湖绝大部分港口的土地,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尊重立法机关,判决立法机关的这个转让决定是无效的。②有关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案的基本案情和评论,参见王灵波:《美国自然资源公共信托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5页。问题是司法否决立法行为,如何解决前述“反多数难题”?即法院推翻立法行为的合理基础在哪里?
首先,民主并非完美无瑕、毫无缺陷,立法机关容易受到外部的非正式的影响,公共信托作为一项技术,可以修补民主中已被感知到的缺陷。正如萨克斯教授所言:“自利且拥有强权的少数,总是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公共资源决策,拥有不正当的影响,导致立法和行政机关忽视广泛的公共利益。因此,法院的功能就是必须为松散的多数利益,在舆论已经唤醒之后,将适当的案件发回立法机关重审,以促进政治权力的平等。”〔28〕理想的世界中,立法机关作为公共信托的受托人,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共机构,最适宜由其来处置和管理公共信托财产。但是,民主是有缺陷的,“一定程度上,司法干预是促使立法机关达至这种理想,使公民得到最好的服务”〔29〕。
其次,公共信托虽是普通法的一项制度,但是其超越于普通法的传统观念,属于宪法上的一项制度,在位阶上高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故公共信托本身可以制约立法。公共信托作为“限制立法机关的隐含的宪法理论,这源自政府就共同遗产的自然资源,是如何运作的基本观念”〔30〕。公共信托,作为主权的一个属性,进入宪法那神圣的境界,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拒绝它。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宣称“在事关全体人民利益的财产之上,州不可放弃其信托”〔31〕而判决州立法机关转让密西根湖岸的行为无效。
最后,精英其实并非司法的准确特性,作为少数的法院推翻作为民选的立法决定,并不会陷入“反多数的困境”。反对司法否决的理由无非是司法机关是没有民主基础的精英制度。这一论据并非完全符合美国司法运行的现实。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作为最高联邦法院,只管辖很少的案件,但是美国的司法权分散在成千上万的联邦、州、市一级中,分散在初审、上诉审和最高审之中。而且,很多州法院的法官,事实上是由选举产生的(尽管联邦法院不是)。所以,“反多数困境”的论据是建立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立法机关是选举产生,司法机关是任命产生,司法推翻立法就是精英的少数反对民主的多数。既然这种假设的前提不存在,如果我们还将司法作为立法决定的橡皮图章,那么公共信托理论就变得没有牙齿。
此外,美国宪政制度建立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而非两个政府部门。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基本制衡,在政府中创造了一个至为重要的张力,它可以防止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残暴滥权。当这些政府部门之间的法律和政治紧张消失,民主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2.对行政决定的司法否决:“谢弗林尊重”的重塑
作为现实,司法对行政的尊重,有可能使得行政机关近乎没有任何监督。可以说,极端的尊重,是法律的一个畸变。司法的真正目的,就是在诉讼中辨别真伪。当法院因尊重一方当事人而不插手其行为的审查,司法程序的关键要素就消失了。鉴于行政机关经常通过复杂的科学技术掩盖其政治的和有偏见的决定,“谢弗林尊重”置法院于行政机关科学伪造下同谋玩家的地位,设法使行政决定逃避法院的质疑和审查。
因此,在公共信托中,为更好地保护受益人在信托资产上的利益,法官应该重塑“谢弗林尊重”原则。公共信托应借鉴私信托法领域所发展出来的那种尊重。在私信托法中,法院根除对任何一方的偏见,严格执行信托义务,坚持对信托资产的保护,禁止对信托资产进行投机和风险管理,要求受托人对受益人忠诚。一般而言,为了保障受托人能够代表受益人的利益,私信托法会赋予受托人享有一些自由裁量权,但“裁量之运用既可能是仁行,亦可能是暴政,既有正义,亦有非正义,既可能是通情达理,亦可能是任意专断”〔32〕。法院不能允许裁量权凌驾于受托人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之上,不允许裁量权能够被鲁莽或故意地滥用。
在公共信托领域,如果任一公共信托义务不能在法院中得以执行,它就不再是信托义务。公共信托义务确保政府消除偏见的可能、保持对受益人的忠诚、尽职尽责以及谨慎地管理公共信托资产。当行政机关违反这些义务时,法院应该撤销违法违规的政府决定。对此,法院必须修订“谢弗林尊重”原则,从而确定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真正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自然的信托资产。
四、司法适用的启示:构建我国自然资源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
造成公共信托自然资源的损害,要么是作为受托人的政府自身,要么是政府以外的第三方私主体。如果是政府行为侵害信托资源的,作为衡平法所有权人的普通公众,可以向法院起诉审查政府的行为;如果是第三方私主体造成公共信托资产损害的,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应承担向第三方提起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义务,政府怠于行使这项职责时,普通公民可以起诉政府不作为,也可以直接起诉造成生态损害的第三方。因此,涉及公共信托的诉讼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私主体起诉政府违反公共信托的诉讼;其二为私主体起诉其他私主体违反公共信托的诉讼;其三为政府起诉私主体违反公共信托的诉讼。〔33〕美国没有公私法划分,所以没有分别设置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是由普通法院一并处理涉及公共信托资源的纠纷。我国分别设置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因此有关自然资源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应该分为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设置原告资格,行政公益诉讼除原告资格的问题外,还包括法院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处分自然资源的行为的审查限度。
首先,原告资格是“接近正义的第一步”〔34〕,根据公告信托理论,应赋予普通公民提起有关自然资源领域的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是法院判决的前提,“无利益即无诉权”〔35〕。从现行法律的规定看,民事公益诉讼有限度地拓展了自然资源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就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起诉①参见《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2014年的行政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公益诉讼,但原告资格已从“法律上利害关系”②参见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2条。拓展到“利害关系”③参见《行政诉讼法》第25条。标准,一定程度上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上的可能。当下以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已是我国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走出的第一步。④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试点近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写入了这两部法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往前推进一步,直接赋予普通公民在自然资源保护上的原告资格,普通公民既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直接起诉损害自然资源的第三方私主体,也可以起诉政府部门怠于履行保护自然资源职责的不作为。“赋予全民公益诉讼的诉权不仅是对全民信托财产请求权的法律保护,更是抽象的全民概念得以具体化的表现。”〔36〕
其次,增强司法权威,加强法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法治原则要求,所有的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所有权利被侵害时都应能够得到救济。〔37〕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起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就体现了这一精神。行政诉讼正是落实这一精神的具体制度。与美国司法审查相比,我国行政诉讼无论是在受案范围还是审查程度上都有较大差距。其表现之一为立法机关的行为、行政规章、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的规定,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表现之二为对于可以审查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只能是间接的附带性审查。在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框架范围之内,我们认为应增强司法权威,加强法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环境问题很少是因一个孤立的原因所导致,也很少是仅仅由一个行政机关负责。法律一般规定由众多行政机关对自然资源进行碎片化管理,这些行政机关都有责任对保护自然资源承担责任。因此,为了解决制度层面上的管理不善,法院必须在制度范围、宏观视野上创新救济措施。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的司法救济措施,必须达到三项标准:(1)它促使政府官员履行其保护自然资源的义务;(2)它保证对自然资源提供实际保护和恢复;(3)它尊重行政机关在现行政治框架中的宪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