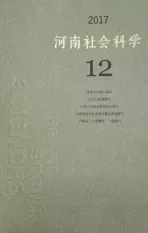道家与谦逊
2017-03-07曹峰,柳悦
曹 峰,柳 悦
(1.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推崇谦逊的传统,例如《逸周书·官人》云:“少言以行,恭俭以让,有知而言弗发,有施而□弗德,曰谦良者也。”[1]788《尚书·大禹谟》将“满招损,谦受益”[2]58视为天道。而《周易》的谦卦更是六十四卦中最美好的卦,没有任何缺陷,这种地位在六十四卦中是绝无仅有的。《谦·彖》云:“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2]47这是将“谦”视为天道、地道、鬼神以及人道共有的美德。即天地鬼神都以各种方式憎恶盈满,喜爱谦虚,人间的君子也是如此,最为谦卑的人,才是最尊贵的、光明的、无法超越的。其实,《易传》的中心话题就是在论述如何处于最佳的生存状态,而使自己不会处于危亡的境地,谦逊恰恰是保持最佳状态的最佳姿势。《荀子·宥坐》也一样,在这篇文章中,荀子借助孔子议论宥坐之器的故事,阐述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道理。最后总结出所谓“持满有道”的哲理,即“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3]520。
《韩诗外传》卷三以下内容把《易传》论谦与《荀子·宥坐》论谦结合了起来。“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则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4]318-319
道家重视谦逊,或者说谦逊就是道家的生活之道,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不需要做太多的说明。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一家不推崇谦逊,讨论谦逊的文字也极为丰富,然而,从理论上全面论述谦虚、谦逊、谦卑、谦下的重要性、必要性,就理论的深度、广度、高度而言,没有一家可以和道家相比。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道家生活之道,那么“谦”字最为合适。即便不使用“谦”字,道家许多论述的精神实质依然是“谦”。在道家这里,“谦”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有效的处世手段、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然而,道家的谦逊和儒家等其他各家的谦逊有何不同,道家为何重视谦逊,道家如何论述谦逊,道家如何实践谦逊?这里面蕴含着深厚的哲理,有必要做出学理上的探讨,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不仅有助于对传统道家义理、价值、意义的发掘,而且也有助于使道家文明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更强的生命力。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虽然提及道家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与谦逊有关,但都十分零散或流于表面,尚未见到过一篇从理论层面全面、系统研究道家与谦逊关系的论文。下面,笔者从整体性、平等性、关联性三个方面,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整体性视野下的谦逊
道家论述谦逊,虽然也视其为美德,但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的范围,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品性,而是放在道论中,在整体的、全局的世界观视野下,将“谦”看作“道”之作用的体现,看作与“道”相配合的最佳的存在方式。
道家的世界观,可以用“道生万物”“道物二分”来形容。这表明,在道家眼中,包括宇宙万物在内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形而上的本体的“道”和形而下的现象的“物”。“道”具有不同于万物的根本性特征,这些特征使“道”成为万物存在与运动的总根源、总依据和总动力,使“道”成为绝对的原理和永恒的存在。本体世界是独立的、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和不依赖于现象世界的存在。相反,现象世界则是有待的、有限的,依赖于本体世界才能得以产生、存在和运行。按照这一逻辑展开,事实上“道”与“物”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主宰与被主宰、本与末、一与多、统一与分散、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道”是使“万物”存在、运动、变化的主宰者,“万物”则仅是因“道”而得以存在、得以运动、得以变化的被主宰者。与“道”“物”关系相对应,在人间,则表现为作为“执道者”之代表“圣人”和“百姓”的主次本末关系。
在韩非子和一些黄老道家那里,这种理论构造确实可以为“一君万民”的君主专制体制服务。然而,有趣的是,这种理论构造却同时为谦逊的观念提供了理论的保障。就是说,道和万物之间、圣人和百姓之间虽然属于主次本末关系,使得万物和百姓不得不依附于道和圣人;然而,《老子》的重点却不在于此,《老子》要突出强调的是,道和圣人从不以生成者、主宰者自居,竭力要把对万物和百姓的控制和影响降到最低点,让万物、让百姓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获得自由自在的生活可能,形成无拘无束、生机勃勃的生动局面、和谐景象,这正是老子所要追求的最高理想。《老子》全文,反反复复地谈论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无为”和“玄德”两大命题。所谓“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什么也不做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消极而言是说统治者要学会做“减法”,中止、减少胡为妄为导致的损失,从而提高统治者的威望和人民的信心;积极而言是说不伤害万物和百姓的“自然”,从而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万物和百姓之利益,让万物和百姓都获得蓬勃的生机;极端而言,这种追求甚至到了“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天地无亲”的绝情境地。由这种“无为”所体现出来的品性,就是“玄德”。“玄德”在《老子》中多次出现,甚至在惜墨如金的五千言中也多次出现,那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37。道和圣人虽然生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却不居功自傲,统领万物却不加以宰制,使万物得以自然而然地成就自我。在人间,通过圣人“玄德”的作用,百姓自身的意志、动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能够放开手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觉自愿、自发自动地建功立业,并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却不认为自己的成功和圣人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5]41(17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5]40(17章)。老子心目中的圣人,不是那种劳心焦神、鞠躬尽瘁,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将百姓引上某条“正路”的人,而只是一个辅助者、一个引导者、一个保姆而已。最好的统治者,下面的人仅仅知道他的存在;差一级的统治者,下面的人亲近他、歌颂他;再差一级的统治者,下面的人怕他;更差一级的统治者,下面的人蔑视他。也就是说,越往下,统治者对百姓的控制力越强,但效果越差。
《老子》整本书都在围绕“无为”和“玄德”做文章,而“无为”和“玄德”的精神实质正是谦逊。例如,老子讲“守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5]74。(28章)希望世人不要一味示强,因为雄强代表更早更快地走向极点。通过“雌”所代表的柔和、让步、宽容、慈爱来慑服人心。所以61章将大国比作“天下之牝”,希望大国在天下扮演女性的角色。
老子讲“处下”。66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5]170。老子以“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为比喻,指出要想统治人民,必须首先在语言上对人民表示谦恭,同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人民后面,让人民不感到重压、不感到妨害,这样人民才会推戴你。就国际关系而言,老子希望大国和小国都能够以谦逊示人,但大国尤其要表示谦恭,这就是61章说的“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5]159-160①。这段话的意思是大国要像江河那样居于下流,居于天下交集、归附之处,在天下中扮演女性的角色。雌性之所以能制服雄性,就因为她们是安静的、谦下的。所以如果大国对小国表示谦下姿态,就可取得小国归附。小国对大国表示谦下姿态,就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和宽容。有时是大国谦下使小国归附,有时是小国谦下使大国宽容。其中,大国尤其应该注意谦下。
老子讲“自卑”。越是地位高的人越是要降尊纡贵,忍辱负重,经得起委屈,经得起卑辱,所以78章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5]18839章说:“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5]106君王自称“孤”“寡”“不穀”,正是以贱为本的体现②。4章和56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5]10、148,就是希望统治者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低调做事、谨慎做人。13章的“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5]29则指出,只有能够做到谦卑者,才有可能看淡一切,宠辱不惊。
老子讲“不争”。《老子》书中多次使用“不争”这个词语,例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5]20意为最高的善如水一般,善于帮助万物,却不与万物争胜。“天之道,不争而善胜。”[5]182天之道不争胜却善于取胜。“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5]192这是说天道利人而不害人,圣人之道,虽有所为,但谦卑不争。老子“三宝”的实质也是“不争”,“三宝”就是“慈”,即宽容、爱护;“俭”,即吝惜、节约;“不敢为天下先”[5]170,即谦下和不争。因为慈爱,故能勇敢。因为节俭,故能广大。因为谦下不争,故能成为天下领袖。相反,舍弃慈爱而求勇敢,舍弃节俭而求广大,舍弃退让而求争先,这是死路一条。“不争”的极致,乃是“报怨以德”[5]164。因为,“报怨以德”虽然包含着难以忍受的委屈和让步,但比起怨怨相报,仍然是明智的选择。
老子讲“虚无”,“虚”和“无”归根结底也和谦逊之道相联。老子用山谷、大海、风箱、乐管乃至生殖器官来形容“道”的作用,因为这些存在都具有空虚、不盈的特征。首先,“有”是以“无”为前提的,是因为“无”空虚、不盈,具备无限的、神妙的、创造性的功能,才有可能主动地、谦虚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代表了未来和希望。而“有”则代表的是有限、既定、既成、现实、规范、堵塞、窒息,所以老子希望人类永远处在“虚无”的境界。其次,从认识的角度看,“虚无”是一种包容、接受的心态,竭力不要让对象失去本然,从而更好地让对象呈现自身。在具体政治情境中,则表现为“因循”和“自然”的理论。这种理论在《管子》四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其经典表述就是《管子·心术上》“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6]164。其经典表述可举《庄子·应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7]307,《淮南子·原道训》“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8]48。
总之,老子在五千言中,通过“无为”和“玄德”,通过将“无为”和“玄德”体现出来“守雌”“处下”“自卑”“虚无”“不争”等行为方式,反复强调了在道家世界观的道物关系、圣人百姓关系中,主宰一方克制、让步的重要性,而这种克制、让步的精神完全可以用谦逊来形容。所以,这是一种整体性视野下被全面表述的谦逊观,而不是偶尔、零碎提及。《庄子·天下》在描述关尹、老聃时作了这样的描述:“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7]1093“濡弱谦下”是其表征,而“空虚不毁万物”则为其理想和目标。《庄子·天下》所选取的老聃的语录、所总结的精神也全部与谦逊相关:“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7]1095可以说,庄子将老聃“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的谦逊精神视作“至极”的境界。《老子》全篇虽然不着一个“谦”字,但后世的诠释却往往从“谦”字入手。例如,河上公本《老子》就多用“谦”来命名各章,称22章为“益谦”,称61章为“谦德”,解释4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为“道常谦虚不盈满”[9]14。再如唐代成玄英的《道德经义疏》大量使用“谦逊”“谦柔”“谦顺”“谦虚”“谦和”等“谦”字句来概括《老子》的思想。
二、平等性视野下的谦逊
道家认为,虽然万物千姿百态、千差万别,但在作为终极根源、终极依据的道面前,万物都来自“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而也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孰高孰低、孰贵孰贱。所以《老子》27章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5]71-72
与绝对的、无限的、无待的“道”不同,万物一定是相对的、有限的、有待的、“不该不遍”(《庄子·天下》)的。如《老子》2章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5]6万物的世界由美与丑、善与恶、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上与下、强与弱、阴与阳、刚与柔、男与女等无穷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因素所构成。人虽然是万物之精灵,但归根结底属于万物之列,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到“物”所持有之性质的局限。在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从事各种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时,不可能不受特定时空、特定位置的限制,秉持特定的立场、形成特定的好恶。因此,必然造成自以为是、相互排斥的狭隘视野。这种局限,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概括,即“以己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以己为中心”表现为人类习惯以高低、好坏、优劣来品评他人和事物,时刻以主观的标准为他人和事物打分,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体现出自以为是的心理。“以人为中心”则表现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万物,认为万物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是不值得尊重的。
对于人的这种局限,庄子的认识最为清醒,他在《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7]115③同时在《秋水》中,他以夸张的口气描述了人的渺小与局限有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礨空之在大泽”“稊米之在大仓”“豪末之在于马体”:
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7]563-564
所以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渺小和局限;第二件事是不把人所做出的种种判断当作唯一的、绝对的判断,并强加到其他人或其他物身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7]577(《秋水》),站在道的立场上,世间万物本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应该一视同仁。但是“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7]577(《秋水》),站在万物的立场上,就会自以为是,坐井观天,以自我判断为中心,把事物差异的相对性当作绝对性看待,或者因为人认知能力以及语言的局限,而无限夸大或不断造就事物差异的相对性。
在《齐物论》中,庄子竭力要打破的就是人类“以己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意识。例如以下这段话: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7]74
池田知久认为,如果把这段话的顺序倒过来,从后向前推,可以说正是庄子的三大批判,第一批判的对象是与“小成”“荣华”相伴随的、以“爱”为代表的感情判断,这是最下一级的判断。在指出感情判断的局限性之后,庄子展开了第二批判,其对象是儒墨围绕“是非”展开的价值判断。第三批判的对象则主要是惠施等名家围绕“彼是”所进行的事实判断④。无论是感情判断、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因为都是基于人的“知”和“言”完成的,因此必然是有限的、不可靠的甚至是可笑的。
在《齐物论》中庄子还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7]93这是警告人类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强加到万物之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正处”“正味”“正色”。在他者面前、在万物面前,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与渺小,以平等的姿态,对他者对万物表示出足够的理解与尊重,这种姿态不正是谦逊的精神吗?
《齐物论》反复提到“以明”,如“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7]75。“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7]63“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7]66这个“以明”,我们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以道观之”的宏大视野,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他者、对万物表示出足够理解与尊重的谦逊姿态、方法、智慧。
正因为道无限宏大、万物无限渺小,所以道家对于万物命运的不确定性、无常性、偶然性也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列子·力命》说“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故曰:窈然无际,天道自会;漠然无分,天道自运。天地不能犯,圣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11]203。对于自然的造化,人类只能以“默之成之,平之宁之,将之迎之”的平静、谦和的心态加以应对。道家认为,世事如幻如梦,这既是事物自身变化的多样性所致,也是因为人类主观精神活动的丰富性所致。对于世事的无常,与其费力地加以琢磨、加以把握,不如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物化”洪流之中,《庄子·齐物论》在否定了“以己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狭隘意识以及种种恶果之后,叙述了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7]112
《庄子·齐物论》在最后出现“梦为蝴蝶”的故事,一定是有用意的,庄子在冷酷无情地揭示了人的渺小和局限之后,人类不免悲观,要想跳出悲观,“物化”不失为一条豁达的途径。所谓“物化”,正是主动放弃寻求人与万物之间的差别,从而以最为平等、最为谦逊的姿态打破物我的差别,寻求与万物之间的齐同。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对自己的塑造,正体现出万物平等、谦卑无争、看淡一切的精神。那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7]1098-1099,“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7]1099。这不正是排除了“以己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谦逊姿态吗?
三、关联性视野下的谦逊
老子40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5]109-110又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5]64(25章)道家以为,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发展之中,然而其运动和发展有规律可循,那就是“反”与“复”。同时事物运动和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单独的运动,必然表现为与其他事物尤其是与之相反事物之间的往来与互动。
中国古人早就认为,事物由正反两个方面构成,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转化,卑小总会走向高大、柔弱总会走向雄强、生命总会走向死亡,反过来,就是新的一次轮回和转化。因此,如何在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使自己处于合理的、最佳的位置,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方面的理性思维极为发达,《周易》的思维、兵家的思维以及史官的思维就是典型代表,道家全面地继承了这种思维,并发展出更为系统、深刻的认识。例如老子说,“物壮则老”[5]79(30章)、“强梁者不得其死”[5]118(42章)、“勇于敢则杀”[5]181(73章)、“坚强者死之徒”[5]185(76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5]185(76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5]122(44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152(58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5]152(58章)等。
同样是辩证思维,与《周易》同时注重刚柔阴阳,甚至更重阳刚不同,道家更注重阴柔的一面,因而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反向思维,老子就是反向思维的大师。在“有无”“正反”的两极互动中,老子重视“无”,更重视“反”。凡人只看到、只知道正面的价值取向,不知道反面的价值取向。老子则积极利用物极必反的原理,将反向的视野和思路发挥到极致。这反面的论述在《老子》中比比皆是。
例如“知足”。44章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5]122,这是说只有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才能保有他的满足。相反,“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5]125(46章),不知足就会放纵贪欲,不知足就会无所顾忌,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作为史官的老子,在这方面的感受远比一般人更为深切。
例如“退身”。这是依据盛极必反的原理,通过对事物发展必然规律的预测,而对走上顶点的人做出的忠告。“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5]21(9章),该放弃就要放弃,该舍得就要舍得,金玉满堂,没有谁能守住。富贵骄横,将自取其祸。功成而不居,这才符合天的法则。
例如“贵柔”。这正是老子赞赏女性、赞赏婴儿、赞赏水的原因。老子在自然界中发现水“处众人之所恶”[5]20(8章),发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5]185-186(76章),柔弱者反而最为刚强,最为长久,最有活力,是最后的胜者。所以他希望人能像水、像女性、像婴儿那样柔弱、卑下,甘于寂寞、屈辱,处在新生的、弱小的、生动的一面,这样就能尽可能地远离死亡、腐朽,摆脱外在污染,保持生命活力。
有人把老子及道家理解为一种阴谋之术,的确“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5]89(36章)等言论,看上去像一种实战计谋,即主动地预见矛盾发展的方向,做矛盾的主人,而不是矛盾的奴隶,被动地等待矛盾发展的结果。但我们相信老子的初衷绝不在于激发人类的智谋,让人类热衷于竞争与杀伐。这类话未必是老子的发明,应该是借用民间的智慧,目的是为了阐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这才是老子的重点所在。所以他会强调“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5]55-5(622章)的道理,即委曲者反能保全,弯曲者反能正直,卑下者反能盈满,凋敝者反能新生,少取者反能多得,贪多者反会迷惑;“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5]117(42章),事物有时贬低它反得到抬高,有时抬高它反遭到贬低;当事物的运行轨迹即将到达发展的顶点时,老子告诉你需要努力延缓发展的速度,设法改变发展的方向,以避免极限的降临;当事物的运行轨迹已经到达发展的顶点时,老子告诉你甚至需要不惜牺牲利益或尊严,以避免衰退的开始。或者从一开始就留出让步的空间,保持伸展的余地。
老子还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5]112(41章)。高尚的“德”,好像低下的川谷;最洁净的“白”,好像有污垢;最广大的“德”,好像有不足;最刚健的“德”,好像很软弱。“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5]122-123(45章),最完善的东西仿佛有缺损,但其作用不衰。最充盈的东西仿佛有空虚,但其作用无穷。最笔直的东西仿佛有弯曲,最精巧的东西仿佛很笨拙,最会辩论的人仿佛没有口才。“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5]78(30章)善用兵者只要达到目标就罢手,不以兵力逞强。成功而不自高自大,成功而不夸耀,成功似乎是出于不得已。“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5]152-153(58章),圣人方正有角但不割伤人,锋利但不刺伤人,直率但不放肆,明亮但不耀眼。“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5]192(81章),要想得到,首先必须付出,圣人没有保留,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世上没有永恒的完美,百分之百的完美,其实并不完美,因为它只是一个即将消失的顶点,预示着衰退的开始,相反,接近完美却不达致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动态的、可以把握的完美。这一类的论述,都是在事物关系中,讨论人最佳的存身之道,最合理的处世方式,这种方式无不指向普通人所追求、所向往的反面。这里没有用一个“谦”字,可哪一个不是指向谦逊呢?老子没有正面告诉人类谦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谦逊,可是他所有的论述无不围绕谦逊展开。后代的道家也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宗旨。例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作者指出,高明的统治者善于在矛盾的关系中把握平衡、建立平衡,但这个平衡有时并非绝对的平衡,而是看似向一方倾斜的非平衡。例如《黄帝四经·十六经》的《雌雄节》希望统治者能够远离“雄节”(或称“逆节”“凶节”),保持“雌节”(或称“女节”“柔节”“吉节”)。陈鼓应指出:“举凡守愚持拙、光而不耀、进退有节、不敢为先、不自大骄人、谦卑逊下、静而不争等等,均属雌节的范畴;相反,则为雄节。”[12]333
《十六经·顺道》也说:“大庭〔氏〕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宛湿(燮)恭俭,卑约生柔。常后而不〈先〉。”[12]390“刑于女节,所生乃柔。□□□正德,好德不争。立于不敢,行于不能。战示不敢,明埶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若此者其民劳不〔僈〕,饥不怠,死不怨。不旷其众,不为兵主,不为乱首,不为怨媒。不阴谋,不擅断疑,不谋削人之野,不谋劫人之宇。慎案其众,以随天地之从。不擅作事,以待逆节所穷。”[12]393-396这一段话涉及为人处世、政治军事外交的所有方面,而中心只有一个,就是在刚柔、进退、强弱、攻守、动静、盈缩中,柔、退、弱、守、静、缩的一方更为有利,因为代表的是生长、创造、平和、稳定、谦虚、谨慎的一方,而刚、进、强、攻、动、盈的一方则代表着危险、骄傲、自满、贪婪、冒进,依据事物必然走向其反面的规律,处于“雄节”的一方必然提前灭亡,但是事实上“凡人好用雄节”。所以,对于一个高明的统治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调节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处于“雌节”这一永远不败之地。《黄帝四经》明确地将此行为方式称为“顺道”,认为谦下不争,持守柔节,正是天之道的表现。
《雌雄节》称黄帝是最能够把握“雌节”之人,“皇后屯历吉凶之常,以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向”[12]332。即黄帝能够洞察吉凶,辨明雌节与雄节两种姿势,分清祸福产生的原因所在。“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夫雄节而数得,是谓积殃。凶忧重至,几于死亡。雌节而数亡,是谓积德。慎戒毋废,大禄将极。”[12]332意思是处于雄节者,即便暂时有所得,最终也无善报;处于雌节者,即便有所损失,最后也会得到报赏。这正是谦逊之道在黄老道家政治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
四、小结
总之,“谦”是道家在生活中对“道”的具体理解和运用。道家最为重视的生长、创造、活力、稳定、平和可以说都是“谦”的产物。我们认为,与中国古代其他各家相比,道家关于谦逊的认识要更为宏大、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因为这种认识是基于整体性、平等性、关联性的视野展开的,不是零碎的、偶然的思考,而是其整个思维体系的重要一环或者说重要结晶。道家谦逊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舍己以物为法”,就主体而言,要克制、忍让、宽容、虚心,对客体而言,要欣赏、尊重、不干预、不强制。通过主体的虚无、空灵、不盈、超越,非既定、非常识、非现实、非规范,带来客体的开放、多元、自由、通畅。通过主体对于谦逊之道的积极运用,从而使自己永远处于最佳的状态,保持最强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这是道家可以贡献给全人类的、历久而弥新的智慧。
注释:
①“则取大国”,当从马王堆帛书本和北大汉简本作“则取于大国”。
②《淮南子》《列子》等道家类的书籍记载了孙叔敖三上三下的故事,孙叔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8]870的表态,正体现着“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精神;其次,“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的处世风格,和低调做事、谨慎做人、看淡一切、宠辱不惊的老子教诲完全一致。
③《列子·周穆王》说:“变化之极,徐疾之间,可尽模哉。”[11]94是同样强烈的感叹。
④池田先生认为,《齐物论》这里事实上还存在针对自身之“万物齐同”展开的第四批判,这项批判完成之后,才能到达最终的“一之无”,并最终确立“道”[10]172-173。
[1]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屈守元笺疏.韩诗外传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96.
[5]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郭庆藩.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8]何宁.淮南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M].王启发,曹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11]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