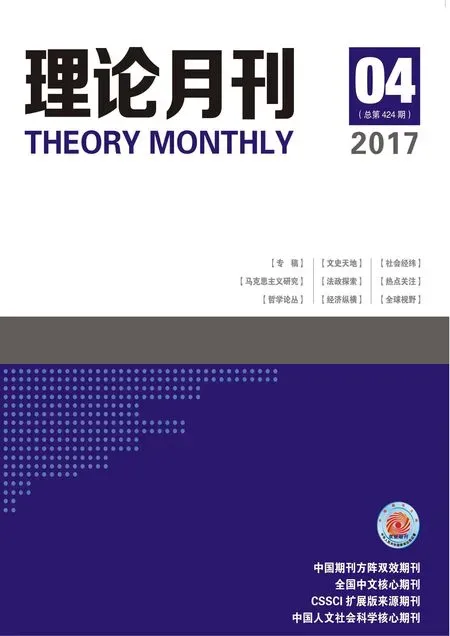论我国被告人对质诘问权的实现障碍及创设路径
2017-03-07□陈岚,郭航
□陈 岚 ,郭 航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我国被告人对质诘问权的实现障碍及创设路径
□陈 岚 ,郭 航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对质诘问权是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它的确立以发现真实为目的,是被告人辩护权的体现。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被告人的这一权利,与其成熟立法及实践经验相比,我国在制度上尚未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在实践中以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在立法上未赋予被告人对质诘问权。针对我国之制度障碍及立法疏漏,宜在立法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规定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最终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质诘问权,帮助法官发现案件真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对质诘问权;证人出庭作证;传闻证据规则;直接言词原则;证言笔录
对质与诘问是人类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形成的古老方法,对质是对事实有争议的双方面对面地相互质问和对证,诘问则是争议双方就争议之事实先后对证人进行询问。对质与诘问是厘清争议事实的有效措施,其目的无外乎发掘事实真相、划分双方责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若证人所陈述之案件事实在控辩双方之间存在争议,而被告人又无法与证人当面质证,则法官可能会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存疑,难以形成心证。即使这一证人证言被法官采纳为定案的依据,其效力也无法使被告人信服,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由此可知,赋予被告人行使对质诘问之权利,不仅是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有效方法,而且是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实质保障。
考察我国关于被告人对质诘问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仅于第五十九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作为对《刑事诉讼法》的补充,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讯问同案审理的被告人,应当分别进行。必要时,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等到庭对质”。同时期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三十八条第四款规定:“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然而,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仅涉及了对质诘问的行为(confrontation action),却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诘问权(confrontation right),也难以使法官判断案件的事实真相。考察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可知,对质诘问之形式在刑事案件庭审中虽存在,但更多体现为检察机关之控诉权力,而非被告人之辩护权利。
为何需确立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是学界探讨较多的话题,多数学者基于控辩平衡的基础理论,认为被告人之辩护权须以对质诘问权加以保障。笔者拟从对质诘问权的基础理论展开,以我国的制度障碍为分析对象,阐述对质诘问权之确立对发现真实之必要性,并结合域外关于对质诘问权的理论基础及立法实践,提出在我国规定被告人对质诘问权的立法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对质诘问权之突破。
1 对质诘问权之界定
对质诘问权,是指在刑事诉讼庭审程序中由被告人享有的在法庭上与被害人、证人及其他同案被告人等面对面对质和诘问的权利。确立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既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的质证方法,又是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实质保障。从对质诘问的基本涵义和法律定位出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其予以界定。
1.1 被告人辩护权之体现
被告人基于宪法和法律规定拥有辩护的权利,对质及诘问则是辩护权的体现,赋予被告人行使对质诘问之权利,是对被告人辩护权利的重要保障。与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器相比,刑事诉讼程序的被告人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利地位,而证人证言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尤为重要。证人证言依其作用分为两种:一是由辩方申请而向法庭陈述对被告人有利证言之证人,此种情形下,被告人一般无需与之对质诘问;二是由控方申请而向法庭陈述对被告人不利证言之证人,对此类证人,被告人或出于对案件事实之异议,或基于人之天性,会要求与之当面对质。被告人与证人在法庭中对质诘问之目的归根到底是辩护的需要,即为自己争取最大的辩护利益,对质诘问之权利也符合有效辩护原则的要求,因此对质诘问权是辩护权的体现。
1.2 以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及侦查人员为对象
传统意义上,对质诘问权的对象范围一般被界定为出庭作证之证人、被害人及其他同案被告人。笔者认为,按照所证明事实之不同为标准,对质诘问权之对象宜分为两类,一类是证明案件实体事实之对象,如证人、被害人及其他同案被告人;另一类为证明案件程序事实之对象,如侦查人员。在证明案件实体事实时,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均属于知悉案件事实真相的人。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对案件之走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证人也有如实作证的义务。从证据学之角度,被告人在法庭上行使对质诘问权,直接与证人、被害人及同案被告人就陈述中的争议事实对质并予追问,则对案件实体事实之发现更为有利。
证明案件程序事实的对象则以侦查人员为主。德国法学家罗科信认为,由于对事实真相之调查并非刑事诉讼之绝对价值,若对侦查行为不设任何限制,则可能隐藏破坏社会秩序及个人利益之隐患。故而刑事案件立案之后,侦查机关应当依法进行侦查活动,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材料。侦查程序获取的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资格是刑事案件庭审质证所审查的重点。如果被告人于庭审时对公诉方所提交证据材料 (特别是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作自白或供述)之合法性存在异议,提出该证据系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取,并提供相关线索以申请法院对公诉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时,法官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就证据材料之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公诉方则需要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为使证据符合严格证明之要件,则需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法官的询问,并与曾经的犯罪嫌疑人,即庭审中的被告人对质,即可检验有争议之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
由此可知,基于发现真实之要求,对质诘问权的对象应为出庭之被告人、被害人、证人及侦查人员,方可在对质中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定性,从而帮助法官对于事实真相之判断。
1.3 以面对面质问为形式
被告人与证人就案件中的争议事实于法庭中进行面对面 (face to face)地质问是实现对质诘问权的主要形式。所谓“面对面之权利”,具有双重内涵:(1)被告有在审判中在场并目视证人的权利(Right of seeing the witness face to face);(2)被告有使证人目视自己的权利①Mattox v.U.S.,156 U.S.237(1895),Coy v.Iowa,487 U.S.1012(1988)。。面对面地对质基于证人的到庭义务和陈述证言义务,是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环节,也是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的有效方法。一般认为,就发现真实而言,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质及诘问为法官询问证人所不可替代。一则被告人作为刑罚之可能承受者,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对案件事实的记忆最为深刻,且最能发现证人陈述所存在之瑕疵,最有能力提出适当的问题,使证人在说谎的情况下无法自圆其说,帮助事实真相的发现。一则在法庭中处于面对面地质证情境下,说谎将会面临被戳穿并被科以责任的严重后果,基于这种心理压力,任何一方均会避免在法庭上说谎。即使证人说谎,也会更加容易被发现破绽和矛盾。因此,通过被告人与证人在法庭上面对面地质证,可以使法官对双方之言语表达、神情动作和所陈述事实进行观察,进而判断证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是否符合证人资格,证言之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
1.4 以发现事实真相为目的
证人证言在法庭上提交并予以质证,就是为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发现事实真相,从而公正地行使国家刑罚权。以对质诘问作为证人证言的质证方法,符合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最好形式。首先,对质诘问权之行使以证人出庭作证为前提,当证人出庭对质时,可在最大程度上排除合理怀疑,尽量逼近案件的事实真相,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形成心证。其次,当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时,对质诘问权之行使可排除被告人自己在庭外因非法行为而被迫所作之有罪供述,是确认证据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有力武器。
概言之,对质诘问权是实现被告人辩护权的重要途径,行使对质诘问权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之有效手段。被告人可以尽其所能,在面对不利证言时有效行使辩护权,避免陷入冤假错案的漩涡。故而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是司法文明的重要一环,应在我国立法中予以确立。
2 对质诘问权之域外实践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均确立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从理论上来看,英美法系国家确立对质诘问权基于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国家确立对质诘问权则基于直接言词原则。虽然其理论渊源不一,但在保障被告人对质权方面殊途同归。
2.1 英美法系国家对质诘问权之述评
受传闻证据规则的影响,英美法系国家较早地确立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传闻证据规则与对质诘问权之间有着深层次的联系①英国自17世纪起便已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同样继受了传闻证据规则,日本也受美国的影响确立了这一制度,樊崇义:《传闻证据的基本问题及其在我国的适用》〔J〕,《证据科学》,2008(16).。刑事诉讼中的传闻证据是指证人在法庭外未经宣誓作出的陈述内容,在庭审时被当作证据提出以证明其所称之事实为真实。由于传闻证据本质上是证人对其所听说的事实的重述,这种证据不能通过交叉询问的方式验证其真实性,所以为确保提供给法庭证词之可靠性,除非有例外规定,否则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应予排除[1]。在对抗式的庭审模式下,当事人在主导程序的过程中需将所有证据提交到法庭并经过控辩双方质证,未经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判决的实质性依据。因此,被告人的对质权在传闻证据规则下得到了保障。
在传闻证据规则的影响之下,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的刑事指控中,被告人都有权利与对他不利的证人对质。这一规定从宪法层面保障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也体现出传闻证据规则是对抗制的必然要求。200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克劳福德案推翻了之前适用的罗伯茨规则,坚决排除庭外之传闻证据,确认了对质诘问权的宪法规定不可侵犯②Craw ford v.Washington,541 U.S.36(2004)。。
受美国法律影响深厚的日本同样在传闻证据规则的指导下确立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旨在保障证据的可信性和当事人的反询问权,《日本国宪法》规定,应当给予刑事被告人询问所有证人的充分机会[2]。其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切证人提出质证的机会,并且拥有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利。”这就在宪法层面确立了刑事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考察日本《刑事诉讼法》,其三百二十条规定:“除三百二十一条至三百二十八条规定的例外情形外,不得在公审期日以书面材料代替陈述或者将以他人在公审日以外的陈述为内容的陈述作为证据。”[3]由此可知,诸如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的证言笔录、办案情况说明等书面形式之传闻证据,原则上在日本不得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至一百五十三条详细规定了证人的到庭义务,不到庭的证人将会被处以罚款、罚金,也可以对证人拘传;第一百六十条和一百六十一条则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没有理由而拒绝作证的证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义务之后,第三百零四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询问证人的权利,从而在法律上较为完善地保障了对质诘问权的实施[4]。
英美法系国家根据传闻证据法则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不仅将被告人的对质权上升到宪法性权利之高度,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将之细化规定,给被告人与证人之对质开拓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较早地确立了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
2.2 大陆法系国家对质诘问权之述评
在大陆法系的立法实践中,直接言词原则体现为被告人对质诘问权的行使。直接言词原则分为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庭在开庭审判时,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到庭出席审判,法官必须亲自直接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直接接触证据和审查证据,只有经过法官以直接采证方式所获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言词审理原则要求法庭的审判活动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同时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如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任何未经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5]。
在此原则主导之下,刑事诉讼的证据未经法官当庭接触和控辩双方的质证和盘问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也得以确立根基。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2)规定:在侦查程序中准许与其他证人、被指控人相互对质。第二百五十条(2)规定,原则上禁止使用此前讯问时所作的记录或者其他书面声明代替对证人的讯问[6]。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对质只能在已接受过询问或讯问的人员之间进行,并且以他们对重要的事实和情节说法不同为前提条件。”[7]我国台湾地区虽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但又汲取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诸多优点,其《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了直接言词原则,还详细规定了对质和诘问两种程序。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Ⅱ)规定:“因发现真实之必要,得命证人与他证人或被告对质,亦得依被告之声请,命与证人对质。”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得诘问证人、鉴定人。诘问属于被告的权利,除有不当外,不得限制或禁止。 ”[8]
基于直接言词原则之要求,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并通过言词形式进行调查,由此使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得以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配套实现。所以,直接言词原则为对质诘问权的孕育提供了健康的养分。
不难发现,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这一范畴均已有了成熟的立法程序和广泛的司法实践。这也表明,对质诘问权并非只能适应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其已经超越了法系之间的隔阂,成为司法文明的一项代表性制度,域外关于对质诘问权的规定对我国确立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3 我国对质诘问权的实现障碍
分析被告人对质诘问权之基本特征,可知其是帮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有力途径。被告人对质诘问权之实现,不仅有赖于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规定,而且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密切相关。然而,反观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关于被告人权利和证人出庭作证之规定,不仅没有被告人对质诘问权的实现空间,甚至互相之间存在矛盾,不利于法官发现真实。
3.1 对质诘问权之制度障碍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迟迟未予建立,以证言笔录代替证人质证成为对质诘问权的制度障碍,不利于法官厘清案件之事实真相。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之要求,更是对质诘问权行使之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分析以上条款,辩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条件,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条件,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则表明法院有着最终的裁量权,相较于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这一条款本身已限缩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但纵观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在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要求如此苛刻的情形下,诸多学者给出的调研数据都表明,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一直是非常突出的问题[9]。与研究数据相呼应的是,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多名资深检察官及律师均称在自己承办或代理的刑事案件中没有出现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刑事案件中辩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之情况并不多见,证人证言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一定重要,因此法院才会认为证人无必要出庭。二是我国的公民社会尚未发育完成,存在厌讼的思想传统,民众避讳涉入诉讼,消极回避出庭作证。三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在更多情况下依赖于证人证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证言笔录。
前两原因无须赘言,笔者认为第三个原因是构成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被束之高阁的主要原因。证言笔录,又称为“询问笔录”,一般是指证人在接受侦查人员、公诉人的询问后就案件事实所作证言的书面记录。证言笔录不仅记载了证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而且记载了侦查人员、公诉人询问过程和结果的记录[10]。证言笔录在法庭之外由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记录后提交至法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了调查核实物证、书证的程序:“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以上条款明确规定证言笔录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补充形式。这一条款表明,我国并无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言笔录可以合法替代证人出庭质证。如果说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一种进步,那么这一法律条文则使进步之意义显得无足轻重。
从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是否必须出庭作证之规定前后矛盾,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属于证据种类之一,证人证言应当是证人出庭作证时的口头陈述,而非在庭外作出陈述的记录,证人证言也必须藉由证人经过控辩双方质证并查实。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从立法上肯定了证言笔录“作为证据的文书”,可代替证人证言进行质证。但证言笔录既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规定形式,也无法实现证人证言的功能,如何能够代替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呢?显然,以上法律规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被束之高阁。
从证据理论上看,证言笔录既不符合证人证言的理论内涵,也不符合物证书证的形式要求。证言笔录不是证人在法庭上向法官所作出的陈述,而是依据其在法庭外陈述证言所作出之笔录。在证据学意义上,证人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陈述本身属于原始的证据方法,而记载证人陈述的证言笔录,属于由证人陈述派生而出的衍生品[11]。作为衍生品的证言笔录并非证据本身,它只能对证据作出转换形式的记录,因此而不属于任何证据种类,更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予以质证。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具不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以规避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便无法与证人面对面地对质,更不能对一份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回答的笔录进行诘问。当被告人对这份笔录存在异议时,只能与出具证人笔录的公诉人进行质证,也就是俗称的“质纸证”。但公诉人并非证人,其对案件的事实真相之了解显然只是基于证人的转述,公诉人仅能依据该证言笔录进行发言,被告人无法就争议事实发掘更多细节。
概而言之,既然法律规定了证人证言应予质证,就应当存在控辩双方的对质情形或者至少存在被告人对证人证言就争议事实的诘问,证人与辩方在庭上之对质诘问的过程即可帮助法官查清案件事实真相。然而证人的角色一旦由证言笔录所替代,则法庭上仅有公诉人宣读证言笔录,辩方无法就证言笔录内容之瑕疵或矛盾争议之处进行质证,这种“质纸证”的形式严重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架空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导致法庭上的质证流于形式,更无从论及发现真实。
3.2 对质诘问权之立法疏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证人证言需经被告人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框架性原则,但进一步讨论,被告人应如何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对证人和证言的质证是否有所区别,如何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在质证中查实,我国刑诉法对这些关键问题均无意细化。
如前文所述,刑事诉讼程序之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均属知悉案件事实真相的人。为使法官对争议事实产生清晰的判断,则需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于法官面前各自陈述其所知晓的事实并就争议部分对质,方可使法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定性,从而辅助其对事实真相之判断。若作出有争议证言之证人不出庭作证,或证人虽出庭但不被允许由被告人与其对质,则不利于发现真实。为解决这一难题,2013年1月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必要时,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等到庭对质。同时期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第四百三十八条第四款规定: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但分析以上两处涉及被告人对质情形的司法解释条款,不难发现以下几点疏漏: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仅规定了被告人被动而有限的对质行为,不利于法官发现真实。该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讯问被告人时,认为有必要可传唤同案被告人到庭与之对质。称之为“被动”,是因为对质行为由法院传唤同案被告人而发起,只有在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可以开始对质,如果被告人对证言有异议,则无权要求证人或其他被告人出庭对质。称之为“有限”,是因为对质的主体与对象仅限于同案审理之被告人,而不包括同样了解甚至亲历案件事实真相的被害人或者其他证人,被告人仅能与同案被告人对质,却无法与对自己作出不利证言的被害人或证人进行对质。在非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存在同案被告人,则唯一被告人更无法获得对质之机会。在未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质证的情形下,法院如何借助有争议的证人证言查明案件之事实,是司法实践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虽然以上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利用对质的机会使法院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然而由于立法的实际疏漏,使对质的适用情形及对象过于狭窄,对证据质证之作用微乎其微,难以帮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真相。
其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之目的在于检控犯罪,而非帮助法官发现事实真相。最高检《司法解释》规定对质的主体与对象为被告人及证人,规定了公诉人在被告人与证人就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时的对质建议权,相较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将对质诘问行为仅限定于同案被告人确实有所扩大。但考察其内涵,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其实并没有赋予被告人对质诘问的权利(right),而是赋予了检察官对质的权力(power),证人出庭的情形也仅是帮助检察官与被告人对质,其目的仍然在于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12]。在2014年4月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中,刘汉与另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的当庭对质即可显示出对质行为的这一特点。财新网转发的《新华社刊发刘汉案庭审纪实》①引自财新网,2014年5月23日报道,笔者在提取这一报道时有针对性地提取了与本文相关的材料。[EB/OL].http://www. caixin.com/2014-05-23/100681598.htm l(2016-10-10)。一文中这样描述:
在刘汉案中,公诉人当庭宣读孙某某证言,指证刘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害王永成犯罪。在4月3日的庭审中,刘汉在法庭中突然提出:“我强烈要求法庭让孙某某出庭,与我当面对质,很多事情就清楚了。”
公诉人认为,如果孙某某本人能出庭,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4月12日,孙某某出庭作证。刘汉在法庭上向孙某某发问:“我跟你说叫你去教育他,还是我跟你说叫他们去教育他?”
孙某某回答:“你说叫我去把他做掉。”
随后,公诉人明确指出:“这足以证实,刘汉已经承认孙某某向他汇报过王永成准备炸汉龙,而且对孙某某作了明确指示。”
从该案的庭审纪实中可看出,虽然被告人刘汉无权提出对质,但是公诉人基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考量,认为有必要对质而发起了证人与被告人的对质程序。在对质过程中,证人孙某某回答刘汉的问题后,公诉人更越俎代庖,自行宣布此对质行为证明了刘汉的犯罪事实。由此不难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质行为由公诉人提起,为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服务,是公诉人对质权力的体现,而非被告人的对质权利。
对质诘问权之基本内涵要求在保障被告人之合法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被告人与证人之对质与诘问活动,厘清案件事实,帮助法官发现事实真相。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均未规定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司法实践中为数不多的对质行为也与对质诘问权的真正内涵和其追求之目的背道而驰,故而我国现行法律中证人证言之质证形式不利于实现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
4 我国被告人对质诘问权的立法建议
如前文所言,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没有遵守直接言词原则,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上摇摆不定,以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导致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缺乏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实践中存在的少数被告人与证人的对质诘问行为,既非被告人之权利体现,又非为发掘事实真相而设,其等同于公诉机关控诉被告人犯罪的工具。参考世界上典型法治国家及地区之立法经验,一般就对质诘问权之设立存在两个层面:一则在国家宪法层面赋予被告人对质诘问权,将该权利上升至宪法权利以保护被告人权利不受侵犯。二则从刑事诉讼法层面细化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规定在何种情形下被告人得行使对质诘问权。对照我国国情,如何确立符合中国法治要求的对质诘问权?笔者认为,我国被告人对质诘问权之设立,不可能仅是一纸法律条文,更应建立在对证人作证制度的科学规定和执行上,否则对质诘问权即是空中楼阁,无法从实质上保障被告人应得的权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入手,以立法保障。
4.1 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考察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并非没有参照直接言词原则,而是在部分法律条文依据直接言词原则设立以后,又在另一部分法律条文中打开一个缺口,使之无法严格实施。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需要打破立法层面的桎梏,引入直接言词原则之相关概念,根据我国司法实践的特点对其予以界定,指导司法实践去适应和遵守。我国宜在立法中严格限制书面证言,明确诸如证言笔录、情况说明一类的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迫使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司法机关重视办案程序的合法性要求,采取合法手段获取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4.2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公诉方在需要的时候会提出证人或者同案被告人出庭与被告人进行对质,以证明被诉者之犯罪事实。究其原因,是公诉机关享有对质诘问之权力,而被告人只得履行对质的被动义务,虽然这种现象颠倒了对质诘问之根本内涵,但却从侧面印证了我国设立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并不存在难度和障碍。一方面,既然公诉机关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与被告人对质,那么被告人也应该有与之平等的权利,否则会处于诉讼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无论从刘汉案还是薄熙来案中,均可发现控方申请的证人出庭与被告人对质的情形,说明此项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完全可行,只要公权力机关严格要求,证人出庭并非真正的难题。
因此,我国宜在直接言词原则之要求下完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我国已经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不履行义务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但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基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造成了证人出庭率极低、证言笔录大行其道的异化现象。首先,在证人自身方面,我国可以仿照德国及日本的立法实践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予以明确化、实质化,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否则将对其科以罚款、罚金或其他更严重的处罚。其次,在证据认定方面,宜规定非例外情形,则证人必须出庭且经控辩双方质证后才可将证言作为定案的依据。再次,要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合法权利。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宜规定控诉机关、审判机关及其他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得干涉、阻碍证人出庭作证,不得对出庭作证的证人以暴力手段进行威胁或恐吓,全面落实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制度。
4.3 规定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
首先,对质诘问权的顺利行使有赖于庭前程序的有效准备,因此我国宜规定被告人在庭前会议中有权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笔者建议,在庭前会议中被告人、辩护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根据公诉方所提交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作证内容,针对争议事实和程序问题,自行决定是否申请证人或侦查人员出庭接受对质。在此基础上,被告人将有效行使对质诘问权,提高诉讼效率,发现案件真实。
其次,我国宜将对质诘问权作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按照直接言词原则之要求,凡提供证言的证人、案件的被害人、同案被告人及侦查人员等,非法定许可事项,则必须就自己所知晓的案件事实或程序事实出庭作证。被告人提出对证人证言有争议时,非法定排除事项,法庭应允许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或侦查人员当庭面对面地对质,并由控辩双方依次诘问。被告人就案件之实体事实或程序事实向证人、被害人或侦查人员等对象发问对质时不受他人干扰或禁止。如果证人、被害人或侦查人员等拒绝出庭、拒绝就争议事实回答被告人提问或故意回避问题,则争议事实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法庭侵犯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则属于程序性违法事项,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27条,应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对质诘问权是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这一权利之设立,有助于完善被告人之辩护权,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帮助法官发现事实真相,使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法治诉求。
[1]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缩影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31.
[2]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等.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54.
[3]日本刑事诉讼法[M].宋英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3.
[4]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张凌,于秀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78-281.
[5]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
[6]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等.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0.
[7]龙宗智.论刑事对质制度及其完善[J].法学,2008(5).
[8]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92.
[9]房保国主编.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39.
[10]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1.
[1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10.
[12]易延友.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责任编辑 赵继棠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4.018
D916
A
1004-0544(2017)04-0112-07
陈岚(1962—),男,湖北蕲春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航(1988—),男,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