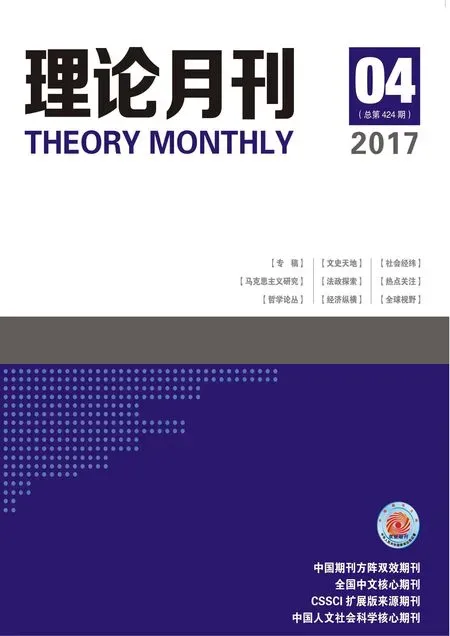“联邦”的创制与转义
2017-03-07□刘耀
□刘 耀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联邦”的创制与转义
□刘 耀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联邦”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政治术语,但它并非汉语中原有的词汇,而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制而来。“联邦”一词最早出现是用于对译英文中的united states,但随着国人对世界认识的加深,“联邦”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开始被用于对译英文federal一词,并最终固定下来。以“联邦”一词为例,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互动的模式,即西人创制、国人定义,但是国人在定义的过程中不得不以西人创制的新词为基础,这也正反映了中国近代思维的困境所在。
联邦;合省;合众;近代术语
“联邦”这一概念仅仅在近代中国传播了百年,而随着清末中央集权的削弱,联邦制在很长的时间内被国人广泛讨论,但是人们很少去关注“联邦”这一政治术语,它是何时在中国出现的,又是以怎样的形态传播开来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近代术语的生成,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有着大量的新词涌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时间既短,而学者们精力有限,所以未能将研究细化到每一个新词,对它们作深入的探究,“联邦”一词也正是如此。因此,本文拟对“联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作词源学上的检讨,并借此来探讨“联邦”一词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中西文化互动。
1 “联邦”的古今演绎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法家、道家都秉持着各自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央集权的政治设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一直影响到后世。自秦汉大一统之后,虽然也曾有过分封制的反复、晚唐的藩镇割据、明清的土司制度,但是这些体制只是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一种方式,其目标并非建立一种“联合王国”。而在中国古汉语中,也没有出现过“联邦”这样的概念。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国人开始接触到介绍联邦国家的材料,联邦的概念也开始生成,并出现转化。今天,“联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被定义为:
联邦,亦称“联盟国家”。由若干成员单位(邦、州、共和国等)组成的同一国家。现代复合制国家的一种主要形式。国际法中的主体。有联邦的宪法、法律、立法机关和政府。联邦同成员单位间的权限划分由联邦宪法规定。各成员单位也都有自己的宪法、法律、立法机关和政府。各成员单位的公民同时又是联邦的公民。联邦最高立法机关通常有一个院以成员单位平等选派代表为原则组成。 如美国、瑞士等[1]5165。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中的“联邦”指的是一种国家政治形式,既然“联邦”一词是利用既有汉字的新生词汇,那它又是怎样创制出来的呢?
“联邦”由“联”与“邦”组合而成,为联合结构词,这种复合词是汉语新词的主要模式,梁启超先生也认为汉语不仅仅可给旧字以新义或创立新字来创造新词,而且还可用字来构成新的复合词。[2]122但是以“联邦”为例,从汉字的古义出发,“联邦”一词应该指的是一种国与国的联合,而与它现在的含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今天人们对“联邦”一词的定义虽与中国古汉语的含义不合,却与西方对“联邦”的定义颇为接近。在西方,学者们对“联邦”的精确定义有着许多学术争论,但人们还是设置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定义,即:
一种区域政治组织形式。它通过其存在和权威都各自受到宪法保障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而将统一性和地区多样性同等纳入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制之中。这种组织形式的独有特色是权力至少在两级政府中进行分配,统一性和地区多样性并存不悖[3]254。
由此可见,“联邦”一词的含义乃是从西方语义中发展而来的,而非从中国古代汉语中生发出来的,那“联邦”一词又是怎么在汉语中出现的呢?
2 “联邦”的出现
“联邦”作为一专业术语,最早出现在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861年,而“联邦”一词的出现正反映了早期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但是,裨治文笔下的“联邦”一词并非对译英语的federal一词,而是对united states的一种翻译,“联邦”的出现,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他为何会选择 “联邦”一词翻译united states呢?
在美国独立前,中国与北美就有一定的贸易往来;美国独立后,这种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但是,中美之间的交往仅限于经贸领域,中国人对美国谈不上任何文化习俗的认识[4]5。在中文书籍里,最早记录美国历史的是谢清高的《海录》一书,其中以百余字记述“芊里干国”,但这记载很不全面[5]761。与之相较,马礼逊所撰《外国史略》可能是第一本较为完整的叙述美国史的中文著作。在书中,马礼逊简要地描述了美国的地理状况及其建国历史,并将united states音译为“育奈士迭国”[6]930-931,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正是以此为开端的。
1833年,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该刊至1838年在新加坡停刊,共经5年。该刊的主要内容涵括了历史、传记、地理、自然史、医学、工艺及应用科学、自然科学与文学等诸方面,其中不乏对美国情况的记载。但在《东西洋考》中,对美国国名的翻译却始终没有统一,有着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北亚墨利加兼列国、亚墨利加列省合国、北亚默利加合邦、北亚米利加合郡、亚墨理驾总郡或兼合邦、亚米利加兼摄列邦、亚默利加统邦、亚米利加兼合国、亚墨哩加兼合列邦、美理哥兼郡[7]91,其中的“兼列国”“列省合国”“合邦”“合郡”“总郡”“兼合邦”“兼摄列邦”“统邦”“兼合国”“兼合列邦”“兼郡”之名均用来翻译united states。由此可见,当时的传教士不断搜寻和创造新的汉语词汇来表述united states,但几乎每一个新词都是用之即弃,未得到广泛的认可而成为死语。这不仅是“因汉字与外国字不同,故难写外地之名”[7]93,更多的是因为既有的汉语系统中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美国的政治形态,所有united states一词才会出现如此多的译名。
如果说马礼逊与《东西洋考》的编著者们对美国的介绍是零散而不成体系的话,那么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则是第一本专门而系统地介绍美国的中文著作。在该书中,裨治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地理状况、物产以及建国历史,并对美国各邦一一作了介绍。在谈及“合省”这一概念时,裨治文作了如下解释:
合省者,因前各治其地,国不相联,政无专理,后则合其省而以一人为首领,故名之曰合省[8]。
由此可见,裨治文所谈之“合省”正是其对united states一词的中文翻译,并以中国的“省”来对译state,他的这种作法是为了让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因为在中国并没有state的概念。此时裨治文的译法可能受到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早期刊物的影响:
花旗国,其京曰瓦声顿。此国原分为十三省,而当初为英国所治。但到乾隆四十一年,其自立国设政,而不肯再服英国。……花旗国今分为南、北、中三地,而共有十八省也,日后此国谅必为亚默利加全地之最大者[9]79。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省”指代state,裨治文使用“合省”指代united states,某种程度上属于“以中译西”,即以中国原有的概念来翻译西方的词汇,这反映了西方人在介绍洋词入华时,中国固有话语的主体地位。
裨治文的 “合省”之说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国学者,梁廷枬在其《海国四书》中有关美国的材料主要来自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予奉纂《粤海关志》,分载贡市诸国。而在广东海防书局,亦曾采集海外旧闻,凡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详着于篇。独米利坚立国未久,前贤实缺纪载,案牍所存,又多系市易禁令,间有得于通事行商所口述者,亦苦纷杂,难为条绪,欲专着一篇不可得,则仍置之。两年忧居,耳不复闻夷事。有以其国人新编《合省志略》册子见示者,尽初习汉文而未悉著述体例者之所为。因合以前日书局旧所采记,稍加考订,荟萃成帙,略如《五国故事》、《吴越备史》,而详核有加焉。仍其今称,题曰《合省国说》,用广异闻而备外纪[10]51-52。
由此可见,梁廷枬接受了“合省”之说,并且认可了将美国的各个州视为“省”的看法[10]52。但是“合省”之说并不符合美国的现实,美国的联邦制下的各个邦与中国单一制下的省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之时并没有采用 “合省”一说,而是使用了united states一词的音译“育奈士迭”,或意译为兼摄邦国,并将state看作是部落:
粤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乃洲名,非国名。西洋称部落曰士迭,而弥利坚无国王,止设二十六部头目,别公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名其国育奈士迭国,译曰兼摄邦国[11]397。
由此可见,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作为最早系统介绍美国的中文书籍,但他以“合省”对译united states的作法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合省”一词努力地寻找中西方话语体系的共通点以弥合现实中中西方政治制度的鸿沟。但正因如此,它没有恰当地表达united states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差异,这种以共通性为基础的翻译削弱了united states作为他者的存在价值,“合省”这种自动化的用语不能引起中国人的足够注意。
1844年,裨治文又出版了《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一书,这本书是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基础上写成。从题目上看,《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主要是对前著的译名作了改动,以“合众国”代替了“合省国”。但是,书籍内容变化不大,基本沿袭了前著,如以 “省”对应state,书中很多地方仍然沿用了“合省国”之说:
又其次则有榆、栗、松、柏、杉、柳及养蚕之桑等,故合省国亦有绸缎。以上各种树只数省有之。至各处皆有者,则苹果、葡萄、沙梨、桃、梅等果。惟甘蔗、稻谷则只合省之南方有也[12]30。
由此可见,裨治文虽然使用了“合众”一词来对译united states,但是他在书中依然保留了“合省”之说。在梁廷枬写作《合省国说》时,他也注意到了裨治文有使用“合众国”之说:
近日,米利坚国人有以汉文自志其本国事者曰《合省国志略》,(或自称曰合众国。)其言与利玛窦大同小异,所知者止四洲[10]53。
梁廷枬的《合省国说》一书写作于1844年,当时裨治文或已采用“合众国”之说,但是二人俱对“合众”之说存有保留,因此他们才会在书中更多的保留“合省”之名。
尽管裨治文对“合众”的使用仍有保留,但是“合众”一词逐渐为西方译介者所接受,他们纷纷使用“合众”来指代美国。《遐迩贯珍》(1853-1856)用词的转变反映了这一点,在1854年第2号,《花旗国政治制度》一篇中:
英与花旗二国,本同根源宗派,其政制均如一辙,后乃背析宗邦,自立为国,所谓合郡国也,兹篇所述者,即彼国之政制并将其所以与英国区别不同之处,详言以中之,判析宗邦之初,诸郡于始不过暂为萃聚众力而起。原因宗国征税新例,不协于彼土舆情,故群兴而相抗为敌,及得逞其志后,总须联结牢固、缀合亿万众如一体,终乃建立盟约,言明结合联属之由[13]667。
由上文可知,虽然1854年《遐迩贯珍》的编著者仍然使用“合郡”对译united states,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国家体制的特点,特别指出“萃取众力”“缀合亿万众”,“合众”已经呼之欲出,该刊后期即摒弃“合郡”这一译名,而转用“合众”:
朕又曾与亚麦利驾之合众国联约,此约既立,向日繁难事件久未议决者,今则公平允决矣[13]542。
一凡有船只,不论由何外国、省、府,载有人来本省者,其人依照本省之规条,不能入合众国之民籍者,每位来客,拟收饷银伍拾圆。[13]491
由此可见,19世纪50年代中期是“合众”一词的接受时期,《遐迩贯珍》编者的态度正反映了这一点。
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人普遍接受“合众”这一译名来指代美国,这在《六合丛谈》(1857.1-1858.6)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合众与日本和议既成,乃立通商条约,以垂永久,集议于西莫大衙署,其约共计九条,节其大略如左,一、合众商舶至长崎海口,欲补损漏,则雇日本人修理,舟中所需淡水、煤炭、食用等物,则听其自行置办。二、西莫大居民,既不肯与外国商人工作,如修船、购物等事,则于其地准设副领事官一员,并许合众人赁屋居住。三、核算货价时,合众金银洋饼亦准行驶,但当权其轻重,而以日本之经营为准,凡合众者,价减百分之六,为铸洋工价之费。四、合众人犯法,则交领事官处理,依合众律定罪……[14]706
《六合丛谈》的这段文字记载的应当是1857年7月赫黎斯在下田同日本官员签定的《日美条约》,其规定了美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增开长崎港为通商口岸,美国人可以在开放港口长期居住。而《六合丛谈》的这篇报道中通篇以“合众”指美国,以“合众人”指美国人,以“合众律”指美国法律,可见“合众”开始指代美国,而“合众”这一译名已经取代了“合省”“合郡”等词,为西方译介者广泛接受,用之对译united states一词。
虽然外国传教士们摒弃了“合省”“合郡”之说,转用“合众”,但是“合众”一词只是较为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创立的国家精神,而并未概括出其具体制度特点,因此,为united states寻找更合适的译名的工作仍在继续。1856年,裨治文对其《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并将其命名为《大美联邦志略》。在此书中,裨治文开始使用“联邦”一词,这也是在汉语世界里第一次出现“联邦”这一词汇:
即位之日,新君誓云,予小子输诚昭告,而今而后,君临联邦,恪供要职,原创政典,尽守勿失。至于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陆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若君欲派使臣,及各属官员,前往别国,或本国办公,皆当与元老会商,元老以为可,始克如派[15]27。
文中所出现的“联邦”一词,均是用以表达美国这一概念,则裨治文此时是以“联邦”对译united states,他已经不再使用“合省”与“合众”这两种译名了。因此,他在书中对美国各个地区行政区划的译名,除了极少数使用“部”以外,也都由“省”改为“邦”。
《大美联邦志略》对当时的中国人接触和了解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第一批受清政府派遣去欧洲游历的中国官员斌椿就在其书中提及:
卫公来京师,赠我《联邦志》(美国使臣卫廉士,驻北京六年,前载赠予《联邦志略》,所言疆域政事甚详);才士丁玮良,著书讲文艺(美国文士丁玮良,学问甚优,以所著《地球说略》等书见惠);初如井底蛙,开编犹愦愦。书云地形方,主静明其义;岂知圆如球,昼夜如斯逝[16]181。
王韬对该书也极其推崇,他在赞赏来华西人的著作中特别强调该书:
自泰西诸儒入旅,著述彬彬后先竞美……靡不辑有成书,言之有要。而其中尤切于事实者则若慕维康之《大英国志》、裨治文之《联邦志略》,即以其国之人,言其国之事,不患其不审而实,可以供将来考索[17]308。
由此可见,《大美联邦志略》一书在当时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最重要的作品,“联邦”一词也开始深入人心。
诚如上文所言,裨治文在其《大美联邦志略》一书中,“联邦”一词所对译的英文乃是美国的国名united states,而非今天人们所讲的联邦制度federal,那么这样的意义转移又是在何时发生的?
3 united states抑或federal:“联邦”的再定义
在现代中英文翻译中,人们一般使用federal来对译“联邦”,而非united states,但在《大美联邦志略》,“联邦”对译的是united states,那么federal与united states二词在英文语境中,涵义是一致的,抑或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呢?
在英语世界中,United states最早是指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荷兰王国,但随着尼德兰的分裂与荷兰脱离法国的统治,united states在欧洲也就无法找到相对应的实体国家,然而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united states在北美找到了相对应的实体国家[18]79-80。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在使用U.S.来表示美国国名的英文缩写。而在英语世界中,federal一词的形成过程正是契约文化制度化的反映。西人编著的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一书中,对federal一词作了详细的词源检讨:Federal,本义是附属于一项立约、契约或条约;在公约神学(或盟约神学)中,特指附属于神与人之间关于拯救的约定。其第二义是指附属于一种由两个以上的state组成的政治实体,同时这些state或多或少地保有处理内部事务的独立性[18]795。 由此可见,federal这种政治形态是从西方契约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united states和federal二词在英语中有着本质的差别。时至今日,在中英文翻译中,united states已然是对译“合众国”的专有名词,而federal则主要指“联邦”制度。但在裨治文写作《大美联邦志略》之时,他却是使用“联邦”一词来对译united states,特指美国。那么,在汉语世界中,“联邦”一词由对译united states到对译federal,其词义转化是在何时开始的,而这种变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联邦”这一概念就有两种不同的应用,他既将其看作一种国家间的战略性联合:
夏、商以前不尽可考,但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晋以联邦伐他国者四十四,各联邦伐晋者十二;楚以联邦伐各国四十,各联邦伐楚者十一;齐以联邦伐人国二十一,联邦来伐者三;宋以联邦伐人国者九,联邦伐之者亦九;鲁伐他国九,他国来伐六;卫、郑伐他国者八,他国伐卫十五,伐郑十九;吴、陈伐他国八,他国伐吴、陈皆六;蔡伐他国六,他国伐蔡六;燕伐他国二,越伐他国三:几三百战。其余曹、许、莒、邾、滕、薛及一切小国,从人伐而被人灭者无岁不有,及削邑围邑者亦不计[19]71-72。
同时他又对“联邦”的现代意义有着深刻的见解:
德二十五联邦,又合为一。意以十一国合为一……而德、美以联邦立国,尤为合国之妙术,令诸弱小忘其亡灭[19]87。
合国有三体: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夫联合邦国之体有三:有各国平等联盟之体,有各联邦自行内治而大政统一于大政府之体,有削除邦国之号域,各建自立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之体。凡此三体,皆因时势之自然以为推迁,而不能一时强合者
也[19]88。
康有为的第一种理解可以说是从古汉语语境出发,结合了“联”与“邦”的古义,将其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中;而第二种解释则是完全从现代意义的角度出发,将“联邦”视为一种稳定成熟的政治制度。他的这两种对“联邦”的理解都已经与裨治文将“联邦”与美国对等的作法有了本质上的差异,但是此时的康有为仍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他一方面使用“联”与“邦”的古义,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意义上的“联邦”,此时康有为笔下的“联邦”,乃是“联邦”这一概念再定义的一个过渡阶段。
到了20世纪初期,“联邦”作为一个制度名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在汪荣宝、叶澜编纂的《新尔雅》一书中,“联邦”开始明确被定义为一种制度:
数多之国家互为约束,设立中央机关 (即中央政府),使任通共事务而诸国仍有完全之独立权者,谓之联邦国。(联邦国)中央机关之权限如下:甲、在各国联邦之合意约束范围内,则有活动之权力;乙、除合意约束外,中央政府对各国,无命令强制之权;丙、即其权力范围内之事,非经联邦各国政府之手,不得执行。其中中央机关之权力,盖甚弱也(如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后至1866年之德国联邦是)[20]302。
虽说是“联邦”,但是《新尔雅》中所讨论的“联邦”更接近于今日所说的邦联。同时,它也没有忘记讨论一下真正的联邦制度:
数多之国家,公共约束组织一中央政府,此中央政府者,有总括内政外交与命令强制诸国之权力,而诸国除中央政府允许之权力外,别无他等权力者,谓之连合国,亦谓之合众国(如美国及今日之德国是)[20]301-302。
《新尔雅》中所说的“连合国”“合众国”更接近与今天所讲的联邦制国家,因此孙中山先生才会在兴中会纲领中提出建立“合众政府”而非“联邦政府”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当时,“合众”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联邦制度,而从《大同书》和《新尔雅》中可以看出,当时“联邦”一词的解释则相对混乱。
虽然《新尔雅》一书对“联邦”的定义与今天相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它已经分清了联邦和邦联的差异,较之康有为又前进了一步,而李大钊则明确辨析了“联邦”和“邦联”两个概念。李大钊在其《平民主义》一书中就明确定义了联邦制度:
联邦就是一国有一个联合政府,具有最高的主权,统治涉及联邦境内各邦共同的利益,至于那各邦自治领域以内的事,仍归各邦自决,联合政府不去干涉[21]38。
李大钊不仅揭示了联邦制的本质,而且他还解决了康有为和汪荣宝等人的困境,他将国家间的联合定义为“邦联”,即上文中所谈及的康有为对“联邦”的第一种理解:
邦联就是各独立国为谋公共的防卫、公共的利益所结的联合,加入联合的各国,仍然保留他自己的主权。这联合的机关,全仰承各国共同商决的政策去做。古代希腊的各邦,后来瑞士的“康同”,德国的各邦,美国的各州,都曾行过[21]38。
可见,李大钊解决了康有为《大同书》中对“联邦”的两种不同解释间的矛盾以及《新尔雅》中“联邦”“合众”两个概念的差异,明确了将“联邦”来对译英文中的federal一词。
康有为、汪荣宝、李大钊等人没有被动地接受裨治文对“联邦”的定义,而是选择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联邦”对译federal一词,这正是因为中国这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部世界,对西方的制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此,他们对西方的理解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层面,而是开始了自己主动去认识和定义西方文化。对“联邦”一词的再定义正是这种转变的最佳表现。而因为“联邦”一词词义发生转移,“合众”一词再次回归,重新被用于对译united states一词。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对“联邦”一词的翻译可谓几经波折,从最早为了对译united states,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裨治文),使用了“合省”“合众”“合郡”等多种译名,直到最后选择了“联邦”一词。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国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以“联邦”对译united states过于局限,在他们看来,“联邦”一词的含义更适于表达federal这种制度,而对united states的翻译则又回归到了“合众”一词,这正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的一种互动。
4 余论
“联邦”一词的出现,反映的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但是这种互动并不是在一种平等的状态下完成的,因为文字的翻译会受到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影响[9]13,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之间的心理差距并不大,因此,裨治文才会使用“合省”来对译united states,而他使用“联邦”一词时,中西方的政治平衡已被打破,因此他才会不顾“联”与“邦”字的古义,不再附会汉语的表达习惯,创造了 “联邦”一词,用于对译united states,并且为当时的国人所接受。但正是因为传播者与受传对象的这种心理差距变大,所以才出现了康有为对“联邦”一词既使用其古义,又使用其今义的做法。
西人的翻译过程反映了他们寓西于中的努力,从初期强调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接近中国现实政治,以之定义西方政治制度,到成熟的运用汉字拼接概念,以强调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特点,伸张其自在的主体性,说明其独立价值。可见文化交往的过程同时是一个文化主体从自我辨析到自我定位、再到自我认同的过程。而“联邦”一词的生成,虽然遵循了汉语词汇生成的程式,但是在中国社会学术转型的关键性时期,由西人占据了强势话语。
国人虽然接受了“联邦”这一新词汇,但随着他们对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们将“联邦”一词泛化为联邦制度,即federal一词的中文译名。国人虽非被动地接受西方人的“规训”,而是有着自身独立思考的存在,但这种独立思考却是建立在西方人创造的新词汇的基础上,这也正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困境所在。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2]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3]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4]吴翎君.晚清中国朝野对美国的认识[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
[5]谢清高.海录[C]//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编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6]魏源.增广海国图志[M].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
[7]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裨治文著,刘路生点校.美理哥合省国志略[J].近代史研究资料,92.
[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梁廷枬.海国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1]魏源.海国图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12]张施娟.裨治文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13]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4]沈国威编.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5]裨治文.联邦志略[M].上海:墨海书局,1861年.
[16]斌椿.海国胜游草[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7]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John Simpson,?Edmund 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Blue Leather Edition Twenty-volume Set,XI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1989.
[19]康有为.大同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0]沈国威编.新尔雅:附解题·索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21]李大钊.平民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文 嵘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4.012
D033
A
1004-0544(2017)04-0080-0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7JZD0040)。
刘耀(1987-),男,江苏宜兴人,历史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