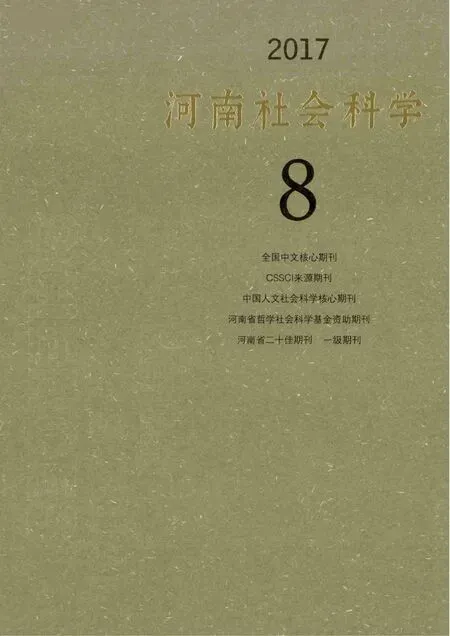论物之受侵的侵权责任
2017-03-07郭明瑞
郭明瑞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论物之受侵的侵权责任
郭明瑞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这是对财产权受侵害时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损失额计算方法的规定。这里所指的受侵害的财产权既包括有形财产的财产权,也包括无形财产的财产权,亦即既包括所有权及各种物权,也包括知识产权,甚至包括债权及其他财产权益。
由于财产的形态多样,侵权形态多样,侵害财产所发生的侵权责任也就会多样,而不仅仅为赔偿损失这一种责任。即使在适用赔偿损失责任上,对不同形态财产的损害的计算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损失与侵害网络财产的损失,在具体计算方法上就与侵害物权的损失计算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就将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与侵害财产权的民事责任分别在第一百一十八条和第一百一十七条作了规定。《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有将知识产权排除在财产权之外之嫌。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没有作此区分是有道理的。但是,应当看到,《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财产权实际上是指物权。就此而言,《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将物权与其他财产权区别也存在不足。因为物为物权的客体,作为有形财产或有体物,其受侵害时的损失的计算与作为无形财产或无体物的其他财产受侵害时的损失计算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侵权责任法》就财产侵害的赔偿责任仅作此一条规定,又显得过于简单。由于“财产权益是民事权益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以及虚拟经济中的财产权利”①,而对各种财产权益侵害的后果又有不同,有必要分别予以规定。侵害他人物权是侵害他人财产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包括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动产等财产进行毁损,致使该财产的外在形式、内在质量遭受破坏,甚至完全丧失,直接影响其价值和使用价值②。从《民法通则》的规定看,侵害他人之物并不一定都发生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另外,侵害物虽然为侵害物权的行为,但侵害物权的行为未必就定会侵害物。例如,妨害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属于侵害物权的行为,依《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妨害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的侵权责任。而妨害所有权行使的侵权行为并未侵害所有权之客体的物。如此看来,侵害物的责任与侵害物权的责任也是有区别的。
由此可见,值民法典编纂之际,在修订《侵权责任法》时很有必要完善财产侵害的责任规则。这项任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应是对侵害物的侵权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对物的侵害,从侵害后果上看有三种形态:一是侵占,二是损坏,三是毁灭。相应地,也就会发生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三种侵权责任。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简述,以求方家指正和立法者修法时参考。
二、侵占物的侵权责任
侵占物为侵占财产的行为,是指非法地占有他人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侵占财产以对他人所有的财产的非法占有为特点③,因此,侵占物的行为直接侵害的是权利人对物的占有权能。当然,因为所有权包含占有权能,所以侵害对物的占有权能也是对所有权的侵害。但因为不仅所有权人享有占有权能,其他非所有权人合法占有物的,其占有也受法律保护。侵害非所有权人占有的,也应为对物的侵占,合法占有人也就有权请求侵占人承担侵占物的侵权责任。侵占物属于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但这里的财产权不能仅限于所有权或物权,也包括其他权利。例如,甲将其物交付乙保管,乙对该保管物的占有是有合法根据的,此时丙从乙处将甲的物抢夺走,不仅甲可请求丙承担侵占其物的侵权责任,乙也可请求丙承担侵占财产的侵权责任。
侵占财产最典型的表现形态是“位移”,即由所有权人或者合法占有人占有、支配的特定的财产物,转而被行为人所占有,物的所在位置发生了变化④。因此,侵占的构成是以无法律根据地占有他人之物为要件的,而不论占有人的占有是否有过错。这里的占有仅指对物予以实际控制,而致使权利人不能控制,不论占有人是否有为自己利益而占有的意思。侵占占有的行为人应承担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不法占有的物返还给合法占有人,这也就是承担返还原物的侵权责任。返还原物当然以不法占有人对原物的占有为条件。如果原物已不存在,不论是物已毁灭还是已被第三人取得,物的侵占人都不再承担返还原物的侵权责任,而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如果在物之不能返还或者在对物的占有上侵占人并无过错,则其也会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返还原物也就是返还财产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都规定了返还财产是民事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因此,侵占物的,应当依法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权利人在物被他人非法侵占时,有权请求侵占人返还财产。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是否会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呢?对此学者中曾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主张返还财产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而应适用取得时效的,笔者就持此种观点;有学者主张返还财产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的;也有学者主张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应区别对待,区分登记的物权和不登记的物权,基于不登记的物权产生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⑥。《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依该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该规定进行反面解释,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依《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权利人请求返还未登记的动产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也就是说,自权利人知道其物被他人非法占有及占有人之日起,3年内未行使返还请求权的,侵占人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对抗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保护。
值得讨论的是,这里的动产物权中的登记是指何种登记?是所有权登记抑或也包括其他权利即抵押权登记呢?这是需要解释的。从《物权法》的规定看,动产登记包括两种:一是特殊动产的所有权登记。依《物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的所有权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侵占这类已进行所有权登记的特殊动产,登记的真正权利人要求占有人返还的请求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这应无疑问。那么,非登记的真正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呢?这值得讨论。例如,甲将其机动车转让给乙,乙已交付车款,甲也将车交给乙使用,但双方未办理车辆登记过户,该车仍登记在甲的名下。后该车被他人开走,事后乙得知该车被丙开走,因碍于情面,乙没有向丙索要。3年后乙要求丙返还车辆,丙提出乙的返还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因乙不是该登记的权利人,因此,乙的返还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甲虽为登记的权利人但其非真正的权利人,也不是占有人,不享有返还请求权。但是,若此时乙将该车的权利转让给甲,甲请求丙返还该车的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呢?如乙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转让的,按本条文字面解释,则不适用诉讼时效。为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立法应对此种关系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动产抵押权的登记。依《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里的动产抵押,不仅包括有所有权登记制度的特殊动产抵押,也包括无所有权登记制度的动产抵押,如生产设备、产品、原材料等的抵押。假设某人以这类无所有权登记制度的动产设立了抵押权且办理了登记,而该抵押物又被他人侵占,所有权人请求侵占者返还财产时,侵占人以诉讼时效届满对抗的,所有权人可否以该动产为登记的物权之物而主张不适用诉讼时效呢?从诉讼时效的规定看,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不适用诉讼时效。这里登记物权的权利人是抵押权人而非所有权人。因此,只有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人请求返还抵押物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抵押权人只有于抵押权实现时才得以行使该项请求权。
因占有是对物加以使用的前提,侵害使用人对物的占有的,当然也会使权利人无法行使其使用权能,即使用权能受到侵害,但使用权能的受侵害并非侵占的直接后果。因此,对于物的侵占,其救济的方式就是恢复物的占有;而对使用权因受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则只能通过赔偿损失解决,其损失额依使用权受侵害的损失计算方法确定。可见,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是可以也会与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并用的。
三、损坏物的侵权责任
损坏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损坏有的称为损毁,“损坏财产是以对他人所有的财产进行毁损为特点,使该财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受到破坏,使原所有权人的财产拥有量减少,以致丧失”⑦。这种广义上的损坏包括物的毁灭和损坏。狭义的损坏不包括物的毁灭,是指将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予以破坏,使“其外在形态被破坏、变形或者内在质量降低,影响原有的使用功能,降低了原有的使用价值”⑧。笔者这里使用的是狭义损坏物的概念。损坏物,使物不能与受侵害前一样得到使用,损害了物的使用价值,因而侵权人承担的应是使物恢复其原有的使用功能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方式就是《民法总则》和《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恢复原状。《物权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中只有恢复原状,而无修理、重作、更换。那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恢复原状的责任是否包括修理、重作、更换呢?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指出,恢复原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害前的原有状态,而狭义的恢复原状仅指将受到损害的财产修复⑨。这种广义的恢复原状是他国法上规定的损害赔偿的一种方法,所谓“损害赔偿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即指此义。但笔者认为,我国法上的恢复原状的含义与他国法上的恢复原状之含义不同,仅指狭义的恢复原状。有学者认为,恢复原状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指通过修理、重作、更换等方式对受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进行救济⑩。从《物权法》的规定看,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方式中,恢复原状和修理、重作、更换是不同的责任方式,而《侵权责任法》中也没有将修理、重作、更换规定为侵权的责任方式。因此,笔者认为,《物权法》的规定有必要修正。修理、重作、更换是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而不是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侵权责任中的恢复原状仅指将损坏的物修复,以恢复其原有的使用价值。
由于恢复原状须侵权人以自己的财力为之,即其付出自己的财产承担其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因而,一般情况下,损坏物的恢复原状的责任成立,须侵权人有过错。只有在法律规定的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下,才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即只要损坏他人之物,侵权人就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例如,高空作业的塔吊倒塌砸坏他人的房屋,不论作业者有无过错,均应承担将该房屋修复的恢复原状的侵权责任。
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以被损坏的物有修复的可能和必要为条件。如被损坏的物已无修复的可能,则自不能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在此情形下,侵权人的行为已不是损坏物,而是毁灭物,而使物毁灭的,侵权人只能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在被损坏的物可以被修复,但是或因修复费用过高,从经济上看不合算;或因修复对于物之权利人已无意义,其不要求修复的,物的损坏视为毁灭,侵权人也只能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在物之损坏被视为毁灭的情形下,折价赔偿是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恢复原状的责任和赔偿损失是否可以并用呢?有观点认为二者不能并用,只有在依该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就该重大损失赔偿的,才可并用。笔者认为,能否并用取决于如何理解重大损失。依笔者所见,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是可以并用的。如果侵害人损坏物,该物可以修复,则侵权人应当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尽管物之修复可恢复物的使用价值,但受害人仍会因物之损坏导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损失。例如,损坏房屋的,因修复期间房屋不能居住受害人另租他屋居住的租金损失,被损坏的车辆修理期间因不能营运而发生的营业收入损失等,此类损失即为因物之损坏而导致的使用价值损失。因受损的物即使修复,权利人将该物转让时其价格也会低于未受损时的价格。此种价格降低的损失即为交换价值受损的损失。可见,在物之损坏的场合,无论是造成权利人使用利益损失,还是造成权利人交换利益损失,权利人都应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的责任,不仅可以并用,并且是常常需要并用的。
四、毁灭物的侵权责任
在物之毁损不能恢复原状或不必恢复原状时,物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完全丧失,属于物之毁灭或灭失。此时,侵权人只能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赔偿损失是否包括实物赔偿呢?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赔偿损失不包括实物赔偿,实物赔偿属于恢复原状;有观点认为,实物赔偿也是赔偿损失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这与对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的含义理解不同有关,但在实务上没有多大实质意义。笔者主张,实物赔偿也是一种赔偿方式,赔偿损失主要是指金钱赔偿。
赔偿损失的基本规则就是完全赔偿。所谓完全赔偿,也就是对受害人因物之被侵害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予以全部赔偿。因此,损失如何计算,也就成为是否坚持完全赔偿原则的关键。
《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法计算。之所以以财产损失发生的时间点计算赔偿价格,是因为一个侵权案件审判终结需要一段时日,如果对于价格标准不作确定,则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混乱⑪。有学者指出,以该条规定的“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作为基本计算方法,并不特别准确,其实应当按照确定判决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更为准确⑫。这一观点值得赞同。仅以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损失,在市场价格下降时对受害人不会有影响。但在市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从受侵害至案件审判终结之期间受害人的损失应由自己承担吗?而这一损失确也是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依市场价格确定,强调的是损失的确定应依客观标准,而不依主观标准。既不能以受害人感受的损失为标准,也不能以侵害人的主观过错为标准。受害人的损失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但实际损失并不是指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即实际可得利益的损失。如前述的交易价格降低的损失、车辆的运营收入损失等,即属于可得利益的损失。在确定实际损失上,为保障损失确定的准确,还须贯彻与有过失规则和损益相抵规则。
与有过失,是指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者扩大也存在过错的,要减轻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⑬。这里所说的贯彻与有过失规则,要求受害人对于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应当将因受害人的过失而导致的损失部分从受害人的损失额中扣除,亦即侵权人对这部分损失不予赔偿。这实际上仍是贯彻“责任自负”原则。因为受害人的损失既然与其过错有关,其就应自行承担部分损失。一般来说,在侵权人侵害物致该物损毁上,受害人是不存在过错的。在侵权人故意侵害时,即使物的权利人在物的保管、放置等方面有不妥,也不能认为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因此,在物之毁损的赔偿中,难有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但是,笔者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特别是侵害人并非故意而受害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也应有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例如,某人将其车辆停放在明令禁止停放的位置,因他人之物坠落而将该车损坏。在此情形下,受害人即车主应当承担部分损失。此外,两车相撞造成车辆受损,也会发生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
损益相抵,又称损益同销,是指受害人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因而获得利益时,应当将该利益从赔偿额中抵销,加害人仅对抵销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⑭。损益相抵规则实际上要求侵权人仅对自己造成的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与有过失规则在物之侵害的赔偿中少有适用,损益相抵规则在物之侵害的赔偿中却多有适用。例如房屋被毁,若房屋的材料为权利人所得,则其所受的房屋被毁的损失应从房屋的价值中扣除权利人因此所得到的材料的价值。
在物之毁损的赔偿损失责任上,尚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在确定侵权人赔偿损失的范围上是否限于可预见损失,二是人格物之损害是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物之毁损的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但是在损失的范围如何确定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属于应赔偿的损失;另一种观点主张,不能因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负担,《侵权责任法》不仅是权利保护法,同时也是合理划定人们行为自由界限的法律,如果对侵权人要求过多,则会影响其行为自由,有违利益平衡的原则,可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⑮。有学者根据现实中出现的天价葡萄等案件,认为对财产损害赔偿应当适用预期利益损失规则。如果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亦不公平;如果适用预期利益损失原则,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较为妥当⑯。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侵权责任不同于违约责任,在违约责任中,对于损失的计算应适用可预见规则,这也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侵权责任的赔偿损失中对于财产损失一般不能适用预期利益损失规则,因为这不存在双方事先的利益安排。当然,从保护行为自由和人们的财产权益的平衡上,只有在行为人非故意造成物的损毁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根据行为人的过错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行为人是否应当赔偿和行为人是否赔得起是两回事。
人格物,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物,不同于一般的动产或不动产。人格物的价值是没有或者难有市场价格的,因此,侵害人格物的侵权责任应与侵害一般物的侵权责任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侵占人格物的情形下,只要该人格物还存在,就应适用返还原物的责任方式。对于人格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人格物的返还请求权也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其二,在损毁人格物的情形下,不能以市场价格或者以估价方式来确定赔偿的损失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肯定了对于毁损人格物的,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侵权责任法》中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分别规定侵害财产的赔偿和侵害人身权益的赔偿,第二十二条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人格物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不是财产利益,因此损毁人格物是对他人人身权益的侵害,而非财产权益的侵害。因此对于人格物损毁的赔偿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但是,由于毁损人格物,也不是对所有人的财产造成损失,因此,也不能适用第二十条的规定⑰。笔者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侵害人格物的赔偿,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在修订《侵权责任法》时,应对侵害人格物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当然,哪些物可归入人格物,哪些物不能归入人格物,需要根据司法实践和人们的认知情况确定。
注释:
①②⑪⑮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6、96、97、98页。
③④⑦⑫⑯⑰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42、142、144、145、157页。
⑤但返还财产的含义较返还原物更广。返还原物仅指将有体财产归还给权利人,而返还财产还包括返还权利凭证,返还身份证件、驾驶证等。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7页。
⑥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3页。
⑧⑬⑭魏振赢:《民法》(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684、688、688页。
⑨⑩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9、640页。
2017-05-20
郭明瑞,男,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烟台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